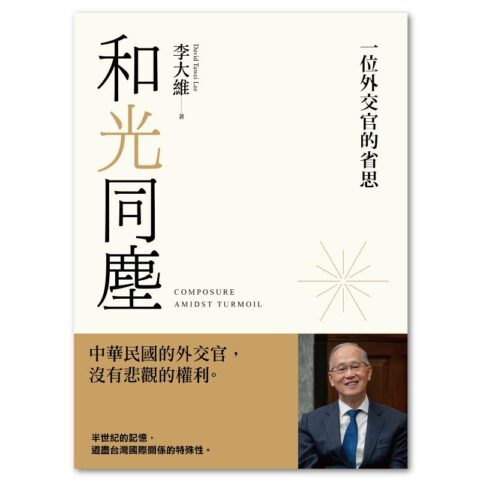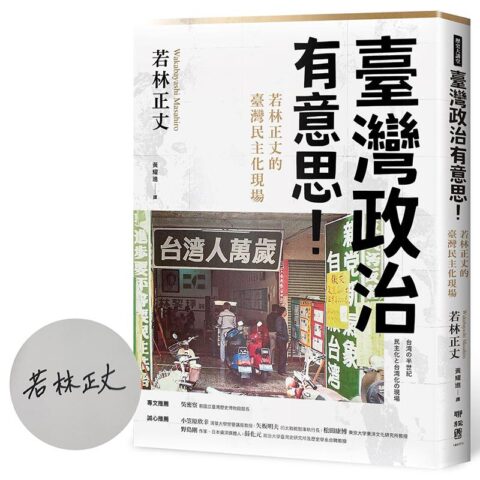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
出版日期:2023-01-19
作者:林毓生
裝訂:精裝
EAN:9789570865745
系列:林毓生作品集
尚有庫存
自由、多元的社會,是個人在社會中享有自由。
自由最主要的基石是法治,
自由的社會是最有秩序、最能利用知識與最尊重人的尊嚴的社會,
也是最有生機、最少浪費與最有組織的社會。
要建立這樣的一個社會,首要之務是建立一套法治的制度。
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口號,在中國已有百年的歷史。這些源自西方歷史文化的觀念,對中文世界裡的許多人而言,至今仍是相當生疏。《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所收各篇論文,直接或間接討論建立自由、民主、法治與理性的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的種種,希望把「五四」的啟蒙工作往前更推進一步。
作者:林毓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等。
自序
一
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
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
近代中西文化接觸之史的涵義:以〈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為例——為紀念張君勱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二
政教合一與政教分離
法治要義
法治與道德
使命感、歷史意識與思想混淆
再論使命感——兼答墨子刻教授
清流與濁流
三
台灣究竟是不是一個多元社會?——簡答楊國樞教授
什麼是多元社會?——再答楊國樞教授
四
處理政治事務的兩項新觀念——兼論為什麼建立法治是當前的第一要務?
五
紀念「五四」六十五週年
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漫談胡適思想及其他——兼論胡著〈易卜生主義〉的含混性
魯迅思想的特質
魯迅政治觀的困境——兼論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活力與限制
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
胡適與梁漱溟關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論辯及其歷史涵義
知識分子與中國前途
新儒家在中國推展民主的理論面臨的困境
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簡答王元化先生
附錄:論傳統與反傳統——從海外學者對「五四」的評論說起 王元化
什麼是「創造性轉化」?
意識形態的沒落與台灣的前途
《中國意識的危機》日文版序言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節要)
自序
這部《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主要是收輯了我最近六年來陸續用中文撰寫的不同類型的文字,以及與幾位青年朋友合譯的原用英文發表的論文。
因為全書各文直接或間接討論到建立法治、自由、民主與理性的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的種種,當一位朋友建議採用現在的書名的時候,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見。
本書各文的撰寫,主要是希望把「五四」的啟蒙工作往前推進一步,今年適逢「五四」七十週年,我以誠敬之心以本書的刊行來紀念這個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日,並盼讀者惠予指正。
本書之編輯與校訂,多承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先生、林載爵先生與方清河先生的鼓勵與幫助,衷心至為感謝。各文撰寫的過程甚為艱苦,如無內子宋祖錦女士的支持與協助,是無法進行的,我在這裡向她敬致謝忱。
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
引言
這篇文字源自我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台北(提前)舉行的「殷海光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學術座談會」的談話紀錄。當時因為時間的限制,只能大概地談個梗概,後來看到一篇以同情的立場所作的簡單報導,但內容卻有許多錯誤;我才更確切地體會到,在中文世界裡,如要討論一些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一定得作較為詳盡的說明。
自由、民主與法治作為口號來講,在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由於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方向與西方的歷史、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方向甚為不同,所以,與西方歷史、文化背景關聯深切的自由、民主與法治的觀念,到今天對中文世界裡的許多人而言,仍是相當生疏的。基於這項認識,我原先只想就黃柏棋君的紀錄稍稍訂正盡速發表的計劃,必須放棄;我不得不將那份紀錄作大幅度的修訂與擴充。
不過,本文受了文章體裁的束縛,所能論及的自然仍是相當有限(詳切的論析,要靠大部頭的著作才能辦到)。基本上,我藉論析中國自由主義先驅人物胡適先生與殷海光先生在談論容忍與自由時所呈現的歷史的意義與思想的局限性來說明: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一向認為道德與思想是政治秩序的基礎。這種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以法治為政治秩序的基礎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進一步地說,雖然儒家文化所主張的政治秩序乃由道德與思想構成的觀念,是中國知識分子使命感所由生的精神與思想資源之一;但,這種觀念,如被僵化地或基教式地(fundamen-talistically)堅持著,反而會成為建立法治的阻礙。在這個脈絡中,我試圖說明西方自由主義所肯定的容忍、多元與法治的觀念在思想上相當複雜的意義,與在歷史上相當曲折的演化軌跡。我並藉西方純正自由主義所持之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說明了為什麼法治是建立自由與民主的必要基礎。
本文是從論析胡適先生與殷海光先生關於容忍與自由的言論出發的。在五○年代底,胡先生有關容忍與自由的討論與殷先生讀後的回應,是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我覺得在「殷海光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學術座談會」上提出來討論,有其紀念的意義。然而,更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國主張自由民主的人,過去都多多少少受過胡先生或殷先生,或他們兩位共同的影響;因此,我如從論析他們的言論出發,這樣容易使我的論析比較能夠具體一點、切實一點。胡殷兩先生在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上,均有歷史性的貢獻;不過,他們的思想也呈現了歷史性的局限。今後如果我們不關心自由與民主在中國的前途則已,如果我們要想在中國促使理性、法治、自由與民主往前推進一步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突破胡殷兩先生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性的局限。我想這是合乎他們所肯定的,根據自由精神來討論大家關心的問題的方法與態度。
本文最後特別呼籲,發揮社會力量來建立法治,並以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近幾年可喜的發展為例,說明社會力量可由民間以類似該基金會的組織方式加以凝眾,以便促進法治的建立。這種辦法是遲緩的。但,在中國—除非發生歷史的奇蹟——法治的建立的確是要走一大段長遠的路,才能達到的;而這遲緩的工作卻是扎根的工作。台灣黨外當然也可能對自由與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但,他們必須先設法謀求內部的共識與團結;否則,力量在內爭中相互抵銷,客觀上也就難有成績可言。宗派主義(sectarianism)往往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抗議分子在稍有權力之後,難免的歷史現象。今後黨外如何突破這個歷史的局限,則是他們當前的重大課題。
至於為什麼在中國建立法治,竟是如此艱難呢?這當然是一個極為繁複的問題,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各方面的原因。單從思想史的觀點出發,其根本原因涉及到中國沒有政教分離的傳統,以及「天人合一」、「盡心、知性、知天」所蘊含的「內在超越」的觀念,究竟其意義何在?其社會含意(social implications)是什麼?
「天道」是超越的、無限的,此點儒家並非不知。故《中庸》云:「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天」並非指對超越的天道完全掌握或控制。但,儒家宇宙論所蘊含的人與「天道」銜接與溝通的方式,則與西方基督教傳統中「外在超越」的觀念下人與超越的上帝銜接與溝通的方式,迥然相異。儒家「內在超越」的觀念,使人與宇宙有機地融和在一起——人性內涵永恆與超越的「天道」,「天道」因此可在「盡性」中由「心」契悟與體會。儒者認為「超越」與「無限」內涵於人性之中;因此,由「盡性」可體現天道,故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易言之,「內在超越」的觀念導致了人與「天道」銜接與溝通的特殊方式:不假外求,直接訴諸生命中「人性」的實踐。「道心」不是由「啟示」得來,它是從「盡性」與「踐仁」的實際生命過程中由「人心」內省、體會與契悟而得。一個深受此種宇宙論潛移默化、影響至深的人,自然感到生命本身有無限的精神資源與充沛的道德意義,他在實際生活中所表現的風格,自有其莊嚴。即使遭遇橫逆,他卻對人生之痛苦能作悲憫式的沉思。他對生命有著誠敬的執著;這種對生命能夠把持得住的境界,是建立在他覺得生命本身是無限的意義之源的信念之上。而這種信念之肯定是源自「人」與「宇宙」並未疏離,「人」與「宇宙的實在」有機地融和為一之故。
從追尋、發掘人生的意義的觀點來看,儒家傳統所提供的思想資源,我個人覺得是有極為重大的正面意義的。(至於儒家傳統的架構,在二十世紀崩潰以後所出現的種種扭曲的現象,則是另一問題。我在別處曾多所論述,此處不贅。)儒家對生命的肯定,絕不是用「意志」強加可得者。相反地,西方自尼采宣稱「上帝已死」至沙特一派的存在主義之所以認為生命之意義只能由「意志」強加肯定,正是因為他們認為「生命是荒謬的」緣故。
然而,從希望建立法治的觀點來看,儒家「內在超越」的宇宙觀,卻提供不出很多的資源來。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傳統中,超越的實體,既然是超越的,人們如欲與之接觸的話,就只能依靠與超越實體有特殊關係的媒介(agent 或 agency)——如先知,或先知傳統及啟示傳統下建立的教會——提供的橋樑進行之。這種與超越實體所產生的特殊關係,被認為是超越實體所賦予的,不是在時空中有限的人的自身力量或由人為的努力可得者。換句話說,由於人的有限性,不假外求是無法與超越的實體接觸的。基督新教喀爾文教派,在更嚴格地服膺「外在超越」的邏輯意義之下,則認為無限的、超越的上帝不是各方面均屬有限的人所可知的。
從西方「外在超越」的觀點來看,儒家「內在超越」的觀點是令人費解的。(問題在於:人如何不假超越的實體所賦予的媒介,就可與「超越」銜接與溝通?)當然,從中國「內在超越」的觀點來看,西方「外在超越」的觀點,也是令人費解的。
在純理念的層次上,儒家「內在超越」的觀念只說人與天道合融,人可契悟天道;然而,天道自有其超越人的一面,既非人所創造,也不是人可完全控制或掌握。但,在「內在超越」的宇宙論籠罩之下,儒家傳統中並沒有強大的思想資源阻止儒者強調人的內在力量幾至無限的地步,也沒有強大的思想資源使「政教分離」的觀念在中國產生。(有了這個觀念,才能在思想的層次上,避免政客們利用宗教與道德的形象與語言去追逐與濫用權力。西方「外在超越」的觀念則易使人落入另一危機:以為人的內在毫無力量,人的一切皆為外在的勢力所控制。)易言之,「內在超越」的觀念中,雖然在純理論的層次上有「內在」與「超越」之間的緊張性(tension),但「內在超越」的觀念確有滑落至特別強調一切來自「內在」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儒家傳統中直接導致把道德與思想當作人間各種秩序的泉源與基礎的看法,以及遇到了困難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便以「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對付之。此種頗含烏托邦質素,強調人的內在力量的思想,自然使中國人不易建立類似西方的法治觀念;「法治」強調法律高於一切——這是與西方「外在超越」的宇宙觀及「上帝是立法者」的觀念分不開的。處於到處都在強調人的內在力量的思想文化之中,自然在中國也不易形成一套完整的社會理論來說明:為什麼在法治之下,自由是組織與發揮社會力量的基本原理。雖然,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展示了一些有關自由的社會功能的了解;但,這種思潮,因無法治傳統的支持,所以一直沒有得到適當的發展。(另外,為統治者服務的法家思想與這裡所謂的法治思想是有基本衝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