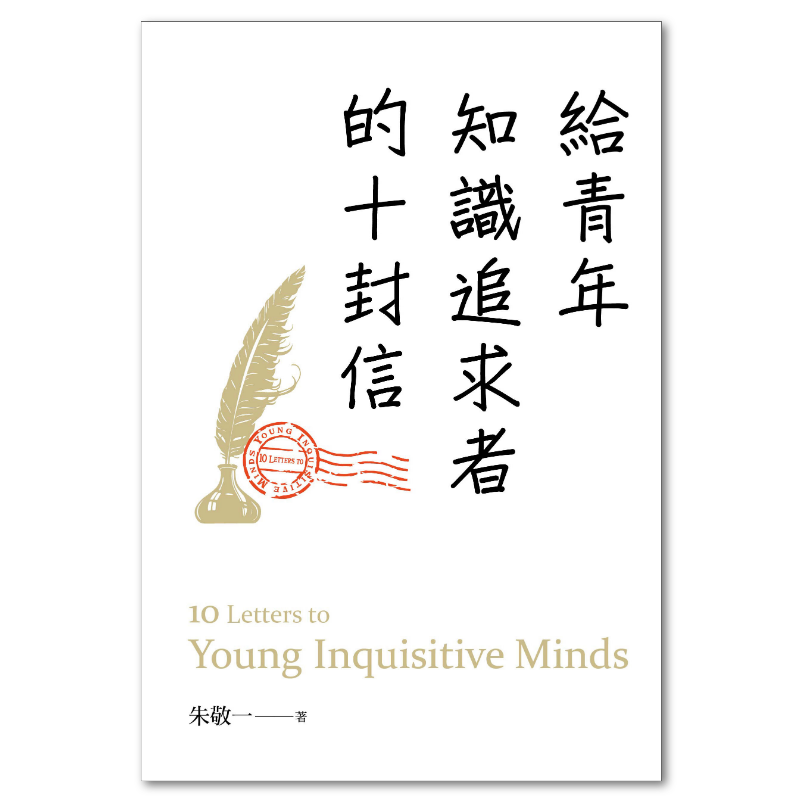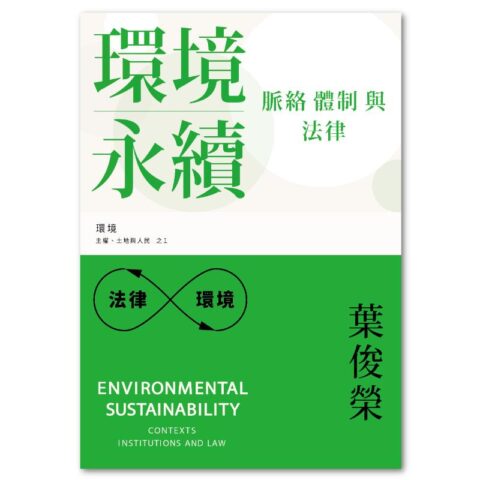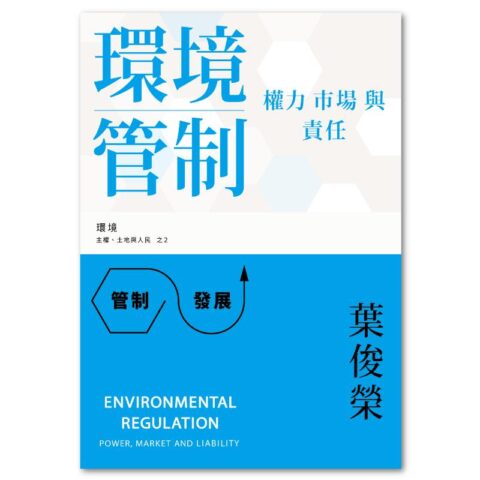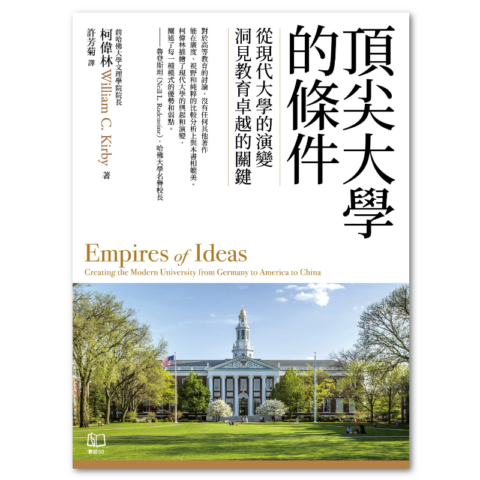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全新版)(10 Letters to Young Inquisitive Minds)
出版日期:2018-05-29
作者:朱敬一
印刷:彩色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08
開數:25開,高14.8×寬21cm
EAN:9789570851229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在普遍高學歷的現今,追求知識的途徑更多、更豐富
更需要經時間沉澱、淬鍊的中肯建言
經過十餘年的沉潛,走在求知路上的朱敬一院士,始終心繫台灣的青年學子。
在《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全新版)》裡,朱敬一院士告訴我們不因歲月磨滅的體悟:追求知識之人要喜歡胡思亂想,如此一來才有創新;在創新之時也須專精,求取廣泛訊息當中最精華的著力點深求;深求的過程中,尚需觸類旁通,望眼更廣大的市場、圖破自身的領域,而在這漫漫長路上,一顆強健的心能助你抵禦大小打擊。追求知識的姿態是活潑又嚴肅的,而知識是既廣且深、既能窮盡,又無法窮盡的。
如今,大環境的變化帶動求學問的途徑改變;做學問的風潮改變,加深了青年人的徬徨與猶疑。不知不覺間,「求知」成了一件複雜的事。究竟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去「求」,又該求得什麼樣的「知」呢?進入學校或研究機構的平台後,如何在事業與最根本的做學問之間求取平衡?而知識的價值,又是評鑑可以衡量的嗎?
朱敬一院士建議所有欲踏上追求知識道路的年輕人們,都問問自己:「我屬兔嗎?我白嗎?我是白兔嗎?」做學問說難是極難,但若要簡單地說,總歸與初心、一股腦往深處鑽的傻勁有關。在涉入更深的知識之路甚或是規劃人生時,我們都該回歸最本源,在踏出第一步前須認清自身的能耐、衡量自己是否能擔得起求知路上的諸多挑戰、磨難。學問與人生同是廣袤、纏結難解的密林,即便是白兔在其中也需懂得生存之道。
追求知識之路難行。朱敬一院士的《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全新版)》,寫給在橫跨科學與人文的廣闊求知場域裡的知識青年追求者們,勇敢尋覓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吧!
作者:朱敬一
1955年生於台北市,先後就讀東門國小、仁愛國中、建國中學、台灣大學商學系、1985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旋即返國,在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從事教學研究。2016年10月,政府借調朱教授擔任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
朱教授於1998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為近20年選出之最年輕院士。2003年渠獲頒總統科學獎,當時也是國內第一位獲獎者。朱教授於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
朱教授於1999年開辦國科會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以及人文社會養成班,並親自赴北、中、南、東四地高中,分別開授一學期十五週之「社會科學概論」,播種耕耘,作育下一代的人文社會研究人才。
作者再版序
推薦序
一 這是給知識青年的智慧箴言──童子賢
二 「懂」學問的價值──葉丙成
三 治學如演戲,瀟灑走一回──林南
四 朱門秘笈──王德威
第一封信 先廣博而後專精
第二封信 「不住相」讀書
第三封信 以通儒為典範
第四封信 一門深入或遍地開花?
第五封信 有胡思亂想,才有知識創新
第六封信 勇敢走向國際
第七封信 虛心面對無情的評審
第八封信 理解「學術市場」的運作邏輯
第九封信 既入,看學術界有哪些誘惑
第十封信 未入,先弄清楚自己的性向
再版序(節錄)
年輕學子在初入社會之際,總是徬徨無助的。記得自己十八歲大專聯考時,志願卡其實是胡亂填寫;當時只知把前一年的聯考錄取分數依序排列,自己就依樣畫葫蘆,幾乎完全比照辦理。當初我念的是商學系,但是說實在的,十八歲的時候根本弄不清楚商學、經濟、財稅有什麼不同,更不了解政治、法律、心理、社會、人類學等學門各是在念些什麼。自己進入經濟學這個領域,確實是「因誤解而結合」。
不僅念大學科系是懵懵懂懂的,連我出國念博士、回國做學術研究,都是偶然的因緣。大專聯考選填的志願是「社會科學」類組,其實我當時不了解什麼是「社會」、什麼是「科學」、什麼又是「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念的是經濟學,但坦白說,一直到三十幾歲,我才真正理解經濟學與其他學門之間的關係。我三十歲起在台大與中研院教書、做研究。然而究竟什麼是研究?知識探索究竟要經歷些什麼過程?研究者究竟在追求什麼?這些問題也是幾經折騰,才理出個頭緒。如果我自己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領悟箇中道理,別人是不是也可能有類似的迷惘呢?年輕人如果因為迷惘而有扭曲的認知,或是做出錯誤的決定,不是很可惜嗎?
聯經出版公司為了讓年輕人少走冤枉路,乃推出一系列「十封信」的短書,為可能要踏入各個領域的年輕朋友,做相關的介紹。林載爵先生讓我負責「知識探索」這一區塊,乃寫成此書。本書的前七封信,是寫給所有可能對知識探索有興趣的讀者的,包括高中生與大學生。至於第八封信則較為深入,是為已經或將要從事學術研究者寫的。前七封信刻畫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的醞釀背景、推演過程,並描述其圓融貫通的典範。第八封信向讀者介紹投入學術研究將會面對的環境,讓可能要投入知識探索者有些心理準備。九、十兩封信則是總結,並提出若干客觀的環境誘惑與主觀的「性向」描述,由讀者自我檢視其是否適合踏入此途。雖然設想的閱讀對象涵括各個領域的知識探索者,但是由於自己只在經濟、法律、哲學、演化生物學方面略有涉獵,若干實例背景則稍微側重這些領域,希望不至於妨礙讀者的閱讀。
此書從初版刋出至撰寫修正版,已經超過十年。十年光陰使我的知識探索之路經驗更豐富、體認更深刻,也更能在關鍵處省思提點。中國決定修憲去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日內瓦大雪紛飛窗外白茫一片,台灣掀起衛生紙搶購熱潮⋯⋯,關心國事天下事的心情起伏,也只能隱藏在修書改稿的文字中了。
推薦序
一
這是給知識青年的智慧箴言/童子賢 和碩集團董事長
朱敬一老師以「知識探索」為主題,給青年知識追求者(Young Inquisitive Minds)寫了十封信,以飽含關懷與愛的筆調,為年輕而焦灼的靈魂作開示。信裡談廣博通識教育、談風簷展書讀而「不住相」的讀書經驗、也談「孔雀開屏」經濟學與創新知識、更談學術路上一有邪神二有學閥三有誘惑的經驗。朱師以諄諄善誘又以當頭棒喝叮嚀啟迪年輕知識追求者。而期望「年輕人可以少走冤枉的路」。
朱敬一老師治學以至誠至勤自我要求極高而聞名,讀書萬卷遂成通人,成名甚早但也(如北宋蘇軾)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他是狷介之士,有著「看他風中盡搖擺,這樣腰肢我沒有」的風骨,因此雖貌似忠厚呆笨(朱師自稱)但其實頑「反動」(眾人旁觀),堪為青年表率。所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朱敬一是也!
這樣專情於學術卻又關心民瘼的知識大腕辛勤寫書信給青年,其實用心良苦用情至深,是寄望啟迪更多有胸襟有見識有品德的知識青年。知識青年因此值得暫時放下課本一讀此書(一如對待米其林一星),而有志終生研究知識探索知識的菁英青年更需細細品味此書(一如對待米其林三星)。
朱老師囑我看稿前曾提醒我大約三小時可閱畢全書,但我展開書頁發現他高估了我輩凡人,我想若要深度體驗、要細細探索,若要追溯滾滾長江般龐博知識源頭,我們當如讀《蒙田隨筆》一般,值得花上十倍時間細細品嚐其米其林三星級的知識饗宴。
這十封信談人生、談求學、談憧憬都相當深刻,其實也算是一冊朱老師知識之路的《懺情錄》。且朗讀半首「偽」晚安詩*讚頌:
是誰傳下這「知青」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頸間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裡的旅客
我接觸過許多「知青」,多數是出身建中北一女,數一數二名校的天命真女、天之驕子。這些可愛聰明的年輕人當然也是考場常勝軍,PR值常在百分之九十九至不濟也是百分之九十八。但驕子驕女一樣也有不少煩惱;除了少年維特的煩惱,還有填志願選科系煩惱、畢業前後人生何去何從煩惱!
在「知識探索」途中,知青要選擇作命運的「駱駝」,抑或要在知識長河中作寂寞「過客」呢?
我猜想了二條路:
其一、青年愛知識,PR在九十九.九而夢想一輩子探索、追求知識,走「人皆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樂」的學術人生。提醒知青們,既然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追求痴情,就要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光榮孤寂」的心理準備。
其二、青年愛知識,一開始都是二情繾綣的,一心但願人長久,但最終也都只能千里共嬋娟。因為優秀學生畢業後一樣要走上人生旅途:邊換工作邊遞履歷表、邊推著嬰兒車又一邊操心房貸利息。上智者學而優則仕則醫則商,下愚者只剩案牘勞形。讀醫學系時候談史懷哲、讀物理系時立志當愛因斯坦、讀經濟系時嚮往海耶克、凱因斯,如今一概無可奈何花落去,都只剩往日情懷。因此許多人開始懷疑:「我讀書幹嘛?」
但在此提醒鼓勵知青們,讀書變化氣質,健全人格,在個人於社會都十分重要,千萬不要做太功利太短視設算。而上述二條路,只要持續保持好奇心且尊敬知識、訓練獨立思考,則二者俱佳。
於此,我也提一些問題與現象藉此表達對青年的期望:
一、剛才談青年人的許多煩惱,我想替台灣年輕人再多添一點煩惱:台灣學生眼中常只有台、清、交、政、成、中研院、工研院..互相比較。但「風物宜長放眼量」,我們不止活在台灣也活在世界。提醒大家,跨出台灣時「世界是平的」。
眺望世界的盡頭,在地平線上還會遇上牛津、劍橋、哈佛、史丹福還有麻省理工,因此學習面對世界、面對挑戰、建立自信、不卑不亢十分重要。
自信源於自知也源於自愛與自重。若只能在台灣考試第一「驕其妻妾」,則面對世界又如何自處?台灣如何寄望與世界接軌呢?(朱老師已經在第六封信談〈勇敢走向國際〉)。
二、知識分子因知識而開闊,但有時也因知識而倨傲而偏狹。佛家談業障,讀書人則或輕或重而有「知識障」,常以自己專業的尺量遍世界,而額頭上常刻著「老子天下第一」,則「臭老九」氣味太濃討人厭還算其次,若誤事誤國誤訂單,則事情不諧矣!
大型計劃常常需要團隊分工團隊合作,不管工程建設、物理研究..皆是如此。心胸不開闊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領導團隊?更有一點,「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其實不只是戲曲故事,現實生活也常見如此。
讀書養氣,一味累積知識並非人生最重要的事。有知識並不等於有能力,有才華並不等於有品德,如同有錢不等於有品味一樣。戒之慎之!
三、台灣教育自小學起把教科書當聖經,把標準答案當箴言。老師以「傳授」知識為主,甚少「解惑」。導致學生很少向老師發問質疑,也不習慣與同儕辯論詰難。這教育風氣不是好風氣。
因為「書本上的知識」只是「舊」知識,古聖先賢「得知於心、應之於手」的環境已改變,故如莊子「天道」所寓言的:書本所載只是「聖人糟粕」而已。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有屬於自己的答案。試看:空氣污染、地球暖化、多元成家、二性平權、網路崛起、農藥使用過度、少子化、高齡化..這都不是二百年前的聖人大師學者關切的課題,尼采叔本華不會給你答案的。
十九世紀卡爾.馬克思是一個敢於知識創新的「通儒」,正如朱老師第三封信〈以通儒為典範〉說的,他跨諸多領域,綜合經濟學、社會學、哲學與歷史觀點,去望、聞、問、切,替十九世紀社會弊病把脈一番,然後開出政治學的解答,以《資本論》、《共產主義宣言》為強力藥方。今年是二○一八,恭逢卡爾.馬克思一代宗師共產聖人二百年誕辰,有為者亦若是!
當代年輕知識分子是否有雄心大志踵武前賢,濂、洛、關、閩、馬克思、凱因斯之後,又「知識創新」一番嗎?互勉之,有為者亦若是!
是為十封信讀後感言。
二
「懂」學問的價值/葉丙成 台大電機系教授
身處這時代,想不焦慮還真的很難。打開手機(不是打開報紙),映入眼簾的盡是一堆永遠沒時間搞懂的新名詞。當中有的超夯,有的卻是還來不及了解就要退流行。網路每隔一陣子就看到 Boston Dynamics 公司的影片,他們做的那些面目可憎的無頭機器戰犬跑上跑下、長腿人形機器人搬重物後空翻。每每看了讓人心生寒意。
網路上整天看到人家說什麼虛擬貨幣、區塊鏈,欸唉(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說什麼以後很多人會被機器人、欸唉取代而失業。看到牛津大學的研究報告,說二十年內四成七的現有工作都會消失。又看到什麼全球二十五個國家都把程式設計列為中小學生的必修課,十年後全世界會有一大票人都會寫勞啥子程式,而自己卻對這一竅不通。
看到這個變化這麼快的世界,想到自己的未來、孩子的未來,你的焦慮又更深了。你心裡阿Q地安慰自己:「沒關係,只要像以前一樣拼命讀書,高分考進名高中、名大學,人生就會成功!」真以為這種阿北阿嬸年代的成功模式,在未來二十年的世界,還能一樣有效嗎?這種想法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在這資訊高度爆炸、技術快速演進、商業模式不斷翻新的現在,與欸唉當道的未來,要如何才能擺脫焦慮?要如何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價值?
你需要「學問」。
等等,「學問」這種東西,不是什麼教授、專家才需要的嗎?「學問」於我何有哉?外面世界變化這麼快,哪有時間「做學問」慢慢耗?別急,我們先探究一下何謂「學問」?每個人或有不同的定義,但我認為「學問」最重要的,就在於學「問」,也就是「學會如何找到好問題」。我個人認為這是未來欸唉時代,人類最重要的能力!
為什麼?
去年某次公開演講,我曾被問到未來如果人工智慧當道,教育該如何改變、因應?我說:「人工智慧厲害的,是它比人類更快解決問題。然而人工智慧不會定義對人有意義的好問題。」我們的教育,必須培養年輕人「學會如何找到好問題」的能力,在未來他們才不會被人工智慧取代。
有道是:「人之異於欸唉者,惟學問耳。」「學問」不再是教授、專家獨有;各行各業的人們都需要「學會如何照到好問題」的能力,才能創造出自己的獨特價值、才能出類拔萃。
若「學問」如此重要,那該如何構建?去唸大學──知識的最高殿堂,是否就能學會「做學問」?
很悲哀的,在大學教書十七載,我看過太多太多的大學生,都是為了「念大學」而念大學。真正因為「想學」而念大學者,幾稀!為「念大學」而念大學的這些人,大學四年往往只學會了「應付」;應付考試、應付作業、應付學分規定,總之只要能夠畢業拿到那張紙,就算是對爸媽有交代了。至於如何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如何「做學問」,這些少有人在意。而老師之間,有能力教學生如何「做學問」的,更是少!
怎麼辦?
你需要這本《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此書彌足珍貴,朱院士把龐雜的知識體系,在書中做了非常清楚的分類與介紹。當年利瑪竇製《坤輿萬國全圖》,中土之人始知世界。而今朱院士撰此書,讓青年學子得窺學海全貌,進而有勇氣悠遊學海。這並非易事。須知步調繁忙的現代,眾人對時間都很功利。「做學問」此等需長久累積之事,若無人傳授法門,一般人多不會貿然投入。朱院士不但分享自己「做學問」的法門,且以親身經歷作見證。看完他書中的故事,會讓你躍
躍欲試,也想開始探索自己有興趣的知識,養成自己的「學問」!
此外本書最讓我驚豔的,是書中所提「做學問」法門,與「創新」之道完全相通!
全世界都鼓勵年輕人創新,但大家往往忽略成功的創新有其重要前提:「你有沒有解決一個好問題?」一個沒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創新,是沒價值的創新。一個成功的創新者,必須能比別人更早找到好問題,才能跑在別人前面做出有價值的創新。在書中〈不住相讀書〉一章,提到讀書應不功利地廣泛涉獵;長年下來累積點點滴滴記憶,接著再透過「串珠珠」過程串出別人沒想過的獨到問題。讀到這我忍不住拍案!這跟我們在做的創新創業過程,不是一模一樣嗎?
在資訊快速全球化流動的時代,線性思維所能想到的創新,老早就被某國某地的路人甲乙丙丁想過了。如何想出沒人想過的創新點子?上面提到的「串珠珠做學問」過程,我認為正是解方!當你能夠把不同的知識串起、連結,想出沒人想到的獨特好問題,自然就有機會做出解決那問題的創新。因為這獨特問題從沒被人想到過,所以你為了解決這問題而生出的創新,自然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只要參透這道理,我們就會發現「做學問」與「創新」,原來是一體兩面!若能讀通此書,對於創新也是極有幫助的。我認為這是本書的另一重要價值。
除了上述種種,此書最讓我佩服的,是朱院士怎能把教人「做學問」之事寫得如此有趣!這當是與他的調皮個性有關。當看到他書中所寫的這段:「看看自己適不適合走進知識探索的叢林。用白話文說,就是照照鏡子,問自己:『我屬兔嗎?我白嗎?我是白兔嗎?』」我當下笑得前俯後仰,捧腹不已。我知道著書之人最痛恨路人破梗,為什麼這句話這麼好笑,我不能說,你看了就知道!
綜而論之,在快速變化、充滿變局的未來,每個人都要能建構屬於自己的「學問」,才能不焦不慮、自信地面對這世界。有了此書「學問」將不再是教授、專家等少數人所有。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做學問」。
懂「學問」,我們才能活出身為人的真正價值,也才不用怕被那勞啥子欸唉取代!
在二○一七年,新回國的年輕助理教授起薪大約是每個月八萬元。如果他(她)的配偶沒有在外做事,而家中有一、兩個小孩,則這八萬元的收入要養家是相當辛苦的。同年台灣的每人每年平均所得是七十四萬元,乘上三,表示三口之家平均年所得二百二十二萬元。這比助理教授一年一百萬左右的薪俸,可是多了許多。可見助理教授在台灣只能勉強算是中產階級。就算此人熬了十年升到正教授,其月薪也不過十一萬元,以一年十三.五月薪計,年入一百四十八萬,衣食固然不愁,但若要因此像顏回那樣「不改其樂」,恐怕也不容易。
但是前述的七萬或十萬月薪只是正薪,還沒有包括「外快」。如果此人認真投入學術研究,則有很大的機會得到科技部的研究計畫,主持人遂有主持費每月一萬五千至三萬元的補貼,不無小益。二○一七年科技部人文社會領域研究計畫申請案計有七千五百多件,通過率為百分之五十五.一。因此,只要此人不是在學術界的後段班,得到補助的機率應該是不小。如果每月有一萬五千元的補助再加上原本七至十一萬元的薪水,待遇當然也算是不錯了。教授本薪與科技部的研究補助,一般而言都是學界可以接受的外快收入。除此之外,學術界朋友還有許多雜七雜八的誘惑,該不該碰沒有什麼法律規範,就得看個人定力了。以下,我們就一項一項加以檢視。
教授們機會最多的外快,就是科技部以外的研究計畫。這些計畫可能來自交通部、國發會、文化部等政府單位,或是台經院、中經院、某某文教基金會等財團法人,也可能來自商業銀行、藥廠、創投等大企業。他們為了某些政策或經營目的,需要學者專業的研究分析,於是以研究計畫的名義外包委託。一般而言,政府單位的研究計畫比較寒酸,計畫主持人每個月大概只有兩萬元不到的津貼;但是民間企業則彈性較大,計畫報酬可以低自萬元起,高至數百萬元。這些計畫有些是透過大學的會計系統而送到教授手中,有些則是與教授個人直接訂約。前者各大學還可以收一些管理費,後者則大學完全撈不到油水,收入悉數進入教師口袋。
什麼樣的教授會拿到政府或企業的研究計畫呢?一般說來,除了專業能力之外,這也與教授的人面與人脈有關。年輕新進人員人面不熟,也還沒有什麼學術聲望,不會有人找你做計畫。但是如果你的系裡有人脈廣布的資深教授,擔任許多大計畫的「中盤商」或「大盤商」,則他就有可能把你網羅在旗下,分派一個小計畫給你;久而久之,待你羽翼成熟,便可自立門戶了,這位資深教授或許也更上層樓。於是他與你之間始終維持著如此「和諧」的互動,將來時機成熟,你說不定也就自然篡位,取而代之成為研究計畫的大盤或中盤。
大致說來,對年輕教授而言,接政府或企業研究計畫的誘惑是很強的,原因有二:第一,它與學術研究並沒有真正脫節,其所分析的現象,往往是交通動線需求、全民健保財務、銀行壞帳來源、WTO對台灣產業的衝擊、綠色國民所得帳的計算、南台灣古蹟保存等。這些計畫的內涵往往是學術研究工作的下游應用,而不是涉及知識創新本身。每個研究計畫固然可能在執行與觀察中得到創新的靈感,進而發掘出真正創新的研究題材,但這一類的事例在台灣極少,幾乎只能當「例外」來看。
國外有沒有類似教授接計畫的情況呢?有的。例如美國司法部曾經有幾件涉及知名大企業的案例,一是訴訟知名電腦廠商IBM涉嫌違反該國的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二是訴訟貝爾電話公司違反該法,三是在二十世紀末對微軟公司提出同樣的控訴。這一類反托拉斯案能否成立,涉及廠商產品的定義為何、多種產品之間是否有行銷的關聯、定價的行為是否合乎經濟法則、市場的競爭是否受到干擾、消費者的權益是否會降低等等專業計算。於是在每次訴訟中,正反雙方都各自尋找一大群經濟學者,找種種學術理由為自己做證。由於判決結果影響的利益可能有上百億美元,因此廠商花錢也不手軟。在這幾件案例中,經濟學家有些人發了財,也有些人從經手的案例中寫出幾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另外一門經常吸引學者大量投入的領域則是法律。愛克森(Exxon)石油公司一九八九年北海漏油案,肇因於該公司油輪在北海觸礁,造成原油外洩而影響生態。在訴訟中,將生態回復原狀的費用估算是一回事,要不要對愛克森課予懲罰性賠款(punitive damages)是另一回事。就回復生態原狀而言,其估算十分複雜。多少野鳥、多少魚群、多少遊客等等,其設算的數字略做改變,結果就有天壤之別。就懲罰性賠款而言,一般對於執行疏失的自然人課予懲罰較無爭議,但對於公司這樣的「法人」課予懲罰,其意義則有些模糊。懲罰公司是不是處罰無辜的股東呢?企業經理會因此而更加謹慎嗎?在此案中,正反雙方都聘請了一些美國名校的法學與環境生態學教授助陣。當然,知名教授經此一案也是狠賺了一筆,而其中若干人也因此而撰寫了幾篇學術論文。但是整體而言,這些應用性研究計畫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只是點綴性質。
一般而言,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學術性較高,但企業的研究計畫則著重應用。對於教授參與學術性不高、應用性極強的研究計畫,我們該用什麼態度看待呢?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得看個人的目標志向而定。如果你對學術研究、知識創新的自我期許極強,那麼最好避免參與這些計畫。如前所述,這一類研究真正能夠產出亮麗研究成果的機率極小,對於學術創新確實會產生「分神」的影響。但是如果你在個性上原本就較具現實親和(empirical attachment)傾向,覺得把知識應用到各個社會面向是一種成就,那麼犧牲些許研究創新的時間去參與計畫亦無不可。然而這樣的參與有一個前提:千萬不可與教學研究的本業本末倒置。身為教授,我們有義務不斷地接觸吸收專業領域內的新知識,也有義務對學生傳授這些新知識。如果我們對於外在研究計畫的參與,忙到影響我們閱讀期刊、參與研討會、撰寫論文,則就是本末倒置了。每一個參與外來研究計畫的人,必須要檢視自己的時間分配,問問自己究竟是「專職教授兼差做計畫」,抑或「計畫中盤商兼差做教學研究」。如果是前者,可以接受;如果是後者,那就是尸位素餐,對不起學校也對不起學生,年輕學者千萬不要走到這步田地。
用個例子說明,更能釐清教授接應用性研究計畫的分際。教授做學術研究,就像是聲樂家唱藝術歌曲一樣;而應用性研究計畫,則像是聲樂家唱流行歌曲。世界首席男高音多明哥(P. Domingo)到五十幾歲才灌第一張抒情流行歌曲唱片;在此之前,他都是唱歌劇等藝術歌曲。歌劇不好唱、難度高,但是有助於歌唱功力的提升。流行抒情曲容易唱、銷路好,但對歌藝功力的提升幫助不大。多明哥一生,大概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唱藝術歌曲,百分之二十的時間唱流行歌曲,我認為這是個理想的比率。越是年長,唱流行曲的比率可以略微提升,而年輕有潛力的聲樂家則不適合太早去唱流行曲。在初入學術生涯的前十五年,奉勸你最好是苦蹲寒窯,實實在在地奠定自己的學術根基。
當然,應用型的研究計畫並不是每個領域都有的。在大學中,中文系、哲學系大概很難有機會參與什麼外包計畫,因為社會沒有這一方面的需求。數學系裡做理論研究的,也鮮少有研究計畫會找上門。大部分應用性的研究計畫,都集中在管理學院、工學院、法律系等領域。某個科系教授外務太多,難免會引起其他系同僚的敵視。在大學裡,如何面對這樣的可能敵視,也是年輕人事前需要想清楚的。
學界還有一種接研究計畫的醜態,就是「搶資源」。例如,有許多研究原本是彼此獨立的,但是如果湊在一起冠上一個「整合性」、「國家型」、「前瞻性」的大帽子,也許就能騙到更多資源。這個時候,學校的行政主管就會想到邀請一位大尾學者、院士來領軍。等到大計畫核定下來,一大筆預算都歸這位大尾院士掌控,包括設備購買、出國經費、電腦更新、研究生獎助等。大尾學者浸淫在這樣主宰資源配置的情境下,只要稍欠反省能力,慢慢就與「學閥」庶幾近矣。
我在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掂掂身高體重生辰八字的分量,近二十年來應該算是個超級大尾。如果真的要去搶計畫預算,我大概可以攻城略地戰果豐碩,在台灣的人文社會領域鮮有對手。但是三十幾年來,除了極少數做田野問卷的計畫,自己好像沒有申請過一年超過一百萬台幣的計畫。我其實極為痛恨學閥;做國科會主委期間,幾乎是不顧得罪人地砍掉莫名其妙的國家型計畫,也對於名實不符的大計畫主持人嚴加管理。國科會所有的副主委、處長,全部不准替自己借調的學校或同事爭資源,違反者我會不假辭色地予以處分。年輕朋友如果問我對他們有什麼嚴厲的告誡,我的答案非常簡單:千萬不要讓自己變成學閥。
教授與研究員的另一項誘惑,則是擔任某某公司的專業顧問、某企業的董事或監察人、某大學的兼任教師等等。這一類的工作往往需要每月或每週若干小時的投入。一般而言,各大學都訂有兼職的時數限制,雖然看起來是「君子協定」,校方真正執行查核的機率甚低,但是這些限制確實是維持教授專心投入本業所必要。如果你因為種種理由超越了這樣的時數限制,也許就該面臨一個選擇,究竟要不要辭去本職。許多人也許會掰出不得已的情境以為解釋,但是這裡牽涉的問題,是通案的專業倫理,而不是個案的特殊背景。
台灣早年學術界的許多教授在參與外務久了以後,就由量變轉為質變。先是逐案接政府研究計畫或擔任顧問,久而久之政府業務熟了、官僚體系的運作通了、政府高層的關係好了,就借調至公務機關任職,逐漸踏入仕途。過去數十年政府官員或企業主管之中,來自學界而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包括梁國樹、郭婉容、孫震、邱正雄、薛琦、陳博志、陳師孟、許嘉棟、林全、林華德、李庸三、胡勝正、吳榮義、朱雲鵬、林忠正、林向愷、施俊吉。以上姓名,皆出自台大經濟系教職員名錄。如果翻到台大法律系,則歷屆大法官與相關法律機關的官位,幾乎由該系專兼任教師占去了過半的名額,包括翁岳生、馬漢寶、王澤鑑、施啟揚、戴東雄、柯澤東、林子儀、李鴻禧、廖義男、黃宗樂、許宗力、葉俊榮、羅昌發等人。如果把歷任總統算進去,台大法律系幾乎是紅不讓。至於與台大政治系有關的,則有連戰、錢復、吳庚、李鍾桂、丁守中、魏鏞、許慶復、蔡政文等人。
大體而言,學術界出任政府官員的,當以政、法、經三個領域為最多,當然其他領域也有不可小覷者。例如李登輝出自台大農經系,台大醫學院進駐衛生醫藥領域,王志剛、高孔廉、黃俊英出自企管領域;但這些畢竟只是少數。法、政、經三大社會科學領域,絕對還是學者從政最大宗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