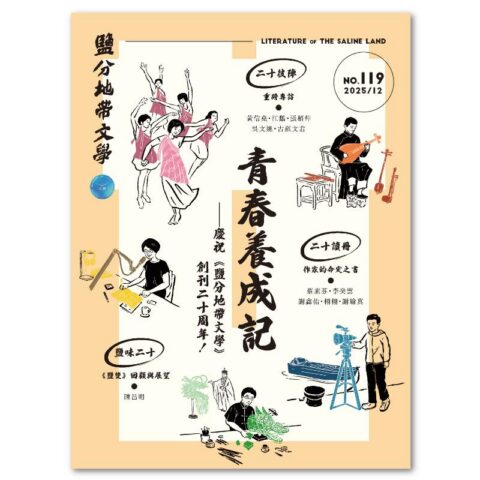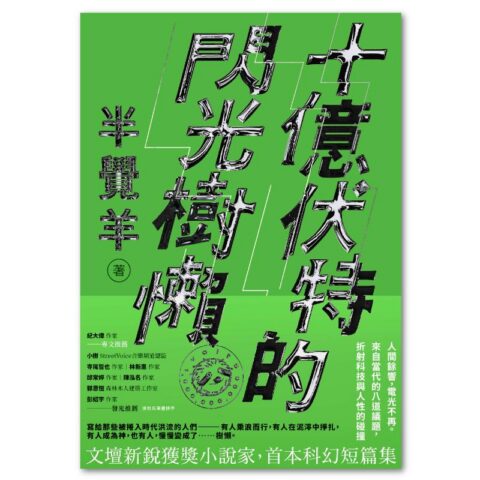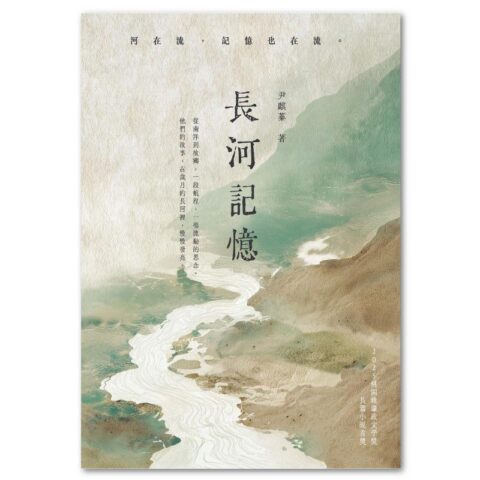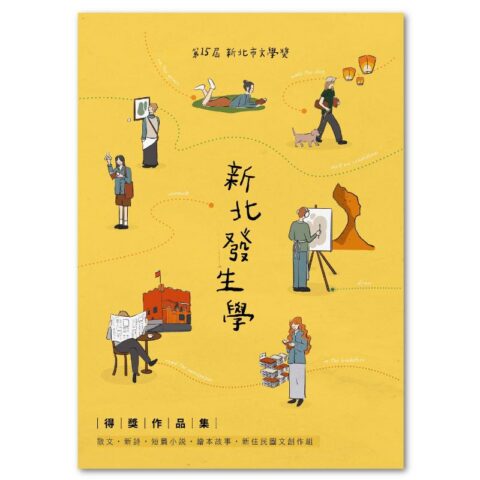一個詩人的誕生:對他者的生命敘事
出版日期:2022-07-07
作者:何日生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24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2cm
EAN:9789570862591
系列:何日生作品集
尚有庫存
十五篇人物特寫,透析社會百態的善意與念想
電視金鐘獎最佳新聞節目《大社會》的報導原型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詩人,這首詩,不管是優美或苦澀,歡樂或悵然,我們都要寫好這首生命的詩。悲與喜是生命中的兩大翅膀,憑著它們,我們才能在無窮生命的天際中盡情翱翔。
──何日生
人文學者何日生,回首過往十多年的新聞媒體從業生涯,揀選歷年編採探訪內容,以15篇人物專訪及思索回顧,引領讀者細細體觀生命思索。
採訪人物與事件包括: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者崔小萍導播、花蓮豐濱難產婦女理性、在臺深根的加拿大環保人士劉力學、花蓮專門超渡無名屍的修平法師、堅守信仰拒絕服役的邱家人、因血友病輸血而感染愛滋的病友李錦章、幼女冤死而不斷挑戰司法上訴的父親周鳳山、排灣族的作家同時身兼森林警察的撒可努、自小失學為生計唱戲的少女芳秀、遭線民反咬而被起訴的警察吳金龍、三位痛失愛子轉念為大愛的慈濟志工、骨髓移植的專家湯瑪斯博士‥…等。
受訪者來自各階層角落,經歷人生重大挫折與考驗的受難者、默默為社會奉獻的利他之人,以及超越自我生命障礙的勇者。透過作者的洞察之眼、體念之心,盼願將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化為文字,見證社會中隱藏的堅韌與生命之詩。
名家推薦
日生這本書,時光回到原初:他還是新聞人的時候,他的觀察與記錄、所思與所感。經過這些年歷練,他選出過去新聞生涯的十多篇散文,文章依舊,但時隔多年,此時他為何而選,一定與他當年屬筆為文時,心境大有不同。
──羅國俊|願景工程基金會執行長
《一個詩人的誕生》,內容很多是出自《大社會》節目中他所採訪的對象,《大社會》在日生近四年的製作、主持之下,不只拿到金鐘獎,也為臺視新聞關懷弱勢的理念,得到很充分的體現。他離開臺視以後,《大社會》多次在臺視重播又重播,可見這種關懷底層的動人故事,永遠都是受到大眾的偏愛與青睞。
──廖蒼松|前臺灣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前公共電視總經理
他就是詩人,他總是知道在什麼時候去說出可以替別人引路前進的話語,而那樣子的話語,如黃昏在山間吹來的風,會把你吹醒;又像清晨的太陽光,灑在你的身上把你喚醒般,他就是這樣……。
──撒可努|作家、獵人學校創辦人
透過這些訪談和紀錄,最後呈現給觀眾的不是譁眾取寵灑狗血的速食新聞,而是能讓觀者去同理去思考去理解的深度人物報導。就像何日生老師在書中所寫下的每一個受訪者與採訪者之間生命交會的激盪,那是一種良善的傳遞,關於愛的能量交流。
──陳慧翎|金鐘獎戲劇導演
作者:何日生
佛教哲學與宗教NGO領域之實踐者暨研究者,長年致力於慈濟人文工作。著有《慈濟學概論》、《一個詩人的帶誕生》、《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利他到覺悟: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建構式新聞》、《一念間》、《慈濟實踐美學》、《清水之愛: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與Bill Kazer(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合著 《Co-Existing with the Earth》;策劃編輯《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敘愛》、《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等書。
其所著《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獲得臺灣「金鼎獎優良出版品」、美國首屆「舍衛國人文獎」、中國大陸「2020年向光獎——年度研究特別獎」。
現為哈佛大學CAMLab特聘學者、慈濟大學副教授。2018-2020為哈佛甘迺迪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南加州大學傳播碩士。多次受邀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北京大學等進行專題講座。
資深媒體人,電視主播與製作人;多次榮獲臺灣電視金鐘獎。所製作之《清水之愛: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世界骨髓移植紀錄片,入選2014年國際艾美獎(Emmy Award, International)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推薦序
◆ 人我交融───利他行於文哲之間/羅國俊
◆ 新聞記者───社會的心理治療師/廖蒼松
◆ 如山間吹來的風/撒可努
◆ 生命交會的激盪/陳慧翎
一、一個詩人的誕生
二、她輕如鴻毛
三、山與海的交界
四、翻山越嶺的愛
五、嗅出家鄉的人
六、生之海
七、我選擇坐牢
八、曝光
九、沒有歲月的河
十、祖靈的孩子
十一、躍升的鳳凰
十二、童年的封印
十三、洞穴裡的光
十四、伊瑩的恩典
十五、西雅圖天空的一抹雲
後記|寫在本書之後───在生命中相遇
作品出處年表
後記/寫在本書之後──在生命中相遇
這本書所記錄的對象都是我的受訪者。在我十多年的新聞生涯中,我有幸與他們相遇。對我而言,他們不是我工作上的採訪對象,而是在生命中與我相遇的朋友、貴人、善知識。
在他們的故事中,我經歷見證人生的悲苦與歡喜,生命的脆弱與勇氣。這是雕塑一個生命人格,甚至是創造任何有意義的人文作品必要的素質。如同文學家巴爾札克說:「在藝術裡所要堅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氣,而是在才氣之外,充滿生命,並且使生命賦予意義與價值的歡樂與悲苦。否則人們只能複製,而不是創作。」
我一直以新聞記者為榮,雖然在我早年的生命中,沒有預期會當記者,甚至在早期的歲月中,也沒有那麼喜歡當記者,直到我遇到這些朋友,我照見他們的生命,與他們的生命交融,或許就那麼幾天,在歲月的長河中那麼短暫片刻,但是他們給我的記憶與影響仍然非常深遠。我帶著感恩的心,回溯他們的故事,敘說他們的毅力與勇氣,他們在悲傷中沒忘記愛,在困苦中沒有放棄希望,他們都是生命的勇者。
這些故事多半發生在我四十歲以前,是我在製作、主持台灣電視公司《大社會》節目中走訪的故事。我在說他們的故事之前,說說我新聞生涯的故事,因為當了記者,我才有因緣認識他們。
我的記者生涯從二十五歲開始,我到台灣廣播公司擔任主持人及新聞記者。那一年我退伍,去找我當時在台廣上班的學長張曄,被張曄的同事看中了,希望我加入台廣。我沒有認真地找工作,有一家廣播公司已經很好了。台廣總經理馬長生見了我,在相談一段時間以後,他說了我一生都很感恩與難忘的話:「日生,你很優秀,你這種人才在台廣不會待久,如果為了台廣我不會用你,如果為了廣播界多一個人才,我會用你。」說完這話,我們的面試就結束了。第二天,我接到電話,被台廣錄取了。
在台廣的歲月,我製作一個音樂節目《西方的話》、採訪新聞、以及參與《王者之見》的新聞節目。一開始跑新聞是由一位郝大姊帶著我,到內政部、到警政署、到環保署跑新聞。郝大姊是一位大美女,很高、很磊落、很霸氣,當年應該未滿三十歲。她父親是一位海軍中將,先生是一位外交官。她對我很好,對我很提攜,常常一起跑完新聞,就到她的新聞節目《王者之見》當中說今日新聞。
有一次郝大姊跟我說:「像你這樣新聞採訪一結束,就能侃侃而談新聞內容,只有中廣的資深記者能做到。」當時戒嚴時期,中廣獨大,人才濟濟。我在台廣工作不到半年,我主持的音樂節目就入選提名當年金鐘獎最佳音樂節目主持人。當時台裡都很驚訝,那一年,台廣只有我一人入選金鐘獎。
郝大姊在我進入台廣一年左右離職了,跟著夫婿外派。她跟馬長生總經理商量,讓我接《王者之見》節目。所以之後,我同時主持音樂節目《西風的話》,以及新聞節目《王者之見》。馬長生與郝大姊都是我生命的貴人。
從事廣播一年後,我又認識了一位兄長閻大衛,他是當時中廣《全國聯播》節目製作人及主持人。當年《全國聯播》節目的時段是早上七點鐘,全國的廣播只播這個節目,所以影響力非常大。我們各廣播電台偶而會送「主題報導」給中廣《全國聯播》節目。那一年,我二十六歲,到中廣送一則新聞報導給《全國聯播》節目。閻大衛在中廣見了我,相談一陣子以後,他告訴我:「當年我進中央廣播電台,我的前輩白銀告訴我,大衛,你在廣播界一定會飛黃騰達。」大衛說:「我今天把這句話送給你。」
閻大衛於是希望我加入中廣。但是我到台廣才一小段時間,不好離開。於是在台廣總經理的同意下,我在台廣及中廣《全國聯播》節目任職,當專題記者,跑國會,跑重大新聞。所以我兼了三份工作,製作主持《西風的話》、《王者之》、以及《全國聯播》專題記者。我在台廣的第二年,《西風的話》再次入選金鐘獎最佳音樂節目與音樂節目主持人;而《王者之見》則榮獲新聞局最佳社會建設獎。那是我當年的福報。
山與海的交界
一、拂曉
花蓮豐濱,是被一群蜿蜒的大山所切割出來的一塊狹長的緩坡地,山勢峻峭,逼臨著無垠的大海,形成一種優美又壯闊的氣勢。原住民的祖先,幾千年前就到這裡落腳。對他們來說,山是生命的源頭,而海是靈魂的歸宿,在那無人細數的悠久年代中,歲月,像海的潮汐,千年不變;死亡,像山中飄零的落葉,那樣地自然;而生命,亦如海浪的起伏,掀起歡樂、也掀起痛苦。
清晨三點多,農曆十六的月亮顯得特別地圓,斜照在海面上,和天邊盡頭那一絲若有似無的霞光交融著,盪漾出銀白的浪花,令人分不出是月光或是霞光。潮水拍打著海岸,編織出一層薄薄的水霧,三月清晨,空氣中仍然透著一股寒意,新發的秧苗在曉霧中等待著春暖。世代以來,花蓮豐濱一帶的噶瑪蘭族及阿美族的子民,就在這樣的清晨中醒來,然後耕種、打獵、捕魚,千萬個日子靜靜地過去了,什麼也不曾來驚擾他們。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新社村的潘宛老已經兩夜未曾闔眼,他不時拿著毛巾擦拭著太太理性(Li Shin)的額頭,不時掀開麻被,注意理性是否還在出血。理性痛苦的呻吟聲,在清晨的寧靜中顯得分外淒厲,已經生產了兩天,再不送醫院恐怕是保不住了。
老潘回頭看著熟睡的幼兒們,噙著眼淚,難捨地摸摸他們的臉,他避開理性的眼光,擦拭淚水,然後立刻起身,拖著疲憊的眼神,跨著踉蹌的步伐,走了幾十步,停在一個茅草屋前,急促地敲打著門。陳文謙在睡夢中被驚醒,開了門,驚異地看著老潘的神色。他知道情況不妙:「我馬上來!」陳文謙轉身進屋內,抓了一件衣服,他的太太從床上不安地探著頭,兩人交換了一下的眼神,憂悒,凝重。
海風吹著蘆葦,蘆葦花回應著早春的美意已經全開,在月光下,一如夜裡的訪客,頻頻向人招手點頭。李烏吉三點不到就起身,和老公趕路,從東興部落到新社也要走上半個小時。姊姊理性生了兩天,昨夜來通報的人也未說明究竟情況怎麼了,姊姊會不會在天亮前就生了呢?還是……前兩胎不是都很順利嗎?怎麼會……李烏吉暗自揣忖著,在澹然迷濛的微光中,繼續快步地趕路。一九六○年代,從東興到新社只能靠著海邊這一條寬幅約三十公分的小徑,四周芒草、蘆葦長得比人還高,月色逐漸稀薄,似乎已經預示著晨曦光明的到來。李烏吉在前,她的先生落在十多公尺後面,兩人默然不語。
此起彼落的浪濤聲接續地拍打著,像是亙古以來的詠嘆,也像是生與死的預言,水波在沙灘上流連,唏唏嗦嗦地嘀咕著,似乎一點都不知曉、憐憫夜行者內心的焦急。潮氣輕落在李烏吉的臉上,像是跳躍的音符,冰冷、無知地敲打在憂懼的臉龐;在拂曉前的黑暗中,海潮聲把整個山頭、大地都吞沒在它無止盡的吟唱中……。
在新社的山腳下,一處茅草搭蓋的民宅,緊挨著河邊,那是距離理性的住處不到一百公尺的山下,理性的養子潘武雄一早起身,看了熟睡的妻子林世妹一眼,起身走到廚房,從水桶裡添了一瓢水,隨便抹了抹臉,穿上一件薄長袖,把山刀繫在腰帶上,他的動作很輕,怕驚擾到還懷著身孕的妻子的睡眠,畢竟媽媽理性的事,不可以讓妻子知道,以免傳染、觸霉頭。
和世妹結婚已經兩年,這是第二胎,希望生的會是個男孩子。潘武雄輕輕地掩上門,快步往山上走。潘武雄是潘宛老的養子,爸爸嫁給理性(阿美族的招贅)已經六年,生了兩個弟妹,沒想到第三胎這麼不容易。送到醫院路途遙遠不說,不知道得要花多少錢?去年冬天收成的稻子,年還沒過,債主早已經把穀子都拿光了,還能剩多少錢呢?
爸爸的家,距離自己住處往山上不到三分鐘的路途,兩年前自從阿嬤和繼母理性大吵之後,他們就分家了。武雄和阿公、阿嬤一起住,爸爸和理性住在山上。潘武雄沿著家裡的河道往上走,河水冰冷清澈,他打著赤腳,溯河前行,山頭在微弱的月光籠罩下,輪廓逐漸清明,深藍的樹林,像是著上黑墨未乾的畫紙,有著溼透的寫意。
不一會兒工夫,他來到爸爸的屋子前,看見陳文謙已經用竹子在編織坲落(竹擔架)。潘武雄站在門口,消瘦的臉龐凝視屋內一角,爸爸潘宛老正在幫媽媽理性收拾簡單的衣囊。武雄接著拿起一根竹子幫忙陳文謙編織坲落。他們以兩根竹子為一單位綁在一起,每兩根竹子之間間隔有一個手掌寬,他們以十字交叉的格子狀,依序編成一個躺椅似的擔架。
「妳怎麼不再努力一下?」李烏吉手握著姊姊,話才說出口,淚眼已經滑落,理性看到妹妹出現,情緒更是激動起來,抖動的身體和不斷的呻吟聲,讓她看來極端痛苦。「我已經努力兩天了,我真的沒有力氣了。」理性抽搐著回答,「這幾個月我都只能吃煮熟的香蕉,實在沒有力氣。」「那送醫院有一段路,妳要挺得住,無論如何總要把小孩生出來。」
李烏吉翻開姊姊蓋著的一床薄麻被,看見姊姊正流著血,部分血跡已經凝固,孩子的頭已經露出來,可以看見清晰的頭髮。李烏吉傷感地拭著淚水,眼見孩子就要出來了,怎麼會這樣子呢?潘宛老從屋外走進來,疲憊又焦急的眼神透露著很深的不安。「可以動身了!坲落已經編好了。」陳文謙和潘武雄以及理性的表弟一起把坲落平放在地上,潘宛老用一床薄薄的麻被鋪在坲落上,潘宛老及潘武雄合力將理性輕輕地移動,在眾人合力下,理性已經躺在坲落上。
六歲的潘金田在睡眼惺忪中醒來,看見大人忙進忙出,他的神情懵懂而無助。李烏吉走到床邊,要潘金田再躺下,催促他趕快睡覺。她拍著潘金田的背,眼神不時看向躺在坲落的姊姊,潘宛老已經準備就緒,手裡拎著一袋簡易的衣服,到醫院也要住個幾天吧!潘宛老的家這時候擠進更多的人,陳文謙的弟弟和太太,鄰居嘎灶的太太也一起過來探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