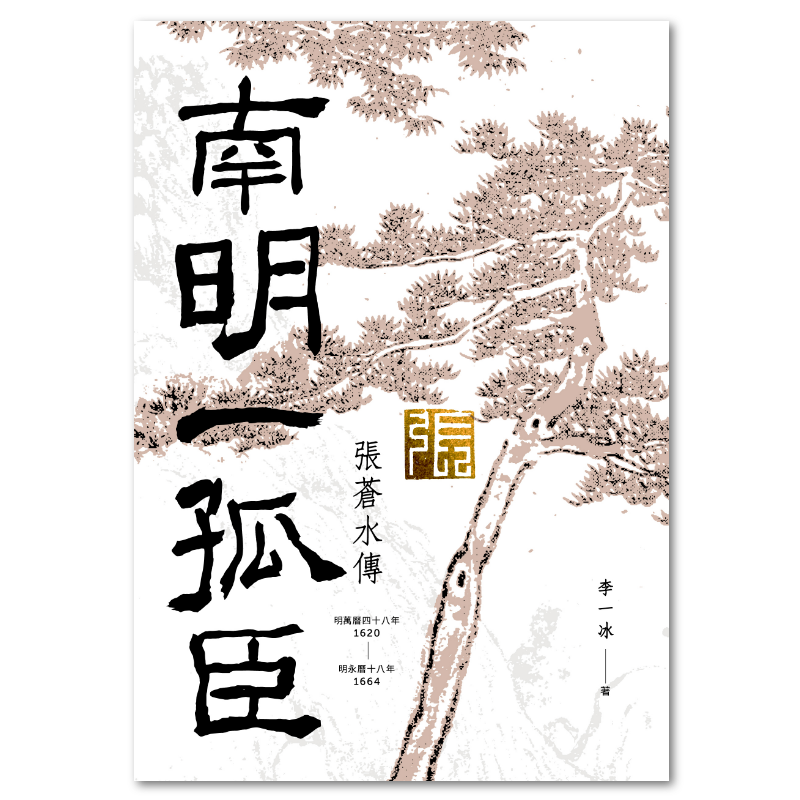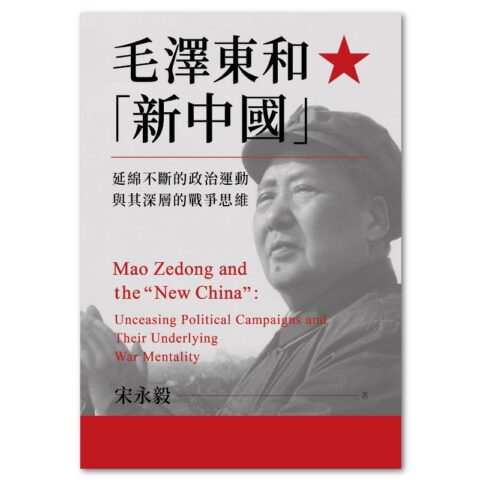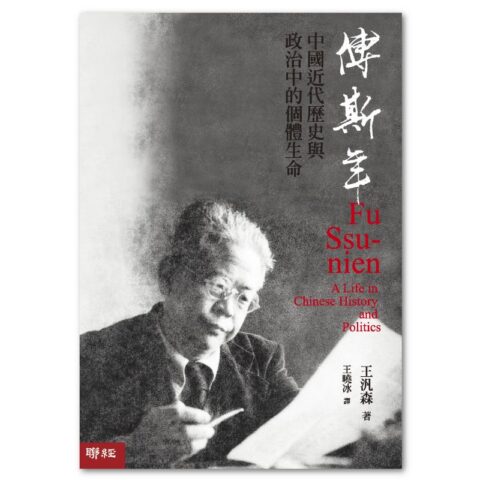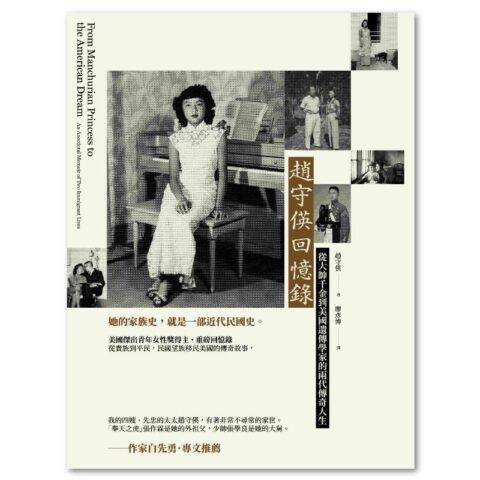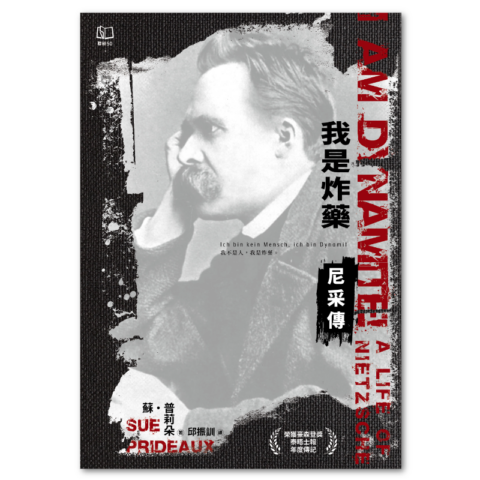南明一孤臣:張蒼水傳
出版日期:2022-12-08
作者:李一冰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6117
系列:李一冰作品集
尚有庫存
傳奇之書《蘇東坡新傳》作者李一冰,
長年以來不為人知的另一部神祕傳記作品……
失敗的英雄,在庸凡俗流中,是只有寂寞的。
張蒼水出身官宦人家,與鄭成功並列明末抗清名將,曾親率部隊連下安徽二十餘城、堅持抗清19年,以民族偉人的形象而為人熟知,更是留下多部作品的民族詩人。1949年,李一冰來臺途中,經過舟山群島,憶起張蒼水當初即於此地奉魯王、據浙海、抗清兵,有感於歷史冥冥重演,於是決心為其立傳。
李一冰認為,張蒼水憑藉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計成敗,百折不回,實屬儒家哲學至高無上之傳統。他以張蒼水流傳至今的詩文為骨幹,輔以詳盡的歷史考據,通過文學,一筆一畫細摹出他的血肉,使這位大將畢生的高峰低谷、喜怒哀樂,得於數百年後,盡收讀者眼底。
《南明一孤臣:張蒼水傳》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的《明末孤臣張蒼水傳》;後10年之間,作者三易其稿,又於1967年增補修訂成《張蒼水傳》,本次重排新印,獲對張蒼水有深入研究的香港大學陳永明教授捐贈筆記,增添最新史料、修補闕落訛失,為全書做了最詳盡的注腳。
作者:李一冰
1912-1991,原名李振華,以「一片冰心在玉壺」之意取筆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原籍為安徽。畢業於浙江私立之江大學經濟系,後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陸續於新文學重要刊物發表白話散文。
民國36年(1947),隨叔叔李辛陽來台,於經濟部物資調節委員會擔任科員。民國40年(1951),不幸捲入弊案成為代罪羔羊,判處八年徒刑定讞,然因未收到拘禁通知而未入監。56歲時遭索賄未果,遂被重提前案,監禁四年後假釋出獄。
獄中四年,李一冰熟讀蘇軾詩作兩千多首,同時整理《東坡事類》、蘇軾年譜等重要書籍,於民國68年(1979)寫成《蘇東坡新傳》,共計七十餘萬字。另著有《南明一孤臣:張蒼水傳》。
前言/李雍
自序
第一章 鄞縣城中一少年
第二章 浙東起義
第三章 海沸山奔的大時代
第四章 三入長江
第五章 北征記
第六章 徘徊閩浙
第七章 濡羽救火的鸚鵡
第八章 從入山到就義
附錄
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黃宗羲
張蒼水年表
前言
方余少時,讀書錢塘江滸,週末返城度假,往來必循西湖南岸,出湧金門,過錢武肅祠、淨慈寺而至南屏山麓,則一抹粉牆照眼,庭鴉噪聒,院宇沉沉者,四明張蒼水先生墓園也。所惜是時,總在西山落照、暮靄漸冪之際,故雖月數往復其門,而均無由展拜。以為來日方長,不圖一別鄉井,垂三十年,不得重見西湖,終孤茲願。
一九四九年來臺途中,舟行海上,天際隱約,展現青痕,或人指為舟山群島,頓憶蒼水先生奉監國魯王據浙海、抗清兵者,寧非依此一線乎。浩浩東海,千古如一,感國運之邅迍,凜歷史之重演。於是讀其遺書,兼及關連故籍,以遣客愁,積有時日;以為張氏血路心城,摶風搏浪者一十九年,獨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精神,不計成敗,百折不回,實屬儒家哲學至高無上之傳統。哀其遇而景其行,遂有撰作張傳之意。
唯時臺灣求書之難,難於登天,一疑未解,每為掩卷,初草「明末海師三入長江事考」,刊於《大陸雜誌》,李學智先生見而善其述作之意,特為長文,諸多訂正,空谷跫音,佩慰無似。由是有所見聞,輒自改修,十年之間,三易其稿,猶以未能盡讀昔賢載記及近出史料,取資覆覈,不敢輕率問世。
一九五九年八月,金門構築工事,發現魯王真塚。明永曆十六年寧靖王朱術桂所立「皇明監國魯王壙志」並時出土,不特堪資取證舊史,而魯王一生為國族艱苦奮鬥之遺烈,重復激盪人心,采耀南天。蒼水先生奉魯王起義浙東,徙行入海,一十九年,「始終為魯」,故延平稱之為純臣,綜其一生行誼,貫徹魯監國朝,張傳實同於魯紀。此作或亦有當於民族精神之表揚,忠義之敦勵,爰付剞劂,幸垂 覽教。
一九六七年秋九月 杭州李一冰自記
二零一四年三月 李東、李雍重校
■ 第一章 鄞縣城中一少年
明崇禎十年前後,浙江寧波府首邑──鄞縣城中,有一位絕頂聰明的世家子弟,突然變得墮落起來,使他鰥獨的父親為之痛心疾首,使他家的親戚朋友為之搖頭嘆息,凡是知道他家情形或認識他父親平素為人端方不苟的人們,談到這位少爺,沒有人能同情他的荒唐。
卸任解州知府張圭章這位獨生少爺,長得個子瘦長,面目清秀,皮色雪白,十足是個典型的文弱書生,然而當他說話的時候,聲音非常洪亮,而且目瞳炯炯有光,顧盼非常,如他的朋友明末大儒黃梨洲所說:「自幼跅弛不羈,然風骨清華,局幹敏達,落落不可一世。」
他不修邊幅,不矜細行,故意穿著惹人側目的絳紅色道袍,徜徉街市。
這位年在弱冠的青年,他不滿現實,而豪情萬丈,無處寄託,又管束不住年輕人動盪的心志,因此接二連三地做出荒唐事來。全祖望年譜說:「公少好黃白之學,嘗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游於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據說他曾輕財結客,擁有一大堆談兵挾策之徒,做他的朋友。後來忽又縱情賭博,歡喜「呼盧狂聚」,「……時時從博徒遊,擲立盡,輒大噱稱快為笑樂」。
實在說,他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孩子,十二歲上就死了母親趙太夫人,他的父親沒有再娶,一身擔負了嚴父慈母的雙重責任,望子成龍的心理太急切,對他的管教素來嚴厲,居常鞭扑捶楚,不稍顧惜,反而形成一種絕對的反抗心理,如火燎原,終至不堪收拾。
這份世居鄞縣縣城西北廂的張家,雖非累代簪纓的巨室,但也是宋朝張文節公知白的後裔,為鄞城的舊家。清代浙東史家全祖望論甬上族望說:「甬上之張,為四姓之一,其最著者曰文定公之宗;次之曰君子堂,則經略都御史楷之宗,由慈水來者;……處士之宗,名位稍不逮,顧以孝友著里中,稱為雍睦堂張氏。」張圭章也是雍睦堂張氏子弟之一,出生於萬曆六年,少年時代在科場上很不得意,曾以秀才受聘於山陰黃忠端公家做家塾老師,教授黃家子弟,博束脩以自養。他的生平,《鄞縣誌》入〈名賢傳〉,記如:「張圭章,字兩如,領天啟甲子鄉薦,屢上南宮不第,謁選得河東鹽運使判官。」又《寧波府志》人物傳:「……殫心鹺務,著賢能聲,以淡於仕進,致仕歸。為人剛毅正直,嚴於訓子,處鄉族皆有義行。」圭章兄弟四人,他為長子,二弟堯章,早亡。三弟憲章,字性近,號完素,有三個兒子:嘉言、昌言、德言。四弟封章,字季超,號元白,族譜說是一個「燦漫天真,樸實無二,有隱君子風」的人,無嗣,以三房的次子昌言承祧。
圭章夫人姓趙,結婚多年,只有一個女兒,直到圭章四十三歲那一年上,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一六二○年)的六月初九日,才養了個遲來的兒子,這兒子便是一度「不理於眾口」的張煌言。
煌言字玄箸,號蒼水,趙夫人養他的時候,夢見五彩祥雲入室,所以小字阿雲。他生來非常聰明,只是身體很瘦弱,極為善病,也許是父母中年以後所生的孩子,先天單弱的原故,所以不病則已,「病輒瀕死」。
身體儘管孱弱,頭腦卻是挺好,六歲上學,教他讀書,一上口就能誦讀,到九歲的時候,不論他那嚴格的老父,把怎樣沉重的課業往他頭頂上壓下去,然而他還要偷出空來學作詩。《奇零草》自序說:「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為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為之。」張圭章於天啟四年中了甲子科的舉人,其時煌言五歲。接著他幾次北上會考,都沒有能夠考上進士,眼看年已半百,知已難有「金馬玉堂」的前程,只得轉向「謁選」捷徑,捐了一個刑部員外郎的散差,後來派得一個河東鹽運使司判官的職位。
大概他對河東鹽運確實有過一番努力,不久就又調署河北解州知府,他是帶了一家同到任上去的。
圭章在解州做官做到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年)辛未,他的老妻趙夫人就在解州任上忽然病故,此時煌言還只十二歲,從此就沒了母親。
圭章垂老喪偶,哀悼之餘,就此看破世道,不但不再續娶,鰥獨終身,而且距此不久,他就辭官歸里,從此在老家裡閉門課子,不問外事,一片血心就只注意在這個兒子身上。
果然,少年張煌言不負老父的期望,崇禎八年乙亥,他十六歲就在家鄉──鄞縣縣學中了秀才。
煌言的秀才考試,還有一段逸話:據說當時因為天下多故,崇禎皇帝詔令各省選拔童生,除照考經義辭章之外,還須加試射箭一道,目的在提倡文武合一的教育。不過事屬初倡,應考的童生平日未經這項訓練,無法認真,主試的官吏大抵都只虛應故事,有個名目罷了。但是,張煌言卻曾遵照功令認真練過,所以臨場試射,居然三發三中,贏得滿場的喝彩。
然而,人生的少年時期,竟是那樣多變。
煌言結婚很早,大約十八、九歲,便已娶了夫人董氏,二十歲上,生子萬棋。二十四歲,又生一女。
當他十八九歲時,平凡的讀書生活,已不能滿足他的精神活動,忽然有一種詭異的幻想,攫住了這青年人的好奇心理,他迷起道家所傳說的「黃白術」來,同時還一心一意地鍛鍊絕粒運氣的方法,辟穀求仙,鬧得本來不很結實的身體,奄奄一息,闔家的人環繞在他床前涕泣相勸,他才放棄了那些虛無縹緲的玄想。戊戌年他三十九歲,駐師舟山,作〈述懷〉二首,其一即是回念這段故事。有曰:
弱齡尚遐異,辟穀慕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誤煙火,塵鞅日以攢。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蕭然世外味,曾無九還丹?仙靈重名教,忠義固其端。所惡精已搖,何以生羽翰?神理或不滅,毋勞白玉棺?
然而,繼此而後的,他卻是糾合了一班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之餘,繼又縱情聲色,呼盧狂賭起來。煌言只為博取「千金一擲」的痛快,竟負下了一身賭債,逼得走投無路,終於偷出家裡田地產業的契據來,要想變價還債。
這樣子的事情,正如紙難包火,圭章先生立即發覺,激怒得拚命杖責這個敗壞張家門風的逆子,同時通知遠近親友,對他作了一個全面性的經濟封鎖。
煌言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是賭場的債主並不放鬆他一步,依然追逼得日甚一日。
幸而此時,他遇到了平生第一個知己:鄉人全美樟。
美樟字木千,號穆翁,他早就聽過煌言的故事,但是並未見過這個不齒於鄉黨的少年,恰巧在煌言這個最困難的關頭,他倆一見,穆翁便獨違眾論,慨然說道:「斯異人也!」
全家並不富有,但他為了救拔這個非常的青年,竟把自己所有的負郭良田,變賣了三百兩銀子,代他還清賭債,並且勸他慢慢地折節改行。士為知己者死,煌言終生服膺這位義友,後來他的獨生女兒許配給穆翁的次子,他們兩人也就成了兒女親家。他女兒追述她父翁二人的交誼,有曰:「督師(煌言)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穆翁)稍斂其芒角。」
日後,煌言在海上,全家俱賴穆翁照料,他又在黃岩預備了一個幽僻的住處,一心等待煌言萬一事敗歸來,可以避居,這種生死交情,自非尋常風義所能及。
後來康乾時代的浙東史家全祖望就是穆翁的同族侄孫,也就是煌言女兒的夫家族侄,因此,他對煌言別有一重親切的感情,窮畢生之力,搜輯遺文軼事,而且每年會集同文,舉行私祭,其因緣即在於此。
◇ ◇ ◇
煌言自此重理舊業,折節讀書,至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二十三歲時,以「八十二名寧波府鄞縣學增廣生」的資格,前往省城應考崇禎壬午一科的浙江鄉試。這一科鄉薦的經義題目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用其中於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子以容民畜眾」,「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天地之大德曰生」等。
壬午科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葵庵,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東滋陽人,而他的房考老師則是青浦人錢世貴,字聖霑,崇禎庚辰科進士,曾任浙江諸暨縣的知縣。
煌言就在這科考中了舉人。
煌言考試的成績很好,本房座師錢世貴不但對於他的文章大加激賞,而且竟從文字氣體上,看出煌言的風格和識見,以褚遂良的大節、宋廣平的堅毅相期許。這篇薦語,非常贍美。如言:「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性獨豔冶,此先輩於文章家神骨之外,兼登氣體,然必以茂美韶令為入格。此卷勢如驚鱗躍波,情如翔鴻接翼,步驟益閑,符采倍耀,取其章美,足以衣被天下矣。論開創微言,聲出金石,判比度,不失分寸。五策敷陳時事,條達通明,知為才識兼茂之士,佇看大受者也。」房考座師這樣推重,主考官的評騭也不尋常。
編修吳國華的批語是:「雅思雋筆,萬籟俱澄。」
左給事范淑泰的評語是:「不事高深,澹然自足。」
於是這二十三歲的生員,就在這次鄉試中了舉人。
中了舉的士人,除須準備赴京會試之外,為謀生計,有人坐教館,有人選編鄉闈卷子的名篇,交給書坊印成選本出售,收取編輯潤資,謂之「選政」,但選者也須薄有聲譽,選本才銷售得出去,如《儒林外史》中的馬二先生,便是替嘉興文海樓書坊精選三科墨程,居然也稱「選家」的便是。煌言中舉後,也曾搞過這玩藝兒,所編題曰「銘燕」,無非賺些潤筆,作為北上會試的盤纏而已。
照明代的科舉制度,鄉試的次年即為會試之期,各省的新科舉人,都要計偕入都,北上應考。大約煌言也曾於次年──即崇禎十六年遠赴北京應癸未科的大考。不過,這一次他卻並沒有考上。而且在他南返不久,就已爆發甲申國變,整個中國因李闖攻陷京師而全面動盪起來,烽火漫天而起了。十年後煌言追懷昔遊,有曰:
棄繻猶及到燕關,慘澹風雲十載還。狼鬣自從當日舞,龍髯能得幾人攀?漢陵弓劍存亡後,晉室衣冠興廢間。轉眼書生成故老,慚無媧石補江山。
他自幸拋卻儒冠、從戎救國以前,還來得及以一個新科舉人的身分參加禮部會試。此後,他就與飄搖的國脈同命,再無那樣從容的際遇了。
◇ ◇ ◇
煌言出生在萬曆朝的最後一年(一六二○年),天啟一代七年,正是他童年的黃金時代,然而明代的政治,卻就壞在這兩代皇帝──神宗和熹宗的統治之中,君昏政秕,閹宦擅權,把一座三百年的大明江山,直搞得天昏地黑,水盡山窮。等到崇禎皇帝即位,早已內憂外患,交相倚伏,流寇起於西北,女真盤據兩遼,烽火滿野,邊患連年,國家的命運,久在風雨飄搖之中,面臨崩潰的邊緣了。
崇禎帝初即位時,雖然極想奮發有為,頗有一番英明果敢的新氣象,懲除閹黨,任用清流;然而敗亂已入腹心,積重一時難返,加以崇禎求治心切,操持過激,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把握不住一定的方針,無論軍國大政的決策,內外臣工的選擇,都常常朝令夕改,忽起忽降,在位十七年間,秉政的首輔,就更用到二十餘人之多,朝局焉得不亂?而且,中樞的步調如此不穩定,又如何能望地方政治的修明,加以法令如毛,責望急切,譬如揚湯止沸,自然求治反亂了。而明末士大夫間盛行結黨的風氣,又使得崇禎對於他們個個都覺得可疑起來。既不能信任結黨的士大夫,生長深宮的皇帝,便很自然地重蹈了明室帝王傳統的痼疾,回頭專任太監,付以監軍、典鎮、理財等重任,把國家的命脈──軍隊和財政交到這班宦官手上,還有什麼希望,終於弄得人心離散,禍亂一經爆發,便不可收拾而終於覆亡。《明史.流寇傳》載李自成批評崇禎的話:「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實在是非常客觀的評論,不能以人廢言。這樣一個悲劇性格的皇帝,偏偏遇上這麼一個悲劇氣氛濃重的時代,天下怎得不亂!明室怎得不亡!
朝政如此,而地方政治的黑暗更甚。飢餓線上的農民,實在是流寇叛亂最大的資本。
明朝的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壓榨,異常苛刻,在官田的名目之下,皇族有皇莊,勳臣有官莊,這些莊田初還限於畿輔,後來遍及郡縣,竟占當時全國耕地七分之一的面積,這本來已是一種驚人的霸占了;何況管皇莊的太監,管官莊的豪僕,對於農民的敲榨剝削,又是無限的驕橫;地方官又任意派遣徭役,廢時失業,捐租重重,吸血吮髓,沒個休止,再加以崇禎年間的水旱蟲災,又遍地皆是。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農民,便個個抱著鋌而走險的思想,一有機會,無不參加叛亂。一股一股官逼民反的叛亂與暴動,必須用兵鎮壓,而官兵的兇殘甚於盜匪,酷吏的掊剋敲剝,又永無饜足,遂使一部分老實而不敢叛亂的農民,也不得不因逃避官家的逼迫投身「寇黨」,於是,「流寇」的勢焰日益旺盛,力量日益龐大,陝西的李自成終於成了滾雪球的中心,儼然成了農民叛亂集團所擁戴的闖王。
闖王攻入皇城,崇禎皇帝縊死煤山,偏偏吳三桂又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帶領清兵入關,終使中國臣民,淪於異族。
煌言的青年時代,就是這麼一個內憂外患交乘的痛苦的時期。
甲申國變後,煌言不能沒有「安得此身生羽翰,高摶橫擊待攀鱗」的苦悶。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南都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擁戴福王由崧即位南京,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當此危亡關頭,人人都有赴難之心,何況煌言。他曾於這年秋天,隻身跑到南京去了一次。然而當時的南都,朝中正士正被奸邪排斥,大權幾已全為馬瑤草(士英)、阮鬍(大鋮)所把持,金陵城中正瀰漫著招權納賄、腐惡荒淫的景象,以煌言這麼一個年僅二十五歲的新科舉人,自然一無際遇,「請纓無路」,空手而歸。
翌年,煌言曾因友人朱夏夫(兆殷)的介紹,去訪謁過紹興知府于穎。
穎字穎長,江蘇金壇縣人,崇禎辛未進士。他是守土有責的地方官,很有遠大的眼光,這時候,紹興籍的理學名臣劉宗周,已被馬、阮排擠,致仕回籍,于氏在任,當此動亂,事事請教於這位前輩,竭力作一切禦侮保鄉的準備。
煌言很受于知府的看重,兩人訂交自此。
他們暫時都只能憂心忡忡地靜觀時局的推移衍變。煌言回到鄞縣附近的駝峰山中,閉戶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