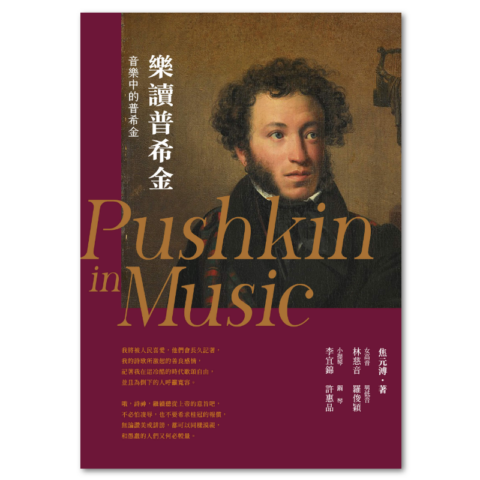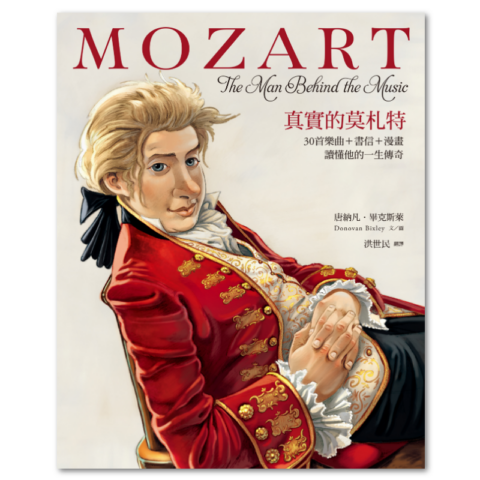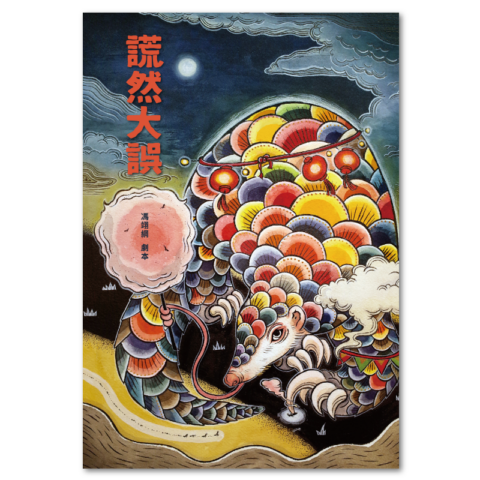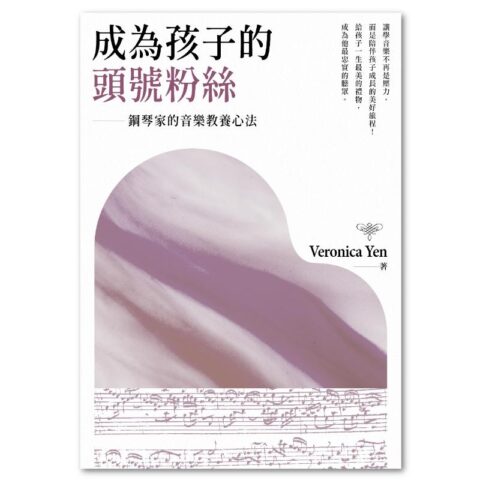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
出版日期:2024-05-02
作者:游靜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28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2.8 cm
EAN:9789570872965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電影是時代變遷的見證者!
本書重溯香港上世紀20至90年代的文化脈絡,
建構出香港電影中文化政治的史觀,
對昨日與今日的香港,提供不一樣的理解。
作者游靜爬梳大量原始資料,穿梭於電影個案解讀、影人自述,及時空政治脈絡分析;大歷史與微歷史之間,國、粵片兼論,細緻勾勒出香港百年璀燦光影,洞察歷史足印的偶然與必然,為華語電影研究、殖民及冷戰研究、香港文化研究,開創新天。同時提出關鍵探索及叩問:
▎對香港的思考成為協助反思其他華語文化歷史的資源。
▎作為華語電影世界的夢工場,香港電影的獨特貢獻在哪些方面。
▎香港電影史如何與文學史息息相關?
▎香港電影成為無權無勢的庶民抒解焦慮不安的重要場域。
▎李小龍的奮不顧身是香港傳奇的比喻。
▎香港主流道德價值曾經歷怎樣的翻新打造。
▎「大冷戰」與「小冷戰」如何影響香港電影發展?
▎香港電影史如何同時見證殖民治理與文化冷戰的軌跡?
▎資本主義現代性怎樣改造性/別關係,風月片如何展現反殖心結。
▎新浪潮電影如何叩問香港的冷戰前沿位置?
▎喜劇是香港夢的呈現?無厘頭揭示時代的壓迫、港式主體的反撲?
透過回顧香港電影史,進一步深思過去耳熟能詳的電影、人物、性別角色、文化歷史及其構成,體味今天華語以致全球流行文化,如何依舊從這份龐大深厚的歷史遺產中取經。
國內名家一致推薦
王君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副教授)
井迎瑞(前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
李焯桃(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董事局主席、M+香港電影及媒體外聘策展人)
林文淇(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教授、台灣電影研究中心主任)
重點就在括號裡(影評人)
張小虹(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
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
馮美華(獨立藝文工作者)
黃建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
聞天祥(影評人)
羅卡(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特约研究員)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序)
好評推薦
很喜歡游靜老師談楚原導演以及李翰祥導演一段,當時年紀輕,看完只覺得輕浮。經老師分析,深感我當年真是大錯特錯。──重點就在括號裡(影評人)
構越香港電影70年發展,游靜以不同的史觀,為主流華語片論述,作出新平衡。也凸顯了港產作品的豐富性。 ──黃建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
原以為香港電影「這麼近」,本書卻能讓我們看到「那麼遠」。拜讀完,香港於我也有了更複雜的情懷與意義。」──聞天祥(影評人)
(推薦語依推薦人姓氏筆劃排序)
作者:游靜
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學士、紐約社會研究新校媒體研究系碩士、紐約惠尼藝術館藝術創作獨立研讀課程畢業生、倫敦大學皇家郝露威學院媒體藝術系博士、夏威夷大學洛克菲勒獎助人文學科博士後。曾主編香港《電影雙週刊》,並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著有《另起爐灶》、《裙拉褲甩》、《性/別光影: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史前紀》、《大毛蛋》、《我從未應許你一個玫瑰園:香港文化政治生態》、《游於藝》、Filming Margins:Tang Shu Shuen, a Forgotten Hong Kong Woman Director:編有《性政治》、As Normal As Possible: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等。詩集《不可能的家》獲2002年香港文學雙年獎詩組推薦獎。電影及錄像作品曾入圍臺灣金馬獎、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展等。《好郁》榮獲葡萄牙費加拿霍斯電影節影評人大獎、《流》榮獲日本視象論壇評審團特別獎等。
第一章 姊妹家國:雙重現代性
第二章 荒江女俠:江湖的南遷
第三章 孤島天堂:人間的重生
第四章 南國人情:中聯的多快好省
第五章 進退兩難:愛國的黑線
第六章 冷戰熱血:玫瑰的青春
第七章 李小龍傳奇:(反)殖民欲望與毀滅
第八章 風花雪月:李翰祥的回眸
第九章 香港新浪潮:英美語系的新成員
第十章 富貴時代:喜劇之逼人
第十一章 屎尿屁主體:無厘頭的反撲
中英文參考書目
自序
本書以電影歷史切入,重溯香港上世紀三十至九十年代的文化脈絡,希望藉著重構香港電影文本及文化政治的史觀,對昨日與今日的香港,提供不一樣的理解。
全書維度橫跨近八十年,企圖更有系統地審視香港電影作為上世紀文化生產的重要場域,剖析不同時代階段、電影類型、不同政治背景影人的承傳與參與,並非以整合、誇言全局的視點出發,而是選擇以顯微鏡下的歷史碎片拼湊出,一幅幅既有矛盾糾結也有傳承演化的香港電影圖像,綜述並解讀每一幅的當代政治意涵及之間的關係,從而體味今天華語以致全球流行文化,如何依舊從這份龐大深厚的歷史遺產中取經。本書以文化歷史為經,以論述分析為緯。為避免概論式流於虛泛的敘述,本書著重具體案例細讀,及案例與案例之間的承傳、變異關係,組成的論述與對話。案例涵蓋同時代、跨時代或跨地域不同電影文本之間的對照、文學與電影改編之間的對話,同時不忘討論影星與導演作為電影「作者」的貢獻、電影公司的理念與出品的時代意義,及一些持久的類型電影淵源。書中以不同時期具代表性的實例,粵語、國語片兼論,從而顯現香港電影的多元豐富面向,讓不同種類的資料構成的敘事顯得更具體生動,展現切入與解讀電影歷史的諸種方法、不同方法的組合與相互補足的可能。透過進一步深思香港過去耳熟能詳的電影、人物、文化歷史及其構成,也許能夠加深了解這城走過來的步履,及如何走到今天的過程。
我生於六十年代香港,是戰後的第二或第三代,成長的資源遠比家中姊姊或哥哥充裕。整個童年都在公共屋邨度過,並沒有體驗過父母來港初期住在山邊木屋與板間房的生活。至母親去世前幾年,透過與她斷斷續續的訪談,才發現家人盡經歷過《一板之隔》(一九五二,朱石麟)、《危樓春曉》(一九五三,李鐵)、《木屋沙甸魚》(一九六五,黃鶴聲)中的場景。從中國大陸隻身逃來,熬過最艱難的十多年難民期,他們心中的倖存與危機感,伴隨他們一生。在朝不保夕的環境下求存,並沒有紀錄生活的餘暇與心情,但我父親在抽屜最角落處一直埋藏著一部沉甸甸的照相機,那個黑色皮囊大概包裹著他們在廣州黃金時代的記憶。
電影成為重新認識我出生前的家、我出生前的香港的最重要路徑。據母親憶述,父母在四十年代廣州拍拖時,看的都是國語片。難怪童年僅有幾次看電影的記憶,都是被母親帶去看《蘇小小》(一九六二,李晨風)及《梁山伯與祝英台》(一九六三,李翰祥)等國語片。應該是一個字都聽不懂,但四十多年後,仍然記得銀幕上白茵與江南風光相互映照、凌波與樂蒂服裝相襯的顏色,與母親從戲院內哭到戲院外,半天總是眼眨淚光的無言。看電影是我與她難得獨處的時光,也是她與自己獨處的時光。疑似共同分享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用說破。這便是電影。
童年時模仿黑白電視上的女殺手與黑玫瑰,肯定是我最早的性別教育。戲院放《唐山大兄》(一九七一,羅維、吳家驤)與《精武門》(一九七二,羅維)久不下片,父母在家有事要辦,給哥哥一手零錢,遣散他帶我去看。只看到李小龍真笨。可見我自小便對肌肉男沒好感。初中時迷上的《長腿姐姐》(一九六○,唐煌)、《星星.月亮.太陽》(一九六一,易文)等,給予最速食的民族意識培訓,想像一個終於脫離苦難期的現代中國。
所以我這一代完全是冷戰的產物。殖民地給現代華人提供了避秦之地。母親以左右兩方建構的前現代中國憶悼她的過去。我被推進殖民地教育機器,迅速學習看外語片;姊姊拍拖看占士邦(臺譯:龐德)帶上我,反正有男的買單。至我賺到自己的零用錢,就一頭栽進歐日藝術電影堆中。抬頭,新浪潮導演出道了,他們的美學與風格,中介的歐美日電影教育,也在書寫我。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集體宣言寫在屏幕上,我們對於這時代,有話要說;七十年代流行的功夫與風月,不足以表達這社會,不足以表達「我」。
八十年代後期,從港大畢業,應金炳興之邀,為香港《電影雙週刊》出任執行編輯,後接任總編輯。當時新浪潮氣勢已過,但影響還在。現在回看,如果不是新浪潮,我大概不會視出國念電影為當時唯一志願。後來在倫敦大學攻博,論文選擇以唐書璇為題,大概也跟十年前的《電影雙週刊》經驗有關。出國前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負責文宣工作,與電影部主管黃愛玲朝夕相對,孕育了往後三十年,亦師亦友的因緣。
二○○二年博士口試剛過,獲愛玲邀稿,參與國泰/電懋專題研究,於是開展了我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合作。本書中第八章的初稿,是應愛玲策劃《風花雪月李翰祥》(二○○七)專題而作。第一章及第四章的初稿,寫成後的第一位讀者,也是黃愛玲。若非愛玲持續督促、鼓勵,這個橫跨二十年的計劃,不可能長成今日的面貌。自從她去了不再需要書的地方,雷競璇先生饋贈愛玲珍藏的資料,這些一直貼身陪伴我,彷彿她仍在耳邊叮嚀,必須脫離與超越人云亦云,包括過去的我,各種定見與謬誤。
感謝過去十年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夥伴:郭靜寧、吳君玉、陳彩玉、華哥、傅慧儀、吳若琪,惠賜研究及講座上的支援。本書第二章及第十章初稿曾收錄於香港電影資料館《探索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香港電影》(二○二二)及《創意搖籃—德寶的童話》(二○二○)專書中。第三章與第五章中的部分段落,曾於電影資料館出版的《尋存與啟迪:香港早期聲影遺珍》(二○一五)、《李萍倩》(二○一八)上發表。謝謝上述刊物的所有編輯及校對付出的心血。
書中的大部分內容,為我在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工作時構思;謝謝九年來關照我的陳清僑、墨美姬(Meaghan Morris)、許寶強與羅永生。此書得以定稿,感激近年在臺給我家的感覺,各兄弟姊妹的扶持:陳若菲、吳靜如、司黛蕊(Teri Silvio)、郭力昕、白瑞梅(Amie Parry)、林建廷、宋玉雯、陳祐禎、黃道明、廖偉棠、曹疏影。特別感恩如天降甘露般、多年來對我不離不棄的(前)學生與助理們:蕭美芳、洪榮杰、陳浩勤、姚偉明、黃誼綝、羅冠杰、鄭晴韻;尤其感謝蕭美芳犧牲一整個暑假,不厭其煩反覆查核勘校書中引述的文字及影像資料;沒她的兩脇插刀,此書面世肯定是綿綿無絕期。
謝謝陳曉婷及蕭淑芳分享香港圖書館資源;雷競斌先生幫忙購書;楊小賢在查找電影資料方面一而再的協助。謝謝Raymond Tsang及Tom Cunliffe對第四章英文稿修訂過程中的支持、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謝謝羅卡叔叔多年前接受我的訪問、上海大學王曉明老師的啟發與提點、劉成漢先生接受我的筆談、小思老師多年來的鼓勵。書中第三、四、五、六、七、九、十一章,以及全書的重新修訂改寫,為過去三年在臺灣與疫情搏鬥下,在病隙及工餘課餘擠出來的成果,在此感謝漢學研究中心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慷慨提供研究資源,尤其是黃文德、陳相因、葉毅均、歐陽及蔣宜芳小姐的真誠協助;王君琦與楊小濱撥冗主持講座。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同仁的指正激勵,及《電影研究的方法及議題》、《流動影像中的政治》、《英國殖民現代性》等課上與同學的熱烈討論,為滋養寫作的泉源。
聯經出版公司逸華兄如定海神針般多年來對這計劃的信任、耐心與溫柔的鞭策;主編孟繁珍小姐的鍥而不捨及細緻包容,叫我不得不擠出吃奶的力,為求有所交代。最後得謝謝本書論及的所有導演及作品,是您們對香港奮不顧身的再現與論述,提供給本書反思歷史、反思來路的條件。給最早帶我看電影,讓我陪哭的母親。感謝Polly的照顧、dnf的同行。
本書中提及的電影,在第一次出現時,除非其他背景資料如電影公司或主要工作人員如編劇等為本書討論對象也會一併列出外,基本上資料格式如下:《片名》(出品年分,導演);引文中提及的電影如資料不全,則儘量在註腳中補遺。礙於篇幅、個人能力與體力,本書只能討論浩如煙海的香港電影歷史中極其微小的部分,必有疏漏,一切文責自負。一如周星馳的至尊寶執意介入歷史又悟其無法逆轉,或李翰祥至尊寶的處變不驚:「操那,嘎小個」(1);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游靜
二〇二三,炎夏
台北、香港
李小龍傳奇:(反)殖民欲望與毀滅
一個經過訓練的好演員如今非常難得—需要他真實,做回自己。對我來說,演員是他自己所有的總和—他對生命的高度認識、合適和良好的個人品味、他樂與哀的經驗、他的激情、他的教育背景,還有更多更多—如我所說,是他所有的總和。再多一個元素便是:一個演員在特定情況中必須如其所願地表現自己。
我,李小龍,將會成為第一個美國片酬最高的東方超級巨星。作為回報,我將以自己身為演員的能力,給予觀眾最刺激、最高品質的表演。一九七○年開始,我會名揚世界,此後直到一九八○年年底,我將擁有一千萬美元的財產。我將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並達到內心的和諧與快樂。
李小龍憑藉自身苦練的「功夫」,成為第一位讓香港電影成功打進美國及全球市場,並把功夫文化帶至全世界的國際巨星。他在武術電影與功夫文化的地位,在他逝世已經五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沒人能超越。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他視為香港電影甚至中國文化的代名詞。
過去對李小龍傳奇及其所衍生議題的研究,粗略可以分為下列幾個方向:李小龍的明星形象作為作者,及其製造的文化論述;他製造身體景觀的視覺快感與感官意涵,對武術/功夫動作視覺呈現的革新創造、表演武術/功夫及製作武術電影中強調的身體真實性(authenticity);他創立的截拳道如何把武術與哲學糅合,對武道/藝/意論述化的貢獻;對數十年全球青年文化,包括但不限於亞洲及新好萊塢電影、歐美搖滾樂及嘻哈,持續深遠的影響及被再生產,與在第三世界及弱勢族群中作為反帝國主義抗爭符像的標誌性地位,尤其是對美國黑人、南美、中東及亞裔文化的啟發加持,以他作為一種方法;在家國主義、中國性及陽剛性之間的協商;武術/功夫與中國及亞洲社會邊緣性的關係,等。本章受益於過去豐富的功夫研究成果,除了討論李小龍一九七○年從美國回到亞洲後參與的四部半電影:在泰國拍攝的《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一九七二,李小龍)、與美國華納合作的《龍爭虎鬥》(一九七三,羅伯特.克勞斯),及沒完成的《死亡遊戲》(一九七八,李小龍、羅伯特.克勞斯)外,也企圖重新連結李小龍的武術生涯,跟他的家庭成長背景,他的童年與少年經驗;他赴美前、在美與回港後的演出,期能更脈絡化地審視李小龍所呈現的現代「中國」武術,他所呈現的「武」,如何與香港親左電影、殖民陽剛性與欲望不可分割,又如何被當時的全球地緣政治所建構及轉化。
透過重溯李小龍一九五九年即十八歲赴美前在香港的成長經驗,童年與少年期間拍的電影,與後來回港拍的電影,兩段歷練之間的關係,從而思考他身上,他中介、移置並創造的話語及文化遺產中,顯現的香港與中國現代性,及其演變。如果說武俠片是把中國文化中一種源遠流長的想像,一種普及的文化符號,重新翻譯進現代社會的媒體,李小龍作為武術功夫片的代表人物,不單是企圖把「武」這個文化符號,翻譯進現代化的殖民地香港,更要借香港作為橋梁,在冷戰氛圍下翻譯到歐美。他以身體打造的極端陽剛性作為工具,把香港在他身上刻墾的殖民欲望,拚了命翻譯成美國夢。作為一個全球媒體符像,在他苦心經營或不經意凸顯出來的文化衝突與矛盾,甚至於過世後歷久不衰的影響力,一方面凸顯香港電影散發的殖民現代性魅力,另方面也可見香港在冷戰現代性氛圍下,看似享盡優勢實則被榨乾榨盡的艱難處境。
跟二戰前後出生的大部分香港小孩不太一樣(如他演出過的大量貧困兒童角色),李小龍家境並不貧困;父親在香港擁有多棟物業,在順德及廣州也繼承祖居,事業在二戰期間幾乎從沒中斷,母親家勢更是顯赫而且複雜。跟二十世紀香港出生的大部分小孩一樣,李小龍的家庭與教育文化背景混雜。他的整個創作與生命歷程可以說是在協商與糅合,他中介的華南與上海(9)風格,又同時作為英屬殖民地產物的多樣文化身分。他在香港日據時代及戰後的童年、在美國初出茅廬的經歷,至七○年從美回港發展時,香港早已歷經冷戰世代,面對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媒體美國化,一九六七年騷亂後更正式進入去政治化、急速壓縮的資本主義階段,這些文化脈絡,如何協助孕育出李小龍這個媒體符像?我更企圖進一步詰問,這些元素,是否也可能導致李小龍肉身的難以持續(unsustainability),只能曇花一現?
.混血現代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小龍出生在舊金山唐人街東華醫院,起名李振藩。美國產科醫生為這個男嬰起了英文名字Bruce Lee。他父親李海泉是香港粵劇名丑,當時正在美國巡迴演出;母親何愛瑜是何甘棠與中俄混血兒情婦張瓊仙所收養的中歐混血兒(另一說是何甘棠的私生女),自小生活在上海,十九歲時來港。何甘棠為港澳地區華商首富何東爵士同母異父之弟,也是香港著名買辦,在港自建大宅「甘棠第」(一九一四年落成,香港法定古蹟,現為孫中山紀念館)。李小龍這個作為(四分之一)混血兒的背景,成為他日後學業與事業的絆腳石:在美國被指「太中國」,在跟葉問學武期間也被同門告發他血統不正,聯合起來向葉問施壓,揚言如果不把李小龍趕出去就不繳學費。葉問迫於無奈,只好讓李小龍離開武館,並暗自授意個別徒弟黃淳樑、張卓慶等私下與李小龍練武。(10)這個背景,也許不得不造成了李小龍在日後的武術與電影作品中,將不斷要證明及展演他中介了的中國性。而且,李小龍的性別長成又跟他的種族成分同樣麻煩。李海泉與何愛瑜的第一個兒子,出生後不久夭折了。為了騙過專門吸食男孩魂魄的「金甲神」,父親特意替李振藩打了耳洞戴上耳環,並起小名「細鳳」。李小龍窮盡一生精力為自身打造,並需要不斷維繫與展演的超級陽剛性(hyper-masculinity),有多少是為了擺脫華南父權傳統對陽剛的壓抑?
李振藩在美出生,只是因為父親剛好在美登臺。李振藩三個月大的時候,活躍於香港及美國之間的導演伍錦霞,正在舊金山拍《金門女》(Golden Gate Girl,一九四一),剛好需要一個幼年王萊露的嬰兒鏡頭,這是李振藩第一次登上銀幕,也可以說是扮裝演一個女嬰。電影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美國上映。一九四一年一月,美國「一九四○年移民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規定出生於美國的人都可以申請為美國公民。這一連串的巧合決定了李小龍,將會到美國學習並最後成為好萊塢巨星這命運。李海泉的演出結束後,待取得了李振藩的出生證與美國移民,及歸化局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頒發的「美國公民出埠回國證書申請書」後,一家三口在四月六日乘船,五月中旬回到香港。
一九四○年的香港,收容了許多大陸逃避戰爭的難民,衛生條件很差,秋天爆發霍亂。李振藩回港後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場,接近死亡邊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攻陷香港,香港進入了三年八個月的淪陷時期。日本占據香港期間,影人紛紛倉皇逃生,拒絕與日方合作拍片。香港淪陷時期並沒有產出電影。李海泉為保一家性命,為日本人演粵劇。
.階級啟蒙
可能是遺傳或環境的因素,當我在香港學習的時候,對電影製作產生了濃烈興趣。〔……〕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真正的中國文化。我被它深深地吸引著,而且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環境對塑造人的性格和品性的深層次影響。〔……〕
李振藩自幼在家看父親教導徒弟演戲,耳濡目染,偶學一招半式,而且生性活潑、精力旺盛,最喜歡看連環畫,經常逃學去打架滋事;光小學五年級就讀了三年。一九四八年,李海泉答應讓難以馴服的兒子在《富貴浮雲》(一九四八,俞亮)一片中演一小角;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間,李振藩以李鑫、小李海泉、新李海泉、李敏等藝名參與拍攝了《夢裡西施》(一九四九,蔣愛民)、《樊梨花》(一九四九,畢虎)、《花開蝶滿枝》(一九五○,俞亮)等。當時由中國崑崙影業公司出品、改編張樂平漫畫的《三毛流浪記》(一九四九,趙明、嚴恭)正在香港上映,票房報捷。於是製片商想照辦泡製粵語片《細路祥》(一九五○,馮峰),同樣以社會邊緣兒童的遭遇描繪當下香港民生。《細路祥》是漫畫家袁步雲筆下的人物,先在報刊連載,後結集成書,戰前已流行於粵港。但要找到一個會演戲、年紀與漫畫人物細路祥相仿的童星並不容易。當時籌備電影的編劇左几、導演馮峰與原作者袁步雲遍尋不遇,直至他們在李海泉家遇上十歲的李振藩,才敲定人選。這位以李龍作為藝名的天才兒童,成功演活了一個父母雙亡、初時失學後來可以上學也不肯上、肚子餓就偷燒鴨吃的壞孩子男一號,還特別在偷了燒鴨後,在鏡頭前表演一個他在叔伯們那裡學來的連續側手翻。電影叫好叫座,叫他初嘗當主角的滋味。《細路祥》後他改名李小龍,從《人之初》(一九五一,秦劍)開始,參加演出一連串探討社會問題的親左或寫實主義電影,包括《苦海明燈》、《千萬人家》、《父之過》(一九五三,孫偉)、《慈母淚》、《危樓春曉》、《兒女債》、《愛》與《愛》續集(一九五五,王鏗、李鐵、李晨風、吳回、珠璣、秦劍)、《孤星血淚》(一九五五,珠璣)、《孤兒行》(一九五五,錢大叔、李佳)、《守得雲開見月明》(一九五五,蔣偉光)、《早知當初我唔嫁》(一九五六,蔣偉光)、《詐癲納福》(一九五六,蔣偉光)、《甜姐兒》(一九五七,吳回)、《雷雨》等,最後離港赴美前拍下《人海孤鴻》(一九六○,李晨風)。包括《金門女》在內,李小龍的童年與少年時期一共演了二十三部電影。
.受創陽剛
新一代男性如何超克上一代的折損陽剛性,是五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共同命題。初到美國時,李小龍嚮往歐美白人陽剛性,同時對自己難以融入表現焦慮。眾所周知,李小龍拒絕替好萊塢演那種身穿唐裝、雙眼畫成斜線、身後掛一條小辮子、歐美主流文化中標誌著黃禍恐懼的華人男性形象。二戰後美國白人主導的流行文化中,唯一可以被接受的東亞臉孔只能是日裔(最好是檀香山日裔);日本是在冷戰地緣政治下最服膺美國的東亞國家,而中國只能被再現為前現代、備受毀滅的符號,從而反襯出美國作為優越現代性霸主的地位,所以李小龍在電視劇《青蜂俠》(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中被安排演日裔的青蜂俠僕役副手。童年時經歷過太平洋戰爭、從小受殖民教育、練就一身功夫並早已在粵語片中嶄露頭角的李小龍,當然覺得深受委屈。香港無綫電視買下《青蜂雙俠》(後來改名《青蜂俠》)並作為配音片集推出,安排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逢周六播映。根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無綫電視發布的節目介紹看來,劇集上映時無綫電視甚至不知道這位演青蜂俠助手的,就是從前的粵語片演員李小龍,反而把他的名字譯作「寶士.李」。
李小龍低估了好萊塢作為意識形態機器把外來文化—尤其華人—他者化的能力。不無諷刺的是,當李小龍不惜輟學,搬到洛杉磯一心要打進好萊塢時,好萊塢卻對他不屑一顧,只給他出演這種鞏固文化二元論及美國白人優越主義的角色。顯而易見的是,好萊塢無法也不懂處理與呈現,像李小龍這樣的華人陽剛身體,作為一種具有主體性及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物。至他幾年後回港,在電影中不斷戰勝日本與白人男性,打破了亞洲大部分票房紀錄後,好萊塢才回過神來,要邀請他簽約。而李小龍的身體,以爆破式速度成為全球受壓迫(異類)陽剛性,表達冷戰創傷的抗爭代言,正正凸顯了好萊塢長期製造又無視這些龐大的非正典(歐美)市場需求。李小龍最後一部出演的好萊塢電影(也是李小龍完成的最後一部電影)《龍爭虎鬥》中,李(李小龍)的對手韓(石堅),實為一個類傅滿州型人物,旨在凸顯現代中國性的腐敗兇險且不脫封建(奴役婦女、販賣鴉片),反而美國白人高手羅柏(約翰.薩克森)因為道德高尚拒絕被韓收買,成為李的戰友。片末韓及其手下被收拾乾淨後,電影特別安排李與羅柏對望,李豎起大拇指向羅柏比個讚的手勢,羅柏也做一個回敬李的表示,以重申美國現代性於維持世界秩序中的關鍵位置,把李小龍的身體收編入一個冷戰文本中。片中演配角的成龍、洪金寶、元華、元彪、劉永及演李小龍徒弟的董瑋等,亦預示了香港武俠功夫片傳統繼李小龍後的延續。
.武術英雄
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猛龍過江》,是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在歐洲取景的影片,當年打破了東南亞幾乎所有地區的票房紀錄。電影的高潮設在古羅馬競技場(鬥獸場),李小龍單人匹馬與國際空手道冠軍羅禮士決鬥。本書第二章提到,武俠片一大特色可以說是強調身體、尚武精神與自然風土三者間的關係,也同時需要把這三種元素(及其組合)景觀化;自然風土是俠士逍遙自在、不受約束的外在呈現,也是確認俠士精神與武藝的殿堂。對在戰後香港成長、沒「鄉」可回、自少在天主教會學校(香港稱「貴族學校」)讀書、深受殖民都會現代性洗禮的青年李小龍來說,古羅馬競技場,就是讓他心生敬畏、可以作為確認並協助景觀化他的精神世界與武藝的殿堂,他的「自然風土」。這個位列中古世界七大奇蹟、被認為是歐洲古文明的標誌性建築物,不但是古典時期帝皇展示權力的象徵,也是角鬥士展現武藝、狩獵及戲劇表演、奴隸爭取自由的場所。不僅如此,古羅馬競技場在天主教傳統中,也有非比尋常的宗教意涵。約在六世紀末,競技場內部建築了小教堂;自一七四九年,競技場作為文物受保護,是因為早年有基督徒在此殉難,故宣布其為聖地,也成為近現代羅馬天主教舉行儀式的場所,包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生前每年都在此紀念殉難烈士。十八世紀時教宗本篤十四世,從古羅馬競技場開始「苦路」(Via Crucis/耶穌上十架前的一段路)行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古羅馬競技場再次在人們的視野中出現,正因為教宗聖保祿六世在一九六四年恢復了這項傳統。李小龍千辛萬苦選擇這裡作為他編導電影的最重要場景,他想像的那種武術英雄主義,其中的悲壯或自我犧牲情緒,是必須與歐洲文明—尤其與當中的天主教及其苦行傳統—接軌的。
一九七○年八月十三日,李小龍在鍛鍊時沒做充分熱身,扛著一百二十五磅的槓鈴做「體前屈」時,嚴重傷及腰部,檢查後醫生診斷為第四腰椎神經永久受損。醫生告誡他不能再踢腿。他在床上躺了三個月後,無法接受自己為永久性傷殘,自此他將長期服用止痛藥。這時候李小龍還不到三十歲,電影事業才剛起步。在往後出版的李小龍著作及他妻子琳達寫他的傳記中,可見他對自身的體能訓練,要求嚴苛,強迫自己鍛鍊身上每一寸肌肉,即使身體受重創後仍從沒鬆懈。在拍攝華納兄弟公司製作的《龍爭虎鬥》時,李小龍的腰傷並沒有痊癒,以致拍一些尤其強調腰腹力量如後空翻、側手翻接後翻飛騰過人牆等高難度動作時,有著腰傷的李小龍需要借用替身元華來完成動作。為了演出時減少衣服上的汗印,讓他的動作拍起來更好看,他進行了移除腋下汗腺手術。拍攝《龍爭虎鬥》期間工作過勞,據載至少有七次以上頭痛發作,需要暫緩,甚至有一次昏倒在錄音室,數小時不省人事。這次倒下後約十星期,他就一睡不醒了。
為了擺脫華人陽剛焦慮與創傷,拒絕面對自身的局限,一生刻苦耐操,仰望成為好萊塢巨星,贏得美國主流市場的垂青;李小龍奮不顧身、追求完美與目標的意志、無邊的渴望,成就了他的英雄傳奇,也協助製造了他曇花一現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