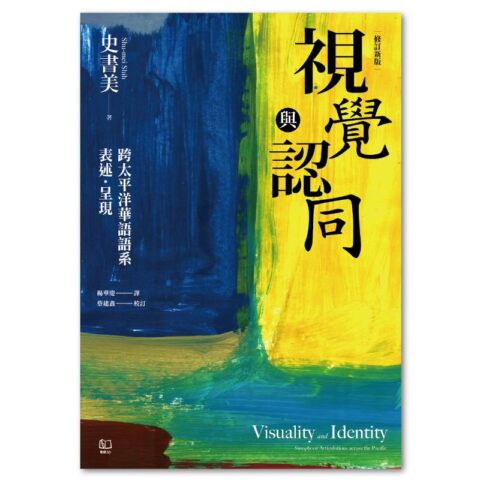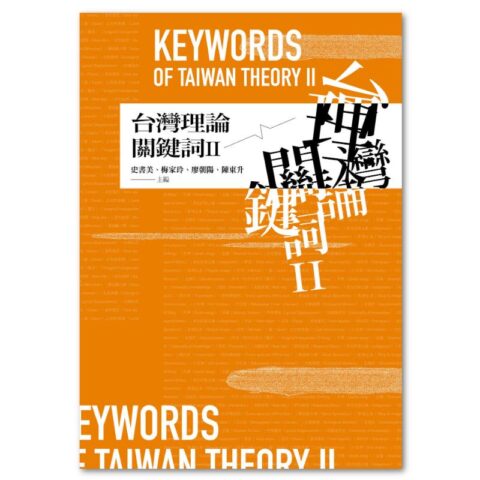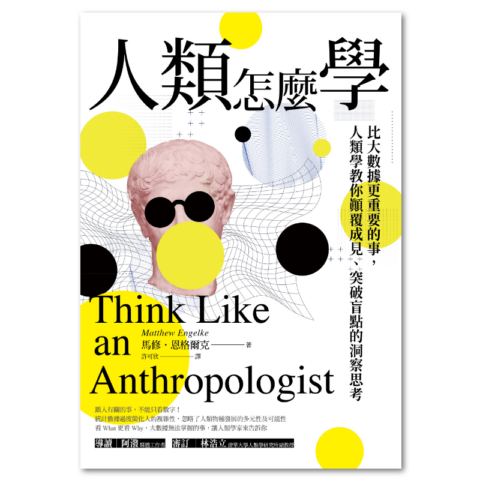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
出版日期:2007-07-02
作者:大木康
譯者:辛如意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17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1597
已售完
本書介紹明末清初的歷史上著名的綺艷之地,秦淮八艷的故址、《桃花扇》的舞台——南京秦淮。此地在晚明時,有連街的豪奢華樓、國色天香的美女群芳爭豔。秦淮河對岸的江南貢院,每隔三年舉行鄉試科舉,江南地方的才子莫不雲集於此。在秦淮這個香艷的舞台上,誕生了侯方域與李香君、冒襄與董小宛等膾炙人口、傳頌千古的浪漫故事。
言及明清文化史,青樓文化是不容忽視的一環。本書聚焦於南京秦淮的青樓,就秦淮的歷史、秦淮居民的生活、秦淮的四季、秦淮的選美活動、秦淮文學等各種相關的角度,解讀這個特殊時空環境的文化。作者曾經單手拿著古地圖,實地造訪秦淮,嘗試在現代風景中發掘四百年前的文物風流。另外,例如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諸多日本文學名家,也都曾經傾心於南京秦淮的浪漫風流,創作出許多與秦淮相關的文學作品,本書對此也做了詳盡的介紹。
通過此書,四百年前的秦淮河畔的綺旎風光,彷彿又在眼前重現。
作者:大木康
大木康(OKI, Yasushi),1959年出生於日本橫濱。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廣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攻中國明清文學、明清江南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遊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東京:青土社)、《馮夢龍《山歌》研究》(東京:勁草書房)、《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福岡:中國書店)等書,及其他相關論文多數。2006-2007,於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開設「明清文人專題研究」、「晚明文學與出版」、「中日比較文學」、「日本漢學研究」等課程。
譯者:辛如意
臺北市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名古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所碩士,同研究所博士肄業。喜愛閱讀、翻譯文學作品,譯作包括《我的箱子》、《川之光》、《狐笛的彼方》、《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空色勾玉》、《風神祕抄》等書。
序章 日本文學中的秦淮
1芥川龍之介《南京的基督》
2谷崎潤一郎〈秦淮之夜〉
3佐藤春夫〈秦淮畫舫納涼記〉
4永井禾原《來青閣集》
5《板橋雜記》與江戶洒落本
6成島柳北的《柳橋新誌》
7回顧明末秦淮的時光之旅
第一章 土地的記憶——秦淮前史
1秦淮河
2六朝金粉
3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
4唐代的秦淮
5南唐之都
第二章 秦淮遊廓的形成與興衰
1明朝建立與富樂院
2十六樓
3舊院
4明末的秦淮
5舊院的位置
6舊院焚毀與秦淮沒落
7清乾隆年間的秦淮復甦
8太平天國造成的破壞與重建
9民國時代的秦淮
第三章 遊步秦淮
1邂逅秦淮跨橋
2秦淮的河房
3夫子廟(學宮)
4南京貢院
5書店街
第四章 舊院妓樓一瞥
1美的極致
2《水滸傳》裡的妓院
3酒菜與精品
4妓院結構 —— 李香君的閨室
5香君故居
6關於妓院匾額
第五章 妓院人物百態
1妓女
2鴇母
3ㄚ鬟與保兒
4教坊司
5幫閑
第六章 妓院的遊樂
1找樂子的步驟
2妓女的技藝
3尋樂指南
第七章 秦淮的四季與習俗
1秦淮春和
2秦淮盛夏
3秦淮秋涼
4秦淮初冬
第八章 姑娘的選美競賽與花案名次
1花案
2妓女與遊行盛會
3秦淮的花案
4妓女的花案名次
5秦淮妓女的嬌美
6《金陵百媚》
7狀元董年
第九章 秦淮名妓與遊客列傳
1秦淮名妓群芳譜
2秦淮遊客列傳
第十章 秦淮文學
1余懷的《板橋雜記》
2《秦懷詩鈔》
後記
參考文獻
附錄論文:馮夢龍與妓女
大木康序
我1975-76年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選修了京都大學佐伯富教授一門關於中國鹽業史的課程。每次上課時,佐伯教授總是恭謹地將一方精緻的深色「風呂敷」置於講台上,像茶道儀式般,有條不紊地打開方巾,取出講義,開始當日的授課。像是中國的儒者或當代西方紳士的訓練一樣,佐伯教授對穿著的禮節也非常重視,再熱的天氣,授課時也堅持穿西裝、打領帶,一次竟因此中暑昏倒在課堂上,引起一陣騷動。我對佐伯教授當年授課的內容已毫無印象,但對他如儀式般揭開方巾,和中暑昏厥的場景,卻記憶猶新。
十年後,我在赴美國留學途中,在東京稍作停留,並前往東大東洋文庫拜訪田仲一成教授。在田仲教授的引領下,參觀了仁井田陞的收藏,算是象徵性地進入了日本漢學的殿堂。此後幾年,為了應付系裡的學分要求,我第三次從日文一開始,密集地選修日文課。對我和大部份以中國史為專業的美國同學而言,和伶牙俐齒、能言善道的哈佛大學部學生一起牙牙學語的過程,除了徒增挫折感和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外,日文老師高效率的組織教學,顯然並沒有為我們的日文閱讀能力,帶來脫胎換骨的轉變。但另一方面,我從我的指導教授Philip Kuhn的第一本經典著作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看到他對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的介紹和推崇,開始對鈴木中正等人對清朝社會史和民眾叛亂的研究,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因為研究所需,進一步閱讀了秋月觀瑛、窪德忠、福井康順、酒井忠夫、田仲一成人關於中國佛教、道教、善書和戲曲的研究。
現在回想起來,我第一階段密集的日文訓練和對日本漢學的涉獵,其實和我的美國經驗密不可分。而美國漢學界對日文和日本漢學的重視,除了日本漢學在二十上半葉的突出表現和累積的學術傳承外,和二次大戰後,美國漢學的初創萌芽、中國的再次閉關自守及學術傳統的中斷,顯然都有極大的關係。1950-80年代中國的鎖國和學術研究的僵化,切斷了美國學者赴中國蒐集資料和田野考察的主動脈,也大大降低了美國學者對中國學術研究成果的需求,日本的資料收藏和研究成果則佔據愈來愈重要的位置。
從1990年左右,我對日本漢學研究的認識,有一段長時間的停滯,其中除了語言障礙、時間不足等因素外,大環境的改變和研究領域的移轉,也都很有關係。中國的開放,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對日本漢學的地位及美國漢學中的日本因素的影響,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問題,我在此僅能提出此一印象式的觀察,而無法深論。但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研究領域從社會史轉向文化史和明清的士大夫文化及城市生活,卻顯然是我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未能持續關注的主要因素。我過去稍有涉獵的日本學者對明清社會經濟、宗教及民眾叛亂的研究,代表的是日本(及美國)中國研究的主流學術傳統,和我對明清文人文化的新嗜好,顯然有極大的距離。
在我這個由俗而雅,從現代到明清的文化轉向中,乾嘉學者和當代中國大陸學者所作的詩詞戲曲的考證、詮釋、年譜編纂和研究論著,提供了基礎而關鍵的助力,讓我進入傳統複雜的士大夫文化的嘗試,不致過於支絀和挫折。而也就在這個試圖進入另一個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文化傳統的過程中,我讀到大木康教授的相關著作,看到另一位現代異邦人,對另一種傳統的文化型態、生活方式,同樣抱持著極大的同情和興趣,並作出細緻而全面的闡釋。我原有的一些遲疑和不確定感因而得到紓減,並能更心安理得的體會發現和探險的樂趣。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答應為大木康教授《中國遊里空間》的中譯本寫一篇序言,除了因為我在修改〈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一文時,受益於此書之處甚多,而思有所圖報外,也因為大木教授的這本書重新喚起我對日本學者的中國史研究的興趣,想對日本年輕一代學者在中國文化史、城市史乃至日本近世文化史和城市史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我在過去十幾年中,研究課題由近代上海轉至清代揚州,並由揚州進而上溯至明末金陵,使用的資料也更具文學色彩。幾年前在構思如何重建明末士人的南京回憶時,更決定用《桃花扇》和《板橋雜記》兩本文學著作,作為重建的基石。大木康教授的這本秦淮研究,雖然徵引資料浩繁,但他以余懷的《板橋雜記》、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冒襄的《影梅庵憶語》等文學作品作主要根據的出發點,卻和我不謀而合。大木教授在後記中,提到他從大學時代接觸到《板橋雜記》的日譯本開始,就被這本書中的美感經驗所震懾,自此愛不釋手,成為日後寫作本書的主要契機。和我自己也是從大學時代開始,首次接觸日本學者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卻無所長進的經驗相比,大木教授的自敘,一方面顯示出他的早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文學作品無所不在,浸潤渲染的力量。雖然我第一次閱讀《板橋雜記》的年齡,比大木教授晚了約三十年,但對書中的興亡之感、離亂之情和美學意境,卻有著同樣強烈而難以釋懷的情感,並決定用這本書和《桃花扇》的描述,來重建一個中國城市的繁華歲月。
但只有在讀了大木教授的研究和後序後,我才了解到余懷的作品,不僅能穿越時間的阻隔,在幾百年後,對我這樣一個現代的中文讀者產生震撼力,並早在十八世紀,透過各種日文譯本,在鎖國的江戶時代,對日本人的秦淮想像和日本自身的冶遊文學產生極大的影響。如果不是透過大木教授的考訂、爬梳,我們實難想像余懷這一位在中國文學史中相對隱晦的「艷遊文學」作家,竟也像白居易、蘇東坡一樣,在日本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大木教授從中日文化比較研究的角度探討了余懷、秦淮文學對日本人的秦淮想像和冶遊文學的影響,我有機會為此書的中譯本,略盡棉薄之力,似乎就成為義不容辭的工作。
我幾年前讀到美國霍浦金斯大學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一篇文章,討論揚州從1600年迄今,不同的文字資料如何作為「文化地圖」,而對不同時期,不同國籍的揚州遊客產生不同的形塑作用。以1930年代為例,同樣帶有殖民色彩的外文旅遊導覽中,英文寫的中國導遊書,往往對揚州卻乏好感或一筆略過。日文的導遊書,則透過對唐代揚州佛教的介紹,蘇軾、歐陽修的相關詩文,和《揚州畫舫錄》的描述,讓日本遊客有了全然不同的揚州印象。 日本人長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作品的浸潤,讓他們在進入中國歷史名城和文化遺跡時,有著和西方人很不同的想像、感知力和美感體驗。
揚州如此,南京亦然。大木教授的研究,正好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用大量的書寫、文學和圖像資料呼應了梅爾清精彩的論斷。我們因此進一步了解到,在揚州之外,南京是另一個(或者更重要的)寄託日本人的異國想像的文化名城。以一種近乎偵探小說的筆法,大木教授從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二十世紀作家以南京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出發,將我們一步一步引入一個和Hershatter筆下的二十世紀的上海歡場 大異其趣的風月世界。
作為一個亡國之都,南京傷感的歷史,當然不始自二十世紀日本人的佔領,也不始自孔尚任、余懷華麗的悼亡、追悔之作。作為一名文學史家,大木教授同時為當代的日文和中文讀者,精確地勾勒出秦淮所承續的文化傳承。從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樓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到南唐李後主的〈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南京在明亡之前的歷史,其實一直是以一種傷感、唯美的形象流傳於世。大木教授也不時透過文字的考證,指出余懷、錢謙益和六朝文學的傳承之處。
雖然大木教授謙稱他並不打算像一個有才情的創作者那樣,活靈活現地呈現秦淮風月的情緻,但全書的結構、佈局和敘事,卻不時透露出作者文學訓練的背景。這個精心搭建的框架,飾以無所不包的細部資料,讓我們對秦淮遊里空間的每一個面向,都有深入的了解。大木教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工夫和成果,在我寫〈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一文時受益良多,也讓我再一次體認到日本中國學者紮實的傳統。這裡我只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不論是在《桃花扇》、《板橋雜記》,還是張岱的《陶庵夢憶》及其他的明人記敘中,都對柳敬亭這位知名的說書藝人,有極深刻的勾畫。也許因為柳敬亭作為一位藝術家的形象過於突出,我完全忽略了他和明末知名的清客丁繼之等人共有的「幫閑」身分。「幫閑」的角色,看似無足輕重,卻是明清士大夫文化和城市逸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錢謙益的詩作中就有幾十首以丁繼之及丁氏河房為對象,陳寅恪更詳細考證了丁繼之在秦淮河上的丁氏河房,如何一度被錢謙益用為反清復明活動的基地。 大木教授在此仔細追溯了幫閑一族的系譜,從孟元老記載北宋都城汴京景象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南宋臨安的《都城紀勝》,到《金瓶梅》中與西門慶廝混的應伯爵,看似細瑣,卻為我們探究明清與宋代城市生活的異同,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大木教授藉著豐富多元的資料,將明清秦淮放在一個更悠久的文化傳統中考察,而賦予這個遊里空間更寬廣的意涵的作法,在對「《水滸傳》裡的妓院」一節的描寫中也充分反映出來。故事的場景是《水滸傳》中的頭號俊男燕青,奉宋江之命,前往汴京(今開封)拜訪都城第一名妓李師師,希望藉由李師師與宋徽宗的私情,轉致宋江亟思被朝廷招安的苦心。在引用了《水滸傳》中燕青進入李師師閨房後的相關描述後,大木教授隨即指出這段以北宋汴京為背景的描述和明末江南,乃至秦淮妓院間的關係:
《水滸傳》故事發展的舞台背景雖然在中國北方,然而成書問世卻在明末的江南地方。宮崎市定曾在論文中指出,《水滸傳》裡描述的房舍屋宅主要是南方建築,而非北方之物。雖然描寫宋代都城汴京的故事經緯,實際上可能反映著江南或是秦淮的風情故趣。
大木康教授所承續的日本漢學傳統,讓他營造出的明清秦淮,更加堅實緜密。和在時間、資料上的拓展相輔相成的,則是經由實地的探勘、考察,將秦淮這個可以馳騁無限文學、美學想像的源頭,固著在一塊南北長300公尺,東西寬100公尺的有限土地上。當我沉浸在《桃花扇》和《板橋雜記》所舖陳出的美學情境和亂離之感時,大木教授這段對舊院面積所作的考證,讓我有一種恍然若驚,從文學回到歷史,從想像回到現實的強烈感覺。無限的文學想像和堅硬的地理座標間的張力,讓秦淮的遊里空間變得更耐人尋味。大木教授的深描細究,配合上豐富的地圖、版畫、圖片和照片,讓我們在不同文化、不同時空、不同場景間的穿梭,變得更為悠游裕如。
大木康教授在哈佛大學訪問一年中,完成此書的初稿,可謂成果豐碩。相形之下,我在哈佛一生懸命,勉強得來的日文知識,則變得後繼乏力,形同具文。另一方面,我最近陸續讀到田仲一成《中國戲劇史》(云貴彬、于允譯,北京廣播學院,2002)、《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和本書的中譯本,收獲良多,深深覺得我們對日本學者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認識不足,特別期待能看到更多類似譯作的出現。
序章 日本文學中的秦淮
秦淮——昔日南京的風月場所。這處燈紅酒綠的裏巷名聲,更以臨靠秦淮河水渠的妓院及浮波水上的畫舫(遊船)而聞名遐邇。本書嘗試從秦淮發展最繁榮的明清時代,而且是以明末清初為主的這段時期,對此地重新加以詮釋。
明末清初的時代,包括在後面章節登場的孔尚任戲曲《桃花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為首的眾多名妓在秦淮此地登場,而當代一流的才子也雲集於此。詩酒徵逐的良辰美景不曾間斷,因此衍生出段段旖旎戀曲。在秦淮的悠久歷史之中,明末清初可說是一段顛峰期。秦淮作為明清兩代文化的重心要地之一,對文化發展發揮了極大作用。如果不識秦淮,就是對明清江南地方的半數文化一無所知,這種說法一點也不為過。
中國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這兩代期間,大約相當於日本室町到江戶及明治時代。猶如當時的中國人士會珍視當地般,對於將中國文化各個層面都視同範本的日本人而言,秦淮也是夢寐以求的地點之一。更何況鎖國時期的日本一般百姓並不能隨心造訪秦淮,這或許更加深了對該地的嚮往之情。
南京秦淮在戰前的日本文學作品中常成為故事舞台,而日本人的中國遊記裡也必然會對此地添上一筆。其中最耳熟能詳的,大概就屬芥川龍之介 的小說〈南京的基督〉吧。
芥川龍之介的〈南京的基督〉
女主角宋金花是十五歲娼妓,為了養活年邁父親才情非得已下海為娼,她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房間牆上掛著黃銅製的十字架和基督受難像。不幸身患楊梅瘡(梅毒)的金花從姊妹淘那裡聽說既然遭人染疾,只要再傳染給別人就會痊癒。聽到這番話,從此她就開始拒絕接客。
某日,一位不知是東西方民族的客人走進她的屋內。儘管語言不通,男士仍然熱心地與金花談價,而價格從二塊美金一路漲到十塊美金。她心裡正在忖踱此人十分眼熟的時候,忽然抬眼一看,發現他就是牆上懸掛的耶穌現世。於是金花「第一次知道戀愛的歡喜」,甘心破戒委身於這名男士。
當天晚上,金花夢見燕窩魚翅等山珍海味擺滿一桌,有位光圈環繞的外國人對她面露微笑。次日清晨醒來後,她才發現外國人早已不知去向,不僅如此,她還發現自己沒收到應得的十塊美金。然而此時「奇蹟」卻出現了,金花的楊梅瘡完全不藥而癒。她心想「那個人就是耶穌基督」,就急忙爬下臥榻向著基督祈禱。
劇情於是急轉直下。此後,據說逗留在上海的和洋混血兒喬治.莫瑞原本還為自己在南京買私娼時,趁妓女熟睡之際拔腿潛逃而沾沾自喜,不久卻因感染惡性梅毒以致發瘋。一位訪金花的日本旅人在聽過這個「奇蹟」故事後,不禁自問:「事到如今,這個女子依然認為那個混血的無賴漢就是耶穌基督。我到底該向她揭示真相呢?抑或永遠保持緘默,讓她當作是一場如昔日西洋傳說般的美夢呢……?」,日本旅人問金花:「此後妳不曾發過病嗎?」,而故事是以金花回答「是的,一次也沒有」時「臉上泛出燦爛的光輝」作為尾聲。
在結尾的部分,到底主角該蒙在鼓裡才幸福,還是察明真相比較恰當呢?在訴說以上這個近代課題之餘,芥川喜愛的異國風景,而且成為這個恰似「昔日西洋傳說」的故事舞台不是別處,正是此地南京秦淮。〈南京的基督〉發生的舞台,根據記載是在「南京奇望街」。而奇望街是真實存在的地名,也是貫通秦淮北側的要道(現在改名健康路),必須由此進入秦淮地方。最近則有一部電影「南京的基督」,金花一角是由日本女星富田靖子所飾演(區丁平導演、嘉禾影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
〈南京的基督〉發表於大正九年(一九二0),此時芥川龍之介尚未遊訪當地,而是在翌年的大正十年方才實地前往南京。他在遊記作品集《江南遊記》〈南京(中)〉裡,對實際遊訪秦淮有如此說明:
若從橋上眺望,秦淮不過是一條平凡的溝川。川幅約與東京的立川同寬。兩岸人家連房比屋,據說皆是飯館酒家之屬。家屋上空的新樹正展露枝梢,在此可望見無人畫舫三、四艘,舟楫相繫於暮靄之中。古人云:「煙籠寒水月籠沙」,此番風景已不復見。而今日所謂的秦淮,不啻俗臭紛紛如柳橋。
踏出飯館,既是夜中。家家電燈明晃,映照著載妓的人力車,彷彿行駛於代地河岸(東京柳橋,隅田川河岸之通稱),然卻未見姝麗一人。我懷疑〈秦淮畫舫錄〉中的美人,究竟有幾人堪值千金不換。倘若媲美〈桃花扇傳奇〉的香君之品秀端麗,且莫說秦淮妓家一處而已,即使遍遊四百餘州,亦恐無一人可望其項背。……
芥川龍之介對於實地遊訪秦淮的種種遙想,似乎是幻滅殆盡了。這可說作家在造訪名勝後難免有感而發,不過在此同時,卻也訴說著芥川原本對這趟旅行的期許之深。
且說芥川未曾實地遊訪秦淮,卻仍蘊意執筆〈南京的基督〉的理由,就如同在作品結尾的記述所提,「撰寫此篇時,參考谷崎潤一郎氏作品《秦淮一夜》的草稿相形見拙之處甚多,附記以表感謝之意」,由此可知,這篇作品是受到谷崎潤一郎 於前年大正八年(一九一九)發表的〈秦淮之夜〉所啟發而來。
谷崎潤一郎〈秦淮之夜〉
谷崎潤一郎從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十月至十二月從天津、北京、漢口、上海等地為首,旅跡遍及中國各地,途中曾造訪南京並前往秦淮遊覽。〈秦淮之夜〉也是經這次實地遊覽而生。故事主角「我」到南京旅遊,透過一位會說日語的中國嚮導,經介紹來到秦淮,在酒足飯飽之後,穿梭尋訪了如迷宮的內巷妓院。「我」在初來乍到的地方,遇見一位名字叫「巧」的妓女。
她的臉龐在暈暗的燈光下浮現,既肉感又圓潤,白皙到散發出光輝,尤其略薄的鼻扇,淨透著明澈的微紅。嬌艷更勝的是那比身上穿的黑襦服再漆亮幾分的髮絲,還有無限嬌娜、彷彿難掩驚奇般圓睜睜的明眸裡蘊含的靈動表情。我在北京雖然也遇過形形色色的女子,卻從未見過這等絕色美女。實際上,在如此煞風景、如此昏暗而髒牆污壁的家裡,竟有如此琢磨得珠圓玉潤的女子居住其中,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使用所謂的「琢磨」一字,是舉凡形容此女的美貌之中再恰當不過的措辭了。此話怎說呢,即使她的玉容算不上是最典型的美人,然而無論是肌理光澤、眼波流轉、髮髻款式或整體身段,她都將自身如何受調教成一名洗鍊藝妓的可愛姿態,充分地發揮得淋漓盡致。
小說接下來仍繼續形容這名妓女,主角「我」對這位據稱在此地身價最高的妓女完全心醉神迷。然而卻因為與她談不攏價碼,僅僅一睹丰采就打道回府。「我」雖然如此尋思:「將她華貴似幻的倩影就如此深藏在內心深處,然後安詳地踏上歸路,這反而是我夢寐以求的方式。」不過嚮導卻表示還有更便宜又能找樂子的地方可去,於是主角又在黑暗中又窺探了兩、三間,卻總遇不到條件相符的女子。最後在奇望街警察署的裡側家中,邂逅了一名叫做「花月樓」的妓女。她自稱最近無客上門,談價三塊美元隨即成交,而「我」決定在此投宿歇身。
語畢,嚮導及虔婆從別房退出後,女子扣下入口的板戶門栓,並上了閂子。接著她絮絮叨叨、嬌聲嗲氣地說了一堆聽不懂的話,這才展顏微笑起來。那明眸與櫻口含著憂影,意想不到的是她以那神采奕奕的表情,全心全意地向我獻媚拋情。就連中國話的連隻字片語都全然不解的我,面對那楚楚可憐的媚態卻不知如何對應,為此不禁惆悵感傷起來。
「花月樓、花月樓。」
我稍微用中國話不斷呼喚她的芳名,雙掌間托著那細長的臉龐。托著觀看的是一張幾乎完全藏匿在掌中大小的甜美臉兒,若使力擠壓就會壞碎般柔軟的骨造。在我認為,那彷彿是大人般工整、又如嬰孩般水靈靈的五官。我突然感受到的是一股從胸底澎湃升起的激昂情緒,似是永遠捨不得放開那托住的容顏。
這部作品到此即劃下句點。主角呼喚著女郎的名字、牢牢捧住她的臉頰,就在精彩絕妙之處突然戛然而止。這看來似乎是一篇二流作品,而且谷崎潤一郎也未曾將它收在自編的全集裡,或許正如作者在全集自序中提及的,「自身讀來覺得情何以堪的作品、無意讓人閱讀的作品,我決定努力使其消聲匿跡」。即使如此,主角一面由嚮導領路穿梭在漆闇的迷宮中、一面驅步遊走在各家妓院的描寫,其實迥異於芥川對秦淮唯有「未見姝麗一人」的成見。谷崎精湛地找出那絕無僅有的「姝麗」,且能發揮珠璣妙筆加以細膩描摹,這不禁要為谷崎觀察女性的犀銳眼光,以及筆觸恰切自如的功夫而戰慄莫名了。這更足以說明谷崎深為秦淮的魔力魅惑至此啊。相對之下,芥川則是將本篇作品中的秦淮僅視為異國風情的舞台來作處理。
佐藤春夫〈秦淮畫舫納涼記〉
佐藤春夫 也是曾經遊訪秦淮地方的作家之一。佐藤在時間上稍晚於谷崎及芥川,是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由當時任職南京國民政府藝術部的電影股長兼劇作家田漢的嚮導之下,遊覽了秦淮地方並乘坐畫舫(田漢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在畫舫遊船結束之後,佐藤終於信步來到花街。
這是一條暗巷,縱然我認為四處都不見街牌,但匪夷所思的是,不知何故自己竟清楚知道這條路的名稱就是釣魚巷——釣小路,這件事直到現在仍記憶猶新。除了星輝以外毫無光亮的路旁,我發現這世上壓根兒也料想不到會有的東西。一條猶如凝脂般雪白、直暴露到大腿附近的女人酥腿正蟠繞在路邊。這名婦人由於溽暑難耐而來到戶外、橫躺在冰涼的石板上,想必在睡眠中無意識地將褲子褪了去。……面對褪去褲子的婦人在路旁倒頭就睡的放浪姿態,我不禁懷疑自己的眼睛起來。即使思忖既有此地當有此舉,只是與其認為真有其物,倒不如說是非份妄想下見到的幻覺來得更恰切。她的大腿是如此白皙、如此靡豔,在人前也能如此毫無忌憚的擺露痴態。……
這段情節不愧是出自佐藤春夫之筆,烘托出懸疑而獵奇般的氣氛,雖說原本只是一夜夢譚,然而婦女睡在路上大腿全露等描寫,的確誠如芥川所謂「俗臭紛紛」的最佳寫照。佐藤春夫此後雖有踏進妓樓,在文中卻記載著「眼下所見,毫無足以眷戀不捨的貨色」。
谷崎潤一郎為秦淮女性的魅力一見傾心,以中肯的筆觸將之勾勒成形;芥川龍之介點出秦淮的異國情調,將此地視為「昔日西洋傳說」的故事舞台並加以運用;佐藤則著眼於世上罕見的獵奇光景,特意留添一筆。雖然作家們是各異其趣,不過確實都意識到南京秦淮,其實是個充滿異國情趣及獵奇嗜趣的地點。
在此姑且不再逐一細舉作品,在戰前出版的中國旅行記,例如德富豬一郎(蘇峰)的《支那漫遊記》〈南京の見物‧秦淮〉(大正七年 一九一八)、那波利貞《燕吳載筆》〈秦淮畫舫〉(大正十四年 一九二五)、中河與一〈秦淮の畫舫〉(初出未詳。中河於大正十五年遊南京)、大屋德城《鮮支巡禮行》〈南京懷古‧秦淮情緒〉(昭和五年 一九三0)、後藤朝太郎《支那及滿州旅行指南》〈秦淮の畫舫〉〈南京〉(昭和七年 一九三二)、西晴雲《江南百題》〈秦淮湖畔〉(昭和十三年 一九三八)、橋本關雪《支那山水隨緣》〈南京(秦淮)〉(昭和十五年 一九四0)、後藤末雄《藝術の支那、科學の支那》(昭和十七年 一九四二)等作品皆遊訪南京秦淮,且舉一項作為著筆記載。更有在關於中國風俗的戰前著作中,必然也會分配一章的篇幅來描寫南京秦淮。例如後藤朝太郎《支那民情を語る》(昭和五年 一九三0)及《支那の體臭》(昭和八年 一九三三)、《支那風土記》(昭和十年 一九三五)、澤村幸夫《江浙風物誌》(昭和十四年 一九三九)等書。
永井禾原《來青閣集》
谷崎、芥川、佐藤三人分別在民國時期,也就是奠定首都於南京以後才造訪秦淮的作家群,然而在前清就抵達南京秦淮遊訪的日本人也為數不少。原因在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七月,日本與清朝締結清日修好條規並互設公使館,兩國人民因此能互訪交流。
作家永井荷風 之父永井久一郎 ,也是遊客之一。永井久一郎系出尾張藩士,維新以後成為明治政府的官僚,任職於內務省、工部省及文部省。最後以文部省會計局長一職退休,再轉任日本郵船公司,以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所謂的空降部隊,然後於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以上海分店長的身分遠赴上海。
永井久一郎,號禾原,以漢詩人聞名於世,留有著作《來青閣集》十卷(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刊行)。現在若翻閱《來青閣集》,即可了解禾原留任上海之際,在中國各地旅行時創作的自娛詩、以及與當地諸名士交往時寫下贈答詩的情形。在禾原交往的人士之中,有清代南京名詩人袁枚的子孫、或是參與戊戌變法有功的文廷式、日後遊訪東瀛時撰寫《書舶庸談》這部以詳細調查日本收藏漢籍記錄的董康、被視為清末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等人。與這些人士往來的地點,則是上海、蘇州及其它地方的妓院。
南京秦淮對禾原而言,也是神往已久的聖地。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禾原在雪中首度探訪秦淮,以下是當時創作的〈雪曉騎驢過秦淮二首〉(《來青閣集》卷二)中的第二首。
滿江飛絮不勝寒,
繡閣無人起倚欄。
只有風流驢背客,
秦淮曉色雪中看。
詩中河面上正粉雪飛舞,讓人感到不勝其寒。在這樣的日子裡,早起憑欄的美人儷影都未嘗拜見。唯有一位跨騎驢背的風流客,頻頻眺望著雪中的秦淮朝景。
此時的永井禾原,恐怕因為只從門外窺睹秦淮而大感遺憾吧。此後又經過寒暑三載,永井在明治三十四年(一九0一)首次真正暢遊秦淮,從這次一償宿願所詠的〈秦淮雜詩十首〉(《來青閣集》卷四)來看,可知作家當時似乎相當心滿意足。其中一首是如此寫著:
古渡垂柳藏晚鴉,
六朝金粉舊繁華。
東瀛詩客風流甚,
走馬先行陸八家。
在古渡口(桃葉渡)的殘陽餘暉中,隱約可見烏鴉築巢在垂柳間。在秦淮以詩歌頌詠這塊曾是六朝金粉繁華極至的地方。喜好漁色的東瀛(指日本)詩客甫抵南京,就迫不及待地縱馬急馳陸八家,作者還另有註明「陸八乃妓院之名」。接著再看第二首:
長板橋邊載酒過,
閑情綺夢夜來多。
劫余更見煙花盛,
六院新聲百翠娥。
倘若載酒過訪南京舊院的長板橋附近,在不知不覺間,華宵如夢境般喧然而至。戰亂之後(此指太平天國造成的荒廢),終於得以重見煙花昌盛的景貌。六家妓院裡唱著時興新調,眾百美女坐擁如雲。原註是「金陵舊院已完全煙消雲散。現存三和、陸八、李三、韓義、小獅、劉琴共六院,妓女則有百餘名。」。起首句中的「載酒過」,是出自唐代杜牧在徜遊揚州妓院所作〈遣懷〉一詩的「江湖落魄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而來,禾原自我影射了這位愛好風流的詩人。從每首詩中,都可窺出禾原探訪南京及遊覽聞名遐邇的秦淮妓院時,那股喜出望外的心情。
隨後永井禾原在見到東京新橋的名妓秀香女史穿中國服露面的情景,就於明治三十六年在《來青閣集》裡添加秦淮舊遊的回想作品(卷五)。(有關名妓秀香,在明治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大和新聞」附錄裡有其照片,大正三年《新橋煉化地藝妓人名表》板新道之部、本叶屋中可見「秀香」之名。根據田村榮太郎《銀座 京橋 日本橋》雄山閣 一九六四〈新橋藝者繁盛記〉指出,叶屋似是日本郵船相關人士聚集的場所,因此禾原出入此地完全符合情理)。禾原在明治四十三年接受駐留南京的日本官商諸紳的邀請,為此留下秦淮畫舫遊樂之作(卷九),由此可見作者對秦淮眷戀至深。
在永井荷風的論述中,嚴父禾原是以留洋歸國的基督教徒及高級官僚之姿,與兒子荷風以寫花街柳巷為小說題材的柔性訴求,呈現儼然對立的風格,有很多論證觀點都強調荷風的生活方式其實是刻意與父親相抗衡。
的確,從永井荷風與父親的期待背道而馳,不願躋身官界或實業界而成為區區一介文士來看,無疑就是一種叛逆行徑。以當時的普遍觀念來說,高級官僚與落魄文士在社會上的地位根本是天壤之別。不過尤其在明治時代,新橋或柳橋等花柳界的繁榮全靠官僚或實業家們的捧場支持,連永井禾原在《來青閣集》中也毫不避嫌將與聲色場所相關的作品納入卷中。由此可知,為父的禾原與荷風同是在狹斜巷中眠花宿柳之人。
根據荷風的〈東京風俗話〉(《葛飾土產》一九五0所收、一九九四年版全集第十九卷)指出:
雖然連藝妓也隨時勢所趨,逐漸淪落到淨是些微塵屑末之輩,然而直至明治末期似仍講求風格品味。當我在孩提時代,家中亦有藝妓往來頻繁。在賓客雲集之際,召喚常來捧場的藝妓為客人斟酒作陪。由於家裡每個月舉行詩會,此時會來兩、三名藝妓,她們並非僅斟酒而已,還替客人磨墨或鋪展唐紙,打理揮毫書畫的種種用度。這是從江戶時代即流傳下來的風習,但因時勢更迭而在不知不覺中佚失。
由以上這段敘述可知,永井禾原以漢詩會友的過程中與藝妓的關係實同匪淺。
如此看來,永井父子之間其實也未必有極大的隔閡。當然兩人對狹斜裏巷的觀感角度若說不同確實不同,不過儘管如此,彼此所見可說表裡如一吧。
即使侷限在漢詩世界,永井荷風的《雨瀟瀟》(大正十年、一九二一)中介紹的中國明末豔詩人王次回可說令人印象深刻,而讓荷風發掘此人詩作的也正是禾原在《來青閣集》卷八所收的〈新歲竹枝詞倣王次回體即用原韻〉十三首連作(明治四十一年)。此作與王次回《疑雨集》卷二的〈新歲竹枝詞〉和韻,由此可見禾原也熱切矚目王次回的作品。姑且舉一首禾原的詩來看看:
爭新時樣一年年,
女伴春妝列綺筵。
腰帶長垂金色燦,
疏花點綴畫裙緣。
流行風款年年換新,女郎們穿上新裝,陪侍在筵席間。只見長串垂下的錦帶燦然奪目,衣袂上點綴著充滿意趣的花飾圖樣。「竹枝」雖是詠風月之詩,然而這首詩卻是描寫新年裡侍宴的藝妓所穿的羅裳正裝。由此可見,荷風的確承襲不少父親禾原的文思。
《板橋雜記》與江戶洒落本
永井禾原為何如此迷戀秦淮?日本人對秦淮地方的意象及憧憬,其實並非始於明治時代,而是在江戶時代就已深植人心。至於將秦淮意象在日本根深蒂固的契機,應該是歸功於余懷的《板橋雜記》——也就是本書在以明末秦淮為主題探討時視為最重要的資料,而該書在江戶時代就已經在日本刊行問世了。
《板橋雜記》是作者余懷在明末遊覽秦淮的作品,明亡後,為了追念遭戰火肆虐殆盡的秦淮,因此提筆記錄明末時的盛況。《板橋雜記》在日本最初的全文重印是在明和九年(一七七二),其中附有山崎蘭齋的譯文,並由大阪心齋橋筋順慶町尾崎町坂陽書房甲谷佐兵衛所刊行。此後於享和三年(一八0三)由江戶淺草新寺町和泉屋庄二郎再版,更於文化十一年(一八一四)由同店的江戶書林和泉屋庄二郎更改書名為《唐土名妓傳》,此後並重新刊行,足見讀者的需求量之大。
《板橋雜記》於明和九年刊行以後,對江戶文藝的影響可說俯拾皆是。正如麻生磯次在《江戶文學と支那文學——近代文學の支那原拠と讀本研究》(三省堂、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的三一四至三一九頁之中,針對《板橋雜記》與江戶洒落本的共通點舉凡六項論證所指般,本作首先影響所及,就是對寬政期出現的洒落本給予莫大的刺激。
這可從山東京傳 的《傾城買四十八手》(寬政二年、一七九0)可見一斑。山東京傳的此作附有扉頁插繪,畫中有一名妓女騎在碩大的鯉魚背上讀書信。圖上的題字則是:
慾界之仙都
昇平之樂國
據山東京傳所示,「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無疑的是指江戶吉原的喻詞。這種表現必然取自以下提到的余懷《板橋雜記》卷上開頭所作的一段記述。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南京是帝王建都的地方。公卿顯貴的府邸並立如雲,皇室的王孫公子身披輕裘趨車縱馬而行。從貴族子弟到街坊少年、江湖俠客帶劍吹簫尋訪妓家。一干人等每逢開宴設席必召官妓,輕羅霓裳香氛襲人。方才酒過三巡杯盞交錯,留客痛飲一番,酒宴就已結束,棋局也近尾聲,地上散落著耳環及忘失的髮簪。此情此景,真不愧是欲界仙都、昇平樂國啊。
山東京傳見到《板橋雜記》裡的這句話,有意將江戶吉原與明末秦淮的意象相疊合。其次這句「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的表現,也並非余懷所創的用詞。其實余懷是直接從明末清初江南文壇的巨擘錢謙益的〈金陵杜夕詩序〉(徐釚《續本事詩》卷四 引王嗣京之段)中的一句表現加以潤飾而成。從原文中即可見端倪: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游談者指為樂土。
四海昇平,陪都佳麗,為官者誇讚此地為仙都,狎遊人士指稱此處為樂土。
然而,錢謙益也必然意識到在明朝萬曆年間,為秦淮妓女列芳名席次的曹大章所著的《秦淮士女表》序文。而在序中提到:
此誠欲界之仙都,而塵寰之樂境也。
甚至更可以說以上的表現在六朝梁朝的陶弘景所撰的〈答謝中書〉中亦可見到:
實是欲界之仙都
陶弘景以隱士身分為人所知,這篇文章雖然是讚許山水之美,不過尚在南京建都的六朝時代,陶乃居南京郊外的棲霞山,因此也與南京有所關連。中國人在所寫的文章裡一字一句皆有典故來歷,實在不能輕忽略讀。
成島柳北《柳橋新誌》
提到《板橋雜記》的影響,就不能輕易忘記這位幕府末期及明治時代的文人——成島柳北 所著的《柳橋新誌》(初篇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次篇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關於此書,根據前田愛的〈《板橋雜記》と《柳橋新誌》〉(《國語と國文學》昭和三十九年三月、亦收於《著作集》第一卷),不僅指出這兩書具體的共通點,更以余懷對秦淮隨明亡湮滅的情況,以及成島柳北對幕府瓦解後在經出身薩摩國及長門國的官吏撐腰,導致柳橋 繁榮到無寧是俗惡至極的情況,犀利點出了兩位作者在批判立場上的歧異。有關這點,前田的論述十分詳盡,筆者在本書中不再特別附加說明,不過例如《柳橋新誌》中記述了妓女在製新衣時會向熟客要唆出資的情形。
故各擁狎客,以逃斯勞。若夫狎客則不得旁觀而不援其費也。《板橋雜記》裡所謂「衣飾皆主之者措辦,巧製新裁,出於假母。……(中略)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崇禎距今過二百年,地之相去數萬里,而風情酷肖,可謂奇矣。(初篇)
故而妓女們各自擁有狎客,藉此免去添衣所費的鉅資。於是在場旁觀的年輕狎客,不得不立即掏腰包賞錢讓姑娘添裝才行。《板橋雜記》裡所謂「衣飾皆由主客籌措,巧樣新裁則有假母一手包辦。……(中略)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崇禎距今已過兩百年,秦淮與柳橋相距亦有數萬里之遙,然而風情酷似如此,堪謂奇聞。(初篇)
作者將《板橋雜記》裡描寫明末秦淮的狀況與當時的柳橋現狀互作比較,指出兩地風俗頗為相似之處。此外還提到:
柳橋之盛也至矣。何無一人才氣雄拔,鳴名於都內者乎?余曼翁列金陵珠市名妓,作小傳,佳人之跡百世不朽。余今欲記柳橋紅裙,以淮擬之,而未詳有一個行實可記者。
柳橋的繁華已達於鼎盛。然而才氣超群、名滿江戶城內者竟無一人。余曼翁列舉金陵珠市的名妓,為其譜上小傳,而佳人芳跡永垂百世不朽。我記下今日柳橋紅裙,欲仿效余曼翁的構思作為依據。然而,尚未詳聞有任何一位值得立傳的紅粉佳人。(初篇)
成島柳北在欲意執筆《柳橋新誌》時,明確表述是有意「依據」余曼翁的名妓小傳、亦即余懷的《板橋雜記》。就是以明末秦淮=柳橋、余懷=柳北的形式,並藉由明末秦淮作為參考基礎,然後才構成《柳橋新誌》的記述內容。
明末秦淮的時光之旅
以上就是對日本文學中描述的秦淮地方作一概觀。在日本文學中即使歷經時代更迭,是否有可能歸納出一類稱為「秦淮文學」呢?
不過在「秦淮文學」方面,岩城秀夫譯著的《板橋雜記》(《板橋雜記.蘇州畫舫錄》平凡社東洋文庫 昭和三十九年)卷末雖有精簡扼要的解說,卻欠缺其它作品的相關詳情,或有關秦淮文學作品等專門論述的著作。此外近年在中國,也逐漸關注到舉凡妓院曾為文學創作及逸樂享受的溫床,在這方面,雖有相關的專著,但是到目前為止妓院和妓女的實際情況仍存在許多懸而未解的課題。筆者撰寫此書時的意圖是希望以南京秦淮為事例,而為上述問題提供些許線索。
這趟明末秦淮的時光之旅如能順利達成,筆者將由衷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