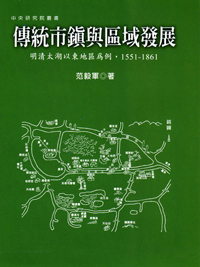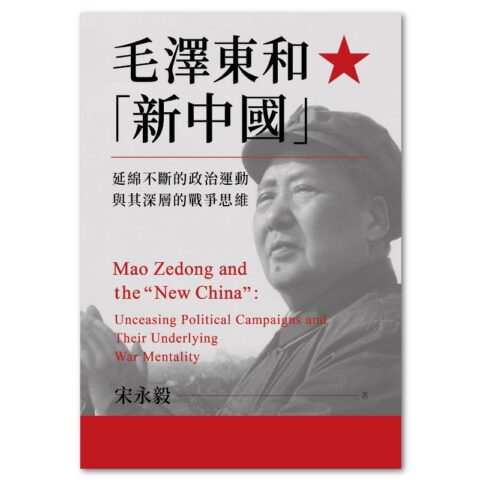傳統市鎮與區域發展
出版日期:2005-09-22
作者:范毅軍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32
開數:18開
EAN:9789570828849
系列:中央研究院叢書
已售完
包括蘇南在內的明清江南地區,向來是社會經濟史家勤於耕耘之所。研究成果自1950年代以來,連篇累牘,罄竹難書。後起於1980年代以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研究,迄今亦累計達數百篇以上論文及數本專書。有見於市鎮研究的方法與視角尚可推陳出新,本書續以蘇南市鎮為研究焦點。分析力求對市鎮各種屬性可量化為能事。此外則側重從空間地理位置的角度來探索市鎮。相對於既有研究,此可歸納出一些新意。就整個明清江南社會經濟而言,亦可加深其認識與瞭解。
作者:范毅軍
范毅軍。美國Stanford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計畫執行秘書。
專長:明清與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歷史地理、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序言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市鎮與鹽鐵塘主幹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一、長江口南岸沙洲區
二、梅李與楊林塘區
三、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
四、淀浦河流域
第三章、市鎮與淀(淀浦河)南浦(黃浦江)東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第四章、市鎮和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
一、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東部
二、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西部
第五章、結論
參考文獻
一、 傳統文獻與地方志書
二、近人論著
圖 表
表1-1明清歷年常關稅收額表
表2-1長江口南岸沙洲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
表2-2梅李與楊林塘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
表2-3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
表2-4淀浦河流域市鎮名稱、等級與數量變化表
表2-5鹽鐵塘主幹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表3-1淀南浦東區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表3-2淀南浦東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表4-1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東部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表4-2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西部市鎮名稱、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表4-3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市鎮數量與等級變化表
圖1-1明清時期全國與江南地區常關、工關和重要商路分佈圖
圖2-1明中葉(1550年止)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
圖2-2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1551~1722
圖2-3明中葉以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1723~1861
圖2-4黃渡鎮圖
圖2-5黃渡境全圖
圖2-6吳淞南境水利圖
圖2-7南翔鎮圖
圖2-8江灣鄉圖
圖2-9珠里總圖
圖4-1康熙年間甪直鎮圖
圖4-2乾隆年間甪直鎮圖
圖4-3康熙年間甪直鎮形勢圖
圖4-4乾隆年間甪直鎮形勢圖
圖4-5嘉慶年間黎里鎮全圖
圖4-6光緒年間黎里鎮全圖
圖4-7周莊鎮全圖
圖4-8周莊鎮圖
圖4-9盛湖圖
圖4-10盛澤鎮圖
序言
本書寫作構想直接源自筆者1992年底博士論文殺青時所獲致的一些見解,間接則受1970年代後期初踏入史學研究領域為學徒時的領會所啟發。個人歷年的研究工作表面上雖未達到環環相扣的程度,但關心的主旨卻始終如一,都以近代通商口岸開放以後,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大變局為依歸。無論其事涉一般國計與民生或進而影響近代民主與科學的發展,問題均化約成傳統中國社會基本經濟結構與功能的變與不變這一面向,作為探索的起點,期能對傳統中國過渡到現代的歷程及其意義有所認識並做適當的詮釋。
經濟結構與功能牽涉範圍廣泛,從土地利用、租佃制度、商品流通、市場結構、商業組織與商業倫理到貨幣的使用等均屬之。筆者在初窺歷史堂奧時,即專對中國國內區域間的貿易流通深感興趣,並遍讀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所編製的海關年報與海關十年報告、特別報告等。由於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及其轄下各口岸管理機構從設立初始到相當一段歲月,均由西人所主持,傳統與國內貿易流通有關之事務,國人往往習焉不察,而疏於記載,但在西人眼中卻是焦點所在,因而留下許多西文的記錄。而尤其特殊者,則是近代海關除逐年系統性編制通商各口岸對國外的貿易流通數據外,同時亦編列國內埠際的貿易統計,特別是開港初期,商品流通數據以外,通商各港的海關年報多搭配與本口岸腹地有關的社會經濟調查報告,在近代國內區域之間的商品往來得以系統量化之餘,再輔以文字說明,因得以比較精準的瞭解國內當時貿易流通的趨向與本質。
近代口岸開放初期,國內區間的商品往來,自不免仍富有濃厚的傳統色彩,隨西力介入日深則日淡,是傳統經濟體制開始經歷一大變局。欲更深入瞭解此一變化,則不能不上溯明清,對傳統時期國內商品的流通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筆者博士論文因此以之為專攻,完成〈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的寫作。全文綜合明清傳統常關的設置、分佈與課稅諸要素,在一個明清全國性的商路網絡中,歸納出今日蘇南即傳統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正是國內大宗商品輻輳之地。換言之,推動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蘇南實發揮關鍵的作用。基於這項認知,想對當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近年來乃有一系列論文的寫作與發表。本書則是承其後之作。
其實包括蘇南在內的整個江南地區,向來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家勤於耕耘之所。自上一世紀五零年代以來,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開始蔚為顯學。歷來研究成果連篇累牘,罄竹難書。僅以後起之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研究而言,其雖盛起於1980年代,但迄今累計亦已達數百篇以上論文及數本專書。筆者竟不揣淺陋,不但繼續選擇江南地區做為探索的舞台,且聚焦於蘇南的市鎮,主要有見於傳統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尚有可以推陳出新之處。要言之,筆者力求對市鎮各種屬性可全面量化分析為能事。此外則側重從空間位置的角度來探索市鎮。
由於是既有工作的延續,本書有關市鎮分類的方式、各個市鎮等級決定的原因等,有些在其它已發表的著作中有說明與分析者,就不再一一註明以免累贅。
最後尚有一點須申明者,本書雖注重不同市鎮的等級分類及其空間分佈的關係,但現有史料也只能用來探索市鎮可能的大小及其正確的地理位置而已,尚不足以就功能的角度說明鎮與鎮之間實際互動的關連性。換言之,單憑現有史料,並不能從空間上斷定各個市鎮之間等級結構的關係。既然如此,對既有的各種空間分析的模式,特別如被G. William Skinnner廣泛應用來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基本結構的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影響頗為深遠的各種議論,就無從驗證其有效性。因此,本書無意在理論上有所發揮。現階段的研究,一切仍以史料考訂與實證分析為重,以現有素材待未來史料蒐羅更為齊全或醞釀出更適切的方法可資運用時,自不會迴避理論方面的討論。
序言
本書寫作構想直接源自筆者1992年底博士論文殺青時所獲致的一些見解,間接則受1970年代後期初踏入史學研究領域為學徒時的領會所啟發。個人歷年的研究工作表面上尚未達到環環相扣的程度,但關心的主旨卻始終如一,都以近代通商口岸開放以後,傳統社會所面臨的一大變局為依歸。無論其事涉一般國計與民生或進而影響民主與科學的發展,問題均化約成傳統中國社會基本經濟結構與功能的變與不變這一面向,作為探索的起點,期能從中對傳統中國過渡到現代的歷程及其意義有所認識並做適當的詮釋。
經濟結構與功能牽涉範圍廣泛,從土地利用、租佃制度、商品流通、市場結構、商業組織與商業倫理到貨幣的使用等均屬之。筆者在初窺歷史堂奧時,即專對中國國內區域間的貿易流通深感興趣,並遍讀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所編製的海關年報與海關十年報告、特別報告等。由於近代海關總稅務司署及其轄下各口岸管理機構從設立初始到相當一段歲月,均由西人所主持,傳統與國內貿易流通有關之事務,國人往往習焉不察,而疏於記載,但在西人眼中卻是焦點所在,因而留下許多西文的記錄。而尤其特殊者,則是近代海關除逐年系統性編制通商各口岸對國外的貿易流通數據外,同時亦編列國內埠際的貿易統計,特別是開港初期,商品流通數據以外,通商各港的海關年報多搭配與本口岸腹地有關的社會經濟調查報告,在近代國內區域之間的商品往來得以系統量化之餘,再輔以文字說明,因得以相當精準的瞭解國內當時貿易流通的趨向與本質。
近代口岸開放初期,國內區間的商品往來,自不免仍富有濃厚的傳統色彩,隨西力介入日深則日淡,是傳統經濟體制開始經歷一大變局。欲更深入瞭解此一變化,則不能不上溯明清,對傳統時期國內商品的流通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筆者博士論文因此以之為專攻,完成〈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的寫作。全文綜合明清傳統常關的設置、分佈與課稅諸要素,在一個明清全國性的商路網絡中,歸納出今日蘇南即傳統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正是國內大宗商品輻輳之地。換言之,推動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蘇南實發揮關鍵的作用。基於這項認知,想對當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近年來乃有其它一系列論文發表。本書則是承其後之作。
其實包括蘇南在內的整個江南地區,向來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家勤於耕耘之所。自上一世紀五零年代以來,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開始蔚為顯學。歷來研究成果連篇累牘,罄竹難書。僅以後起之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研究而言,其雖盛起於1980年代,但迄今累計亦已達數百篇以上論文及數本專書。筆者竟不揣淺陋,不但繼續選擇江南地區做為探索的舞台,且聚焦於蘇南的市鎮,主要有見於傳統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尚有可以推陳出新之處。
要言之,筆者力求對市鎮各種屬性可全面量化分析為能事。此外則側重從空間位置的角度來探索市鎮。前者在盡可能扭轉傳統市鎮研究多受史料制約,而有以偏蓋全的弊病。此如歷來研究,多傾向集中對少數非代表性,卻因相關資料豐富的市鎮,進行反覆研究,其獲致的結論往往被過度衍生成對江南一般市鎮社會經濟性質的普遍認知。關於後者,則市鎮與所在周遭鄉間以及鎮與鎮之間的互動,可具體反映城鄉之間各種錯綜的關係,是瞭解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實況的一個重要線索,然而現有研究措意於此者甚少,因此擬對之試圖有所補正。
基於上述前提,本人目前已先後發表四篇論文,分別是:〈明清江南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 、〈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 以及〈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 。除第一篇論文屬學術史範疇,針對歷年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成果作一個總的回顧外,第二論文概括指出市鎮分佈密度與蘇南區域開發動向的關連性。第三篇論文主要的發現是:1、明清以來,江南地區陸續有許多新興市鎮出現,但也不斷有許多相繼消失。能長時間持續存在的,只佔市鎮總數的一小部份;2、絕大多數市鎮的規模都很小,而個別市鎮規模之見明顯擴大者,為數亦頗為有限。據此幾乎可以斷言,明清江南地區都市化的基本特性之一,乃市鎮廣泛性成長(extensive growth)更甚於集約性的成長(intensive growth)。
市鎮的一般性質既明,而其在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角色為何,則尚有待進一步的詮釋。這方面乃有上述第四篇論文之作。主要在探討明中葉也就是1550年止,蘇南市鎮既成狀態及其所反映蘇南開發的實況。本書承其後,繼續探討至1861年止也就是近代開港通商前後,市鎮持續發展與蘇南一般社會經濟的關係。全書寄望透過對市鎮本身具體而微的分析,進一步聯繫到其與整個區域之間的互動,從而有助於瞭解傳統時期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的本質與特性。
由於是既有工作的延續,本書有關市鎮分類的方式、各個市鎮等級決定的原因等,有些在其它已發表的著作中有說明與分析者,就不再一一註明以免累贅。
最後尚有一點須申明者,本書雖注重不同市鎮的等級分類及其空間分佈的關係,但以現有史料而言,僅憑其大小與位置而缺乏對鎮與鎮之間具體互動關係的瞭解,實不足以斷定各個市鎮之間等級結構的關係。現有各種空間分析模式如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區域分配理論(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ory)等,就有派不上用場之嘆。不過,現階段研究且強調史料考訂與實證分析,以現有素材待未來史料蒐羅更為齊全或有更適當方法可資運用時,或可在理論上有所建樹。
第一章:導論
自上一個世紀五零年代中期以來,以探索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萌芽〞議題為主,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在中國大陸史學界中曾蔚為相當活躍的一支顯學。流風所被,歐美、日本漢學界在這一領域中也多有所發揮。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中國境外就其涉及領域之廣泛與深入,尤其是對日後許多探索取向深具啟迪之功者,何炳棣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一書,堪稱是最重要的一部專著。 至於中國國內,傅衣凌於五零年代中期出版的《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一書,其中所抒發的議論,也可以說是為日後整個大陸學界的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奠下了論域的基本範疇。
儘管中外特別是中西學人之間,關於如何詮釋〝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語詞的意涵,曾有過不同的見解,但就反映此一〝萌芽〞要素的具體現象而言,歷來根據中外學人特別是大陸學者廣泛發掘出來的史料,無論是從人口大量增長、 國內貿易流通量擴大、商品市場擴充、 商人與會館行會公所之興起、 經濟作物廣泛種植以及官私手工業遞嬗等角度觀之, 中外學人對於總體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遠邁前代此一說法,殆皆無所置疑。進一步,這一水平在清乾嘉時期臻於鼎盛,西方學者或慣以High Qing稱之,也多被學界視若常識般的廣泛接受。
質言之,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以來,中外許多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論著,儘管分析角度、詮釋內容以及引證的資料各有不同,其中間或也引起一些激烈的論辯,如晚近美國黃宗智對明清華北與江南經濟提出內捲化(involution)觀點而引起的爭論等。 然而,所有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在明清社會經濟日趨繁盛這一前提下完成的。明清社會經濟較前代為發達固為事實,但對於這一前提的認知本身,或者如何進一步規範與定義這個前提,對學界而言似乎從來都不構成為一個問題。
晚近在中國大陸新刊的一些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著中,儘管〝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字眼仍不免會被提到,但顯然已遠不如早期〝資本主義萌芽〞論鼎盛時期那樣,幾乎像是被奉為圭臬一般的言必稱引之。 尤有進者,還有少數研究者曾正面挑戰此一學說,而主張大幅修正或摒棄之。 不過,這些都還侷限於〝資本主義萌芽〞說有效解釋範圍的論辨而已;是就源諸於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資本主義模式,可否作為詮釋或規範明清社會經濟發展,所提出的一種思維概念上的質疑。另外從實質內容出發,具代表性者,有范金民和夏維中二位合作以及范金民個人分別在1990年代初期和末期發表的兩部專著。 二者在綜合運用大量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針對明清蘇州府和整個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進行廣泛的實證分析時,儘管其基本見解仍不外是肯定〝資本主義萌芽〞論所主張的明清社會經濟蓬勃發展這一現象,但對某些既有看法,字裡行間則隱然透露出其似有過度誇張之嫌,而持適度保留的態度。
然而,真正最難能可貴的,則是早在1985年當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尚方興未艾時,由許滌新、吳承明二位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表面上雖是就195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成果的總其成,實質上卻是對歷來基於〝資本主義萌芽〞觀點解釋明清的社會經濟狀況,做出了相當深刻的反省與修正。 相較於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論者對於明清社會經濟各方面發展所持過度樂觀的看法,該書則明白持相當保留的態度。然而,該書作者本非以批判〝資本主義萌芽〞論為職志,而且主要還是在於肯定而非否定明清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狀態之形成,只是指出其許多嚴重不足之處而已。 職是之故,隱藏在〝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包裝下,該書自出版以來,其對舊說所具有的批判性,既未對傳統明清經濟史研究趨向之變革與否,發揮過啟示性的作用,也未就該書出版時尚方興未艾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導引出任何新的思維方向與問題意識。因此,就其重要論點從未在學界引起廣泛的議論而言,該書真實的價值其實有被普遍漠視之嫌。
自1980年代以來,承襲〝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遺緒,有關江南市鎮發展的論述,開始在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範疇中嶄露頭角。僅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專對這一課題就累積下了數百篇以上的論文和幾本專書。 其實,傅衣凌早在《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那本專著中,也提到了江南經濟發展與市鎮相關的一些問題,但市鎮本身當時還不是作者專注的對象。1964年傅氏進一步發表了〈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乃專門就江南市鎮在傳統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開始有所發揮。該文著重說明:純粹基於商業與手工業活動的發展,明清特別是十六世紀後半到十八世紀前半兩百年間,江南地區無論是在市鎮本身的規模或數量方面,都有明顯擴大的跡象。再就商品流通範圍以及商業運行的機制而言,透過這些市鎮所產生的商品活動,其性質多已超出地方性的消費範疇,開始整合進全國性遠程貿易的市場體系中。 傅氏後一觀點實乃構成〝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關鍵要素之一。對此,大陸學界還曾一度就中國是否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發展出了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或民族市場;或者此一市場正確的定義為何,開展過一連串的辯論。 關於前者,其涉及江南市鎮本身諸問題,傅衣凌以後則尚須遲至1980年代,方成為明清社會經濟史學界熱切關注的焦點之一。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其論述源流、要旨、成果、方法論及其利弊得失等,筆者已另有專文做過總的評述。
既然是承襲〝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遺緒而發展出來的,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先天上就不免受限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框架的制約。實踐結果,許多研究者的確亦未能掙脫早期〝資本主義萌芽〞論盛行時的問題意識與基本觀點。如此一來,研究對象儘管縮小到以江南市鎮為中心,從而開啟了一個可對各種相關社會經濟活動開展微觀分析的契機,然而,總體結果則不過是對既有之明清社會經濟發展格局的認識,憑添一個新的議論對象,間接再予以肯定一番罷了。易言之,對一般學界而言,上述對傳統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認知這一基本前提本身,依然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從方法論的角度觀之,無論是〝資本主義萌芽〞論盛時的許多研究者,或是以研究明清市鎮為專精者,皆不免是以一個含糊籠統尚待進一步驗證,或者是並不成熟的命題,來概括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概況,爾後又引經據典的來證明這一命題。如此,自不免陷入了循環論證(tautology)的謬誤。檢討此一謬誤產生的根源,應該與研究者所探討之主體對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如何面對此一主體對象有關。
早期的明清社會經濟研究者,多習慣以一個籠統的明清中國作為論述的對象。然而,以其幅員之廣,所跨時距之大,研究者實如同面對一片比當代歐洲還大的土地,上下求索其自西方中古以來一直延續到近代的史事。此必不可免的會模糊許多問題的焦點。而更普遍的,就是易形成以偏概全的弊端。就在如此情況下,乃造就了早期〝資本主義萌芽〞論者對明清一般社會經濟史所持的基本見解。長久以來,這些見解在一般研究者心目中多已根深蒂固,形成一個不為論者所疑的認知前提。因此,後來既便是在中外漢學界中普受提倡的區域研究,或者是迄二十世紀末透過大量明清市鎮研究所獲致的種種業績,最終仍多只是重申了傳統〝資本主義萌芽〞論者,關於明清社會經濟蓬勃發展這一模糊的概念罷了。換言之,晚近縱使應用較進步的區域研究方法,或採取市鎮研究取向,舊的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典範,顯然仍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與作用。而這也正是傳統明清社會經濟研究亟待掙脫的一大困境。
〝資本主義萌芽〞論這一概念的提出,本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是夾雜學術以外一些現實因素交相運作的結果。往者已矣,當前的要務則是能對舊說展開批判性的認知;藉著反省與檢討明清社會經濟各種深層結構性的問題,從而重新認識明清中國。更有進者,則是在整個中國史或世界史的發展進程中,得以重新予以適當的定位。針對此,基於過去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缺失,新的值得思索的方向有二:一、如何對傳統明清時代已知之各種社會經濟活動,就其時間與空間屬性方面,重新做較周延的定義與規範;二、上述這些錯綜複雜的活動,可否匯總在一個具有時空縱深度的平台上,因得以察其長期的互動與影響?欲實現這些構想,或可應用區域研究的特長,同時將多種社會經濟活動限定在一個其藉以發生的實體環境中,具體探討其演化及引伸而來的種種問題與現象。
基於上述這些原則,起而行,筆者目前已有一系列的論著發表。除一篇前已提到,是對當前明清江南市鎮研究概況做一個總的回顧以外,其餘都是以明清時期江南的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也就是太湖以東地區,作為探討的基地;時間則跨明中葉迄開口通商前後;觀察的焦點則集中在作為各種社會經濟活動賴以發生的市鎮本體及其相關的各種問題。 至於研究取向方面,與現有一般江南市鎮研究稍有不同者,乃特別注重市鎮本身及其相關問題在一定時空中的變化,並力求其量變之可具體觀察與分析。為實現此一構想,筆者一方面充分利用現有涵蓋蘇南地區大比例尺的地圖,以彰顯明清各個不同時期市鎮空間分佈的狀態、趨向與變化;市鎮相互之間及其與周邊地區的作用關係。其次,對於所引用的史料,則務求其涵蓋史事的時間跨距與地域範圍,可以較清楚的界定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的主編者,就其寫作方式強調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 這也正是筆者研究方法上力求遵循的基本原則。
上述一系列論文之外,同以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為範圍,筆者另完成了〈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一文的研究。 該文與其它幾篇文章的不同處在於:前已有者除了對研究現況做綜合評述以外,探討趨向著重從量的概念,展現市鎮長期以來實質的增減及其在空間分佈方面的動向。其次則根據某些現象,從質的角度,進而歸納出市鎮總體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凸顯的某些基本特性。本書則轉以個別市鎮本身的發展歷程及其與周邊的關係為重。研究原則著重在市鎮作為蘇、松、太地區主要社會經濟活動賴以發生的有形實體,基於市鎮興起與區域發展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這一原理,市鎮本身以及與之相應的各種變化,自可作為量測當地社會經濟活動的具體指標。指標既明,則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實況自可以彰顯。
圍繞著市鎮的起源、發展與分佈,〈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一文,大致勾勒出迄1550年代止,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境內開發的動向。事實上,以一般市鎮而非府、州、縣城等政治中心在當地開始出現的年代而言,這一動向可說是上起宋、元,甚至更遠溯至唐代以來,長期積累的一個結果。其基本特徵乃在於蘇、松、太地區作為江南此一歷來被視為明清全國首富之地中的尤為佼佼者,既使到1550年止,區域內部的發展,其實仍富有濃厚的向境內邊際效益低的土地拓殖的色彩。如果如王業鍵所言,清代全國可區分為已開發、開發中和未開發地區, 則一直到明中期時,僅在江南地區既使進一步縮小到像今日蘇南這一方最富庶的土地上,也可做類似的區劃。過去對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多疏於指出這一特徵。在歷史的時空發展缺乏明確層次感的情況下,任何對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省視,自不免流於過度的一般性,此更遑論就當時全國範圍內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性質所做的任何論斷了。
迄今為止,無論名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或者單純視之為明清社會經濟較前代出現較顯著的成長跡象,學界對其發軔的年代多泛指為明中葉時。至於較確切的時間,則有說始自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或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的。 這與〈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一文,以市鎮為指標,歸納出蘇、松、太地區發展的動向,在時間的斷限上大體吻合。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本身,自然為同一地區日後持續經歷明末清初、乾嘉盛世而臻於頂峰階段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前後可茲比較的基礎。本書就是在這一前提下,以蘇南市鎮本身發展及其所牽涉的幾種核心議題為中心,繼續探索1551到1861年間,也就是相當於明中葉以來直到近代開口通商初期,其地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各種變化、性質及其意義。相對於近代通商口岸開放以後所面臨的急遽變化,本文所關注的正是傳統中的變與不變。
既然擬觀察總體社會經濟演進與市鎮發展的交互作用,因此,在進入主題以前,就有必要綜合目前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從更廣闊的角度,對包括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在內的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做一個提綱挈領式的回顧。此基本以選取一些較具量化意義的指標,或者可明確反映前後變化的歷史現象,作為回顧的依據。對於一般僅可供泛泛描述性的事件則儘量避免之。如此做,一方面可以將市鎮為主的微觀研究,襯托在宏觀的背景下,時時相互觀照,以免蒙見樹不見林之譏。然而更積極面,則是在以市鎮為主的研究過程中,各種賴以發生的社會經濟活動,可具體落實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以便得到較精準的認識。就既有之與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展史相關的一些認知,此不啻是提供了一個可具體反省其有效性或重新詮釋的機會,或者竟亦可藉以激發新的問題意識與開拓新的討論空間。
主要從蘇南地區在明清國內長程貿易發展史中的地位與作用著眼,基於明清常關稅收制度的建立與擴張、歷年常關稅收的變化、重要貿易路線分佈以及關鍵商品的流通動向等,筆者曾為文指出,由於明清戶部所屬常關職能以開徵遠距離貿易的商品通過稅為主,因此,明代宣德四年(1429)開始設立內地常關這一事件本身,基本上從制度面標誌著明清國內貿易活動開始趨於活絡。此後一直沿襲到清末,綜合常關的增置、常關分佈地點、歷年關徵額的成長、糧食與布匹作為傳統最關鍵商品的流通動向、重要商路的分佈諸要素,可以更加動態地反映江南地區在明清全國商品流通中樞紐地位的日益加重,而蘇南又居此樞紐的核心位置。
當宣德四年常關制初建立時,僅有的7個常關(當時又習稱戶關或鈔關)──漷縣(介於天津與北京之間)、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楊州、上新河,除上新河地處南京附近外,其餘皆分佈在江北的大運河沿線。隨後在十五世紀後半段期間,上述諸關或易名或取消,而陸續又有新設者。其中沿長江所設的有九江和金沙關(武昌附近);江南大運河沿線則有滸墅(蘇州附近)與北新(杭州附近)二關。以後又陸續有崇文門(北京)、蕪湖與正陽關(安徽鳳陽)的出現。終明之世,上述諸關有些時興時廢,最後只有崇文門、河西務(原漷縣關移置)、臨清、淮安、楊州、滸墅、北新、九江和蕪湖9個常關繼續運作到清代。
清代常關數量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長。清初順治年間(1644-1661)在明代的基礎上,增加到17個。這些新增者,4個在北京周圍以及張家口與殺虎口(山西朔平府)兩地。另外明代沿淮河而設的正陽關以及南京附近的上新河關恢復建置。南方地區江西與廣東交界梅嶺兩側原有的地方稅口,則分別被提升為隸屬戶部的贛關(江西南安)與太平關(廣東南雄)。康熙年間(1662-1722)常關總數進一步增為22個。新增者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屬海禁解除以後沿海而置的5個海關──山海關、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與粵海關。迄乾隆二十六年(1761)止,又再增設12個常關,總數達到34個。此後常關分佈趨於穩定,一直到清末都不再有任何大的變動。乾隆朝新增者多屬一些設置於內陸邊地的貿易關卡,如呼和浩特(內蒙)與打箭爐(川藏交界)常關等是。這反映中原與內陸邊疆地區的貿易往來,這時也開始有趨於活絡的現象。至於中原地區本身,反映廣東與廣西之間貿易流通的加強,則先後有梧州關與潯州關的設立。而最重要的,則是沿長江舊有的蕪湖、九江關以上,明代曇花一現的金沙關附近新設有武昌關(或稱武昌廠)。再向上游推進到四川,則有夔關的設置。
比較明清兩代常關的分佈,明代最早集中在江北的大運河沿線,以後則逐漸擴及蘇南與浙北地區。沿長江部分,雖然一度曾上溯到武漢地區有金沙關的設置,但後來只及於長江下游的九江與蕪湖兩地設關開徵商稅。清代則除沿舊有大運河沿線外,常關開始擴及沿海與沿長江的中上游,進一步且深入內陸地區。這反映清代以來全國貿易流通的範圍比明代有顯著的擴大。 對此,主要依據明清商路的擴充以及重要商品的流通,吳承明曾有專文做過論述。 不過,針對明清國內市場的逐步擴大,從時空的角度,依據明清常關設置的過程與分佈上的變化,可予以更清楚的界定。
相對於明中葉以來特別是清初以後,常關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分佈範圍日益擴展,國內貿易流通額當然相對也持續有大幅度的增長。一個最簡易的辨別方式,就是觀察歷年常關稅收總額的變化。就現存全國性常關稅收額資料而言,從最早的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起,一直到清嘉慶十七年(1812)止,以《明實錄》、《萬曆會計錄》、《大清會典》等官書上有記錄的幾個年份為例,可以清楚看出常關稅收額前後有相當大幅度的增加。(表1-1)以兩個最接近本書所涵蓋的起迄年代1578和1812年為準,前後增長幾達20倍之多。如果持較保守的態度,以明末以及清乾隆朝稅收額各最高的一年計(1640與1788年),則前後增長也達6.5倍之多。
表1-1 明清歷年常關稅收額表 單位:兩
大運河 長江 沿海 總計
1480 120,000
1578 219,000 93% 15,300 7% 234,300
1597 387,000 95% 20,000 5% 407,000
1625 424,430 88% 57,500 12% 481,930
1628 550,000
1630 600,000
1640 800,000
1652 554,190 68% 259,910 32% 812,100
1686 654,790 61% 414,020 39% 1,068,810
1735 1,745,570 47% 1,246,300 33% 729,480 20% 3,721,350
1753 1,985,440 43% 1,469,610 32% 1,139,060 25% 4,594,110
1777 2,110,760 41% 1,793,020 35% 1,253,890 24% 5,134,290
1788 1,856,660 36% 1,705,730 33% 1,663,260 32% 5,202,270
1812 1,684,210 36% 1,565,710 34% 1,378,660 30% 4,628,580
說明:引自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130。
在上述貿易擴張趨勢下,吳承明估計,一直到近代通商口岸開放以前的傳統時期,中國國內長距離流通商品的最大宗,明代是:一、糧食;二、棉花與棉布;三、絲和絲織品。其餘較重要者,則是鹽、茶二項。 清代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國內市場中居關鍵性的商品幾乎與明代沒有兩樣。所有這些商品中,糧食與棉布所佔的比重最高,另外再加上棉花,三種商品貿易值合計,可以佔到國內商品流通總值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雖然吳承明並沒有推估明代主要流通商品在國內貿易總額中各佔的比例,但如同清代,同樣以糧食、棉布和棉花所佔比重最大,應該是可以斷定的。換言之,綜合明清兩代傳統國內貿易流通的本質,不外就是以滿足衣食所需為首要的糧食與棉布和棉花的交換。而糧食、棉花與棉布的產銷要地,也正是國內貿易往來的重心所在。明清時期蘇南東半壁包括部分常熟縣和全部太倉州與松江府地區,是全國棉花與棉布最重要的產區。而蘇南本身同時又是全國米糧的主要集散地。來自長江中上游等地的糧食除大量供應蘇南本地消費外,也有相當數量由此進一步轉銷浙江、廣東和福建等地。
上述輔以常關制之設置、普及以及主要商品的產銷動向,可以彰顯蘇南地區在明清全國貿易流通方面的特殊角色與地位。進一步藉助於明清全國貿易路線分佈圖,可將蘇南地區此一特色更形象化的展現出來。
明清兩代曾有一些具商業背景的人士,編撰對外出從事商賈活動者非常實用的路程手冊或商業導覽,如《一統天下路程》、《示我周行》、《商賈便覽》等刊行於世。 其內容除介紹各地經商慣習及行旅中須注意的事項外,主要多是遠行者應遵循的交通路線和每日居停所止等資料。綜合這類圖籍所提供的地理訊息,可以勾勒出一個明清時代全國性的商業交通網絡。又基於上述戶部常關本身的職能,其所在自然也就是商品匯聚與主要商路通過之地,將明清兩代戶部常關位置所在,標示到明清貿易路線圖上,自然可以從錯綜複雜的網絡交通圖中,透析出整個明清國內貿易路線中的主幹及其旁支。主幹不外就是沿海、沿長江、沿大運河與沿贛江的貿易路線。前三者形成一個 的結構。進一步綜合糧食、棉花與棉布這些首要商品的流通動向,結果可以發現全國主要貿易路線的機能,最終都直接或間接與江南,特別是蘇南地區產生高度的關連性。如果再考慮清代各關稅收額之多寡這一要素,從國內商品流通的角度言,空間上可以將明清中國由東向西簡單區分成三個層次。(參見圖1-1)
(圖1-1)
圖上最內圈包括淮安關、蕪湖關、滸墅關、北新關、江海關與浙海關在內,其範圍比一個傳統的江南地區要大,相當於施堅雅所謂的長江下游巨區(the macroregion of the Lower Yangtze)。而這幾個關以清雍正、乾隆朝時為例,每年關徵額的總和,均佔全國常關稅收總額的很大一部份。 第二圈以內除涵蓋上述諸關之外,又包括其餘絕大多數的明清戶部常關所在。其範圍相當於明清中國本部精華區相當大一部分。第二圈以外的涵蓋範圍,進一步擴及少數邊地常關所在。如果說糧食與棉花和棉布的交換,構成明清國內傳統貿易活動的最大宗,則最內圈核心所在的蘇南,作為棉花、棉布與糧食產銷的集散所在,其與外地的商業整合,就如同水波漣漪般地逐漸擴散,由內圈及於外圈,越內則頻度越高,互動也就越強。
綜上觀之,蘇南地區不啻是促進與推動明清國內貿易發展的關鍵所在。當地市鎮的發展,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形成的。正因為如此,眾所皆知之明清蘇南市鎮的獨特發展,就全國範圍而言,可謂非典型的事例。因此,瞭解當地市鎮發展的實況,正有助於瞭解明清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極限。反之,以全國經濟發展之實況作為背景,亦有助於反襯出明清江南市鎮發展之實質作用及其意義。此外,基於明清江南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市鎮蓬勃興起這些既有的概念,中外許多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地域社會時,往往形成明清縉紳地主階級在城或在鄉、城居地主、城鄉分離,以及與城市文化相關的諸多命題。 而何所謂城與鄉?其間的分際如何?又如果有所謂的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或都市文明,其所據以形成的空間範疇又如何規範與界定之?再者,明清時期全國範圍的人口大量增長在學界已成共識,而集中於蘇南地區又有棉紡織工業獨特的發展,如此伴隨著全國人口增長趨勢以及本地手工業的獨特發展,則蘇南人口及手工業在城與在鄉的比例分配又如何?這又直接牽涉到江南都市化程度以及傳統手工業發展的基本性質這些議題。 這些問題究根詰底,其實都與市鎮有不解之緣。因此,本書將集中以1551到1861三百年間蘇南地區所有曾出現過的市鎮為主,就史料所可允許的範圍,從微觀的角度,對其前後變化一一究明之。此寄望於市鎮本身性質與發展概況既明,則上述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既使未必能迎刃而解,至少也提供了一個紮實的,未來可資進一步探索的基礎。
以本書欲探討的期間而論,1551到1861年亦長達300年以上,跨筆者歷來探討明中葉以來,蘇、松、太地區市鎮總體發展趨勢與擴張性質六階段分(1550年以前、1551-1722、1723-1861、1862-1911、1912-1949、1949以後)中的兩個階段:1551─1722年以及1723─1861年。 此各相當於明末清初及跨清盛世以至於開口通商前後。當時市鎮量的成長,以明中葉的1550年止為底,分別由161個增加為261和334個。 成長率分別是62%與28%。
其實單純根據市鎮量的擴張,尚遠不足以充分顯現江南城鎮化的實質意義,仍須就各個市鎮本身進行分析,方得以歸納出更有意義的內涵。筆者較早從量化的角度,在〈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中,曾估計明中葉到1980年代,所有蘇南地區各個鎮在不同時期的等級大小及其變化,因而歸結出江南市鎮發展有少數大者恆大,多數則興衰起落頻繁的一些通性。〈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一文,開始轉從傳統歷史寫作的角度,對持續至1550年止,蘇南既有之各個市鎮的實質內容與概況一一有所闡述。本書則進一步延伸及於1861年,續觀其地市鎮由明末清初經歷乾嘉盛世而有之變化,及其與周邊地域的互動。
期藉助於空間關係來凸顯市鎮本身及其與周邊發展的關連性,本書完全遵循對前一期也就是明中葉(1550年止)的探索模式,以涵蓋傳統蘇、松、太地區五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尺地圖做為憑藉,將1551年以來全部舊有與新生的市鎮一一標示在紙圖上,再就其分佈趨向區分成幾個大區與次區,以期在面積較小而又可相對應的空間範圍內,以各個市鎮為中心,進行前後期的比對與探索,最終則以歸納出市鎮與不同區域發展間的一些特性為依歸。
關於分區方面,就全國範圍而言,蘇南地區所佔的幅員甚小,地形地貌相對於全國其它各地,同質性也很高。除西側緊鄰太湖周邊的部分地區有丘陵起伏外,基本上可以沃野平疇稱之。既使如此,明中葉時基於市鎮分佈的地緣關係、水域疏密的程度,以及水、旱田相對的區隔性而言,本地仍可進一步區分成三大塊:一、鹽鐵塘主幹區;二、淀南浦東區;三、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在這些大區中有些又可以再細分。本書將沿襲同樣的劃化,以三大區中的市鎮為中心,分章進行探討。如此將市鎮完全置身於一個以自然地形地貌為背景的環境中,以觀察其與周邊地區所衍生的各種關係,此一則可以不受人為行政劃分如府、州或縣界為區隔所形成的干擾;再者,分區侷限在一個前後相同而又有限的地域範圍內,對於市鎮的舊有、新生、延續與衰亡及其影響與作用等,亦便於做更具體而微的考察。
又在前所提之〈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中,筆者綜合各種直接與間接證據加以考訂後,對於明中葉以來所有見諸於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的市鎮,就不同時期按其規模大小,分別賦以四個不同的等級。 一、通常一個鎮有二、三百戶人家或人口數在1,500以下的,歸為第一級;二、凡是有戶四、五百或人口在2,500以下者,歸為第二級;三、無論是戶數或口數都在第二類之上者,歸為第三級;四、縣治(有些縣治又同屬府治)以及州治所在,則不論其人口或家戶數多少,都一律歸為第四級。 本書以下章節凡論及各鎮等級時,都將逕以已歸類的等級稱之,而不再一一申明其出處與緣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