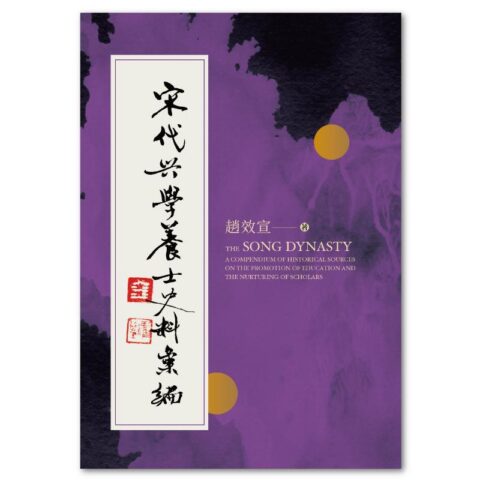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形成
出版日期:2004-08-05
作者:丘為君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52
開數:25開
EAN:9789570827118
系列:中國明清史
已售完
本書旨在探討近代中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三位啟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如何將十八世紀的知識領袖「戴震」,轉化成一個近代的文化生產場域,並產生了我們這一時代的重要知識論述。
戴震是在儒學內部最早發現「以理殺人」的思想家,從而成為五四反傳統肯定個人欲望、權利的先驅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據學代表人物。當他窮畢生精力考證經典時,西方已開始科學革命,知識體系迅速現代化。而一般認為,乾嘉之學的興起,使清代學術陷於遠離自然和社會的瑣碎考證,無疑對中國近代知識的形成具有負面的作用。戴震集啟蒙先驅和考據經師於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將戴震的考證和他的義理觀互相隔裂開來。這樣一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現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沒有甚麼關係;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便完全被視為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本書旨在探討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與清代思想主流考證學間的關係。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判與甚至是否定傳統的過程中,近代中國就知識與思想發展的角度而言,經過了什麼樣的歷程而有了今天的風貌。「轉型期中國」(1895-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在他們以「啟蒙」的旗號對傳統做激烈攻擊的過程中,是如何透過對清代知識主流考證學的反省,來詮釋並轉化那個被詛咒、污名化的「傳統」??尤其是儒學傳統,並進一步地使它與自西方引進、具有威望的所謂「科學知識」接軌。
作者:丘為君
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碩士、博士。經歷:台大歷史系兼任副教授、美國柏克萊加大訪問學人、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目前為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儒學義理系統、比較文化與思想、史學方法與理論;尤其是以近代中國的現代性經驗為主要研究主題。出版品有專書《走入近代中國》(合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編著)、《鹽水鎮誌》(合著)、《西洋史學叢書》九冊(主編)、《知識人的出路》、《自然與名教: 漢晉思想的轉折》,以及論文<杯葛.抗爭.反歧視──美國民權運動>、<來自抗爭的權利──美國「言論自由運動」>、<權威與自由: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歷程>、<啟蒙、理性,與現代性:啟蒙運動的歷史反思>、<戰後台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合著)等等。
金觀濤序:中國式自由主義的自我意識
導言
第一篇 章太炎與戴震論述的開啟
第一章 批判的漢學與漢學的批判
第二章 戴學在清學中的地位認定
第三章 作為清學中堅的戴學系統
第二篇 梁啟超與戴震論述的誕生
第四章 戴震學的誕生
第五章 梁啟超戴震研究的方法與特色
第六章 戴東原的哲學
第三篇 胡適與戴震論述的典範
第七章 從批判傳統到新詮國故
第八章 戴震「新哲學」的歷史基礎﹕反玄學運動
第九章 戴震「新哲學」的內涵﹕道論、性論、理論
結語
附錄: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義涵
主要參考文獻
代序:中國式自由主義的自我意識
金觀濤
由於歷史已不再能闡明未來,人類的心靈在黑暗中徘徊。
—托克維爾
2001年8月丘為君教授來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知悉我正在做有關戴震哲學與中國式自由主義之間關係的研究。為君兄告訴我,他寫作多年的著作《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即將出版,希望我為該書作序。我認為,為君兄將戴震與中國近代學術體系相聯繫,並以戴震學的形成作為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誕生之標誌,這是極為重要的論斷,值得思想史研究者重視。
今天一談起戴震在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位置,學術界常常是處於一種自相矛盾、令人難堪的地位。眾所周知,戴震是在儒學內部最早發現「以理殺人」的思想家,從而成為五四反傳統肯定個人欲望、權利的先驅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據學代表人物。當他窮畢生精力考證經典時,西方已開始科學革命,知識體系迅速現代化。而一般認為,乾嘉之學的興起使清代學術陷於遠離自然和社會的瑣碎考證,無疑對中國近代知識的形成具有負面的作用。戴震集啟蒙先驅和考據經師於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將戴震的考證和他的義理觀互相隔裂開來。這樣一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現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沒有甚麼關係。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完全被視為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
2000年在蔣經國基金會資助下,我與劉青峰、周昌龍、張壽安夫婦和王靖宇教授合作,開始探討有關自由主義的中國本土資源問題。我和青峰研究的題目是比較戴震哲學的理念型(Ideal Type)和胡適的實驗哲學。當時,引起我們做這項研究的是這樣一個疑問:為甚麼作為五四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會對乾嘉考據大師戴震有終生不渝的興趣﹖我們寫了一篇論文來探討這一問題,並得到兩個有點意外的結論:第一,戴震之所以能提出綱常名教「以理殺人」的論斷,是由於他持有一種類似於西方唯名論式的方法論。他認為唯有個體或具體的陳述才是真實的,任何普遍的規則,包括綱常名教都只是名,它們之所以正確,無非是反映一個個具體案例的共性罷了。這樣,戴震雖然並不反對儒家倫理,但堅持任何倫理原則必須從具體個案中抽出;當用普遍的倫理的原則去扼殺人自然的感情、否定具體情景中可以理解的行為時,就可以「以理殺人」。第二,胡適的實驗主義真理觀表面上來自杜威,但在本質上卻是戴震哲學的翻版。
表面上看,戴震建立的考據學知識體系似乎和他的新義理觀沒有甚麼關係,但是如果將其提高到終極關懷層面來分析,則發現兩者恰恰是同一心靈的表現。戴震意識到,唯有個體和具體的陳述才是真實的,這意味著某種有現代意識之心靈在中國文化中的湧現。但與此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中國文化是以道德為終極關懷,道德背後的基礎是常識。一旦抽象、普遍的理不再存在,那麼為了理解甚麼是道德,就必須把修身轉化為一種「求知」和「去蔽」的考證活動。這與十七世紀新教徒不同,他們是去發現足以證明上帝全能之新奇的宇宙規律。換言之,戴震一輩子建立起來龐大的考證知識體系,只是在常識理性支配下崇尚個體為真實、追求道德活動的結果。胡適思想模式與戴震的同構的意義更不尋常。兩者的同構似乎表明:戴震式的視個體和個別陳述為真實的方法是五四後中國知識份子接受西方自由主義之前提。也就是說,五四新知識份子也往往同樣持常識自然觀並以道德為終極關懷。這樣,在他接受西方現代知識體系時,並不妨礙其知識活動仍遵循類似於戴震的典範。換言之,如果戴震視個體為真實是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那麼清代考據學也可以視為中國近代知識論述的源頭。
我們說,戴震的心靈和學術活動具有某種現代色彩,絕不是說中國現代知識體系和自由主義是從這一源頭發展出來的。無論現代自然科學、社會人文科學,還是個人權利、民主共和觀念,均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所謂中國式自由主義將戴震哲學作為自己的本土資源,其準確含義是指當五四後知識份子接受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以學術作為終極關懷時,他們會發現自己心靈和戴震存在著同構性。這樣一來,中國近代知識之誕生和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且所謂中國近代知識體系,並非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主體,而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知識活動的某種特殊典範。這一典範之成熟和戴震學的形成關係密切。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戴震學如何形成,是追蹤中國式自由主義心靈在西方衝擊下產生之過程,它對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研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這正是為君兄的這本新作《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的意義所在,它為中國近代知識論述之誕生與思想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眾所周知,對戴震的介紹、研究和推崇主要是通過章太炎、梁啟超和胡適三個人的工作來實現的。但為甚麼恰恰是他們三人﹖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各對戴震學的形成作出了怎麼樣的貢獻﹖戴震學形成的思想史的含義又是甚麼﹖為君兄用富有說服力的證據指出,戴震學的凸現意味著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而章、梁、胡三人正好代表了戴震學形成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有多重角色,首先他作為古文經學大師,也是清代考據之學的傳人,深知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知識體系絕非支離破碎,而是存在著自身的意義結構的。其次章太炎是唯識論最深刻的論述者和倡導者。唯識論視社會組織、群體為虛幻,使得章太炎是晚清最早的個體主義者。事實上,也正是這兩個思想史因素使得章太炎成為戴震學的開啟者。
如果說章太炎注意戴震是由於某種思想傾向上的巧合——對考據意義結構的了解和唯識論的個體主義,那麼梁啟超對戴震之重視則代表了對自由主義中國本土資源的意識。為君兄十分深刻地指出,梁啟超是在他生命最後十年才認識到戴震學的重要性,這是梁啟超政治生涯的失敗轉而以學術為志業的結果。梁啟超與嚴復同為西方自由主義的最早介紹者,但他在政治哲學甚至思想方法上,從未認同過唯名論,也不是一個個體主義者。何況作為康有為的學生,從事今文經學的早期經歷而使得梁啟超不太能理解戴震考據系統的意義結構。那麼,為甚麼梁會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推崇戴震,並成為促使戴學在中國誕生第一人呢﹖正如為君兄所指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梁啟超發現戴震追求知識之方法和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科學精神相合。梁啟超已經感受到,五四後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果以學術為志業,那麼戴震和相應知識體系是不可忽略的中國傳統。
梁啟超雖然可以視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也是戴震學的催生者,但梁啟超的思維模式不能代表五四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的學術活動典範也與戴震不同。真正與戴震心靈同構的現代知識份子是胡適。胡適在成為五四時自由主義代言人之前,並沒有讀過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但胡適一看到此書,就被其吸引,認定戴學是中國新時代科學的哲學之源頭,並從此一生為捍衛戴震在中國學術界地位和道德形象而奮鬥。正因為他的提倡,確立了戴震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中不可動搖的地位。為君兄詳細討論了胡適對戴震新義理觀及研究方法的論述。我認為這一論述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成熟和自我意識之呈現;第二正因為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考據之學只是崇尚個體的心靈在常識理性限定下從事學術之結果,那麼類似的知識論述一旦誕生,並不會隨著社會現代轉型而終結。事實上,無論是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還是1920年代末中國式自由主義者轉向純學術而發起的古史辨運動,不是戴震知識體系之現代繼續嗎﹖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只是我閱讀為君兄著作的心得,絕不能用它來代表這部著作複雜而深入的內容。我只是想用此來凸現這本書的重要性。為君兄和我談起戴震學的研究,常感慨今天的學人因該題目過專過窄而輕視它,甚至認為與現代毫不相關。我對此深有同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思想史上,人類越是陷入某種思想典範之時,對這種典範之起源則越不感興趣。今天隨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凸現,不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陷於戴震式的學術研究嗎﹖至今我仍記得與為君兄談話時的情景,悠揚的上課鐘聲陣陣傳來,在相思樹林的上空迴響。不知何故,我心頭湧起一種難言的傷感,已經多少年沒有聽到這種鐘聲了。思想史研究者是以思想的興起和演變作為學術研究的人。在戴震的時代,道德真理和歷史終極意義尚未解構,以求知為終極關懷的個人主義心靈雖然緊張,但還不至於陷於空虛和絕望。而今天自由知識份子出於對社會發展規律之否定,不得不在越來越瑣碎的知識追求中消耗生命,等待死亡。這時追溯戴震學的形成確實是意味深長的。它使我想起梅瑞慈寇夫斯基(D. Merezhkovskii)在《先行者》中的詩句:
「這裏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當時四周幽暗,萬物皆在沉睡。」
它不僅屬於戴震,也屬於今天不甘於淪為細微瑣碎知識追求之思想史研究者。
導言
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清末民初的研究﹐不論是美國、日本,或者是大中華地區,都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那便是傾向於「傳統崩潰」及其所衍生的相關議題。以北美來說,自二十世紀中葉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裡取得領導地位、並以提出「西力衝擊說」(theory of Western impact)而建立其學術特色的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不論是在他影響深遠的早期代表性著作、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或則是在史學專題領域裡建立其典範地位的《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條約港口的開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1953年兩冊本),或者是他晚年心力灌注所在、以「略遠詳近」作為風格的遺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中,「傳統崩潰」一直是他關注的重點。就費氏而言,中國邁向現代的過程之所以困難重重,其關鍵在於盤據中國達千年之久、作為中國文化基調的儒家學說與思想。在他看來,帶有「禁慾主義」(asceticism)世界觀特徵的儒家思想,與強調「世俗主義」(secularism)的現代性,本質上是互相衝突的。換句話說,中國傳統的崩潰,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儒家中心觀」的崩潰。
對照美東史學理論興趣相對薄弱的費正清,理論意識強烈、具建構宏大體系企圖的柏克萊加大李文遜(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則更將這種「傳統崩潰」研究特質,淋漓地表現在他有關中國研究的主要著作中。這位被美國學界稱之為「莫札特型」(Mozartian)的學者,在他1965年出版的三卷本代表性著作《儒家中國的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裡,展現了與費正清見解不相背的觀點。李文遜認為,近代中國的發展基本上在反應西方的挑戰(Western challenge);然而由於無法有效回應來自帶有擴張主義企圖的西方挑戰,中國最終是屈辱地被迫放棄它自認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主義(culturalism),從而接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意義上的「現代化」。此一轉變,是中國由作為「絕對性」象徵的儒家世界大同主義,轉向「相對性」的西方實用主義價值。就意義而言,由於儒家世界大同主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中國此一轉向也就意味著傳統儒家已經敲響了喪鐘。同費正清的立場一樣,這位早夭的猶太裔美籍學者堅信,中國的儒家傳統與現代性是不相容的。
最能結合理論與實際以開展「傳統崩潰」課題的學者,恐怕要屬在近代中國研究領域享有崇高聲望的日本京都大學小野川秀美(1909-)。與美國費正清和李文遜屬同一世代崛起的學者,小野川秀美在他的代表性研究裡,展現了與美國「西方本位主義」觀點不同的風貌。不同於費、李兩氏的消極性論點,小野川認為中國在晚清對西方挑戰所做的回應,其實是生機淋漓的。在其享譽學界的名著《清末政治思想研究》(1960),小野川氏從「中國中心觀」出發,以洋務論、變法論及革命論等三階段作為敘述架構,生動地闡述了晚清高潮迭起的政治發展:1860年代「師夷長技以治夷」的自強論、1890年代以「經書」與「西政」為核心的改革論,以及1900年代與變法派合作終至分手的革命派的論述。小野川秀美的洋務論、變法論及革命論等三階段論證,表面上看似乎比費正清和李文遜具化約論傾向的「挑戰/回應」(challenge-response)說細緻與繁複,但本質上仍然不脫「傳統崩潰論」取徑,即便小野川秀美本人並不刻意地展示自己為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積極支持者。
在大中華區域,就中國大陸大言,「傳統崩潰」更是清末民初時期研究者的基調。與西方學者不同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大陸學人在1990年代之前,似乎傾向於機械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僵化地詮釋中國在近代時期所做的轉變。以曾經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1918-2000)為例,他基本上並不全然認同洋務論、變法論,與革命論等具有「政治性質」的三階段論證,而是主張從「社會性質」來看待近代中國的變革。這位與中共中央有深厚淵源的學者,贊同一種為中國大陸學界與政界所接受的共同看法,認為中國傳統的徹底終結,應該以1949年「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為界線,在此之前至1840年鴉片戰爭的一百一十年歷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可以界定為「中國近代史」;在此後的「社會主義時代」,則可稱之為「中國現代史」。
在代表性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80)裡,胡繩將上述的「社會性質」史觀,用馬克思學說的「階級革命」理論與「反帝鬥爭」觀點,進一步地以四期來探討中國從晚清至民初之間的變動與變化:第一期,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失敗(1840-1864);第二期,從太平天國失敗後到義和團運動(1864-1901);第三期,從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到辛亥革命(1901-1912);第四期,從辛亥革命失敗後到五四運動(1912-1919)。根據胡氏,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社會革命力量是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農民,至於第三期與第四期的社會革命力量則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姑且不論胡繩分為四期的「社會性質」歷史觀點,是否比小野川劃分成三期的「政治性質」歷史觀點來得有效,他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與「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視為傳統秩序崩潰與新秩序建立之分水嶺的史觀,其「政治性質」事實上是十分明顯的。
對照「傳統崩潰論」主張者的研究取向,本研究旨趣正好相反;它重視的不是相對具消極性意義的崩潰面向,而是強調中國傳統在轉進現代(modernity)時,若干具有積極性的建設性面向。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在轉進現代之際,並不是以「全面性潰敗」作為唯一的反應,它也有其他適宜的應對機制。從物質層面(尤其從軍事層面)看,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本質,作為亞洲長期第一強權的中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全面而快速潰敗的表現,的確令人映象深刻。但是若從文化層面看,情況似乎沒有那麼悲觀。事實上就清末民初時期而言,相對政治與軍事層面上每況愈下的表現,文化創新的力量,則可以說是活力充沛的。弔詭的是,文化上這種生機淋漓的現象,卻是與為人所詛咒的、逐漸升高的國內、外壓力有關。
如果說壓力帶有價值判斷的色彩,那麼與此一字眼接近的「張力」(tension),或許更貼切我們所關切的課題。從歷史角度看,當某一社會在經歷劇烈變動時(例如由傳統急遽轉入近代),經常會面臨某種難以承受的「張力」狀態。由於沒有更恰當的字眼來形容此一「張力」情境,我們姑且稱之為「轉化中的張力」。以近代中國為例,這種帶有焦慮特質的「轉化中的張力」,至少與兩種變化有關:第一,來自帝國外部的力量;其次,來自帝國內部的力量。前者相對容易理解,它主要是與西方列強(與稍後的俄國與日本)的帝國主義有關。此一力量對有二百年帝國霸業的清室造成何種心理壓力,我們可以從專制王朝最敏感的軍事武力一項窺見一斑。當外來的、帶有強制意圖的西方(與俄、日)擴張主義,逐漸發展成清朝建國以來前所未見的軍事與外交壓迫時,以少數族群(滿人)為基礎的統治菁英,除了竭盡所能尋求體制內各種應變資源,同時還冒著巨大危險,去接受體制外的、極可能帶來不確定後果的其他資源¾¾國家體制外的地方武力組織,以共同對抗因外患而趁機挑戰國家體制與社會秩序的本土性叛亂團體。
然而「轉化中的張力」並非如多數人所注意到的,純粹是由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壓迫所啟動的。事實上,它也有很大的部分是來自內部的力量:例如作為社會變遷重要指標的人口成長,便是在清末民初歷史發展中,經歷了一場準「馬爾薩斯式困境」(Malthusian predicament)。根據何炳棣的研究,十八世紀初葉,中國人口大約在一億五千萬左右,但不到一百年卻暴增一倍,於1794年到達三億一千三百萬人。在這種近乎戲劇性變化的發展裡,中國人口到了1850年的太平天國革命前夕,更是激增至四億三千萬人。如果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古典人口理論,即人口呈幾何級數成長而食物呈算數級數成長,具有參考價值話,那麼像中國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度裡,在耕地面積與耕種技術未能有效突破的前提下,人口大增便意味著耕地面積相對減縮與生計問題相對困難。作為被馬克思所注意到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農民起義事件,太平天國革命軍之所以能在以江南的十六個行省中攻佔三百多個重要城鎮,並使內戰綿延達十四年(1850-1864)之久,顯然與中國當時的農民生存困境有關。
上面的「傳統轉化論」說明,並非意味作為理解近代中國變革現象的「傳統崩潰論」歷史解釋無效,或者是說,儒家秩序的崩潰不曾存在於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裡。的確,就外貌而言,作為傳統學術與文化權威的「經學」,是在處於瓦解而不是增強的過程。我們這裡所想指出的是,中國傳統(不論是儒家還是非儒家的)在晚清那個經歷時代的巨變裡,並非純然以「全盤性崩潰」的面貌來反應西方的挑戰。事實上,「轉化中的張力」在某種意義下,啟動了中國知識菁英某種潛能。這種潛能,有些確實是出自儒家的「經世」意識,例如適時地引進「優勝劣敗」的進化思想,或者積極地闡釋與鼓吹「富強」的觀念,便是對當前政治社會危機做出有效的反應。但是,這種潛能也有不少甚至是超越了現實中的危機,而指向更深層的關懷,例如像對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探討,以及對生存之本質或生命之價值與意義做出不凡的思考等。
本研究的課題不是關於考據學在「後滿清時期」的發展。作為考據學泰斗的戴震之思想以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也不是本書的重點。基本上,我們這裡提出了這麼個問題:在激烈地批判與甚至是否定傳統的過程中,「轉型期中國」(1895-1925) 就知識與思想發展的角度而言,經過了什麼樣的歷程而有了今天的風貌。或者更精確地說,「轉型期中國」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在他們對傳統的激烈批判裡,如何有意識地詮釋並轉化那個被詛咒、污名化的「傳統」¾¾尤其是儒學傳統,並進一步地使它與自西方引進、具有威望的所謂「科學知識」接軌。在這個「舊酒新瓶」(也許是「舊瓶新酒」)的改造工程中,我們看到同時擁有相對豐富知識資源(包括傳統與現代)的章、梁、胡三位啟蒙學者,憑藉著他們在中國知識界的不凡影響力,將十八世紀的知識領袖「戴震」,轉化成一個近代的社會文化生產場域,並產生了我們這一時代的重要知識論述(intellectual discourse)。
必須指出的,本研究並非要探討「後戴震時期」的「戴震學」,或「戴震學派」在「後戴震時期」的形成與意義。因此基本上我們不擬上溯到十八世紀那個以考證作為形式的知識論述。在方法論上,我們強調的是探索「戴震學」現象的「開始」(beginnings),(更精確的說,在近代的開始),而不是具有無限上綱意義的「源頭」(origins)。誠然,「開始」與「源頭」意思接近,不過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角度而言,兩者意義卻不相同:「源頭」意味著「原因」(causes)而「開始」則意味著「區別」(differences)。職是之故,本書對考證學在傳統中國的發展與意義著墨不多;但是對章太炎、梁啟超,與胡適這三位近代中國最具威望的理論家,在其區別地詮釋考證學的近代意義上,則有所關注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