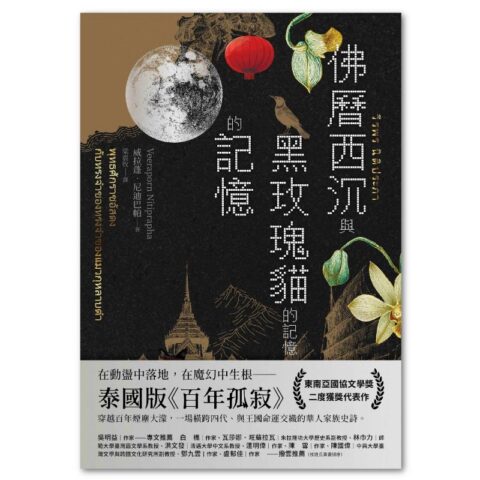夜曲
原書名:Nocturne
出版日期:2010-10-29
作者:石黑一雄
譯者:吳宜潔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0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7001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人生宛如一首歌而那個願意聽我唱歌的人身在何方?
五首曲目,五個音樂與日落的故事
英國布克獎得主石黑一雄,繼《長日將盡》《別讓我走》最新抒情力作
終究,只有音樂能回答音樂。
卻也還好有音樂,在這樣破碎的世界裡,我們便還存在著對完好的希望。
Venezia,威尼斯。一位露天咖啡座的吉他手,在聖馬可廣場巧遇母親昔日的偶像、曾經紅極一時的實力派歌手。為了音樂,他們即將付出無可估計的代價。
London,倫敦。大學時代的死黨在多年之後聚首,因為熱愛音樂發展出的友情,如今卻失去了最關鍵的那個部分。在熟悉的音樂響起時,往昔的美好即將再現?
Malvern Hills,墨爾文丘。在姊姊經營的咖啡館打工的音樂系學生,今天要帶的客人是巡演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夫妻檔;山間吹起一陣風,夫唱婦隨的音樂人生,開始轉向……
Los Angeles,洛杉磯。鬱鬱不得志的薩克斯風手,決定變臉求活,走上人造型男一途;滿臉繃帶的他卻突然來到舞台,這下是見光死還是提前適應新人生?
最後,再度來到Venezia,威尼斯。年輕大提琴手遇見一位神祕的老師,他尚未被挖掘的天賦,將因此被世界看見?
將心的碎片細細一一撿拾,安納在夜色與樂音之中
世界級的小說家石黑一雄,令人傾心的深情五連作
紐約時報、衛報、洛杉磯時報、娛樂周刊、泰晤士報、倫敦書評等國際媒體高度注目
各界創作人 著迷推薦──
★劇場音樂家-陳建騏 ★樂團1976主唱-陳瑞凱 ★《聽見蕭邦》作者-焦元溥
★導演-林書宇 ★作家、導演-傅天余 ★作家-李欣倫
★音樂人-張懸 ★作家-陳柏青 ★詩人-鄭聿 ★詩人-羅毓嘉
★《MUZIK謬斯客古典樂刊》發行人-孫家璁 ★台大社會系專任助理教授-李明璁
★樂團熊寶貝主唱-餅乾 ★音樂人-黃玠 ★音樂人-吳志寧 ★資深樂評-馬欣
★《對我說髒話》新聞台版主-DIRTY TALK ★自由創作者-高倩怡JOJO KAO
★文字創作者、假文藝青年俱樂部主唱-Tzara ★樂團滅火器主唱-楊大正
★THE WALL音樂展演中心-傅鉛文orbis ★樂團草莓救星主唱、木吉他手-腊筆
1989年,時年36歲的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以第三部長篇《長日將盡》獲得英國文學最高榮譽──布克獎,使得其後的每回出手都備受注目。繼2005年的《別讓我走》,石黑一雄首次推出主題一致的五個短篇連作故事集──《夜曲》。在《夜曲》出版前,石黑一雄接受《衛報》訪問,正式對短篇小說集不如長篇小說這一普遍的看法提出見解。石黑一雄表示,對多數的文集而言,可能是作家在一段時間作品的收錄,「但我一直抗拒說這本書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因為,小說家也是會出版短篇小說集,但是小說家出版的集子比較像是他們把過去三十年寫的短篇,丟進麻布袋就出版的感覺。而這本《夜曲》,我卻是坐下來從開始寫到結束。」
成名甚早的石黑一雄鮮為人知的是,他一開始創作的標的並不是文學;五歲開始學鋼琴、十一歲就迷上搖滾樂的他,年少時就如同所有有過音樂夢的搖滾青年一樣,不停地創作歌曲,錄製試唱帶寄給各大唱片公司。石黑一雄表示,但早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已清楚,自己在音樂方面的天賦有限,不可能成為專業的音樂人:「我無法在音樂界繼續走下去,但卻發現,我寫得出小說。所以我覺得,從寫歌轉變成寫小說,是一個很自然的改變與決定。」因此,無論是早期作品《群山淡景》所顯露的氤氳調性,還是《長日將盡》如歌的時代變遷,皆透出石黑一雄小說經常被提及的「音樂感」,在故事之外,氣氛的營造更是石黑一雄的小說世界最核心的元素。
在最新作品《夜曲》裡,音樂被石黑一雄擺到最明顯的位置。五個故事的主角都是為了生活庸庸碌碌、極其平凡的人物。不管年歲是落於青春正盛之時還是中年之初,這些人物共通擁有的是未竟的夢想,一個從來沒有實現的理想人生;音樂在小說裡成為人物間情感的連結與樞紐,許多未能說出口的,都在小說點寫的樂曲裡傾瀉而出。五個皆為第一人稱寫作的短篇,故事從義大利威尼斯起終結至威尼斯;如同原書副標題「五個音樂與夜幕將臨的故事」,高潮多發生在夜晚或落日餘暉之際,再者,讓角色的身分相近但又不說破的設定,呼應著音樂語言餘音不絕的迴盪特質;因為音樂,讓五個看似不相連的短篇以之收納,這就是石黑一雄一再強調的:「這還是一本小說,只是分成五個不同的樂章。也許,更好的說法是,這本書比較像是一張專輯唱片,你就是不希望有些歌被用單曲的方式發行。」。
作者:石黑一雄
1954年11月8日生於日本長崎,1960年其父轉往英國國家海洋學院進行研究,舉家遷居英國。大學時代石黑一雄進入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主修英文和哲學,畢業後再到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攻讀創意寫作學位。著有多部獲獎小說,作品被譯超過三十種語言。1995年,因著對文學的貢獻而獲頒OBE勳章,現為英國皇家文學會研究員。
石黑一雄目前共出版六部長篇小說:1982年《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獲得「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獲英國及愛爾蘭圖書協會頒發的「惠特布萊德」年度最佳小說獎(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和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提名;1989年《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榮獲英國布克獎,並登上當年《出版家週刊》暢銷排行榜書單;1995年《未能撫慰者》(The Unconsoled,石黑一雄唯一一本尚無中譯作品)贏得「契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Cheltenham Prize);2000年以《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再次獲得布克獎提名;2005年《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入圍布克獎最後決選名單,並獲全世界文學獎獎金最高的「歐洲小說獎」(European Novel Award)。
年輕時尚未成為作家的石黑一雄曾投入社福工作,其移居者的特殊背景,使其常跟V. S. 奈波爾(V. S. Naipaul)、薩魯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等以英文寫作的非英語系作家相提討論,但「移居者的身分」恰恰是石黑一雄小說裡最隱晦甚至不成為寫作重點的「反高潮」,個人如何不被群體因素例如種族給框架,側重現代人個人孤獨景況的深沉寫作特質,被英國衛報評為「當代最接近卡夫卡小說世界」的作家。
譯者:吳宜潔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瑞汀大學兒童文學碩士。覺得人是最奧妙深邃的文本,期許自己能盡可能地詮釋、解讀。現為專職譯者,譯有「瑪麗.包萍」系列、《完美:一個背叛與重生的故事》等。個人部落格「葉的雨滴」:leafrain.blogspot.com
抒情歌手
或雨或晴
莫爾文丘
夜曲
大提琴手
媒體書評推薦
石黑一雄的短篇集《夜曲》,收錄的都是失意的故事,只不過主角換成中年人,而且多從事音樂工作,一如石黑年輕時也曾在酒吧和地鐵獻唱。五個短篇也頗有組曲意味:人到中年,卻只能自欺欺人。像〈或雨或晴〉裡有婚姻危機的丈夫,請老同學來家裡作客,卻是為了讓妻子知道還有人比他更落魄;〈夜曲〉中的薩克斯風樂手,為了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允許妻子的情人資助自己整容,還希望一張新臉能挽回婚姻;〈大提琴手〉裡前途無量的匈牙利新秀,找了一位根本不懂琴的美國女子指點,就因為她聲稱自己會是個大器晚成的巨匠,結果她所嫁非人,他則淪落飯店餐廳當伴奏。音樂在石黑的筆下成了架空的理想,所有的人物只能在欺瞞之中,尋找片刻的尊嚴。
/《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從義大利的露天廣場到莫爾文丘,從一間倫敦公寓到奢華的好萊塢旅館裡的祕密樓層,《夜曲》是一系列沉穩而幽默的、對於感情如何遭背棄的沉思。故事的主角有年輕的夢想家,也有咖啡館樂師,還有過氣明星。他們或沉浸於一日之終的感傷,或遭遇了友情或愛情的終結。石黑一雄以其古怪而異質的幽默感處理這些黑色主題。他繼續使用第一人稱男性的不可靠敍事法,其效果與他的近期小說並無二致:一種來自內心的、或者說懺悔式的語調。這些短篇小說令人回想起石黑一雄最著名的小說《長日將盡》,它們超現實的氣息與《未能撫慰者》形成共鳴,而故事裡對於愛與痛的探索則建立在《別讓我走》的成就之上。
/中國《南都周刊》
書中的每一篇故事,都有其心碎之處;有些片段無疑是傑出的喜劇,而這些片段,足以深深吸引讀者,這正也是石黑一雄作品的菁華。
/湯姆.弗萊明(Tom Fleming),《觀察家》(The Observer)
這些故事不是真的關乎音樂,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更像是感情關係的研究,關於名聲、成就等再現實不過的處境。
/強納森.柯伊(Jonathan Coe),《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不同於過去作品……書中有許多相當有趣的段落。
/克里斯多福.泰勒(Christopher Tayler),《衛報》(The Guardian)
這是一本可愛、聰明的書。那些時光流轉與悠揚的音符,讓這趟旅程絕對值得。
/克莉斯提安.豪斯(Christian House),《獨立報》週日版(Independent on Sunday)
石黑一雄這些故事的人物似乎似曾相識,無論是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名人,作者對這些故事、情緒以及想法,在在表現了世界的真實模樣。他的創作有種原創的可辯性。不過,有時出乎意料之外——發想自奇想與同情,當然,其中也隱含了虛榮——在其中一個故事〈夜曲〉,第一個故事裡被冷落的妻子似乎再度回到小說當中,將石黑一雄的作品拉到另外一個層次。
/丹尼爾.蓋瑞特(Daniel Garrett) ,《當代小說評論》(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石黑一雄的作品,有著如歌似的韻律,反覆出現的主題,發展出不同的模樣。初讀這些故事,它們狀似不具表情:措詞生硬、敘事單調、故事結構搖擺不定,但字裡行間卻透出音樂語言中指稱的高泛音(意指聲音被擊出後所產生的回音),隱藏在看似單調的敘事底下;掩卷之餘卻頻頻回聲,餘音久久不散。
/珍.施玲(Jane Shilling) ,《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
五個故事都出現不可靠的男人,通篇全採第一人稱敘事。給人的感覺就如同石黑一雄近期的小說:極其私密,或說是告白式的,語氣刻意輕鬆。《夜曲》像是集合許多從容不迫又好玩的思緒,刻畫出漸行漸遠的感傷。石黑一雄以他古怪、獨樹一格的幽默,帶出這些小說的幽暗主題。
/露絲.史卡爾(Ruth Scurr) ,《泰晤士報》(The Times)
這一組精心打造的故事,沒有用上太多材料卻是驚喜連連,使讀者讀來感覺豐富、樂趣橫生。讀完這五個故事不禁令人好奇,石黑一雄下一次又將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故事?
/麥可.葛拉(Michael Gorra)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名家推薦
在生命的低迴處,樂聲還沒響起的靜默一拍中,我腦海裡偶會浮現萩原朔太郎的詩句:「把心比喻成什麼好呢?」只逕問,不許答,那也許是關於「音樂的比喻」最好的回應。終究,只有音樂能回答音樂。而在石黑一雄的小說中,他不借音樂回答人生,生命只是音樂的一個不諧和音,人們所驥求,何其卑微,無非是某一瞬間的合拍,或水波拍櫓處於彼岸所傳來的和聲而已。卻也還好有音樂,在這樣破碎的世界裡,我們便還存在著對完形的希望。
/作家 陳柏青
《夜曲》正是這樣一本小說--生活的富饒或困頓,從來不曾真正改變我們為某個人演奏的心情,我們只是忘記了,忽略了,總有一種方法可以帶領我們回去。結褵二十七年而為了「遊戲規則」分開的歌手和女明星,懷抱夢想的音樂少年,貌合神離明明想靠近卻無以為繼的中產夫妻,其貌不揚的爵士樂手……石黑一雄在作者自述中說各個篇章之間並無必然關聯,但其實隱於文字背後反覆重現的變奏、複沓的迷魅小調,是時時刻刻潛匿在你我、我們、與他們之間,那細瑣的生存關係之齟齬、斷裂、和傷害。
/詩人 羅毓嘉
捷運上讀《夜曲》,文字很好,很沉穩,心很快就靜下來。有畫面有意象還有一種舒緩的節奏,捷運報站名都遙遠像遠方。或者我已經在遠方了。
/作家 李桐豪
或雨或晴
愛蜜麗和我一樣,喜歡老派的美國百老匯歌曲。她偏好快節奏的曲目,像是艾文.柏林(Irving Berlin)的〈貼臉相偎〉(Cheek to Cheek)和柯爾.波特(Cole Porter)的〈愛的開始〉(Begin the Beguine),我偏好苦甜參半的民謠——像〈又見雨天〉(Here’s That Rainy Day)、〈不曾入心〉(It Never Entered My Mind)。雖然差距頗大,但那個時代要在英國南部的大學校園找到同好,簡直近乎奇蹟。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各種音樂類型都聽。我有個姪子今年秋天上大學,迷上了阿根廷探戈音樂,他也喜歡愛迪.琵雅芙以及最新的獨立樂團。不過,在我們那個年代,品味選擇沒這麼廣。學生大致分成兩派:一是長髮寬衣的嬉皮,酷愛「前衛搖滾」;一是整齊端莊的古典樂迷,其他音樂一概棄如敝屣。偶爾,你會巧遇嗜愛爵士的人,但這些人通常是所謂的跨界類型——狂放無盡的即興,而那些最初始、讓人愛上音樂的美麗歌曲,他們是不會看在眼裡的。
所以,當發現有另一個人也欣賞美式音樂時,真是鬆了口氣,而且還是位女性。和我一樣,愛蜜麗專門收集黑膠唱片,鍾愛細膩、直率的唱腔——你經常能在骨董店找到這些我們父母那輩丟棄、遭到賤價出售的唱片。她偏愛莎拉.芳恩(Sarah Vaughan)和查特.貝克;我鍾情茱莉.倫敦(Julie London)和佩姬.李(Peggy Lee);辛納屈或艾拉.費茲傑羅都不是我們的菜。
頭一年愛蜜麗住校,她的房裡有台手提式唱機,是當年相當流行的機種。看起來就像只大帽盒,淺藍色的表皮,單顆內嵌式喇叭,得先掀開蓋子才能看見裡面的轉盤。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音質滿粗糙的,但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倆總窩在一塊兒,開心地連聽上好幾個小時;取下一張唱片,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針挪去另一張上頭。我們喜歡比較同一首歌的各種版本,然後相互討論歌詞和歌手的詮釋:這段非得唱得這麼酸不可?〈我心上的喬治亞〉(Georgia on My Mind)——究竟該把喬治亞當成個女人、還是美國的一個地方來唱?我們尤其喜歡那種歌詞明明洋溢著歡樂、唱腔卻令人徹底心碎的唱片——像是雷.查爾斯(Ray Charles)的〈或雨或晴〉(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愛蜜麗是如此熱愛著這些歌曲,因此,每次聽到她與其他人討論起裝腔作勢的搖滾樂,或是毫無內涵、那掛加州歌手,我總是詫異不解。有時,她跟他們討論某張「概念」專輯的熱忱,並不亞於我們倆討論起蓋西文或霍華德.愛倫(Howard Arlen)時的專注;我只能緊咬嘴脣,以免透露出我的不悅。
那時的愛蜜麗,身材修長又美麗,大學時代要不是那麼快就和查理定下來,肯定會有一大票追求者排隊搶著追。但她從來不是喜歡打情罵俏的那種女生,所以一和查理在一起,其他人只有打退堂鼓的份。
「這是我把查理留在身邊的唯一理由。」有一次,她板著臉這麼告訴我。看到我一臉震驚,才爆出一陣笑。「只是玩笑啦。查理是我的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查理是我大學最要好的朋友。大一那年,我們幾乎一整天賴在一塊,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認識愛蜜麗的。第二年,查理和愛蜜麗在城裡合租房子,雖然我是那邊的常客,但和愛蜜麗窩在唱機旁談天說地已成往事。因為,每次我過去,總有好幾個學生坐在一起有說有笑的,還有一台豪華音響不停發送震耳欲聾的搖滾樂。
幾年下來,我和查理一直維繫著親密的友誼。雖然不像以往那麼經常見面,但主要是因為距離關係。我在西班牙待了幾年,之前還有義大利和葡萄牙;查理大多的時間住在倫敦。唔,不過,要是這樣聽起來像是我是旅人遊子,他是居家男人的話,可就妙了。事實上,查理一年到頭飛來飛去——德州、東京、紐約——參加他各項位高權重的大型會議;我則年復一年困在同一棟潮溼的建築物裡,出拼字考試試題,或用慢速英文重複同樣的會話:我的—名字—叫—雷。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小孩—嗎?
我大學畢業、開始教英文時,感覺挺不賴的——有點像大學的延伸。語言學校在當時的歐洲如雨後春筍般竄起,雖然教學本身十分單調,工時又冗長,但在那個年紀並不會在意這些。你會花許多時間待在酒吧,輕易結交上朋友,讓人覺得身處一個廣大的人際網路,彷彿能擴張到全世界;隨便就能碰到秘魯或泰國來的人,讓你覺得只要你想,你可以無止盡地縱遊四方,再遠的角落也能靠朋友找份工作謀生。你永遠都會是這個溫暖又無盡的流動教育大家庭的一分子,大夥兒總是舒適地窩在一起,點杯酒,暢談前同事、跟精神病沒兩樣的學校主管,還有怪異的協會成員等等。
八○年代晚期,去日本教書成了大家的話題,很多人靠這個大賺了一筆。我認真擬了計畫,卻從未成行。我也有考慮巴西,還讀了幾本書研究當地文化,連申請表都寄了。但不知怎麼的,就是去不了那麼遠的地方。於是我在南義大利、葡萄牙待了一陣子,最後回到西班牙這裡。轉眼間,你已四十七歲,昔日舊識早已被新世代取代,聊的是不同的八卦,嗑不一樣的藥、聽不一樣的音樂。
這段時間,查理和愛蜜麗結了婚,在倫敦安頓下來。查理曾同我提過,等他們生小孩時,我得當其中一個孩子的教父。但這件事後來也沒成真,因為,他們一直沒生出小孩,現在,我想也為時已晚。不得不承認,長久以來我對這事感到失望。或許是我一直幻想當他們孩子的教父,好讓我在這兒的生活和他們在英國的生活有個正式的連結,無論這連結多麼微小。
總之,這年夏初,我會去倫敦和他們住一陣子。這是事先就規劃好的行程,出發前幾天,我還撥了通電話確認,查理說他們倆「狀況極佳」。因此,在經歷堪稱微恙的幾個月以後,我滿腦子想的只有縱容一下,徹底放鬆放鬆。
那天陽光普照,當我出現在他們家附近的地鐵站,我還在想不知道自從上回的拜訪以後,「我的」房間又多了哪些新擺設。幾年下來,每回總有些微更動。一次是角落多了個閃閃發光的電子裝置,另一次是整個房間重新裝潢。無論如何,我的客房總有比照高級旅館的服務:鋪好的毛巾、床邊的鐵盒餅乾、鏡台上的CD選輯。幾年前,查理帶我進去,他看似隨興卻隱藏不住得意地一直在把弄開關,讓一盞盞巧妙配置的燈光忽明忽暗:床板後頭、衣櫥上方等等。還有一個開關會發出低鳴,兩扇窗的百頁簾隨即垂降。
「唔,查理,我為什麼需要百葉簾?」我是這麼問的:「我希望醒來時能看見窗外。一般的窗簾就可以了。」
「這片百葉簾可是瑞士貨,」這是他的回答,彷彿解釋了我的問題。
但是這一次,查理帶我上樓時口中喃喃有辭,來到我房間以後,我發現他一直在找藉口。同時間,我所眼見的景況真是前所未見,床上一無所有,僅有的床墊長了斑點,歪歪斜斜鋪著。地上是一疊疊雜誌跟平裝書、一捆捆舊衣服、一根曲棍球棒、一個倒向一邊的擴音器。我在門邊停駐,只能乾瞪眼,查理試圖清出一些空間好放我的行李。
「你看起來一副想找飯店經理理論的樣子,」他酸酸的說。
「不、不,只是有點不尋常罷了。」
「一團亂,我知道。真是一團亂。」他在墊子上坐下來,歎了口氣。「我以為那些清潔女傭會把東西處理好,但顯然沒有。天知道哪裡出了錯?」
他似乎相當沮喪,忽地站了起來。
「走,一起吃個午餐吧。我來留個紙條給愛蜜麗。我們可以吃個又長又優閑的午餐,等我們回來的時候,你的房間——整間公寓——就會搞定了。」
「可是我們不能讓愛蜜麗一個人清啊。」
「噢,她不會自己動手的,她會找清潔工人。她知道怎麼統籌他們。我呢,連他們的電話都沒有。對了,午餐,吃午餐去吧。點個三樣菜,再配罐酒,就是一桌大餐了。」
查理口中的公寓位在一條富裕繁忙的街上,一間四樓排房的最上面那兩層。一出前門,我們直接走入嘈雜的人車聲之中。我跟著查理走過商店、辦公室,最後來到一間小巧的義大利餐廳。我們沒有訂位,但是服務生像朋友一樣和查理打招呼,幫我們帶位。環顧四周,我發現這裡多是穿西裝、打領帶的商務人士。幸好查理和我一樣邋遢。他一定猜到了我的思緒,因為我們坐下來時他說:
「噢,你真家居哪,雷。唔,現在一切都變了。你出國太久了。」接著,他又用大得有些嚇人的聲音說:「我們看起來可真像成功人士。這裡的其他人充其量只是中產階級。」然後他朝我微傾,小聲許多的說:「唔,我們得談談。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忙。」
記不得查理上次要我幫忙是什麼時候的事了,但我假裝隨意點頭,等他說分明。他玩了玩菜單,接著放下。
「事實上,我和愛蜜麗最近有點膠著。不久前,我們索性完全避開對方,所以她才沒有在家裡迎接你。這也表示,你得在我們之間選一個。有點像那種戲劇情境,一個演員分飾兩角。你不可能在同一個空間同時見到我和愛蜜麗。很幼稚,對吧?」
「那我來的時間真是不對,吃完午餐以後,我會馬上離開。我可以跟我的凱蒂阿姨待在芬奇利。」
「你在說什麼?你完全沒聽懂。我剛剛不是才告訴你,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我以為你的意思是這樣……」
「不,你這個笨蛋,該離開的人是我。我得去法蘭克福開一個會,今天下午就飛。兩天後我就回來,最晚星期四。這段時間你就待在這裡,幫我疏通打理一下,讓一切恢復原狀。當我回來的時候,就只需要開心地打聲招呼,吻吻我的愛妻,過去這兩個月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兩人重修舊好。」
說到這裡,女服務生過來點菜,她離開後,查理似乎不願意繼續談論剛剛的話題,話鋒一轉,問起我在西班牙的生活。我每每開口,無論好事壞事,他一概浮現微微的苦笑,然後搖搖頭,活像是我讓他最深的恐懼成真。我一度想告訴他我的廚藝突飛猛進——幾乎是單打獨鬥,為四十幾個學生、老師準備自助式聖誕大餐——但話才說到一半,就被他打斷。
「聽著,」他說:「再這樣下去不行,你得遞出辭呈。在這之前要為新工作卡好位。那個葡萄牙抑鬱症患者,就用他鋪個路。保住馬德里的位子,然後把公寓退了。懂吧,你得這麼做。這是第一步。」
他張開手,一一細數他的指示。我們的餐點上桌的時候,他還有幾根指頭沒數完,但他當做沒看到,繼續把話講完。我們才開始吃,他又開口了:
「我看得出來,你一定不會照我的說做。」
「不、不,你所說的每一個建議都很有用。」
「你回去以後會一如往常。一年後我們再見,你抱怨的會是一模一樣的事。」
「我沒有在抱怨……」
「你知道的,雷,能給你建議的人實在不多。過了某個階段,你得好好支配自己的人生。」
「好,我會的,我保證。那你剛剛說的呢,幫忙的事?」
「噢,沒錯。」他若有所思的嚼著食物。「坦白說,這是我邀你過來的真正目的。當然,能見到你總是很開心。但對我來說,主要想請你為我做件事。畢竟你是我最老的朋友,一輩子的朋友……」
忽然間,他又吃了起來;然後我嚇到了,他竟然默默地啜泣了起來。我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他只是悶頭不停地把義大利麵剷進嘴裡。這樣過了幾分鐘以後,我又伸手拍了拍他,依然沒什麼效果。接著服務生帶著開朗的微笑走了過來,確認我們點的菜有沒有問題。我們倆都說好極了,等她走了以後,查理似乎恢復了一些。
「嗯,雷,聽著。我想請你做的非常簡單。我只是想請你接下來幾天好好陪陪愛蜜麗,當個討人喜歡的客人。就這樣。等我回來。」
「就這樣?你只是要我在你出門時,幫忙照顧她?」
「沒錯。或者說,讓她照顧你,因為你是客人。我安排了幾件事給你們做,上上戲院什麼的。最晚星期四我就回來了,你的任務就是逗她開心,讓她保持好心情。這樣,等我回來說『噢,親愛的』、抱抱她時,她只會說:『噢,哈囉,親愛的,歡迎回家,一切好嗎?』並且給我擁抱。然後我們就可以一如往常,那些恐怖的事情就會像全沒發生過。你的任務就是這樣。其實挺簡單的。」
「很高興我幫得上忙,我會盡力的,」我說:「可是,查理,你確定她現在的心情適合招待客人嗎?你們之間顯然有點危機。她的情緒一定和你一樣低落。說真的,我實在不了解你為什麼選在這個節骨眼找我。」
「你說你不懂是什麼意思?我找你,因為你是我最老的朋友。沒錯,我確實有很多朋友。但碰到這種事,經我深思熟慮以後,我發現就你最合適。」
我得承認我其實挺感動的。不過,我還是覺得漏了什麼東西,覺得他還有什麼事沒說。
「如果你們兩個都在的話,我可以了解你邀我過來的原因。」我說:「我能想像該怎麼處理。你們倆在冷戰,找一個客人當擋箭牌,兩個人只好保持風度,自然而然僵局就會化解。但你人不在場,根本起不了作用。」
「就當作是為我努力看看吧,雷。我覺得會有用。你總是能逗愛蜜麗開心。」
「逗她開心?唔,查理,我確實想幫忙。但是你可能有點搞錯了。因為說真的,我倒是認為我根本逗不了愛蜜麗開心,即使在我們關係最好的時候也一樣。前幾次來你們家的時候,她對我……很明顯地已經感到不耐煩了。」
「聽著,雷,姑且相信我這一次吧。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們返回頂樓時,愛蜜麗也在公寓。我得承認,她老了好多,我真的被嚇到了。距離我上次來的時候,她不僅胖了很多,那張天生優雅的臉孔,浮現清晰的皺紋,一路不悅地連到嘴邊。她坐在客廳沙發翻看《金融時報》,我進門時,她的表情頗為陰鬱。
「很高興見到你,雷蒙,」迅速在我臉頰親了一下,然後又坐回去。她的樣子讓我恨不得趕緊道歉,選在這麼糟的時間打擾。但還來不及說什麼,她拍了拍她身旁的位子,說:「來,雷蒙,坐下來回答我的問題。我想知道你最近所有的事。」
坐下來以後,她開始詰問我,挺像查理剛剛在餐廳那樣。查理在一旁打包行李,在房裡進進出出,翻找各種東西;我注意到他們沒有直視對方。比照剛剛查理所說的,他們倆同處一室時並沒有那麼不自在。即使沒有直接對話,查理卻用一種怪異、突兀的方式加入對話。舉例來說,我在跟愛蜜麗解釋為什麼找一個室友和我分攤租金很困難時,查理忽然從廚房大喊:
「他住的那個地方,根本就塞不下兩個人!那是給一個人住,一個比他有錢得多的人!」
愛蜜麗沒有回應,但她一定把話聽進去了,因為她之後接著說:「雷蒙,你實在不該選那樣的公寓。」
如此這般無意義的對話就這麼持續了二十幾分鐘,查理不時地從樓梯或在走進廚房時穿插幾句,常常以第三人稱發表對我的意見。說到一個段落時,愛蜜麗忽然說:
「噢,說真的,雷蒙。你讓那個陰森森的語言學校把你徹底搾乾,又任由房東剝削,結果你做了什麼?跟腦袋空空、有酗酒問題、連個工作都沒有的女生上城鬼混,你簡直是故意想惹惱我們這些還肯理你的人!」
「那種人存活機率不高啊!」查理從走廊冒出來。聽得出來,這會兒他把他的行李箱拉出來了。「要是青春期過了十年以後還繼續那樣,還勉強說得過去,但你是快五十歲的人啦!」
「我才四十七歲……」
「你說你才四十七歲是什麼意思?」我就坐在愛蜜麗旁邊,她的聲音實在不必要這麼大聲。「才四十七。這個『才』,正是摧毀你的根源,雷蒙。只是、只是、只是。我只是盡全力罷了。只有四十七歲。很快你就會變成只有六十七歲,只是該死的繼續原地打轉,只是想找個該死的小地方窩著而已!」
「他得把該死的自己好好整頓一下!」查理從樓梯間往下吼:「把他該死的襪子拉到他該死的卵蛋那兒!」
「雷蒙,你都不會停下來好好問問自己是誰嗎?」愛蜜麗問:「當你想起自己的潛能,你都不會感到可恥嗎?看看你把自己的人生過成什麼樣!真是……真是令人失望透頂!令人火大!」
查理穿著雨衣站在門口,好一會兒,他們倆同時對我吼著各式各樣的事。接著查理嘎然而止,宣布他要離開了——彷彿對我厭惡至極——然後就消失了。
他一走,愛蜜麗也忽然停下來。我趁機站起來,說:「抱歉,我去幫查理提一下行李。」
「我自己的行李幹嘛要人家幫忙提?」查理從走廊上說:「我只有一包東西。」
但是他讓我跟他走到路上,留我站在他行李旁,他走去路邊招計程車。路上似乎沒車,他小心地把身體往外傾,半舉一隻手臂。
我走去跟他說:「查理,我覺得這樣不會有用。」
「什麼不會有用?」
「愛蜜麗真的恨我。你看,她才見到我幾分鐘就變成那副德行。誰曉得三天後會變成怎樣?你憑什麼覺得你回來見到的會是一片和諧光明?」
就在我說這些話時,我忽然有所領悟,靜默不語。查理注意到我的安靜,轉過頭仔細看我。
「我想,」最後我說:「我知道為什麼是我,不是別人了。」
「啊哈。雷終於靈光乍現了嗎?」
「嗯,或許吧。」
「有甚麼差別嗎?我要你做的事還是一樣,完全一樣。」他的眼裡又泛起淚水。「你還記得嗎,雷,以前愛蜜麗總說她有多信任我的能力?這麼多年來她一直都這麼說。我相信你,查理,你一定會做出一番成就,你真的很有才華。直到三四年前,她都還這麼說。你知道那有多惹人厭嗎?我本來過得不錯。而且我真的過得不錯,好的不能再好。但她總以為我有什麼天命……老天,該不會是該死的世界總統,天曉得!我只是個安份度日的平凡傢伙,她卻不懂。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有錯誤的核心。」
他緩慢地沿著人行道走,整個人心不在焉。我折回去拿他的行李,拖著輪子一路跟著他走。路上還挺擁擠的,要趕上他並不容易,行李不時地撞到其他路人,但查理依舊以穩定的速度前進,絲毫沒有注意到我的不便。
「她以為我讓自己失望了,」他說:「但我沒有啊。我好的很呢。當你非常年輕時,有無限的理想抱負固然很好,但來到我們這把年紀,你得……認清自己的處境。每當她忍無可忍、重提這種事時,我的腦袋會一直這麼轉:客觀,她得客觀一點。我也一直對自己說,瞧,我過得好極了,看看其他人,我們認識的那票人。看看雷,看看他把他的人生搞成什麼豬樣。她需要客觀。」
「所以你把我找來,扮演客觀角度先生。」
最後,查理終於停下來和我四目相接。「別誤會我的意思,雷。我並不是說你是慘敗的鐵證或什麼的。我知道你不是毒蟲或殺人犯。但現在只有我們倆,就直說了,你並不是屬於高成就型的人。所以我才找你幫忙,請你為我做這件事。我們已經走到末路了,我很絕望,需要你幫忙。我究竟要什麼,老天?我只要你拿出平常的貼心模樣,不多也不少,就當是為我好好的演齣好戲。雷蒙。為了我和愛蜜麗。我們還不算真的結束,我心裡清楚。在我回來以前,幫我撐個幾天。這樣的要求不算多,對吧?」
我深吸一口氣說:「好,好,如果你覺得這樣會有用的話。但愛蜜麗遲早都會看穿的,不是嗎?」
「怎麼會?她知道我在法蘭克福有個重要會議。對她來說,這件事再單純不過。她只是照顧一個客人,就這樣。她喜歡做這種事,而且她也喜歡你。瞧,有計程車了。」他拼命揮手,司機朝我們開來。查理緊抓著我的手臂,「謝啦,雷。你會為我們開展新局的,我知道你一定可以。」返回公寓後,愛蜜麗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歡迎我進公寓的樣子,像是招呼年長、身體虛弱的親戚,臉上浮現鼓舞的微笑,還在我手臂上輕輕拍了拍。我同意來杯茶,她領我進廚房,安排我在桌前坐下,接下來幾秒她就那麼站在一旁,一臉憂慮的望著我。終於,她輕聲地說:
「剛剛那樣對你真是抱歉,雷蒙。我沒有權力用那種態度對你說話。」接著她轉身沖茶,又繼續說:「距離我們大學時代已經好多年了。我總是忘了這點。我絕不敢跟其他朋友那樣說話。可是一看到你,唔,我總是有錯覺,以為我們又回到那個時候,回到我們那時的樣子,就把現在給忘了。你千萬別放在心上。」
「不,不。我一點都不在意。」腦袋裡還回蕩著先前和查理的對話,表情因此有點分心。我想愛蜜麗誤會了,因為接下來她的聲音變得更加柔細。
「很抱歉害你生氣。」她小心翼翼地在我面前擺上一碟餅乾。「是這樣的,雷蒙,那時候的我們,無話不說,無所不談,你總是聽著聽著就笑了起來,我和查理也跟著笑,所有事情都很開心。我真傻,竟然以為你還是像過去那樣。」
「唔,說真的,我差不多還是那個老樣子。我真的沒多想。」
「我沒發現,」她繼續說,像是沒聽到我的話:「現在的你有多不一樣。你一定瀕臨崩潰邊緣。」
「唔,愛蜜麗,我真的沒那麼糟……」
「我想,過去這幾年一定讓你筋疲力盡。你就像站在懸崖邊的人,只要稍稍一推,你就會崩解。」
「妳的意思是墜崖。」
她原本忙著裝滿水壺,這會兒忽然轉過頭來瞪我。「別這樣,雷蒙,別說那種話。連開玩笑也不許。我絕不想聽你那樣講。」
「不,你誤會了。你說我會崩解,但如果我是站在崖邊的話,那麼我會墜落,不是崩潰。」
「噢,你這個可憐蟲。」她似乎還是沒聽懂我的意思。「過去的雷蒙,現在只剩下一副薄薄的空殼子了。」
我決定這回還是別答腔的好。好一會兒,我們就靜靜地等水滾。她為我沖了一杯茶,自己倒沒有,她將茶杯擺在我的前面。
「很抱歉,雷,但現在我得回辦公室了。有兩個會議我絕不能錯過。要是我早一點知道你的狀況,說什麼都不會丟你獨自一個人,一定另作安排。但是不巧,我現在得回去。可憐的雷蒙。你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兒,要怎麼消磨時間?」
「我沒問題的。真的。說真的,我剛剛還在想:我何不趁妳出門時把我們的晚餐弄好?或許妳不相信,但我的廚藝可是大有長進。聖誕節前才剛辦過自助式大餐……」
「你想幫忙,真的好貼心。但我想你還是休息吧。畢竟你對我們家廚房不熟,怕增加你太多壓力。何不好好放鬆,泡個藥草澡,聽點音樂。我回來時再打理晚餐就好。」
「但是你忙了一天以後,一定會不想進廚房的。」
「不,雷,你休息就好。」她拿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上面有我的專機號碼,還有我的手機。我現在得走了,但你隨時都可以打給我。記得,我不在家的時候,別做任何會讓你有壓力的事。」
好一段日子,一直覺得要在自己的公寓放鬆並不容易。要是一個人在家,我總會焦躁不安,總覺得錯過外頭什麼重要的會面。但如果我一個人待在別人的空間,卻能被一種舒適的寧靜感包圍。我喜歡癱進一張不熟悉的沙發,旁邊有什麼書就拾起來看。愛蜜麗走了以後,此時此刻,我就這麼做。或者至少,在跌進二十分鐘小睡以前,我努力讀了幾章的《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醒來時,午後陽光灑入公寓。我走下沙發,用鼻子嗅了嗅。或許清潔婦真的在我們吃午餐時進來過,或者愛蜜麗親自打掃過;總之,主客廳現在看起來相當完美無瑕。乾淨整齊以外,堪稱風格獨具,擺了當代設計師的家具和藝術品——雖然,不客氣的人可能會說太過做作。我稍稍瀏覽架上的書,瞥看他們的CD收藏。幾乎清一色是搖滾或古典,搜尋一會兒以後,終於在一個暗角找到一小區,是向弗雷德.阿斯泰爾(Fred Astaire)、查特.貝克、莎拉.芳恩這些人致敬。我不懂愛蜜麗為什麼不多用翻錄CD取代珍貴的老唱片。但我沒多想,就走進廚房了。
我打開幾個櫃子,想找點餅乾或巧克力棒,卻剛好注意到餐桌上有本小筆記本。表皮是紫色的布做的,在簡約花色的廚房色系中相當醒目。剛剛愛蜜麗急急忙忙正準備出門時,她在這張桌子整理包包裡的東西,我在一旁喝我的茶。顯然她不小心把筆記本留下來了。幾乎在同一個瞬間,我忽然有個念頭:這本紫色筆記本一定是某種私密日記,而且是愛蜜麗故意留下來的,目的是要我好好閱讀翻看。不論出自什麼原因,看來,她覺得對我無法好好坦白,於是選擇以這種方式,跟我分享內心的煎熬。
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瞪著筆記本出神。接著我伸出手,指尖滑入扉頁,小心謹慎將筆記本捧了起來。但愛蜜麗縝密擁擠的字跡瞬間將我手指推開。我從桌旁走開,告訴自己別探人隱私,無論愛蜜麗在情緒失控時可能有怎樣的念頭。
我回到客廳,重新縮回沙發,又讀了幾頁《曼斯菲爾德莊園》。但這下子,我發現自己無法專心,思緒不停回到那本紫色筆記本上面。萬一這根本不是出於意外怎麼辦?說不定她其實規劃了好幾天?她小心翼翼地計畫這一切,只為讓我一睹為快?
又過了十分鐘以後,我回到廚房,繼續盯著那紫色筆記本又一會兒。然後我坐下來,就坐在我之前喝茶的位置,把筆記本移到我面前,攤開。
很快地,我便發現,要是說愛蜜麗向日記吐露心事的話,那本札記鐵定不在這裡。眼前的筆記本充其量只是繽紛的約會記錄而已,每個日期底下潦草記著給自己看的備注,有些顯然特別激動。其中一條用粗體氈頭筆寫著:「如果還沒打電話給瑪蒂達,到底為什麼不打?快打!」
另一條則是:「把該死的菲力普.羅斯搞定。還給馬里昂!」
然後,當我翻到下一頁時,我看見:「雷蒙星期一來。真是的。」
又翻了幾頁:「雷明天出現。該怎麼活?」
最後,當天早上,在一堆瑣事裡面寫著:「為抱怨王子買瓶酒。」
抱怨王子?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接受這裡指的人就是我。我想過各種其他可能——是客戶或是水電工?——但最終,日期、情境完全吻合,我不得不接受,沒有比我更適合的人選了。忽然間,被她這麼貼標籤讓我覺得好不公平,一股強烈的力量襲來,還來不及回神,那一頁已被我揉在手中。
其實,並不是什麼特別暴力的舉動,我甚至沒把那一頁撕下來,只是瞬間握緊了拳頭。下一秒,我很快恢復控制,當然,為時已晚。我張開手,發現這一頁連同底下兩頁都成了我暴怒底下的受害者。我試著將它們撫平,整回本來的形狀,卻屢次恢復成原狀,彷彿它們最深層的心願是化作一團廢紙。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只是不停在受創的紙頁上,慌慌張張重複熨壓的動作。正當我準備接受一切的努力皆為徒勞時——無論我現在做什麼,都已無法掩匿罪行——懵然間,我發現公寓某處有電話鈴聲響起。
原先我決定不理,繼續思考剛剛發生的一切可能隱含的意義。但答錄機響起,我聽見查理留言的聲音。或許是我感受到一線生機,或許是我想要找個人告解。總之,我發現自己衝進客廳,一把將電話從玻璃咖啡桌抓起。
「噢,原來你在啊。」我打斷他的留言,查理似乎有點生氣。
「查理,聽著。我剛剛做了件非常蠢的事。」
「我在機場,」他說:「班機延誤。我想打去在法蘭克福等接我的租車公司,但我沒把他們的電話帶在身上。我需要你幫我查一下。」
他開始發號施令,告訴我哪裡可以找到電話簿,但我卻打斷他說:
「聽著,我剛做了一件蠢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電話沉默了半晌。然後他說:「或許你在想,雷,或許你以為有別人。以為我是要飛去找她。我忽然覺得,你是這麼想的。畢竟,這跟你觀察的完全吻合——我離開時愛蜜麗的樣子,那一切。但是你錯了。」
「沒錯,我同意。但是,有件事我得告訴你……」
「別說了,雷。你錯了。並沒有別的女人。我現在要飛去法蘭克福開一個會,換我們在波蘭的代辦。我現在就是要去那裡。」
「嗯,我聽到了。」
「這一切和別的女人完全無關。我誰也不看,至少不是正眼瞧,是真的。該死的實話,沒有別人!」
他開始吼了起來,雖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候機室周圍的嘈雜。這會兒他安靜下來,我豎起耳朵,聽他是不是又在哭,卻只聽到機場的噪音。忽然間,他說: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嗯,沒有別的女人。那,有別的男人嗎?承認吧,我知道你這麼想,對吧?說吧,承認吧!」
「說真的,我從沒想過你有同志傾向。就連那次期末考以後,你喝到爛醉,假裝你想……」
「閉嘴,你這個笨蛋!我說別的男人,是指愛蜜麗的情夫!愛蜜麗的情夫,是否有這號該死的人物存在?我在想的是這個。依我的判斷,答案是沒、沒、沒。都這麼多年了,我把她讀得透徹。但問題就在於,正因為我讀得懂她,我也能看出其他端倪。我看得出來,她開始在考慮。沒錯,雷,她在看其他男人。像該死的大衛.柯瑞那樣的男人!」
「那是誰?」
「該死的大衛.柯瑞是個挺走運的殷勤鬼、大律師。我知道他有多走運,因為她把該死的細節都告訴我了。」
「所以你覺得……他們有在見面?」
「不,我剛才說過!沒有,還沒有!總之,該死的大衛.柯瑞沒空陪她。他已經娶了個萬人迷,幫康德.納斯特出版集團做事。」
「那你沒問題了……」
「不,因為還有麥可.艾德森。還有羅傑.范德柏格,他在美林證券可是顆新星,每年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聽我說,查理,請你聽我說。我這裡出了點問題。我承認規模算小,但仍然是個問題。請聽我說。」
最後,我終於能把這裡的情況告訴他。我盡可能忠實的陳述,雖然,對於我以為愛蜜麗是故意留告白訊息給我的那點,算是輕描淡寫。
「我知道真的很蠢,」講完後我說:「但她把筆記本留在那裡,就擺在廚房桌上。」
「嗯。」查理這會兒聽起來冷靜許多。「唔,所以你就由著自己去了。」
他笑了起來。我感覺到安慰,也笑了出來。
「我想我反應過度了,」我說:「畢竟又不是她的私密日記,只是本備忘錄而已……」我的聲音逐漸減弱,因為查理還是繼續笑,笑中有股歇斯底里。然後他停下來,平淡地說:
「要是被她發現,她鐵定會割下你的卵蛋。」
我怔怔然聽著機場噪音,電話一陣死寂。接著他繼續說:
「差不多六年前,我也偷看過一次。我坐在廚房,她在煮東西,我只是不經意的看看——漫不經心地瞎聊,才正要翻開瞧瞧,結果馬上被她發現。她說她不喜歡我這麼做。就是在那個時候,她揚言要割下我的卵蛋。她手裡握著擀麵棍,我就說她拿那傢伙沒辦法進行。接著她說,擀麵棍是之後才要上場的,鋸掉以後還用得上。」
電話那頭傳來飛機班次廣播。
「所以你建議我怎麼做?」我問。
「你還能怎麼做?就繼續把它們壓平吧。說不定她不會發現……」
「聽著,雷,我心亂如麻。我想告訴你的是,愛蜜麗幻想的這些男人,他們並不是真的備胎情人;她覺得這些人好,單單是因為她相信他們成就卓越。她沒有看到他們隱藏的缺陷。他們純粹的……殘忍。他們都是她的同事。而且這是最可悲、也最諷刺的地方——內心深處,她愛的人其實是我。她還愛我。我看得出來,我看得出來。」
「所以說,查理,你沒有任何建議。」
「不,我沒有任何該死的建議!」他又火力全開的大喊:「你等著看吧!你上你的飛機,我上我的。到時再看哪台先墜機!」
就那樣,查理走了。我癱回沙發,深呼吸。我告訴自己得把狀況搞定,同時,卻直感覺胃傳來微微的抽痛與噁心感。我的腦袋爬過各種訊息,一個辦法是直接逃離公寓,從此和查理、愛蜜麗斷訊個幾年,之後再給他們寫封措辭謹慎的信。不過,即使以我現在的狀況,我也知道這個計畫根本是冒險。另一個好一點的辦法是一瓶瓶進攻他們的酒櫃;等愛蜜麗回來時,她會覺得我只是個可憐的醉鬼。這樣,我就可以大剌剌地坦承我偷翻了她的日記,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還蹂躪了幾頁。說真的,在這樣瘋狂的場面裡頭,我甚至可以化身成受害的一方,大吼大叫,告訴她我看到她那些話,心裡有多酸、有多受傷——這就是我仰賴多年的朋友,她的愛和友誼曾伴我度過孤獨異旅的低潮時光。儘管這些辦法實際上來說是可行的,我卻也感受到某種東西——某種逼近底線、我不敢近距離檢視的——我知道對我來說,這麼做是不可能的。
◎以上節錄自《夜曲》〈或雨或晴〉部分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