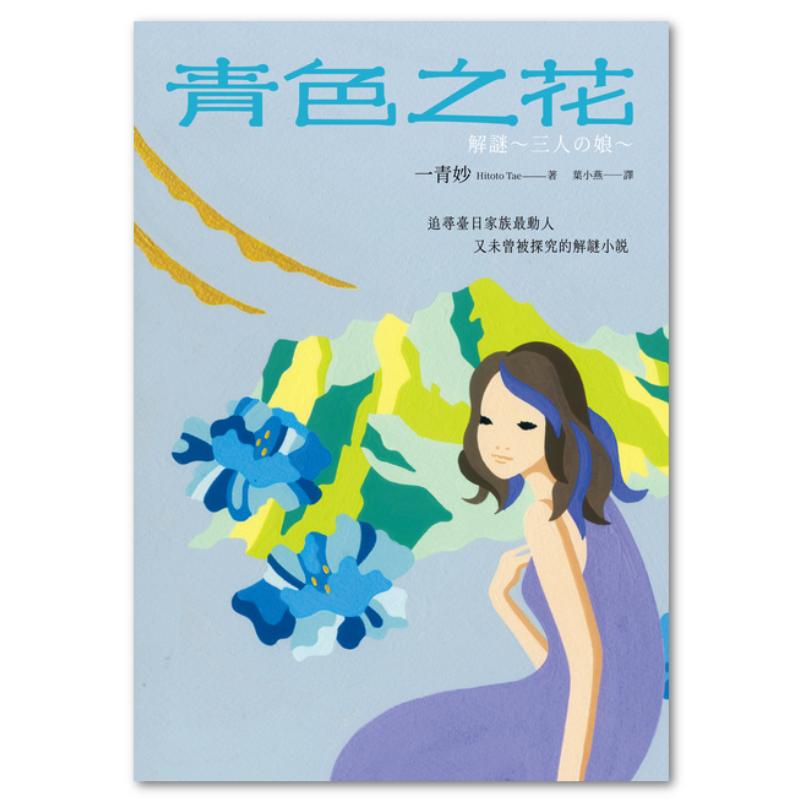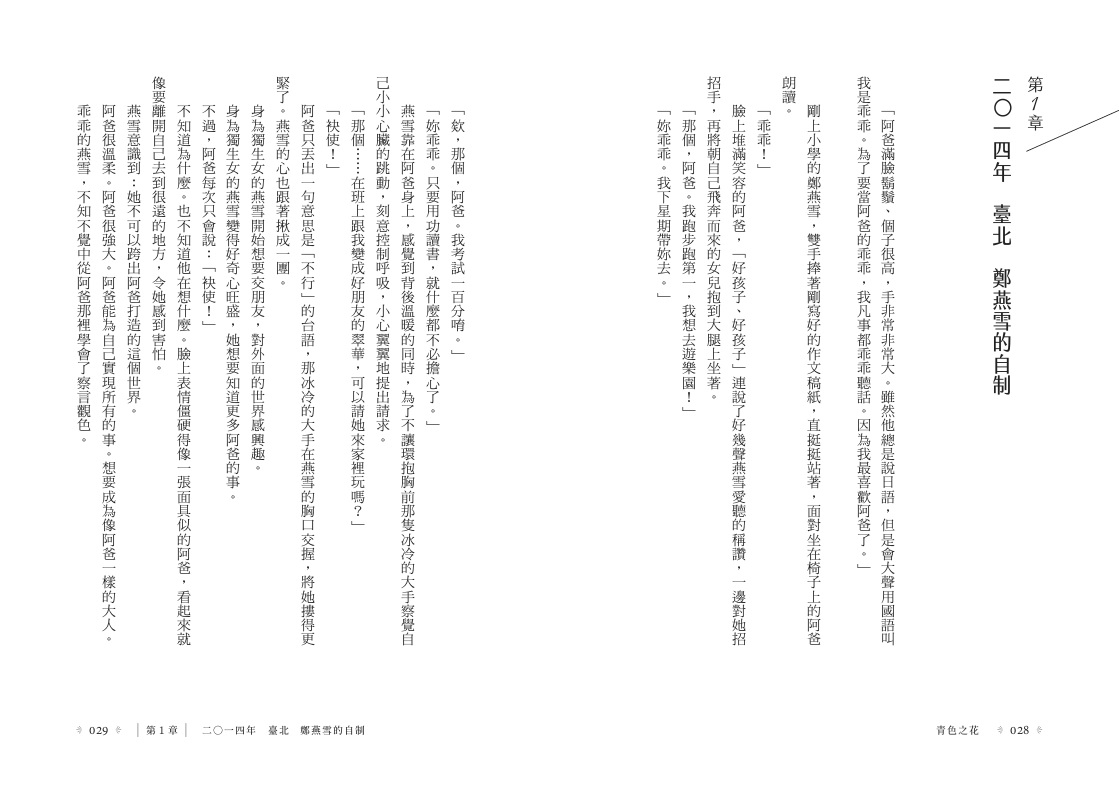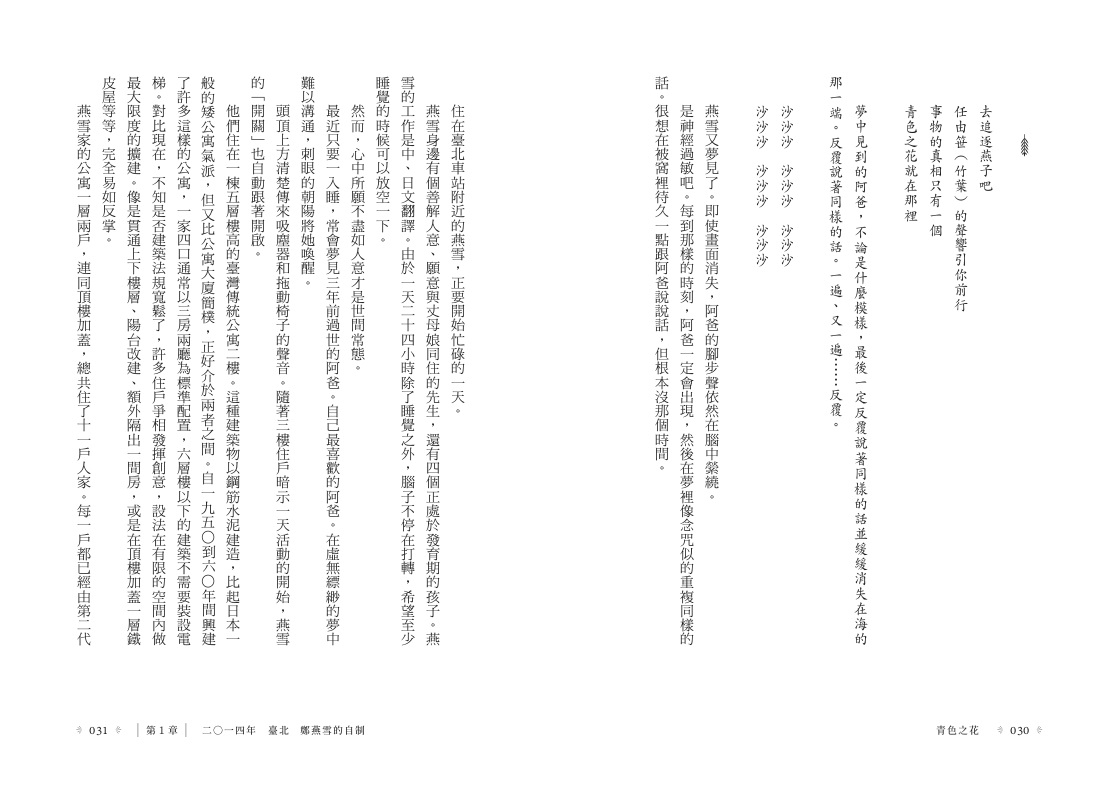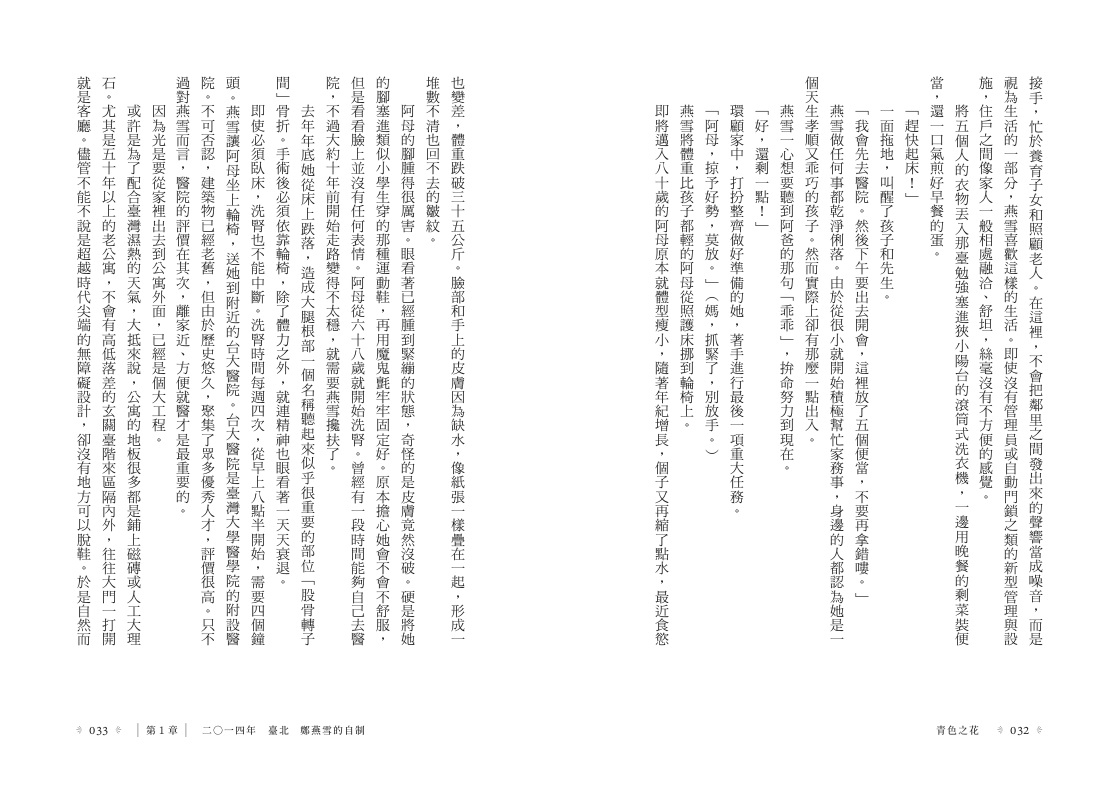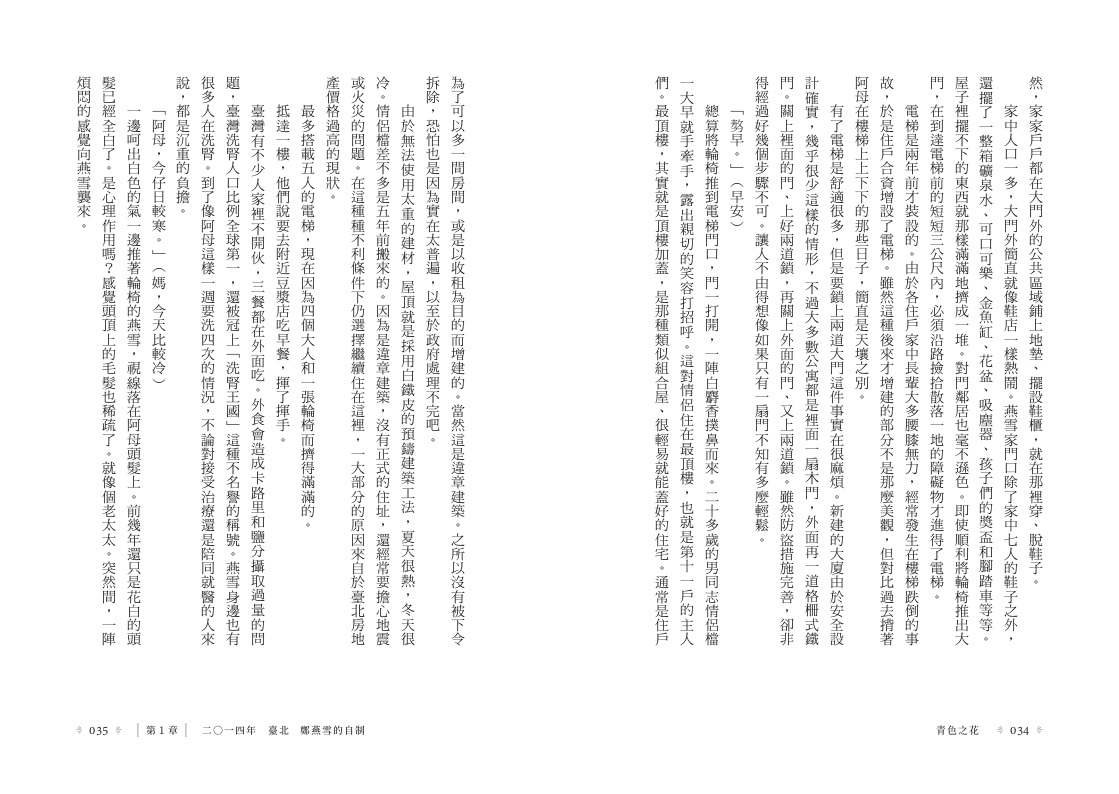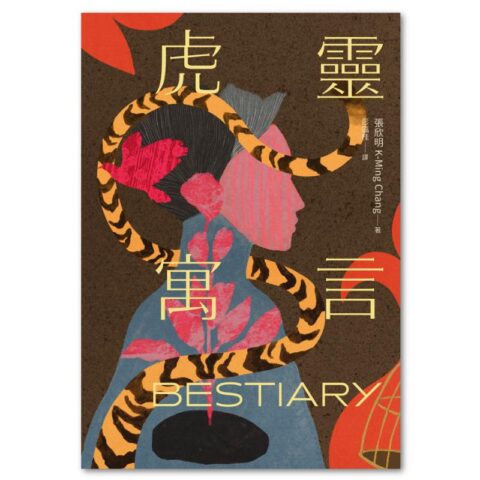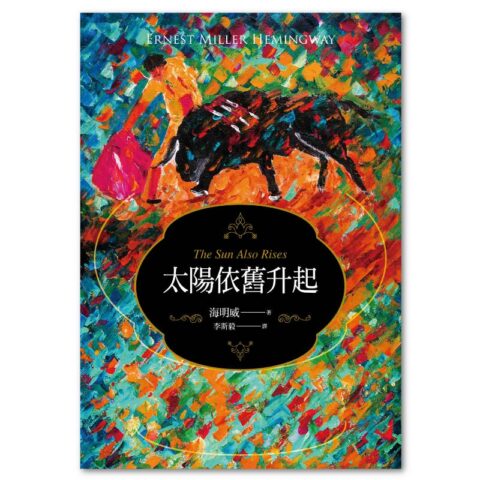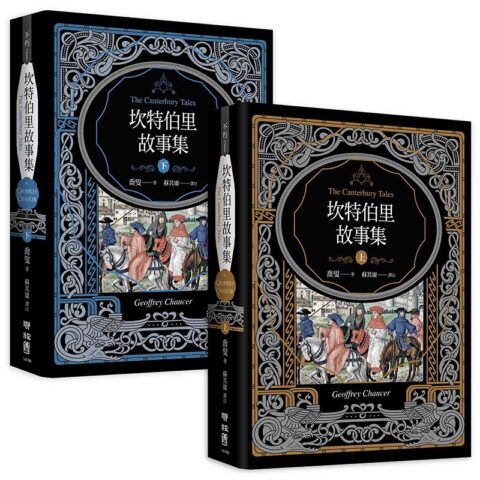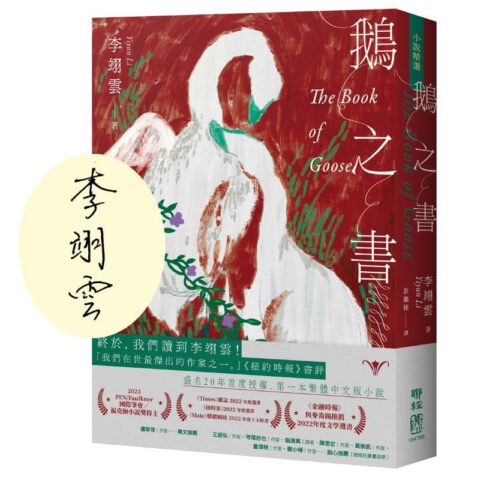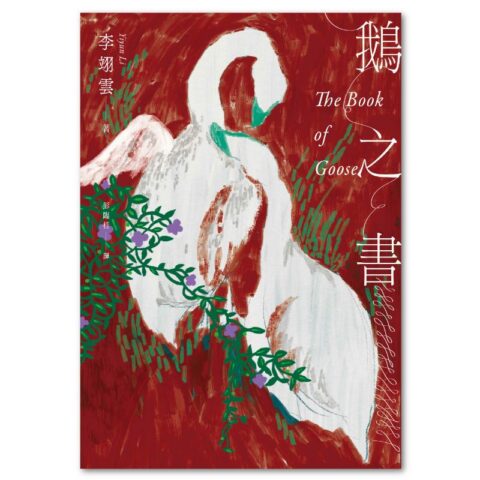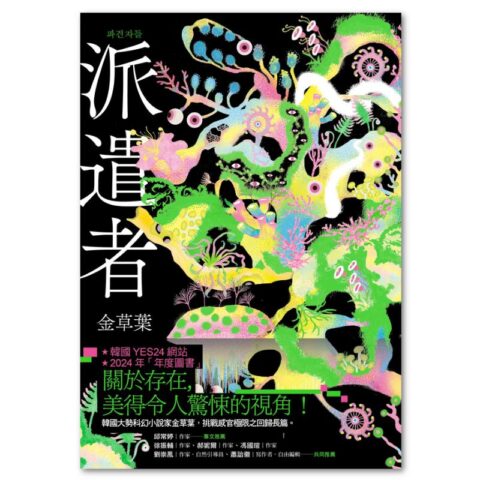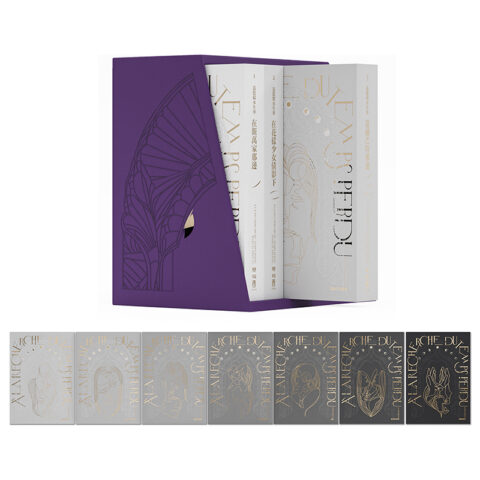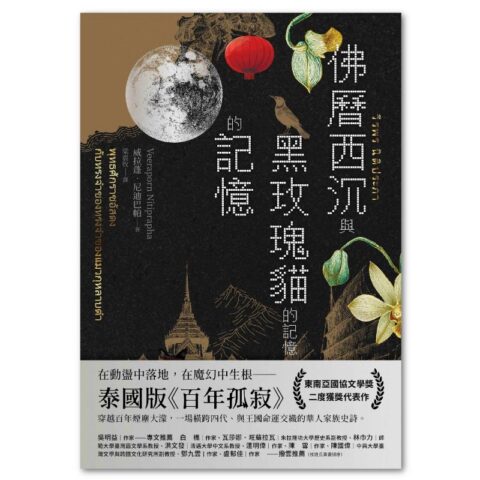青色之花
原書名:解謎〜三人の娘〜
出版日期:2025-07-24
作者:一青妙
譯者:葉小燕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00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2.1 cm
EAN:9789570877311
系列:小說精選
尚有庫存
追尋臺日家族最動人又未曾被探究的解謎小說
記憶是最深的謎題,愛是最難的解答。
穿越歷史煙塵、家族靜默與夢想的遺跡,
她們不是在尋找罪與罰,而是在發掘被隱藏的真相。
半世紀以前,三位青年在臺大教室相遇,他們滿懷理想正義,卻在風起雲湧年代裡走向迥異的命運:背棄責任偷渡日本,只留下名為「青色之花」夢想的逃避者;投身革命深陷牢籠,連結束自己勇氣都喪失的膽小鬼;還有守護秘密地圖而遭誣控,最終選擇將一生埋進學術幽谷的無語學者。
時光流轉,一張陳舊的合照牽引了三人各自女兒的命運,她們開始在歲月縫隙中拼湊父輩的過往。原以為自己的傷痕來自父親的缺席、否定與限制,當塵封的「青色之花」謎團悄然綻放,女兒們才意識到無聲的父輩曾經歷過怎樣的風暴,又是如何改變了她們的人生。
一青妙以細膩筆觸凝視家族記憶與臺日歷史沉默,創作了第一部小說作品。本書不只是橫跨半世紀的兩代父女對話,更是對「夢想是否值得付出一生守候」的探問,成就了一場既溫柔又深刻的解謎真相之旅。
▍好評推薦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崗∣導演、作家
李柏青∣小說作家
重點就在括號裡∣影評人
張維中∣作家
栖來光∣旅臺日本作家
蔣亞妮∣作家
羅毓嘉∣詩人
作者:一青妙
臺日混血作家。父親是昔日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長男顏惠民,母親為日本女性一青和枝。小時候就讀衛理幼稚園、私立復興小學,十一歲遷居日本,中學時期父親早逝而改從母姓,大學時期母親亦病歿。
自牙醫學系畢業後即從事牙醫師工作,同時兼顧以舞臺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並一心致力於臺日文化交流活動。2015年出任臺南市第一位親善大使,2016年成為母親故鄉的石川縣中能登町觀光大使,2025年獲聘為石川縣觀光大使,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推廣臺灣觀光與文化,堪稱臺日交流的重要推手。
已出版作品包括《我的箱子》、《我的臺南:一青妙的府城紀行》、《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等。其中,《我的箱子》更改編成舞臺劇《時光の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2019年開始於臺灣各地巡演,至今好評不斷。
譯者:葉小燕
自由譯者。曾任日語教師、臺灣高等法院特約通譯。譯作有《被討厭的勇氣》等四十餘本。
序幕 一九四七年 來自神戶
Ⅰ
第1章 二○一四年 臺北 鄭燕雪的自制
第2章 二○一四年 臺北 高妙玲的自卑感
第3章 一九四七年 臺灣大學
第4章 一九四九年 從臺北到臺中
第5章 二○一四年 東京 岡部笹收到的相片
Ⅱ
第6章 二○一四年 埔里
第7章 二○一四年 擦身而過的三個女兒
第8章 二○一四年 臺灣大學之謎
第9章 二○一四年 二二八事件
第10章 一九四九年 四六事件
第11章 一九四九年 臺灣 能高山
Ⅲ
第12章 二○一四年 東京 梅華
第13章 二○一四年 東京 請求公開
第14章 一九九二年 臺北 藍瑞山 重逢
Ⅳ
第15章 二○一四年 過去與現在的連結
第16章 二○一四年 再到臺灣
第17章 二○一五年 妙高 燕溫泉
尾聲 二○一九年 前往基隆
作者後記
序幕 ∣ 一九四七年 來自神戶
如果世界無色 什麼都無味
如果世界無形 什麼都無依
如果世界無情 什麼都無畏
如果世界無明 什麼都無常
下不完的雨總算停了。
這場雨,從出了神戶港之後一直下到現在。究竟連續下了幾天?冰冷的雨讓船客的腦子也凍僵了。
太陽汲取甲板各處殘留的雨水為養分,黃金般耀眼的光芒瞬時增色不少。
「阿爸,這邊這邊。」
「終於放晴了。」
「細膩(小心)!不可以跑太遠喔。」
為沐浴在這久違的陽光下,船艙內的乘客紛紛來到甲板上,日、台語交雜聊著天。
不顧父母叮囑,精力充沛嬉鬧奔跑的孩子;一板一眼擺動著手腳做體操的老人;忙著清理甲板的船員。為了讓蜷伏僵硬的身子舒展開來,每個人都忙著活動筋骨。
「這馬當時?」(現在幾點了?)
拄著拐杖的老人用台語問了旁人。
「我去幫你問那個哥哥!」
經過老人身邊的男孩一臉天真無邪的表情,他從容不迫舉起右手,元氣十足地以日語回應。男孩因為有藉口可以躲掉鬼抓人遊戲裡要扮鬼的倒楣事,眼睛都亮了起來。向前跑去的那頭站著一個年輕人,胸口處露出一截懷錶的錶鏈。
瘦瘦高高的年輕人穿著一身深藍色學生制服,他閉上雙眼,手中緊握著一本書,倚靠在綁了救生圈的欄杆上。
彷彿與那些為天氣放晴而歡欣喧鬧的人劃清界線似的,年輕人的四周沉寂到有點陰森可怕。即使船隻搖晃,他也不為所動。踩在絲毫沒有乾涸跡象的一攤汙水上的腳跟處,散發出任何人都難以靠近的一股凝重而潮濕的氣息。
露出學生制服外的手還有脖子十分蒼白。是血液不流通、宛如蠟像般沒有生命與活力的肌膚。他還有呼吸嗎?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對生命的意念,看起來彷彿只剩一副軀殼在那裡。
仰望天空的目光孱弱無力,上衣的立領兩側繡有金銅色櫻花徽章,鮮活耀眼。
男孩晒成棕色的小手,有如劃破異次元世界般向前伸出。年輕人聳起肩膀深深吸了口氣,若有似無地開了口。
「我……什……人。」
年輕人的喉結生硬笨拙地蠕動著,擠出幾個不完整的字。
他說話的聲音,男孩並沒有聽見。
「哥哥,現在幾點?」
男孩踮起腳尖,伸手想摸年輕人胸口那條晃動的鏈子。
「我是啥人!」(我是什麼人!)
年輕人撐起靠在欄杆處的上半身,嘴巴張得大大的,喉結上下滑動用日語大聲喊道。
男孩嚇一大跳,不由得一把揪住年輕人胸口的鏈子,只是身子無法支撐就那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骨碌碌……懷錶脫離了鏈條,從年輕人胸口飛出去在地板上滾動。
男孩追上懷錶,撿了起來。
秒針不動。長針與短針交疊在錶面的羅馬數字XII上面。男孩拿著懷錶一會兒貼近耳朵,一會兒上下晃動,年輕人慢慢向他走近。
男孩與年輕人頭一次四目相交。
「呀……」
男孩輕聲尖叫,扔下特地撿起的懷錶,拔腿逃開。
年輕人的臉上,有眼睛、有鼻子,也有嘴巴。不過,空蕩蕩的彷彿少了些什麼重要的東西──是眉毛和睫毛。看不出到底是生氣?開心?還是困惑或悲傷?就像個臉上光溜溜的怪物。
他毫不在意眾人的目光,緩慢拾起懷錶隨手丟進上衣口袋。
「我是啥人!」(我是什麼人!)
年輕人刻意再回到積了一攤汙水的欄杆旁,翻開封面寫著《青色之花》的那本書,不斷喃喃自語。
戰爭結束兩年了,全日本還處於憂心物資匱乏、死命探索活路的階段。
穿著學生制服的年輕人看不出年紀。深藍色制服的上衣袖口與口袋滾了黑邊,褲子上臀部和膝蓋的位置並沒有磨到發亮的痕跡,也沒有變形。仔細上過鞋油的黑皮鞋在那攤積水上顯得極不相襯,散發出耀眼的光澤。
一名穿著白皮鞋的男子避開地上積水,在年輕人面前停下腳步。表面凹凸不平的牛津鞋,鞋面到鞋尖部分是切割式翼紋設計,鞋尖處裝飾有經典雕花紋。
純白的波浪雕花紋緩緩移動方向,逐漸占據年輕人的視野。是個眼熟的圖案。年輕人一抬起頭,耳邊傳來低沉和緩的嗓音。
「迵世界無青色的花佮青鳥仔(全世界哪裡也找不到青色之花與青鳥)……要早點醒悟,青色之花與青鳥哪裡都不存在。」
站立在年輕人身旁的男子,做了一個雙手輕輕闔上書本的手勢。精心剪裁的白西裝搭配胭脂色領帶,純白色巴拿馬帽壓低帽簷遮住了雙眼。
儘管被帽子遮擋見不到臉,卻有種熟悉懷念的感覺。想不起究竟是誰。不,或許是不願想起也說不定。
若問敷島大和心,輝映朝陽山櫻花
男子在年輕人身旁,以一種與方才低沉嗓音成對比的輕柔有節奏的高昂聲調吟唱起和歌。受這熟悉的歌曲牽動,年輕人的意念轉向頸部立領處盛開綻放的徽章。那是為皇室與貴族子弟創立的教育機構「學習院」的標幟。
「要被這假象禁錮到何時?忘了那些國學什麼的吧。我們在日本不過就是華僑而已,當不了日本人的。緊精神(趕快醒來)。」
男子低沉和緩的聲音再次響起。
「大和心、天皇、萬歲、大日本帝國、我是日本人……」
年輕人的喉結不斷上下滑動,說到一半卻停頓下來。一陣沉默之後,像是忘了那名男子的存在似的將視線移回到書上,然而無關乎書上的內容,他的意識裡就只是一再重複著同樣一句話──
我是佗一國的人?(我到底是哪一國人?)
「與美國交戰,你能夠以日本人的身分去應戰嗎?」
彷彿看穿年輕人內心一般,男子如此問道。他叼著口袋裡掏出來的菸,拿火柴點燃後,深吸了一口。
自稱陳舜臣的男子比年輕人大四歲,生長在日本並擁有日本國籍,但據他表示,他現在成了「中國人」。
「陳先生是哪一邊?」
「雖然很想說臺灣人就是臺灣人,但終究哪邊都不是。被殖民者……說不定是最恰當的說法。所以我對於同為殖民地的印度很感興趣。」
陳舜臣這番出人意表的回答,讓年輕人內心大受打擊。
儘管身處日本,陳舜臣依然被灌輸了身為中國人的文化誦讀等素養,他也和年輕人一樣經歷了失去國家的考驗,但他以堅苦卓絕的意念讓自己接受一切,搭上了這艘船。
「我在大學學過印度語。順便也學了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藉由語言,可以見識到形形色色的處境。『局外人』到處都有。任誰都害怕成為被排除在外的人,然而那樣的狀況無關乎個人意願,就是會突然來個措手不及。」
戰爭中,不太確定是什麼時候了,陳舜臣曾計畫要去中國甘肅。由於甘肅那邊住了很多說阿拉伯語的回教徒,當時他心中設想,或許能為戰事助一臂之力,試圖要動員那些回教徒。
「……那或許就是我的『青色之花』。」
才不過是幾年前的想法,他略顯羞愧地對年輕人吐露,自己竟然曾經對荒誕無稽的異想天開那麼認真。
聽到這種荒唐離奇的事,年輕人萌發好奇心,回復了生氣。
兩人不僅從內地的義務勞動服務、皇國史觀開始談論起,還聊到從小在不明所以的狀況下被灌輸的《詩經》、中國漢文古籍以及日本文學等等。從陳舜臣那兒,年輕人還聽說了魯迅、郁達夫等等近代文學家的名字。
海風漸強,陳舜臣掀起巴拿馬帽重新戴好,一直遮蓋在帽子下的那張臉,轉向了年輕人。
雙方聊了好一會兒,這卻是頭一次清清楚楚見到彼此的樣貌。陳舜臣有張童顏,看起來遠比年輕人所想像的還年輕;而年輕人的模樣,則比陳舜臣所料想的更加委頓滄桑。
年輕人才剛開始要面對的苦惱恐怕沒那麼容易化解吧。只不過,希望能激勵這個與過去的自己有幾分相似的年輕人,他遞了一本小記事本過來。
「……這是阿拉伯文?」
「是波斯文。」
是以墨水書寫,像摩斯密碼般由一些點和曲線組合成的特殊文字,同時並列著有稜有角的日文。
奮起吧,莫厭人世流轉無常
且安坐,樂由此生隨波逐流
世事自然倘若不變
自無一物沾染汝身
「我對臺灣一無所知。所以是為了解臺灣而前去。任何時刻,希望你……迷惑、苦惱的時候能回想起這一段就好。後會有期了。」
太陽隱身雲朵背後,陳舜臣嘴角微揚,對即將重返現實回復原本樣貌的年輕人展露燦爛笑容後離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曾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被戰勝國中華民國接收了。
直到戰爭結束前,人們搭乘連結日本與臺灣的內台航路船往返兩地。鼎盛時期,據說一年有十萬名以上的乘客浮盪太平洋上,在兩個島之間自由來去。如今這艘船上,卻全都是手持單程票從神戶返回臺灣的人。
雖然不是像高砂丸、高千穗丸或富士丸那種設備豪華的船,但其實船名早已無關緊要。更別說連有沒有票都不具意義了。
只要可以平安無事抵達臺灣就好。
因為這艘船,搭載自願返回故鄉臺灣的臺灣人,不過就是一艘回歸的船而已。
渴望返回臺灣那群人的殷切期盼,與被逐出日本而不得不上船的另一群人的心灰意冷摻雜交錯。船隻在太平洋上肅穆前行,浪濤洶湧奔騰不息。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發現了蓊鬱的島嶼並稱之為「美麗島」(Ilha Formosa)的臺灣。這雨,像是為大家宣告臺灣已經近在眼前,終於停歇。
海上望見一座小島浮現,那是臺灣最北邊的島──彭佳嶼。正中央有座白色燈塔聳立。由於小島地形平坦,這突起物顯得格外醒目。幾個鐘頭後,出現一個比 Agincourt(日治時期對彭佳嶼的稱呼)還要大上好幾倍的島,就像隻巨大的綠色鯨魚似的。然而在年輕人眼中,又像是橫臥的綠色女神。起初還只是若隱若現,不久,那輪廓便清晰地映入聚集在甲板上的人群眼中。
「祖国だ」(是祖國)、「阿母」、「台湾に戻ったぞ」(回到臺灣嘍)、「万歳」(萬歲)、「お父さん」(爸爸)……
船開進基隆港,日語和台語此起彼落。
船隻靠岸帶來一陣劇烈晃動,船身就此與臺灣的土地合而為一。人們的雙頰全都紅通通,情緒高亢。不過,年輕人獨自被孤立在歡欣鼓舞的群眾之外,仍是一臉宛如蠟像般的神情,目光茫然望向天空。
過去,年輕人曾經以一個懷抱不安與期待的十歲少年身分從臺灣去到日本。為的是要在內地學習。
從麴町的租屋處,在共住的女管家目送下,前往步行幾分鐘外的番町小學上課。不久後,便進入了四谷的學習院。
寒涼依舊、殘雪未融的一九四五年二月,B-29轟炸機在小學前方投下了炸彈。住家遭火焰吞噬,後來便寄宿同學家中。
戰爭之下,少年成長為青年,在迎來戰爭結束的同時也失去了身分認同。在日本建立家庭、經商的臺灣人選擇歸化並留在日本,然而年輕人的家人在臺灣。年輕人在百般不捨的心情下,毅然決定離開日本。
從正在進行搶修工程的東京車站一抵達大阪車站,便看到卡車和吉普車來回穿梭,一些鼻梁高挺、髮色不同的人在路上走著。自一九四五年秋天起,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開始進駐日本各地,神戶市區內也有許多美軍。
一些沒被燒毀的牢固建築物,掛上寫了拉丁字母的招牌,三宮車站南側往海邊那一片燒焦的曠野,屋頂呈半圓形、有如長條魚板似的兵營整齊排列。
即使在這裡,孤獨疏離的感覺依然向年輕人襲來。
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港口,神戶港繁華興盛,從茶葉到黑死病通通照單全收,為何自己卻非得被驅逐出境不可。再怎麼樣不講理也該有個分寸,一肚子不管是誰都想對他破口大罵的怨氣,就這麼在遣返船上搖搖晃晃好幾天。走近那落在故鄉大地上的舷梯,後方一擁而上的人潮打消了他折返的念頭,於是重重踏在這著實令人不快且滿是泥濘的基隆土地上。
港口迎接的人群擁擠紛亂,沒看到年輕人雙親的身影。連弟妹、嬸嬸或堂兄弟都沒出現。
碼頭上,負責核對身分的警官臭著一張臉四處打量。瞟了下船的人一眼,不是和同事低聲交談,就是高舉警棍在頭上揮舞以示恫嚇。破舊的制服更加凸顯出他們的冷漠無情。
儘管經過長途的旅程,年輕人依然一身深藍色學生制服搭著光澤明亮的皮鞋,直挺挺的背脊,看起來相當有教養。他那泰然自若的態度在人群中格外顯眼,警官簡直像發現敵人似的靠了過來,死纏著向他放話。
「哪來的制服?」「以後再也不能用日語。」「去哪兒?」
不是日語也不是台語,是一串沾黏混濁骯髒的聲音。聽不懂在說些什麼。
啊──這群傢伙一定就是傳聞中的中國國民黨了。
不知該如何回答的年輕人將臉一湊近,也不曉得警官們是不是因為那張沒有眉毛和睫毛的臉才嚇一大跳,全都一副僵硬的表情悻悻地走開了。
基隆,是以港口為中心將街道打造成棋盤狀的城市。港口之外的三面有山環抱,從車站、學校、神社、市場、商店到住宅,全部聚集在港口周圍的平地上。所有地點集中在步行三十分鐘內的範圍,是一個走著走著差不多都會遇見熟人的大小。
年輕人背對港口,與趕往西邊火車站的人群方向相反,朝著位在東邊的老家邁出步伐。
是隔了三年嗎?完全適應在日本的生活之後,想家的頻率與戰爭的嚴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斷了聯絡。雖然聽說臺灣的空襲並不嚴重,但自己曾經生長的基隆卻完全變了個樣子。
岸田和服店、吾妻美容院、有馬助產士、丸長商店、Tsukasaya 文具……曾經由日本人經營的那條活力旺盛的商店街已經空蕩蕩的。走得再久,也不見記憶中的景象。
漸漸開始擔心起家人來了。
走了大約二十分鐘吧。被削去一大塊的地面上裂了一個大窟窿。這是原來老家的位置。積在窟窿裡的雨水散發著惡臭。年輕人不以為意並探頭張望,盯著自己映照在有如漆黑深淵般黑亮水面上的模樣。
原本裝飾在家中梁柱上和庭院裡的燈籠慘兮兮落了一地,像是不值一文錢的破碎玩具。家裡倒塌崩落一大半的門窗已經被拆除,日常用品或家具全都清空,一樣也不剩。
不見人影,年輕人在水窪旁一屁股坐了下來。比日本燒了個精光的景象還淒慘,只剩絕望的氣息在空中飄散。無依無靠的感覺油然而生,一手緊握住懷錶,抬頭望天。
曾經盛開繚亂的杜鵑花、池中拍了手就會靠過來的鯉魚、有著氣派迎客松的日式庭園,全都化為灰燼。所有一切面目全非,唯有種在玄關旁的那株櫻花依然綻放。一陣風吹落了花瓣,他怔怔地看著花兒隨風漫舞飄揚。
年輕人與家人對話用夾雜著臺灣話的日語,他是接受日語教育的世代。
那個年代,人們以「臺灣」、「內地」來稱呼臺灣和日本。
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的年輕人,在內地的學校與日本同學並肩學習,用同樣的課本,說同樣的語言。在戰爭期間這樣的背景和學習院的環境之下,他與同學們一起拚命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國家而認真思考日本的未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年輕人與老師、同學們以學徒隊身分在深山裡靜靜迎接這一刻。當時他十七歲。
他們不是在最前線戰鬥,而是為增加糧食生產,放下課本,將鉛筆換成了鋤頭,天天在田裡耕作而已。即便如此,有些日子還是會配發三八式步槍,要他們進行操作演練。四公斤的重量對手臂來說很吃重,但每每見到刻在上面的菊花紋,就會意識到自己保管的是來自天皇陛下的物品而感到自豪。心中早已做好應戰的準備。
「因為你是臺灣人,可真是好呢。」
今後將會如何?還想不出個所以然的狀況下,同學的這句話聽來刺耳。羨慕的話語化身為毫不留情的暴力,狠狠擊中他的心。
年輕人確認了一下手中緊握的懷錶時間。
懷錶的時間指向十七歲那年夏天、那個日子的「XII」點。他的時間從那年夏天的那個日子、那個時間起就靜止不動了。為了曾經當成好友的同學與自己想法分歧而感到悲傷,他想,自己是什麼人?向來自認為是日本人,如今不被接納的事實卻擺在眼前。
拿著家裡給的生活費,每天就只是在睡覺,沒有食慾而且面無血色。眉毛脫落、睫毛掉了,情感和表情也消失不見,最後變成一個呆滯而臉上光溜溜的怪物。同學們因為他容貌上的改變感到吃驚。
戰爭結束兩年了,沒有理由繼續留在日本。於是年輕人決定要離開。
回臺灣是正確的嗎?
當初應該要歸化為日本人嗎?
回臺灣要做什麼才好?
是否該揮別日本和臺灣,前往新天地?
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航行中,無數個疑問浮上心頭,但依舊找不到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