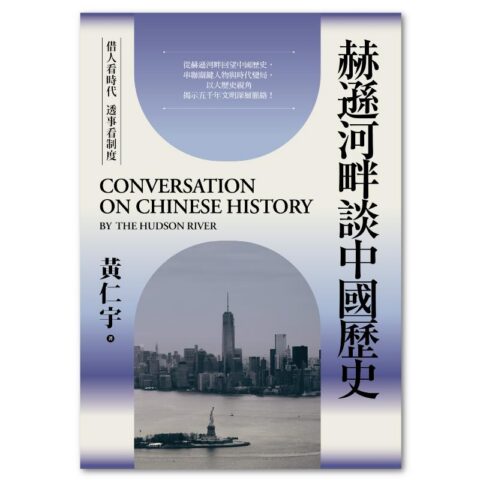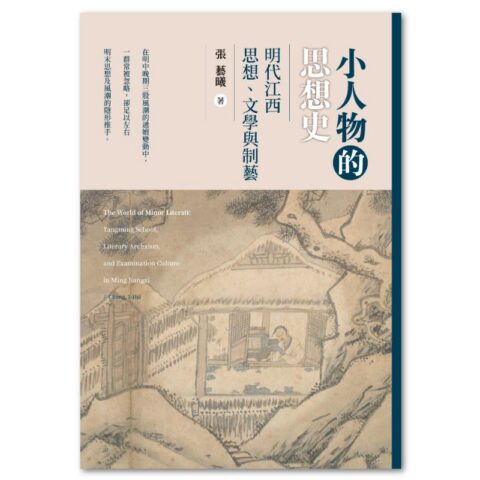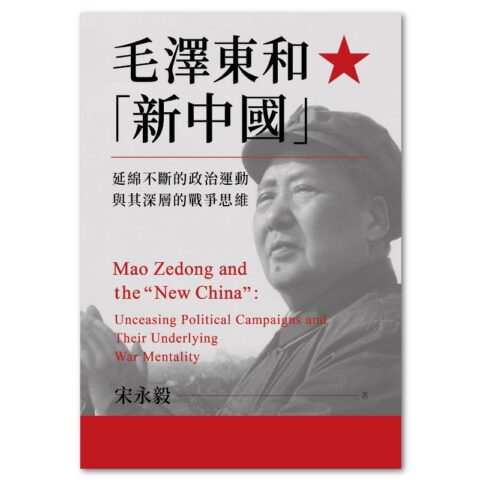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
出版日期:2021-08-26
作者:陳弱水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52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75c
EAN:9789570858945
系列:陳弱水作品集
尚有庫存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利用新的研究手段
希冀為中國歷史文化開拓出異於過往的認識
展現被忽略或遺忘的全新視野
陳弱水對傳統中國歷史和文化採創新的研究取向、撰述方式,呈現不同形式的求新努力。本書包含了實證性的個案研究,以及綜合與解釋性質等兩類論文,並區分為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兩種層面,所觸及的課題有:王權、宦官與軍人、華南原住人群、「義」與「正義」、魏晉玄學的形成、婦女文化、政教關係。這些篇章幾是相對隱晦、僻處於知識邊疆的問題和現象,其研究範圍囊括很長的時段,探討的核心議題也十分重要,代表作者投入中國歷史文化新認識的付出和心得。
歷史研究能照射至人間世的各個角落,陳弱水認為,「被遺忘的人群,被忽略的重要現象,不論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都有機會重新露面,有機會成為我們反思過去,了解當代,開創未來的依據。」
作者:陳弱水
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行政服務方面,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副所長、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等學術專書五種及論文數十篇。
自序
社會政治篇
從東亞歷史經驗看英法王權
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
前言
一、方法論的考慮
二、「山越」補論
三、從姓氏看東南原住人群
結語
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
一、長安宦官的社群性格與相關問題
二、宦官的出身背景以及與軍人的關係
三、婚姻、職業、鄰里關係和其他特色
四、小結
思想文化篇
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義」——兼論「義」與「正義」(justice)
前言
一、古代中國的「義」
二、「義」觀念的變化、發展與應用
三、「義」與西方觀念
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
上篇 玄學的突破
下篇 玄學興起的背景
代結語:玄學與中古文化思想
王弼政治觀的一個解釋
中國中古佛教與國家關係的若干考察——從歷史看「宗教」的中國處境
前言
第一階段:佛教與國家的共生共榮
第二階段:國家的控制與佛教的屈服
第三階段:儒家復興潮流中的佛教與國家
餘音
唐五代女性的意義世界——兼顧基層與菁英的考察
前言
一、三教與唐代女性
二、民間婦女文化
三、尚美主義與女性形貌
自序
這本書收了我近年的一些論文,除了一篇,都曾經發表過。把這些文章匯集在一起,主要是覺得它們都有些新意,而且幾乎都關係到中國歷史文化上比較大的問題,可以供知識界和學術界多方參考。由於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中古,大部分文章屬於這個範圍,但多數涉及很長的時段,另外也有兩篇是有關近代以前中國的通論。
本書的論文採用了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和撰述方式,代表著不同形式的求新努力。因此,揭示本書特色的最好辦法,也許是先介紹各篇文章,再做歸結。以下就依照文章在書中的次序,逐一說明它們的寫作緣由與意旨。
「社會政治篇」的第一篇文章是〈從東亞歷史經驗看英法王權〉。這是偶然之作。國立政治大學林美香教授主編《百合與玫瑰: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邀我撰寫跋文,我從學生時代以來一直對歐洲史有興趣,因此欣然同意。我在仔細閱讀該書各文後,依照書中所論,將英法王權和以中國為主的東亞王權做了比較。傳統中國的王權現象向來為學者所關注,有非常多的論說。我這篇文章的要點,是從東亞王權的角度來觀察英法王權的特色,這樣所映照出的中國王權的圖像,可能比過去的一些說法來得更具體清晰,有助於大家反思這一個重要的老問題。
和前文相反,〈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是準備和寫作都歷時很久的實證研究。這篇論文探討從漢末到隋朝中國東南的原住人群,這裡的「東南」,特指安徽南部山地、浙江中南部以及福建。中國長江以南,原來居住的都是非華夏的土著,除了少數地域,華夏化是秦漢以後才開始的,這個過程持續非常久,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間,華南地區有大批非華夏或華夏化程度很淺的人群。學界對這些人群了解相當有限,遠遜於北方的胡人。我關注這個問題,希望能在學界既有業績的基礎上,對從漢末到宋代的華南土著進行系統的探討,但因為手頭一直有其他研究在進行,還沒能如願。
不過,關於早期華南土著,有個問題長期吸引我,決定先行探討,本文就是這項工作的成果。在長江以南,上述東南多山的一帶,相當晚才和中國的郡縣統治發生密切關係——基本上是孫吳以後,當地的居民當然是以土著為主。但在南朝末年以前,除了在很短暫的一段時間,有限的地理範圍內,這個廣大的地區沒有見到任何族稱,其他訊息也很少,我們對這裡的認識有很大的空白。我希望有所突破。由於資料零星,加上問題性質特殊,我採取實驗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我以當地的姓氏作為主要課題,除了由此獲得對東南人群的具體了解,對於華南華夏化的歷程,也觀察到前人未曾楬櫫的模式。
「社會政治篇」的第三篇文章是〈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這是我從墓誌中發掘的問題。我在廣泛閱讀唐代墓誌的過程中,注意到宦官不僅是政治勢力與內廷官員,而且在長安建構了自己的社群,我感覺,探察這個現象,能夠拓展我們對唐代社會和文化的認識。宦官不能生育,他們透過婚姻和收養,組建了家庭與家族,居住在特定的地點,代代相傳。唐代宦官的這種生活是另類的,但他們用以建構社群的元素則廣泛存在於唐代社會。此外,唐代宦官社群的對外關係以軍人為主,特別是關中軍人,這一點發現也增加了我們對長安及其周邊社會的認識。傳統唐代史料中的訊息集中於政府高官和上層士人,學界對社會其他成分了解很薄弱,近年大批出土的墓誌含有不少宦官和軍人的資料,本文利用這些資料,稍微進入以前人們知道很少的世界——也許可以稱為「社會中間層」的世界。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思想文化篇」,收論文五篇。第一篇〈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義」—兼論「義」與「正義」(justice)〉取自我的另一本書《公義觀念與中國文化》(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收入本文的原因是,本書有不少文章涉及傳統中國史上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加上這篇,應該可以呈現給讀者更廣闊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圖景。「義」是傳統中國的重要觀念和價值,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有類似的想法。在中國,「義」觀念有特殊的命運。「義」在學術思想上有重要性,主要限於從春秋到西漢,東漢以下就逐漸邊緣化,但此後,這個觀念卻在民間流行很廣,內容多樣,有超乎其古典涵義之處。到了近代,西方justice觀念傳入,一般譯為「正義」或「公義」,「義」的意識似乎又因此有所提升。本文是對傳統中國「義」觀念的整體說明,並與justice觀念進行比較,希望能揭示中國「義」觀念的關鍵特色和當代潛力。
接下來的文章是〈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漢晉之際思想變動,玄學興起,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心靈圖景。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有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對我而言,一直有個疑問:漢末以來,知識界百花齊放,諸流並競,為什麼玄學最終成為主流?漢晉之際是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複雜多變的一個時段,過去學者進行研究,有兩個主要方式,一是著眼於此時的思想情勢,一是追索玄學的來源。對了解玄學的興起,這兩個方式似乎還是有所不足。前一種研究讓我們認識到漢晉之際發生了廣幅的文化和思想變化,但玄學的出現和這些變動有什麼關係,並不容易看清楚。後一種研究雖然對玄學的淵源提出了有價值的說法,但在漢末以來的大變局中,只挑選有玄學影像的元素進行討論,就歷史敘述而言,有目的論的嫌疑,好像推動玄學興起的力量就是漢晉之際思想的主線。真的如此嗎?
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我採取一個非正規的研究方式。我顛倒了歷史時序,先分析從曹魏到西晉玄學思潮的要素,再根據分析所得的認識回頭觀察東漢後期以下的思想動態及其與玄學興起的可能關係。東漢晚期開始,士人的心態和行為都發生變化,局面很複雜,先仔細了解玄學本身,有助於辨識玄學形成的背景和動力。此外,過去的玄學研究,往往集中於抽象的核心觀念,對玄學作為關懷廣闊的思潮性質重視不夠,本文分析玄學的多元要素,也能比較明確展現玄學與漢晉之際歷史環境的關係。我的非正規研究對玄學興起的問題應該有重要的澄清作用。本文確認,玄學的興起是很突然的,這一點顯示,歷史上的重要思潮未必都經過長期的醞釀,在某些條件下,突發的思想也可能有強大的力量和深遠的影響。
「思想文化篇」的第三篇論文是〈王弼政治觀的一個解釋〉,這是我研究玄學興起的副產品。王弼(226-249)的《周易》、《老子》注和相關著作是玄學成立的關鍵。這兩部經典的內容和王弼的注文往往很抽象,很「玄」,好像離具體的人間事務很遠。不過學者已指出,王弼的作品其實有政治思想的色彩。本文主要在說明王弼的政治觀與歷史環境的相關性,特別想展現,在儒家早已成為正統的文化情境,道家型的政治思想可能有怎樣的樣貌和涵義。在本文,我應該也揭示了王弼政治社會思想若干較少為人注意的部分。
接下來的文章是〈中國中古佛教與國家關係的若干考察—從歷史看「宗教」的中國處境〉。如果把宗教界定為對人以外力量的崇拜和相關活動,或者說,一切關於「靈」的信拜,宗教在中國一直存在,而且在古代非常興盛。但有教義、有組織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則是因為佛教傳入,才在中國出現。漢末道教教派的產生是否受到佛教影響,不得而知,但佛教為中國最早的制度性宗教,是沒有疑問的。從佛教進入中國到現在,已經有兩千年之久,宗教(特指「制度性宗教」)卻一直是「有問題的存在」(problematic existence),正當性一直受質疑,發展受到壓制。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國家對宗教的疑忌。我是從這個關心出發,討論從東晉十六國到北宋初期(約四世紀至十世紀)佛教與國家的關係。
我在學界既有研究和個人史料探索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三階段說」,作為對中古政教關係的初步通盤說明。有關中國佛教和國家關係的研究相當多,但不是都注意國家和宗教間的緊張,事實上,在中國佛教史的一般性描述和討論中,這一點常被忽略。希望本文能幫助大家認識這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歷史的回顧也應該能透露宗教在當代中國遭逢困境的部分緣由。
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唐五代女性的意義世界—兼顧基層與菁英的考察〉。這個主題是從我的專書《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7)所引發的。這本書主要採取社會史的視角,研究女性在唐代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但不免也接觸到女性生活中的意義問題,因此書題中有「文化」一詞。該書出版後,我對書中的「文化」部分一直不很心安。原因是,這部分基本上是對於我所觀察到的現象的意義層面之抉發,我沒有特意選擇文化涵義豐厚的課題,也很少針對婦女文化直接進行論說。多年後,我覺得,我也許可以再做一件事:設法對唐代婦女文化建立理解的架構。本文就是這項工作的成果,除了唐代,也兼及五代。
勾勒唐五代女性的意義世界是有點冒險的。關於時代比較早的婦女,原本訊息就少,這些資料又多集中於統治階層及其周邊,但要建立大體的認識,必須踏出狹窄的菁英圈,發掘更為隱晦的民間婦女生活樣貌,所得如何,事先很難預知。本文在重重限制之下,設法辨識唐五代婦女文化的主要元素,指出它們之間的關聯與斷裂。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為唐五代婦女文化提供一個系統但又呈現多元和衝突的圖像,一個盡可能貼近現實的架構,讓讀者獲得巨視的觀點,這樣,我們對有關婦女的個別案例,將能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礎。
總結而言,從撰述的形式來說,本書包含了兩類論文,一類是實證性的個案研究,另一類有比較強的綜合與解釋性質,無論是哪一類,這些文章其實都代表我對我所感知到的一些中國歷史和文化重要問題的新探索。本書觸及的課題有:王權、宦官與軍人、華南原住人群、「義」與「正義」、魏晉玄學的形成、婦女文化、政教關係。在其中,學界對王權和玄學探討已多,但其他幾乎都相對隱晦,僻處於知識的邊疆,本書盡量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希望能為這些問題開拓出新的認識。我最大的心願是,歷史研究能照射至人間世的各個角落,被遺忘的人群,被忽略的重要現象,不論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都有機會重新露面,有機會成為我們反思過去,了解當代,開創未來的依據。
過去十餘年,大多數時間,個人公務非常繁重,研究寫作的時間變得零碎。本書所收的文章幾乎都是在這種情境下完成的。在這段忙碌的時期,除了緩慢進行我長期耕耘的唐宋之際思想演變研究,我也利用空檔,探討若干蓄之於胸已久的其他個別問題,有時受邀寫稿或演講,也藉機進行這項工作。現在這些成果結集於此,是生命史上很可紀念的一件事。是為序。
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
前言
本文研究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首先要對這個課題涉及的時地提出說明。在地域方面,所謂「東南」,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安徽南部、浙江、江西與福建,秦漢以後,在很長的時間內,這裡還是原住人群活躍的地域。不過,在這個範圍之內,本文要排除兩個部分,一是杭州灣南北的平原,此處很早就成為江南的華夏核心區,另一則是江西,留待以後另行探討。本文涵蓋的地域可以用西晉武帝太康四年(283)的行政區做相當精確的表達—即當時的新安郡、東陽郡、臨海郡、建安郡和晉安郡。這個區塊的最大特點是多山,陳隋之際夏侯曾先的《會稽地志》如此描述會稽郡的地理位置:「南面連山萬重,北帶滄海千里」,上述五郡,大體就是這片「連山萬重」之地。
在時段上,「早期中國東南」的「早期」主要指東漢晚期和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的脈絡裡,原住人群的概念基本上是針對華夏而發的,秦以前,長江以南華夏化的地區很少,談不上有意義的原住人群問題。秦漢之際,江南華夏化稍深的地方大概只限於當今江蘇南部、江西與湖南北部。舉例而言,漢文帝即位(西元前179)之初,南越王趙佗(當時仍稱帝)給他一封信,其中說,南越「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長沙指長沙國,就是後來的湖南中北部偏東一帶,「其半蠻夷」恐怕還是低估。至於南越所在的今廣東地,幾乎可說是全蠻夷了,趙佗在信中即自稱「蠻夷大長」。兩漢時期,特別是漢武帝(西元前157-87)之後,隨著郡縣統治在華南的擴大和深化,華夏民與土著的分野浮現,漢末北方大亂,更令政府與江北移民的力量深入南方,廣大的華南土著深受衝擊。設法從他們的立場來認識這塊土地的歷史,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的時段,就整個中國史的架構而言,一般稱作「中古前期」。不過,兩漢之時,除少數區塊,本文所涵蓋的地域基本在中國統治之外,而且除了史籍所載的東甌、閩越國以及考古發現,我們對這個地區在漢末以前的情況可說毫無所知。以此,就這個地區而言,從東漢晚期到隋代只能說是早期歷史,而很難說是中古,因為「中古」假定了之前有「古代」,但在漢末之前,這裡大部分只能屬於「原史」時期。本文題目中的「早期」是界定「中國東南」而非「中國」的,但本文行文仍必須經常顧及中國史的整體脈絡,使用「中古」一詞和朝代名稱,還請讀者理解。
本文立意從事早期中國東南土著的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是我對這個歷史問題有興趣。長江以南遠離華夏形成區,東南則本為所謂百越之地,早期在此建國的吳、越,華夏化的程度都很低,越國尤其如此。秦漢以後,華夏文化開始在長江下游平原生根繁盛,到唐宋之際,這裡連同東南的其他許多地域,一躍而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的新中心。關於這段歷程,深度的研究似乎還相當有限,以原住人群為中心的探討更是罕見。
其次,我想做個實驗:看如何研究歷史上的邊緣人群,更確切地說,如何研究文字社會中幾乎沒有文字資料的人群。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人類生活,不但在知識上,我們想了解各種各樣的人群,盡量多知道一些,而且在道德上,有責任如此做。我們不應該特別偏重某些人群,或某些形態的活動,如果這樣,我們得出的圖像是片面的,大體認識也容易偏差。可是在現實上,歷史學基本上是依賴文字資料所得出的知識,我們最了解的或是最能了解的,就是與文字關係密切的人。這些通常是有權者和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身邊的人。簡單說,歷史研究的一個困境是,就知識目標和倫理責任而言,它的對象是人類生活整體,但我們所奉行的方法準則,卻強迫我們不斷把眼光放在特定的人群,強迫我們默認生產話語的人掌握了歷史的發言權,於是,在歷史知識邊緣或其外的人,往往比在現實的處境中還要邊緣。如何突破這個困境——即使局部突破也好,是歷史學的重要課題。
現在想具體說明,我為什麼選擇早期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與福建的原住人群作為研究課題。我想探討這些地帶土著的根本原因是,在早期帝制中國,這裡是南方原住人群的聚居地,但有關的記載卻特別稀少——少於華中、華南大部分其他地區,甚至連族稱都很難看到,政府與華夏士人通常只在特殊的時刻才對這些人群有所記錄和書寫,很適合作為探測史料與歷史知識關係的園圃。以下分區略作介紹。
首先是安徽南部。這主要指安徽在長江以南部分的山區,其實也包含浙西一小塊地區,約略等於西晉宣城郡的南半部與新安郡,其核心地帶就是後世的徽州。直到漢末,在這裡活動的都是與郡縣統治關係甚稀的土著人群。
其次是位於今浙江中部偏西的錢塘江上游衢江流域盆地,約當西晉時的東陽郡。在東漢後期(二世紀中葉),此地只有兩個縣:烏傷(今義烏)和大末(即太末,金華與衢州之間),郡縣化的程度約同於安徽南部。
再來則是前文所說的會稽以南「連山萬重」之地,即今浙江中南部山地與福建。橫亙整個漢代,這裡至多只能算是帝國的極邊疆。在東漢後期,從今浙江臨海以南至福建、廣東交界約十六、七萬平方公里之地,只有三個縣:章安(今臨海)、永寧(今溫州)、侯官(俗稱東冶,今福州),而福建境內只一縣。在此區域,政府有效管轄的範圍有多大,華夏化程度如何,可想而知。漢末許靖從會稽搭海船到交州(今越南北部),說他和同行者「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指的就是這一帶,至於「不見漢地」,則是逕視此為域外了。在文化上,漢帝國的實質東南邊界在哪裡呢?從行政區劃分看來,大概在會稽郡北端,今杭州灣南岸、錢塘江下游之地。三國吳末帝鳳皇三年(274),會稽人邵疇上言皇帝孫皓:「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邵疇可能是郡治山陰人,他的話似可支持上述的判斷。
本文研究的就是上述幾個地區,我將利用不同的取向探討兩個課題,一個採用比較傳統的歷史研究法,另外一個則具有實驗性。在進入具體的個案之前,我想對如何研究資料稀少的問題,略作方法論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