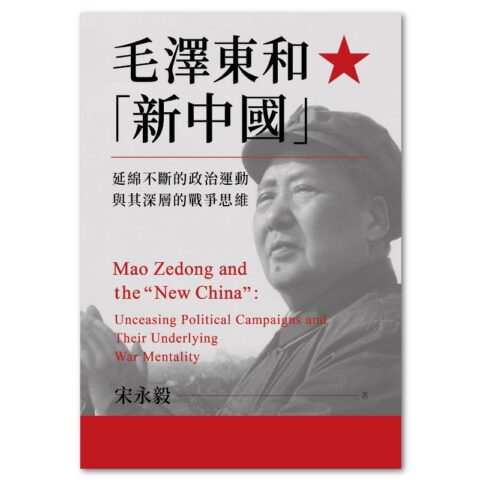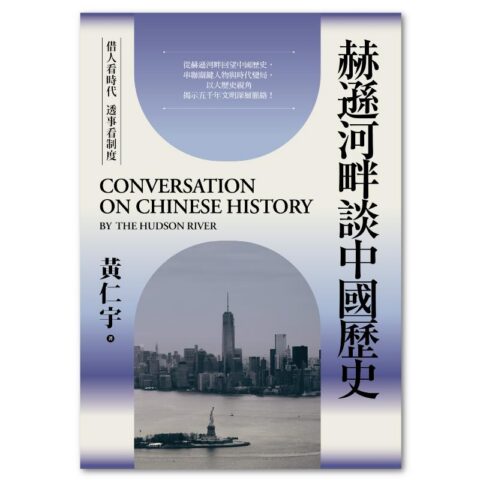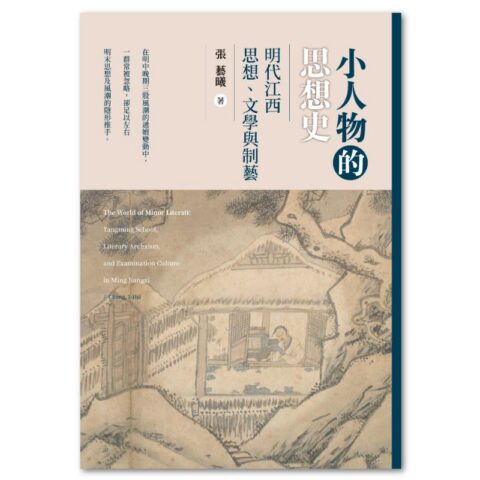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
出版日期:2020-04-01
作者:張邦彥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20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6cm
EAN:9789570855104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催眠術是清末民初時期最眾聲喧嘩的大眾科學,
展現菁英與常民、科學與迷信、心理學與靈學
在界線上的浮動和滲透,
並帶來深遠的社會和文化效應。
《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從科學史的角度,結合社會文化史與思想史的關懷,主張必須對近代中國的「科學」採取複調式的理解,超越五四科學主義話語及學院菁英的基調,呈現異質歷史行動者相互競逐、應和的多元聲音。
張邦彥醫師從大眾的日常生活出發,考察催眠術的傳播方式,並解釋人們對催眠術懷抱正反兩極情感的因由。接著聚焦於催眠學會的科學實作,分析學會從事劃界工作及拓展科學網絡的策略,兼論及催眠術對現代自我的形塑。最後透過爬梳催眠術與靈學的糾纏,追索近代中國心理知識的分化軌跡,指出學院心理學、催眠學會、靈學會看待科學的殊異立場。藉由這些彼此關聯的面向,重構動力精神科學在近代華人世界興起跌宕的多重圖像。
作者:張邦彥
1988年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目前為台大醫院醫師。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醫學史、科技與社會研究。
序一 複調視野下的催眠術/黃克武
序二 精神與科學的另類史/王文基
第一章 導論
一、楔子
二、什麼「科學」?誰的「科學」?
三、大眾科學史的視野
四、大眾科學意義下的西方催眠術
五、催眠術與近代東亞
六、全書安排
第二章 驚奇與憂懼:日常生活中的催眠術
一、電磁化身體觀的浮現
二、新式出版物中的催眠術
三、催眠術的展演
四、講習所的設立與政府的壓制
五、思想性的線索:群眾心理學和「暗示」觀念的興起
六、經驗性的線索:犯罪事件的指證與文學的再現
七、歷史性的線索:失魂與附身的恐慌
八、小結
第三章 機構的發展:催眠學會活動中的商業、政治與科學
一、前言
二、精神療法的興起
三、催眠學會簡史
四、催眠學會的市場經營
五、催眠學會的政治操作
六、催眠函授中的「商業交易」與「互惠交換」
七、規範下的人與物
八、小結
第四章 心理知識的分化:催眠學會、靈學會與學院心理學
一、前言
二、催眠學會的靈學主張:「生機論」與「機械論」的思維
三、靈學領域的競爭者們
四、回到早年Psychological與Psychical的孿生關係
五、學院心理學與靈學的衝突
六、一場《新青年》上的直接對話
七、從科玄論戰思考「精神」與「科學」的關係
八、小結
第五章 結論
一、譜寫近代中國科學史的複調
二、界限劃分、知識分化與自我的形塑
三、過去與未來
後記
參考文獻
圖目次
圖1 麥克勞根療病電帶
圖2 《科學畫報》內的一幅動物催眠插圖
圖3 《新法螺》封面
圖4 魔術團表演之催眠術實況
圖5 中國精神研究會廣告
圖6 〈催眠術親身實驗記〉小說附圖
圖7 收錄於《繁華雜誌》第4期的滑稽小說之插圖
圖8 一份1845年法文報紙中的插圖
圖9 余萍客與古屋鐵石合作催眠一名日本婦人
圖10 芳洲於1917年替北京地方會員講學後合影
圖11 屋鐵石的《高等催眠學講義錄》
圖12 芳洲的《催眠學函授講義》
圖13 心雨的《最新實驗催眠術講義》
圖14 國心靈研究會實驗講演會的現場照片
圖15 心靈》雜誌上的一份催眠療症實驗報告
圖16 萍客示範撫下法的施術圖
圖17 海濤所繪製的無線電與千里眼類比圖示
後記
25歲那年,我即將從醫學系畢業,面臨了何去何從的抉擇。進入醫院,完成專科訓練,人生的道路看似自然而然向前延伸;但我不免遲疑,是否要將青春的大好時光投擲於日復一日的醫療工作?在一場醫院忘年會結束後,幾個一同實習、喝得微醺的朋友仍意猶未盡,跑到醫院對面的超商繼續閒聊。我們人手一瓶啤酒,漫無目的地展開話題。忽然有人問我:「這真的是條你想走的路嗎?」聽到這句再普通不過的問句,我竟沒來由地開始啜泣,終至哭掉一整包面紙。誰知道這個令人詫異、尷尬的反應,竟改變了我接下來幾年的旅程。就像催眠術一樣,酒精在那個當下也催化了一場無意識之旅,讓我聽見內心的聲音。在成書之際,我必須要感謝那個令人尷尬的時刻、在場的友人,以及手中的啤酒,讓個性謹小慎微的我,決定做出不一樣的嘗試,最終孕育了這本作品。
本書改寫自我的碩士論文。2015年我離開醫院進入研究所,踏入我的指導老師王文基教授的研究室,跟他說我想學習怎麼做歷史研究。我在大學剛入學時曾修過他開設的「身體史」課程,懵懵懂懂地讀了Foucault、Elias、栗山茂久等人的名作,當時想不到八年後還能有一段師生緣分。從學於王文基教授的這些年,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回憶,我所獲得的不只有知識上的累積,他更為我示範嚴謹、謙遜的治學態度。身為一個學術新手,我深感幸運他願意撥出許多時間、心力,逐字逐句閱讀我的論文,並提出深刻、鉅細靡遺的建議。如果沒有他的期待與付出,我無法一次又一次撐開自己的極限,讓自己走得更遠一點。我同樣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其他師長們,包括傅大為、林宜平、陳嘉新、楊弘任、郭文華、范玫芳幾位教授,他們總是能帶給我啟發與溫暖。而我對臺大社會系的賴曉黎教授也感念在心,大學時期他接受我旁聽他的幾門課程,當時打下的人文社會思想的基礎,至今依然受用。
兩位參與我學位考試的師長提拱我關鍵的幫助。黃克武教授過去關於上海靈學會的研究啟發我甚多,通過學位考後他更鼓勵我將論文改寫成專書出版,並將我的作品引介給聯經出版公司。若少了他的提點和鼓勵,我大概不敢奢想出書一途。巫毓荃教授跟我有著相似的求學背景,他的經驗很能支持我面對生涯抉擇時的徬徨。而他對日本催眠術史掌握精熟,一路以來不吝替我解惑,對本書建立東亞催眠術發展脈絡至為重要。
我也要感謝聯經學術叢書編輯委員會同意出版拙作,這個決議對於年輕研究者如我是莫大鼓舞。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評論我也銘記於內,一位幫助我修正若干缺失並強化書稿的可讀性,一位則給予我慷慨的肯定。而主編沙女士在編務上多有費心,我亦在此獻上誠摯的感謝。
從寫作論文到完成專書,我一路上承蒙許多善意的協助,謹在此一一致意。賴品妤、蔡庭玉幾乎讀遍了我每一個版本的稿子,並每每直言不諱提供意見,陪我反覆琢磨寫作上的各種問題。李昕甯、鄒宗晏、楊文喬、趙子翔、陳俐伊、陳柏勳、陳禹安、曾心民等朋友也曾經讀過書稿的部分章節,懇切地跟我分享他們的看法。本書部分史料得自於劉紀蕙教授和陳雅妮女士,尤其是透過王文基教授取得陳女士的收藏,讓研究增色不少。我也謝謝陳建守曾跟我分享他看到的相關研究資訊,Eom Young-Moon分享他對韓國催眠術發展的觀察,以及蕭育和、洪均燊、尹燕哲幫助我取得研究需要的文獻。研究所畢業後再度進入臨床工作,行醫與寫作經常讓我蠟燭兩頭燒,幸好醫院同事們(特別是謝秉儒、廖哲緯、陳秉暉、江宛霖)願意分擔和體諒,才讓這本書能夠如期完成。
如今回想,寫作這本書的過程猶如一場奇幻之旅。幾年之前,我還不曾想過自己會縱身跳入歷史的領域,我的史學訓練近乎闕如,對學術寫作也一知半解。我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我願意另闢跑道,夜以繼日地追趕,想盡辦法克服各種自我質疑,而有目前這些初步成果?此刻要給予一個全面的解釋對我而言仍顯得艱難而費解,但我想部分可能源自於我在醫學訓練中感受到的某些匱乏吧。比起死亡率、存活期、相對風險、生命品質、疾病負荷等以測量為導向的醫學概念,一直以來我更好奇個體怎麼與自身,與他所屬的群體、群體之外的他者,以及他所身處的環境、時代,建立有意義的生命連結。我固然承認以科學的手段解決肉體耗損、病痛的重要性,但我亦在意個人與集體是如何建立他們的身心靈和外在世界的秩序,或在失序中謀求療癒、共存、革新的安身立命之道。終究,我們的生命除了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它既立足於自然世界,也同時寓居於過去記憶與未來期待的交會之所。我的日常臨床工作崇尚專注於當下的冷靜與理性,但透過書寫過去人們的諸多努力、嘗試、對理想或可欲事物的追尋,不論他們偉大或渺小、成功或失敗、脆弱或堅韌,很大程度上都讓我重新找回被壓抑的熱情與感性。這本書如果不是直接回應這些關切,也至少部分是在這樣的心態下編織出來的。
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摯愛的家人。或許因為世代及教育背景的差異,使得我經常不知道如何向他們解釋自己在做些什麼,他們也困惑於為何我總是深鎖房門,足不出戶。但即使如此,他們仍然寬厚地支持我的每一個選擇。從過去到現在,我何其有幸能帶著他們的祝福及體諒,朝向未知而開放的將來。
第二章 驚奇與憂懼:日常生活中的催眠術
電磁化身體觀的浮現
1905年的某一段時間,上海《申報》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同樣一則廣告——長命洋行的療病神帶。一名留著絡腮鬍、身穿西裝的外國人用雙手捧著一條電帶,電帶放出無數電氣,射向打著赤膊、留著長辮的中國男子。再仔細一看,男子的腰上也纏著這麼一條電帶,電帶上有電鉤交通電流,電鏢控制開關,電線則連接到銅箍,銅箍貼著命門、丹田、腎部,讓電流直達腦筋、下通湧泉、旁及奇經八脈五臟六腑。廣告圖像周圍環繞文字,開頭寫著:「本行所售之電氣藥帶乃著名西醫麥克勞根所創製。」電帶號稱能治療各種疑難雜症,從身體嬴瘦、小便赤澀、月經不調,到傷寒、肺結核、癱瘓。
之所以在本章的開頭提起這一則廣告,我的目的不在於讓讀者多了解一項過去的新商品,而是希望藉此挖掘某種較深層的意義關連,以呈現中國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其中一面。中國的現代性,如李歐梵所言,涉及一種新的時間意識,讓「今」與「古」成為對立的價值,並且將「當下」視為與過去斷裂、連結輝煌未來的轉折時刻。晚清民初的數十年間,是現代性意識萌發的關鍵年代,新事物接二連三地到來,人們的經驗之流暴露於不斷的驚奇之中。而這些新事物並非單獨地被接受;相反地,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整體的轉變下,以不同於過去的方式把握個別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帶這項醫療商品,就跟本書要探討的催眠術一樣,是在一種新的身體論述浮現的前提下,才在中國社會裡獲得廣泛的接納。這種新的身體論述,我稱之為「電磁化的身體觀」,它形塑大眾的現代性經驗,並使催眠術獲得新的認識可能。
當我們細看電帶廣告的內容,會發現裡頭主張:世界中的物質無不帶有自然電氣,而人體的精神氣血亦有賴電氣維持,透過電帶由外而內補充、調節人體電氣,即能夠增進健康,緩解病痛。再考究長命洋行的產品來源,可知它來自於19世紀末美國芝加哥Dr. M. L. Mclaughlin公司出品的Dr. Mclaughlin’s electric belt。這類電氣醫療產品風行美國並暢銷中國,是一個時代集體心態的縮影,無論1890年代美國的愛迪生電力網絡,或者20世紀中國的口岸城市、殖民地台灣,人們不斷目睹電氣化帶來現代生活的改變。一名研究者曾經用「電氣神學」(electric theology)來形容當時人們對電力的崇拜,彷彿在它所及之處賦予一切事物生命與力量。李歐梵在他知名的《上海摩登》裡也提到,上海的摩登作家們「沉醉於都市的聲光化電,以至於無法做出任何超然的反思」。聲光的新形式感官體驗來自於電氣的發明,電磁相生,「電磁化」可說定義了近代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面向。
我們在此看見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力設施作為外部技術系統,提供人們視覺、聽覺的新刺激,而身體對電流、磁力流的體驗則成為內部的對應。療病電帶以有形的方式創造電流交通的身體感,而催眠術則帶來無形的內在電磁體驗,許多人形容感應到能量在軀幹四肢流動,甚至設想腦筋能夠放射電磁波動。就此而論,現代性不只由物質的現代化所促動,也牽涉人們的身體意識及身體想像上的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身體觀絕非一朝一夕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傳遞、接觸和抗拒後,才在特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產生廣泛影響。電磁化身體觀最早在18世紀的西歐萌芽,1773年,維也納醫師梅斯梅爾宣稱在治療個案奧斯特林小姐(Fräulein Oesterlin)身上發現了先前人們不曾察覺的物質——動物磁力。這位催眠術的先驅指出,宇宙間布滿流體,且「天體、地球和有生機的身體間存在交互影響」,疾病產生於磁力流的不均勻分布及阻滯。他的磁性催眠學說吸引無數追隨者,並擴散到西歐各地。1830年代,磁性催眠術從歐洲傳入美國,昆比繼承這項磁化治療,許多昆比治癒的病患描述催眠過程像是「抱著一顆電池站在絕緣凳上」。1851年時,美國催眠師多茲甚至出版一本名為《電氣心理學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lectrical Psychology)的著作,以正負電性來解釋疾病的原理。這套疾病的電磁解釋,影響了後來療病電帶的發明。
不過,電磁化身體觀卻沒有緊接著在中國出現,而是要等到19世紀末。這段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差,不是來自知識或技術在傳遞上的延遲,而是過去天朝的優越心態,使得新的身體觀缺乏適合的出現條件。事實上,中國人在梅斯梅爾發展出這套治療的10年內就對此有所聽聞。1783年8月1日,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致信給巴黎的耶穌會長官貝爾坦神父(Abbé Bertin),表示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跟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非常相似的學說——中國功夫(Kong-fou chinois)。「倘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堯舜、黃帝、神農、乃至伏羲的時代,有一種差不多類似於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的治病方法,那麼無疑至今仍有一些還流傳著。」他還指出,梅斯梅爾的理論中的磁性雙極(deux Pôles)即是太極系統裡陰陽的特殊、附屬形式,而氣的不平衡則造成疾病。錢德明的觀點除了來自自身觀察,也很可能來自於他跟中國人溝通的經驗。而19世紀初,法國耶穌會出版的《外派傳教士教化書信選集》(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更印證了這點,一名傳教士寫道:
他們〔中國人〕總是希望說服我們,所有對社會有用的科學與藝術都是在歐洲人動念之前的幾世紀創造於中國。一個很簡單的證明就是:磁性催眠術的發現應歸功於他們。這門技藝被他們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而即使到今天,那些道士仍顯示他們比我們的梅斯梅爾及其他法國磁性催眠專家更加優越,不管在理論或在實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