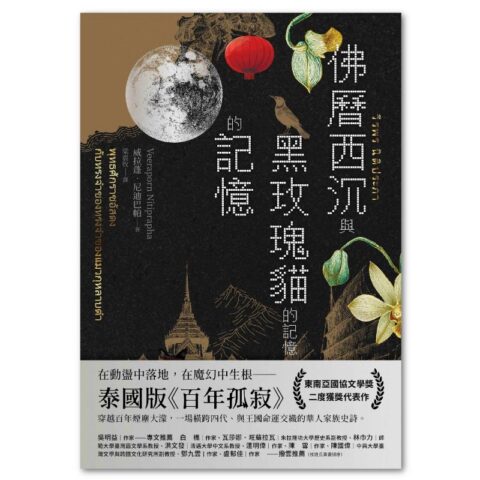野蠻人之神:太平天國
出版日期:2022-10-13
作者:施益堅
譯者:林敏雅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4861
系列:小說精選
尚有庫存
多麼可悲啊,這場革命本該創造出全新的中國!
西方觀點書寫「太平天國」的傑出小說;
國外讀者驚嘆:原來中國曾有過基督教革命!
★ 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德國圖書獎年度決選之作 ★
★ 2009、2012、2018三度入圍德國圖書獎年度決選 ★
★ 德國媒體、書評、讀者一致好評、驚豔盛讚 ★
滿清的迂腐,西方的傲慢,文化的誤解
面對時代巨輪,野蠻的究竟是你還是我?
19世紀的中國出現一個轉化基督教教義而成立的政教政權:太平天國。一個落第秀才自稱上帝之子,在長期累積大量民怨的社會氛圍中一擊中的,以天父為名的農民動亂,遂蔓延成這股野火燎原般的「長毛之亂」。對世界懷抱憧憬和理想的德國傳教士菲利普,遠渡重洋到中國,盼望透過宗教感召促進東方的現代改革。然而位處時代紛擾中心,夾在中國與西方武力通商的矛盾、清廷與叛軍的衝突、宗教理想與社會現實的差距,他的內心逐漸動搖困惑……
施益堅以德國作家身分,書寫近代東亞史上慘烈的歷史景況,試圖開啟另一種思辨且富人性化的想像空間:無論是大英帝國的外交特使額爾金伯爵、滿清帝國湘軍首領曾國藩將軍,或是太平天國的理想主義者「干王」洪仁玕,時代英雄也可能是千古罪人。在急遽變化而失去方向的世界態勢中提出深刻批判與反思:相互指謫迥異之人的野蠻與傲慢,其實乃為一體兩面之事?
好評推薦
▍專文導讀
李弘祺|國立清華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齊聲力薦
林運鴻|文字工作者
陳耀昌|作家
(以姓氏筆畫排序)
1860年代的中國被強力抨擊:一場新興崛起的宗教狂熱分子大規模的暴動,掃蕩當時的社會架構,同時歐洲強權以武力入侵壟斷貿易市場。作者施益堅成功將當時分崩離析的年代描摹傳神,敘事節奏鏗鏘有力讓人讀來起勁,用字遣詞也十分優雅到位,清楚傳遞當時不安的時局。
──2018年德國圖書獎評審委員評語
在臺灣居住多年的德國小說家施益堅,其新作《野蠻人之神:太平天國》,便選擇了一種充滿反思的「西方視角」──讀者會訝異於一名德國作家對於中國古老傳統的深刻洞察,但又能夠發現,本書解剖歐美帝國主義的誠實銳利。
──林運鴻(文字工作者)
作者:施益堅
1972年出生於德國的比登科普夫,主修哲學、宗教學以及漢學,在東亞生活與工作了15年。曾先後到中國、日本、臺灣等地做研究和居留,觀察每一座城市的風土人情。而在臺灣居住的時間最長,同時完成第一部小說《邊境行走》,注定與臺灣讀者締結最深刻的緣分。曾任德國國家研究機構學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國立中興大學駐校作家。
《邊境行走》,甫出版即震撼德國文壇,成為各書店裡讀者詢問度最高的作者之一,並入圍2009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德國圖書獎(Deutscher Buchpreis)年度決選(同時入圍者還有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賀塔.穆勒),且獲得觀點文學獎(aspekte-Literaturpreis)最佳作者首作。第二部長篇小說《離心旋轉》於2012年出版不僅入圍該年度法蘭克福書展之德國圖書獎年度決選入圍,更獲2014年柏林藝術獎之文學類獎(Berliner Kunstpreis Literatur)。繼前作《離心旋轉》從丈夫的角度審視自己的人生後,2015年出版的《對手戲》鋪陳女性深度心靈剖析。2018年第四本長篇作品野心更勝,爬梳歷史敘寫有關太平天國動亂的小說《野蠻人之神》,再度入圍法蘭克福書展之德國圖書獎年度決選。2021年完成新作《梅雨》,目前仍持續創作中。
譯者:林敏雅
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留學德國特利爾大學。曾旅居日本、荷蘭多年,目前定居德國,從事德、荷文翻譯工作。
導讀:施益堅的太平天國/李弘祺
0.序曲:無名氏之見
1.香港|上海,1860年夏天
2.秦國的大洪水|上海,1860年夏
3.大沽口(白河口)|1858年5月,直隸灣
4.極樂寺|1858年5月,直隸灣
5.戴玻璃眼珠的陌生人|香港—廣州—梅嶺關,1859年夏/秋
6.有三寸金蓮的女人|布魯姆霍爾,1859年秋
7.鄱陽湖上的霧|贛江行,1859年9月/10月
8.崑崙山蟒蛇精投胎轉世|安徽省,1859/1860 冬
9.縣令歸來|鄱陽湖府邸,1860年冬/春
10.如虎添翼|祁門大營,1860年春/夏
11.海上之城|上海,1860年夏天
12.千魂之江|上海,1860年夏天
13.異鄉女神的目光|額爾金勳爵在天津,1860年9月
14.在時間的地平線上|祁門,1860年9月初
15.北京紅牆|前往北京,1860年9月
16.寒風之都|曾國藩赴北京,1869年9月/10月
17.紅毛鬼|曾國藩上訪北京,1860年10月
18.圓明園|額爾金伯爵抵北京前,1860年10月
19.亞丁的理髮師|額爾金伯爵在上海,1860、1861年冬
20.天京之春|南京,1861年春
21.玉皇大帝令下|曾國藩將軍在安慶前,1861年春/夏
22.陌生客|天京,1861年冬、1862年春
23.通往彼岸的橋樑|額爾金伯爵在印度達蘭薩拉,1863年11月
24.續夢庵
25.悖逆之子|南京,1864年夏
26.結局
人名索引
導讀(節選)
施益堅的太平天國
李弘祺
施益堅(Stephan Thome)博士是德國出名的小説家,已經出版了五本小説,其中三部曾經被著名的德文書出版獎提名並入圍,可見他在小説著作上的成就。這本書使用小説的方式來描述十九世紀中葉,非常複雜的中國内政及外交的演變:集中在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這些歷史演變的重要人物:從洪秀全(以及洪仁玕)到曾國藩到英國外交代表額爾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全名中譯為「第八代額爾金伯爵,同時也是第十二代金卡爾丁伯爵」)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因此它可以歸類爲「歷史小説」,而重要性就不僅止於文學,更在於作者所要演繹的歷史的本質和解釋。讀這本「小説」的人除了可以欣賞文字魔力的引人遐想之外,更能從它看到人類歷史的繽紛多彩。這本書在這兩點上都有出色的表現。再因爲它所觸及的「事件」和人物是我們大部分人所非常熟悉的,因此自然地會引起中譯本的讀者們的感動。他們可以經過認同,反思和印證書中的故事,產生一種情感的過濾和昇華。
本書從太平天國講起,到英法聯軍簽訂合約爲止。作者借用一個虛構的人物(菲利普)來交錯編織書中的情節。這個虛構的人是一個不很老實的基督徒:他喜歡浪跡天涯,不尊崇傳統,借用傳教士的身分,遠走中國,結果見證了太平天國的動亂,中英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當然,這個人的所見所言就是作者的觀點和聲音。
作者借用的是歷史的想像,透過文字的精彩來表達他對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看法。首先,施益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擁有柏林自由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熟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這點在書中到處可見。我敢說華人對十九世紀中國史的瞭解如果僅限於大學的程度,那麽他們很可能還比不上施博士,因爲十九世紀的中外關係的歷史記載不只限於中文圖書,許多紀錄還存在於英、法、德,乃至於俄國的資料當中。因此一位能具備宏觀視野的歷史學者一定要能參考中外史料。施益堅在中文之外,還能參考上述語言所記錄的史料,因此他所掌握的視野遠遠勝過即使專門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中國史學家。這本「歷史小説」一定可以在研究這段歷史的衆多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
太平天國的歷史定位在清朝滅亡以前當然是負面的,因此説不上有什麽合乎我們現代人所説的歷史敘述或客觀瞭解。清朝滅亡後,我們才進入一個可用批判眼光來探究它的時代。二十世紀大部分中國人對於太平天國的定位受孫中山先生的看法所左右,大多認爲它是一場民族革命,要推翻滿清外族的統治。雖然這樣的解釋在國民黨當政期間,沒有得到大力的鼓吹,但是基本上到抗戰前夕,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對它抱持的是相對正面的印象。
第一個對太平天國做出有系統研究的無疑是簡又文。他的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國史的學術地位。他更是孫中山的看法最好的詮釋人。因爲他曾經在耶魯大學與芮瑪麗(Mary C. Wright) 及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交流論學,並在那裡出版得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73),因此對西方學者如何透過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太平天國有相當的影響,即使他的史學(基本上反對所謂的「農民革命」或「階級革命」說)缺乏一貫性也缺乏系統性。羅爾綱比簡年輕一些,對太平天國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貢獻。他主張太平天國是一場「貧農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式的立場;整體來説,他還是採取正面的、屬於民族主義的態度來處理太平天國的歷史。總的來説,中共對太平天國的態度顯得較為正面。
我認爲國民黨的態度模稜兩可,主要就是因爲如果過分地强調民族革命的色彩,那就會很難客觀解釋曾國藩的角色。爲什麽這麽説呢?這是因爲蔣介石要利用曾國藩的思想來充實中國民族思想的内容。蔣介石認爲曾國藩的「名教」思想比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信仰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於是國民黨的太平天國歷史變成了曾國藩(和湘軍)平定動亂,保護中國歷史文化的鬥爭。尤有進者,國民黨在台灣更需要用曾國藩的思想來提倡中國人的傳統價值,因此不能過分提倡太平天國批判或反對中國文化的主張。
西方人對太平天國史的興趣則主要是在於洪秀全和洪仁玕的基督教信仰;即使到今天,也還有很多西方學者逃不離從宗教的本質來探討太平天國的束縛。2007年出版的《 太平天國:叛亂與對皇朝的褻瀆 》(Thomas H. Reill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也還對於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如何受到《希伯來聖經》(通常稱爲《舊約聖經》)「十誡」影響的研究,而2016年出版的《太平天國的神學,基督教在中國的地方化》(Carl S. Kilcourse: Taiping Theology: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843-64)更直接討論基督教思想的中國化問題。在他們看來,太平天國的政治乃至於神學思想基本上還是能從基督教的觀點處理。不過,總體來説,自從施友忠和簡又文的書相繼出版之後,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對太平天國的寫作從此可以擷取前此比較少人看到的中文資料,開拓了新頁。史景遷於1996年出版的《太平天國》) 可以説是一錘定音之作。它的重要性除了有系統地使用不少英國國會圖書館的外交檔案之外,更成功地對太平天國史做出全面性的解釋。
史景遷的中心課題就是想要瞭解洪秀全爲什麽會變成這麽一個動亂的領袖:他的思想、他的歷史背景,還有他令人着迷的毅力。史景遷指出這些東西不幸卻加增了中國的混亂和明顯的沉淪 ,而西方人因爲宗教緣故,不知不覺地捲進了這個他們完全不瞭解的紛爭。難怪史景遷會把英國最受尊敬的外交官額爾欽説成「不對的人」。西方的宗教和東方人對太平天國的錯誤──或至少是誇張的──瞭解,也造成了一種不可原諒的歷史錯誤。
史景遷文采出色,因此能用詩意的文字化解一般歷史敘述的乏味,使得太平天國的研究在西方又產生新一輪的興趣。施益堅所推崇的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就是一個例子。他寫的《天國之秋》(The Autumn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2012)將太平天國所帶來的動亂和影響寫得非常徹底,可算是一種新的「戰史」。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有了比較持平或寬容的認可,甚至於認爲西方記者把太平天國的基督教過分渲染醜化,致使洪仁玕近代化的憧憬沒有實現的機會。之所以如此,有兩點:一個是西方記者集中在上海,聼到的主要來自官方説法,因此產生「太平軍是一群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野蠻人」想法。其次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基督教還是保持排斥非信徒的傳統,只要有絲毫與正統教義偏離的想法就被視爲異端。在裴士锋看來,這兩者都造成後人對太平天國極大的誤會。
施益堅對基督教的立場是開放的,他認同英國傳教士會的説法,主張拜上帝會的教義不外是所謂的「亞流派」(Arianism)的想法。因此他和裴士鋒一樣,明顯對太平天國的宗教觀有相當的同情,這就好像近年來西方基督教會不再隨便指摘在中國產生的靈恩教會是異端一樣,兩人對於過往基督教會鄙視太平天國的態度並不認同。更進一步來説,施益堅也不認爲西方人對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有真正的興趣。他們不支持洪秀全,一言以蔽之,就是經濟的利害關係。施益堅在小説中借用額爾金的話說出英國攻打北京,並放棄支持太平天國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貿易的考慮。額爾金作爲英國的貴族,擔負重要的外交任務(他的弟弟當時也帶兵在北京),他的考量當然是英國國家的長遠利益。
在施益堅的眼光中,額爾金伯爵雖然對中國文化缺乏認識,但卻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英國紳士(雖然系出蘇格蘭)。施益堅把他描寫成一個懷疑亞羅號船上並沒有真的懸掛英國國旗,並且為英國出兵感到羞恥的人。他也不再提額爾金縱容士兵進入圓明園搶劫的這個説法。最後這點現今一般認爲是法國官方的決定。有的史家更根據王闓運、李慈銘的記載,指出其實中國人比法國人還早進去破壞,因爲咸豐皇帝逃亡之後,守衛人員散逃,於是附近的窮旗人就進去擄掠。法國軍隊還是在獲得長官許可後才跟隨進去,已經比難民晚了一步。無論如何,法國人放火,畢竟不是光彩的事。施益堅也提到,即便西方人也對法國軍隊的行爲做出激烈的批判。
施益堅技巧地引述了額爾金的父親在希臘的醜事來襯托圓明園的破壞。額爾金的父親就是早年把雅典衆神廟的大理石浮雕拆下並運回英國的人。這些大理石雕刻品占有大英博物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參觀的人絕對不會錯過它們,但也是現代英國人感到心理上非常矛盾或曖昧的「收藏」而希臘政府積極追討希望可以要回去的寶藏。所以拜倫對他父親的指責自然地在額爾金心中不斷地激引他作爲一個文明人的深沉反思,在夢中迴響。當他想起雨果的指摘,内心不禁有萬分複雜或羞慚的思緒。
施益堅在書中幾度透過反省的語氣來探討十九世紀的「進步」觀念。本來小説裡面並不適合討論這類思想的問題,但是額爾金不是一般人,他生活的世界不是世俗賺錢糊口的世界,他要的是文化藝術的熏陶,嚮往的是一種克服或超越物質的境界。在他看來,這才是所謂的進步。所以他會説出這樣的話:「不要將進步理解成軍事力量的增加。當一個國家能不再只是斤斤計較物質的條件時,國家才會强大」。用黑格爾的話來説,中國缺乏那種追求心靈自由的「精神理念」。
一、香港
上海,1860年夏天
那時我是幸福之人,有一個心愛的女人,雙手仍健全。這是我到了上海之後,有了很多時間思考才意識到的。六月即將過去,我躺在屋子裡,屋頂的橫梁在炎熱下呻吟。附近的港口傳來人聲嘈雜,很多人想在叛軍攻來之前離開上海。聽人說,船家一張船票要到十銀元,而且只是把人送到河對岸,接下來的毫無保證,得自求多福。越來越多難民如巨浪般從長江流域洶湧而至,戰爭驅使他們不得不往前。如果路途上我沒有遭遇到這場災禍,不得不臥床九個月,我早就到達長江下游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了。非也?也許我會遇到更大的災難,使我不只犧牲左手?
幸好我慣用右手。除了間隔時間的發燒,我無事可做。收留我的詹金斯牧師和他的妻子瑪莉安(Mary Ann)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人,他們在房間裡放了幾張紙,說是要給我寫信用。可是我能寫給誰?
偶爾我會和伊莉莎白說話,但是也只有在夜裡,當我失眠,記憶取代了夢境的時候。我回憶從我的旅程開始以來發生的一切。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條界線,守住了才不致變成另一個人。而在差點喪命的那一天之前,我早已經越過那條界線還渾然不知。在國內革命失敗之後,我原本打算到美國展開新的生活,但是事與願違,新的生活——現在我不再確定它是否存在。我們踏上追尋的道路,卻不知它通往何處。我路經鹿特丹和新加坡來到香港,在香港有段短暫的時間我很快樂,之後我漸漸深入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在鄱陽湖上遇到一個槍法比我快狠的盜賊,任阿隆佐.波特(Alonzo Potter)也救不了我的手。現在我失去了一切,沒有什麼好後悔的,但下一步該如何走我也不知道。
只有一隻手,還能協助推翻滿清皇帝嗎?
沒有人知道叛軍何時而且會以多強大兵力抵達上海。直到幾個星期之前他們還被困在南京,而現在他們的軍隊已經遍佈長江流域,造成各大城市的恐慌。就如那時拿破崙派遣到義大利的軍隊,他們總是從敵人的腹背襲擊,河流和山川也擋不住進攻。根據《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報導,太平軍已經佔領了蘇州,我也親眼看到杭州上方的煙柱。那是從南方來的貧窮農民和燒炭工人所發動的叛亂,他們相信追隨的是上帝的兒子,他們稱的天王正是我最要好朋友的族兄。那封邀請我到南京的信我藏在長袍的口袋裡,雖然浸了水破爛不堪,但是上面的印仍然可辨。唯一的問題是以我這樣四肢不全的身軀是否還有勇氣上路,穿過威脅全中國的巨流洪水逆流而上。
我叫菲利普.約翰.紐坎普(Philipp Johann Neukamp)。布蘭登堡地區一個木匠家的長子。可是自從一年前離開巴塞爾崇真會(Basler Missionsgesellschaft)之後,成了無業遊民。那之後發生的事我從未告訴任何人,為了清楚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必須稍作補充。1848年發生的事件我假設眾所週知:我在當中扮演的角色雖然無足輕重,但是事後我還是不得不遠走他鄉避避風頭。我原本打算在荷蘭籌足錢便搭船前往全世界唯一不是由貴族而是由自由人士統治的國家。靠雙手賺錢我一點也不陌生。在穀倉、人滿為患的宿舍裡過夜,甚至露宿我都不在意。我有兩個天賦,在我人生中讓我獲益匪淺,尤其是到了中國之後:我的外語天才以及健壯的體格。在鹿特丹港口我不怕沒有苦工可做,才幾個月之後我的荷蘭語已經足以讓我找到更好的活兒。Jong & Söhne是一家專門裝潢船隻內部的工廠,他們雇用了我。可是我想遠渡重洋到美國所須要的費用仍然是遙不可及的目標。然後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只一句話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這或許是我第三個天賦,在對的時間點遇到對的人。我在德國學徒漫遊時期,遇到羅伯特.布魯姆,雖然我只上了六年的學,他帶著我參加了席勒之友的聚會。布魯姆讓我可以坐在萊比錫劇院的最高層樓座觀看《唐.卡洛斯》(Don Carlos)。之後他對我說了一句話,那是我之前只隱約感覺得到,但是不甚了了的真相:君主制是對人民的大逆(Monarchie ist Hochverrat am Volk)。至今如果可以我仍舊恨不得前往維也納,手刃溫迪斯格雷茨(Windisch-Grätz)那老傢伙,一刀刺進他枯萎的心臟。但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總之我在鹿特丹遇到了郭士立(卡爾.郭士立)。
那是1849年底,一個溫和多雨的冬天。去上工的途中,我看到一張演說的佈告,一個德國傳教士要報告他在中國的經歷,下工之後我實在沒什麼事好做。當時郭士立正在歐洲各地奔走演講為他的福漢會(Chinesischen Verein)籌集資金,他所到之處,演講廳裡總是擠滿人。在鹿特丹的聖勞倫斯大教堂也不例外。他做中國漁夫的打扮,敘述舊約裡的一個先知,而且是用德語和荷蘭語,夾雜許多陌生的字眼,我聽得心醉神迷。他說到土地貧窮和腐敗的朝廷官員,那些人很像我所知道的警察和檢查員,他還說到父母強迫自己的孩子上街乞討以免餓死,然而路有餓死骨仍然常發生。他的演說聽眾總是聽得入神,演說完之後人人虔誠地爭相把錢投入捐獻箱。那感覺就像幾年前唐.卡洛斯一樣。我沒有錢,於是我問演說的人,除了捐錢我還能做些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腦子裡在想什麼。郭士立心裡早有主意。「你的身體夠健康強壯?」他一邊打量我,一邊問。
我毫不遲疑地點頭。
「信仰虔誠?」
我點頭。
「到中國來,」他說。「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他留了一道很寬的八字鬍,面帶迷人的微笑。他的建議實在瘋狂,讓我不由得再一次點頭。
福漢會不屬於任何教會,這正合我意。它的資金是靠捐款,要不就是郭士立本人,要不就是他走訪過的城市之後幾乎都會成立的支援會。他描述困境與安慰、同情與希望的精彩絕倫演說無人能比。他所到之處,聽他演說的聽眾立刻看到一個等待救贖而且救贖正接近的世界。後來將伊莉莎白送到香港的柏林在華婦女傳道會(Berliner Frauen-Missionsverein)也是要歸功郭士立。同樣的荷蘭弟兄傳道會也是多虧了他,我是以聲明儘快出發前往遠東為目標加入的第十五個成員。在這之前我在鹿特丹也參加了一個郭士立年輕時參加過的學院。他的美言加上一份修潤過的履歷,他們讓我加入了,費用由福漢會負擔。學歷不足不是問題,在傳道會的圈子他們並不重視是否上過大學,我的同學中有幾人不只正確拼寫拉丁文連拼寫自己的母語都備感吃力。接下來幾個月我沒有學到關於中國的任何事物,甚至連語言課都沒有,課程只包括聖經研究、講道及基督教歷史。起初我感覺自己像寄生蟲,幾乎像騙子。我是傳教士?那些教師很嚴格,但是在信仰問題上態度開明,只強調與令人厭惡的「教皇至上論」(Papismus)劃清界線。隨著時間推移,事情越來越合我意。學校宿舍裡乾淨的床單,是我在家時從來沒有過的。偶爾我接到父母親來信,他們欣喜逆子終於走回正路。而我告訴自己,萬不得已我也可以從中國到美國去,當福漢會通知我渡海的旅費已經籌齊,那感覺就像1848年春天那段神奇的日子。巴黎來的消息讓我們相信世界將永遠改變。
其實我不習慣洩露太多自己的事。我從阿隆佐.波特那裡學到一個男人歷練越多越該沈默。每天早上詹金斯牧師出門之後,房子裡就會變得很安靜。這房子是一長排相似房舍中的一棟,多節彎曲的懸鈴木、桑樹還有修剪過的籬笆包圍著院子。據說上海英國人的社區就像聖約翰伍德區(St. John’s Wood),那應該是倫敦的郊區,我沒去過倫敦。在我的家鄉,房屋鱗次櫛比,金匠、桶匠和木匠的工坊上面有低矮的房間。火始終是可怕的威脅,但是要是能免受祝融之災,就很可能終老在出生的屋子裡(萬一發生火災,那當然更不用說了)。要不是童年的一個事件,讓我從此產生了一個信念:我的人生注定要奉獻給偉大的事業,也許我永遠也不會離開家鄉。十歲的時候我得了麻疹,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早晨我醒來,世界一片黑暗,秋天已經來了,我聽到屋子裡的腳步聲,我揉揉眼睛。我妹妹走到床邊問我,身體是不是好了。我要她打開百葉窗,她回答我窗戶是開著的。我再次揉了揉而且眨了眨眼睛。我可以感覺到露易絲就在身邊,而且聞到她剛喝了熱牛奶的氣味。甚至可以感覺到她的眼光正對著我的臉,可是我什麼也看不見,就連閃爍的光點也看不到。一片漆黑。
這兒是你的牛奶,她對我說。
我是從耶穌讓一個失明的人重見光明的故事上知道「失明」這個詞的。除此之外地方上有一個老人,他需要老婆牽著才能走出門。但是失明的小孩子我從來沒有聽過。第三天大夫來看我,他說他沒辦法解釋,但是他已經看過兩次這樣的事,兩次都是得了麻疹的男孩。他建議用醋熱敷眼睛,完全的休息,眼睛有可能就會恢復了。阿諾德(Arnold)牧師也來看我而且他似乎有他的解釋,他低聲向我父母說明。他要我躺在床上,雙手緊握放在被子上然後祈禱。他的語氣明明就是在說,我該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任。整個冬天我躺在床上,雙手冰涼,每天數小時的祈禱,心中藏著難以形容的恐懼。為了避免任何人打擾我,他們把我的床搬到洗衣間旁邊的房間。只有給我送吃的東西時,我的弟妹才允許進來。有時候我白天睡著,晚上醒來聽見的只有屋子裡的寂靜。因為臥床太久,聖誕節的時候我父母帶著我進教堂,我竟然在教堂昏倒了。那之後對我的管制才逐步放寬。治療其實沒有任何效果,醫生也已經束手無策。當雪開始融化時,我父親決定是該接受無可避免的現實的時候了,而且至少將能做的做到最好。在工坊裡有些活他閉著眼睛都能做,瞎子為什麼不行?差不多這個時期我也停止了禱告。我把所有記得的罪過都已經吿解完,但是並沒發現有哪一個罪過需要受這樣的懲罰。我對弟妹偶爾粗魯,在學校有時成績太差,有一次從廚房儲藏室偷了一塊蛋糕。我的朋友在外面嬉戲玩耍的時候,為什麼我卻眼睛瞎了躺在床上?
最後一次禱告我祈求:讓我重見光明,那麼我才會繼續禱告。
我向來就有叛逆的傾向。作為家中的長子,我應該做弟妹的榜樣,可是我不適合這樣的角色。但我是個好學生,所以校長還說過我也許可以去上波茨坦的師範學院,如今我錯過了那麼多課,而且反抗的傾向越來越強烈。我父親餐桌禱告時我鬆開雙手,我母親讀聖經給我聽時,我全力以赴想其他的事。在工坊裡我學會用觸摸來區分木材的種類以及使用簡單的工具。但是如果有人捉弄我,我便會憤怒發狂,此時需要兩個成年男人才能制服我。彷彿是周圍的黑暗讓我內在的黑暗面顯露出來。地方上不少人認為我著了魔。
後來就在復活節來臨前,我突然感覺自己看到了一片亮光,而且就在工坊窗戶的位置。我眼睛閉上,亮光就消失,而當我看著另一堵牆壁,什麼也看不到。接下來幾天那感覺越來越清晰,對比也越來越明顯。我害怕這一切是錯覺的恐懼和當初失明的惶恐一樣強烈,但那不是錯覺。世界慢慢從黑暗中浮現,到了復活節——確確實實是復活節那天——世界恢復原來的樣子,如同充滿形狀和色彩的大海。如今我還在夢想有一天早上醒來雙手俱全。然而即使這樣的喜悅能成真,也比不上童年那時曾滿足我的歡喜。當時我張開手臂在野地上奔跑。整個地方都在談論這件事。有人還在我面前伸出手指問我有幾根。後來阿諾德牧師在傳道時也提到我,說那是五旬節的奇蹟。
一切似乎恢復平常,然而其實沒那麼簡單。內心的不安困住我,我同時感覺目空一切但又焦慮,腦子有怪誕的想法而且被惡夢折磨,夢中世界突然變黑暗。我坐不住,想奔跑。有時在奔跑中我閉上眼睛,然後跌倒,但是內心感到不可思議的輕鬆。我在學校的學習成績越來越差,再也沒有人建議我以後可以從事教師的工作,這正合我意。我不相信所有要我服從的人,包括老師還有聲稱上帝會寬恕我的牧師。祂玩弄了我,不是嗎?我離開學校回到父親的工坊,但是不久我就感到受限制。
當學徒的第三年,我決定啟程開始我木匠的學徒漫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