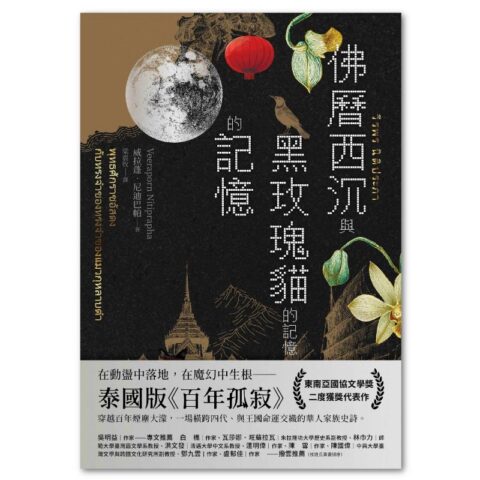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
原書名:自然主義文学盛衰史
出版日期:2019-06-28
作者:正宗白鳥
譯者:王憶雲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長14.8×寬21×高1.75c
EAN:9789570853377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尚有庫存
與其說在一般人世見識人生,我毋寧是在文壇觀看人生。
正宗白鳥的《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是回想,是自敘傳,是日本文壇史,同時也是文學史。
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社會氣象一新,文學界也在自然主義文學的興盛下燦爛萬千,誕生了許多關鍵、風格嶄新的經典之作。正宗白鳥與島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人,便是此一時期引領風騷,種下未來日本文學新傳統種籽的代表性文學家。
正宗白鳥之名也許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較為陌生,但其作家、評論家的雙重身分,在日本文學的脈絡中不僅是橫跨時代的代表,更是反映文壇趨勢的一面鏡子。他的小說以瀰漫著無力、虛無感著稱,同時孜孜不倦、持續地撰寫大量評論,其論述眼光精準、筆筆鞭辟、褒貶並陳,觀察角度無私得近乎冷酷,透過他之筆呈現出的日本文學面貌,更為寫實、立體,是為閱讀、品評日本文學作品的重要指標之一。
《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是由正宗白鳥近70歲時開始連載的10回專欄文章集結而成,圍繞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關鍵作家與作品為主,時間橫跨明治、大正、昭和年代,近60年時光,不啻是日本文學斷代生成史,記載了作者與當時諸多作家的往來,對各種作品的發想、討論與評價,除了自然主義作家與作品外,他也廣泛論及夏目漱石、森鷗外等同一時代的作家及其著作,是一本個人回憶錄、一本文壇史,更是極具研究價值的文學史。
作者:正宗白鳥
本名正宗忠夫。早稻田大學文學科畢業後,曾任讀賣新聞記者,1910年辭職,成為專業作家。其風格獨特,在日本的評論、戲劇界佔有一席之地,擁有高度評價。同時他也曾任日本筆會會長、藝術學院會員,並獲頒文化勳章。
譯者:王憶雲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專業領域為日本近代文學。曾任曾任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兼任講師、台北市立成功高中兼任教師。譯作:《領導者必先知道的事:松下幸之助給你的95則成功啟示》、《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小泉八雲怪談》、《不為人知的日本面容》、《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日本瞥見記:異文化的觀察與愛戀》等書。
導讀 日本自然主義與作家正宗白鳥 王憶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附錄
一、近代文學作家索引‧簡介
二、正宗白鳥年表
三、重要研究及資料
導讀/《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一書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天皇以玉音承認戰敗後告終,日本被美軍占領,民主主義的思想再次取得正統地位,而對「過去的」近代文學深刻反省,也成為文壇的主流趨勢。
身為文壇耆老,白鳥選擇在1948年3月開始於雜誌《風雪》連載〈自然主義盛衰史〉,一共連載十回。同年11月由六興出版社將連載內容集結成冊出版。1951年由創元文庫出版的新版,在書名中加進了「文學」兩字,改為「自然主義文學盛衰史」。本譯注所使用的本文,選擇以福武書店版《正宗白鳥全集》收錄的為主,是再次修訂創元文庫版後的本文。附帶一提,講談社文藝文庫版的本書,則是目前日本一般讀者最方便購入、閱讀的文本。此次經由科技部計畫將這本書譯為中文,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得以接觸到較為陌生的這個層面,譯者最後將書名定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以強調這是一本關於日本獨特的自然主義的文學史。以下本書簡稱為《興衰史》。
有關《興衰史》的內容,我們可以引用當年連載雜誌《風雪》4月號〈編輯雜筆〉裡的具體說明:「這是以泡鳴、花袋、秋聲、藤村等作家編織而成的親身回顧,亦是橫跨明治、大正、昭和的日本文學生成歷史,重要的文獻。」在一般文學史教材之中,日本的自然主義是個在日俄戰爭結束後興起,到了明治末年便已衰退的思潮,前後算起來不過五、六年光陰,但是這些被歸類為自然主義的作家,並未因為思潮有了新的轉向便從文壇銷聲匿跡,他們各自有著自己的作家人生,並且各自在大正、昭和時期交出了成熟的作品,這些累積讓白鳥的《興衰史》一書敘述得以橫跨近六十年時光:由坪內逍遙與二葉亭四迷的登場開始,一直到昭和時期島崎藤村開始寫《東方之門》(1942-1943,未完),德田秋聲書寫《縮圖》(1941開始連載,1946集結為單行本,未完),這些自然主義作家一個又一個離開人世為止。
換句話說,白鳥身為最長壽的自然主義作家,回顧起自己進入文壇以來的一切。他看到的不光是自然主義,在《興衰史》中登場的當然有島崎藤村、田山花袋、岩野泡鳴、德田秋聲等自然主義作家,同時亦論及夏目漱石、森鷗外,甚至是菊池寬等身處同一個時代的作家活動。讓我引用學者佐佐木徹關於本書的精要解說如下:
《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是回想,同時也是自敘傳;是自敘傳,同時也是文壇史;是文壇史,同時也是研究性的文學史,還多少有著讓作品成為可讀之物的些許苦心。因此,這本書得以是自然主義文學研究上(包含白鳥研究),不可缺少的參考文獻。而且,白鳥的書寫並未固執於身為自然主義作家的次元,所以並未偏袒自然主義。
談及日本戰後的文藝評論家,最廣為人知,現今依然擁有眾多讀者,首推小林秀雄吧!在日本文學史上,他被視為讓評論得以離開小說、詩作,成為一種獨立文類的關鍵人物。小林秀雄生涯最後的作品,是在雜誌《文學界》連載的〈關於正宗白鳥的作品〉,始於1981年1月,但小林秀雄卻在連載中去世,無法完成。小林秀雄在這篇作品中提及,正宗白鳥晚年作品有著強烈吸引他的力量,讓他所獲甚多,其中戰後的代表作,毫無疑問的是《興衰史》,白鳥的文章「達到了驚人的純度」,並展現了他那「依循現實且天才般的眼光」。儘管白鳥肩負著自然主義作家之名,卻依然保有著他那撰寫評論一貫的態度,凝視現實,這是本書受到諸多正面評價的重要原因。
而不管是在《興衰史》,或是白鳥的其他評論中,我們會發現一個相當顯著,卻又困擾著讀者的特徵。那就是白鳥面對他的論述對象,時常晃動自己的準星,讓人無法嘗到一槍斃命的快感。高橋英夫便說:「經常才剛覺得他在讚揚對方,卻馬上就變成冷漠的口吻,開始說這無聊、乏味,這點也讓人無法掌握白鳥真正的意思。」正是如此。
於是我們會在《興衰史》中,看到白鳥毫不避諱地說著那些日本自然主義的「壞話」,卻又同時把看來正面的意義攤在讀者眼前。
日本自然主義作家與作品是特別的群體,在世界文學史中無法找到類似的例子,這一派的作品靠著稚拙的技巧、雜亂的文筆描寫平凡人的困難與苦悶,而且,不試著引起讀者興趣,是特色之一。
如何內省自己生存之苦,又該如何呈現出來,這些問題在自然主義者之間沉重地飄盪。名為「私小說」的自我告白作品,時至今日仍未在文壇絕跡,但現在的,比起當時,態度上可是悠然自得。當時的作者,對於他人閱讀自己的作品,多少抱持著羞愧之情。
夏目漱石的《吾輩是貓》這篇異色之作於《杜鵑》連載,成為世人談論的話題時,自然主義尚未萌芽。當他接連不斷地發表《倫敦塔》、《少爺》、《草枕》等等風格多樣的作品,名聲響徹文壇內外,此時,另一群人開始鼓吹自然主義,席捲文壇。站在自然主義文學的立場而言,漱石文學可以說是敵人之一。自然主義思想興起於必然,共鳴者亦絡繹不絕,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此派作家鮮少秀逸之作,小說的銷路無人可及漱石。當然,有部分的原因是作品品質不佳,稍嫌無趣等等,另一方面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人與官學出身、曾任帝大講師的漱石不同,他們既無官學的學歷,也並非官學的教授或講師,自然在讀者之間的評判落於下風。現在回想起來有些愚蠢,但直到明治末期為止,世人對官學與私學價值輕重的觀感無可動搖,漱石與森鷗外的作品不管如何,總因作者之名而得到重視。
從作風來說,漱石的作品與自然主義有著無法相容之處,田山花袋、岩野泡鳴等人屢屢批判漱石,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的自然主義追隨者都討厭漱石。長谷川天溪強調暴露現實所生的悲哀以及人生幻滅,但他也喜歡《少爺》,曾經寫下善意之評;我們也對《草枕》一書愛不釋手。話說如果我的記憶無誤,島崎藤村從未對漱石有所評論,我也未曾從藤村口中聽到有關漱石的是非之評。此乃藤村之所以為藤村之處,我覺得非常有趣。《破戒》甫問世不久,在上野精養軒有場聚會,漱石與藤村均到場參加,漱石喜歡《破戒》一書,便拜託同樣出席的某人,「幫我跟藤村介紹一下」,那人便詢問藤村,據說藤村堅辭。耳聞此事,我試著去想像藤村的內心,端看解釋之法,這種作家的心理實在相當耐人尋味。
究竟是誰先開始這麼說的呢,我的記憶並不清晰,說是漱石文學乃低徊意趣的產物,是一種文字遊戲,這話成為自然派的意見,一種定論,就連鷗外的文學,也被說是遊戲文學。坪內逍遙創設文藝協會,在大久保余丁町的自宅設立演劇研究所時,試演場正面的匾額上便寫著「遊於藝」三個大字,據說臨摹自弘法大師的筆跡,逍遙想必認為遊於藝是戲劇的本質,也是正確的藝術觀吧。然而,花袋、泡鳴、藤村等人卻不喜歡「低徊意趣」、「遊於藝」等字眼。花袋在書寫時,嘴巴總掛著水火之苦,把生存的苦惱比喻成溺水、火炙之苦,甚至還說是「扒皮」,意指在創作過程中,感受到的是自己扒下自己皮膚的痛苦。想當然耳,藝術不是種遊戲。泡鳴也頻頻述說苦痛的心理或苦悶的哲理。漱石在《後來的事》中寫道:「要是說起討厭什麼,他內心明白,沒有什麼比矯揉做作的眼淚、煩悶、真摯、熱誠等等更讓人厭惡。」諷刺當時的自然主義文學,不過,漱石的這種批判卻非確當之言。花袋撰寫《棉被》、《生》、《妻》時,又或是藤村書寫《家》、《新生》時,他們確實感受到漱石等人無法窺知的苦痛,泡鳴或近松秋江書寫自身經驗的時候,也感受到不為人知的苦痛。我與他們來往,所以非常清楚。從漱石或逍遙等人的藝術觀來看,這種苦痛或許是一種愚昧的苦痛。自己扒除自己的皮,亦是愚昧之舉。甘願躍進濁水之中泅泳,躍入火焰之中,實是無益。一般的文學家或許會說,就以《少爺》、《草枕》那樣的態度開拓自己的藝術世界不就好了嗎?
但是,他們這些自然主義作家,熬過苦痛進行創作,才交出了那些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或是世界文學史上,皆未有前例。暴露自己的醜態,認為這是文學的正道,這卻不是生性謹慎的鷗外、逍遙、漱石等人可以辦到的事情,甚至以旁觀者的身分看著他們,自然覺得像個蠢蛋。因為最為魯直才看來不像個蠢蛋的是藤村,他最深知創作之苦、水火之惱。《家》以及《新生》可以說是當時自然主義文學目標的苦痛結晶。創作之際的苦痛,古往今來眾多作家均有所體驗,像是紅葉等人,一字一句理應都經過削骨之痛,就連才氣縱橫的漱石,或許也為創作經歷了無法安眠之苦。然而,當時的自然主義者之中,卻存在著與共通感受相異的,一種特別的苦痛。如何內省自己生存之苦,又該如何呈現出來,這些問題在自然主義者之間沉重地飄盪。名為「私小說」的自我告白作品,時至今日仍未在文壇絕跡,但現在的,比起當時,態度上可是悠然自得。當時的作者,對於他人閱讀自己的作品,多少抱持著羞愧之情。
近松秋江說他自己並不是自然主義者,他的作品比起我稍遲才獲得認可,富含情意纏綿之趣是他的特色,批評家也就不把他視為自然主義一員,但此時回首觀之,我堅信他的作品,可以歸類為自然主義。在暴露自我的這一點上,他的作品堪稱鶴立雞群。《給離去妻子的信》是成名之作,在這之前,他在《早稻田文學》發表了短篇《餐後》,這篇可說是他的處女作,德田秋聲對我讚賞過這篇作品。小說中主角,也就是作者,一邊聽著同居女性談起過去與男性的回憶,另一方面卻描繪他不堪嫉妒的心境,而秋聲那陣子的作品之中剛好也描寫了類似的心理,我們對於描繪與自己相同經驗的作品共鳴、感到有趣,是種普遍的讀書心態。秋江很早就推崇秋聲的小說技巧,私下也進而深交,但因為他本姓「德田」,總被人誤會德田秋江是德田秋聲的親人或是門人,只好搬出自己過去崇拜不已的近松門左衛門,冠在自己雅號前頭。以上是我的推斷,但這推斷不會有錯。
儘管秋江聲明自己並非自然主義信徒,但卻與此派的主要人物交情深厚,樂於拜訪人的他,有著頻繁拜訪各方文壇人士的癖好,就連漱石府上也時常登門打擾。於是,他曾經在某篇文章寫道:「漱石家中,門生聚首談笑,和氣藹譪,而自然派的人們只要湊在一起,便要爭個面紅耳赤。」泡鳴讀到這段文字,大表不平,說:「漱石的朋友們把秋江當外來之客,自是客氣應對,怎會拿這種事來比較兩邊。」花袋的文章中曾經提到:「把〔齋藤〕綠雨身上的嘲諷拿掉,就是秋江。」不識綠雨的我,讀了這段也能想像綠雨的個性。綠雨經常拜訪他人,把東邊耳語送至西邊,又把西邊耳語傳至東邊,不免遭人厭惡,秋江也有相似之處。儘管我不善社交,但在橫跨半世紀的文壇生活中,不免與形形色色的人有所接觸,我最熟知的文壇人士,應當就是這位近松秋江。透過雙親、弟妹、妻以及幾位親戚,我好不容易才了解人為何物,若是要談及文壇知交,則是靠著秋江,我才了解人是什麼。學生時代的他,遭到同窗輕視,進入文壇後,為了生活資金掙扎,依然被雜誌編輯以及友人看輕,不當一回事。他熱切追求的那些女性也是,並不把他當一回事。在我的眼中,他那可悲的一輩子,扮演著沒有價值的生命,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你若仔細端詳,卻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打從學生時代直到後期,他一直有著夢想,儘管事與願違而心有煩憂,但卻能持續做夢,這可說是一件幸福的事。他那以「離去妻子」揭開序幕的數篇愛欲小說,不管是《疑惑》,或是《黑髮》,盡皆清楚地展現了他糾纏不清、優柔寡斷的本性。這糾纏不清、優柔寡斷之處,正是他作品的特色,但其實在藤村、花袋身上也能看到糾纏不清、優柔寡斷,並不稀罕,但卻只有秋江不像他人苦心思慮、運用理智,而是單純地暴露糾纏不清的事實,這點與藤村等人有所不同。我好幾次聽能言善道的他談起《疑惑》素材的現實故事,一開始覺得有趣,後來不免生厭,而且不光是我,連其他朋友也這麼說。藤村等人一定不會像秋江這樣,隨便抓個人,就把那樣見不得人的內心話掏出來。想想自己,假設我有了與秋江相同的經驗,必然不會像他那樣毫無保留地寫下來。因此,我懷疑藤村的《家》、《新生》是否隱藏著應寫而未寫之事。我記得藤村曾經針對泡鳴說過:「不管什麼事都赤裸裸地寫出,並不盡然是件好事。」秋江的書寫,定然並無保留,畢竟他所寫的,全是自己經歷的事實。如同藤村所言,赤裸裸地什麼都寫,並非優秀的小說作法,因此,拙劣的作家要是以這種方法寫,可能會交出不堪卒讀的作品,但就秋江的作品來說,他不客氣地信筆寫下事實,同時展現了抓住讀者內心的筆法。在一個個場景的描寫中,他同時把「我」這個角色的心理動搖細膩地描繪出來,在描寫娼妓或其他女性時,也比藤村、花袋等等不解風情的作家更加出色,比之於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正統的女性描寫,反倒在質樸的筆法中讓女性更加活靈活現。秋江經常舉出實例,談起秋聲描寫絕佳之處。
在這裡,我試著提出一個文學鑑賞的問題。認識作家的人物原型,是會讓閱讀更為豐富,或是反會阻礙正確的鑑賞呢?泡鳴作品中的女性,有兩三位我經常碰面,但我自己卻無法從她們身上感受到絲毫魅力。而且,在讀泡鳴作品時,對這些人物的認識,會讓他的作品像是散文,失去情調,大殺風景。就連秋江的「離去妻子」,亦是我熟識的人物,閱讀之中一邊想到當事人,一邊看著作品中細緻描述的人物行動、言語,的確有些樂趣,但在同時,他居然固執地對那樣的女子糾纏不清,讓我心生厭惡。不過,這文學鑑賞方式僅限於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