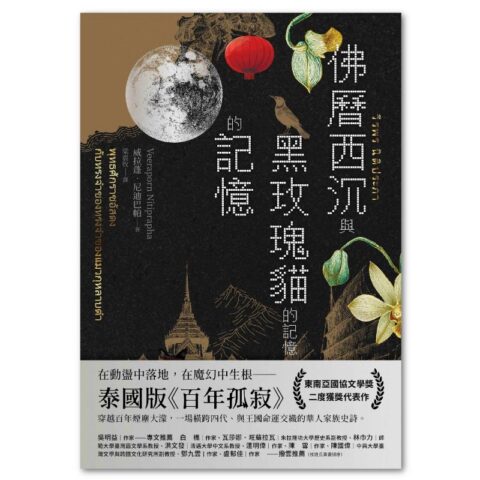最後一隻豬
原書名:Die letzte Sau
出版日期:2012-04-13
作者:帕提克‧霍夫曼
譯者:宋淑明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72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39784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對於豬腸子來說,香腸就是一場革命。
一部讓小說家、詩人、劇作家都驚奇的德國小村故事,聚餐之前,備「豬」就位!
甘耀明、陳思宏、鴻鴻、魏松(台北歌德學院主任)聯名推薦
這是一場豬的盛宴與道別,然而在大快朵頤之前,每個人都五味雜陳!
東德萊比錫附近的村落慕卡,遷村過程的百般滋味,都在殺豬道別的當下湧現……帕提克‧霍夫曼用輕鬆幽默的鋪排方式帶出一家人的悲喜、歷經兩德統一變遷的時代縮影。
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東德的遷村計畫就陸續開始進行,在原東德這個生產煤礦的村莊,還有最後一個家族也即將要搬離了,三代人聚在一起,該如何面對過去、現在並討論未來!面對兩德統一、環境大變化,未來的新旅程要如何展開?每個人隱藏心中的祕密都在這殺豬道別的一天,娓娓道來……
小說設定的時間是1992年十二月五日,週六,在萊比錫南方的一個村子慕卡。這裡的露天褐煤的開採始終沒有停止過,雖然褐煤工業的末日近在眼前,葉輪機仍然運轉如昔,挖土機一步一步逼近。一年前,東德的村民就已經開始慢慢遷離,史萊格一家是最後留下的家族,眼看也即將與自己熟悉的家園與村莊揮別。在這樣團聚的一天,他們打算屠宰亞伯雷希特豢養的最後一隻豬,一場家族聚會就要開場了!一大清早,請來的居然是一位女屠夫,打算把他們留下的最後一隻豬也給處理了……香氣四溢以前,這一天會怎樣度過呢?
最後的一隻豬遭逢的命運也呼應著時代變遷,牠一塊塊被卸下的肢體猶如一層層分崩離析的世界,也讓人們深刻反思過去與未來!一個(東德)社會從共產主義變成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不公平,也在其中顯現!
作者:帕提克‧霍夫曼
1971年生於德國東部波爾納,過去在東德取得高中文憑,卻在西德服兵役。他在大學主修哲學、德國語言暨文學,以及歷史,待過波昂、萊比錫、莫斯科以及史特拉斯堡等城市,博士學位研究胡塞爾理論。2002-2009年生活在雅典,任職於汽車出租分公司,並擔任過記者、司機、自由譯者與德語老師。2009年起生活在柏林,《最後一隻豬》是他首部出版的小說作品。
譯者:宋淑明
德國慕尼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曾任慕尼黑大學、柏林洪堡大學講師,兼任中山大學講師。著有《德奧,這玩藝!》戲劇篇,譯有《邊境行走》、《焚書之書》、《男人的玩具》、《女人的玩具》等。
2012年台灣中譯本留念/帕提克‧霍夫曼
德國和台灣中國文化因為豬隻而緊緊相連。不管是德國還是台灣,豬都代表好運和財富。雖然德國的豬仔文化還不到像在台灣中元普渡時那種神聖規模,但如同小說裡的描述,我們德國幾乎把全豬都做成各式不同的香腸,卻不認識來自福爾摩沙(Formosa)赫赫有名的(famos)的料理珍品(譯者:formosa與famos幾乎同音,意為「台灣」相等於「赫赫有名」):大腸包小腸。容我這麼說,也許是因為我的同胞不習慣意外的驚喜。
對豬仔的高度珍惜,基於萬物之靈的人類如同哼哼嚎叫的豬仔也是可以消化一切,再把所消化的轉形利用這樣的觀點。只有在藝術創作的領域─或者是哲學處理的問題,「無法消化的部分」才是重點。這就是小說中藉一個二十世紀大災難後東德一家所探索的主題。
書中被屠宰的豬隻重162.5公斤,在任何時候這個重量都幾乎不可能與台灣拜拜用的大豬公相提並論。但是我衷心希望,我們處理豬肉的技術、小說中人物的好胃口以及最後不能不提到的他們對香腸溫柔的對待,能夠給喜歡肥肉的祖師爺和台灣讀者一個補償。
2012年三月
陳思宏
東西德統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長久以來,我們聽到了許多來自西德的統一闡述,《最後一隻豬》終於給了我們來自東邊的聲音。作者勾勒出一幅德東的平凡農家畫,時值1992年冬天,兩德剛統一不久,女屠夫宰了農莊裡的最後一隻豬,這殺豬的儀式把全家都聚在一起。
豬殺了,統一了,歷史蝗蟲過境之後,這個煤礦小鎮破敗蕭條,一家人三代同堂,一起站在極易碎的時間點上,不知如何走向未來。書裡充滿最尋常的家庭對話,跳接、離題、爭吵、揭瘡疤,讀者在細碎的對話裡,逐步發現每個角色的秘密,所有關於秘密警察、戰爭、共產、性向的家庭祕辛,全都一一抖出。
這是本需要耐心閱讀的小說,敘述跳接,閱讀的鏡頭不斷地在農家各個角落晃動、在過去與現代當中切換。一旦進入了本書文字的韻律,就會聞到殺豬的腥味,在製作血腸、處理豬內臟器官之間,讀者跟著這家人經歷了悲喜的一天。這一天,是兩德統一之後,平凡的農家週末。但這一天也是個歷史切片,作者脫離了歷史大敘述的視角,聚焦土地與小人物,審視東西德統一。《最後一隻豬》是個悲喜寓言,血淋淋的殺豬細節,隱喻時代的殘酷與慈悲,映照德國近代的動盪,是一本充滿聲響、氣味、顏色的小說。
甘耀明
這是《動物農莊》的德國「進階版」寫實小說,加入更多的人間荒謬屠宰場、政治狂想曲、黑色煤礦幽默劇,一隻豬的命運竟然這麼多戲,太有意思了
陳思宏
《最後一隻豬》是個悲喜寓言,血淋淋的殺豬細節,隱喻時代的殘酷與慈悲,映照德國近代的動盪,是一本充滿聲響、氣味、顏色的小說。
陳思宏
《最後一隻豬》是個悲喜寓言,血淋淋的殺豬細節,隱喻時代的殘酷與慈悲,映照德國近代的動盪,是一本充滿聲響、氣味、顏色的小說。
魏松(Markus Wernhard),台北歌德學院主任
德國曾經與今迥異:帕崔克‧霍夫曼所著的小說《最後一隻豬》,場景設在一個東德荒潰中的村子,描述方式與當代同步,且觀察敏銳。讀者在閱讀的同時,可以藉由這一個告別自己家鄉村落的家庭的故事,認識這段罕被提起的德國近代史。
「該死的!」鶴妲忽然大叫。「亞信,去看看鍋爐。」
莎賓娜正一隻一隻地玩著手指,沒有注意到媽媽受苦的眼睛。「我在烏茲堡念了兩年大學。法律。」她坐在陌生女人的背後,觀察她褐色的髮辮、小小的耳朵以及,跟眼神比較起來柔和許多的側面。「大學裡的人都對我們東德人有偏見,他們以為我們不是軍人,就是頂尖的運動員。」
「兩個星期內我們必須搬離這裡。」鶴妲轉向女屠夫。「我們是最後一批還沒有搬到新社區的人。我們的房子裡,就是我們的雙拼組屋,去年秋天有一半都在淹水。冬天的時候,地下室的水管還爆了。這樣怎麼能住人,完全不行啊!不過現在已經修好了,而且我們也不能再繼續在這裡住下去。這裡不屬於我們,而且,現在我一個人也做不了這裡的工作了。」
好像這一切都還不夠麻煩似的─要不是那個女人在場,安娜格蕾特開始大叫─莎賓娜還把食指中間的骨節越過大拇指搬到一旁。
安娜格蕾特在桌下偷偷瞄一眼手上的錶。她覺得,她父親把夾著血腸捏在一起的麵包浸在咖啡中的時間太長了。當他把頭擺在咖啡上方,將麵包從杯中提出時,濕掉的麵包跟母體分離掉落,消失在咖啡裡。當他撮著唇吸吮乾麵包中濕潤的部分時,她嘴角不自覺往下牽動。咖啡表面浮著一層油暈。她很高興母親沒有開始叱責父親。
「當我發現,我在西德能夠做出事業的時候,便去了柏林。」莎賓娜的呼吸讓陌生女人背上的汗毛豎直。女屠夫的手安靜地放在桌上。一百七十五公分高,六十公斤重,莎賓娜猜想。她很想抱住這個女人的臂膀,拉扯一下,希望能得到她的注意力,撫摸一下莎賓娜。
亞伯雷希特躬身向前。「這是第三次投資失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帝國的貨幣就已經不太值錢了。但是二三年的時候幣值不僅跌到谷底,這個谷還是一個深淵。成年禮時我得到的禮物是一只錶,它停了,我帶到萊比錫去給錶匠修理,那時候一塊奶油要價足足十萬第三帝國幣。」
「那修錶呢?」沃夫岡問。
「過了一個禮拜我該去取錶時,一塊奶油已經漲到一百萬了。我只好把錶留在那裏。之後貨幣改成黃金馬克,大家又能東山再起。我當學徒的第一年,一個星期有兩馬克三十五芬尼的收入。我父親開始做生意,先是賣馬鈴薯,然後也賣蔬菜,生意非常好。一九二八年他買了這座農莊和田地,我們有一輛卡車、兩匹馬,還雇用了兩個女人。一九三五年我得到一部英國勝利牌摩托車,750cc,四零年打仗時被徵收了。二次大戰之後,幾乎什麼都不剩,接著四八年的時候我們的錢變成東德馬克。」
「賺東德馬克沒有人富得起來。」沃夫岡說。
「那時買賣是犯法的。」安娜格蕾特大聲說。
「他可是用他的財產資助了兩次世界大戰。」雷奈尊敬的說。即使是跟祖父,說話用第三人稱也令他有點尷尬。但是他不想有例外。
「到最後,我們大家都得賤價賣煤。龜孫兒子還用馬克將我們的財產都減半,如果我們現在把農莊和田地出賣的話。」老人搥打自己的前額。
「烏布利希和何內克追了四十年也沒趕上人家。」亞信手一揮。「他們把我們的國家治理得精疲力盡。」
「但是我以前賣給政府一隻肥豬,可以拿到一千馬克。現在呢?一個蘋果和一顆蛋!根本不必開始養豬。」老人反嘴。
「反正你一毛不拔,從來不花錢,有什麼好抱怨的?」沃夫岡譏刺地說。
「像你們這樣高的退休金我們這一輩人根本別想指望!」頌雅說。
「媽媽,搬進新家以後,妳一定要給我買新的被子。」安娜格蕾特插話進來。
「那舊的要怎麼辦?」
「我們醫院那邊有紅十字會捐衣箱。」卡特琳說。她偷偷的朝女屠夫那邊望:娜娜真是個馬屁精。等她穿上屠夫沾滿了血的圍裙站在那裡的時候,看她還有什麼好話說。
「以前要一一把羽毛與硬梗分開,那真不是容易的工作啊!」頌雅意味深長地說。
「現在沒人要做了。」安娜格蕾特說。
沃夫岡撞一下亞信:「星期二的事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鶴妲搖頭,「我們這邊這些東西要放到哪裡去?!」
「柏林?」亞信回問,「行政協議?」
沃夫岡點頭:「你知道那代表什麼嗎?」
「我們第一次這麼多人睡在同一個屋簷下。」卡特琳說。
「要慶祝的話,新房子裡也夠大。」頌雅回應。
亞信點頭:「露天廢礦、腐鏽的挖土機以及停產的煤磚工廠、低溫煉焦場,這些現在都是國家接手處理的工業廢料、遺留問題,包括翻新改造、環境保護。這樣一來,褐煤所有的問題就都解決了。」
這個對話引起頌雅的興趣:「我以為煤礦的事早就結束了,剩下的只是景觀設計師的工作。」
「這裡的景觀變化,」雷奈說,「比人的變化還快。」
亞信竊喜。之後幾年,他的工作無慮。
「協議訂定之後,產業私有化就不會再礙事了。我們又能用褐煤來賺錢。至於就業機會,當然條件會比較簡樸。抱怨、三心二意都無濟於事。只有現代科技才能拯救煤礦。」
看著一家人團團圍住那個女人坐著、說著,多麼幸福。頌雅希望時光能永遠停留在這一刻。
「我最小的孩子還在睡。」鶴妲說。「從她七歲得腦膜炎躺在醫院時,她就有精神病。像現在這種天氣,屋裡有這麼多人的時候,她能睡這麼久,我很高興。」
「你們有另外多買了什麼嗎?豬舌?豬肝?」女屠夫詢問道。頌雅否認。「重要的是,有足夠的洋蔥。」女屠夫趕緊安撫她。
「比我們所需多得多。」亞伯雷希特保證。
「冷藏庫裡準備了足夠的空間?」
「新房裡,」鶴妲回答,「我一定要買一個冷藏櫃。」
「肉品檢驗員連絡了?」
「七點半會過來。」
荻安娜坎帕剌德先對鶴妲點個頭,再對亞伯雷希特點個頭示意,然後起身。在這個共同的動作後,接著將會是椅子往後推、你先我後的擾攘,當大家圍著自己的手肘團團轉時,只有雷奈看見那個陌生女人如何不經意的碰觸莎賓娜的腰,看她一眼,馬上又轉身搭上亞信的肩膀。莎賓娜像化石一般站在那裏,似乎被電擊。女屠夫的眼睛沒有去看雷奈。
安娜格蕾特邊罵邊擠到擋了大家的路的女兒身邊。鶴妲繞過桌子,看到莎賓娜三角褲上一截裸露的臀肉,伸手把她的T恤往下扯,試圖將T恤塞進褲子裡。她身體一擺,掙脫了母親,溜進洗手間,後背抵住門,大大地吸一口氣。就是那個地方。在女屠夫的拇指下,她幾乎融化了,性亢奮讓她幾乎噴尿。綠色的眼睛。穿著橡膠鞋的荻安娜。
「開始囉,開始囉!」雷奈跟著大家走出去。
他們把女屠夫的掛車推進院子,來到洗衣房前。女屠夫發下指令:桌腳、兩個皮做的袋子、砍柴用的大木塊、瓦斯瓶、燃燒器、絞肉機、灌腸器、掛車推到這邊、搬到那邊,這樣那樣。當她把木板墊固定在桌上時,她猛力搖晃一下桌子,看墊板是不是牢固,然後在附兩個木鈎的墊板上掛上刀具。「梯子,支架?」
亞信看著亞伯雷希特。後者蹙眉:「支架在木框架房屋裡。梯子?啊,你,去打穀場那邊看有沒有。」雷奈拔腿起跑,抱來一把破爛不堪的梯子。「傻孩子,不是這一把。」祖父驚怕的說。「這把梯子是用來撐住雜物間的牆壁,讓牆壁互相靠著不會倒。曬穀場上不是還有另一把嗎?」
雷奈搬來了對的那把梯子。女屠夫點點頭,拿出四個拔除豬鬃的鈴狀器具置放桌上,其中兩個頂端有鈎子,然後圍上僵直的、曾經一度是白色的圍裙。「我需要幾個湯碗、一個搪瓷做的水桶、幾支攪蛋器還有一個大桶子,用來裝豬血。」鶴妲指指四周,告訴她一切早已備齊。「現在開始好好的用木柴生一個火。最好在爐上燒沸一大鍋水。你們都已經有經驗了?」頌雅和卡特琳點點頭。
「如果豬沒有腸子的話,」沃夫岡對她眨眨眼,「我們應該能夠自己動手。」
「腸子確實很不好處理,需要極度的耐心,才能將腸內的滯留物洗滌乾淨。沃夫岡,當豬側躺在地上時,請你抓緊牠的後腿。誰來接血?」
「我可以。」雷奈的眼神像在徵求許可。
「你拿著湯碗來接。頌雅要是攪累了,卡特琳,妳接著攪。」
「豬圈裡只剩一隻豬。」亞伯雷希特喉頭一緊。他忽然覺得他很需要拐杖來支撐自己,但是拐杖在廚房裡,他忘了拿出來。誰都沒有看一眼,他走出洗衣房。頌雅和卡特琳交換一眼抑鬱的眼光。
女屠夫拿起一道繩索,檢查了螺栓槍(譯者:屠宰時用以擊暈牲畜的工具),拔出兩把吸鐵石上的刀,腰間圍上刀套,襯衫袖子捲至二頭肌處。莎賓娜鼻翼擴張,呼吸加速。女屠夫身後,沃夫岡、頌雅、亞信和卡特琳走進院子。
(樂譜)難道我,必須去,去獸欄,去獸欄,而你,心愛的,留在這裡。
雷奈將樂句吹進心迷意亂的表姊耳裡。
「你白癡哦!」莎賓娜噓他。
「看到她,」他碰碰她放在唇中間的食指,「就是貓王艾維斯也很難以自己。」然後從門縫間溜了出去。
荻安娜坎帕剌德打開豬圈的門,找到燈的開關,開了燈,在身後再關上門。幾道厚重、骯髒不堪的牆以大約肩膀的高度將豬圈分成四個欄位。右邊前面的畜欄裡,豬隻舒服的躺在新鮮的乾草上。這是一隻高貴的德國種豬,標緻的耳朵是豎立的,兩耳間的距離讓女屠夫立即能判斷皮膚下應有早熟、肥厚的油膘。鐵條蓋住一半的石溝槽的角落裡還有飼料,因為那裡豬鼻子夠不到。她打開鐵打的柵欄,進入豬圈裡。豬仔吃力地站起來。她猜測豬的重量是三又四分之一公擔(譯者:德國重量單位:一公擔 = 五十公斤)。就在這一瞬間,她已將繩索套上豬的左後腿。豬隻聞嗅著她的圍裙,嗷嗷鼾叫。又大又髒的一大團灰色摩擦著女屠夫的腿。
沃夫岡、亞信和雷奈站在堆肥和房子前緣之間窄窄的空間裡,他們身後是頌雅和卡特琳。
「她根本在裡面裝了子彈。」雷奈下巴指向置放窗台上的螺栓槍。
「她難道要瞄準牠的腦袋。」
亞信不耐地瞪著豬圈的門,「怎麼可能!」
「蹦一聲,」沃夫岡說,「一顆螺絲釘跳出來,撞擊豬的腦袋。」
亞信眉毛向鼻溝的方向倒垂。
「然後呢?」雷奈問。
「豬就腦震盪昏倒了。有時候因為慣性定律豬還能再走兩步才倒下。」
「那牠是被麻醉,不是已經死了?」
「動物保護協會是這麼規定的。」沃夫岡點點頭。
「不是啦,是希特勒規定的。」雷奈的臉發光。「他當上總理後的第一個生日就規定沒有麻醉就屠宰牲口是犯法的。」
「希特勒不是吃素嗎?」卡特琳問。
「不是,他是奧地利人。」頌雅說,她只聽到這段對話最後一句的一半。
「這樣猶太人就沒有符合猶太教潔淨意義的動物好殺了。」雷奈解釋道。
沃夫岡推一下他的外甥:「如果你念經給牲口聽,那牠在被殺前也已經差不多昏迷了。」亞信的眼神又更陰鬱了。
「真慘。」雷奈倒抽一口氣。
「有時候槍出錯,或者牲口的頭特別硬,應聲不但沒有倒,還好端端的站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那屠夫就尷尬了。他得再射一次。」沃夫岡吐出一口痰,落在他的腳前。
亞信嫌惡地看著他,他的表情似乎在問你一定要這樣嗎?「我剛才真該開一瓶啤酒。」他的嘴躲在鬍子後蠕蠕動著。
豬圈的門開了。豬仔哼哼哼搖搖擺擺的走出來,牠的一生中這是第二次走在院子裡的鋪石路面上。跟在豬隻後面的,是手上握著繩子的女屠夫。
剛好在莎賓娜終於撞開卡住的門出來時,撞擊聲響起。她直直地瞪著院子:豬爆炸了!所有的人圍成一個半圓。什麼,這是什麼把戲,什麼魔法?四隻腳伸得直直的,好像每條腿底下都有一個看不見的火箭噴射系統,豬隻在女屠夫肚子前面飛起來,牠既不反抗,不四肢亂蹬,也不作困獸之鬥來抵抗牠體內為什麼會爆炸的這個事實。驚惶、直挺挺的脖子、做出滑稽古怪動作的力量都已經不屬於這隻豬。這一擊將牠的肌肉、筋腱瞬間一網打盡。而肌肉、筋腱的第一反應都朝同一個方向凍結,豬沉默地飛離地面─莎賓娜感覺彷彿她的眼光能夠讓豬隻停留在空中似的。
然後,女屠夫往後退一步,豬從空中掉下來,好像動畫電影中的畫面。似乎自然定律猶豫了一個霎那,才將地心引力又重新啟動。豬隻斜斜地、啪掉在鋪石路面上,側身躺著,嘴巴微微張著,一動都不動了。
站在門口的莎賓娜不知道整個過程到底經過多久。與豬仔一起經歷最後一口氣的驚嚇,哽在她的喉嚨中久久無法下嚥。她急急把下巴往上推,緊緊閉上嘴,舌頭抵住門牙:用鼻子呼吸似乎比較沒有流淚的危險,她覺得。她瞪著女屠夫,女屠夫毫無表情的臉上所有的光芒陰森森地消逝。莎賓娜嚥了一口口水。
女屠夫一隻腿跪在豬身上。胸骨上方離開胸骨兩指寬之處,她揮刀斜斜向後刺進去,豬頸脖上主動脈分枝之前就把它切開:「碗!」雷奈將湯碗的邊緣緊緊貼在豬身上。女屠夫把完全沒入的刀刃往上推。血從細細的刀縫中噴射出來,在空中畫個拋物線,落點剛好在容器裡,雷奈的臉上也遭了一些魚池之殃。慢慢地她把刀抽出來,讓血規律地從豬身上湧出。湯碗裝滿了後,她用三隻手指擰住傷口,止住血流。雷奈將血倒入水桶中。頌雅開始攪拌。碗摩擦了一下地磚,還它沒重新靠上豬脖子以前,女屠夫已經將開口處放開。當血漸漸變少,她抓住豬的前腿開始轉圈。「熱水好了嗎?」
「馬上就要燒開了。」莎賓娜說。卡特琳換手攪拌。因為攪拌的緣故,泡漸漸沫多起來。傷口中現在流出的是一條涓汨的細流,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結塊。女屠夫揮動豬的前腿,將最後一滴血液從豬隻體內壓擠出來。然後她放下豬軟綿綿的前腿,站起身。
雷奈觀察這隻獸。牠凝重地躺在院子裡,身上沒有一絲生氣,只剩下原料和加工。他摘下金邊眼鏡,將鏡片上的汙跡刮乾淨:「有這種眼鏡的話,希姆萊(譯者:Himmler,納粹德國一名重要政治人物,曾為內政部長、黨衛隊首領,對屠殺猶太人、同性戀者、共產黨人和羅姆人以及許多武裝黨衛隊的戰爭罪行有主要責任)會很驕傲(譯者:因為他的特徵是金邊圓框眼鏡)。」
「梯子、支架拿來!」女屠夫下令。
「『而將這件事堅持到底,端正不移,令我們更堅強壯大,這是從沒有被提出、從不需被提出的光榮史頁。』(譯者:希姆萊著名演說)」他重新戴上眼鏡。「『總之我們可以說:我們胸中秉懷對民族的大愛來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我們的內心、我們的靈魂以及我們的性格都不會因此受害。』」
「該死的!」鶴妲忽然大叫。「亞信,去看看鍋爐。」
莎賓娜正一隻一隻地玩著手指,沒有注意到媽媽受苦的眼睛。「我在烏茲堡念了兩年大學。法律。」她坐在陌生女人的背後,觀察她褐色的髮辮、小小的耳朵以及,跟眼神比較起來柔和許多的側面。「大學裡的人都對我們東德人有偏見,他們以為我們不是軍人,就是頂尖的運動員。」
「兩個星期內我們必須搬離這裡。」鶴妲轉向女屠夫。「我們是最後一批還沒有搬到新社區的人。我們的房子裡,就是我們的雙拼組屋,去年秋天有一半都在淹水。冬天的時候,地下室的水管還爆了。這樣怎麼能住人,完全不行啊!不過現在已經修好了,而且我們也不能再繼續在這裡住下去。這裡不屬於我們,而且,現在我一個人也做不了這裡的工作了。」
好像這一切都還不夠麻煩似的─要不是那個女人在場,安娜格蕾特開始大叫─莎賓娜還把食指中間的骨節越過大拇指搬到一旁。
安娜格蕾特在桌下偷偷瞄一眼手上的錶。她覺得,她父親把夾著血腸捏在一起的麵包浸在咖啡中的時間太長了。當他把頭擺在咖啡上方,將麵包從杯中提出時,濕掉的麵包跟母體分離掉落,消失在咖啡裡。當他撮著唇吸吮乾麵包中濕潤的部分時,她嘴角不自覺往下牽動。咖啡表面浮著一層油暈。她很高興母親沒有開始叱責父親。
「當我發現,我在西德能夠做出事業的時候,便去了柏林。」莎賓娜的呼吸讓陌生女人背上的汗毛豎直。女屠夫的手安靜地放在桌上。一百七十五公分高,六十公斤重,莎賓娜猜想。她很想抱住這個女人的臂膀,拉扯一下,希望能得到她的注意力,撫摸一下莎賓娜。
亞伯雷希特躬身向前。「這是第三次投資失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帝國的貨幣就已經不太值錢了。但是二三年的時候幣值不僅跌到谷底,這個谷還是一個深淵。成年禮時我得到的禮物是一只錶,它停了,我帶到萊比錫去給錶匠修理,那時候一塊奶油要價足足十萬第三帝國幣。」
「那修錶呢?」沃夫岡問。
「過了一個禮拜我該去取錶時,一塊奶油已經漲到一百萬了。我只好把錶留在那裏。之後貨幣改成黃金馬克,大家又能東山再起。我當學徒的第一年,一個星期有兩馬克三十五芬尼的收入。我父親開始做生意,先是賣馬鈴薯,然後也賣蔬菜,生意非常好。一九二八年他買了這座農莊和田地,我們有一輛卡車、兩匹馬,還雇用了兩個女人。一九三五年我得到一部英國勝利牌摩托車,750cc,四零年打仗時被徵收了。二次大戰之後,幾乎什麼都不剩,接著四八年的時候我們的錢變成東德馬克。」
「賺東德馬克沒有人富得起來。」沃夫岡說。
「那時買賣是犯法的。」安娜格蕾特大聲說。
「他可是用他的財產資助了兩次世界大戰。」雷奈尊敬的說。即使是跟祖父,說話用第三人稱也令他有點尷尬。但是他不想有例外。
「到最後,我們大家都得賤價賣煤。龜孫兒子還用馬克將我們的財產都減半,如果我們現在把農莊和田地出賣的話。」老人搥打自己的前額。
「烏布利希和何內克追了四十年也沒趕上人家。」亞信手一揮。「他們把我們的國家治理得精疲力盡。」
「但是我以前賣給政府一隻肥豬,可以拿到一千馬克。現在呢?一個蘋果和一顆蛋!根本不必開始養豬。」老人反嘴。
「反正你一毛不拔,從來不花錢,有什麼好抱怨的?」沃夫岡譏刺地說。
「像你們這樣高的退休金我們這一輩人根本別想指望!」頌雅說。
「媽媽,搬進新家以後,妳一定要給我買新的被子。」安娜格蕾特插話進來。
「那舊的要怎麼辦?」
「我們醫院那邊有紅十字會捐衣箱。」卡特琳說。她偷偷的朝女屠夫那邊望:娜娜真是個馬屁精。等她穿上屠夫沾滿了血的圍裙站在那裡的時候,看她還有什麼好話說。
「以前要一一把羽毛與硬梗分開,那真不是容易的工作啊!」頌雅意味深長地說。
「現在沒人要做了。」安娜格蕾特說。
沃夫岡撞一下亞信:「星期二的事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鶴妲搖頭,「我們這邊這些東西要放到哪裡去?!」
「柏林?」亞信回問,「行政協議?」
沃夫岡點頭:「你知道那代表什麼嗎?」
「我們第一次這麼多人睡在同一個屋簷下。」卡特琳說。
「要慶祝的話,新房子裡也夠大。」頌雅回應。
亞信點頭:「露天廢礦、腐鏽的挖土機以及停產的煤磚工廠、低溫煉焦場,這些現在都是國家接手處理的工業廢料、遺留問題,包括翻新改造、環境保護。這樣一來,褐煤所有的問題就都解決了。」
這個對話引起頌雅的興趣:「我以為煤礦的事早就結束了,剩下的只是景觀設計師的工作。」
「這裡的景觀變化,」雷奈說,「比人的變化還快。」
亞信竊喜。之後幾年,他的工作無慮。
「協議訂定之後,產業私有化就不會再礙事了。我們又能用褐煤來賺錢。至於就業機會,當然條件會比較簡樸。抱怨、三心二意都無濟於事。只有現代科技才能拯救煤礦。」
看著一家人團團圍住那個女人坐著、說著,多麼幸福。頌雅希望時光能永遠停留在這一刻。
「我最小的孩子還在睡。」鶴妲說。「從她七歲得腦膜炎躺在醫院時,她就有精神病。像現在這種天氣,屋裡有這麼多人的時候,她能睡這麼久,我很高興。」
「你們有另外多買了什麼嗎?豬舌?豬肝?」女屠夫詢問道。頌雅否認。「重要的是,有足夠的洋蔥。」女屠夫趕緊安撫她。
「比我們所需多得多。」亞伯雷希特保證。
「冷藏庫裡準備了足夠的空間?」
「新房裡,」鶴妲回答,「我一定要買一個冷藏櫃。」
「肉品檢驗員連絡了?」
「七點半會過來。」
荻安娜坎帕剌德先對鶴妲點個頭,再對亞伯雷希特點個頭示意,然後起身。在這個共同的動作後,接著將會是椅子往後推、你先我後的擾攘,當大家圍著自己的手肘團團轉時,只有雷奈看見那個陌生女人如何不經意的碰觸莎賓娜的腰,看她一眼,馬上又轉身搭上亞信的肩膀。莎賓娜像化石一般站在那裏,似乎被電擊。女屠夫的眼睛沒有去看雷奈。
安娜格蕾特邊罵邊擠到擋了大家的路的女兒身邊。鶴妲繞過桌子,看到莎賓娜三角褲上一截裸露的臀肉,伸手把她的T恤往下扯,試圖將T恤塞進褲子裡。她身體一擺,掙脫了母親,溜進洗手間,後背抵住門,大大地吸一口氣。就是那個地方。在女屠夫的拇指下,她幾乎融化了,性亢奮讓她幾乎噴尿。綠色的眼睛。穿著橡膠鞋的荻安娜。
「開始囉,開始囉!」雷奈跟著大家走出去。
他們把女屠夫的掛車推進院子,來到洗衣房前。女屠夫發下指令:桌腳、兩個皮做的袋子、砍柴用的大木塊、瓦斯瓶、燃燒器、絞肉機、灌腸器、掛車推到這邊、搬到那邊,這樣那樣。當她把木板墊固定在桌上時,她猛力搖晃一下桌子,看墊板是不是牢固,然後在附兩個木鈎的墊板上掛上刀具。「梯子,支架?」
亞信看著亞伯雷希特。後者蹙眉:「支架在木框架房屋裡。梯子?啊,你,去打穀場那邊看有沒有。」雷奈拔腿起跑,抱來一把破爛不堪的梯子。「傻孩子,不是這一把。」祖父驚怕的說。「這把梯子是用來撐住雜物間的牆壁,讓牆壁互相靠著不會倒。曬穀場上不是還有另一把嗎?」
雷奈搬來了對的那把梯子。女屠夫點點頭,拿出四個拔除豬鬃的鈴狀器具置放桌上,其中兩個頂端有鈎子,然後圍上僵直的、曾經一度是白色的圍裙。「我需要幾個湯碗、一個搪瓷做的水桶、幾支攪蛋器還有一個大桶子,用來裝豬血。」鶴妲指指四周,告訴她一切早已備齊。「現在開始好好的用木柴生一個火。最好在爐上燒沸一大鍋水。你們都已經有經驗了?」頌雅和卡特琳點點頭。
「如果豬沒有腸子的話,」沃夫岡對她眨眨眼,「我們應該能夠自己動手。」
「腸子確實很不好處理,需要極度的耐心,才能將腸內的滯留物洗滌乾淨。沃夫岡,當豬側躺在地上時,請你抓緊牠的後腿。誰來接血?」
「我可以。」雷奈的眼神像在徵求許可。
「你拿著湯碗來接。頌雅要是攪累了,卡特琳,妳接著攪。」
「豬圈裡只剩一隻豬。」亞伯雷希特喉頭一緊。他忽然覺得他很需要拐杖來支撐自己,但是拐杖在廚房裡,他忘了拿出來。誰都沒有看一眼,他走出洗衣房。頌雅和卡特琳交換一眼抑鬱的眼光。
女屠夫拿起一道繩索,檢查了螺栓槍(譯者:屠宰時用以擊暈牲畜的工具),拔出兩把吸鐵石上的刀,腰間圍上刀套,襯衫袖子捲至二頭肌處。莎賓娜鼻翼擴張,呼吸加速。女屠夫身後,沃夫岡、頌雅、亞信和卡特琳走進院子。
(樂譜)難道我,必須去,去獸欄,去獸欄,而你,心愛的,留在這裡。
雷奈將樂句吹進心迷意亂的表姊耳裡。
「你白癡哦!」莎賓娜噓他。
「看到她,」他碰碰她放在唇中間的食指,「就是貓王艾維斯也很難以自己。」然後從門縫間溜了出去。
荻安娜坎帕剌德打開豬圈的門,找到燈的開關,開了燈,在身後再關上門。幾道厚重、骯髒不堪的牆以大約肩膀的高度將豬圈分成四個欄位。右邊前面的畜欄裡,豬隻舒服的躺在新鮮的乾草上。這是一隻高貴的德國種豬,標緻的耳朵是豎立的,兩耳間的距離讓女屠夫立即能判斷皮膚下應有早熟、肥厚的油膘。鐵條蓋住一半的石溝槽的角落裡還有飼料,因為那裡豬鼻子夠不到。她打開鐵打的柵欄,進入豬圈裡。豬仔吃力地站起來。她猜測豬的重量是三又四分之一公擔(譯者:德國重量單位:一公擔 = 五十公斤)。就在這一瞬間,她已將繩索套上豬的左後腿。豬隻聞嗅著她的圍裙,嗷嗷鼾叫。又大又髒的一大團灰色摩擦著女屠夫的腿。
沃夫岡、亞信和雷奈站在堆肥和房子前緣之間窄窄的空間裡,他們身後是頌雅和卡特琳。
「她根本在裡面裝了子彈。」雷奈下巴指向置放窗台上的螺栓槍。
「她難道要瞄準牠的腦袋。」
亞信不耐地瞪著豬圈的門,「怎麼可能!」
「蹦一聲,」沃夫岡說,「一顆螺絲釘跳出來,撞擊豬的腦袋。」
亞信眉毛向鼻溝的方向倒垂。
「然後呢?」雷奈問。
「豬就腦震盪昏倒了。有時候因為慣性定律豬還能再走兩步才倒下。」
「那牠是被麻醉,不是已經死了?」
「動物保護協會是這麼規定的。」沃夫岡點點頭。
「不是啦,是希特勒規定的。」雷奈的臉發光。「他當上總理後的第一個生日就規定沒有麻醉就屠宰牲口是犯法的。」
「希特勒不是吃素嗎?」卡特琳問。
「不是,他是奧地利人。」頌雅說,她只聽到這段對話最後一句的一半。
「這樣猶太人就沒有符合猶太教潔淨意義的動物好殺了。」雷奈解釋道。
沃夫岡推一下他的外甥:「如果你念經給牲口聽,那牠在被殺前也已經差不多昏迷了。」亞信的眼神又更陰鬱了。
「真慘。」雷奈倒抽一口氣。
「有時候槍出錯,或者牲口的頭特別硬,應聲不但沒有倒,還好端端的站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那屠夫就尷尬了。他得再射一次。」沃夫岡吐出一口痰,落在他的腳前。
亞信嫌惡地看著他,他的表情似乎在問你一定要這樣嗎?「我剛才真該開一瓶啤酒。」他的嘴躲在鬍子後蠕蠕動著。
豬圈的門開了。豬仔哼哼哼搖搖擺擺的走出來,牠的一生中這是第二次走在院子裡的鋪石路面上。跟在豬隻後面的,是手上握著繩子的女屠夫。
剛好在莎賓娜終於撞開卡住的門出來時,撞擊聲響起。她直直地瞪著院子:豬爆炸了!所有的人圍成一個半圓。什麼,這是什麼把戲,什麼魔法?四隻腳伸得直直的,好像每條腿底下都有一個看不見的火箭噴射系統,豬隻在女屠夫肚子前面飛起來,牠既不反抗,不四肢亂蹬,也不作困獸之鬥來抵抗牠體內為什麼會爆炸的這個事實。驚惶、直挺挺的脖子、做出滑稽古怪動作的力量都已經不屬於這隻豬。這一擊將牠的肌肉、筋腱瞬間一網打盡。而肌肉、筋腱的第一反應都朝同一個方向凍結,豬沉默地飛離地面─莎賓娜感覺彷彿她的眼光能夠讓豬隻停留在空中似的。
然後,女屠夫往後退一步,豬從空中掉下來,好像動畫電影中的畫面。似乎自然定律猶豫了一個霎那,才將地心引力又重新啟動。豬隻斜斜地、啪掉在鋪石路面上,側身躺著,嘴巴微微張著,一動都不動了。
站在門口的莎賓娜不知道整個過程到底經過多久。與豬仔一起經歷最後一口氣的驚嚇,哽在她的喉嚨中久久無法下嚥。她急急把下巴往上推,緊緊閉上嘴,舌頭抵住門牙:用鼻子呼吸似乎比較沒有流淚的危險,她覺得。她瞪著女屠夫,女屠夫毫無表情的臉上所有的光芒陰森森地消逝。莎賓娜嚥了一口口水。
女屠夫一隻腿跪在豬身上。胸骨上方離開胸骨兩指寬之處,她揮刀斜斜向後刺進去,豬頸脖上主動脈分枝之前就把它切開:「碗!」雷奈將湯碗的邊緣緊緊貼在豬身上。女屠夫把完全沒入的刀刃往上推。血從細細的刀縫中噴射出來,在空中畫個拋物線,落點剛好在容器裡,雷奈的臉上也遭了一些魚池之殃。慢慢地她把刀抽出來,讓血規律地從豬身上湧出。湯碗裝滿了後,她用三隻手指擰住傷口,止住血流。雷奈將血倒入水桶中。頌雅開始攪拌。碗摩擦了一下地磚,還它沒重新靠上豬脖子以前,女屠夫已經將開口處放開。當血漸漸變少,她抓住豬的前腿開始轉圈。「熱水好了嗎?」
「馬上就要燒開了。」莎賓娜說。卡特琳換手攪拌。因為攪拌的緣故,泡漸漸沫多起來。傷口中現在流出的是一條涓汨的細流,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結塊。女屠夫揮動豬的前腿,將最後一滴血液從豬隻體內壓擠出來。然後她放下豬軟綿綿的前腿,站起身。
雷奈觀察這隻獸。牠凝重地躺在院子裡,身上沒有一絲生氣,只剩下原料和加工。他摘下金邊眼鏡,將鏡片上的汙跡刮乾淨:「有這種眼鏡的話,希姆萊(譯者:Himmler,納粹德國一名重要政治人物,曾為內政部長、黨衛隊首領,對屠殺猶太人、同性戀者、共產黨人和羅姆人以及許多武裝黨衛隊的戰爭罪行有主要責任)會很驕傲(譯者:因為他的特徵是金邊圓框眼鏡)。」
「梯子、支架拿來!」女屠夫下令。
「『而將這件事堅持到底,端正不移,令我們更堅強壯大,這是從沒有被提出、從不需被提出的光榮史頁。』(譯者:希姆萊著名演說)」他重新戴上眼鏡。「『總之我們可以說:我們胸中秉懷對民族的大愛來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我們的內心、我們的靈魂以及我們的性格都不會因此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