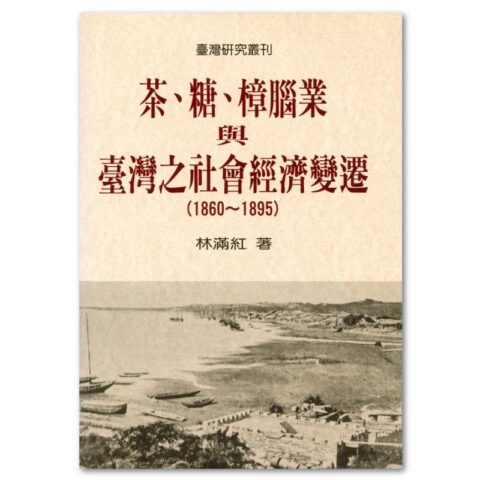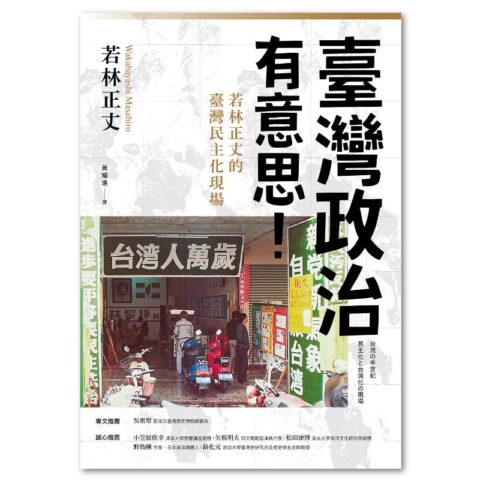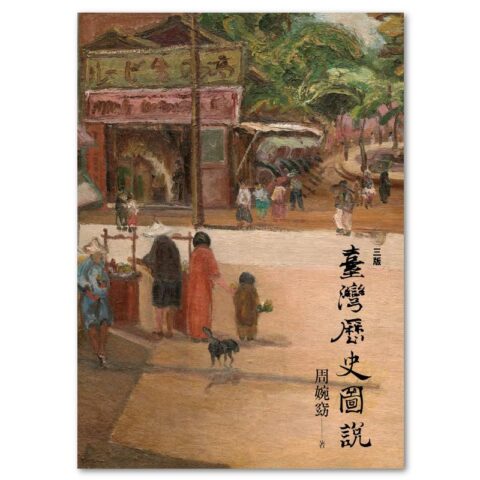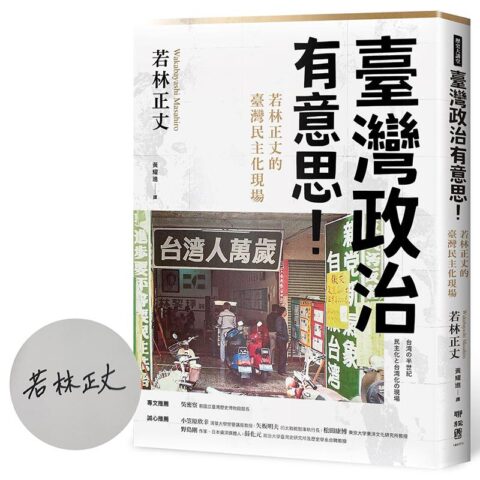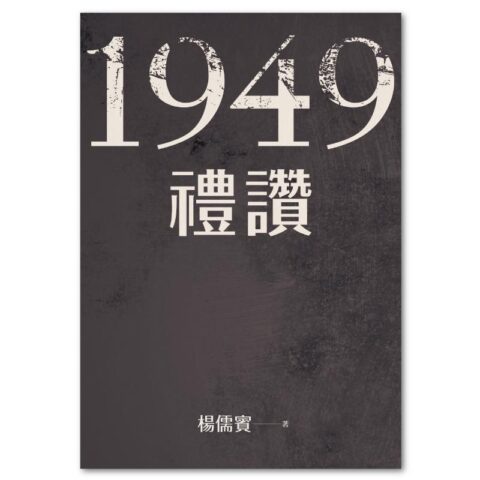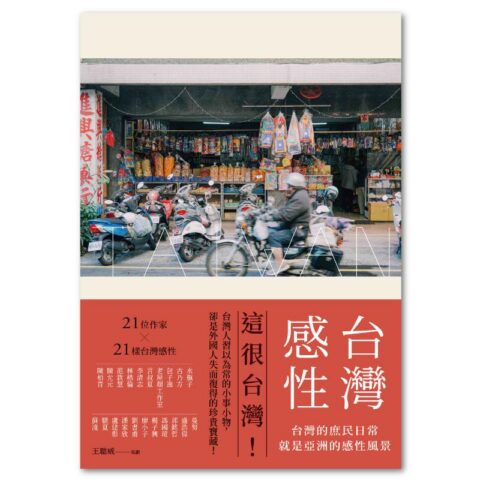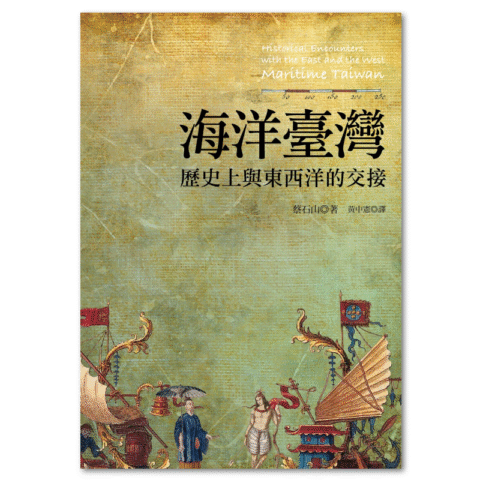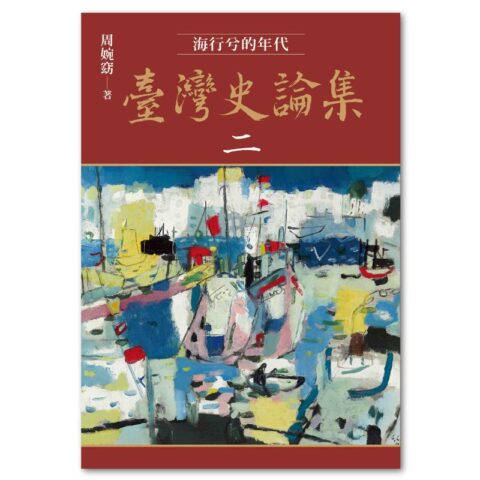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思想7)
出版日期:2007-11-22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2150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先生解除了實施39年的戒嚴令。當時之所以解嚴,主因應是外在的,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及蘇聯先後「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冷戰體制鬆動;但也有內在的原因,包括新生力量的挑戰與國民黨統治意志的衰退。至今20年過去,比起1990年的學運、或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解嚴對於台灣的意義,似乎聞問者較少。確實,由於解嚴乃是統治者的決策,與此前或者後來大規模民眾參與促成的運動性變化性質不同,在歷史上的位置也就不會一樣。但是,如果說解嚴代表整個社會逐漸回到常態的政治生活,那麼20年來的諸般現象,應該更能展示這個社會的根本性格所在。掌握這種性格,是我們要以解嚴為本期《思想》專輯主題的用意所在。 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四位,分別從社會運動、傳播媒體、民主與資本主義、以及人權法治幾方面,對解嚴之後台灣的得失成敗,提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評價。他們對解嚴寄以厚望、對解嚴之後的發展給予肯定、但同時也在社運政治化、媒體資本化、金權政治、以及弱勢人權幾方面,指出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難題。應當知道,如今這些問題已經無法歸咎於一個凌駕在上的威權體制,而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共同責任。 從較為寬廣的視野來看,解嚴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改變雖然可觀,可是其間的不變也需要面對。在我們所關切的思想、文化、學術領域,變與不變的對比,更值得玩味。解嚴以來,台灣的文化意識、價值意識、所處世界的意識,都呈現了多少的移轉,可是基本的軸線如今何在,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除了本期發表的四篇力作,本刊又在十月舉辦過「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陳芳明、唐諾、劉亮雅、張錦忠幾位共聚一堂切磋攻錯,其內容可望在下一期的《思想》發表。 至於文學之外,戒嚴與解嚴對於哲學、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又造成過甚麼影響呢?如果影響不大,那是因為台灣的戒嚴狀態原本即無傷於這些學門呢?是因為解嚴原本只有政治意義,並沒有改變社會結構與集體意識呢?還是因為台灣的思想文化學術與戒嚴體制原是同源,都是冷戰、反共、以及威權式現代化的產物,只要解嚴後的局面因襲著這些大環境因素,也就無礙於思想文化學術二十年來的新瓶舊酒相安無事? 在本期的眾多精彩文章之列,我們要請讀者特別注意劉世鼎先生關於澳門五一抗議遊行的討論。常有人說,要透視一個重大社會事件,需要兼顧「結構」與「形勢」兩方面的分析。在這方面,劉先生的大作堪為典範。這樣的觀察視野,同時呈現長期的趨勢與當下的動態,讀者自然會認識到事件的來龍去脈與過程的生動真實。本刊盼望繼續發表這樣的社會分析。 「思想筆談」則是本刊新闢的欄目,旨在促進中文知識界的對話與互動。本期針對自由主義當前處境的討論,即是由大陸、香港、台灣多位學者共同促成。在這個天涯比鄰的時代,類此的專題對話機會仍屬可欲不可求,我們很珍惜這樣的機緣,相信讀者也能領會其間的深意。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陳瑞麟:論「真」
萬毓澤:「當前的問題即歷史問題」:90年後回顧俄國十月革命
劉世鼎:澳門的新殖民主義:透視2007年五一大遊行
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
李丁讚:社運與民主
馮建三:台灣傳媒及其政策變遷20年:以中國為背景與想像
張鐵志:台灣新民主的詛咒?——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
廖元豪:法治尚稱及格、人權仍須努力:解嚴後的台灣憲政主義發展
思想筆談: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上
江宜樺: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
許紀霖:政治自由主義,還是整全性自由主義?——思考當代中國知識和文化領導權
高全喜:現代自由主義如何應對美德問題?——以麥金泰爾所謂「休謨的英國化顛覆」為例
應奇:擺盪於競爭與和解之間:當代自由主義之觀察
思想狀況
鄭鴻生: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
劉蘇里:知識人的眼界與立場
思想鉤沉
李有成:1902之霍布森
雲也退:桃莉絲‧萊辛:誤讀中煉製的火藥
新書序跋
單德興:越界的創新,創新的越界:《越界與創新》代序
思想采風
黃瑞祺:會見哈伯馬斯訪問紀要
陳瑋鴻:不讓眼淚模糊雙眼——猶太浩劫研究之父逝世
馬慶:泰勒新著:論世俗時代的信仰
致讀者
致讀者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先生解除了實施三十九年的戒嚴令。當時之所以解嚴,主因應是外在的,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及蘇聯先後「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冷戰體制鬆動;但也有內在的原因,包括新生力量的挑戰與國民黨統治意志的衰退。至今二十年過去,比起1990年的學運、或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解嚴對於台灣的意義,似乎聞問者較少。確實,由於解嚴乃是統治者的決策,與此前或者後來大規模民眾參與促成的運動性變化性質不同,在歷史上的位置也就不會一樣。但是,如果說解嚴代表整個社會逐漸回到常態的政治生活,那麼二十年來的諸般現象,應該更能展示這個社會的根本性格所在。掌握這種性格,是我們要以解嚴為本期《思想》專輯主題的用意所在。
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四位,分別從社會運動、傳播媒體、民主與資本主義、以及人權法治幾方面,對解嚴之後台灣的得失成敗,提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評價。他們對解嚴寄以厚望、對解嚴之後的發展給予肯定、但同時也在社運政治化、媒體資本化、金權政治、以及弱勢人權幾方面,指出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難題。應當知道,如今這些問題已經無法歸咎於一個凌駕在上的威權體制,而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共同責任。
從較為寬廣的視野來看,解嚴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改變雖然可觀,可是其間的不變也需要面對。在我們所關切的思想、文化、學術領域,變與不變的對比,更值得玩味。解嚴以來,台灣的文化意識、價值意識、所處世界的意識,都呈現了多少的移轉,可是基本的軸線如今何在,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除了本期發表的四篇力作,本刊又在十月舉辦過「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陳芳明、唐諾、劉亮雅、張錦忠幾位共聚一堂切磋攻錯,其內容可望在下一期的《思想》發表。
至於文學之外,戒嚴與解嚴對於哲學、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又造成過甚麼影響呢?如果影響不大,那是因為台灣的戒嚴狀態原本即無傷於這些學門呢?是因為解嚴原本只有政治意義,並沒有改變社會結構與集體意識呢?還是因為台灣的思想文化學術與戒嚴體制原是同源,都是冷戰、反共、以及威權式現代化的產物,只要解嚴後的局面因襲著這些大環境因素,也就無礙於思想文化學術二十年來的新瓶舊酒相安無事?
在本期的眾多精彩文章之列,我們要請讀者特別注意劉世鼎先生關於澳門五一抗議遊行的討論。常有人說,要透視一個重大社會事件,需要兼顧「結構」與「形勢」兩方面的分析。在這方面,劉先生的大作堪為典範。這樣的觀察視野,同時呈現長期的趨勢與當下的動態,讀者自然會認識到事件的來龍去脈與過程的生動真實。本刊盼望繼續發表這樣的社會分析。
「思想筆談」則是本刊新闢的欄目,旨在促進中文知識界的對話與互動。本期針對自由主義當前處境的討論,即是由大陸、香港、台灣多位學者共同促成。在這個天涯比鄰的時代,類此的專題對話機會仍屬可欲不可求,我們很珍惜這樣的機緣,相信讀者也能領會其間的深意。
台灣新民主的詛咒?: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
張鐵志
1.資本主義與民主的歷史性鬥爭
整整二十年前,台灣戒嚴的鐵幕被緩緩揭開,民主的黎明閃耀著。
這二十年,台灣也同時經歷了另一場大轉型:舊體制的資本主義模式開始朝向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市場開放──轉型。原來被國家控制的經濟活動和產業高地逐漸開放,加上資本和貿易的日益全球化,私人資本逐漸壯大。
資本主義與民主的歷史性鬥爭在這個島嶼激烈展開。
資本主義和民主是現代性的最主要制度。但對於兩者的關係,思想家們眾聲喧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擔心,以多數統治為原則的民主,會傷害做為資本主義根基的私有財產;今天的右派則認為兩者相互支持、互為條件 。左派則始終主張資本主義與真實的民主(而非形式民主)根本不相容。
的確,資本主義主義與民主有著根本性的矛盾: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平等主義,資本主義卻必然產生不平等。從人類歷史來看,這兩者實際上是彼此穿透、形塑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體制侷限了資本主義中市場或商品化的程度,例如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工人普選權,在歐洲推動了福利國家和混合經濟。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滲透進民主體制的規範性原則,例如民主體制所賦予的政治公民權原則,在實際上卻是有財富者永遠會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不論他們是否需要直接取得政治職位。
那麼,在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政治經濟大轉型中,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鬥爭鹿死誰手呢?或者,彼此如何改變了對方在台灣的實踐呢?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影響是社會科學的古典問題。但我們似乎只有各種關於資本主義發展是否會推動民主轉型的理論,例如現代化理論相信中產階級會推動民主,Rueschmeyer et al(1992)指出勞工才是承載民主的主要行為者,O’Donnell則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在拉丁美洲反而帶來了官僚威權政體。然而,沒有一個理論架構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如何影響一個新興的民主體制。
要問資本主義對民主的影響,必須反過來探詢民主體制又有多大能力形塑資本主義,因為兩者是互相形塑。本文認為,這兩者的鬥爭主要在兩個場域。
第一是金權政治,這是資本主義侵蝕民主制度的場域。在所有國家,市場都會介入政治,亦即行動者在市場上擁有的資源,會影響其政治參與的強度,這是所謂「以錢換權」。金權政治的另一面是,政治權力對市場運作的介入,亦即「以權換錢」。在這裡,政治權力對市場的介入指的是個人式的、特定的(specific)的關係,而不是對市場做結構性的改變。
資本主義與民主鬥爭的另一個場域,是社會不平等。這要端視民主影響市場的程度,亦即民主體制透過國家政策影響市場對資源與財富重分配的程度。民主體制是一人一票,所以中下層階級應該有意願也有能力透過民主機制推動社會資源的重分配。所以,如果金權政治觀察的是政客與企業間的「錢權交換」關係,在社會平等的面向上,則是公共政策對市場的結構性改變。
另外,要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對民主的影響,必須先界定在特定國家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才能確定對該國民主的可能影響。
威權時期的台灣資本主義,是一種「發展性國家—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八零年代後期開始,台灣一方面進行民主化,另方面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轉向新自由主義:人民與市場的力量同時被釋放出來,展開一場巨大的鬥爭。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界定九零年代以來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主要是指私有化與市場開放兩個層次。當然這是一種對歷史的簡化。因為一方面,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是有限的,例如在九零年代,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仍然很強,又或政府仍然欲主導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在市場開放的同時,台灣也建立了若干福利政策──但這個市場化與福利建構的矛盾,正是本文所欲探索的資本主義與民主之矛盾的體現。
本文將首先界定威權時期的資本主義模式,並分析其如何影響政治反對運動的動員策略,以及民主化的動力。接著討論八零年代末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如何改變台灣資本主義的新面貌。第三和第四節分別討論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兩大鬥爭場域:金權政治和社會平等;最後回到起點,提出九零年代的變遷所造成的階級矛盾之擴大,是否取代省籍分歧。
2.舊黨國資本主義與民主化的開啟
從經濟奇蹟到「寧靜革命」,台灣似乎成為 許多人眼中現代化理論的最佳範本。基本的論證是:經濟繁榮和私人部門的擴大導致多元的社會結構,並創造一批新中產階級,而為民主化提供動力。
但誠如吳乃德(1989)所提醒的:我們不能找出台灣的「現代化現象」後,接著描述台灣的政治變動。如果一個國家真的出現現代化理論預期的變項,那麼應該要問的是:「這些因素在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發揮了促進民主化的作用?如果是,又是透過怎樣的具體的政治過程,這些現代化的共同因素和這個社會的獨特因素,造成何種獨特的歷史複合體,共同創造了這個國家的民主政治」(p158-159)?
的確,要回答一國之內資本主義對民主的影響,必須先檢視台灣的特殊資本主義形構,其如何提供了政治反對運動和市民社會的動員基礎,及反對運動如何和政治菁英互動。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被稱為發展型國家,即國家透過產業政策、關稅保護、價格扭曲等政策工具,高度介入、引導市場的發展。東亞發展性國家都是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來進行資本積累,但相對於南韓是以大財閥做為出口主力,台灣則是以中小企業作為主要出口動力。在制度之外,發展型國家具有成長至上的意識形態,以效率犧牲平等,所以福利體制殘破,也缺乏進步的社會重分配機制。東亞社會安全支出遠低於拉丁美洲國家,例如在1980年,台灣只有17%的人有某種醫療保險,而南韓只有24%的民眾有。因此,發展性國家成功的秘密是,國家在生產和資本積累之外,幾乎不擔負任何責任。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具有一個其他東亞國家沒有的特色:黨國資本主義。戰後國民黨政權接收日本遺留下的資產及動員體制,建立對經濟活動的嚴密管制,並由國營事業、黨營事業高度控制各種經濟資源,以及各產業部門的統治高地,如能源、電力、金融、交通產業等。國民黨進一步策略性地分配黨國資本主義獨佔的資源以交換政治支持,例如把全國性的租金分配給政治關係良好的外省資本家和本省家族資本,把區域性寡佔經濟則分配給地方派系(朱雲漢,1989)。從六零年代,國家也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但不會讓私人資本在政治及市場上挑戰黨國資本主義的優勢地位。
這樣的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民主轉型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雖然台灣的社會福利落後,且勞工權利被嚴重壓制,台灣卻由於各種歷史條件下,能在快速的資本積累過程中,達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相對社會平等,也因此階級矛盾並不明顯(當然不是不存在)。另一方面,台灣卻具有巨大的省籍矛盾──亦即威權體制下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沿著省籍切割的不平等,於是政治反對運動便以省籍分歧,而非階級分歧作為主要社會基礎,以本土化做為民主化的主要動力。
台灣資本主義的另一特色──黨國資本主義──也造成同樣的政治後果。黨國資本和大資本構成國民黨經濟統治聯盟的核心:前者佔據大部分的經濟資源,而少數大資本家(不論本省外省)則依賴國家的政策保護和優惠。所以黨外運動自然是以在統治聯盟邊緣的中小企業為社會基礎。另一部份社會基礎是來自工農部門,但是僅限於在國民黨統合主義和地方派系侍從主義的組織之外。進一步來看,這個經濟資源的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基礎是有著族群意涵的:大部分外省族群的經濟地位是依附在黨國資本主義下,而中小企業及工農是以本省族群為主,這也決定了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族群性 。
簡言之,台灣資本主義的特色,包括階級矛盾的黯淡,以及黨國資本主義的支配,使得台灣民主運動的反對論述主要是以族群間不平等為根基的本土化路線 。除此之外,黨外運動也以較可以召喚不同族群支持的民主化論述來作為動員策略。然而,隨著民主化工程在九零年代逐漸完成,民主對抗威權的政治分歧退出歷史舞台,就只剩留下認同政治。並且,這個認同政治在新舞台上有了新角色:九零年代台灣主體性的上揚,強化了與中國的對抗關係,是故原來的省籍矛盾更被添加上國家認同矛盾的複雜化。
同時,原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也在九零年代展開了巨大轉型,這個轉型將如何形塑台灣的新民主發展呢?
3.新自由主義大轉型
從八零年代中期開始,既有的「國家主導─黨國控制」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漸受到經濟自由化的挑戰。1985年,國民黨政府邀請產官學界舉行「經濟革新委員會」,提出「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做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軸,並有許多關於解除市場管制和民營化的具體建議,但並未被採納。
真正導致八零年代後半的經濟自由化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民間的私部門,而是國際壓力 (Chu, 1994)。首先是國際經濟體制的變遷,導致台灣的貿易和金融體制經歷巨大轉變。例如新保護主義迫使台灣進行台幣升值和貿易自由化,逐漸要求台灣取消更多管制和開放市場,也使得國家官僚的政策工具(信貸分配、利率管制、外匯管制等)逐漸失去效用。其次,科技和資本的全球化使得企業降低對國家提供資源(資金、資訊、技術)的需要,並且增進其風險吸收的能力。海外投資選擇的增加,更強化了資本家的談判力量。
就國內市場開放方面,資本家越來越來開始挑戰以往國家由上而下主導的發展模式和對特定產業的壟斷。如從1986年開始,包括統一、中信要求菸酒開放民營,台塑要求建六輕、民間營造業向榮工處、唐榮、中華工程挑戰,要求公共工程由議價制改為公開招標,要求加油站開放民營等等。由於一方面美國要求國內市場開放的壓力增大,二方面民主化的力量削減了黨國體制的鎮壓性力量,這些要求更得以強化。
於是,87年底前已經開放了民營加油站設立,高速公路路權、旅行社、民航業等;1988年又通過證券交易法,讓證券商設立改採要件主義;五月決定電信加值與終端設備服務開放民營;1989 年開放美國保險公司來台,以及修改銀行法,開放民間設立銀行,為九零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大轉型,即市場開放與私有化,開啟了先聲。
但1990年郝柏村上台擔任行政院長,推出龐大的六年國建計畫,顯示國民黨的經濟官僚仍依循既有的發展策略,強調公共投資。直到1993年連戰任行政院長後推出的「振興經濟方案」,才更強調將投資的對象放在民間資本家,開始更大規模地推動經濟自由化。1995年更以「亞太營運中心」做為主要經濟戰略,推動台灣的自由化和國際化。
於是,在九零年代,過去高度壟斷的產業逐漸開放或私有化,包括金融、電信、電力、航空、大眾運輸、石化業中游、煉油等部門。1994年通過的「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提供了BOT的法源,更開放出利益可觀的大餅。這些鉅額利益重組了台灣的資本地圖,並改變國家與資本、國家與市場的關係。
經濟自由化首先強化了集團化趨勢。依據天下雜誌的統計,從1993年到1999年,台灣前五十大集團的總營收佔GNP之比例,從35%上升到52%。前十大集團的總營收,占GNP的比例則由18%上升到25%(瞿宛文、洪嘉瑜,2002)。這些大財團明顯是自由化的受益者,因為許多產業的開放都必須依靠雄厚的資本。例如前三十大財團包括有線電視的兩大寡佔者(力霸、和信),以及行動電話和固網業的所有參與者(同前:90)。
更進一步來看,原來就在寡佔經濟體制享有特權的財團,不論是原來就以服務業為主的集團(如霖園、新光、富邦、力霸),或以製造業轉進服務業的企業集團(如遠東、統一、潤泰、太平洋電纜),相較於高科技業或製造業為主的集團,都更積極參與特許市場開放:它們在新開放特許市場的參與項目平均是三家以上(瞿宛文、洪嘉瑜,2002)。例如1990年銀行開放設立後,十五家新銀行之主導集團的核心產業大都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最多的就是傳統產業,包括華新麗華、太子、遠東、大眾、台南幫、聯邦、力霸等七家。另有三家是地方勢力為基礎的財團:高雄陳家、高雄王家與長億集團。
這個現象具有重大的政治意涵:因為原來這些傳統財團在舊體制下就是憑藉著和政治菁英的良好關係而取得特權,因此一旦面臨新市場的開放,這些想要轉型的財團必然會繼續過去依靠關係為主的模式,在新市場中競爭。除了舊財團的轉型外,新財團也可能在這個新的市場重整機會中,憑藉著良好政治關係,成為這一波經濟自由化的贏家。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威京集團與長億集團(見後文)。經濟自由化並未消弭國家分配資源的能力,反而是提供了另一種國家選擇性分配資源的機會。而誰能夠成為贏家,往往要看執政者的政治需求。
新自由主義改變了台灣的經濟面貌,但卻未改變政商關係的本質。
4.金權政治:扭曲的市場與民主
在台灣九零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型過程中,並非如許多正統經濟學者所認為,市場可以清除租金,反而是出現一種特別的金權政治,深深扭曲市場和民主政治的運作。這個金權政治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是民主化讓更多利益團體、資本家和地方派系得以進入政治場域。這是九零年代初,學界與媒體最注意的現象(王振寰,1995;陳東昇,1995;郭承天,1997)。例如,1989年解嚴後的首次立委選舉,有企業背景立委63人,佔全體61.76%。國民黨黨籍立委中有48人有企業背景,佔國民黨籍立委66.7%(蕭有鎮,1995)。1992年財團候選人的暴增,以及多位大財團老闆的直接競選,更使得民進黨以「反金權」作為競選主軸之一。其結果是117名立委中,78人擔任企業職務或受企業明顯支援,佔全體立委66.67%(張鐵志,1999)。1995年的第三屆立委選舉,許多大財團立委如吳東昇、翁大銘、陳建平、吳德美、王世雄、蔡勝邦退選,以至於學者稱之為「資本家棄權現象」(郭承天, 1997)。但這些退選現象至多只是證明「統治階級不需直接統治」(Block,1977)。因為這些名聲顯赫(惡名昭彰?)的立委,可能更不利於直接在國會中為己牟利或競選。是故財團透過支持代理人參與政治,以及政客尋求財團資助,或上任後擴張投資事業仍很普遍。到了1998年第四屆立委225人中,92人有財團背景,佔全體40%,比例仍相當高。而國民黨立委有財團背景者有61人,佔黨籍立委49.6%(商業週刊586.587期)。
金權政治的第二個層面,是國民黨與資本家的新政商侍從主義,而這很大部分是經濟自由化的產物。
當國家在自由化壓力下將以往牢牢控制的龐大經濟資源逐步釋放出時,執政黨得以透過再管制的過程,分配恩惠給對其政治支持具有重要意義的團體。畢竟,即使原來壟斷性產業開放,仍然是僧多粥少,只有少數企業可以拿到新開放出來的龐大利益,而政商實力往往是新的獲勝者身上最明顯的印記。事實上,不論市場開放或私有化的承接是否是根據政治關係,只要私人資本家普遍認知有這個可能性,而國家又掌握大餅的分配權力,資本家就不得不與執政者維持良好關係。
以90年代初的銀行開放設立來說,在申請的十九家中,最後通過的十五家大部份都有強大的政商關係:即若非原本就有良好政商關係的大財團所投資,就是地方派系財團主導投資;而所有有立委投資者也都上榜。相對的,落榜的蘭陽、匯通、富國和五洲等四家則都缺乏有力的政商關係(陳尚懋,1998)。
再以民營化來說,「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民營化主要採讓售資產和一次或多次股權出售兩種模式。前者必然落入財團手中,如統一接手台機鋼品廠,東南水泥接手台機船舶廠。而眾所周知,統一集團的負責人高清愿乃是國民黨中常委,而東南水泥的大股東林炳坤則是國民黨籍的澎湖縣立委 。股權讓售雖然較可能出現符合社會公平的結果,但在台灣仍展現了利潤的高度集中性。事實上,負責承銷釋出股權的證券商主要都集中在特定幾家政商關係良好者。國民黨的暱友威京集團、曾任國民黨立委及省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的金鼎證券、地方派系高雄陳家的群益證券都是主要獲利者。而最大贏家,更是黨營事業的大華證券和中華開發。
進一步來看,不論是舊財團或是新崛起的財團,真正的大獲利者都是具有堅強政治動員能力的財團。例如,在舊財團中,力霸集團取得固網業務(東森寬頻電信)、銀行(中華銀行)、票券(力華票券)、有線電視(力霸東森)等眾多產業開放的成果。另一方面,力霸集團的負責人王又曾乃是連任多屆的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而商總或工總這些公會,也一向不避諱為執政黨助選,如辦工商座談會或大型造勢活動直接訴求工商界人士,由三大公會發表聯名信呼籲企業支持國民黨,直接動員所屬各級公會成立後援會等。而動員人數,商總曾評估可達百萬(工商時報,1993/11/2)。三大工商總會的諸理事長不只稱職地扮演公會領導者的動員角色,作為黨的要員,本身財團更是卯足了勁助選。
而在新興集團中,長億和威京集團可以說是這一波自由化中戰果最豐碩的新興企業。本來只是中部建設財團的長億集團,憑藉著良好政商關係而大幅擴充事業版圖。在金融自由化後先大舉進入金融業,成立數家證券公司,並設立泛亞銀行,得以透過信貸強化政商關係。長億並在九零年代中期取得三大開發計畫──這三者全都是自由化的產物:六年國建中十二項建設之一的月眉大型育樂遊樂區;電力工業開放首波十一家中的長生電廠;以及中正機場捷運BOT。這些鉅額利益的獲得,雖使其迅速躍升為下一世紀台灣最受矚目的財團,但是不論機場捷運或是月眉開發案都在競標過程中引起許多爭議。(Chang,2005a) 在長億龐大的經濟利益,及其所引起的爭議背後,乃是堅強的政治實力。楊天生本人是國大主席團主席,其子楊文欣為連任省議員,並曾違紀選上省議會副議長;其女婿郭政權則為立委。楊家在台中更是幾乎超越傳統紅、黑兩派的最有力政治力量。楊天生本人和李登輝、宋楚瑜交情深厚;如宋楚瑜省長競選總部即由楊天生提供。楊天生更擔任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威京集團是另外一個九0年代靠著強大政商關係在自由化過程中獲利的財團。它在民營化過程中不僅獲得最多承銷案,更引人爭議的就是透過收購委託書,入主中工、中石化。而如同長億,威京集團也具有堅強的政治關係。負責人沈慶京本人也是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委員,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沈慶京對於助選也是不遺餘力。作為股市聞人,他歷次大選時都以財力支持黨籍候選人,動員證券商,對投資人喊話。在94年省市長大選時,他並且聯合楊天生,幫國民黨候選人台北市長候選人黃大洲和省長候選人宋楚瑜在北中南舉辦投資人之夜。(張鐵志,1999)
長億和威京這兩個九0年代憑藉政商關係迅速崛起的代表性財團,最高負責人都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會委員,也都和黨營事業有密切合作。如機場捷運和高鐵BOT都是長億和中華開發合作;1998年泛亞銀行面臨財務危機時,也是由黨營事業接管。1999年10月,黨營事業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更說服十一家銀行團,聯貸35億給面臨財務危機的長億集團(商業週刊,1999.11.1)。威京的超級開發案「京華城」,則由中華開發主導銀行團聯貸120億元;花東電廠則是中石化和中華開發合作。而他們只是黨營事業所建構的政商網絡的一環。
這是台灣在九零年代金權政治的第三個層面,也是最關鍵的核心,亦即黨國資本主義的重生。經濟自由化不但沒有瓦解原來以壟斷特權為根基的黨國資本主義,反而讓它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攫取鉅額利潤,並利用這些新資源和政治優勢結合眾多財團,而成為國民黨新政商侍從主義的樞紐。
當陳師孟等在1992年出版《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之時,其實正是黨營事業大轉型開始的歷史時刻。例如,他們在書中指出原本黨營事業合作的主要對象乃是公營事業,到1988年徐立德主掌國民黨財委會後,才改以民間大財團為其最愛,如新光、台塑、台泥、東帝士、長榮、華隆等。但是,就在該書出版的次年(1993),國民黨從財委會獨立出來,成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後改名為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吸納許多重要資本家為委員,將國民黨和財團的合作關係更制度化。
九零年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更讓黨營事業得以從國家手中承接各種新資源。以金融自由化來說,原本國民黨在銀行、票券、和證券金融業都是獨佔或寡佔;金融市場開放後,黨營事業卻比別人更積極擴張。在證券業,到1998年底,七大控股公司持股的券商包括大華證券、復華證券、三陽證券、統一證券、菁英證券、力世證券、永力證券等七家,證金業有長期獨佔的復華證金,期貨業有大華期貨,保險業有93年成立的幸福人壽,銀行業則有高雄中小企銀、華信銀行。1998年本來打算再成立環球商業銀行,而後來在1998年改接收泛亞銀行。中華開發則在1998年改制為台灣第一家工業銀行。在電信事業第二階段行動電話業務的競標過程中,黨營事業投資五家公司,最後中標四家執照。1999年固網業務開放,最後得標的三家中,黨營事業也投資兩家:新世紀資通與東森寬頻。而九零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金額龐大的BOT案,包括機場捷運、高速鐵路和台北一零一金融大樓,黨營事業更是幾乎無役不與,並且黨營事業和其聯盟幾乎都得標(除了高鐵)。(Chang, 2005a)
其結果是,在1992年,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的稅後盈餘是26.1億元,到1998年時稅後盈餘已達122億元。投資事業更從93年的121家,到97年底達216家,擴張兩倍,再到1998年 的282家(梁永煌和田習如,2000)。總資產到1997年底已達1624億。真正驚人的,是這個龐大企業體對市場的巨大影響力。例如,在1995年,光是中央投資與光華投資持有的上市股票,扣除中鋼構特別股,就共計二十九家,佔全部上市公司十分之一(商業週刊,1995/8/28)。林其昂與楊嘉林(2001)的研究更指出,台灣經濟體中有一個「主控計畫體」,其主要成員為國民黨黨營事業集團、中華開發、交通銀行與中鋼,次要成員為遠紡、台泥、永豐餘與東雲,這八個企業集團彼此在人事上和組織上高度連結。根據各企業之間的連結(有共同董監事或共同投資)關係之密切程度分類,與「主控計畫體」中主要成員具有連結關係的上市公司達205 家,佔所有上市公司數目的百分之四十八,若加上四個次要成員,則比例為百分之五十二,亦即有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和主控計畫體有連結。若以十大產業來看,金融業中百分之八十四和主控計畫體有連結。
簡言之,黨營事業獲得重生與擴大,並和新興的財團、地方派系合縱連橫,強力攫取社會資源;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不啻上演著一場赤裸的政治經濟資源掠奪戰。這個過程,也讓執政者能憑藉其堅強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基礎,去籠絡、控制甚至懲罰財團和派系,從而建立更廣大的政治支持。這是對市場的扭曲,也是對民主政治的破壞。
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政商聯盟逐漸瓦解,長億、東帝士、力霸等倒的倒,逃的逃。2006年是最有象徵性的一年,力霸大老闆王又曾被通緝;中信小老闆辜仲諒被通緝。而這兩個企業集團,正是九零年代兩大企業組織全國工業總會和全國商業總會的頭,且王又曾和辜振甫都在彼時擔任國民黨中常委,因此他們可以說是國民黨統合主義在民主化後仍能持續的最重要代表。
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的瓦解,不代表台灣金權政治的消失。民進黨時代下,另一種金權政治模式取代了國民黨新黨國資本主義。一方面,民進黨執政者開始與大資本結盟,尤其金融改革重新衝擊了台灣的資本主義結構。另方面,在政治頂峰之下,許多權力新貴(不論是總統的親戚或是金管會官員)迅速地掉入腐敗的漩渦中。這反映的不只是個人操守的脆弱,更反映了制度上台灣對金權政治從九零年代至今完全缺乏有效的規範。
不論金融改革這個資源巨大重組過程,或是其他各種政商資源交換,此一時期呈現出的是一種比國民黨時期更個人化的政商侍從主義,亦即是以個人而不是以政黨為政商結盟基礎。一個制度上的原因是民進黨不具備雄厚的財務基礎,需要仰賴社會的金援,所以相對比較容易被財團牽制。尤其民進黨本身對內不具有高度組織內聚力,對外也缺乏國民黨的組織穿透力,所以利益交換過程甚至顯得粗糙而混亂。
進一步來看,國民黨因為過去的政治基礎是建立在與社會團體的利益交換上,例如地方派系、社會團體和財團的動員上,所以是以國家經濟資源來換取選票。民進黨則是因為選票基礎是以民族主義動員的認同為主,且缺乏自主的物質基礎,所以更傾向以國家經濟資源換取金錢,而較不是選票。這是台灣兩種不同的金權政治模式。
5. 社會不平等:資本主義戰勝民主?
資本主義與民主鬥爭的另一個場域是社會平等。民主體制下人民有機會影響國家政策,來決定國家是否會矯正市場運作結果的不平等資源分配,還是完全讓市場決定這個社會的贏家和輸家。通常,政治學或經濟學理論預期民主化應該會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因為威權時期在政治上被噤聲的弱勢團體在民主化後被解放,原本被壓制的工會也可以開始代表勞工爭取利益,所以政府應該有更多偏重於弱勢的政策。另方面,由於大部分選民的收入低於一個國家人民的平均收入(因為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享有大量財富),所以選民會用選票支持一定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二十世紀初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正是工人獲得普選權的結果。
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可能強化私人資本對國家的談判力量,而政治場域的開放,也讓有錢者更可能以不同方式參與政治,影響公共政策。
在台灣,從九零年代制訂的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等政策,似乎的確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Wong, 2004)。但是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確實日益擴大。從1993年到2003年十年間,測量平等的吉尼係數從31.32增加到33.85(OECD國家的平均數字是低於台灣的30.6);而最高所得組可支配所得與最低所得組的差距,也從93年的5.41增加到03年的6.05 。金字塔頂端五%的所得,與最底端五%的所得相比,這項差距在1998年為三十二倍,到了2003年增加為五十一倍。
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如稅制改革,也沒有朝向更平等的方向(Chang, 2005b)。個人海外所得、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都不必繳稅。經建會在前兩年的「推動財政改革」報告也指出,雖然綜合所得稅有效稅率會隨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但累進程度並不明顯,因為中、高所得者享受的各項免稅額、扣除額遠高於低所得者。在2005年,全國最高所得的四十位富豪中,有八人一毛都不必繳,有十五個人只繳納一%的稅率。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不但低於最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美國,也在兩千年後低於同為四小龍的南韓。尤其,賦稅制度作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機制,在2004年只改善台灣民眾所得差距的0.14倍,與美、日等國相去甚遠。如主計處的研究指出,「我國稅收減免項目繁多,整體賦稅負擔率遠低於國際水平。」
這顯然是民主化許諾的失落。這也當然不只是台灣,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都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但這不代表台灣只能面對這種不能逆轉的趨勢,畢竟各國的不同制度都對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對不平等的消除,扮演不同角色。因此,我們必須分析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制度條件使得民主化在與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取得勝利。
第一是前一節所述金權政治的影響。畢竟當民主化賦予弱勢團體和工人力量時,同時也開放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後者的影響力當然勝過勞工和弱勢者。台灣從九零年代以來的減稅政治,可以清楚看到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力,而工會運動則相對來說是很弱勢的。
第二是台灣特殊的選舉制度。理論上雖然預期中間選民的偏好會引導政治人物推出比較偏向重分配的政策,但是選民偏好如何反映到政策,端視不同選舉制度。比例代表制因為重視政黨甚於候選人個人,所以最能引導政治人物提供公共財。而台灣的特殊選舉制度,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是政黨角色最低的選舉制度,即使同黨候選人都必須依賴人脈和金脈來競選,所以比較容易引導侍從主義式的資源分配。
第三、過去唯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不僅形塑經濟官僚的意識形態,也深深影響民眾態度。所以民眾並不願意為了平等分配而犧牲經濟成長。這是發展性國家的遺產。
第四、全球化對重分配政策造成侷限。過去十年,政治學界最重要的辯論之一,就是全球化在什麼程度上限制了社會政策。一派認為在資本可以任意流動的全球化條件下,國家不能推出進步的福利或稅制政策,否則資本會外移;但另一派則認為,恰恰是因為全球化造成新的贏者和輸家,並增加了工作變動的風險,所以國家更有必要提供好的社會安全網。在經驗研究上,不論是對歐美或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都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在台灣,這種對全球化莫之能禦趨勢的看法,恰好符合既有的發展主義,所以衍生出許多未經檢驗的迷思,例如唯有低稅賦才能留住投資等等。但事實是,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政府還是有用政策介入市場、追求社會平等的不同能力。而各國的差異,往往是由其國內政經制度和社會力量的角力所決定,而非是不可逆轉的。
第五,原來相信民主會促進平等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中間選民的偏好會引導政策,但這個前提是選舉只有一個面向的議題;亦即如果選舉只有重分配這個議題,那麼結果可能會的確是中間收入選民會影響稅制政策,進行更大程度的重分配。但這個假設受到許多挑戰。例如,政治經濟學者Roemer(1998)提出,如果選舉中除了經濟議題外還有另一個面向(例如宗教或種族),而且選民通常更關切後者,那麼中下階層選民不一定會支持更重視重分配的政策(或政黨),因為他們會更依據非經濟議題的立場投票。這正是台灣的情形:認同議題比階級議題更主導了政治競爭,所以無法實現民主對平等的許諾。
6.未完的結論:去政治化的階級矛盾與新民主危機
回到本文的起點,如果過去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台灣民主化動力最大的影響,是讓認同矛盾主導了台灣政治分歧,那麼九零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所造成的金權政治與惡化的社會平等,不是應該會出現更大的階級矛盾,並轉化為政治分歧嗎?
事實似乎不然。歷史強制在台灣人民身上的幽靈仍然揮之不去:從本土化建立社會基礎的民進黨持續「拼本土」 ,在威權時期以繁榮來掩飾政治高壓的國民黨一直高喊「拼經濟」。然後,民進黨被迫拼經濟,國民黨被迫拼本土。但是,沒有人要「拼正義」。尤其,如上節所述,選民對於認同問題的重視,更壓制了在社會層次上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政治上的主導分歧,並誘使政治人物不會以社會平等作為主要政治主張。
問題是,如果金權政治和社會不平等不能被有效的解決,人民會開始懷疑新興民主的有效性、甚至正當性。其結果可能是政治的犬儒主義,或是對威權時代的懷念。最新研究指出(Chang, Chu and Park, 2007),台灣民眾對民主的支持是東亞幾個國家(南韓、菲律賓、蒙古、泰國)中最低的,且台灣只有不到一半的民眾認為,民主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另一份研究(Chang and Chu, 2006)也指出,腐敗問題在東亞是最影響民眾對民主信心的議題。在台灣,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認為,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
過去二十年,台灣人民辛苦地追尋民主的解放,但得到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一個被市場力量穿透的政治領域、以及一套無法有效規範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的虛弱民主。既有的認同矛盾,仍然壓制著日益擴大的階級矛盾,不容它轉化為有效的政治力量。於是,人民對民主制度喪失信心,並對社會正義的價值開始感到虛無。這些,乃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