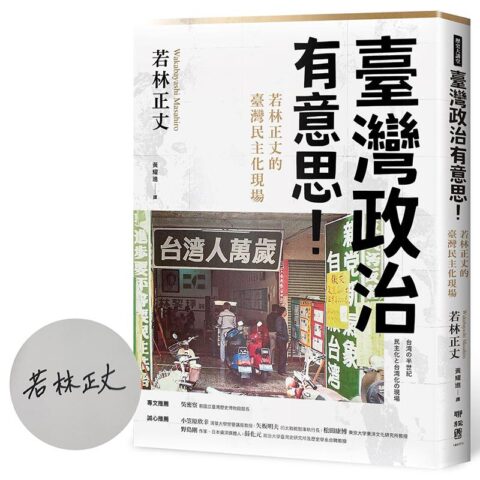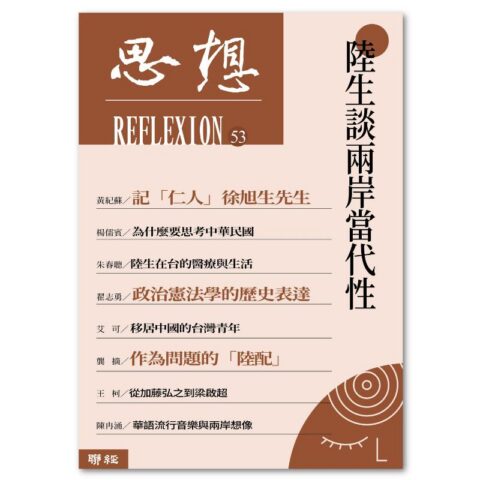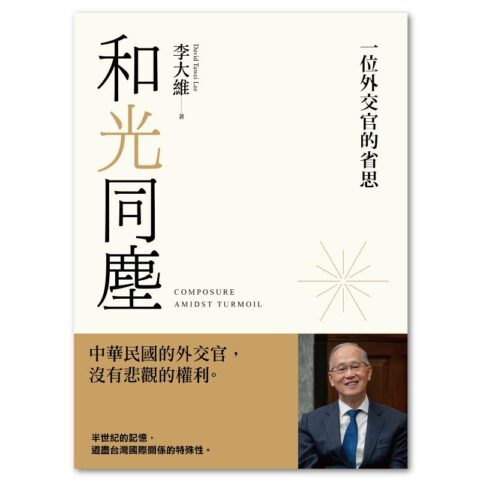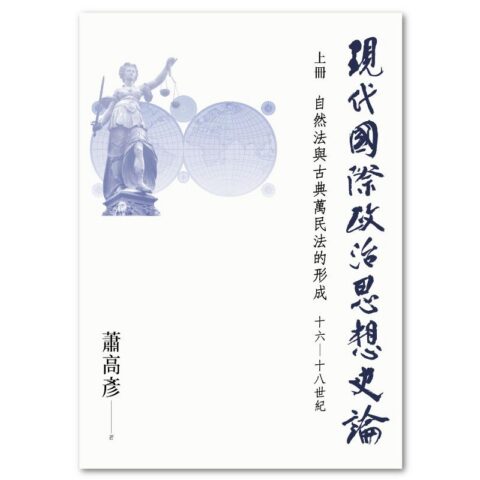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思想 28)
出版日期:2015-05-27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4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5648
系列:思想
已售完
《思想》第28期的主題是「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
與其他各國的海外華人社群一樣,在很大的程度上,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近代中國的危機息息相關,它可說與兩岸三地分享著相同的「現代」命運。然而,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相比,馬來西亞華人卻有其獨特性,這和它的人口比率有極大的關連。馬來西亞華人人口逼近七百萬,曾占全國人口比率三分之一強,至今也還有四分之一,這使得它與屬於絕對少數人口的歐美各國華人社群不一樣,更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新加坡不同。但也正由於此,馬來西亞華人形成了獨特的問題和命運。它雖是少數族群,卻又被認為是對「土著」構成威脅的少數,因而在二戰之後的解殖民化過程中,在新興的民族國家建構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然而也由於同樣的原因,它在社會各個領域中具有自成體系的能力,堅韌地存在著。
簡單的說,在文化上,馬來西亞華人的獨特性體現在其社會自成體系下形成的文化(語言)再生產能力,華文教育體系得到基本完整的保存,「馬華文學」就是其文化再生產的顯例。在政治上,它老早就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中的重要主體力量,脫離了北美洲華裔僅能偶而參政而當選議員或市長的模式。同時,在長期深受種族主義政治霸權斫害下,華人在追求自身平等地位的過程中,在當代思潮或意識上逼迫出了一種民主化、泛人權的政治現代性,並且形成為一股促進馬來西亞民主化的關鍵力量。可以這麼說,馬來西亞華人的「現代」遭遇與當代命運,在學理上頗值得追問與發掘,它與當代兩岸三地有所聯繫但又不同,這之間其實有許多可以對話與對比之處。本期「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專輯,各篇文章主要即圍繞上述馬來西亞華人群體的特殊語境,嘗試從政治、觀念、語言及人文各個角度,回顧及探問華人的基本問題與處境,以期提供華文知識界一初步的理解。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鄭鴻生)
作為政治實驗室的占領中環(劉世鼎)
極權崩潰如何可能?:緬甸的番紅花革命與緩性群眾(吳 強)
跨文化張力中的儒家政治思想:康有為與孫中山的現代化方案與大同社會理想(劉滄龍)
惡的平庸與政治判斷:從阿倫特的角度看(張 念)
馬來西亞: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
前言(許德發)
公民可以差異而平等嗎?:馬來西亞的69年糾結(黃進發)
分歧的社會正義觀?:華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論述與權利爭奪(許德發)
馬來西亞的多語現實和馬華的語言困局(王國璋)
語言、文體、精神基調:思考馬華文學(莊華興)
複製殖民認同:區域主義、去殖民與吉隆坡的建國建築(盧日明)
思想訪談
公民運動與中國轉型:笑蜀先生訪談錄(陳宜中)
思想評論
重訪中國革命:以德性為視角(唐小兵)
理由性動物:《為什麼?》的理由世界(李鈞鵬)
思想人生
趙儷生:一生負氣(李懷宇)
致讀者
致讀者
台灣人到馬來西亞,通常會意識到當地華人社會的凝聚力,華人語言、文化與傳統的完整健在,同時也會注意到華人少數族群與周遭馬來多數族群的分隔與緊張。這個人數接近七百萬的華人社會,曾與多個相異民族相處共存,也遭受過壓迫與敵視,直到今天所能享有的公民權利還是有所折扣,就學、就業以及生活上所遭遇的種種困擾也到了歧視的程度。在現代馬來西亞,華人作為少數族群,如何爭取應有的權益,保障族群與文化的延續,進而維持馬來西亞的多族群、多宗教社會的多元平衡,是一件艱難、沉重而很獨特的挑戰。《思想》注意到馬來西亞華人的經驗與觀點值得重視,因此邀請了許德發先生規劃本期的專輯,藉著中文跨國通用的便利,邀請幾位馬華作者探討馬華經驗的一些面向,供各地華人參考。
馬來華人的族群經驗,在世界各地華人社群中確實非常獨特。略舉數端為例:他們在人口上是少數,經濟上居於優勢,但在政治上處於弱勢,文化則不受國家的承認;馬來西亞官方的「本土主義」旨在維持「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具有濃厚的排華意涵;伊斯蘭教實質上具有半國教地位,並在不少俗世領域握有半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對華人融入馬來西亞社會構成了阻礙。凡此種種,其他地區的華人幾無經歷。也因此,多元共存對大馬華人並不是書本上的理論問題,而是臨淵履冰的生存之道,非如此不足以因應一元化本土主義所造成的壓力。其他以華人為多數主體的社會,往往對身邊的少數族群視而不見,十分需要借鏡馬華的經驗,體會多元社會的真義。
鄭鴻生先生分析對比韓國、台灣與香港對於前殖民國態度的差異,也涉及了港台兩地華人歷史經驗的多樣。他比較香港與台灣的殖民歷史,以及兩個社會中反殖民運動與祖國的關係,說明這兩年台灣與香港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一些特質。鄭先生的寫作一向貼近生活而觀察細膩,常能呈現他人所忽視、無視的趨勢如何發揮了作用,凸顯歷史的某些面向。本期這篇文章亦是如此,值得讀者們參考。
劉世鼎先生論香港占中運動的文章,敘述與反思兼備,對這場震撼了香港與周邊社會的學運多所檢討。與多數參與者的回顧不同,他並不急於分派功過得失。他採取宏觀的歷史角度,用「代表性斷裂」、「去政治化」等概念(應是借自大陸學者汪暉),分析占中的歷史背景與這場運動的內在矛盾,所見更為深入。這篇文章應該會引起不同的意見,我們歡迎進一步的討論。
《思想》前一期(27期)的「太陽花專輯」,係由本刊編委陳宜中與王智明兩位規劃主持,他們並且寫了一個序言,其中說到:
《思想》編委會自5月起籌組本次太陽花專輯,有幸邀集到十位觀點殊異的作者,對太陽花運動展開分析,各抒己見。讀者不難發現,部分不同見解之間的距離頗大,甚至南轅北轍。在今日台灣,這種分殊性是在所難免,但盼本專輯能激發出更多有意義的深度論辯。
但由於編者在作業時的嚴重疏失,這個前言最後竟然沒有刊出。在此,除了向陳宜中、王智明二位致歉之外,也請前期的讀者了解,該一專輯的原本用意——也是本刊的基本立場——正在於激發論辯。不習慣面對異見的人,若能細讀本刊,相信有助於您逐漸克服恐懼,面對這個並不仰仗你我來認可的真實世界。
分歧的社會正義觀?:華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論述與權利爭奪(許德發)
一、前言
自1950年代馬來亞獨立憲制之擬定與談判時期開始,出於族群利益分配之博弈,公平、平等這些屬於社會正義觀念的詞語也夾雜在族群動員之中,充塞於馬來(西)亞各種政治修辭與社會話語之中。實際上,馬來(西)亞的最基本問題是族群問題,社會的利益分化和對立往往都被族群化,而階級問題則相對被模糊,這使得族群之分歧造就了對社會公義觀念的不同視角及詮釋,進而形構了相異的社會公義觀。所謂「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概念乃指被用作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並被視為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它要處理的問題是:社會合作怎麼樣才算是公平的?羅爾斯更指出,正義的對象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即用來分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劃分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和負擔的制度,而正義原則旨在提供適當的分配辦法。換言之,社會正義原則欲通過社會制度調節社會的不平等與非正義之事。因此,一個社會內的正義觀念系統必須被普遍接受,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合作、政治政策實施的正當性,甚至政權的合法性及政治效忠才能有真正的基礎。由此可見「社會正義」之於國家的重要性。
基於此,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無論採取甚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體制,如果要穩定和持續發展,都必須表達基本社會正義。儘管此議題及概念如此重要,但有關馬來西亞社會之內的正義觀之研究似乎闕如。本文嘗試通過獨立以來國內兩大族群,即馬來人(尤以執政巫統為主的主流民族主義者)及華人社會中較為通行的幾個相關概念如平等、公正及公平之論述,探討馬來西亞社會內的正義觀之歷史起源、本質及其演變,並從西方政治哲學的學理視角對之進行初步評價。實際上誠如前述,由於族群權益之嚴重分化,不同的族群自有其不同的理念擁抱,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對這些理念之探究,也意味著對馬來西亞族群問題另一個面向之理解。
二、政治博弈下的政治正義論述
1950年馬來亞獨立運動時期的憲制博弈以及與之相關的權利分配,是以三大族群作為談判及分配單位的。大體而言,族群競逐不外為了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社會地位、或是文化認同的分配。由於獨立憲法決定了各族群在此新興國家未來的地位與前途,因此在這關鍵的立憲過程中,迸發出了各種權利危機與價值張力。在各個族群的權利競逐之中,除了社會動員、關係的操作與實力的衝撞之外,更少不了各種言論、論述與喊話。換而言之,權利競逐的前提又是建立在各自的訴求與權利之爭取的正當性之上的。「正當性」其實涉及到道德層面,因此各大族群不得不提出各自的正義論述,以合理化自身提出的分配原則及方案。
(一)原地主義與不平等的根源
首先,我們不妨直接引述已故著名華文教育鬥士沈慕羽一句仿效孫文的著名說法——「華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需努力」來說明題旨,它頗能概括馬來西亞華人所追求的社會正義——「平等」。對華人社會而言,它面對的是一種刻意的、憲法及政策設計上的不平等。從根源上說,從1920年代開始,隨著英殖民政府推行親馬來人政策,華人社會即開始感受到自身地位之不如人。作為一個被各方認為乃國家的「客人」、「外來者」,這啟始了華人在地的不平等憂患。然而最早感受到不平等意識的乃是海峽華人,如陳禎祿於1932 年12 月即向英國駐馬來亞的總督遞呈了長篇政治宣言,要求賦予海峽華人政治權利、廣泛參與行政會議與立法議會的權利,及允許華人進入政府文員服務組,即殖民政府行政管理層 。這可被視為華人最早爭取平等待遇之始。
事情總有另一面。同樣的,馬來人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大約也始於1930年代,這與華人移民人口的增加有明顯的關係。與英國殖民地當局實施親馬來人政策差不多同個時期,「土著」概念即已出現,它可說是白人殖民地的產物。我曾在另一文章中提過,這是馬來民族主義者「原地主義」邏輯的操弄,把這個國家本質化為Tanah Melayu(馬來人之土),即「馬來人的馬來亞」,並以此合理化、鞏固他們在馬來(西)亞不容挑戰之主體位置。在獨立前,新加坡馬來人同盟(Singapore Malay Union)的尤諾斯(Encik Mohammad Eunos)曾在立法議會上高分貝的喊出:
不論馬來人有怎樣的缺點,可是他們沒有共產黨分子,也沒有兩面效忠,不管其它民族如何講到土地的占領,我確切地覺得,政府充分了解到,到底是誰把新加坡割讓給英人,與馬來半島的名稱是根據什麼人而來的。
而對於華人的本土地位,當時的《馬來教師雜誌》(Mujalah Guru)社論則質問「若我們馬來人生於上海,是否可以只因為我們想要權利和特權,而自稱是上海的土地之子?」塔尼亞.李沐蕾在研究印尼原住民運動時曾指出,運動發起的深層原因是有賴於把「原地哲學」作為權利和認同的基礎。這種哲學尊崇當地人,強調「民族淨化」,認為外來的「他人」不合法,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懲罰、排斥他們。實際上,學者們業已指出,一個支配團體要維繫其優勢地位,除了要能控制資源的分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界定其價值體系及灌輸將不平等合理化的意識形態,如此一來,不平等的結構才具有某種「正當性」,而維繫不平等狀態的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確保劣勢者對不平等的體制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認同,並安於劣勢地位的現實。馬來人反復強調自身「土著╱土地之子」(son of the soil)地位,並由此得到判斷他人「忠誠度」的道德制高點。換言之,「馬來主權」就是馬來西亞非馬來人的最大挑戰及不平等的根源,馬來人也藉此維繫其自身在憲法及政策上之特別地位。尤其在1970年代「後五一三時期」嚴厲、激烈的馬來人特權政策,更讓華人切身體會到自身存在的尷尬。因此,國家獨立之於華社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危機意識」之形成。
延續著英殖民地時代的差異政策以及1948年的馬來亞聯合邦(Malaya Federation)憲法,獨立後的馬來(西)亞透過1957年獨立憲法之草擬,可說「再生產」了社會當中的不平等狀態,使之以固定的結構持續存在,甚至於可以加以延伸至「新經濟政策」之實施。獨立憲法除了賦予馬來人無限期的特別地位,也基本不「承認」其他族群的平等文化權利,正如塔利所認為的,我們一般所談的現代憲政主義過度側重普遍性與一致性,無法面對文化歧異性的事實,疏忽了「文化承認之政治」,結果產生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易言之,馬來亞獨立憲法中的馬來人特權條文結構化了不平等的制度存在,持續了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如所周知,依據獨立憲法153條款,最高元首被賦權以維護馬來人、沙巴及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同時保護其他族群的合法權益。在此條款下,特殊地位的定義在於保障土著在公共服務領域(中央政府)、獎助學金、教育及培訓機構的合理百分比名額(或稱固打),同時保護地位也延伸到所有聯邦法律中所規定的一切何須要准證及執照的領域。此項馬來特殊地位是由馬來亞華人公會與巫統達致的所謂「社會契約」——以公民權交換馬來特別地位——所形成的。這常被作為堵住華人各種追求「平等」的歷史憑藉。大部分華人後來都獲得公民權,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巫統並不把公民權等同於「國族地位」(nationality)。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直到1966年之前從不承認國族地位是公民的基礎,而且一直拒絕談及國家的國族稱謂,這是因為擔心這將為馬來人及非馬來人之間的平等鋪路。顯然,巫統在公民權課題上雖做出讓步,但他們絲毫不放棄「馬來國家」的建國理想:只有馬來人才具國族地位。如此一來「國家的公民」與「民族的成員」已經變得不能混為一談 ,也就是說對國家的「效忠」以及對民族的「認同」,在概念上是兩件事。當時巫統對此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他們「給予」華人的是「公民權」(citizenship),但公民不等同於國族身分(national),所以公民之間自是不平等的。顯然,馬來(西)亞的建國是一種民族與國家捆綁一起的模式,而不是公民建國模式。馬來民族國家建構的理想使得馬來(西)亞先天性的沒有建立普遍公民國家的條件,這也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基本難題。
這清楚表明,從根本上而言,這種所謂「社會契約」下的交換置華人於不平等待遇之中,它體現了華人實質上只獲得「不完整的公民權」(partial citizenship)。從西方公民概念的演化來看,這其實是一個相當怪異的現象。從18世紀以降,民族主義的勃興與公民身分的發達,構成了強大的動力,終於為道德╱政治平等理念的主導地位,在制度、社會層面取得完整、具體的形貌。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相對於其它身分是優先的,它視所有成員為同樣的個人,民族成員於是取得了某種平等的地位,而且民族主義將整個民族高舉到最高的(主權)地位,不僅突出了民族成員的政治地位,也賦予他們某種平等的政治權利。因此,道德╱政治平等的普遍性與優先性,藉著民族主義獲得了穩固的地位,由「國民」這個概念來加以制度化。但顯然的,具體到馬來亞而言,巫統通過民族主義建構,即所謂的「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概念獲得了主權與特權的賦予,卻又通過「外來族群」概念,讓自身的權利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同時置同屬「公民」的華印兩族於不同層次的地位上。
若說殖民地時代華人面對的是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關係,它可說是屬於一種階級上的不平等待遇,但獨立之後,這種不平等則轉變為一個「民族平等」的問題。「平等」於是進入馬來西亞華人的視野之中,從此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思維世界中取得了「正當性」。「爭取民族平等」實際上成為一種全體華人在各層面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意見氣候」(climate of opinion),是往後每一個華人成長過程必定感知得及的族群敘述。因此,華人社會長期追求平等、強調公民權利實踐,可說(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是在爭取做一個完整的公民。華人大體上在獨立前夕已驀然自覺到他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性的時刻,他們更知道憲制與自身角色的絕對性意義。當時頗能代表一般華人的全國註冊華團工委會就認為,「如未能在憲法上明文規定華人在本邦之地位,恐無平等之可言。如在憲法上未通過之前不爭取,將來悔之已晚。」這一席極為沉重的談話可說是現代華人社會沿襲半個世紀之「平等敘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道出了華人危機意識的根本核心源頭,即「平等」仍是未解決的優先問題。
(二)後五一三時期的「馬來議程」與分配「公平」
實際上,在華人憂慮於平等問題時,極為弔詭的是,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在五一三之後撰寫的《馬來人困境》中也曾為文談「種族平等的意義」。他在文中大力為憲法及法律上偏向馬來人的「不平等」辯護,他認為這些法律之實施(包括馬來保留地、獎學金、公務員職位等條款)是為了保護馬來人免於陷入更為不平等的處境,因此是促進「種族平等」的必要措施。文中,馬哈迪雄辯式的引述美國黑人及印第安人的不平等處境,暢談馬來人在經濟、教育、就業中的不平等,而認為政府對馬來人的保護及扶持是必要的,以避免種族間不平等造成「和諧問題」。顯然,對像馬哈迪這樣的馬來人而言,馬來人是處於不平等的待遇之中,甚至認為憲法上的特殊地位並無助於「馬來人達致平等地位」。他亦提到,儘管華人之中也有少數貧困者需要獎助學金,但由於華人受良好教育者相當多,馬來人則遠在後頭,因此「假如少數貧窮的非馬來人獲援助去接受高深教育,那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教育懸殊將會更大」。馬哈迪完全是從種族角度談論貧困與機會,而且從經濟上、教育上認為馬來人遭遇不平等,他進而要求一種所謂的經濟上的「分配式平等」。
然而,到了1970年代之後,「種族平等」在官方或馬來民族主義者的論述中似乎逐漸讓位於「公平」(kesaksamaan)及「公正」(keadilan),而且二者交替使用,沒有明顯區別。經歷了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後,「新經濟政策」(DEB)雷厲風行,國陣政府的差異政策進一步激化。新經濟政策是由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所推動,在《第二個馬來西亞五年發展計畫》中提出:
國民團結是國家的至高目標,如果馬來西亞社會及種族集團,在參與國家發展中,沒有獲得較平等與公平的地位,是無法分享現代化和經濟成長的成果,也將是不能達致的。如果大部分的人民,仍然貧窮及如果沒有立足的就業機會提供,國民團結也不能促成。
因此,政府宣稱新經濟政策要達到兩大目標:(一)不分種族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增加就業機會,以減少貧窮和最終消除貧窮。(二)重組馬來西亞社會以糾正不平衡(ketakseimbangan sosio-ekonomi),進而減少及最終消除在經濟上的種族區分。誠如眾知,所謂的「社會重組」並不是階級或經濟利益單位之間的社會階級關係的改變,它強調的是種族之間的資本占有率,即所謂的土著與其他族群(特別是華人)之間的「社會經濟公正╱平衡」(Keseimbangan/ Keadilan Sosial-Ekonomi),其中要求股份30%比率必須保留予馬來人,以及其他各種種族固打制(包括進入大學就讀的名額)。此中的關鍵字就是「社會公正」及「社會經濟」。最近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針對馬來西亞大學排名下降事件作評論時,副首相慕尤丁就指出,「馬來西亞與其他國家不同,因為(大學)需要考慮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問題及其它目標……,必須考量社會經濟目標,藉此提供援助,準備機會與空間,讓非優秀生進入大學……。」實際上,最能象徵巫統馬來民族主義的正義論述的是國民陣線(國陣)的標誌——天秤——其實就是所謂「公平」的象徵。國陣也是「後五一三」脈絡下的產物,與「新經濟政策」擁有相同的歷史脈絡。
從概念上而言,「公正」與「平等」相較而言,前者強調在一定社會範圍內社會成員通過合理分配後,每個社會成員得其應得。它強調的不是個人範疇,而是一個關係範疇,是就社會成員人與人之間關係而言,並注重社會內部成員之間的平衡性(新經濟政策即強調「Keseimbangan 平衡」)。易言之,它側重社會成員之間的人生追求過程的起點、過程和結果的合理性,具有分配的性質,要求人們在必要的條件下,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適度的調節,使人們各得其所,和諧相處。此外,所謂社會公正,也常與「公平的經濟生活」相聯繫,常常與此相隨的概念是「社會權利」,這可以理解為「機會」,所以馬來人也談「機會平等」。對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就如同奧運會也舉辦殘運會一樣,在不同能力的選手之間不應該處在相同的賽場之中。所以,他們反對「平等」,認為平等不能確保公平的結果。馬來民族主義學者再納克林(Zainal Kling)就曾認為,績效制不應該跨族群,而是應該限在自身種族內進行。對他們而言,這樣才符合「正義」。顯然的,社會公正是涉及國家角色與社會結構,從這裡我們即可理解,對作為掌握大權的巫統或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的思考模式離不開政府的計畫與分配政策,使用「公正」似乎更適合、也更為「正確」,並因此成為「新經濟政策」文宣中的關鍵字。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種族平等」後來較少被馬來民族主義者所應用。
這裡的弔詭之處是,被許多非馬來人認為不平等的新經濟政策,竟在馬來民族主義者巫統眼中被視為對馬來人平等待遇的追求。實際上,「社會公正」確實注重分配,但是新經濟政策卻是從「族群本位」而非「需要」的角度來實行其無差別的平均主義,並堅持最後達到依據族群人口比率拉平差距。新經濟政策以「馬來人優先」,其正當性實來自於民族主義道德,而非「公正」本身。誠如前述,馬來民族主義及巫統所謂的「馬來議程」(Malay Agenda)正是以「馬來原地主義」哲學獲得其正當性的。「原地哲學」作為其權利與認同的基礎,深深影響了馬來人整個政治鬥爭與生活。在馬來原地哲學之中,蘊含一種民族的自尊與受害意識的政治語法。這種傷害來自於外來族群,也來自於殖民統治的經歷。對這個曾經被臣服、被壓迫的民族來說,所謂的「馬來議程」無可否認標誌著重要的民族自強時刻之來臨。哲學家伯林曾表達了民族主義「首先是受到傷害的社會做出的反應」這一觀點。伯林提出「彎枝」的比喻, 暗示了一個民族遭到過羞辱性的征服後,這個被迫「彎曲的枝條」終究要反彈回去,而且會以非理性的反向鞭笞回應曾經遭受的羞辱,成為攻擊性的民族主義。他們的價值完全在於回應民族利益的召喚——民族至上——民族擁有不容阻礙的使命。實際上,民族主義原本即宣稱擁有「天然的道德」,因此對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馬來特權自然是天經地義之事,「差異待遇」從此也得到它的正當性,但同時也使得此「公平」染上了強烈的種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