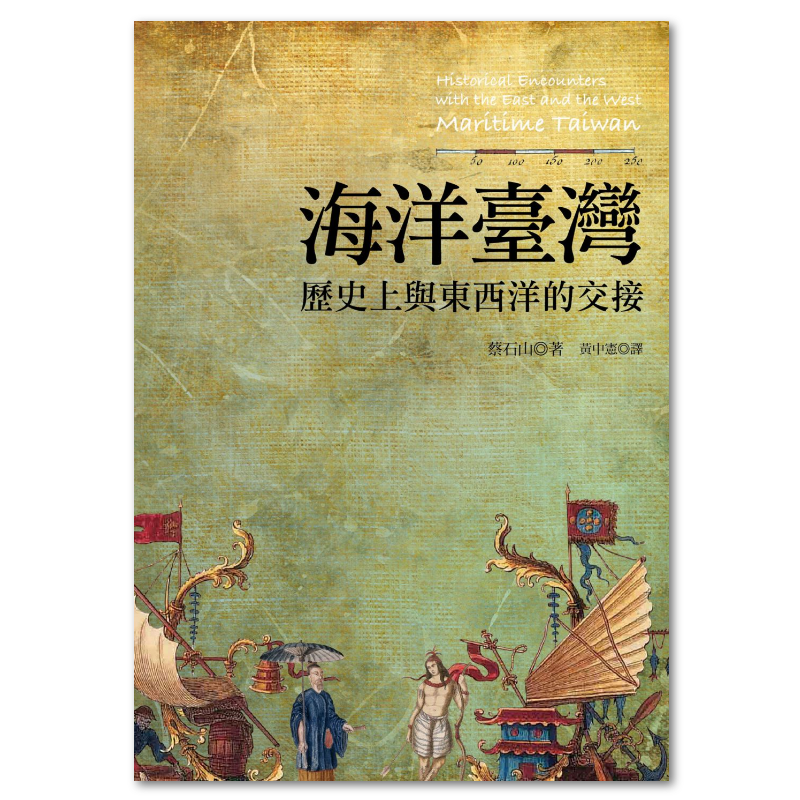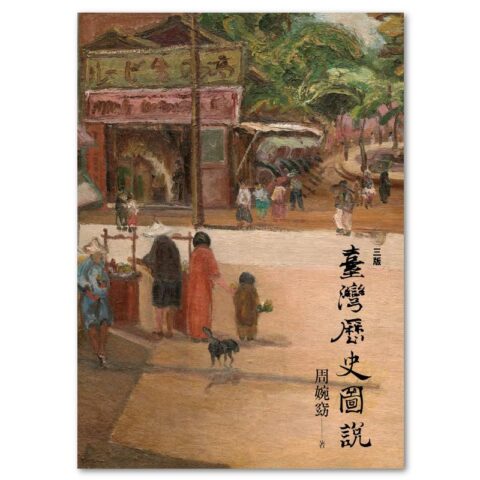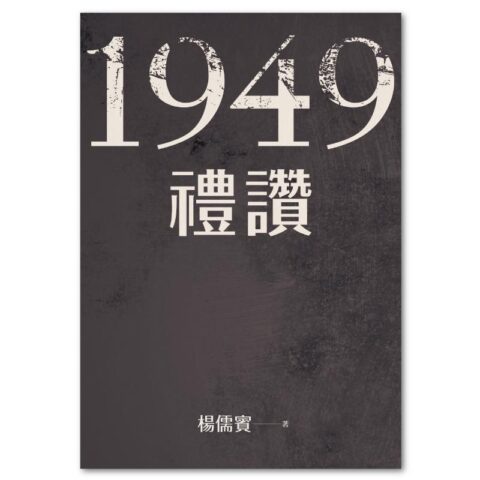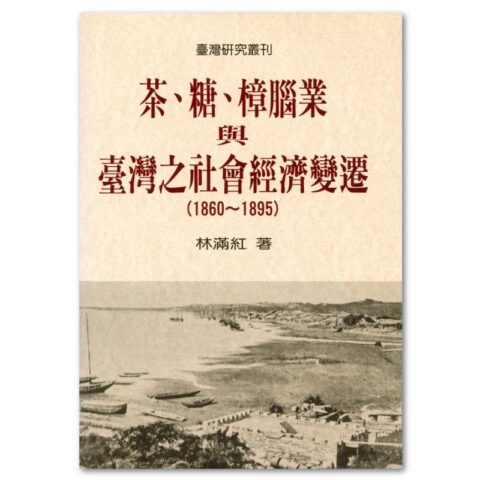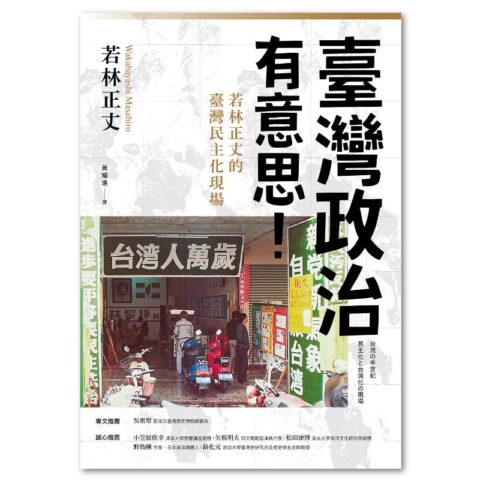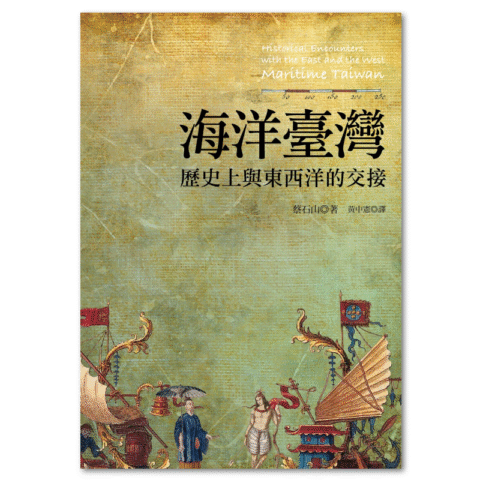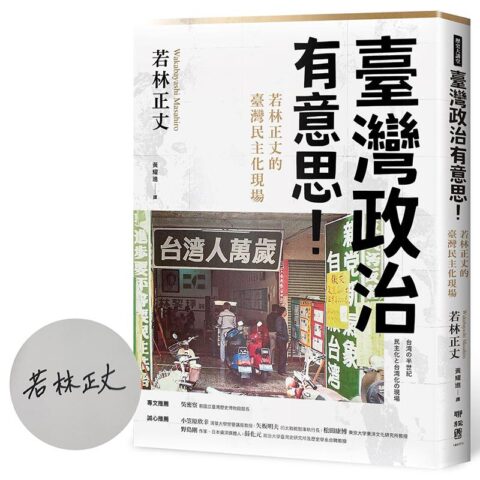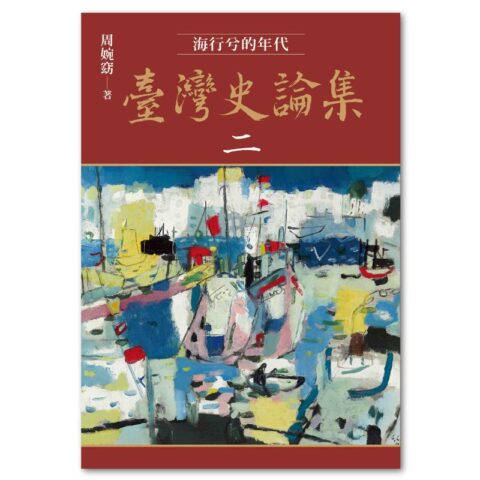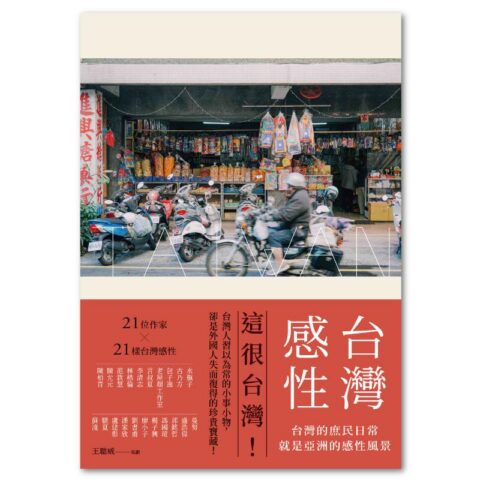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
原書名: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出版日期:2011-01-11
作者:蔡石山
譯者:黃中憲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00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7179
尚有庫存
中國對臺灣的影響,要到十七世紀下半葉才可明顯察覺到,
這與一般人對中臺關係史的錯誤認知其實大相逕庭。
臺灣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資源,
在亞洲海上貿易網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
1921年,在慈善家林獻堂和名醫蔣渭水等在淡水河沿岸組成臺灣文化協會,
推動臺灣文化並發揚臺灣民族意識。
臺灣目前是世上第19大經濟體,
臺灣社會已變得更文明,媒體變得更自由,政治已走上民主、自由之境,
而這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美國在軍事、經濟、教育、技術方面的援助。
過去四百年,
臺灣與荷蘭、英國、法國、日本、美國等歷史上的海上強權有過千絲萬縷的深遠關係。
海洋文化與西方價值觀的合於一身,如今仍可在臺灣風土中見到。
日本、荷蘭、法國、蘇格蘭、英格蘭、加拿大、美國等各國形形色色的遺風和影響熔於一爐,協助促進並主導臺灣的發展。
過去四百年裡,臺灣有著豐富殖民過去與獨特海上活動傳統而充滿活力、吸引多種文化匯聚於一身的地方。
從海洋到島嶼,臺灣的歷史亙古綿長
數百年來,臺灣的地理位置和獨特歷史,
塑造了臺灣鮮明的主體性、文化、價值觀,
透過史學家蔡石山在《海洋臺灣》的精彩描述,
一窺這幾百年來臺灣的演變,
鉅細靡遺地呈現這段歷史的曲折起伏。
從歷史看臺灣與海洋的關係
距亞洲大陸一百多公里的臺灣島,
數百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地商人、移民、海盜與軍事謀畫者輻輳之地。
中國有著排外的長期傳統,
相對的,臺灣則有與遠近其他航海民族互動(包括敵意與友善的互動)的漫長歷史。
《海洋臺灣》充斥外國冒險家到臺灣的迷人故事,
重現了在不同海洋文化與價值觀匯聚臺灣的衝擊之下,
臺灣原住民的悲歌,中式帆船貿易、強大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英國鴉片商和蘇格蘭茶商、耶穌會神父和長老會傳教士、日本殖民統治者、美國援臺官員的人、事、物。
作者:蔡石山
科技部特派講座教授。曾任教於臺灣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柏克萊分校、阿肯色大學、交通大學,以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身分任教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國立大學,並曾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客座資深研究員。除了寫過多篇以明朝海上探險和華僑為題的文章,另著有11本書(7本英文、4本中文),包括《李登輝與台灣的主體性追求》、《明代的女人》、《永樂皇帝》、《海洋臺灣》等書。
譯者: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太平天國之秋》等。
表格、插圖一覽表
誌謝
第一章 導論
臺灣一名的由來
臺灣與其他海洋國家
競奪臺灣
第二章 十七世紀統治臺灣者──荷蘭人、西班牙人、鄭成功
荷蘭人在臺殖民
西班牙人到來
荷蘭人挑戰西班牙威權
將近四十年的荷蘭統治
荷蘭傳教士
賺大錢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鄭芝龍、鄭成功等海盜登場
第三章 貿易網──臺灣、東南亞、中國沿海
鄭成功治下的臺灣
清朝治下的臺灣
海盜橫行臺灣
第四章 英國人在臺灣的足跡──領事館、商行、長老會教堂
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國人重返臺灣
臺灣開放通商
英國長老會傳教士來臺
臺灣的大宗商品引來英國商人
英國人在臺設領事館
第五章 戰略要地──法國攻臺之役
法國人與臺灣的早期接觸
中法戰爭
法國艦隊入侵北臺灣
法國封鎖臺灣
孤拔的遺產
第六章 姍姍來遲的美國人
美國人早期對臺的了解
培里與美國人試圖殖民臺灣的舉動
美商受樟腦吸引來臺
臺灣沿海的美國炮艇和失事船
李仙得將軍在臺足跡
田貝的來臺之行
兩位哈佛畢業生掌理臺灣關務
第七章 日本帝國的根基──拓殖臺灣
日本早期對臺的關注
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
臺灣抗日運動
後藤新平:臺灣民政長官
財閥的到來
同化不代表平等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臺灣──從殖民地變成避難所
日本在臺的殖民教育
日本戰爭機器裡的螺絲釘
臺灣人赴戰區工作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日本進攻東南亞的跳板
臺籍日本兵
戰俘
苦難結束
第九章 戰後臺灣──美國勢力和影響力日增
美國擱置決定臺灣的歸屬
二二八屠殺
臺灣獨立運動
韓戰與臺灣的命運
美援
臺灣成為美國的反共盟邦
金門危機與美國對臺政策
新美中臺三角關係的形成
吉米‧卡特與臺斷交
臺灣關係法
美國與臺灣的民主化
臺、美關係降溫
美國的「模糊政策」
參考書目
索引
金德芳、張格物
國際知名的兩岸問題專家、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蔡氏旁徵博引,利用了從古至今中文、日文、歐洲語文的浩瀚資料,為一個經由海上接觸塑造成形的海島社會,寫下獨一無二的歷史。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克學院臺灣問題專家張格物(Murray A. Rubinstein)
這一獨特而重要的著作——說明全球史的絕佳範例——從更廣闊世界史的角度,探討臺灣史。
第一章 導 論
臺灣一名的由來
在歐洲,1648年的韋斯特發利亞條約認可了現代國家的主權觀念。在東亞,中、日、韓、臺、越南諸國,則進入有著與歐洲大不相同之歷史背景的現代時期。這些東亞國家地理位置相近,同受佛教與儒家影響,因而在文化和體制上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在國家形成和文化聚合上,各有自己的獨特模式。
中國史籍記載,西元前108年,漢朝征服朝鮮半島北部,設立樂浪郡。中國對當地的影響,包括文字、貨幣制度、稻米文化、政治體制,一直持續到西元313年本土部落王國高句麗將漢人趕到滿洲內陸深處為止。
西元前2世紀的大部分期間(至西元前111年為止),越南北部由名叫南越國的漢人叛離政權統治,涵蓋紅河三角洲地區。此後,採行漢字、儒家學說、中國官僚制度的越南北部,被併入中華帝國千餘年,直到西元939年為止;西元1407至1427年間,又短暫併入明朝版圖。
在聖德太子治下(573~621),日本開始襲取中國政府的律令和術語(但非本質和根本原則),襲取中國思想與藝術的基本精神。日本以兼容並蓄的原則襲取中國文化,因此得以在其整個歷史演變過程,在種族、語言、習俗上保持有別於中國的獨立特性。
臺灣的情況則稍有不同。
雖然臺灣島與大陸只隔著一道一百多英里寬的海峽,但中國對臺灣的影響,要到十七世紀下半葉才可明顯察覺到,而這與一般人對中臺關係史的錯誤認知其實大相逕庭。此外,中國文化傳布到臺灣的過程中,不斷遭遇來自更大海洋世界之別種文化的抗衡。
1644年,滿人入主中國,創建清朝,國勢於1800年左右達到巔峰,隨後逐漸衰落。在日本,1603年,軍事政權「德川幕府」建立封建國家,不久採行鎖國政策,除了讓中國人、荷蘭人前來,與外界斷絕往來,直到一八五四年才改弦更張。明治維新(1868)三十年後,日本一躍而成強大、統一的現代國家。韓國在李氏王朝(1392~1910)期間一直是個「隱士王國」,頑強抗拒西方的影響,但1894至1945年間卻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經過三十年內戰和王朝對峙,越南於1673年分裂為安南、東京、交趾支那三國,最後淪為法國殖民地。1648年,臺灣落入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手,該公司以臺灣島為中國絲織品和瓷器、日本銀和銅、東南亞香料的配銷中心,獲利豐厚。但接下來的三百五十年期間,隨著外部強權一再入侵臺灣島,臺灣史成為動亂頻頻的歷史。
16世紀之前,臺灣島上的住民是一些未與其他民族(包括中國人)有接觸或貿易往來的原住民部落。這得歸因於島上天然資源豐富,以及孤懸海外的地理位置。中國人從8世紀起就活躍於沿海航運和對外貿易,但中國的舢舨和貨運帆船往返於東南亞、南亞時,總是盡可能緊貼著中國沿海航行。因此,除了12世紀時開始有漢人漁民定居於澎湖,除了蒙古帝國曾在該地設置一軍事基地,中國商人和水手鮮少踏上臺灣的土地。事實上,在17世紀結束之前,這個島的存在,中國文獻都很少提到。臺灣首次為中國人所認知到時,中國人是以流求之類名字指稱該島。《隋史》(589~618)和《宋史》(960~1279)裡就出現「流求」一名。但這些名字的使用太模糊,太多變,因而最終未沿用下來。現代時期最常用來指稱此島的兩個名稱,福爾摩沙和臺灣,都非中國人所創,而是航行海上的歐洲人所造出來。
16世紀末期(很可能是1582),有艘來自澳門的船,因遇暴風雨,船身嚴重受創,而沿著臺灣島岸尋找避難所,航行途中,船上的葡萄牙水手看到島上的自然美景,不由得讚嘆Ilha Formosa!(美麗島)。船上有位名叫林斯霍登(Linschotten)的荷蘭軍官,迅即將此名寫在其海圖上,給了此島第一個名字。接著,1597年左右,地圖繪製者洛斯‧里奧斯‧科羅內爾(Los Rios Coronel)繪出第一張臺灣詳圖,使西方人開始注意到此島。「臺灣」一名很可能源自17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地首府大員(Tayouan)。大員位在今日臺南市瀕海行政區安平境內,當地人把Tayouan唸作“Tai-wan”,使荷蘭人取的這個名字從此保留下來。中國人跟著把這島叫作Taiwan,從而使這一地名的由來湮沒不明。一如華盛頓年幼時砍櫻桃樹然後坦承自己所為那則流傳甚廣但令人存疑的說法,「臺灣」一名源自中國語這則說法,儘管有鐵證予以駁斥,如今仍廣為中國人所認同。在民族主義高張的年代,臺北的國民政府和北京的共產政權都選擇在學校教育裡反覆灌輸此一語源上的虛構說法。
直到17世紀,臺灣仍是無主之地。中世紀中國人可能已知此島的存在,且到了16世紀末期時,島上除了原住民,已住有少數漢人,主要是漁民、走投無路的難民、海盜。但臺灣絕未納入大明帝國(1368~1644)的版圖,中國人既無興趣,也無必要,去介入一個島上居民普遍未開化的遙遠島嶼。凡是鑽研過明朝檔案(包括《明實錄》)的學者,都可證明「臺灣」一名從未出現於整個明朝期間。要到1683年9月8日,中國才第一次提出臺灣為其領土的主張。要到16世紀快結束,島上三個供漁民取得淡水和食物的補給站(北港、基隆、淡水),變成中國亡命之徒和叛徒盤踞的海盜據點時,中國才開始對臺灣感興趣,開始與臺灣接觸。1574年版的《明實錄》稱這些亡命之徒是「東番」。這些事全發生於荷蘭人在島上建要塞、倉庫、教堂、政府機關之前約五十年。中國有關臺灣的第一份可信的歷史文獻,乃是陳第根據個人實地考察臺灣的海盜活動寫成的《東番記》(1603)。研讀過兵法的福建人陳第,1601年冬步入62歲年紀時,隨明朝總兵沈有容前來追剿當時正避難於臺灣的倭寇。
在當前臺灣應與中國統一或保持獨立這個情緒性問題的爭辯中,主張統一者常援引陳第的著作,辯稱東番的土地屬於明朝。這一論點頗為常見,且看來頗能打動人,但追根究柢既無根據,且流於淺薄。沈有容追剿倭寇,雖曾挺進這個以原住民部落為主要居民的島嶼,卻只進入一次,且不久就撤走。沈有容撤走後,明朝未留下部隊駐守。此外,後來荷蘭人入主時,中國人面對這些白皮膚的歐洲「番人」將島上原住民,還有當時住在島上的少數漢人,都納入管轄,並未出手制止。事實上,提供誘因(包括現金、水牛、免費搭乘荷蘭船),誘使更多漢人定居島上者,乃是荷蘭人。但荷蘭的殖民者未找日本人前來島上拓殖,乃是因為日本九州爆發反基督教運動,導致一百二十名傳教士和日本基督教徒於1622年遭處死,因為一連串貿易糾紛,導致日本船長濱田彌兵衛於1628年夏曾試圖傷害荷蘭臺灣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和其幼兒勞倫斯‧奴易茲(Laurens Nuyts)。
荷蘭統治臺灣三十八年期間(1624~1662),將此島作為其亞洲貿易的貨物集散地,藉此將其亞洲貿易與其全球商業網連結。荷蘭地理學家腓力普‧梅(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進行了臺灣首次的土地測量。荷蘭新教傳教士將基督教和拉丁文傳給島上的原住民,進而將臺灣帶進有歷史的時期(詳見第二章)。與此同時,西班牙人也在北臺灣建立一聚落,挑戰荷蘭人對亞洲貿易的支配。1642年,荷蘭人將西班牙對手逐出臺灣,繼續在臺灣執行其卓有成效的傳教活動和繁榮貿易。但1662年,日本女子所生的鄭成功(1624~1662),率領反清復明志士將荷蘭人趕出臺灣,臺灣的荷蘭化隨之戛然而止。鄭成功於1662年6月壯年早逝之後,臺灣的鄭氏政權仍積極與日本、東南亞公開商業往來和與中國暗中買賣。為餵飽軍隊,臺灣貿易船載著中國、越南東京的絲織品、日本的銀、銅、暹邏的黃金,到東南亞換取量多又較便宜的米。派系鬥爭削弱了鄭氏統治家族,在澎湖一場慘敗之後,鄭家艦隊遭殲滅,鄭成功孫子於1683年9月8日正式向滿清皇帝投降。
有很長一段時間,清廷搞不定該如何處置臺灣這個「既險又遠」的島。事實上,清廷甚至曾想說服荷蘭人買回臺灣,但幫清廷打敗鄭軍的荷蘭人婉拒這提議。1895年,清廷看出就要敗於日本人之手時,決定趁損失不大時早早收手。清廷再度斷定,繼續抓著這個島不划算,因此主動向英國兜售臺灣。但英國首相羅茲貝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和外相慶伯利勛爵(Lord Kimberley)兩度拒絕清廷的提議。最後,1895年,清廷將臺灣割讓日本,完全不顧臺灣住民的心願。
臺灣之從芒刺在背的威脅,轉變為國際政治棋局上可有可無的卒子,始於1684年5月27日清廷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之時。臺灣府署仍設在荷蘭人原建普羅民遮城的地方。1685年,康熙皇帝(1662~1722在位)採取一連串措施,以恢復大陸與臺灣的海上貿易。每年有數百艘中式帆船,利用這一商機,載運稻米、糖、花生油、鹿皮、靛藍染料、大麻,到廈門、福州、泉州、寧波、上海,乃至華北的天津港。稻米、花生油、靛藍染料在中國境內賣掉,糖與鹿皮則通常轉銷日本。駛往臺灣的中式帆船,往往載運棉布(南京棉布)、銀、鐵器、草藥,但大部分只裝著壓艙物前來。中式帆船的船東大部分來自閩南,但也有來自浙江、江蘇、華北、東南亞的商船參與臺灣貿易。十八世紀初期,臺灣府境內成立三個商業行會(臺灣話稱「郊」),以利商品買賣和其他生意往來(詳見第三章)。
臺灣與其他海洋國家
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資源,臺灣很快就恢復其在荷蘭人於17世紀初期所開創的亞洲海上貿易網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臺灣與大陸貿易巔峰時,每年有一千多艘中式帆船來臺。但到了1850年,更大、更快、更有效率的歐美汽船,包括來自英、法、普魯士、丹麥、葡萄牙、祕魯的汽船,已取代較小、較慢、風險較大的中式帆船,肩負起載運臺灣貨橫越凶險臺灣海峽的任務。然後,西方的海上商人把源源不斷的現金和經商本事帶到這亞熱帶島嶼,協助打破官府對樟腦之類產品的專賣(專賣制度助長臺灣的海上劫掠和走私)。美國商行,例如羅賓內(Robinet)、奈伊(Nye)、威廉士(Williams),英國商行,例如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顛地(Dent)、怡記(Elles),定期發船到淡水、基隆、高雄、臺灣府(今臺南)。1855年,美國商人花四萬五千美元改善高雄港口設施,英國籍的燈塔管理員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則在臺灣各大港口設置並維護照明系統。在淡水河口上游十八公里處,緊鄰臺北城北城牆邊,約二十名外國商人──最著名者是德國人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蘇格蘭人約翰‧陶德(John Dodd)、美國人法蘭克‧卡斯(Frank Cass)──替大稻埕碼頭區建造了堤防以防氾濫。他們建造了一處「寬敞舒適」的俱樂部會所,開了幾間店鋪,擔任洋行在臺灣各大港的商業代理人。在今日的貴德街,仍保留有幾棟西式建築。
洋商賣鴉片給島民,利用賣得的錢買茶和樟腦外銷,獲取巨額利潤,但他們也帶臺灣人認識現代的銀行業、商業管理、國際貿易。貿易糾紛的確時有所聞;而且中國有一套涵蓋商業與行政事務的複雜法律傳統,至少書面上有明文記載。但中國法律主要用於刑罰,且施行嚴酷,幾未顧及程序正義和公正,結果就是中國法律在島民眼中形同具文。中國的集權社會──或過去所謂的「東方」社會──貶抑競爭與創新,未能創造出現代經濟體制,認為老百姓無權與官員協商;另一方面,臺灣住民與行走海上的歐、美人來往已久,因此熟悉法律、競爭、個人私利這些原則。事實上,臺灣人把大稻埕的淡水河沿岸稱作「外國人」居留區,1921年,臺灣知識分子,就是在這裡,在慈善家林獻堂(1881~1956)和名醫蔣渭水(1891~1931)領導下,組成臺灣文化協會,推動臺灣文化。
至今仍讓歷史學界莫衷一是的問題,乃是臺灣是否在清朝兩百一十二年統治下被改造為「東方」社會,或臺灣已奮力擺脫中國封閉內向的惰性,發展出外向開放的海洋社會。在這問題能得到滿意答覆之前,我們得強調一樁事實,在清朝兩百年的法理統治期間,臺灣大部分地區從未納入北京中央的實質管轄。作為一地理實體,臺灣的孤懸海外,地處偏遠,使島民不致染上中國對龐然威權與帝國體制的偏愛。皇帝的絕對威權,因從大陸派來的少數官員的貪腐無能,因邊陲島民不受管束的性格,而更進一步受到削弱。島民的確習得儒家倫理,且拜道觀佛寺,在道觀佛寺行中國習俗和禮儀。島上有些上層人士,不管是出於不由自主或出於共同信念,也認同高高在上之中央官員的價值觀。他們習儒家典籍,參加科考,一旦榜上有名,即成為鄉紳,躋身臺灣上流社會。但這一「涓滴細流般」的漢化,對一般人民影響極有限,高高在上的清廷官員,最終未能在根本上將臺灣轉化為真正的「東方式」中國社會。
傳統中國社會向來推崇穩定與和諧,尊古,但不鼓勵開發資源。不過,來自閩、粵的移民,冒險渡過危險的臺灣海峽,深入蠻荒,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自由生活,擺脫加諸他們的嚴格規範,想不受壓抑的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因此,邊疆區臺灣人常違抗清朝當局,糾眾反抗不合理的束縛、官僚的掠奪、帝國的控制。晚至1836年時,嘉義縣、彰化縣的清朝官員仍苦於臺灣鄉間治理的棘手。從1684至1895年,共有一百五十九場大亂,從1767至1887年間,據稱有五十七場武裝衝突。此外,嘉慶年間(1796~1820),惡名昭彰的福建海盜頭子蔡牽(?~1809),糾集一幫海盜,1804年入侵沿海城鎮鹿港。兩年後,他的手下摧毀清廷駐紮臺北的整個兵力(當時駐紮於淡水河岸的艋舺區)。蔡牽在臺灣宣告稱王,建元「光明」,封鎖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海上交通。接下來兩年,蔡牽形同臺灣的統治者,向每艘經過臺灣海峽的船隻強索「保護費」。難怪清朝官方文獻寫道:「臺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劉銘傳將軍出任臺灣首任巡撫期間(1885~1891),試圖將土地稅一年總收入由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銀兩再往上大大提升。但島民,特別是有錢氏族(大租戶)和土地開發者(小租戶),激烈反對。1888年,臺灣省政府收到的土地稅,遠低於劉銘傳所預計的六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劉氏的財政短缺,與政府管轄權的有限有密切關係,乃是臺灣半自治狀態的副產品。要等日本殖民政府徹底測量土地,大幅改革土地稅,才能扭轉這局面。
劉銘傳在基隆設置現代機器以開採煤礦,在北臺灣鋪設電燈,在臺北地區建造了約22公里長的新鐵路,設立電報總局。但革新舉措不夠連貫,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街道漫天灰塵,彎彎曲曲。事實上,劉銘傳得靠關稅收入支應其現代化工程的開銷,而在1888至1895年間,一年關稅收入平均是一百零八萬四千三百六十四兩。清皇帝不放心由中國官員獨掌海關事務,因此不得不雇請外國人掌理通商口岸的關稅收繳。最終是外國籍的稅務司協助提高當地生產,發展貿易,進而產生龐大海關稅收。這些外籍稅務司人數不少,犖犖大者有派駐淡水海關的德國人夏德(Friedrich Hirth)、派駐淡水、基隆海關的美國人馬士(Hosea B. Morse)、派駐南福爾摩沙海關的英國人孟國美(P.H.S. Montgomery)、派駐臺南、高雄海關的美國人威廉‧史品尼(William F. Spinney)。清廷渴求穩定,試圖將其普世性的律法和體制用在遙遠而危險的臺灣上,但派駐臺灣的清朝官員發覺欲使這邊陲島嶼穩定、和諧並不容易。清廷認為臺灣理該歸其統治,且欲維繫住這看法,但事實證明那是過時且魯莽的舉動。最後,清廷沒有且未能在領土、司法或財政上將臺灣完全納入管轄。
只要臺灣因地理因素和歷史條件而繼續作為海上邊陲地區,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基本差異就不會消失。地理上來看,危險的臺灣海峽構成一道天然屏障,將中國主流文化與臺灣的邊疆拓荒者隔開。臺灣拓荒者得適應難以掌控的環境、濕熱的氣候、熱帶疾病、無邊無際的沼澤、無法翻越的高山、野獸、颱風、地震、原住民。因此,中國文化雖傳到這島上,但臺灣予以修正,將其發展成具有獨特臺灣特色的文化。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期間,臺灣是野蠻與文明的交會之地。清廷的管轄範圍幾乎只限於城牆內,因此,臺灣的拓荒農民與原住民打交道時帶著武器。甚至在漢人移民內部,族群對立也司空見慣。例如河洛人與客家人不斷為搶地和水而械鬥。河洛人裡最大的兩個族群漳州人和泉州人,其宗族仇恨往往升高為激烈的地區性械鬥。
這類見諸史籍的衝突多達數百件,使臺灣不適於作為研究所謂明清「巨區」(macroregion)的對象。相對的,由於臺灣與在海上活動的歐洲人、東南亞人、沿海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有深遠的關聯,臺灣反倒是研究全球海上活動史的理想案例。船難和其他暴力事件,以及始終不減的煤、茶葉、淡水、糧食補給需求,往往使這座島受到海上強權的注意。眾所周知的,美國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於1853至1854年那趟打開日本門戶的歷史性航行期間,曾建議將臺灣納為美國的「保護地」,因為誠如培里向總統米拉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所報告的,「這座重要島嶼(臺灣),名義上是中國一省,實際上是獨立之身。」其他具有見識的美國人,例如商人吉頓‧奈伊(Gideon Nye)、傳教士彼得‧伯嘉(Peter Parker, 1804-1888)、外交官湯森德‧赫利思(Townsend Harris, 1807-1878),也建議以一千萬元現金「直接買下這島」(詳見第六章)。早在1825年時,就有英格蘭商人前來基隆購買樟腦,當時臺灣是全球最大的樟腦產地。1842年,兩艘英格蘭船在基隆港外失事,倖存的一百九十七名水手遭處決。賽門‧隆(Simon Long)指出,英格蘭「一度考慮將臺灣納為類似澳洲的罪犯流放地」。後來,1868年,英格蘭為了樟腦官賣問題派砲艇到臺灣(詳見第四章)。
有了砲艇和眾多條約上明訂之權利的保護,外籍傳教士才敢再放心前來臺灣傳播基督教福音。這時,距荷蘭、西班牙傳教士開始在臺積極傳教,已過了將近兩百年。歐洲人第一波傳播基督教的行動,因為鄭成功的殘暴作風而悲慘中止,但第二波基督教傳教活動,雖然一開始困難重重,最終卻獲致長遠的成功。在英格蘭長老教會支持下,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醫生、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和他們大無畏的同僚前來臺灣,從山村到海鎮向臺灣人傳播基督教福音。1885年時,他們已在中臺灣、南臺灣建立三十五座長老會教堂。在這期間,馬偕(George L. Mackay)醫生在加拿大長老教會支持下,也已在北臺灣建立二十座與喀爾文派神學完全契合的禮拜堂。這些英、加籍傳教團,加上英、美人的貿易活動,不只將臺灣帶進汽輪時代,還改善了島上運輸、通訊、醫療、教育方面的基礎設施,從而使臺灣成為全球海上貿易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把臺灣推進現代世界,使臺灣比中國大陸任何省分都進步了數十年。
到19世紀中葉時,中國已因為紛至沓來的外力入侵和帶來嚴重破壞的太平天國之亂摧殘,衰弱不堪,中國社會以積重難返之勢漸漸墮入衰落的深淵。清帝國的衰退始於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的慘敗。十九世紀下半葉期間,清帝國解體之勢愈來愈快,最終失去幾乎所有緩衝國和戰略要地,包括越南與廣州灣落入法國之手;臺灣與韓國落入日本之手;膠州灣(山東半島附近)落入德國之手;香港、九龍、西藏落入英國之手;遼東半島與蒙古落入俄國之手。1874年,日本派約三千六百人的部隊遠征臺灣西南海岸,以教訓三年前殺害五十四名遭船難琉球船民的臺灣原住民。十年後的1884年,法國占領澎湖和淡水、基隆,封鎖臺灣海峽將近一年。法國封鎖臺灣期間(詳見第五章),北京的決策者終於理解到,凡是掌控臺灣者,都能嚴重威脅大陸。因此,他們於一八八五年將臺灣升格為省。接下來四任巡撫,靠主要來自臺灣外貿收入的資金,做了些枝微末節的改革。然後,1894至1895年,國庫空虛而政治停滯的中國,因朝鮮問題與國力蒸蒸日上的日本交戰,結果慘敗,被迫簽署馬關條約,臺灣與澎湖因此割讓日本。
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日軍殘酷鎮壓臺灣人堅決而持久的反抗。但殺了一萬多名臺灣人後,日本殖民統治者改弦更張,改以懷柔政策拉攏臺灣民心。1898年,東京指派醫生後藤新平(1857~1929)為臺灣民政長官,開始一連串改革。後藤撤掉憲兵隊,換上正規警察,採用「保甲」制度以滲透進本地鄉鎮,為島上的菁英階層提供經濟、教育機會。後藤在臺任職期間(1898~1906)成功平息了島民的敵視心態,大大提升島民的生活水平。臺灣總督府還進行了地籍調查和人口普查,1899年設立臺灣銀行。地籍調查記錄了先前未登錄於政府課稅清冊上的六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四英畝土地。因此,臺灣的土地稅收從1903年的九十二萬日圓增加為1905年的兩百九十八萬日圓,增加了兩倍。
土地一旦成為商品,日本財閥立即入侵臺灣市場。到1926年,已有五百多家日本公司在臺設立事業單位。儘管已確立典型的殖民經濟,殖民政府仍建造了超過六千五百公里長的鐵公路,興築混凝土壩和水庫,開鑿一萬六千公尺長的大圳,以促進灌溉和利用水力發電。在推行這一經濟政策的同時,日本政府找臺灣人協助執行其「南進政策」。臺灣總督府提供補助金鼓勵臺人搬到東南亞種橡膠樹、馬尼拉麻、甘蔗、茶樹,以使日本能取得該地區的原料。臺灣的外貿漸漸擴張,不只涵蓋日本和東北亞,還涵蓋香港和中國沿海。在美軍有效占領中太平洋島嶼,1945年開始不斷轟炸臺灣、日本之前,有二十一家定期船運公司提供臺灣與外界的往來服務(詳見第七章)。
在這期間,日本鼓勵島民說日語、改日本名、「穿、吃、住如日本人」,試圖藉此同化臺人。到1930年,只有百分之十二‧三六的臺人能讀寫日語,但到了一九三七年,這比率成長為百分之三十七‧三八,到1940年則是百分之五十一。但所謂的「皇民化」運動(旨在把臺人改造成日本天皇忠貞子民的運動),就沒這麼成功。到1941年快結束時,五百七十多萬島民中,只有七萬人改漢名為日本名。到1945年日本結束其殖民統治時,只有百分之一‧七的臺灣家庭(百分之二的島民)選擇改日本名。總而言之,大部分臺灣人的確學會說日語,卻不願意拋棄自己的民族身分。
1936年,臺灣總督府設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以利用東南亞的原物料,以與侵華日軍合作。到1942年,該公司已投注資金於三十二項計畫,涵蓋從礦、漁、林、農到畜牧、不動產、營造、運輸、商業的多種產業。數千名臺灣技師和專業人員被派到菲律賓、印尼、越南、海南島、中國東北和其他地方,推動和協助管理這些計畫。諷刺的是在東南亞和中國部分地區,臺灣人被迫與日籍同僚合作,隨之搖身一變成為「暫時的殖民者」。例如臺灣人謝介石曾任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的外交部長,還有些傑出的臺灣人在天津、南京、廣州等日本占領城市和海南島位居要職。
偷襲珍珠港後,東京不只將臺灣有效改造為日軍在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征戰的發動平臺,還有系統的動員臺灣人力、物資,以支持日本戰爭機器的升級。日本招募臺灣志願兵入伍,臺籍軍人、軍屬、護士被派到上海、南京、廣州、婆羅洲、帝汶、西里伯斯島(Celebes)、拉包爾(Rabaul,位於索羅門群島)、新幾內亞、中國東北、西伯利亞、其他許多當時遭日軍占領的地方。二次大戰期間總共有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名臺籍日本兵參戰,據估計有三萬三百零四人死於戰場。此外,有八千多名臺灣少年工被帶到日本,製造轟炸機與神風特攻隊飛機的零件。自1945年9月2日(日本時間9月3日)日軍於東京灣密蘇里號美軍軍艦上正式簽署降書以來,已過了六十多年,但有關臺灣人參加二次大戰的新故事仍繼續在出現(詳見第八章)。倖存的臺籍老兵一般來講避談他們在與盟軍作戰時展露的英勇、殘忍的日本武德。但在二次大戰期間,數十萬臺灣人在血腥的亞洲戰場和戰俘營囚犯身上,留下他們的足跡。
競奪臺灣
對於日本投降,五百五十萬厭倦戰爭的臺灣人普遍歡迎;事實上,已有一些臺灣領袖在9月3日日本將臺灣交給橫濱的盟軍最高統帥後,立即開始鼓吹臺灣獨立。但10月25日,日本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將臺灣連同據估計值二十億美元的日本資產交給國民政府將領陳儀(1883~1950)。日本對臺五十年的統治,就這樣給美國炸彈和美軍終結。此後,臺灣地位一直未定,因為不管是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還是波茨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都未言明臺灣該由誰接收。或許可以說,臺灣人注定要再經歷一次認同危機,一如1895年日本從清廷手中奪得臺灣時他們的祖輩所經歷的,一如1661年鄭成功軍隊趕走荷蘭人時,他們的遙遠先祖所經歷的。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臺灣人對中國人有了新的認知和看法,而在大戰期間,這些認知和看法更為強化。這些新的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加上國民黨為支應國共內戰不斷剝削島上資源的催化,最終於1947年2月28日引爆全島暴動。接下來幾星期,國民黨統治者派兵屠殺了數萬臺灣人。此後,臺灣獨立運動一直從這一民族創傷中汲取養分。
一部分因為華盛頓當局希望讓國民黨繼續與共產黨作戰,一部分為了戰後東亞的安全、穩定考量,1947年時的臺灣,在美國心目中,頂多是第三順位的問題,因此決定不干預國民黨對臺人暴動的殘酷鎮壓。不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1888~1959)未讓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舉行的戰後對日和會(共四十八國參與的會議)。接下來杜勒斯施壓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使日本於1952年4月28八日(日本正式恢復主權的日子)與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別簽訂和約。在這兩份和約中,日本宣布放棄對臺灣、澎湖的「權利、權利根據、要求」,但放棄後的受益人一樣未言明;這兩份條約也未明訂將臺灣主權轉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研國際法的荷蘭前總理范奈格(Andreas van Agt)表示,從法律角度看,這兩份條約使臺灣成為未遭任何獲承認的政治實體占有的「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
范奈格從現今臺灣統獨爭辯的角度解讀這段歷史,指出關於臺灣地位有兩派認知。有些人認為中華民國取得了臺灣,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於1949年敗退臺灣後,中華民國有效占領此島。但范奈格本人表示,這一主張是否吻合臺灣的戰後歷史有待商榷,「因為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期間,社會上一直鬱積著反抗高壓政權的心態和有時突然爆發的反高壓政權行動,以及日益高張的……臺灣主體意識。」另一派主張臺灣處於法律未定狀態。持這看法者通常是認為臺灣人有權決定自己政治未來的主權論者。范奈格引用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在1955年所說的話,指臺灣和澎湖的法理主權不明確且未定。
克里斯多福‧休斯(Christopher Hughes)已指出,「中華民國於1925、1934或1936草擬的憲法中,都未將臺灣列為其一省。」二次大戰期間,掙扎求生的中國共產黨遭國民黨軍隊和日軍困在貧窮的中國西北時,黨主席毛澤東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他想對韓國、臺灣「脫離日本的獨立鬥爭」伸出援手。幾十年後,較好戰的中共卻常傷害臺灣新興民主的情感,一再揚言臺灣若敢更動憲法就要攻打臺灣。美國從未清楚承認中國擁有臺灣主權,不管宣稱擁有臺灣主權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迪恩‧魯斯克(Dean Rusk)於杜魯門當政時擔任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後來在約翰‧甘迺迪、詹森兩位總統當政時出任國務卿。他早在1951年5月就公開支持「兩個中國」政策,稱北京政權是「斯拉夫人扶植的更大型滿洲國」,並因為「臺灣人希望不受外力掌控的重大要求」而保證支持臺灣。國際法教授暨臺獨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寫道:「嚴格來講,福爾摩沙與其人民的國際地位未定。就連1954年12月簽署的美國、國民黨共同防禦條約都避開這問題。」
1954年8月17日,中共大規模砲擊金門之前十七天,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獲美國參院通過之前數個月,奧勒岡州選出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韋恩‧莫爾斯(Wayne Morse, 1900-1974),在有關中、臺問題的政策辯論時,於參院做出如下陳述:
參院主席先生,我認為在世界和平有望之後,福爾摩沙問題在國際法庭得到解決的時刻將會到來,而那會是許多年以後的事,說不定五十年、七十五年、或一百年。那法庭將裁定誰在國際法的規範下有權對福爾摩沙行使領土管轄權和治權。
一如荷蘭前總理范奈格,韋恩‧莫爾斯也是國際法專家,1936年在奧勒岡大學成為當時美國最年輕的法學院院長。1964年投票反對「東京灣決議」(授權總統派兵到越南)的參議員只有兩位,莫爾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政治判斷和法律見解深受同僚和其同胞敬重,特別是越戰期間。莫爾斯關於臺灣前途的預言不管會不會應驗,自他發出那預言以來,臺灣已在許多方面有長足進展。臺灣目前是世上第十九大經濟體,臺灣社會已變得更文明,媒體變得更自由(可能有人會說太自由),政治已走上民主、自由之境,而這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美國在軍事、經濟、教育、技術方面的援助(詳見第九章)。這些進步已賦予臺灣新的認同,迥異於仍受嚴密掌控之共產中國之文化的認同。過去四百年,臺灣與荷蘭、英國、法國、日本、美國等歷史上的海上強權有過千絲萬縷的深遠關係(本書所竭力欲傳達的關係)。海洋文化與西方價值觀的合於一身,如今仍可在臺灣風土──包括從港口到要塞廢墟,從教堂到診所,從地契到地名,從商業、銀行的經營手法,到葬了外籍戰死軍人而幾乎被人遺忘的墓地──的匆匆一瞥中見到。
過去的確存在於臺灣各地。日本人花了八年(1911~1919)建成的十一層樓臺北總統府,自1950年代起一直是臺灣主權的重要象徵。日本人於1925、1928年創立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灣大學,如今仍是亞洲名校,是過去、現在、未來臺灣政治領袖、學者、科學家、工程師的搖籃。從17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到18世紀耶穌會的法籍地圖繪製者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從19世紀蘇格蘭籍茶商約翰‧陶德(John Dodd)、英格蘭籍植物學家羅伯特‧郇和(Robert Swinhoe)、加拿大籍醫生傳教士馬偕、美國籍稅務司馬士,到19、20世紀之交日本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950年代末期美國駐華共同安全分署署長赫樂遜(Wesley C. Haraldson),形形色色的遺風和影響熔於一爐,協助促進並主導臺灣的發展。接下來幾章將詳述臺灣與海洋世界交往的經驗,闡明過去四百年裡,臺灣不只是附屬於復仇心切之中國的一個漢化地區,還是有著豐富殖民過去與獨特海上活動傳統而充滿活力、吸引多種文化匯聚於一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