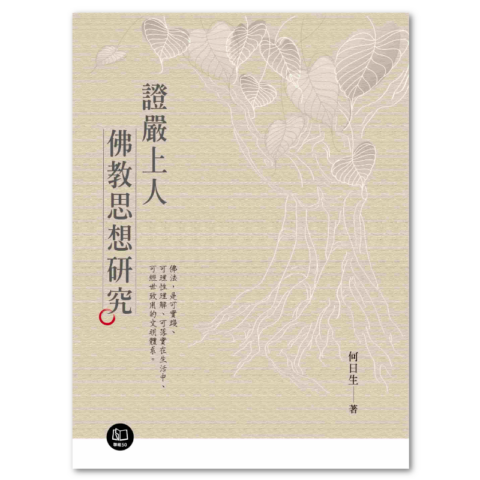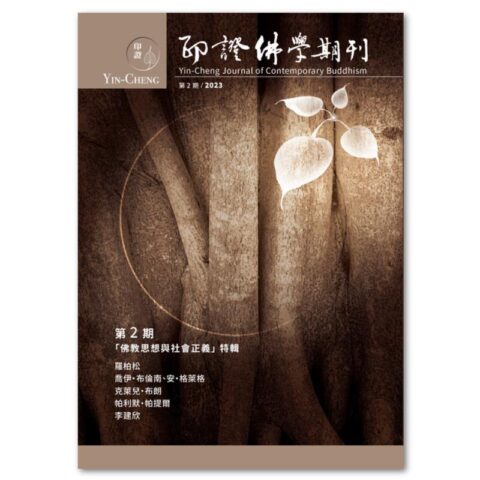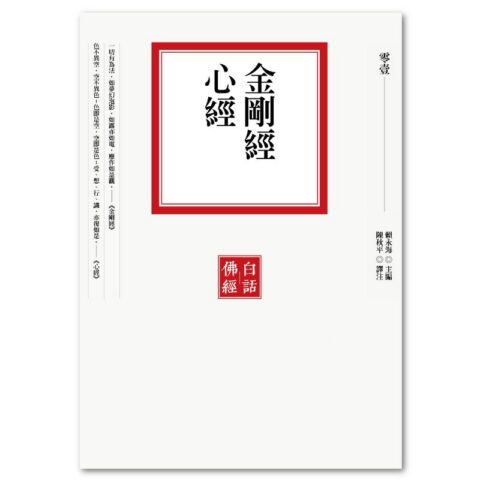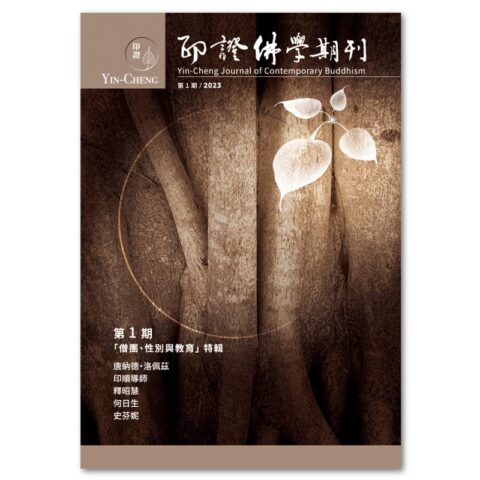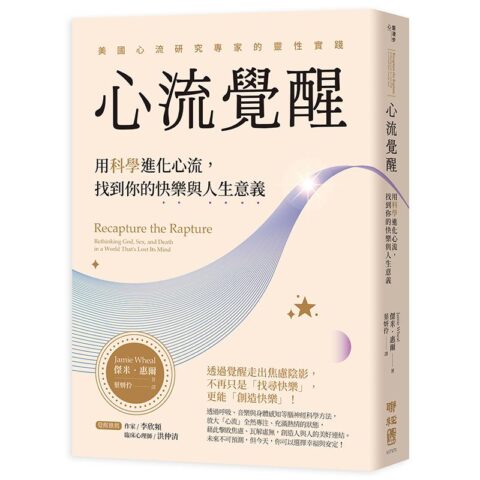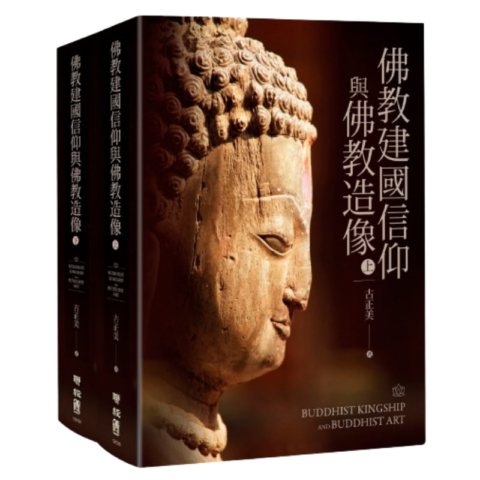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
出版日期:2013-06-06
作者:丁仁傑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8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1664
系列:臺灣研究叢刊
已售完
靈驗、香火、儀式、巡狩、扶鸞、地方性……
《重訪保安村》是《神‧鬼‧祖先》的田野追蹤版,
丁仁傑重訪台南保安村,
結合漢人研究的最新文獻,
將聚落民間信仰的研究延伸,
成為更具有理論整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
保安村是人類學家焦大衛(David Jordan)1960年代末期對台灣西南部進行過村落田野民族誌書寫的地方(中譯本,2012,《神‧鬼‧祖先》,聯經出版),該民族誌中充分討論了有關漢人拜拜、神明會、乩童、問事、賞兵、冥婚、謝土、改運等民間信仰活動背後的社會意涵。
建築在焦大衛的經驗材料和理論視野之上,《重訪保安村》重訪保安村進行田野追蹤,將時間向度納入考量,並結合漢人研究的最新文獻,試圖將聚落民間信仰研究,延伸為更具有理論整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研究中一方面顯示農業村落生活所形成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確實呈現漢人社會的深層認知框架;一方面也顯示出單一聚落宗教活動如何能向上擴張到不同層次而來進行實踐與動員。而當由傳統國家進入現代國家,隨著中央與地方相互扣連方式的改變,不同集體層次間的協商與互動也開始發生轉變,地方社區不再完全是獨立性法人團體,民間信仰由轄境維繫為主逐漸轉變為民族國家內共享之「地方性」創造的主要基石。
《重訪保安村》同時具有民間信仰基本研究命題建構與信仰變遷模式預測的雙重視野,內容則涵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世界裡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靈驗、香火、巡狩、儀式類型、災難治理、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分野與互動等。
作者:丁仁傑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專著有《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1999)、《社會分化與宗教制度變遷》(2004)、《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2009)、《重訪保安村》(2013)。譯有焦大衛(David Jordan)的《神、鬼、祖先》、桑高仁(Steven Sangren)的《漢人的社會邏輯》。
序
序言
第一章、導論
一、關於書名
二、民間信仰的定義問題
民間信仰的定義方式
C.K. Yang的類型學與漢人民間信仰
兩種分析性定義民間信仰的方式
與漢人民間信仰相接近的各種概念範疇與相關定義
三、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文獻回顧
民間信仰的空間範圍與對應的組織層面:祭祀圈
西方人類學家對於台灣民間信仰的討論
同一性與差異性,兼及不同詮釋社群間的互動與並存
基本文化範疇與象徵邏輯
整合性的觀點之一:實踐理論的角度
整合性觀點之二:權力的「文化交結銜接叢」與漢人地方社會的性質
四、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的幾個歷史社會文化向度的說明
以保護型相互關係為主的萬物有靈論
超自然世界已被濃厚的人文化
兩種象徵類比下的重疊性
帝國治理與地方社區自主性互動過程中的民間信仰
五、國家框架遞變下地方社區裡的宗教實踐
中央政府與細胞化的農村社會
不同歷史發展時期中國家與村莊關係的變化
古典國家時期村落的「半法人式位置」與民間信仰
古典國家時期裡的地方菁英與上下層之間的文化流動
六、全書寫作的理論性脈絡
表徵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實踐理論的觀點
實踐場域中的城鄉階序與「中地」
意識型態的有關研究傳統
七、全書寫作的經驗性脈絡
保安村
分析架構中主要經驗性材料的依據
八、各章主要內容
第二章、靈驗︰漢人民間信仰超自然世界的基本象徵結構及其外在顯現
一、前言
二、過去對漢人民間信仰靈驗概念的學術性理解
三、靈驗顯現背後的象徵結構:超越家的界線與進入「結構化」的狀態
漢人民間信仰中不同的超自然範疇
家神與家鬼
結構化
靈驗的顯現:單純性靈驗顯現
四、互動性靈驗顯現:個人或集體與神明間的「交互對等性關係」
互動性靈驗顯現
由個人到社會集體性層次的與神結盟
做靈驗
五、一個關於靈驗現象的異例:大家樂「求明牌」的例子
六、結論
第三章、香火:歷史脈絡中的香火制度及其內涵
一、前言
二、文獻回顧
三、異化
四、香火制度的歷史面向
五、超越性的在地化
分香制度的內涵和性質
漢人社會中的「成神」的概念
地域性之具象化的實現
「滑落差」的概念
超越性的「滑落差」
地方性脈絡中的二度成神
六、結論
第四章、神明階序的結構與展演︰以廣澤尊王巡台為例
一、前言
二、進香、巡狩與遶境:宗教遊行隊伍中的神明階序
三、2009年大陸南安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遊台巡香」
四、宗教階序的建構、神聖權威的承接與靈力的分享
五、漢人民間信仰神明權威階序的結構與展演
階序的作用
地方情境中神明權威的階序性結構
神明權威階序的展演
六、摘要與結論
七、一個實踐理論觀點的補充說明
實踐理論的提出
漢人民間信仰中的神明階序所構成的場域
由實踐理論觀點觀照漢人神明階序
由實踐理論看2009年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的遊台
第五章、社區的集體性通過儀式:漢人民間信仰集體象徵的基本分類
一、前言
二、集體性通過儀式
三、「非參與性的集體性通過儀式」:以「做醮」為例
四、參與性的集體性通過儀式:保安村的例子
五、討論與結論
集體性通過儀式的類型
信仰系統的不同面向與儀式的功能
第六章、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全球─國家─地方」連結脈絡中的民間信仰
一、前言
二、祭祀圈與信仰圈
三、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
四、漢人社會裡的地方性
五、西港刈香的文獻討論與當代現況
西港刈香的文獻
西港刈香的概況
六、西港刈香地方性中的歷史感
七、千歲爺的降臨:一個循環性時間的開始
循環性時間取代固定永恆的歷史起點
千歲爺的靈驗及其將社區予以真確化的作用
對等性層面的真確化之一:做醮以創造「大型地方性」裡的「中心」
對等性層面的真確化之二:王府直接創造出大型地方性裡所需的靈力
八、大型地方性中的路徑與網絡
慶安宮的中心性位置
不同區塊的先後加入
不同區塊加入所形成的新態勢和各庄陣頭的發展
宗教慶典與社區的真確化
大型地方性中的村際網絡
九、「全球─國家─地方」連結脈絡中的大型地方性
中央政府與細胞化的農村社會
不同歷史發展時期中國家與村莊關係的變化
歷史框架變遷下的大型地方性
十、討論與結論
幾個相關的概念
漢人傳統社會的地方性
大型的地方性
大型地方性與現代國家
第七章、地域性民間信仰與教派活動間的分野︰麻豆鸞堂「奧法堂」的例子
一、前言
二、David Jordan與麻豆奧法堂
三、2009年我的再度造訪奧法堂:重新理解奧法堂
四、既有的鸞堂研究
五、討論與分析
「飛鸞」作為一種具有文化特色的「神靈招魂」活動
Bryan Wilson 的教派類型學
非西方社會中的教派的產生
對於奧法堂發展的教派社會學分析
六、摘要與結論
法術型活動氛圍中操控型與改革型行動的建構:宗教的理性化
參加鸞堂之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選擇的盛行化:複雜社會生態中「對應性的可信性」與「反差性的可信性」的相加
本章的限制與未來研究的方向
第八章 結論
一、主旨與摘要
二、由對照中呈現漢人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的界線與性質
三、傳統漢人村落與民間信仰
四、村落進入現代國家與全球化框架
五、與過去各種理論觀點的比較
祭祀圈理論
Watson的標準化理論和Weller的詮釋社群概念
Duara權力的「文化交接銜接叢」的概念
實踐理論
六、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的展望
附錄 災難的降臨與禳除:地方性社區脈絡中的改運與煮油淨宅,保安村的例子
一、導論
二、David Jordan田野民族誌中對於保安村驅邪過程的書寫
三、災難的降臨與禳除:保安村的實例
四、討論與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自序(節錄)
保安村是人類學家焦大衛(David Jordan)1960年代末期對台灣西南部進行過村落田野民族誌書寫的地方(中譯本,2012,《神‧鬼‧祖先》,聯經出版),該民族誌中充分討論了有關漢人拜拜、神明會、乩童、問事、賞兵、冥婚、謝土、改運等民間信仰活動背後的社會意涵。建築在焦大衛的經驗材料和理論視野之上,本書重訪保安村進行田野追蹤,將時間向度納入考量,並結合漢人研究的最新文獻,試圖將聚落民間信仰研究,延伸為更具有理論整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
我在討論中,一方面顯示農業村落生活所形成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確實呈現漢人社會的深層認知框架;一方面也顯示出單一聚落宗教活動如何能向上擴張到不同層次而來進行實踐與動員。而當由傳統國家進入現代國家,隨著中央與地方相互扣連方式的改變,不同集體層次間的協商與互動也開始發生轉變,地方社區不再完全是獨立性法人團體,民間信仰由轄境維繫為主逐漸轉變為民族國家內共享之「地方性」創造的主要基石。
本書同時具有民間信仰基本研究命題建構與信仰變遷模式預測的雙重視野,內容則涵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世界裡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靈驗、香火、儀式、巡狩、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分野與互動等。而在過去,民間信仰經常被看做是傳統文化體系裡的一部分,因此,這也一直被看做是屬於民俗學或人類學的研究範疇。至於社會學,它特別關心「現代性」的進程,以及「傳統」與「現代性」的接合問題,如果說它會對宗教感興趣的話,那不會是在於宗教信仰與象徵本身,而是在於人類的當代生活是否會愈來愈不具有宗教色彩?以及,如果說宗教仍然能與「現代性」共存的話,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興形式?即使當社會學碰觸到民間信仰議題,也會將焦點放在當地域性社會的天然界線逐漸解體和模糊化以後,民間信仰會以什麼樣的傳播或組合模式做為新的介面?簡言之,出於對當代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關心,漢人民間信仰,即使說它涉及到集體生活與權力的面向,很少會是社會學家所關心的重點。
但是,換另一種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是說僅僅把民間信仰看成是聚落界線內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習慣和信仰,而還可以把其看做是屬於人類透過某種象徵性活動,而所產生的一種有著現象學特質的情感狀態,和能產生具體跨越時空或超越時空效果的實踐邏輯,那麼,即使說「地域性」這個性質,仍然會是民間信仰中緊密連帶著的一種屬性,但是民間信仰所能在各種社會網絡和媒介環境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歷久彌新的效應,將不僅是社會學家所能夠研究與分析的主題,甚至於它還是宗教社會學家所必須要加以面對的,既傳統又新興的關鍵性的學術議題。
學界對於漢人民間信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還是出於人類學,問題意識一直擺在︰民間信仰中的象徵與社會組合,是理解傳統漢人社會之人群組合與社會秩序觀的關鍵性環節,因此有其研究上的必要。而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意識,建築在對於漢人社會集體生活之本質的探索,而對這個問題意識所採取的不同分析取徑,其各自的意義,還要被放在更大的對比性的框架裡才會顯現出其各自的獨特性。
整體性的來看,我們發現,人類學家對傳統漢人社會(現代化歷程開始之前的社會)的研究取徑,有的是以村落生活為焦點,有的是以超村落的某些面向為關鍵環節為焦點,舉例來說︰1. 認為農業村落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就是漢人社會的小宇宙,對於一個村落的學術性再現,已經充分表達出漢人社會的全部;2. Skinner的層級性市場與階序性「中地」的理論,認為村落受到其所在市場或政治軍事位置的影響,並非自足的內部系統,一個基本的分析單位也不是村落,而是大約五六個村落所構成的「標準市場城鎮」(standard market town);3. 可能與階序性「中地」理論併在一起來看的觀察視野,這可以包「括祭祀圈理論」(林美容等)和「宗族組織理論」(Freedman、科大衛等)等,分別以「祭祀圈」(族群習慣與宗教儀式層面)或「宗族組織」(血緣與財產共享的組織層面)來解釋漢人地方社會,而且這兩者又可能分別有層級性的構成,進行著相互的連結與支援(如與祭祀圈有關的相互進香關係、主廟子廟進香活動;宗族組織也可能有「地方宗族」與「上層宗族」之別,不同層次間也會有所互動),表面上這兩個理論途徑是和Skinner反其道而行,但事實上只是提出了另外兩種可能是與層級市場關係相平行的人群組合模式,彼此不但不衝突,還可以相互補充;4. 本書沒有多提,但與第一種觀點可以相容的農村的「內捲化」(involution)理論(黃宗智),由農業經濟的觀點來看漢人農村,農村成為一種封閉停滯的生存維生系統,在家庭農場經濟型態中,小單位面積土地上進行集約生產,過多的人口與停滯的技術,永遠無法聚集足夠的剩餘資本來擴大經濟生產規模;5. Duara的「權力『文化交接銜接叢』」的概念,隱然預設了人是權力的動物,而漢人文化傳統裡的文化權力意識形態和社會權力關係網,構成了漢人地方性實踐活動的運作場域,而這個平台也能貫穿於地方與國家之間。
其實,以上的分析觀點,即使有其動態性,但分析視野都還沒有能脫離所謂的對於「古典國家時期」裡的農村位置的定位模式,也就是將國家看成在上的收稅與統治單位,將村落看成是由住民共享但卻又是與國家相對對立的地方自治單位,並將地方菁英看成是資本上下流動過程中的關鍵性環節。但是,當以上這種國家與地方間的關係,以及地方性農業聚落的生存模式和內部權力結構,到了進入「現代國家」以後,會產生什麼樣的轉變?這似乎還亟待以新的視野來加以進行分析性的觀照。
相對於以上人類學對於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傳統,本書是一個從事本土宗教現象研究的社會學家所另闢蹊徑而產生的一個關於「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社會學觀點的『序論』」。本書在扣緊民間信仰由傳統社會過度到現代社會裡的社會位置與社會功能之刻,先刻意避開了漢人社會根本組成與社會連帶性質的討論,也避開了民間信仰的社會變遷的問題,而重新以(或更嚴謹地說,「某一種的」)社會學的觀點,由核心內容(靈驗、香火、通過性儀式、「地方性」建構等)、到邊界(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間的關係與界線),直接進入漢人民間信仰的象徵邏輯,釐清這些信仰中各關鍵要素形成背後的有關環境與歷史框架(靈驗觀的文化特殊性、香火制度的形成、國家框架的遞變、地方環境生態裡的權力關係等),並在將民間信仰當作一種現象學上的特質(如「地方性」),和當作一種農村民眾實踐場域裡的重要溝通平台(階序性「中地」關係中的權力的建構與展演)的前提下,再經由此來說明以這些象徵邏輯為媒介所連結出來的社會關係(祭祀團體、神明會、地方聚落、宮廟法人等)的性質。而經過本書這樣一個「序論」性的分析與說明,也有助於宗教社會學能產生更深厚的基礎和更寬廣的關懷,可以進一步去處理漢人社會基本性質、社會變遷、宗教變遷等等各方面的課題。
當然,也因為本書只是一個基礎性的「序論」,著重點在如何能夠建立基本的有助於分析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概念或工具,至於所創造出來的「工具箱」,如何能夠和其他的理論關懷相扣連或相配合,這還不在本書主要的討論範圍內,而是下一步仍有待繼續擴展與延續的學術性的目標。
至於前面所提到的所謂「某一種的」社會學的觀點,這並不見得一定要與人類學(特別著重文化層面)或民俗學(特別著重地方性的歷史與風俗特徵)間劃清界線,而是說在取法人類學與民俗學既有發現的同時,本書的研究取徑所更為重視的,是將宗教象徵性活動,放在更完整的日常性集體生活的脈絡中;本書也更為重視較為持久性的制度性(不斷重複出現而已成為民眾間共同相互預期裡的一部份)層面;同時,我也會借重M.Weber以來的社會學「理想類型式的」分析工具,而在多方向歸納與演繹的綜合中,嘗試呈現出手段與目的、個體與集體、行動企圖與結構限制等等間更具有辯證性質的社會圖像。
第二章、靈驗︰漢人民間信仰超自然世界的基本象徵結構及其外在顯現
一、前言
靈驗,可以被放在「萬物有靈論」的範疇底下來被考量。我們在導論中曾提到過,研究「萬物有靈論」著名的人類學家Descola所提出的一種「保護型」,或是「階序性的涵攝型」「萬物有靈論」的意象,和漢人社區農業生態裡滋生蔓長的地方性民間信仰,有著某種類似性,這一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本章後面還會談到人群與超自然間的結盟關係,那時相關論點會被看得更清楚。
然而,在漢人社會裡,萬物有靈的概念也曾經過了相當漫長歷史的人文化以及某種程度的系統化,雖然各式各樣有關「自然或超自然界有其靈驗效應」的民間信仰無所不在,但是某種最主要而且也是最具普遍性的靈驗發生的模式,已經在漢人民間社會裡發展得相對成熟而穩定,而在相關系統性討論還不多的情況下,若我們能將這個模式予以具體清楚與更為分析性的加以區別出來,以做為了解漢人民間信仰的一個基礎,這在學術上將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作為本書實質性討論的第一個章節,本章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就理解漢人民間信仰最具普遍性也最具關鍵性的文化概念「靈驗」,進行系統性考察與理論討論。在我們這個基礎性的討論裡,將結構性的鋪陳漢人對於超自然世界主要範疇及範疇之間互動關係的基本假設,並進一步說明了這些假設的引申,會產生何種後續性的宗教實踐與資源動員。由靈驗背後的象徵結構開始,到因靈驗而產生神明與人群的結合,到因此而產生香火與進香的宗教實踐,但因此而出現「地方性」概念裡的時間與空間的建構,這些民間信仰裡的關鍵性環節,彼此環環相扣且來回相互影響,但是漢人民間信仰最根本的起點,是由這一個「相信神明會在人間產生某種效應」(也就是靈驗的基本假定)而開始而向上推演的,因此,關於靈驗觀背後所認定的超自然範疇的類別、性質、這些範疇與個人或人群間的關係、超自然範疇內的類別轉換間所可能會產生的效應等,這幾個部分都是最重要的引發漢人民間信仰後續象徵操作與宗教實踐的基本元素,也是我們想要理解漢人民間信仰運作的最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知識。
過去對漢人超自然世界或靈驗觀的相關研究雖然非常多,本章中利用台灣南部跨時性的田野案例,再有所引申而發展成為更嚴密的「理想類型式」的推論,本章中所採取的這種結構性分析與無隙縫的演繹性邏輯推理的闡述方式,能夠將有關討論奠基在較穩固的立足點上,這構成了本書後續幾章推論上的一個基礎,相信這也能有助於在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社會學知識上,產生某些可能是更具有理論累積性的研究方向。
本章考察的步驟,將先由漢人父系社會的「結構化」原則中,說明超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之間的「相互定義」與「相互再生產」關係,進而說明該超自然象徵結構中,如何內在性的預設了靈驗的存在。接著,我將討論由「單純性靈驗顯現」到「互動性靈驗顯現」的歷程,並討論人與神明之間短期或長期「交互對等性關係」中,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靈驗模式,尤其是社會集體與神明進行長期結盟關係中所建構出來的靈驗觀,是靈驗現象背後特別鮮明的社會學面向。最後,我也將提到關於靈驗生產的問題,以所謂的「做靈驗」為考察焦點,我將揭示出來,社會資源動員如何可能創造出更持續而具感染性的靈驗。
漢人民間信仰中,「靈驗」,那種認為「超自然實體在現實世界裡所展現出來的某種效驗」的想法,在俗民宗教觀念中極為普遍,許多研究漢人民間信仰的西方文獻(如Chau 2006;Baity 1975;Feuchtwang 2001;Sangren 1987)也將「靈驗」或「靈」,視為是理解漢人民間信仰的核心概念。為什麼靈驗在漢人民眾的宗教實踐裡扮演著那麼重要的角色?這背後的歷史或社會原因也許很複雜,不過至少我們注意到,長期以來,漢人地方性的宗教活動雖不斷與儒家、道教和佛教融合,也面臨官方力量的整頓,但它根本的性質,也就是靈驗,即使在加入了許多新內容的情況下,似乎從來沒有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替換掉。
靈驗,接近於宗教學研究中所稱的「巫術」(magic),這可以說是一個在跨文化層次有效的概念。其實在傳統社會,甚至於西方在16世紀以前,宗教與巫術之間的界線一直很模糊(Thomas 1971),大致是在17世紀以後,在基督新教教義的改變下,歷史上才開始出現嚴格劃清宗教與巫術界線的情況。
17世紀開始,新教批評天主教的「聖餐禮」(transubstantiation)具有巫術性。新教認為,上帝在日常生活中是全能與無所不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巫術之做為一種對於神聖性的操控,這是不能放在宗教實踐當中的(Tambiah 1990: 18-19)。新教認為,「巫術,預設了巫師會學習如何去控制自然的力量,而宗教卻不同,它假定著一個這樣的世界,一個自覺性的行動者,透過禱告與祈求,而得以產生了生命的轉向。」(Thomas 1971: 41)。基督新教還進一步建立了關於「禱告」與「魔咒」(spell)的基本區別,而認為前者是真正的宗教,後者是「假宗教」(Tambiah 1990: 19)。靈驗,那種相信人在與超自然溝通後所會產生的效驗,於是便成為了基督新教所排斥的一部分,甚至更進一步,基督新教還宣稱,巫術性的操弄根本就沒有任何效驗,因為對於真神而言,人們是無法對祂有所操弄的(Tambiah 1990: 19-20)。
當一個來自於已經被「完全基督新教化」地區的人,如果說當她(他)在面臨著號稱是「有著高度文明化」的中國時,竟然還發現:「靈驗」是這個地區民眾選擇宗教的主要判準,我們可以想像其當時的心情會是極震撼的,正如Valerie Hansen(〔包偉民譯〕1990: 11-12)回憶到她在臺灣做研究時的「初體驗」時這樣說:
我以前一直以為中國人像我們一樣,是將宗教信仰分門別類的。因為我們西方人總將自
己分成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或新教徒等,因此我想中國人也會是分別信仰佛教、道教或
儒教的……出乎意料的是,我所碰到的所有中國人都並不是這樣將自己歸屬于某一宗
教。而且,就我所知,他們既拜佛寺、道觀、又拜民間的祠廟。……〔他們〕只不過是
在求一個「靈」的神而已。幾年以後,我開始關注對宋代的研究:靈。
其實,靈驗之作為一般庶民大眾的宗教判準,這一件事本身並不值得奇怪。甚至於追根究底來說,比起其他宗教,近代西方社會基督新教的不強調靈驗,或許這才是一個特例。不過,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是,在經過中國文明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與文化過程以後,在廣大的華人地區,地方性的靈驗,已經和中央王朝的權力間產生了獨特的互動模式,不同地區的靈驗間,也一直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競爭關係,甚至於靈驗的象徵符號,也成為了地方社群劃定疆界與資源動員的憑藉,這些和靈驗有關,但也和複雜的「文明化」歷程有關的文化與歷史議題,或許才是學者所最感興趣的。
另一方面,關於漫長歷史中靈驗概念的變化,是學者覺得有需要去加以處理的,考察唐宋年間的歷史,Valerie Hansen(〔包偉民譯〕1990: 1-2)認為,靈驗所攸關的,是一個由自然力量,到市場力量,再到國家力量介入的、複雜的「神明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神明力量」的變化:
在中世紀中國的大地上,遍佈著供奉民間神祇的廟宇。據當時的記載,即便是最偏僻的
村落都有不止一個的祠廟,大城市裡的祠廟更是數以百計。人們向神禱拜,祈求下雨、
盼晴、滅蟲、驅盜、平叛、治病、懷胎生子、預防瘟疫……在這之前,多數地方神祇不
被朝廷所承認,他們只在自己曾經生死斯、死於斯、或任宦作吏於斯的範圍內受到崇祀。
到11世紀末年,朝廷開始向神祇賜額封爵。在當時商業革命的過程中,以前只擁有自然
力量的神祇們。開始擁有了市場力量。而且與從前不同,某些神祇開始不僅受到本地居
民的崇祀,還將影響擴大到了整個中國南方。
由以上片段性的引述看來,靈驗是貫穿漢人民間信仰文化邏輯與社會關係的重要概念,值得做深入考察。不過,奇怪的是,雖然強調了靈驗在漢人信仰世界裡的重要,但過去的研究取向,一種方式是將靈驗視為是固定的自變項,學者僅注意到各廟宇或社區歷史中,因神明靈驗而讓某些信仰和人群關係得以擴展的過程;另一種研究方式是密切注意到靈驗的社會性與歷史面向,譬如說注意到人們會經由活動規模與香客人數來判定神明的靈驗,也會由廟宇背後社區間的歷史關連性來建構靈驗,不過各種研究,事實上對靈驗這一套象徵體系本身的實質內涵,從來沒有認真去加以討論過。
顯然的,既有文獻裡對於靈驗觀的基礎性探討,還留有很大有待開發的討論空間,尤其是對於在漢人文化脈絡裡,靈驗背後的超自然象徵體系是什麼?一般信眾如何生產或創造出各種靈驗?這些靈驗觀又如何無所不在的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和靈驗觀有關的最實質性的議題,過去少有人加以深入探討。
二、過去對漢人民間信仰靈驗概念的學術性理解
靈驗,有一種相對比較性的性質,人們會認為某些神和鬼會比其他的神或鬼更靈(Sangren 2000: 59)。靈驗也是高度社會建構性的,它的證明,常透過信徒的言說或是活動。看似主觀經驗的靈驗,事實上往往是通過祭拜人群的大小、廟宇的大小、捐款的多少、和活動的熱鬧程度而被社會性的定義出來的(陳緯華 2008: 80; Baity 1977: 75; Sangren 2000: 56-7)。靈驗背後,有一種俗民世界「循環論證式的邏輯」:「神明之所以靈驗,是因為有很多人在祭拜祂,為什麼會有很多人祭拜一個神明,是因為祂很靈驗」(Baity 1977: 75)。而這個「循環論證式的邏輯」,在「國家與地方信仰之間的相互正當化」的過程裡同樣也常可以看得到。
簡言之,正如Sangren所說(2000: 56-58),對於祭拜者來說,這一類論證背後的「循環性」,必須要具有著一種「不透明的、壓抑的、和被神秘化的」性質,因為,如果人們注意到了這個「循環性」,靈力的基礎可能就要瓦解了;換句話說,人們必須要把靈歸諸於是來自於超自然的實體,而不能把靈當作是一種社會建構性的產物(雖然實際上是如此),因為,如果人們不能把認知轉向超自然界,超自然的力量就不能夠被引發出「來正當化」那個會產生出它(超自然的力量)的社會集體了(Sangren 2000: 57)。
社會性(人數、多寡、廟宇大小)不是定義靈驗唯一的社會標準,地方性的歷史傳統也是一個重要指標,這主要是因為地方歷史對靈驗產生了某種強化和「真確化」(authentication)的作用。這又可以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指廟宇在分香分靈過程中的地位,會影響民眾對靈驗的認知,因此人們會認為,來自湄洲的北港媽祖或鹿港媽祖,通常就會比輩分較輕的分香分靈廟更具有靈力(Sangren 1987: 213-15);另一方面,某個神明的靈驗也必須被放在地方性歷史傳統中被「真確化」,也就是神明必須在歷史上對於某個社群或地域開展出保護性的公共功績(Sangren 1987: 210-211),才能更被確認其靈驗的真實性。
靈驗,是相對於國家權威的一種中央行政體制所無法控制的力量(Feuchtwang 2001: 84-9);或者換一種角度來說,這是民眾定義出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命」,也就是一種「民命」(mandate of people)的形式(Ahern 1981: 94-95)。圍繞著神明的靈驗,會產生出特定的祭祀團體,這又會產生一個由儀式所劃定出來的集體性疆界。以這種方式所劃定出來的社會群體,彼此間可以有著更為平等的關係,而不同於階序性市場層級裡的關係模式(Feuchtwang 2001: 89)。
學界中只有Sangren(1987, 2000)曾經對靈驗觀本身進行過分析。首先,他先定義出漢人民間信仰的基本元素為「陰與陽(失序與秩序)」,接著他假設「靈」,是能在這種二元性之間的做轉介的力量,這等於是承襲了Dumont(1980)所稱「對相互對反性的更高層次的包含」(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以這種基本認知結構,Sangren就漢人的超自然象徵結構做了各種二元對立性的分析,其中,陰與陽間的相對性是考察重點,而那種可以跨越陰陽間的東西或力量,會以所謂的「靈」來做表徵,當我們說神明或一個東西很靈,是因為他有溝通陰陽或是在陰陽間做轉介的能力(1987: 132-165)。進而,Sangren把這一套結構主義的觀點,和馬克斯主義的分析角度連結在一起,而認為:那種被賦予在神明上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靈),它可以被理解為是關於「象徵符號之關係」的文化邏輯的展現,和關於「社會關係之物質性運作邏輯」的一個外顯的形式(2000: 4)。Sangren的觀點的確幫助我們由某個側面(陰與陽),看到了漢人世界社會關係與象徵符號世界的內在運作邏輯,但是這種極為抽象性的討論,也留下來了太多模稜兩可和未解釋之處,而且,事實上這些分析中對於「靈驗觀」背後更為具體性的象徵內涵,從未真正加以細部對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