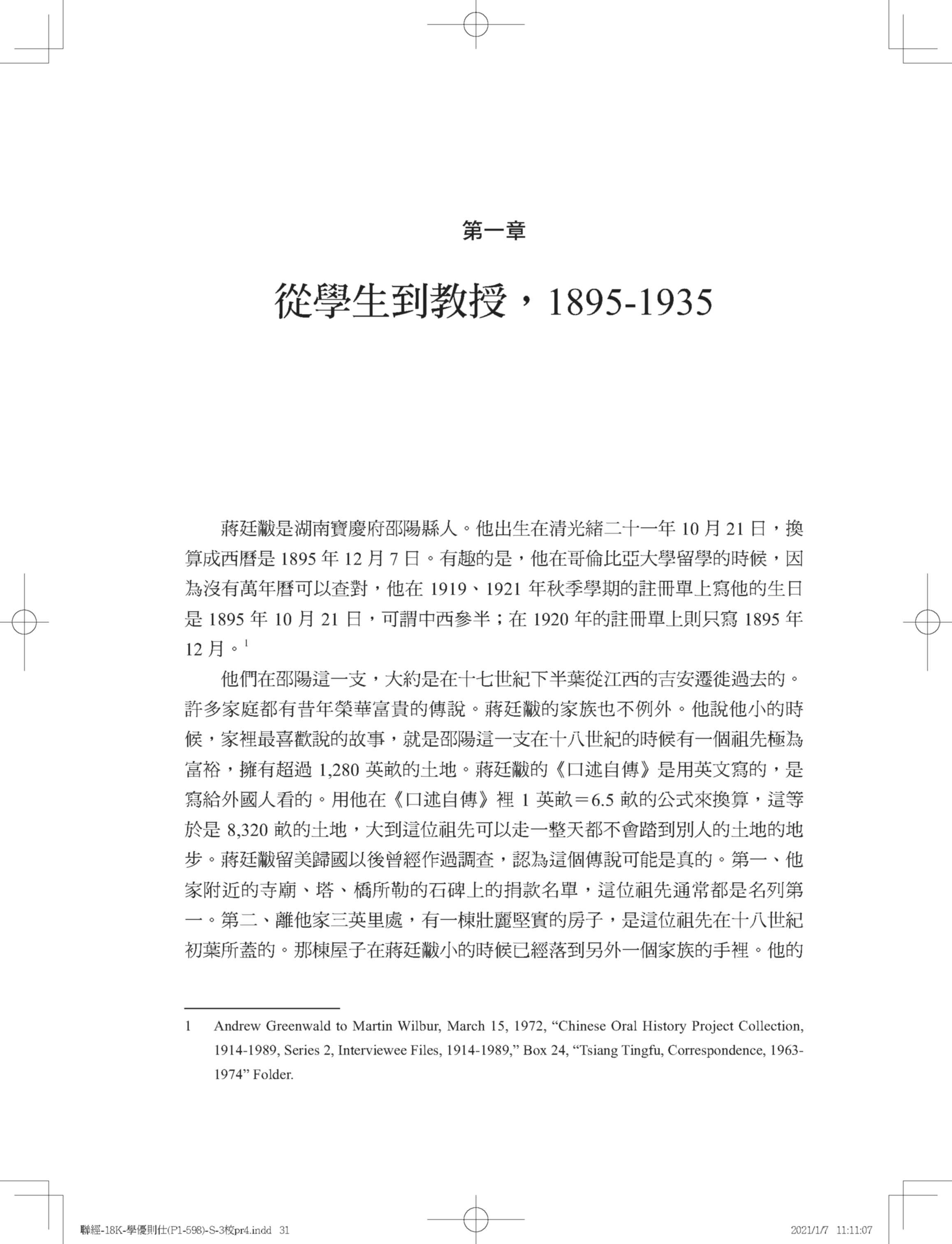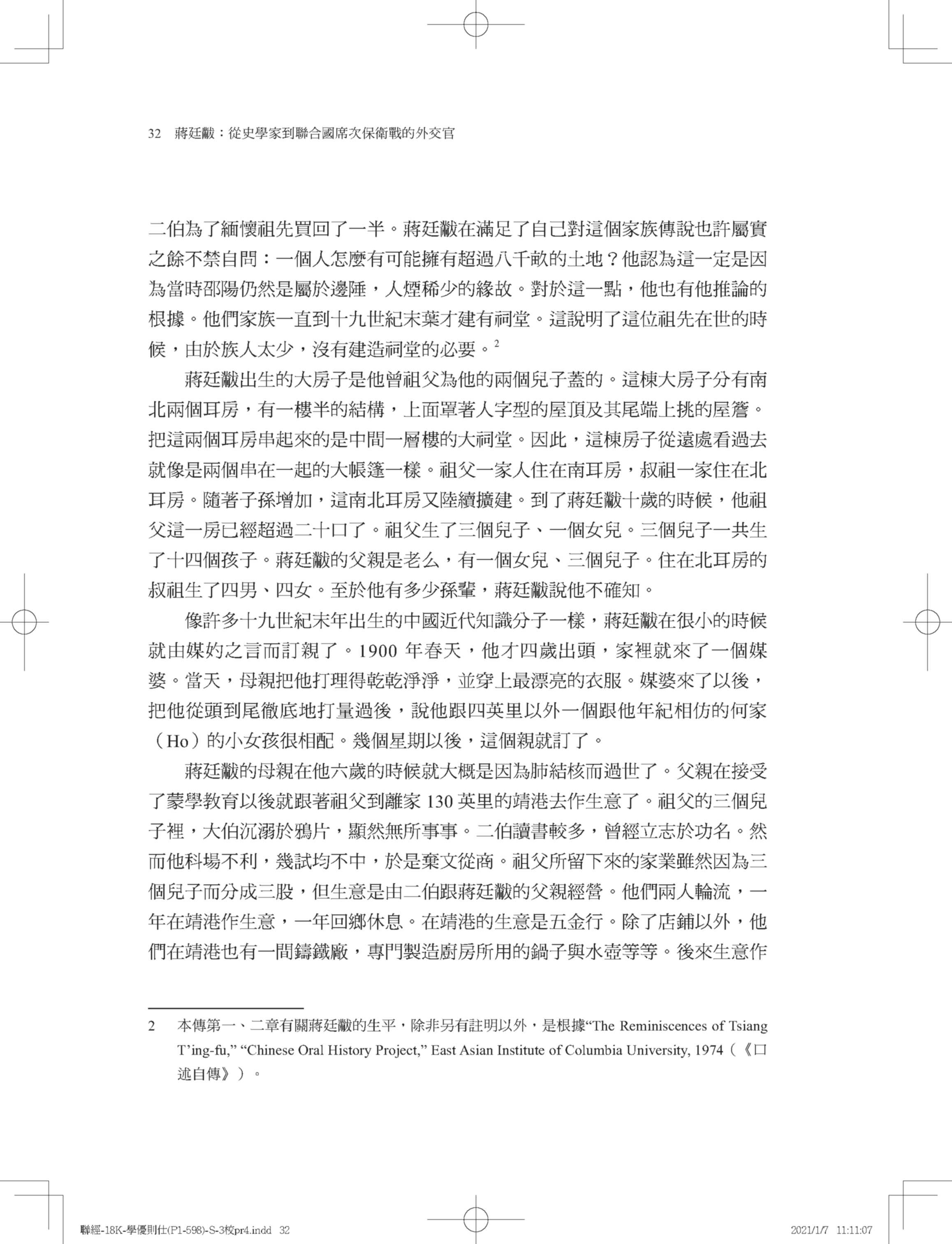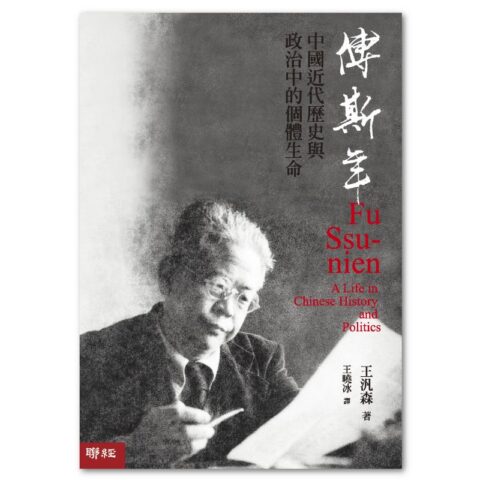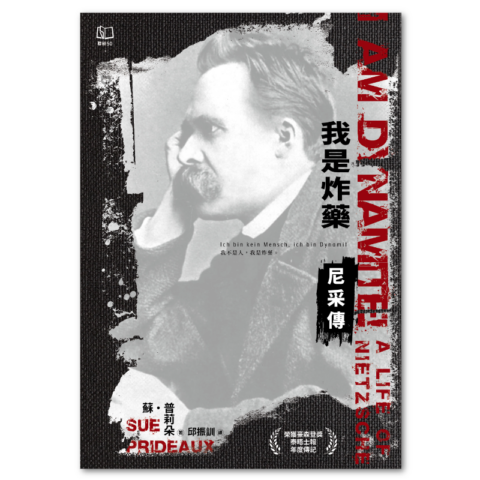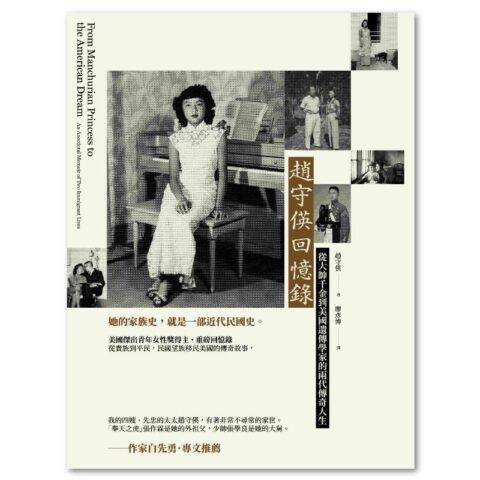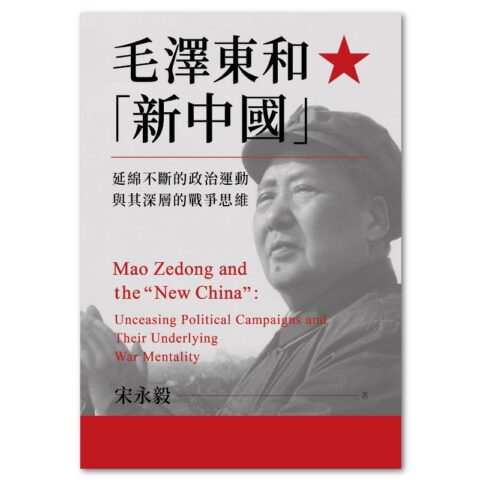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
出版日期:2021-02-04
作者:江勇振
印刷:黑白
裝訂:精裝
頁數:600
開數:18開,長4.5x寬17x高23cm
EAN:9789570856804
尚有庫存
中華民國歷任最久的聯合國大使——蔣廷黻
★ 運用蔣廷黻英文日記(1944-1965)掌握史家從政後半生
★ 直接援引《口述自傳》,修正白色恐怖時期譯本曲筆
「我不喜歡從俗、隨波逐流。我行使我獨立判斷的權利。這個習慣讓我在工作崗位上所付出的勞與憂,都遠超過一般官場上所定義的勞與憂。然而,這樣的態度才能使人生有興味、有挑戰。」——蔣廷黻
「在你從政以後,現代中國毫無疑問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歷史家。……然而,即使如此,我知道作為史家的你,會有史家的視野來意識到你傑出的貢獻。這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美國漢學家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蔣廷黻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學者,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歷任南開大學與清華大學教授。他亦是一位傑出的政論家,評論散見於《大公報》等著名刊物,並與胡適共同創辦《獨立評論》。然而,蔣廷黻在現代中國集體記憶裡重新出土的時間,比胡適晚了近二十年,不只因為其從政生涯遠長於學者生涯,更因他是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敵人。
離開學界後,蔣廷黻歷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與駐美大使,而他在聯合國與美國的首要任務,便是阻擋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阻止美國承認中國。美國頒給蔣介石的兩道「免死金牌」——「緩議方案」與「重要問題」——在他的斡旋下,讓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席次二十年。
江勇振繼《舍我其誰:胡適》四部曲後,為學優則仕的蔣廷黻作傳,以三份難得的珍貴史料為基礎:英文版《口述自傳》、1944至1965年的英文日記,以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描繪出歷經國難驚濤的一代外交官風範,與蔣廷黻個人生命的愛恨灑脫。
江勇振:「許多喝過洋墨水的近代中國人常會用英文寫下不可為國人道也的秘密。胡適如此,蔣廷黻也如此。……蔣廷黻在日記裡批評蔣介石的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而且如果在大使任內就流傳,他的命運至少一定會跟葉公超一樣,被召回而且軟禁。」
▍關於中日戰爭——1938 年8月20日 蔣廷黻寄胡適信:
因為缺乏醫療,許多受傷的人死去。非常高比例的人沒有得到任何救助。有些餓死、渴死。情況非常慘。委員長身邊的人只告訴他好的消息。我不認為他知道實際的情況。……如果戰爭再持續六個月,我們可能會淪落到被敵人和憤怒的百姓夾擊的地步。當然,日本害怕其經濟結構會崩潰。我們不怕,因為我們根本連那個結構都沒有。中國經濟崩潰,就會是以傳統流寇(banditism)的現象來顯現。那些高喊抗戰的人是躲在後方的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真正在戰場上的人所吃的苦。
▍關於美蘇冷戰——1948年6月22日 蔣廷黻日記:
雖然我投票贊成美國的提案,但我並不是完全樂意的。當然,最好的作法是讓核子武器從這個世界永遠消失。然而,究竟是讓美國或蘇聯擁有這個武器?這個選擇很容易。如果蘇聯比較像樣一點(more decent)的話,我是會樂意加入它的陣營來禁止核子武器的。將來,這個世界也許會後悔美國有這個武器。
▍關於國共內戰——1948年12月31日 蔣廷黻日記:
今年值得誌記的是國民黨的崩潰。從它興起到滅亡總共歷時二十五年。其興起是拜民族主義以及北方軍閥的腐敗之賜。其滅亡則是由於:一、長期對日抗戰;二、食古不化(medievalism);三、未能改善老百姓的經濟情況。造成後者的原因是由於沒有眼光,以及由個人野心所造成的長期的內戰。……國民黨在其所存在的二十五年之間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1950年12月4日 蔣廷黻日記
他[顧維鈞]從華盛頓核心人物得來的消息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會讓給赤共。我相當樂觀地進去,而卻沮喪地出來。我就是不理解:如果美國守不住韓國,就撤退好了;中共沒有海軍,沒有辦法到任何地方去打美國:為什麼要平白地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去交易?
▍關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2月12日 蔣廷黻日記:
在協防條約簽署、台灣安全了以後,老蔣將會繼續扮演他導師—領袖的角色,亦即,獨裁者——一個小島上的小獨裁者。他將永遠不會體認到他的缺點或者認清事實。俞國華是他找到的一個理想的行政院長——一個基督徒的應聲蟲;同樣地,張群是他理想的祕書長。前景黯淡。他毫無疑問地會發表一些說教式的文告來滿足他的虛榮心(amour proper)。
作者:江勇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退休。著有《張君勱傳》、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舍我其誰:胡適》 (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等書,多篇論文散見於各刊物、選集中。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從學生到教授,1895-1935
從私塾到教會學校
留美生涯
南開大學
清華大學
第二章 從政論家到進入政壇,1932-1943
《獨立評論》
行政院政務處長
駐蘇聯大使
復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第三章 「聯總」與「行總」,1944-1946
開會、演講、與閒雲野鶴之樂
行總署長
何去何從?
第四章 婚變,1944-1965
交會的漣漪
序曲
對決
第五章 變局,1947-1949
不偏不倚的獨立外交姿態
崩潰
中國自由黨
第六章 聯合國席次保衛戰,1949-1962
控蘇案
蘇聯反將一軍
韓戰:絕處逢生
第一道免死金牌
第二道免死金牌
第七章 駐美大使,1962-1965
「雙橡園」主人
高爾夫球迷
Hilda與孩子們
幕落
前言(節錄)
胡適並不是唯一一個一度從現代中國的集體記憶裡消失的人。蔣廷黻是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跟胡適一樣,蔣廷黻從現代中國的集體記憶裡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政治。這也就是說,他是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敵人。蔣廷黻的問題比胡適嚴重,因為他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及駐美大使。更嚴重的是,他在聯合國以及駐美大使任內最重要的雙重任務是在阻止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阻止美國承認中國。
然而,政治的問題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蔣廷黻重新出現在中國的集體記憶裡的時間比胡適晚了將近二十年。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學術界以及公知對蔣廷黻的定位。首先,蔣廷黻沒有胡適有名。其次,他從政的生涯是他作為學者的兩倍半。他的學術生涯在他 1935 年從政以後就已經結束了。最重要的是,胡適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嚮往民主自由的人眼中的先知。蔣廷黻則不然。他作為政論家的形象一直被錯誤地定型在他 1930 年代「民主與獨裁」論戰裡的獨裁的擁護者。作為獨裁的擁護者,蔣廷黻自然不可能成為中國嚮往民主自由人士眼中的寵兒。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會有胡適熱,而沒有蔣廷黻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沒有蔣廷黻熱,還有兩個特別的原因。首先,研究中國近代史必須把中國放在世界,或至少是經由東亞折射的世界的脈絡之下來審視。這已經是一個常識。要從世界的脈絡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就必須有世界的視野以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其次,蔣廷黻所留下來的資料有很多是用英文寫的。許多喝過洋墨水的近代中國人常會用英文寫下不可為國人道也的祕密。胡適如此,蔣廷黻也如此。祕密用英文寫,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了自保。蔣廷黻在日記裡批評蔣介石的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而且如果在大使任內就流傳,他的命運至少一定會跟葉公超一樣,被召回而且軟禁。
祕密用英文寫,這是對研究者的一大挑戰。研究者必須先知道有那些資料的存在以及要去什麼地方找。研究蔣廷黻的困難之一,就是從 1944 年到 1965 年他過世以前二十二年的日記是用英文寫的。不但是用英文寫的,而且用的是草寫。他所用的是印好的精美的日記本,一天一頁。二十二年之間,他相當有恆地逐日記著,一直到他過世前幾年才稍微有些鬆懈。
這二十二年的日記,蔣廷黻的幼子蔣居仁(Donald Tsiang)在 1989 年捐贈給哈佛大學。蔣居仁夫人的姪女 Michele Wong Albanese(黃愛蓮)當時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的助理。她在 1988 年 9 月 2 日寫信給費正清提起蔣居仁有意把蔣廷黻的日記捐贈給哈佛大學。這對費正清來說是如獲至寶。他立時跟哈佛大學圖書館負責人聯繫,並向蔣居仁致謝。由於大家都認識到這批日記的珍貴性,於是立即著手處理,在 1989 年 5 月完成了捐贈的手續。
蔣居仁在接下去的二十年當中陸續把蔣廷黻的資料捐贈給哈佛大學,最後一次是 2018 年所捐贈的照片。所有這些都是由 Michele Albanese 居間聯繫的。薛龍(Ronald Suleski)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s History, 1955-2005)一書裡,形容這是 Michele Albanese 投入了十五年的心血所完成的一個工程。薛龍用詞貼切,只是他在 2005 年成書的時候完全沒能預想到這最終會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工程。
2004 年,哈佛大學特地在「教授俱樂部」舉辦了一個午宴,慶祝蔣廷黻檔案捐贈給哈佛大學。出席的,除了當時已經出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柯偉林(William Kirby)、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鄭炯文(James Cheng)、Michele Albanese 以外,還有蔣廷黻住在美國的三個孩子:蔣居仁、蔣志仁(Lillian)、蔣壽仁(Marie)。這就是陳紅民、傅敏主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所根據的檔案。
我自己很晚才知道有蔣廷黻的日記。我知道有蔣廷黻日記是我開始撰寫《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與《第四部:國師策士》的時候。我當時知道原件藏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幸運的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圖書館藏有一份複印本。我就利用夏天回台北作研究之便到近史所使用。
我到近史所使用蔣廷黻日記是從一件小糗事開始的。那充分說明了先入為主的成見的可怕。我先入為主的成見是:蔣廷黻的日記想當然耳是用中文寫的。因此,我一直納悶為什麼他的日記沒廣為學者所引用。我在圖書館查了書號以後,就到書庫去找書。當我把那書脊朝上厚厚的一本從架上拉出來的時候,看到上面印的是英文字,我連看也沒看就把它推了回去。我下樓到櫃檯對館員小姐說我找不到我要的書。館員小姐請一位工讀生上去找。他不到一分鐘就走了下來,手裡拿著的就是我剛才抽出來又推回去的那本暗粉色的巨帙。我一面很尷尬地接了過來,一面向那位工讀生與館員小姐致謝。我心裡暗自責備我那麼容易就被先入為主的成見蒙蔽,到了連書脊上印的字瞧都不瞧的地步。
蔣廷黻這二十二年的日記是研究他壯年到晚年不可或缺的資料。我很驚訝陳紅民、傅敏主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沒有收入蔣廷黻資料裡最最重要的日記。當然,我可以了解這套資料集已經皇皇 24 冊。如果再加上 22 冊日記,恐怕沒有一個出版社會願意注入那麼大的資本。
陳紅民說蔣廷黻日記:「全部是用英文手寫,潦草難辨識。對於英語不是母語的人來說,閱讀難上加難,故鮮見中國學者將日記運用在研究中。」所幸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劉義章教授已經組織了一個團隊在從事翻譯。陳紅民說等中譯本出版以後,學者可以通過日記了解蔣廷黻最後二十餘年的思想與活動,「何愁對其晚年做不出精采的研究。」
我自己就深得劉義章教授的幫助。他在 2014 年慷慨地把蔣居仁先生的美國好友 Ann Salazar 所打字整理出來的 1944 到 1962 年十八年間的日記提供給我。蔣居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 Salazar 女士現在已經把蔣廷黻二十二年的日記全都打字出來了。我在此要特別表揚 Salazar 女士對這個浩大的工程所奉獻出來的心力與時間。她所作的辨識工作,特別是用打字稿的方式呈現出來,讓研究者便於閱讀,這真的是功德無量。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 Salazar 女士所作的是初步的辨識工作,研究蔣廷黻的學者如果有幸能夠使用必須再作進一步核對的工作,因為除了日記裡的中文名字與名詞她無法辨識以外,還有辨識錯誤、闕漏、甚至她也許因為認為英文畢竟不是蔣廷黻的母語而善意地替他改正——結果是誤解了——的所在。
言歸正傳。承蒙劉義章教授在提供我 Salazar 女士的打字稿以後,又邀請我參與他所組的團隊。由於我發現打字版辨識錯誤之處所在多有,劉教授又把 1944 到 1946 年日記的掃描本提供給我,以便作翻譯前的核對工作。當時我已經開始寫作《為學論政》與《國師策士》。我用教學與寫作之餘的時間開始核對,一天核對十則日記。在核對完 1944、1945 兩年日記以後,我就發現那會是一個曠日長久的浩大工程。我一天核對十則日記,需要 36.5 天次才能核對完一年。如果能夠持之以恆,核對二十二年的日記,需要 36.5 × 22 = 803,亦即 803 天,也就是 2.2 年。而這還沒加上翻譯所需的時間。我一天可以核對十則日記,但不可能翻得出十則。翻譯所需的時間,我估計要數倍於核對的時間。這是一個需時十年以上的工程。因此,我在核對了兩年份的日記以後,就自知我沒有時間與精力同時教學、寫書、又參與這個工程。承蒙劉教授海涵,讓我退出了他的團隊。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者一定要使用原件。蔣廷黻的日記既然是用英文寫的,研究者就必須看他的英文日記。沒有一個嚴肅的研究者會使用中譯本。原因很簡單:翻譯是否正確?是否有闕漏?文意是否適切地轉譯出來?言外之意是否捕捉到了?
研究者不使用原件就會以訛傳訛,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口述自傳》(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的中譯本就是一個最好的鑑戒。這麼多年來,研究蔣廷黻的人用的都是謝鍾璉所譯的《蔣廷黻回憶錄》。大家習以為常,彷彿用中譯本是學術研究約定俗成的章法。於是,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去使用原本,甚至對比一下。問題嚴重到不是把原件束之高閣,備而不用,而是根本就沒有。就以台灣為例,全台灣居然沒有一個圖書館藏有蔣廷黻《口述自傳》的原本!殊不知謝鍾璉的中譯本不但譯得不夠精確,而且錯誤百出,往往曲解了原意。
第六章 聯合國席次保衛戰,1949-1962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廷黻當天的日記連提都沒提:「豔麗的一天。早上在辦公室,披閱有關滿洲的文件。下午在起草委員會。葉公超出任〔外交〕部長。蘇聯〔代表〕散播謠言要把我的代表團背走:這是神經戰。」次日:「〔從聯合國〕回到〔紐約〕市裡的時候,林咸讓來電,說蘇聯斷絕跟國民政府的關係,承認了北平政權。他問我如何答覆記者。我告訴他回答說:莫斯科會承認其孽種(offspring),再自然也不過。有個記者打電話來問同樣的問題。我給他一樣的答案。打電話給顧維鈞,問他是否會發表一個聲明。他說第一個答覆應該來自於廣東〔當時國民政府的流亡地〕。」3 日:「葉公超發表了一個強硬而且很好的聲明。」4 日:「謠言說蘇聯要在四十八小時之內背走我。」蔣廷黻說他才不信。
控蘇案
國共內戰情勢逆轉以後,國民政府給予蔣廷黻在聯合國的首要任務是控訴蘇聯違反 1945 年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侵犯了中國主權、危害遠東的和平。這就是所謂的「控蘇案」。這個控蘇案在 1949 年聯合國第四屆大會中提出的時候,其目的是雙重的:對內,在把國民黨內戰失利歸罪於蘇聯扶持中共的結果;對外,在阻止國際承認中共。然而,等到「控蘇案」在 1952 年聯合國第七屆大會通過的時候,中共政權已經成立了三年了,承認的國家已經有二十三國。國民黨唯一所得到的是阿 Q 式的精神勝利,由聯合國認證中共的勝利與建國是蘇聯扶持的結果,完全無補於實際。
蔣廷黻在一開始是反對提出「控蘇案」的。他 1948 年 7 月 10 日的日記:「回覆王世杰把中蘇衝突提交聯合國一事。我的建議是不要〔,理由是〕:一、有關大連,蘇聯可以把它交給中共;二、有關扶持中共,蘇聯可以否認,同時徵引美國人的說法來污蔑中國;三、歐洲的情況越來越糟。如果產生決裂,最好是在歐洲而不是在東方。」
聯合國第三屆大會 9 月在巴黎召開的時候,蔣廷黻奉命跟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起控蘇案的想法。在 11 月初幾次的會談裡,馬歇爾都對蔣廷黻說,此舉不但不會給中國帶來好處,而且甚至可以給蘇聯機會反將中國一軍。蔣廷黻承認說他已經接到三次的訓令,每次他都建議不要採取行動。蔣廷黻自己在 11 月 9 日的日記裡說:「看來中央政府還沒有準備好要跟蘇聯對幹,而願意就這麼跟中共打下去。我們為什麼要在巴黎跟蘇聯開火呢?」
然而,11 日在「第一委員會」(當時是「政治與安全委員會」;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上討論裁軍問題的時候,蔣廷黻譴責蘇聯以武器援助中共。他把國共內戰與美國的南北戰爭、蘇聯 1917 年的內戰拿來相類比,說這些都是在外國政府干預下的內戰。他說聯合國要裁軍,首先「應為裁撤布於希臘、朝鮮、中國,乃至全世界之第五縱隊。」蔣廷黻的發言引起蘇聯代表的憤怒,要求主席裁決蔣廷黻違反議事規則。蘇聯代表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發言說中共是一支對抗反動政府的解放軍。蔣廷黻在次日的發言裡反駁國民黨政府是一個反動的政府的說法。可惜,他在日記裡沒說明他用的論據是什麼。
就在蔣廷黻反駁威辛斯基的這天,蔣廷黻收到王世杰的電報,說國內要求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的壓力極大。蔣廷黻說:「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兩天以後,14 日,蔣廷黻就收到王世杰的電報,說政府決定提出控蘇案,而且決定直接向杜魯門陳情,因為馬歇爾對國民政府成見太深。蔣廷黻說:「我對這兩點都不贊同。」
蔣廷黻雖然不贊同政府的訓令,但作為駐聯合國的代表,他必須從命。次日一早,他就召集幕僚討論在安理會裡提出控蘇案的目標以及法律的根據。中午,他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會面,請他給予建議。晚餐過後,他又跟幕僚繼續商議。他在日記裡思忖說:「〔訴諸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即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爭端〕,只會換取一個無關痛癢(innocuous)的決議;〔訴諸〕第七章〔即用經濟制裁或軍事行動維持和平〕,則會被〔蘇聯〕否決。『中國』〔指的是台灣。為了不造成混淆,特加括弧以區別。以下同〕有什麼好處可得呢?」由於蔣廷黻仍然不贊成提出控蘇案,他在 21 日寫了一封信給傅斯年,試圖讓他理解向聯合國控訴是會徒勞無功的。
隨著聯合國第三屆大會在 12 月 12 日閉幕,控蘇案也就在這屆會期裡不了了之了。
然而,控蘇案是箭在弦上,國民黨不發是不會甘休的。1949 年 5 月 20 日:「外交部來電報,要在大會上提議禁止會員國承認用武力或非民主的方式取得的政權。對這個冒險我很震驚。」當天下午,蔣廷黻去醫院看顧維鈞的時候跟他談起那個電報:「他認為這個提議不管在法律或憲章上都站不住腳。而且,美國和英國在承認方面是傾向於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他接著思索〔政府〕是否可能在人事與政策上作出戲劇性的改變。我說在位的人是不可能讓位的。」然而,蔣廷黻必須開始思索控蘇案的進行程序。7 月 27 日:「鄭重地思索在大會提出蘇聯違反中蘇條約。」接著,他在 8 月間跟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在聯合國的代表聯繫,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政府的支持。8 月 21 日午餐的時候,他也跟顧維鈞、宋子文、胡適、和貝祖詒談起向聯合國提出該案是否明智之舉的問題。他說顧維鈞、宋子文、胡適都反應冷淡。
顧維鈞是駐美大使,蔣廷黻是駐聯合國大使。兩個人都被責成向美國政府聯繫準備提出控蘇案;兩個人都認為那是不智之舉。然而,兩者的不同,在於蔣廷黻即使不苟同,在受命以後,積極從事;顧維鈞則顯然是傾向於虛應故事。美國駐聯合國代理大使羅斯(John Ross),在 1949 年 8 月 30 日給國務卿的報告就一語道出了英國駐聯合國大使賈德幹(Alexander Cadogan)爵士對顧維鈞的看法:「我提起說顧維鈞去過國務院。他對提出這個議案的態度似乎不像蔣廷黻那樣明確。賈德幹說這就是顧維鈞,他會抓住機會『跳上』中共的順風車。」事實上,連蔣廷黻都在 8 月 28 日日記裡批評了顧維鈞:「有關『中國』要提的案子,顧維鈞非常謹慎,甚至可以說是膽怯。」
顧維鈞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數能夠得享榮華的貳臣——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能貫穿三朝的「參臣」。他是袁世凱的英文祕書、駐美大使,北洋軍閥政府歷任的內閣總理、外交總長。1928 年北洋軍閥倒台以後,他是國民政府「儆奸邪而申國紀」的通緝犯之一。然而,一年以後,蔣介石就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他在國民黨政府裡官運亨通,歷任駐國際聯盟代表、駐法公使、駐英大使,並在 1946 到 1956 年間再度出任駐美大使。1956 到 1967 年出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雖然他在 1948 年被中共列為戰犯,但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後,他就在次年受邀訪問中國。雖然他在過世以前沒有機會訪問中國,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顧維鈞回憶錄》在 1985 年就已經被翻成中文出版。在民國時期的外交官裡,他是唯一不被中共從民國史的集體記憶裡剔除的一人。
美國在蔣廷黻與顧維鈞分別與其聯繫以後,就已經決定了其對策,亦即,原則上支持,但支持到什麼程度則端賴國民黨政府所能提出的證據是否充分。蔣廷黻 8 月 26 日日記:「羅斯來告訴我說美國會支持『中國』,至於支持到什麼程度,則要看該案在大會裡的發展。」當天會面的時候,羅斯詢問蔣廷黻說「中國」所希望達成的目標是什麼。蔣廷黻在日記裡沒記,但羅斯在給國務院的報告裡臚列了出來:「一、蘇聯違反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二、要求聯合國會員國不承認中共;三、要求會員國給予國民政府道德與物質上的援助。」
蔣廷黻在 9 月 1 日收到外交部電報,任命他為即將召開的聯合國第四屆大會的首席代表,主持控蘇案。9 月 13 日:「外交部所派的第一批人員抵達,帶來一整箱的文件。開始研究這個案子。我跟盛岳〔第一批人員裡懂俄文的專家〕長談,了解了國防部以及外交部專門人員都反對提出這個案子。這個想法是來自於老蔣。派程天放來也是老蔣的意思。」17 日,他請顧維鈞讓他借調陳之邁來參與控蘇案的工作。
9 月 22 日是蔣廷黻在大會上開火的日子:
我要去「法拉盛草原」(Flushing Meadows) 〔當時聯合國在「成功湖」以外另外一個臨時的會址〕之前有點緊張,所以就用跟孩子們玩的方法來讓自己鎮靜。在車上,我的緊張就消除了。大會十一點開始。我很驚訝我是第一個發言的人。許多代表都還沒到。空蕩蕩的席次讓我有點沮喪。然而,我想大家都會拿到書面的報告。我開始用中文作報告〔這是蔣廷黻唯一一次用中文在聯合國發言〕。會場在靜默中緊繃著。我結束的時候的掌聲中等,比我預期的多。代表們像被刺了一樣。希臘代表開隆(Kyron)是唯一走到我的席次來向我道賀的代表……〔午餐過後〕林咸讓給我看一些新聞報導,相當冗長,提到我的地方泰半是正面的。大部分的代表拒絕評論。麥克奈爾(MacNeil) 〔英國代表?〕說:「是一個很好的演說。」一些蘇聯的小丑們說是:「蠢話!」、「天鵝垂死前的悲歌。」南斯拉夫代表說:「無聊!大會能作什麼呢?」
蔣廷黻知道他當天的聲明在聯合國裡所得到的反應是冷淡的。他不但是對一個空蕩蕩的會議廳演講,而且那並不熱烈的掌聲還是超過他的預期的。然而,最讓他欣慰的是,《紐約時報》不但在次日刊載了他的聲明,而且還發表了社論支持他。此外,還另外有一篇報導的文章。這篇以〈從中國來的直話〉(Plain Words from China)為名的社論,稱讚蔣廷黻直話直說,籲請大會嚴肅地面對問題:「他的立論基礎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跟莫斯科相聯的世界組織的工具。」莫斯科的政策:「雷同於沙俄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且更為成功。克里姆林宮對滿洲的控制大於沙俄時期,而且藉由卑躬屈膝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控制中國其他地區的方法。」這篇社論說蔣廷黻指責聯合國只顧在歐洲防堵共產主義,卻任其狂瀾在亞洲肆虐。
《紐約時報》當天的另一篇文章,蔣廷黻在日記裡說:記者「加了他自己的一些推測。」這些推測裡,有兩點值得指出:第一、「中國」不太可能在安理會提出這個議案,因為蘇聯一定會使用否決權;第二、「中國」是否提出這個議案要看其他代表團的反應。而從美國與英國代表團沉默的態度來看,它們顯然不願意見到聯合國辯論這個問題。
《紐約時報》這位記者的推測非常近於事實。雖然控蘇案在 9 月 29 日以 45 比 6 的比數獲得列入議程,但蔣廷黻最大的問題是獲得美國的支持。對控蘇案,美國一直採取消極的態度。這是蔣廷黻以及蔣介石的整個國民政府所一直不理解的所在。他們不了解美國的政策是絕對不打不能穩操勝券的仗,不管是在軍事還是在外交的戰場上。然而,蔣廷黻和蔣介石會一再地誤判,然後落到失望的地步。控蘇案只不過是第一個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