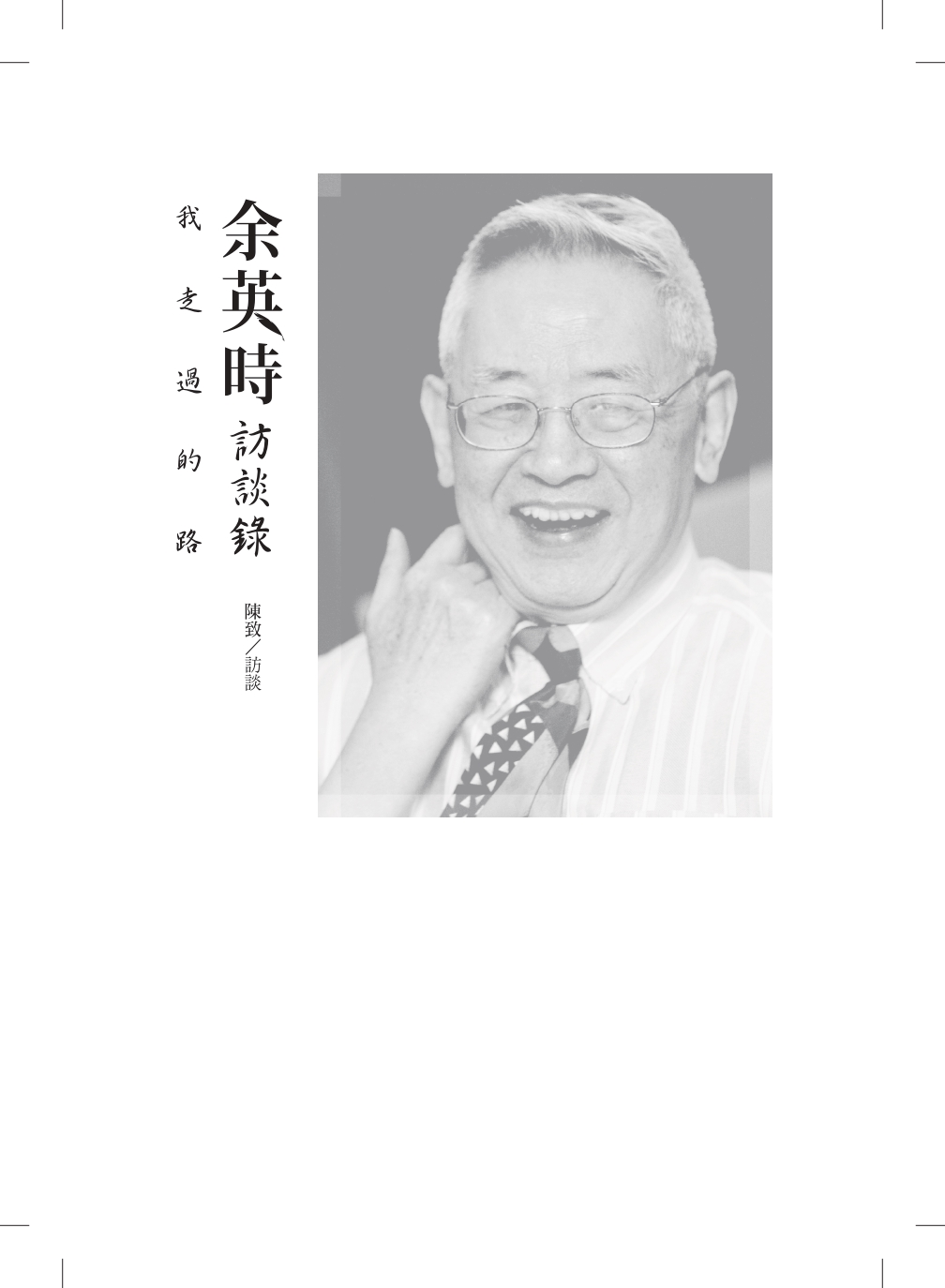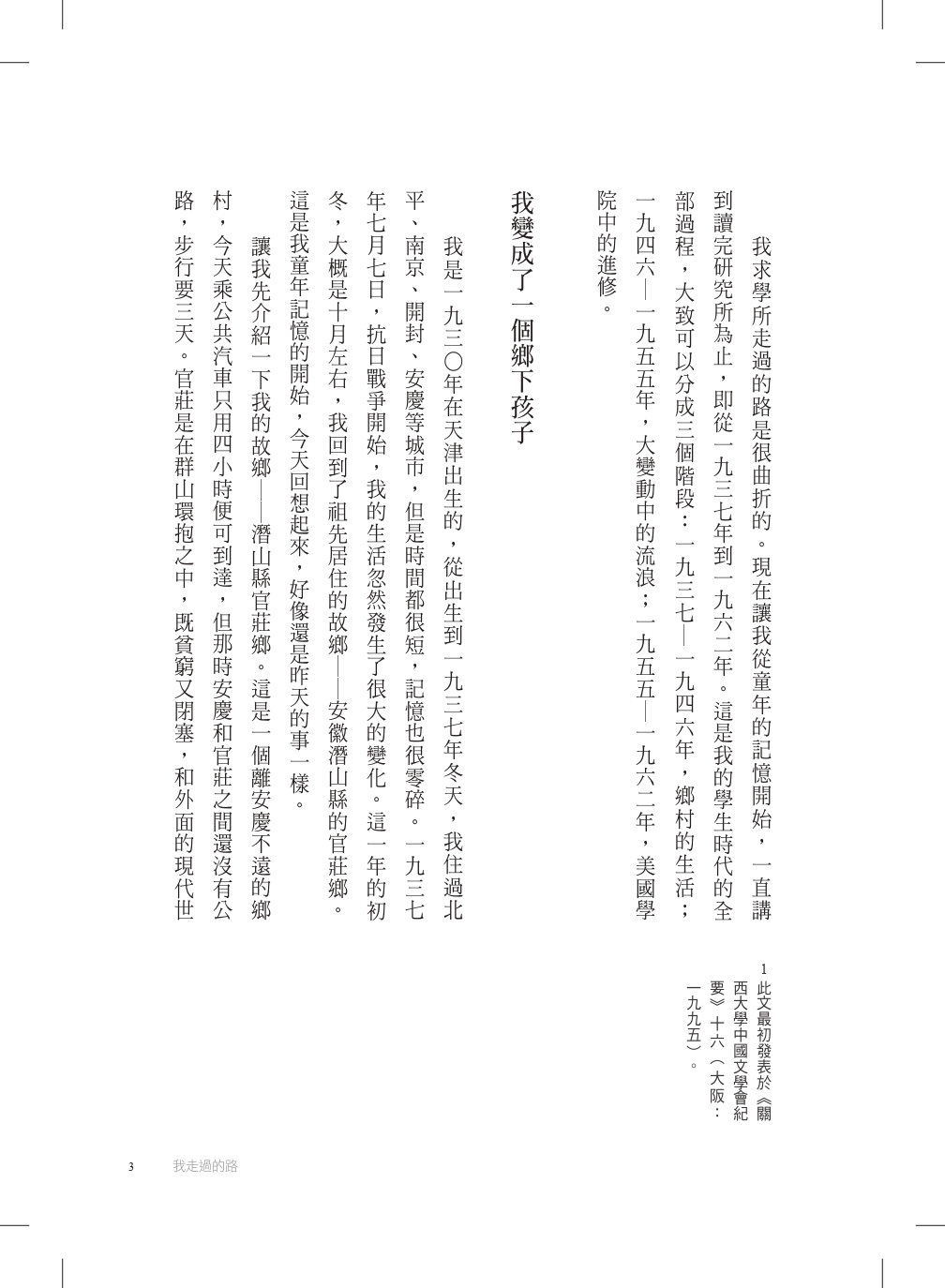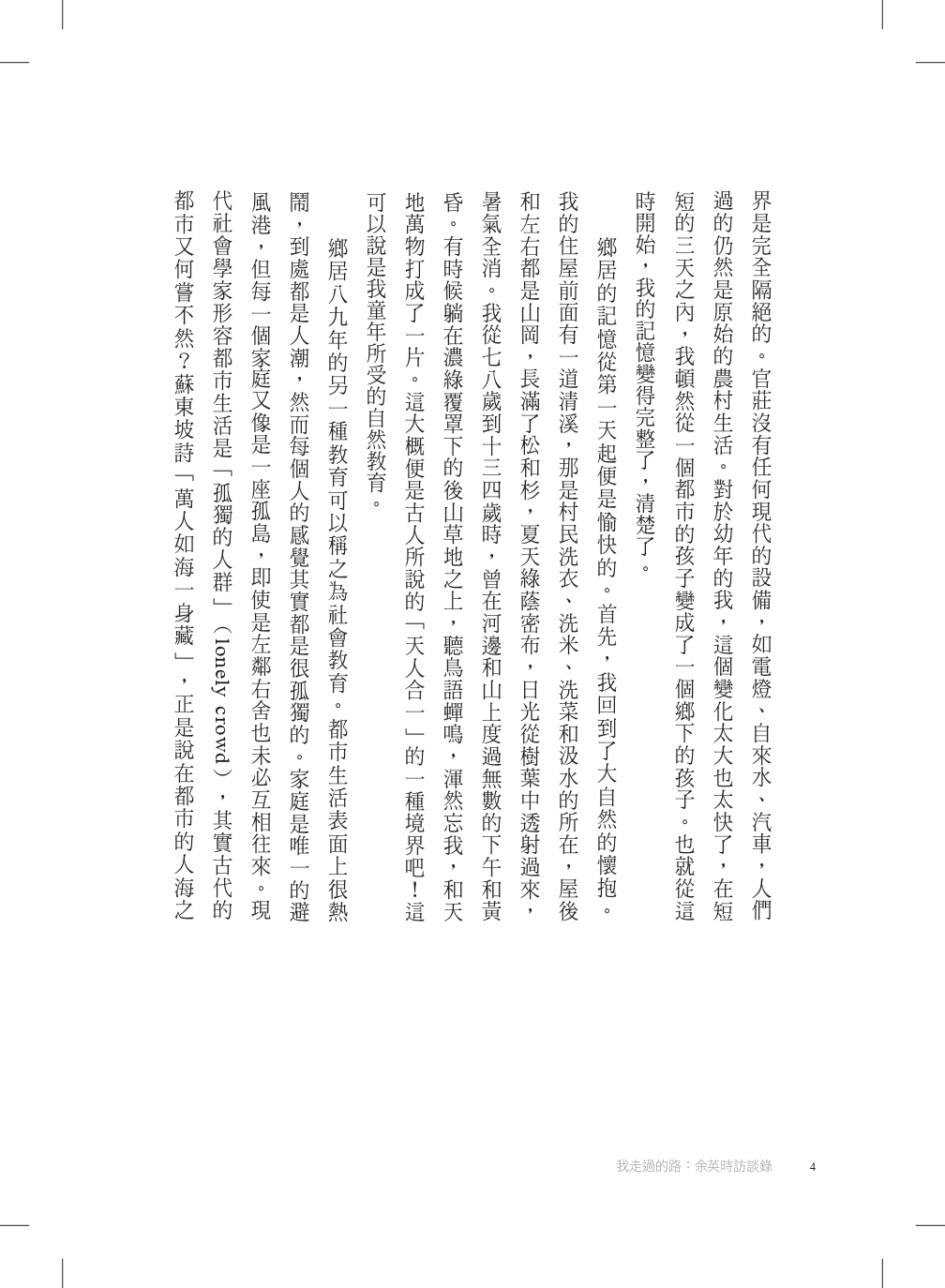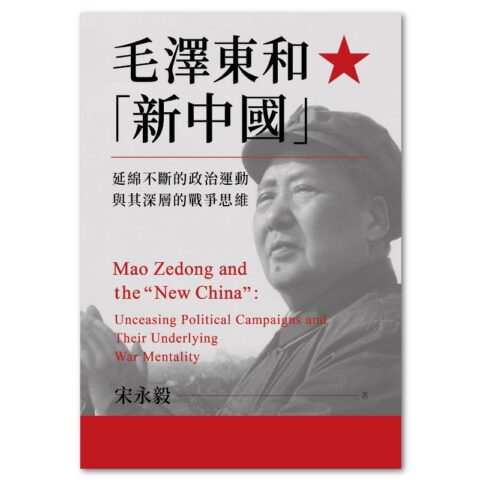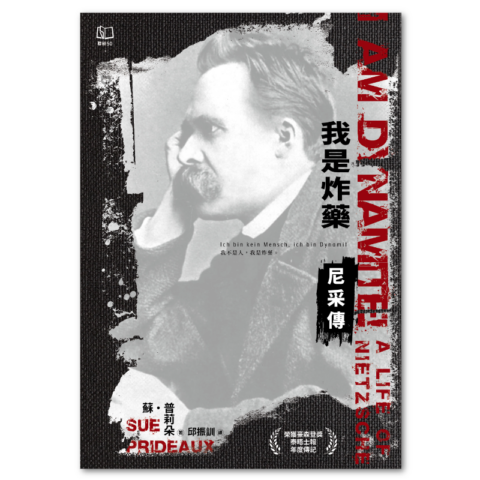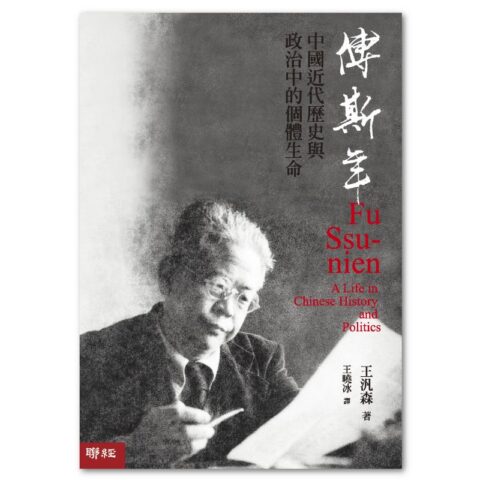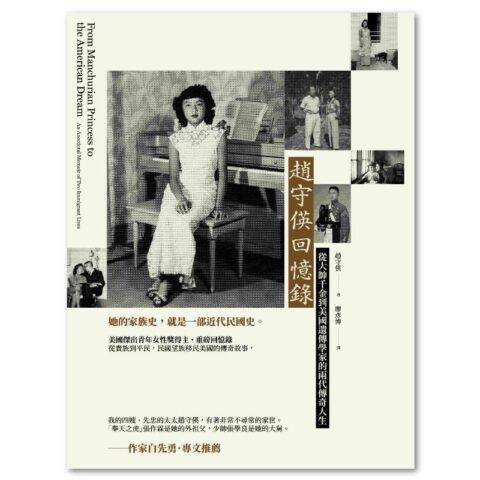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增訂新版)
出版日期:2021-11-11
訪談:陳致
印刷:黑白印刷,彩色16頁
裝訂:平裝
頁數:332
開數:25開,長21×寬14.8cm
EAN:9789570860306
系列:文化叢刊
尚有庫存
第一本紀錄余英時先生談自己年幼生活、
青少年時期、學生時代及思想養成的訪談集。
余英時先生學術思想博大精深,
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
在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
本書由思想史學者陳致透過訪問,
呈現余英時先生的學思歷程。
2006年12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余英時教授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獎。該獎項頒發給諾貝爾獎未包括的人文學科領域中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以肯定他們在學術研究中的終身成就。
余英時先生是在迄今獲獎學人中唯一的華人學者,余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為中外學術界所公認。陳致接受香港《明報月刊》委託,通過越洋電話數次訪問余先生。
訪談記錄著重在余先生治學的途徑、經歷、方法和重點,以及他對學術、思想、人文等各方面的看法等。全書分為〈直入塔中,上尋相輪〉、〈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四篇。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 (1930-2021)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2014年榮獲「唐獎漢學獎」。
⊕ https://linkingunitas.com/YYS
– –
訪談:陳致
1964年出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南京大學古典文學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主要從事詩經、古史與明清學術史方面的研究,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署理院長,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常務副校長。
著有《詩禮禮樂中的傳統》、《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國上古史卷》、《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主編《中國古代詩詞典故辭典》、《周策縱舊詩存》,另有學術論文在陸、港、臺、英、德、美、荷等重要學術雜誌上發表。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
克魯格獎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以通馭專,由博返約:錢賓四先生
國學與現代學術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內向超越」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民族主義與共産主義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
哈佛讀書經驗
早歲啓蒙與文史基礎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洪煨蓮(業)與楊聯陞
俞平伯與錢鍾書
學術與愛國主義
取法乎上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爲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
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天人合一」的局限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後記
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爲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爲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餘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爲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啓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啓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曆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陳:這兩年我們知道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前段時間也在看這本書,您在自序中說到本來是給《朱熹文集》寫序的,結果寫成了一部大著作,這是不是有點兒像梁任公(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那樣?
余:那倒還不一樣。梁任公寫清代學術,他本來已經很熟悉有清一代的學術變遷,然後用十幾天的時間概括出來,寫成六七萬字的長序,最後獨立成書。他並沒有再作新的研究。我是本想介紹一下朱熹的思想怎麽産生的背景的,但研究不斷展開後,就發現了許多問題。以至範圍越來越大,最後變成思想史和政治史雙管齊下,不是專講朱熹一個人了。我特別注意他的歷史背景。隨著問題的不斷複雜化,我又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注意的新史料。比如說周必大的全集,有二百多卷,裡面有很多源文件,還有許多奏摺,都沒有人看過。看過的人也對很多前因後果沒太注意,其中可以瞭解到朱熹和當時的政治關係有多深,比如慶元黨禁。我現在把朱熹在政治上的活動,和他在政治上成爲精神領袖的原原委委全部找出來。這中間他和政治直接牽涉至少有十幾年的時間,的確牽連到權力集團和權力鬥爭,是保守的官僚集團和一個想有作爲的以理學家爲中心的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後者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希望革除弊政,有徐圖規複的宏偉計劃。這與希望維持現狀的一群人形成矛盾。這中間還牽涉到祖孫三代皇帝之間的矛盾,所以頭緒繁多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我是足足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整理清楚的。
陳:這部書的角度我覺得比較特別。因為以前研究宋代理學,主要是從思想史的內部看,很少從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而您在以前研究清代思想,認為清代考据學的興起是由宋明以下理學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logic)給逼出來的,這與研究朱熹的角度好像正好相反。
余:情況不同,因爲對清代的研究,以前從外部聯繫比較多,如說滿洲人入關以後大家不敢講大問題,有些歷史上的忌諱,逼得大家去做考證工作。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解釋。還有解釋就是清朝人反對理學。這些解釋並不是說不對,而是偏了,把思想內部的問題反而忘了。內部有兩個線索,一個是哲學上的爭論,朱、陸和朱、王之爭,使理學把考據給逼出來了,非考證不能解決問題。像毛西河(奇齡)是王學的人物,閻百詩(若璩)是尊朱子的。在此之前更早有與王陽明同時的羅欽順,他在《困知記》裡已經提出取證經書,分判經書裡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這就逼著你回到原典。而王陽明一定要講《古本大學》,這一點就是哲學的爭辯引向經典的真假遲早的問題,其中是有內在變化的。我研究宋代思想是因爲幾百年來多講內部思想紛爭。傳統的說法集中在「理」與「心」之爭,大陸上說客觀唯心論主觀唯心論什麽的,都不免只講內部,不問外緣關係。這和清代學術研究的取向相反,也不免陷於一偏。但那時候思想的爭論事實上和黨爭之間有關係,這是沒有人解釋的。好像北宋王安石的理學、新學到南宋時候已經沒有了。二程與王安石之間的新學之爭,由此發生的政治之爭,似乎到南宋時整個不見了,其實不然。王安石改變社會並不是爲了只是發明一條道理,或者說與佛教鬥爭。這對兩宋的學術來說是講不清楚的。
陳:所以您講原來的兩宋思想研究有抽離的問題。但後來也有一些爭論,您又寫了文章叫《「抽離」、「回轉」與「內聖外王」》,再申論這個問題。那些文章我也都看了。您講抽離是說哲學史家在談兩宋理學發生發展的研究中,一是把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二是把道體又從道學中抽離出來。您能不能再解釋一下這個「抽離」的概念,您是怎麼想的?
余:我所說的「抽離」是就思想史或哲學史上對於宋、明「道學」(或廣義的「理學」)的處理方式而言,其中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將全部宋、明儒學從一般政治、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當做一種純學術思想的動態來觀察。第二層是進一步將「道學」從全部儒學中抽離出來,建構出種種形上系統。第三層則是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作精微的分析,以確定其作爲儒家形上實體的性質。這是因爲宋明道學中本有程、朱「性即理」和陸、王「心即理」的兩大對立系統,一直存在著誰得「道統」真傳的爭論。在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這一爭論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我並不是反對「抽離」,甚至承認以哲學分析而言,「抽離」是必要的。但是我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是從歷史觀點處理宋、明道學和政治文化的關係,採取了與「抽離」相異的方式;在歷史分析之外,更注重綜合。我一向強調「史無定法」,研究方法往往因物件而異。所以我用「抽離」一詞僅僅是關於研究方法的一種描述,並不含絲毫貶斥之意。
陳:您所建構的關於理學的歷史面貌好像和一般的講法很不一樣?
余:這是因爲我的觀察角度不同,提出的問題不同,對於儒學性質的斷定也不相同。宋儒繼承了孟子與韓愈的「道統」說,一開始便提倡回向「二帝」(堯、舜)「三王」(夏、商、周)之「道」,可見他們最關切的中心問題是重建一個合於「道」的人間秩序,而政治秩序(「治道」)尤其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所以在道學興起以後,張載就明白地說「道學」和「政術」是一事的兩面;他的《西銘》則代表了道學家理想中的人間秩序,因此成爲二程教學的經典文本。程頤也說過「道學輔人主」的話。道學承北宋儒學復興大運動而起,整體的規劃並無改變。這一整體規劃,用孔子的話說,便是怎樣變「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但北宋儒者追求「天下有道」的使命感更強烈了,也更具體了。在這一理解下,強調「心、性」修養的「道學」也必須看做是當時儒家整體規劃(the Confucian project)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似乎不宜將「心、性之學」單獨挑出來,當做道學的全部。道學在心、性問題上確和佛教有分歧,但北宋儒學復興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爲韓愈辟佛運動的延續和擴大。這是因爲北宋的佛教轉變了,同樣有「入世」的一面。釋氏之徒也希望「天下有道」,並且把這一希望寄託在儒家身上,從智圓到契嵩無不如此。
陳:所以您對王安石改革和道學之間的關係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您是否可以簡單地概括幾句?
余:王安石改革代表了北宋儒家整體規劃的行動或實踐階段。行動的要求在范仲淹慶歷時期短暫改革中已出現,不過時機仍未成熟。範提倡「士」以「天下爲己任」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宋代「士」的精神最扼要的概括,影響極大,見於石介、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之中。王安石也是在這一精神之下成長起來的。他的「新學」以儒家經典(特別是《詩》《書》《周禮》)爲根據,加上佛教大乘精神的啓發,已具備道學家以來所發展的「內聖」、「外王」互相支援的規模。所以在熙甯變法開始時,道學家程顥也參加了王的改革總部—「三司條例司」。儘管道學與「新學」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不少差異,但二者的目的和思想結構是大致相似的,因此才有極短暫的合流。後來雙方鬧翻了,王安石的固執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道學家的意氣過盛也未嘗沒有責任。程頤事後反思,也承認「吾黨爭之有太過……亦須兩分其罪」。總之,王安石能爭取到神宗的全力支援,使儒家的整體規劃有實現的可能—即所謂「得君行道」—這是當時各派士大夫都一致擁護的。不但程顥參與新法,劉摯(胡瑗的弟子)和蘇轍最早也同在「三司條例司」工作。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這是很中肯的歷史論斷。王安石與道學的關係在南宋仍然餘波不斷,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就王氏「新學」而言,通過科舉,它已成爲官學。高宗一朝執政的官僚仍多由「新學」出身。雖有人提倡「程學」與「王學」相抗,想用二程的道學在科舉考試上取代「王學」,終不能敵。關於這一點,只要讀朱熹的《道命錄》,便可知其大概。道學在南宋成爲顯學是張栻、朱熹等人出現以後的事。第二,王安石所樹立的「致君行道」的典範對南宋道學家繼續發揮啓示作用。這是因爲南宋道學仍然遵守北宋儒學變「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的大綱領。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希望說服孝宗進行「大更改」。他們並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而是要改變現狀,建立合乎「道」的新秩序,然後恢復失去的半壁山河。所以他們先後都捲入了權力世界的衝突,終於慶元黨禁。詳情這裡不能談了。
陳:讀您的著作,我有一個很強的印象,就是您特別強調當時士大夫要與君主「共治天下」的觀念。特別講到宋代理學的出現這些問題,讓人覺得與以前的常識不太一樣。您是不是認爲傳統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他們的道德使命感?在對王陽明研究的時候,您說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覺民行道」。這是宋代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和「致君行道」不成功之後的邏輯發展,還是主要是明代的政治現實造成的?
余: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特色,已預設在「士當以天下爲己任」這句綱領之中。用現代話說,宋代的「士」充分發展了「政治主體」的意識:他們要直接對政治秩序負起責任。所以「共治天下」的觀念同時必然涵蘊了對於皇權的限制。「天下」不屬於「一人」或「一家」,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士」則自居爲代「天下人」參與政治、議論政治,因爲他們來自民間各階層。「致君行道」首先要求「君」的言行必須合乎「道」,這也是對「君權」的限制。從王安石、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等都曾公開地強調「道尊於勢」的理念,他們心目中的「君」,通過分析,則可見只是「無爲」的虛君,程頤所謂「天下治亂系宰相」便說得很露骨,因爲宰相代表了「在位」的「士」。至於「不在位」而在野的「士」則有「議論(批評)政事」的責任,因此宋儒把「士」分成兩類,前者是「天下之共治者」,後者則是「天下之論治者」。這並不是他們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道德使命感,而是政治與道德爲一事的兩面,互相支援,互相加強。一方面,重建一個合乎「道」的政治秩序,使天下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便體現了最高的道德成就。另一方面,道學家特重心性修養,也是以治國精英爲主要物件(從皇帝到士),而不是一般的「民」。所以朱熹對孝宗專說「正心誠意」四字;個人的道德修養爲政治秩序提供了精神保證。
至於王陽明的「覺民行道」,明代的政治生態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背景。明代君主獨攬大權,已不容許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開始便對士階層歧視,「廷杖」便是專爲凌辱士大夫而設的獨特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索性廢除了宰相的職位,便使「天下治亂系宰相」失去了制度的根據。所以黃宗羲把這件大事看作「有明一代政治之壞」的起點。此中曲折已見我的專書與論文,略去不談。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王陽明的時代,「民」的一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才使「覺民行道」新心態的出現成爲可能。所謂「民」的變化,即指十五六世紀「棄儒就賈」大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由於科舉已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士人,另一方面又適逢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張,許多士人都「下海」,向商業世界求發展,因而造成了一個士商合流的社會。商業財富開拓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當時書院、印刷、鄉約、慈善事業、宗教活動等無不有商人參與其間。具有儒生背景的商人階層也積極創建自己的精神領域,他們對於理學表現出深厚的興趣,無論是王陽明的「致良知」或湛若水的「到處體認天理」都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王陽明對這一新的社會變化十分敏感,因此一則說「四民異業而同道」,再則說「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成聖成賢」。陽明早年繼承了宋代道學傳統,仍有「致君行道」的抱負。但王受廷杖、貶龍場之後,此念已斷。他在龍場頓悟所發展出來的「致良知」教,仍然以「治天下」爲最後的歸宿,不過他對皇帝與朝廷已不抱多大指望,轉而訴諸民間社會。明代已不存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他的眼光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社會革新運動。因此「覺民行道」代替了「致君行道」。這個轉變過程很複雜,詳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六章。我對於宋、明理學演變的研究,最初只是想恢復歷史的客觀面貌,但最後得到的論斷則有「通古今之變」的意外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