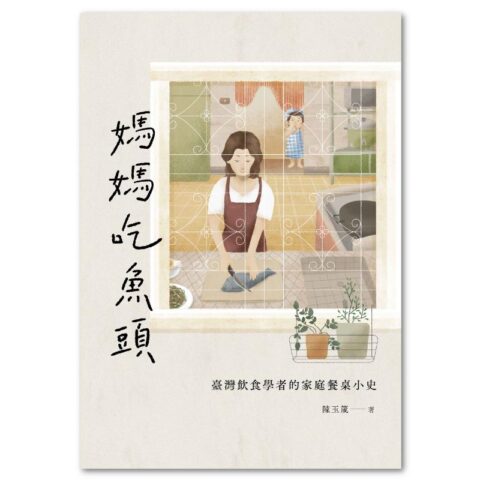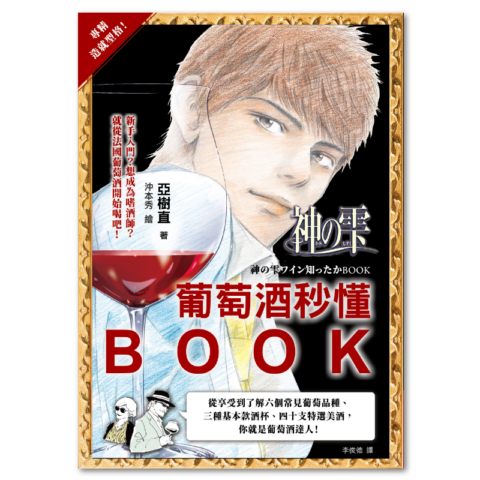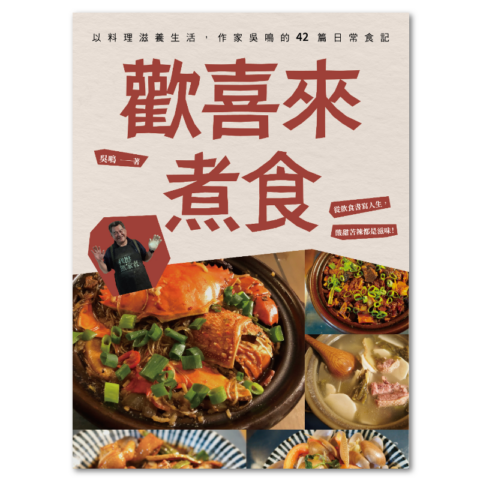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
原書名:ママ、ごはんまだ?
出版日期:2014-03-20
作者:一青妙
繪者:葉懿瑩
譯者:陳惠莉
印刷:單色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5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3576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2013年年度開卷好書《我的箱子》作者一青妙
感動臺日讀者的第二部自傳性作品!
父親出身於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母親是來自日本的異國女子
在二戰剛結束的年代,臺灣與日本陷於混亂不安的氛圍……
身為臺日混血兒的作者一青妙,在成長的過程如何體會、看待臺灣與日本間的文化差異?
嫁作臺灣媳婦的作者母親,又是如何嘗試著從學做臺菜,開始融入臺灣社會?
《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封面由知名設計家許晉維設計,內文插畫由國內知名插畫家葉懿瑩繪製。
我一直沒有機會直接從母親那邊學到做料理的手藝,
但是卻用鼻子和舌頭回憶母親的味道。
我相信母親是透過料理,想把她深深的情愛傳達給女兒們。
打開食譜筆記本,我覺得母親的這種心情強烈的敲打在我的心房上。
──一青妙
2013年3月,一青妙藉由《我的箱子》一書,整理了父母親之間的愛情物語,她的家族物語,以及她和基隆顏家的感情物語。《我的箱子》彷彿女兒寫給爸爸的一封長信,滿懷思念之情。
2014年3月,一青妙的新作《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則有如女兒寫給媽媽的另一封長信,藉由書寫描述媽媽親手烹煮過的每一道臺灣料理,回憶、感受、悼念媽媽的母愛!
〈讀者感言〉
【母親的愛情。妻子的愛情。】
By 100名山 VINE メンバー
因為作者的前一本書《我的箱子》寫得非常好,所以我預購了此書。這回在箱子裡的是母親留下的食譜集。較之前作在講述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家族,本作則是道出了以母親的料理為中心的回憶。書中間或穿插有食譜作法,但要據此而做出料理似乎有些困難。關於臺灣的飲食文化與日本飲食文化上的不同,也說得很有趣。母親在要傳達給女兒(作者)重要訊息時會利用寫信的方式。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方法。透過全書的描寫,可以讓人看到母親為家人製作料理的能量來源就是愛情。我也想讓我家的女兒們看看這本書,讓她們知道自己是如何從母親那兒獲得愛情的。
話雖這麼說,我每天也吃著妻子做給我的料理,母親也還健在,但我卻從未對她們表示過感謝。
因為對於《我的箱子》還有些記憶,經由本作輕微的觸動,記憶就又重新復甦,同時,這部作品也帶給我了極為深刻的感動。
這本書並非與前作類似、毫無新鮮感之作,因此我甚為推薦。
【閱讀本書時,偶爾會飄來臺灣的氣味。】
By ケロshe
接續著前作,我興味盎然的讀了這本書。我的丈夫是在臺北出生、長大的,因此我在讀這本書時,興致特別高昂,所以讀來頗為愉快。同時我也很期待有兩個祖國的作者的下一部作品。
作者:一青妙
臺日混血作家。父親是昔日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長男顏惠民,母親日本女性一青和枝。
小時候就讀衛理幼稚園、私立復興小學,十一歲遷居日本,中學時期父親早逝而改從母姓,大學時期母親亦病歿。自牙醫學系畢業後即從事牙醫師工作,同時兼顧以舞臺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並一心致力於臺日文化交流活動。2015年獲聘為臺南市第一位親善大使,2016年成為母親出身的石川縣中能登町觀光大使,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推廣臺灣觀光與文化,堪稱臺日交流的重要推手。
已出版作品包括《我的箱子》、《我的臺南:一青妙的府城紀行》、《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等。其中,《我的箱子》更改編成舞臺劇《時光?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好評不斷。
繪者:葉懿瑩
譯者:陳惠莉
畢業於淡江大學日文系,從事日文書籍翻譯已有多年經驗,譯作有《出版界大崩壞》、《恣虐的樂園》、《緊閉的門扉》等等。
臺灣版序
小妙,吃飯囉!
母親是鲱魚的孩子?
打掃和蘿蔔糕
「責怪」和「生氣」
回憶中的食譜:鹹蜆仔
旅行時的便當
外國人妻
回憶中的食譜:糕渣
蒸豬絞肉的那個
第二個媽媽
回憶中的食譜:紅豆年糕
籤王粽子
透過料理溝通
回憶中的食譜:番茄炒海參
不看‧不說‧不聽
Q彈雞凍
沉睡星人
回憶中的食譜:三杯雞
豬腿毛
給媽媽的信
臺灣版序
二○一三年對我而言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我的第一本作品《我的箱子》得以在父親的祖國─臺灣出版,拜此之賜,以前感覺十分遙遠的臺灣和我之間的距離一口氣縮短了許多。
同時,我循著已過世的父親的足跡頻繁回臺灣的機會增加了,也因此,這一年是我針對自己的身分認真思考的一年。
我覺得「身分」這個名詞在一路走過複雜歷史的臺灣所代表的意義一定比日本還要沉重許多。
對現在的我來說,身為臺灣人的身分問題漸漸具有深重的意義,因而總是讓我思索良久。
在我面世的作品,也就是去年在臺灣出版的《我的箱子》中有提到過,所以有些讀者可能已經了解。我身為臺灣人的父親姓顏,在臺灣北部的港都基隆出生長大,明確的地點是現在知名的觀光景點九份。顏家當時是擁有金礦和煤礦的財閥名門,父則是顏家的長子。
當時的顏家被稱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父親在基隆的家族擁有龐大的家產,甚至有人說足足有一座山那麼多,聽說房子也都是用檜木建蓋而成的豪宅。但是很遺憾,在戰爭期間,因受到空襲而被燒毀殆盡,經過改建之後,現在則成了中山公園。
父親和身為日本人的母親結婚,生下我跟妹妹一青窈。
我現在使用的姓氏「一青」是罕見的姓,在日本也曾經被誤以為是「臺灣人的姓」。事實上,這是我母親娘家的姓。在石川縣的能登半島上的鳥屋町有一個叫一青村的村落,據說一青這個姓就是從那邊來的。
我在日本出生後不久便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在臺灣生活並接受小學教育。
從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代,臺灣的教育都圍繞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主題上打轉,使用的地圖也是涵蓋有中國大陸的大中華民國的地圖。
大家都知道,臺灣曾有很長一段時期處於戒嚴,但是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連「戒嚴令」是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長大成為一個臺灣孩子。
我升上小學高年級後,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一家人從臺灣搬到了日本。當時我十一歲。之後,就一直在日本生活。
在臺灣,我雖然就讀在地的學校,但是一回到家,和家人間的對話全部使用日語,所以搬到日本後,在生活和學校方面幾乎沒有任何溝通上的問題。
之後,雖然曾經回到臺灣,但都是為了親戚之間的事,幾乎沒有到過臺北以外的地方,更不用說到臺灣旅行或遊樂了。我在日本接受高中、大學教育,因此完全失去了身為臺灣人的自覺和身分,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這一方面也是因為父親的過世使然。在搬到日本生活的所有家人中,只有父親一個人背負著臺灣的身分和責任,但是他在我就讀國中二年級時因肺癌過世了,從此「臺灣」便從我們家的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再加上當時在日本有一個現象,會說英語的人往往能搏得他人羨慕的眼光,但是會說中文的人,卻會讓人覺得你是少數奇怪的族群,所以我並沒有很積極主動告訴他人,自己是臺日的混血兒。
之後,我進入齒科大學唸書,當我二十一歲還在學時,母親就因罹患胃癌而過世。畢業後,我成了一名牙醫,同時也開始演戲,回過神來,才驚覺自己已經年過三十五歲了。
我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人,過著幾乎忘了自己是臺灣人的生活。我之所以再度開始意識到自己血液中的「臺灣身分」是源自常有的「搬家」一事。
距今大約五年前,我下定決心重新改建將近四十年的老家,在整理家中物品時,從櫥櫃裡找出了一個日式的箱子。打開一看,裡面放了許多信件和筆記本。那是一疊信和母親的日記。信件包括父母婚前往來的信和我寄給父親或母親的信。我一封一封拆來看,於是,被我遺忘的臺灣記憶便宛如一道水柱,從本來堵住的水龍頭中噴射般流瀉而出。
信中的一字一句像是父親的諄諄教誨,也包括我和父親一起前往的場所以及我就讀的學校、在臺灣吃過的許多美食等所有與臺灣相關的記憶。當中也有當時還在唸小學的我以現在的我所無法寫就的流暢中文寫給父母親的信。於是,我對之前完全遺忘了自己和臺灣有這麼深厚的關係一事,感到無比後悔。
然而,單是後悔並沒有任何幫助。之後,我以自己所能採行的各種方式,追循著父親生前的足跡,開始造訪父親的朋友,想要重新接合臺灣和我之間曾經斷了的牽絆。
父親生前非常喜歡日本。然而,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敗,變得不再是他的國家,自己則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這件事讓他大為苦惱。
父親的日本同學對當時的情況留有鮮明的記憶,他告訴我:
「日本的敗戰,底定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老師和同學都在日誌上寫下『為了日本的重建』之類的文章和敗戰的心境,然而,妳的父親卻隻字未提。對於日本的敗戰,他從頭到尾不置一詞,然而,過了一陣子,他的眉毛卻突然開始掉落,變成了一張沒有眉毛的臉孔,著實嚇了大家一跳。」
聽說之後父親跟朋友這樣談起:
「以前學校教我們的事情都是騙人的啊。」
「老師說過,你們都是天皇陛下的孩子,是一起稱頌天皇陛下萬歲的同生共死的兄弟。可是,等戰爭一結束,你就成了戰敗國日本的國民,而我則是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國民,再也不是什麼天皇的孩子了。我不是日本人了。我再也不去學校了。」
從此,父親真的就不再去上課,日本敗戰之後兩年,他就撤回了臺灣。
我覺得父親對國家或國籍一事嚴密思考的程度倍於他人。他以作為日本人出生,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就在某一天,所有這些觀念卻整個被顛覆,因為衝擊過大,才導致他的眉毛完全脫落。
當時,父親突然從日本人變成了臺灣人,從此不再是日本人,為了這件事,他著實苦惱了一輩子。
父親雖然是大家族的繼承人,卻選擇了和出身於一般人家的母親結婚,或許這正是他無法完全割捨自己內心深處身為日本人的部分。
父親的早逝似乎有部分是他自己的選擇。
父親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平常他會過著正常的生活,然而一年當中總有一次或兩次,短則數天,長則數月,他會將自己關在房裡,既不開燈,也完全不踏出房門一步,只是不斷喝酒。當時年紀還小的我始終無法理解箇中理由。父親的飲食和如廁問題都在房內解決,其徹底的行徑於今想起,不禁佩服母親竟能忍得過去。
我無法確定父親這樣的行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是聽說自從戰爭結束後,他蟄居的頻率便增多了,所以,我想身分的問題應該對父親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在黑暗中,父親一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一再試著去思考父親苦惱的理由,可是還是無法理解。父親也沒有對任何人詳細說明過。
然而,我把後來找到的父親的密友和親戚們的談話內容慢慢地、一點一滴拼湊起來之後,父親片斷的形像便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母親的名字是一青和枝。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於東京都文京區,上有四姐二兄,依序是姐姐、哥哥、姐姐、姐姐、姐姐、哥哥,是一青家的五女。在戰時物資缺乏的貧困環境中,母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婆,因為沒有奶水,只好拿芋頭和米飯來煮汁餵養母親。可是,外婆在生下母親後半年就因為結核病而魂歸西方,之後就由幾個姐姐輪流照顧母親。
當時在前往疏散地長野縣的列車上,背著母親的阿姨日後回想起來,就像講口頭禪一樣告訴我:「我不斷摩搓著和枝冰冷的小手和小腳,一直擔心她會不會死掉了呢。」
戰後回到東京,發現文京區老家一帶已經被燒成了一片枯野,一家子只好重新在北區尋找落腳處,重新出發。母親的父親在東京都的交通局擔任機械師,支撐著一家的生計,但是考慮到還有七個小孩要照顧,遂於母親三歲時再婚。
「新媽媽」是一個從來沒有生過小孩,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女性。除了身為老么的母親,其他孩子都已經到了懂事的年齡,所以始終無法和這個女人親近,家中瀰漫著抗拒父親再婚的氣氛。但是,唯有母親不斷吸吮著分泌不出母奶的繼母的乳房。
小時候,母親的手腳都像棍子一樣細瘦,肚子則凸了出來,皮膚黝黑,體格就像牛蒡一樣。儘管如此,唸小學時,她卻頂著剪短的髮型,和一群男孩子到河邊玩、一起爬樹,簡直像個男孩子一樣。
翻開母親小學時的聯絡簿,發現她的國語、算術、理科等每一科目都有很好的表現,尤其擅長畫圖,美術成績出類拔萃。
升上中學後,她的畫作得到了高度的評價,甚至獲得了文化祭展覽獎。另一方面,她也開始對外語產生興趣,便進入英語社,積極學習英語。中學三年級時,她當時的級任導師在聯絡簿上寫著「開始凸顯出尖銳的個性,容易遭人誤解」。
是因為本身具有藝術家氣質使然嗎?母親具有強烈的正義感,想到什麼就毫不客氣霹靂啪啦說出來,這種性格是否也和身為老么而被默許的特權有關?無論如何,母親並沒有被看似不幸的幼年時期牽絆住腳步,她快速成長著,甚至升上了高中。畢業後,她到人壽保險公司上班,但是二十歲時就毅然決然離職了。
她離職時,同事們送給她的集體紀念文箋上除了有人寫著「妳走了,我會覺得很孤單」,還有「可別再嚷著忘了手提包或一萬圓紙鈔放到哪裡去了」、「小心不要跌倒受傷了」等內容,可見母親一定是個相當冒失的人吧。
……
母親似乎很喜歡她的父親,而她的父親是個沉默寡言,卻又很懂得體貼他人的人。可是外公在我出生後馬上就過世了,所以我對他完全沒有記憶。
父親和母親的邂逅是相當戲劇化的。
母親離開公司後不久,便在開始打工的配膳工作會場上遇到了前來接待客戶的父親。對母親一見鍾情的父親這樣對母親說:
「能借我看一下妳那個戒指嗎?」
父親竟然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提出這種要求,他的感性超乎我能理解的範圍。但是,母親只淡淡回了他一句。
「這是我哥哥給我的很重要的戒指,所以不能借你。」
父親仍然緊咬不放。
「我一定會還妳的,拜託了。」
結果,母親開出了日後一定要還戒指的條件,答應了父親的請求。我也無法理解,母親為什麼會答應父親如此莫名其妙的要求。
據說,事實上此時母親已經有了說好要共度終身的對象。總之,父親的企圖算是成功了。後來,父親以「弄丟」借來的戒指為由邀請母親一起吃飯,送了另一個戒指給母親當作賠禮。於是,兩人就此展開交往,邁向異國婚姻之路。
一九二八年出生的父親和一九四四年出生的母親相差有十六歲之多。當時三十六歲的父親毛髮稀疏,呈現「地中海」狀態。體型雖然不胖,但是身高也不到一百七十公分。說得客氣點,外表應該算是很普通,但是他一定是有某些地方吸引了一向喜歡年長者的母親。
身為臺灣人的父親在日本統治的時代於臺灣出生,接受日本教育長大,從小就到日本留學,之後的人生幾乎都在日本度過。父親在日語的說、寫方面都十分道地,一點都不會讓人懷疑他是外國人。
所以,母親也才能和他相處融洽。唯一一件讓母親感到疑惑的事情是,父親平日白天時都待在家裡看書或喝酒,根本都沒有在工作。
母親雖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是父親也沒有做什麼說明,所以她大概也只能推測父親的家境一定是還不錯。在母親二十四歲那年,父親第一次招待母親到臺灣旅遊。
……
之後不久,母親便和父親結婚,開始了在臺灣的生活,並生下了我們姐妹。接下來就是成為母親的一青和枝透過料理所留給我的故事。
〈打掃和蘿蔔糕〉
……
我在臺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小學。我十一歲那年的十一月,我們家把生活的據點從臺灣移到了日本。
我們在日本住的是兩層樓的獨門獨院。房間數量很多,還有很多大型窗戶,我覺得打掃起來更辛苦了。用吸塵器吸過,再用濕布擦拭地板後,地板還是會被從庭院飄進來的塵土給弄髒,所以一到下午,就得再擦拭一遍。
家中會用到水的地方也會徹底清理,洗臉台四周水花濺得比較嚴重的壁紙或磁磚接縫處也都上了蠟,以達到防水、防黴的目的。穿舊了的絲襪或牙刷經過母親的巧手加工,變成了可以清除細微之處的打掃利器。我都偷偷稱會利用各種工具徹底清除汙垢的母親為打掃大魔王。
我認為,母親的功力並不亞於現在以打掃術聞名的創意達人松居一代女士。
但是,這麼厲害的母親卻也為廚房四周的整理工作感到頭痛,有部分原因是我的緣故。
雖然開始在日本生活,我卻還是常常賴著母親,想吃臺灣料理。而為了要重現臺灣的美味,就必須使用比往常更多的食材和調味料。
尤其是要做「蘿蔔糕」時,有很多材料都是在日本找不到的,準備工作和調理也很費工夫,事後的整理作業更是一大負擔。
「蘿蔔糕」的發音聽起來很可愛,所以很容易記。在臺灣,日文中的「大根」是寫成「白蘿蔔」。把白換成紅,變成「紅蘿蔔」,就是日語中的ninjin。也難怪,兩者的大小雖然有差,但是形狀類似,所以以顏色來做區別命名是有道理的。在中文裡,所謂的「糕」是將各種穀物磨成粉、搓揉製成的食品總稱。
蘿蔔糕就跟它的名字一樣,像年糕般,外形是白色的,通常切成四方形,但是沒有像年糕那般的黏性,軟硬度適中,用筷子就可以切斷來吃,也是喝茶時不可或缺的有名茶點。蒸熟的蘿蔔糕可以沾醬油來吃,也可以用油將兩面煎出一點焦黃色,再沾醬油食用。煎過的蘿蔔糕表面比較酥脆,裡面則比年糕要滑嫩,兩種口感都很好,所以我很喜歡吃。在臺灣,較多人是煎過之後再吃。
而在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則習慣把蘿蔔糕細切成肉丁狀,和蛋或大蒜、蔥等一起熱炒之後食用。
蘿蔔糕本身並沒有特別強烈的味道,可是卻是我定期就會有想吃衝動的食物之一。
這或許是因為住在臺灣的時候,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利用星期日的中午和母親、妹妹及嬸嬸一起出門去「飲茶」的關係。我們固定去的地方是位於臺北市內的國賓飯店、六福客棧以及圓山飯店等飯店的餐廳。
大都會和我們同行的人是被大家稱為小翠的大姑姑。小翠姑姑年輕時曾到日本的音樂大學留學,在家人中,她是父親之外,日語講得最好,又喜歡講話,個性詼諧的人。她總是大聲笑著,稱母親為「大嫂」,非常照顧我跟妹妹。
母親經常一邊喝茶,一邊忘我的和大姑姑聊天,才看兩個女人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著,下一秒鐘卻又看到她們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我看著她們的一舉一動,不禁深感佩服,她們臉上的表情、手、嘴巴竟然可以同時那麼忙碌的活動著。
也許母親是靠著聊天來抒發她在陌生的臺灣生活所累積出來的壓力吧。
對我來說,一個月一次的飲茶時間是可以享受到美味食物的愉快時間,然而對母親而言,也許就等於是現在所說的「姐妹會」一樣的活動。她因為極力控制個人情感而使得精神和活力銳減,而飲茶活動就是她重新充電的重要時刻。
我們在中午十一點半左右抵達餐廳時,店內一半的座位幾乎都坐滿了客人,孩子的哭聲和太太們的笑聲響徹室內,充滿了活力十足且熱鬧的氣氛。光是置身於這種氣氛中,就夠讓人情緒高漲了。
我們一坐下來便會先點茶水。烏龍茶是絕對必要的,不過有時候也會點茉莉花茶或普洱茶、菊花茶等。
等茶水一送上桌,拉著手推車的阿姨就會立刻朝我們的餐桌走來,就好像有人一聲令下,一起為我們展示放在推車裡的點心,展開一場展示大會戰般。
小蒸籠層層疊疊放在手推車裡,上面有加了糯米的燒賣、呈鮮綠色的翡翠餃子、從通透的外皮可以看到裡面的蝦子,看似美味十足的鮮蝦餃、高級的魚翅餃,以及一定不能少的小籠包等。手推車的阿姨們就像變魔術般,一個一個移開蒸籠的蓋子讓我們瞄一眼,一旦看到自己想吃的東西就得立刻用手指指明示意,否則馬上就會被略過。
比較特別的蒸食要算是以雞爪蒸煮而成的「鳳爪」、用排骨蒸煮的「豆豉排骨」,以及我最喜歡吃的牛肚「金錢肚」。
另外還有一道料理叫「腸粉」,是用米磨成的粉揉推成薄薄的皮,然後在皮當中放進蝦子或叉燒肉,捲起來蒸熟,澆上醬汁食用。這道菜吃起來非常滑嫩順口,往往在回過神後才發現吃太多了。
另外還有春捲、像油炸包(將肉餡、粉絲、洋蔥等餡料包在麵粉裡,油炸而成的俄式點心)的「鹹水角」、油條、非吃不可的炒飯、粥、炒麵等,這些飲茶的料理菜色真是多不勝數。
每一盤料理的份量都很少,這是飲茶的好處,即便人數不多,也可以享受到多種料理的美味。年紀尚小的我跟妹妹可以從主食吃起,包括馬拉糕、杏仁豆腐、蛋塔以及甜點,整個都吃上一輪,所以我們都非常喜歡飲茶。
飲茶料理的種類是如此之多,所以我們總是會試著點平常鮮少吃到的料理來嚐鮮,儘管如此,我跟母親一定會點的一道料理就是蘿蔔糕。
點蘿蔔糕時有一個「know how」。首先要對推著搭載有調理專用鐵板的手推車招招手,然後說「一份蘿蔔糕」。等個大約五分鐘,服務人員就會當場煎好三片香皂大小、四方形的蘿蔔糕。把盛在盤子裡剛煎好的蘿蔔糕沾上醋醬油吃進嘴裡,頓時就有
「來飲茶了」的感覺。
對我們家來說,蘿蔔糕是象徵飲茶的一道料理。
可是,如果要自己做蘿蔔糕,就要經過切、刨、發乾、炒、搓、煮、蒸、煎等許多過程,非常耗時。我只看過店裡從煎糕的步驟開始做起,所以一直認為做蘿蔔糕就像做磯邊餅一般簡單,每當母親問我「想吃什麼?」我總是說「蘿蔔糕」,然後不斷催促著「還沒好嗎?」讓母親著實大傷腦筋。
因為想趕快吃到蘿蔔糕,我也曾經黏在正在做蘿蔔糕的媽媽身邊,所以對製作蘿蔔糕的過程我記得一清二楚。
首先是拿出一條白蘿蔔,開始切。一條白蘿蔔的一半左右都得切成絲狀,所以這個作業非常麻煩。用菜刀切絲時,大量的蘿蔔絲會堆積在砧板上。接下來再用食物調理器將剩下的白蘿蔔儘量切細。切好的蘿蔔放進炒鍋裡煮沸,水面就會浮起白色的澀汁。「再等一會兒就好」母親總是一邊說一邊攪拌蘿蔔,她的樣子讓我聯想到煮著要讓白雪公主吃下肚的毒蘋果的壞皇后,心中不禁覺得有點恐怖。
食材要用到蝦米和乾香菇、中式火腿等,將它們一起用鍋快炒,然後放進正在熬煮蘿蔔的鍋裡一起煮,最後加入白色的「蘿蔔糕的粉」倒進桶子裡。
母親經常從臺灣帶回日本、她稱為「蘿蔔糕的粉」的東西是裝在上面什麼都沒寫的透明塑膠袋裡的。我問那是什麼粉,她告訴我是「在來米粉」。這是在日本不容易買到的東西,卻是製作蘿蔔糕不可或缺的材料。
臺灣本來就是以米食為主的地方,吃的是沒有黏性,柔軟而有甜味,一種叫秈米的長粒種米。在日本殖民時代,吃不慣秈米的日本人遂把有黏性而柔軟的粳米(短粒種)帶進臺灣,臺灣便也開始大面積栽培粳米。從此,臺灣原本生產的秈米被稱為「在來米」,而從日本帶進來的粳米則稱為「蓬萊米」,以做區隔。
蘿蔔糕的粉,也就是所謂的「在來米粉「是將秈米磨成粉狀」的東西。
加了在來米粉的材料經過蒸煮後,就變成了帶有光澤的蘿蔔糕的原形。
冷卻之後、切成四方形,終於就出現了放在餐廳推車上,那令人熟悉的蘿蔔糕的模樣,接下來就是煎烤的工夫了。剛煎好的蘿蔔糕香得讓我覺得等上幾個小時都值得,感覺比在餐廳吃到的要來得好吃幾百倍。
我們一邊大讚好好吃,一邊忘情吃著蘿蔔糕,一旁母親則被處理善後的工作給追著跑,忙得團團轉。
食物調理機還有砧板、炒鍋、兩耳鍋、蒸籠、桶子、篩子還有小竹杓。流理台上堆滿了因沾附油脂而顯得黏乎乎、髒兮兮的用具。
當時還沒有洗碗機那麼方便的東西,所以只能一樣一樣用手洗。一開始清洗,就發現食物調理機的角落若隱若現的有著髒東西,於是便將布條包捲在牙籤上開始擦拭起來。接下來又覺得不能對卡在篩子網眼上的東西視若無睹,於是便用牙刷去刷洗。
用棕櫚刷清除蒸籠上的汙垢後,必須在通風良好的地方舖上報紙,將蒸籠排放上去晾乾。要花上比平常多數倍的時間做清理工作,使得母親這個清掃大魔王也不禁大嘆「太麻煩了」,可是我完全不放心上,頂著一臉沒事人的表情,大啖我的蘿蔔糕。
在我當時生活著的一九七○和八○年代的臺灣,說到早餐外食,主要就是豆漿和燒餅、油條、飯糰。最近我到臺灣的早餐店去吃早餐時,發現除了有我熟悉的選項,還有三明治、漢堡、炒麵、餃子等,甚至還有蘿蔔糕,這讓我大吃一驚。我也看到有人一早就理所當然的點了豆漿和蘿蔔糕,感覺上就跟吃荷包蛋一樣自然。我發覺蘿蔔糕就近在身邊,不禁大喜過望。
可是,點來吃之後卻發現味道很普通。不管在哪家店吃,結果都一樣。粉的味道都太強烈,沒有蘿蔔的風味和纖維口感。外形看起來是蘿蔔糕沒錯,但是味道和我所知道的蘿蔔糕卻大相逕庭。我好失望。
我知道,在早餐店廉價販賣的蘿蔔糕,有大半為了節省成本和手續都極力減少蘿蔔的用量,添加在裡面的材料和蔥也都只有一點點,甚至在米粉中加水做成餅狀,然後就拿去蒸煮。
我還沒有遇到勝過我小時候經常吃的蘿蔔糕的味道。母親所做的蘿蔔糕就有如此深刻而道地的美味,只要一吃進嘴裡,就會立刻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自從母親過世之後,蘿蔔糕就從我們家的餐桌上消失了。好幾次我都想重現蘿蔔糕的美味,可是只要一想到善後的工作,我就一直猶豫著。
不過最近找到母親的食譜一事像是往我背上推了一把,我下定決心,試著遵循母親食譜上的指導,挑戰製作蘿蔔糕。
我用削皮器削掉蘿蔔的外皮,再用萬用薄切器把蘿蔔切成細絲。用攪拌器將一半份量的蘿蔔絲攪得更細,剩下的則放進鍋裡煮至沸騰,冒出白色的水泡。到這個步驟跟母親做的都一樣。在等待熬煮的期間,我先準備蔥和火腿、蝦米、干貝、乾香菇等食材。
接著,我將蘿蔔的煮汁加入在來米粉中攪拌。近年來,在進口的品項數量變得豐富許多的中華食材店中已經可以買到在來米粉了。
將上述食材切絲之後熱炒,和煮過的蘿蔔及攪拌器裡的蘿蔔、調味料等一起放進麵糰當中,再把鍋子放爐上,一邊加入發乾水一邊用小竹杓攪拌。然而越是攪拌,麵粉糰就變得越發粘稠,開始粘附在小竹杓的四周,變得沉重無比。
儘管如此,我這麼努力還是值得的,原本堆積如山的蘿蔔絲慢慢消失了,我把混合全部食材所做成的麵糰倒進桶子裡,再用蒸籠蒸煮約一個小時。
打開蒸籠時,頓時整個人被水蒸氣給籠罩,混合著香菇乾和蝦米味道,中華料理特有的香味撲鼻而來,水潤有光澤的蘿蔔糕出現了。
可是,想切開蘿蔔糕時,蘿蔔糕卻粘附在菜刀上。原來只有表面是光滑的,裡面並沒有凝固。我試著把蘿蔔糕放到平底鍋中去煎煮,卻始終無法凝固。我像吃文字燒一樣將蘿蔔糕鏟起來吃,發現外表雖然不是挺好看,但是味道倒也沒有那麼差。
我懷疑,母親是不是忘了把某些最重要的事情寫進食譜中了?
說起來,母親這個人就像海螺小姐一樣粗線條。外出購物時忘記帶錢包是常有的事;全身打扮得光鮮亮麗,可頭頂上卻還頂著個髮捲;要不就是牢牢地鎖住了後門,玄關門卻忘了上鎖,做什麼事情都是百密一疏。
我一邊在心中對母親發牢騷,一邊快速清洗著堆積如山的調理器具,同時在心中發誓,一定要去熟識的臺灣料理店打聽蘿蔔糕的正確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