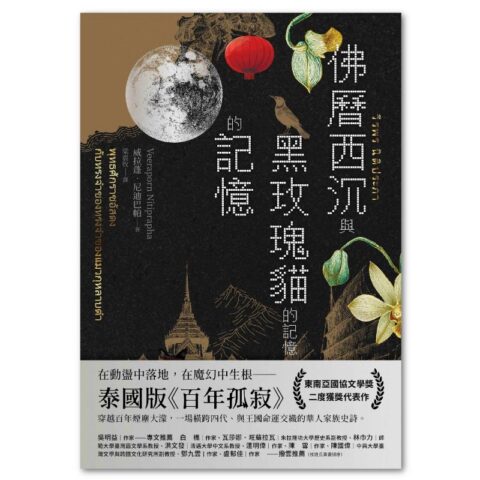守護天使的眼淚
原書名:Fremde Signale
出版日期:2014-07-23
作者:卡塔琳娜‧法柏
譯者:賴雅靜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0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4207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來自法國、蘇聯、紐約的三個陌生年輕人,
互不相識,各自早夭在不同的年代。
但他們都變成了天使,
要用50年的漫長時間去保護一個陌生的女子阿莉!
是命運的擺布?或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
瑞士傑出女作家卡塔琳娜‧法柏 備受國際媒體矚目,躋身瑞士文壇的精心傑作!
「我們不願,人們將我們遺忘。
我們曾有過軀體、願望、夢想。
我們曾經活過。
我們依然活著。
我們就在這本事件簿裡,因為這是由我們講述的。」
小說主角阿莉(又稱阿塔莉)是一位出生在二十世紀的女孩,生於龐大富有的家族,有十個兄弟姐妹,小時候曾因吃下太多植物而病危,長大愛飆車冒險,也曾歷經婚變與癌症。阿莉從出生開始,就有三位天使經常暗地保護她:
米海爾‧斯列丁(1925-1942):一個蘇聯青年,自願從軍,十七歲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對抗德軍的戰役中死亡。
黎內特‧葛連德全斯(1770-1786):在法國出生的女孩,因十六歲照顧妹妹而染上腦膜炎病亡。
波利斯(鮑伯)‧東巴(1938-1951):在十三歲時因罹患癌症病亡於紐約。
傳說年輕就亡故的靈魂可以成為保衛他人的天使,但語言隔閡無法傳達,這三個天使要如何環繞與守護這位女孩阿莉的成長?
這三位早夭的天使,生於不同時代,傳達的訊息對女孩來說就如同陌生的符號,但他們有共同的信念,相信一定有辦法讓女孩度過一切成長險境,讓她長大成人。這三個年輕的靈魂不僅輪番穿插出現,以獨白方式描述女孩的經歷,同時也透露各自的生平遭遇,家庭與牽掛,並看見自己離開人世以後,親人在人間承受的一切。作者卡塔琳娜‧法柏透過這本小說,藉由大膽創新的寫作手法,拼湊她五十年的生活圖像,並成就這部備受瑞士文壇肯定的力作!
※ 國際媒體推薦
「一本諦聽陌生訊號的初音,巧妙將錯雜敘述橫跨五十年人生道路與世界歷史的各種聲音,捏塑成具體形象的精采之書。」──伊娃‧巴赫曼,聖加侖日報(St. Galler Tagblatt)
「一本描述逝去者殫精竭慮的生活,引人入勝的寧靜好書。」時代週報(DIE ZEIT)
「一部微型傑作。」──東福里斯日報(Ostfriesen-Zeitung)
「藉由守護天使的視角講述一部傳記,是個極富原創性的構思;而賦予這種視角屬於自己的身分印記,更是卡塔琳娜‧法柏第三部作品絕妙的藝術手法。」──伊娃‧普菲斯特(Eva Pfister),瑞士《週報》(WOZ)
「瑞士與蘇黎士都該發現,他們擁有多優秀的一位作家。」──胡伯‧溫克斯(Hubert Winkels),文學評論家
「這是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卡塔琳娜‧法柏這位女性作家終於得以傲然被接受為瑞士最優秀的女性作家之一員了。」──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radio)
「冒著許多風險但也大獲豐收:卡塔琳娜‧法柏以她這部極不尋常的小說《守護天使的眼淚》將自己推上了瑞士文壇的菁英階層。」──瑪麗—路薏絲‧齊默曼(Marie-Louise Zimmermann),伯恩日報(Berner Zeitung)
作者:卡塔琳娜‧法柏
1952年生,曾擔任醫師,從事醫療工作多年,現居瑞士蘇黎士。處女小說首作《偶爾我會在天際見到一片遼闊無邊的海灘》以「別出心裁的剪接技巧」令評論家驚艷,並於2003年榮獲勞里斯文學獎(Rauriser Literaturpreis)。2005年出版故事集《我用一把刀計算時間》(Mit einem Messer zaehle ich die Zeit)及其他作品,由畢爾戈出版社出版。
譯者:賴雅靜
1962年生,政大中文研究所畢業。老家在南投,住過三個國家、許多城鎮,目前落腳鶯歌。專事翻譯,譯有《夢書之城》、《阿爾漢布拉宮》、《一切從減》、《時空戀人》三部曲、《大海的盡頭在哪裡?》、《守護天使的眼淚》、《萊茜的祕密》等青少年文學、成人書籍及童書上百種,平日喜歡和小外甥與家中的貓玩耍。
序幕
分娩
十個子女,每個都活得好好的
昔日我們所在的地方
墜落的星星
火與標記
莫遺忘
不是最終章的一章
人名索引
序幕
米海爾‧斯列丁
我是個在為祖國而戰的偉大戰役中喪失性命的英雄。
失敗者是什麼意思?是就歷史觀點而言?是就個人觀點而言?
舉例來說好了,在戰爭中陣亡的是失敗者,僥倖存活的就是勝利者。
但個人既不可能是勝利者,也不可能是失敗者,個人只能是失敗或勝利的一部分。
而我,我是我們戰勝法西斯主義者的偉大勝利中一個死去的部分,我是我們所贏得的偉大勝利的一部分。
但我不知道,怎麼能判定某人在戰爭中獲勝了。我知道的是,戰爭中的每個個人最後都輸了——包括倖存者。
但至少,追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者最後不得不離開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所謂的勝利。
但現在,當我偶爾見到我昔日的戰友們在某個溫暖的六月天伴著他們的妻子在公園裡散步,我忍不住會思忖,我失敗了。於是我會認為我沒能覓得妻子,沒能完成學業,是老天太不公平了。
不公平的還有,我沒有廚房讓我可以陪著妻子喝茶;我不再喝茶,我已死去並且得照看一個封建主義的小生命。
我得照看,好讓另一個人能活命。
這歸屬於我們的事件簿。
我那中途就停止的人生,我如何守護阿莉,還有我們:阿莉與我,阿莉、黎內特、波利斯和我,所經歷過的人生。
我們是個共同體。
我們著重的是大方向。
★
黎內特‧葛連德全斯
偶爾我自覺彷如昔日,如同我還活著時,於是我遙望著天邊的雲朵作著夢。
我追隨雲朵變幻萬千的形態,觀察它們如何堆聚、如何散為絲縷飄移。
我彷如還活著的人般觀望著雲朵,一如往日。
從前我無法想像,世上除了人類與動物,還存在著另一種生命型態。
我說不出,現在我是什麼。
我負責照看阿塔莉,此外無他。
在我們的事件簿裡該收錄什麼?
絕對不只有令人哀傷的事件,不只有令人哀傷的故事。也許該收錄的就是我們生前的人生,還有現在我們把她照顧得多好,不讓她發生任何事故;以及我們與人類有多親近,還有,遭人遺忘有多麼令人感傷。
※
波利斯(鮑伯)‧東巴
如果有一本關於我的書,書名大約會是:
我人生的浮光掠影。
稍後我會再詳細說明。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該如何述說;死時我才十三歲。
年紀才十二歲時,黎內特就像成年婦女那樣工作,她照顧病人,產婦分娩時在旁協助,還認識一個住在豪華宅邸的貴婦穆耶伯爵夫人。至於米海爾,他是個戰爭英雄,他曾經是軍人,曾經摧毀過德國坦克。
我有過美好的人生,其中當然也免不了有些問題。我也有過敵人,甚至還算得上戀愛過,只是我的人生太過短促了。
我本該成為不凡的人物的,我非常聰明。我在學校裡過得並不順遂,我人緣不怎麼好;嗯欸,也許還不差吧⋯⋯我往往只看到事情的黑暗面,但佛克曦‧雷恩總是鼓勵我,她教導我以比較輕鬆的態度看待事情;老實說,這正是她一直以來所教導我的。
我曾有過美好的人生,直到我生病時才變調。
我想念那個世界。
在某些時刻裡,我會像活著的人一樣,感到有點心痛。
☆
分娩
由米海爾‧斯列丁、黎內特‧葛連德全斯與波利斯‧東巴講述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一棟赭色大宅座落在湖畔某個庭園裡,那裡有著一片草地、玫瑰花架、許多參天老樹。
陌生人的生活影像。
一些人在走動,他們來來去去,在桌上擺放餐具。
他們在吃東西,像我還活著時一樣吃著東西。
他們在大宅前方一株雄偉的栗樹樹蔭底下就座喝著東西,樹枝在風中搖曳,湖水泛起陣陣細浪拍打著一段湖邊的堤牆。兩個男孩在草地上嬉戲,聽到一聲高亢的呼喚,頓時轉頭望著屋子。
陌生人的生活,陌生人的環境。
我重新認出了這個世界,但這卻成了另一個世界。
午後時光慢慢轉為黃昏,黃昏轉為夜晚。
古老的大宅裡所有房間的燈火都亮起,之後又熄滅,一盞接著一盞。老樹們簌簌作響,遠方傳來微弱的聲音,是孩童的話語聲,接著又歸於靜寂。
如果我還活著,現在應該是二十七歲。
我應該已長大成人,說不定還結了婚,成了孩子們的爸爸了。那麼我會見到我自己的孩子一一出世,我會協助我妻子,或許還得安慰她。我希望我有一個勇敢的妻子,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妻子,而在她分娩的前夕我絕對不會丟下她一個人不管。
我會和她共同坐在桌邊用餐,陪她等候。
而現在我卻在這裡,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卻怪異地覺得自己恍如新生。
我還未曾見過人類分娩的情形,只看過一次狗兒生產。
我還未曾見過如此瘦弱,卻有著這麼大肚子的女人。在我們那裡所有的婦女都很強壯,至少絕大部分都是。
我來得太早。
這個孩子還沒出生。
栗樹在敞開的窗前簌簌作響,送來些許涼意。
外頭幾乎沒有任何聲響,只偶爾傳來一隻鴨子的呱呱叫聲、波浪拍擊湖邊堤牆的汨汨聲、嘩啦聲,以及其間偶爾一輛汽車從大宅後方大馬路駛過的聲音。
逼近午夜時分,八月的夏日。
這裡不只有我。
我有幫手。
我的幫手——
是來支援我的,這樣對我比較好。
我太過緊張了。
在戰爭中我總是過於緊張,他們沒有增派軍力給我們。
我把這種情況想成了——警訊。
災難來臨前的預感;但這裡一切卻都如此詳和。
我的幫手,生前,是個少女。
現在她就在我身邊。
和我共同等待這個新生兒。
她說,這種炎熱的夜晚她很熟悉。
我也熟悉,基里洛夫西納的夏夜情況也相同。
當房間裡柴火直到夜深時還餘火未熄時。
高敞的窗戶外頭湖泊閃爍著碎光,溫暖的湖水、草地、青草與腐朽的氣息一路飄送到屋內。水讓世界各地看起來全都一個樣,夏夜的湖泊隨處都有。
我能穿透這個女人。
我能穿透她的身軀。
我看得到小寶寶——在她腹內。看得到小寶寶在吸吮,看得到他圓滾滾的腦袋——
他腦袋好大——腦袋這麼大不好,對女生來說很不好。
★
胡扯,腦袋大對女生沒什麼不好,我自己腦袋也很大,而且雙腿細瘦。母親老說我腿瘦如柴,但我仍然是我們家最健壯的,直到最後我一直都像匹馬那般勤奮工作,整個村子裡大家都在呼叫我——不分季節,不論什麼事,老是黎內特,你可不可以⋯⋯或是黎內特,快點過來。
我看過好多分娩的過程,也從旁協助過。瑪莫特出生時我也幫過忙,結果她成了我的孩子,她幾乎不讓母親碰她,因為她想待在我身邊。我們在庭院裡工作時,就把她的搖籃吊掛在糧倉裡視線看得到的地方,讓她在搖籃裡搖呀搖。等她大一點她也老呼喚我:黎內特,或是涅特,涅特其實挺難聽的,但她好長一段時間不會叫黎內特,只會涅特——哦對了,我根本不懂我為什麼也來到這裡。
大概是米海爾太緊張了吧,他那麼年輕,但年紀比我大;我死的時候比他小一歲。
她沒上床。
她等候胎兒出生,她焦躁不安。
我們總是盡可能快快上床,為了多爭取一分一秒的睡眠而奮鬥,尤其夏天白日漫長,蟬鳴嘹亮,熱氣又總是滯留在屋裡。
這個女人發著呆但不上床,她長得極美,肌膚光亮,有著雀斑和富有光澤的紅褐色秀髮。這裡好漂亮,這個小傢伙未來的生活一定會很順遂的。
她被人抱在手上,被人叫做小香腸、蟲兒或阿塔莉。阿塔莉聽起來像匈奴人的名字,像要發動突襲!
但黎內特喜歡這個名字,現在她只叫阿莉「阿塔莉」。
沒有人叫她正式的名字。
她有五個哥哥,最小的叫康斯坦汀,那是個反動的名字,可是很好聽,是個道地的俄國名字。
康斯坦汀。
不是蟲兒,也不是小香腸。
那樣的稱呼不適合他,他的眼睛太聰慧了。
在一個共同體中不該有太多的爭執,但每個人必須維持一貫的坦誠。想找到真正的平衡
點,對我們而言實在不容易。
平靜的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
我只是不太喜歡他們帶著孩子在樹林裡射殺動物,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變得很緊張。
我會緊緊跟著這個小傢伙,近得她都覺得冷。而每次槍聲響起,她跟我就像白楊樹葉般戰慄!
這時黎內特就得設法讓我鎮定下來。如果我恢復鎮定,阿莉也就會恢復鎮定。
我不懂,這麼富有的人家為什麼要在樹林裡射殺動物來吃。
她父親既是工廠老闆、資本家,也是個大富農,是非常有錢的農民,但他很乾淨,跟電影裡我們的富農一點也不像,他總是一副剛洗好澡的模樣。他的肌膚曬成了好看的古銅色,有著一頭白色的長髮,穿著布料厚重的老式外套和褲子。
在我們那裡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服裝了。
只在小說或電影裡才看得到。
我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退化。
我居然會來到這裡,真怪。
政治變得令我費解,我缺乏方向感,我迷失在歷史的叢林裡。
我被德國人殺死,但現在我卻在保護一個小德國人。
如今我們置身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但他們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他們蓋了許多新房子,不論哪裡,龐大的冰箱裡都裝滿了香腸、肉類和水果。
真正的德國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德國屬於美國人跟我們。
他們的總理叫做阿登奧爾。
他們說,他不是納粹。
真正的納粹都還高坐在法庭上和學校裡,而且都跟一個叫理查德‧華格納的有交情。
這是阿莉的母親說的,但我不知道,她的政治知識是否可靠;很可能並不可靠。
我也學到了許多新知識,比如愛因斯坦是個著名的科學家,還有他反對希特勒等等。
他發明了原子彈,但他也跟約瑟夫‧史達林一樣,都是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
而他們也逼他參與戰爭。
這真是個大悲劇。
阿莉的母親也可能發生這種事:大悲劇。
她眼神總是非常憂傷,彷彿認為悲慘的事件隨時會降臨。
我覺得她非常孤單,那是一種沉重的孤獨感,而她很可能已經活在這種孤獨感中許久了,說不定一直都如此;然而她幾乎從來不曾真正隻身一人。
我不太清楚她做的是什麼工作,她整天都在忙,寫許多信,確認各種單子,她有自己的辦公室。
晚上她會接待賓客,有許多賓客來到這裡,幾乎每天都有。之後她就回她的房間,走得又急又輕,彷彿一整天都在等待這一刻,等待一人獨處。
有時她也會過來看看孩子:阿莉和她哥哥,但都是在他們睡著了以後。
阿莉都不讓她離開,如果有人作勢準備離去,她就會大吵大鬧;阿莉不要別人離開自己。
就這樣,偶爾在午夜過後,阿莉的母親會過來,注視著睡夢中的孩子良久良久。
她會站在孩子們的床邊,聽著他們的呼吸聲─跟我們一樣。
然後她就悄悄離開。
回到她房間裡,回到莫大的孤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