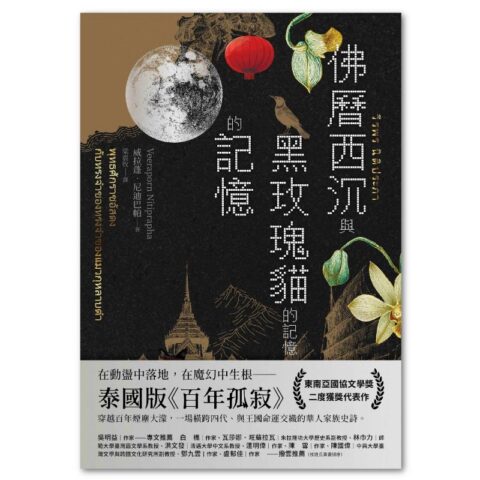孤獨的反義詞
原書名:The Opposite of Loneliness: Essays and Stories
出版日期:2015-09-02
作者:瑪麗娜‧基根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72
開數:25開(21×14.8 cm)
EAN:9789570846072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紐約時報》、亞馬遜書店暢銷書
超過140萬人點閱、耶魯畢業生紅遍全球網路的最後演講
以精準文字探索人性最深處的孤寂,道出年輕世代的困惑與理想
知名作家王浩威、王聰威、朱宥勳、郝譽翔、孫梓評、蔡素芬、鍾怡雯深情推薦
「我們找不到一個詞來表達孤獨的相反意義。
如果有的話,我得說,那就是我此生所追求的;
那就是我衷心感激耶魯帶給我的感受,
也是我害怕明天一早醒來、畢業離開之後,即將失去的感受。」
才華洋溢的耶魯女大生,畢業後五天因意外驟逝
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吸引超過140萬人點閱
慧黠的文字詩意、大膽而力道十足
充分捕捉到年輕世代的希望、徬徨、孤寂、摸索與掙扎……
耶魯大學畢業生瑪麗娜‧基根,立志用生命當一個真正的作家,年僅22歲,已在身後留下豐富的創作,《孤獨的反義詞》這本書集結了她的短篇故事及隨筆共18篇,道出各種人物及形式的孤獨:猝逝的曖昧情人、空巢期的父母、駐守伊拉克的軍官、暗藏刺青的老婦、失聯潛艇的船員、擱淺的鯨魚……等,全然不落俗套,篇篇撼動人心。
2012年5月,瑪麗娜以優異成績畢業,前途一片光明燦爛。她創作的音樂劇即將在紐約國際藝穗節上演,知名雜誌《紐約客》也有一份工作等著她赴任。不幸的是,畢業後五天,一場車禍驟然奪走了這個才華洋溢的年輕生命。瑪麗娜畢業前夕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孤獨的反義詞〉,在網路上被熱烈分享轉載,不僅是因為文中洋溢的無限可能性與現實的對比過於令人震驚惋惜,更在於她說中了廣大同代人的心聲,宛如《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什麼才是屬於我的志向與夢想?如何善用自己的才能為世界帶來改變?瑪麗娜的生命永遠停駐在2012年,而她遺留給世人的文字,將讓人心頭無可迴避地重重一震。
※ 得獎紀錄
入圍水石書店2014年度選書決選
《紐約時報》非小說暢銷榜#11
美國亞馬遜書店暢銷書
※ 國外知名作家推薦
安‧法第曼(Anne Fadiman),美國國家書評獎得主、作家、耶魯大學寫作課講師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西方正典》作者、著名文學教授暨評論家
J. R. 莫林格(J. R. Moehringer),《溫柔酒吧》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 國內名家推薦
朱宥勳──專文導讀
王浩威、王聰威、孫梓評、郝譽翔、蔡素芬、鍾怡雯──深情推薦(姓名排列按筆畫順序)
※ 媒體名人書評
以瑪麗娜・基根22歲的表現來看,毫無疑問可視為「頂級新秀」。她的小說毫不掩飾自己年輕的、對生命的熱望,但她卻也足夠聰慧,總是憂患著美好的一切將何時、如何消逝。如果她的人生是一篇小說的話,我會說,這是一篇很有幽默感的「預知死亡紀事」。
──朱宥勳,台灣知名作家、文學書評刊物《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在她的短暫生命中,瑪麗娜‧基根展現了早慧的文字掌控力。她略帶嘲諷、睿智又熱情奔放的語調令人難忘,而她生氣勃勃的精神,強烈地提醒我們要珍惜當下。儘管每一個句子都隱隱讓人想起她來不及實現的未來,這本卓越的作品集讀來仍令人深感愉悅、受到鼓舞,因為它讓大家知道,作者本人就是個奇蹟。
——J. R.莫林格(J. R. Moehringer),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暢銷書《溫柔酒吧》(The Tender Bar)作者
我永遠不會停止哀悼我所鍾愛的學生──瑪麗娜‧基根。瑪麗娜原本前途不可限量,本書就是部分證明,只可惜隨著她的逝去,這份希望也跟著殞落。綜觀全書,她展現了逼真且張力十足的敘事技巧。除此之外,她更對這一代人大聲疾呼:不要為了區區職場浪費了才華,應該把青春的尊嚴與活力投資於自我提升、改善這個紛紛擾擾的社會。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耶魯大學人文與英國文學教授,著名文學教授暨評論家,《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作者
說出每一個社會新鮮人的樂觀與精神症狀……在此千禧時代,反諷已晉升成了藝術型態;基根為這一代人的集體不安全感帶來覺醒,然而,她的精準描述,唯有同樣深處於不安全感的人才寫得出來。她永遠無法得知讀者從她的作品中得到的幫助,何其遺憾!
──《出版人周刊》
作者:瑪麗娜‧基根
生於1989年,卒於2012年,為獲獎作家、記者、劇作家、詩人、演員,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非小說作品曾發表於《紐約時報》,小說則曾經刊載於《紐約客》網站,並且獲得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短篇小說選介》(Selected Shorts)節目選讀;至於音樂劇作《獨立》(Independents),則獲得《紐約時報》評論家推薦。發表於《耶魯每日新聞》的最後一篇隨筆〈孤獨的反義詞〉在全球迅速掀起風潮,吸引來自98國超過140萬人點閱。
更多資訊請參考網站:www.theOppositeofLoneliness.com
推薦序 如果就停在這裡/朱宥勳
序言 用生命當個真正的作家/安‧法第曼
孤獨的反義詞
【短篇故事】
寒冷的牧歌
寒假
朗讀
天真
翡翠城
行李招領
萬福,滿懷恩典
硬化治療
深海挑戰
【隨筆】
變動中的恆常
我們為什麼關心鯨魚
穀類抗戰
找回末世論的「趣味」
職業殺手
就連薊菜都會存疑
觀察的藝術
獻給「特別」的歌
推薦序
如果就停在這裡/朱宥勳(台灣知名作家、文學書評刊物《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閱讀《孤獨的反義詞》,是最近一年來,第二次讓我想到「自己」的事件。這不太對,一個認真投入文章的讀者,不應該太常想到自己,那意味著入戲不夠深、意味著從第一秒起,我的詮釋就註定有某種歪斜,無論是貶抑或讚揚的效力都要打折。但我沒有辦法。第一次揮不去這樣的念頭,是在今年一月中,稍長我幾歲、才華耀眼程度遠超過身分證上的數據落差,但猶可腆顏稱之為「同輩寫作者」的江凌青,忽然急病去世的時候。
那實在過於突然,就像瑪麗娜・基根一樣,除了命運以外找不到任何可以具體怨懟的目標。
在各方朋友的幫忙之下,我們在二月號出版的書評刊物《秘密讀者》上,策畫了江凌青的紀念專題,試著盤點她在文學創作、電影研究、藝術評論上的成就,還整理了一份目前為止最完整的著作年表。校稿時,我一字一字讀過那些壓抑著哀痛,努力用自身的學識和判斷,向江凌青致上敬意的評論者們所撰寫的文章,除了同樣的悲傷和惋惜以外,我忍不住自問:如果是我,會怎樣呢?如果我就在這一秒死去,《秘密讀者》或其他文學刊物會策畫出怎樣的一批文章?截至目前為止,我的寫作值得怎麼樣的對待?這份著作年表會有多少比例,是我羞於承認的文字?
《孤獨的反義詞》重新喚回了這些自問,特別是瑪麗娜・基根似乎跟我更「靠近」一些:我們只差一歲,同樣熱愛寫小說,在大學階段就熱切地盼望能走向作家之路。而且從她的隨筆,和她寫作班的老師安・法第曼的追憶看起來,她的個性應該蠻嗆的,有一種心有所愛,所以不惜武裝自己來捍衛一切的姿態。再說下去就接近裝熟了,但我至少可以說,如果我們能在某些時空下遭遇,我們可能會是很好的朋友;或者讓我稍稍自抬身價地說,我會將這樣的同輩寫作者當作是可敬的對手。
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閱讀這十八篇短篇小說和隨筆的。
從這本書的編排,就可以看出瑪麗娜・基根身邊的人所致上的煦煦情意。她是在男朋友駕車出車禍時去世的,而本書的第一篇小說〈寒冷的牧歌〉,正好就是女性敘事者在交往中的男朋友猝死之後,如何面對死亡及後續情感糾葛的小說。安・法第曼的序中提到,在她去世的當下,正是基根家人要慶祝父親五十五歲生日的那天,「她的父母正等著她,桌上有龍蝦,媽媽還替她做了無麩質草莓蛋糕,因為瑪麗娜有麥麩不耐症,無法消化小麥製品。」因此當我讀到小說〈天真〉裡面,兩次提到敘事者跑去吃了龍蝦大餐時,幾乎可以違反評論者的職業道德——不能混淆角色和作者——地肯定,瑪麗娜・基根真的喜歡吃龍蝦。這種一點都不重要的細節,通常都是真誠的。然後隨筆散文中,也收了一篇〈穀類抗戰〉,開頭就告訴我們,已經厭倦了無麩質食物的她如何渴望在臨終時刻,能夠瘋狂大吃:「一盒奧利奧巧克力餅、一包金魚餅乾、一個麥當勞漢堡、各種口味的唐先生甜甜圈、酥皮雞肉派、口袋餡餅、大的義大利香腸披薩、法式可麗餅,和一杯冰啤酒。」
如果她的人生是一篇小說的話,我會說,這是一篇很有幽默感的「預知死亡紀事」。
但這些「巧合」都不可是單純的巧合,而是編選者的愛。他們挑選遺作,將之組合成一本書的時候,不可能沒有想到這些事情。隨筆的最後一篇甚至是〈獻給「特別」的歌〉,誠實地說出了所有年輕的藝文創作者內心深處,關於成名和被寫入歷史的渴望,以及對那些已經名列經典的作品是如何地嫉妒和孺慕。這不但再次提醒了我們瑪麗娜・基根逝去的可能性,也在結構上遙遙呼應了〈孤獨的反義詞〉一文,與安・法第曼序文的開頭,那位「有心遏阻文學之死」的勇敢年輕人。
從作品來看,瑪麗娜・基根值得這樣的愛。雖然本書收錄的作品不算多,但其中若干作品,以二十二歲的表現來看,毫無疑問是可以視為「頂級新秀」,寫在文學圈內人的年度球探報告前排的水準。〈寒冷的牧歌〉書寫的情感掙扎既幽微又綿密,最後以一本日記直面傷害、嫉妒與愛情,寫起來十分靈巧,而她略微直白的語言也平衡了小說結構上的「匠氣」,達到了很真摯的平衡。〈寒假〉則令我想到比較早期的艾利絲・孟若,年輕的生命正有一切美好的可能,但上一代人受到的傷害,卻像是陰影一樣預示了生活悲觀的本質。瑪麗娜・基根的小說毫不掩飾自己年輕的、對生命的熱望,她常常寫到那種找到真愛、十分篤定的女子,「這一次是認真的。」但她卻也足夠聰慧,總是憂患著美好的一切將何時、如何消逝,如同〈朗讀〉這篇設想精巧的小說,也包括〈萬福,滿懷恩典〉這篇。後者是我認為她最好的一篇小說,那是一種對日常生活如何艱難的想像力,雖然結局的手法並沒有超過〈寒冷的牧歌〉的模式——沒有交出去的日記,沒有交出去的「替代耶穌」,歸根究柢都是一種遲疑和拒絕。但是從想法到執行,〈萬福,滿懷恩典〉所達致的水準,放諸台灣同輩寫作者的短篇小說來比較,是十分罕見的。
〈翡翠城〉和〈深海挑戰〉這兩篇,則是相對比較生澀,但更讓我惋惜作者在寫作上的可能性的作品。前者寫美伊戰爭的一樁間諜事件,後者寫潛艇在深海中失事、無人救援的絕望,雖然採取了比較取巧的敘事方式,但她敢於挑戰這種難度的題材,卻是讓人驚豔的。
如果就停在這裡。我一邊讀,一邊自問的問題:如果我,或同輩的寫作者就停在這一刻,我們能表現得比瑪麗娜・基根更好嗎?答案是很明顯的,顯然我們並沒有太多能理直氣壯地列在球探名單更前排的名字,畢竟能夠在這個年紀爭取到《巴黎評論》和《紐約客》實習機會的人,幾乎不可能是浪得虛名。但也許,對於這樣一位早逝的同代人,最大的讚譽可能不是「你已經寫得很好了」——這是我最不同意安・法第曼那篇熱情洋溢地告訴我們她多優秀的序文的地方。
不,真正令人難過的是,從這些作品中暗示的潛力來看,她還寫得不夠好。
比起她本來可以達到的那些。
序言(節錄)
用生命當個真正的作家/安‧法第曼(Anne Fadiman,美國國家書評獎得主、作家、耶魯大學寫作課講師)
初次見到瑪麗娜基根,是在2010年11月10日。那天,我在耶魯主持一場院長茶敘,主講來賓是小說家赫爾普林(Mark Helprin)。赫爾普林先生表示,要在當今這個時代靠寫作出人頭地,簡直難如登天。
一名學生站了起來。苗條、美麗、留著一頭紅棕色長髮,還有一雙長腿。她的裙子短得肆無忌憚,火氣很大。她問赫爾普林,這番話是否當真。在場人士集體倒抽一口氣,大家心裡都存著同樣的疑問,但是沒有人有足夠的勇氣(或者夠任性),膽敢把話說出口。
當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來自marina.keegan@yale.edu的電子郵件:
「您好!您並不認識我,我是那個提出質疑的學生……聽到知名作家說這一行正在凋零,並且勸我們找點別的事情做,真叫人傷心。或許,我只是期望他對有心遏阻文學之死的人,能夠多一點鼓勵。」
「遏阻文學之死」──瑪麗娜是在自嘲,同時又百分之百認真。
幾星期後,她申請選修我開的第一人稱寫作班。申請函開頭是這麼寫的:
大約三年前,我開始羅列清單。最初寫在筆記本裡,後來慢慢進化,移到了電腦的文字處理器上。我稱之為「有趣的素材」。我承認,我有一點走火入魔了。不論在課堂上、圖書館裡、睡覺前,或者在火車上,我無時無刻不想著在上頭添加材料。清單上的內容包羅萬象,從描述服務生的手勢,到計程車司機的眼眸,再到我的奇特遭遇,或是表述某一件事情的方法。我的生活,總共有三十二頁密密麻麻的有趣素材。
瑪麗娜在大三下學期選了我的課。課堂上,她援用那三十二頁有趣素材寫了一系列散文隨筆,同學都很佩服她,紛紛在評論報告上給予最高評價:優美、生動、活力四射、栩栩如生、不落俗套、直截了當、感情豐富、有說服力、引起共鳴、精準、自信、坦率、震撼人心。許多學生寫起文章有如四十歲中年人。他們善於表達,卻缺乏原創性;擔心自己的生命太過平凡,因此急著跳過現在的年紀和人生經驗,還沒學會走路就想飛,最後變得老氣橫秋,掩蓋了自己的聲音。然而,瑪麗娜二十一歲,筆觸就是二十一歲:這個二十一歲年輕人有頭腦、英文好,明白青春、徬徨、充滿幻想和挫折與希望的生命,是最好的寫作題材。當她在會議桌旁高聲朗讀自己的作品,總會引得大夥兒噗哧一笑,然後故事急轉直下,讓所有人心碎。
***
瑪麗娜以優異成績畢業五天後,我收到來自另一名學生的電子郵件:
安,很抱歉這麼晚打擾你,不過,我不知道你是否聽到了那個可怕的消息──請打電話給我。
瑪麗娜她們家在鱈魚角有一間度假小屋。那天,瑪麗娜在波士頓近郊跟奶奶吃過了早午餐,男朋友開車載她去鱈魚角,準備慶祝父親五十五歲生日。她的父母正等著她,桌上有龍蝦,媽媽還替她做了無麩質草莓蛋糕,因為瑪麗娜有麥麩不耐症,無法消化小麥製品。她的男朋友既沒有超速,也沒有酒駕,只不過開車開到睡著了。車子撞到護欄,翻了兩次。瑪麗娜死了,男友毫髮無傷。
隔天,瑪麗娜的父母邀請他到家裡來,給他一個擁抱。他們寫信給州警,請求不要以車禍致死的罪名起訴那男孩,因為,「瑪麗娜要是知道男友除了承受此刻的痛苦,還得吃更多苦頭,肯定會很傷心。」出庭時,基根一家人陪在他身旁。訴訟案最終裁定撤銷。
許多年輕人在瑪麗娜的追思會上哭成一團。我從沒見過那麼多年輕人掉眼淚──不光是啜泣而已,還痛哭到全身顫抖,我真擔心他們的肋骨會斷掉。
不到一星期,原本刊載在《耶魯每日新聞》畢業專刊上的文章──〈孤獨的反義詞〉,受到超過百萬人點閱。「我們還那麼年輕,青春正盛,」瑪麗娜寫道,「我們才二十二歲,還有很多時間。」
對於英年早逝的人,人們最惋惜的,往往是她無法實現的未來──她原本可以達到的成就。但是瑪麗娜已經留下許多成就:她的作品豐富,遠超過本書封面和封底之間所能承載的份量。她的父母、朋友和我在收集她的作品時,總試著找出每一篇故事和隨筆的最新版本,我們知道這些文章都還沒達到她願意出版的面貌。她一改起稿來就像著魔似的,即便其他人都認為稿子已經很完美了,她還是不斷地重寫、重寫、再重寫(永遠要精益求精)。我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替她修改作品,只有她自己才辦得到。儘管如此,每次重讀這九篇故事和九篇隨筆,她的個人風格就躍然紙上,我一個字都不想更動。
瑪麗娜不會希望人們是因為她死了才記得她。她會希望大家記得她,因為她很優秀。
***
我見過太多年輕作家放棄寫作,因為他們無法承受這一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敗。這些年輕人有才華,但是欠缺決心和毅力。瑪麗娜三項條件兼備,這就是我確信她會成功的原因。
***
瑪麗娜聽到當今這個時代幾乎不可能靠寫作出人頭地的幾個小時之後,耶魯詩歌朗誦會有一次聚會,她遲到了。一個朋友記得她滿臉通紅,雙眼就像尖銳潮濕的石頭。
「我決定當一名作家,」她說,「用我的生命,當個真正的作家。」
孤獨的反義詞
我們找不到一個詞來表達孤獨的相反意義。如果有的話,我得說,那就是我此生所追求的;那就是我衷心感激耶魯帶給我的感受,也是我害怕明天一早醒來、畢業離開之後,即將失去的感受。
如果用「愛」或「群體生活」來形容,又不夠貼切;那只是一種感覺,有人──很多很多人──和你休戚與共的感覺。很多很多人站在你這一邊。那是帳單都付清了大夥兒還不肯散去的時候;那是清晨四點鐘卻沒人肯上床的時候;那是彈著吉他的夜晚,還有我們已經記不清的夜晚;那是我們共同經歷過、走過、看過、笑過、感受過的時光;以及畢業典禮上千奇百怪的帽子。(譯註:耶魯的畢業典禮有一項特殊傳統,畢業班學生會挖空心思戴上稀奇古怪的帽子,越奇特、越顯眼越好。)
耶魯充滿我們給自己圍成的小圈圈。阿卡貝拉合唱團、球隊、宿舍、社團。就算在最孤寂的夜裡,我們無依無伴拖著腳步回家,疲憊地趴在電腦前──還有這些小圈圈讓我們感受到被愛、安全、有歸屬感。然而到了明年,我們就不再擁有這些,不再跟一票死黨住在同一個街區,不再跟一大夥人一起傳簡訊聊天。
這讓我害怕,遠甚過害怕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城市或伴侶。我害怕失去我們身處的這張網;這個難以捉摸、無法言喻的孤獨的相反──我此刻的這個感受。
但是,我們得弄清楚一件事: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並未成為過去;那是生命的一部分,隨著我們逐漸成長,不論最後搬到紐約、搬離紐約,或者但願自己住在或不住在紐約,美好的年代肯定會一再出現。我打算到了三十歲還要狂歡,打算到老了都要給自己找樂子。一切對於「最美好」年代的追悔,莫不出於這種老掉牙的開場白:「早知道就……」、「要是我……」、「真希望當年……」。
當然,我們難免會有遺憾:那些該讀的書、那個錯過的男孩。我們是自己最嚴厲的批評者,很容易對自己失望。太晚睡、拖拖拉拉、投機取巧。我不只一次回顧高中的自己,然後驚嘆:我是怎麼辦到的?我怎麼能那樣用功?我們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如影隨形,而且永遠都會在心底隱隱作祟。
然而重點是,每個人都一樣。沒有人能睡覺睡到自然醒,沒有人念完該念的每一本書(也許除了那幾個拿書卷獎的瘋子……)。我們為自己設下的標準是那麼高不可攀;也許,我們永遠無法成為心目中那個完美的自己。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那麼年輕,青春正盛;我們才二十二歲,還有很多時間。有時候我發現,當我們在派對之後獨自一人躺著,當我們舉手投降、闔上書本走人的時候,有一種多愁善感的念頭會悄悄鑽進我們的集體意識──一切恐怕為時已晚,別人恐怕已經遙遙領先,比我們更有成就、更有專長,在拯救世界、創造或發明改進的路上,比我們走得更遠。現在要重新開始,恐怕已經太遲,我們必須將就著繼續走同一條路,直到畢業。
剛進來耶魯的時候,我們懷抱著夢想,擁有一股巨大而不可思議的潛在能量──如今,這股能量彷彿一點一滴流逝了。我們以前從來不需要作選擇,如今突然之間,我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前途做出決定。有些人學有專精,明確知道自己要些什麼,並且踏上了正確的道路:準備進入醫學院、在理想的非營利組織工作、做研究。對於你們這些人,我要說聲恭喜,還要說──你們真討厭。
然而我們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迷失在浩瀚的通識教育之下,對我們選擇的道路沒有太大把握,甚至有些後悔。要是當初主修生物就好了……要是大一就開始參與新聞工作就好了……要是當初想到申請這個或那個就好了……
我們得記住的是,任何事情都還來得及。我們可以改變心意,可以重頭開始。去讀研究所、去嘗試寫作。那種「一切都已太遲」的想法實在太滑稽、太好笑了。我們才剛要從大學畢業,如此年輕。我們不能──絕對不能──失去一顆懷抱希望與夢想的心,因為到頭來,當失去一切,我們還能擁有的,只剩下這顆心。
大一那年隆冬,一個星期五晚上,我昏昏沉沉接到朋友的來電,要我跟他們在埃斯埃斯埃斯(Est Est Est)披薩店碰面。我在昏昏沉沉之間,開始拖著腳步往SSS大樓走去(原註:Sheffield-Sterling-Strathcona大樓是耶魯的行政大樓,裡頭有院長辦公室,以及一間大型演講廳),那大概是校園最偏僻的地方了。驚人的是,我費盡千辛萬苦抵達了門口,才發覺事情不太對勁:朋友們怎麼可能跑到耶魯的行政大樓狂歡?他們確實沒有。不過反正天氣很冷,而我的學生證還能派上用場,於是我進了SSS,掏出手機。四下一片寂靜,只有老舊的木頭地板嘎吱作響。隔著彩繪玻璃,我幾乎看不見窗外飛舞的雪花。我坐下,抬起頭。在我之前,這間巨大的演講廳裡曾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坐在這裡。而我此刻孤身一人,在黑夜裡,在紐黑文的暴風雪中,心裡卻湧出一股奇特的安全感,如此不可思議。
我們找不到一個詞,來表達孤獨的相反意義。如果有的話,我得說,那就是耶魯給我的感受;那就是我此時此地的感受。與你們全體休戚與共,一起感受著愛、折服、謙卑,還有忐忑不安。我們不必失去這份感受。
2012年,我們同在一起,讓我們一起在這世界留下印記。
萬福,滿懷恩典
在麻州劍橋一神普救派的聖誕劇中,不論是聖母瑪利亞堅持塗著黑色指甲油,或是約瑟剛剛宣布出櫃,一切全都不礙事。十二月二十五號晚上七點及九點,三位女賢人會跟在東方三哲的後頭出場,其中一個穿著日本和服,另一個穿著非洲傳統服裝。他們送來的禮物不是沒藥, 而是雞湯;不是乳香,而是搖籃曲。牧羊人說了一句關於環保的台詞,旅店老闆則拿著宣告破產的牌子。沒有人由衷信仰上帝,也沒有人由衷不信──於是他們就把重點擺在聖誕歌曲、蠟燭,以及在塗了亮光漆的教堂長凳擠成一團的觀眾身上。
我的女兒艾瑪是耶穌的替角。領養五個月了,這兩個字聽起來還是很不習慣。
「你的女兒是我們的備用寶寶,是吧?」牧師這麼問。
「是啊,艾瑪是替角,」我把她抱高一點,「她剛剛還在說,但願扮演耶穌的那個主角扭傷了腳。」他瞪著我,但是我覺得這句話很好笑。
我通常不會主動派寶寶演出有爭議的耶誕實驗劇,不過前一天,傑瑞打了七通電話給我, 情況緊迫。耶穌得去聖安東尼奧探望住院的奶奶,而第一教區一年一度的耶穌誕生大戲,最出名的就是用貨真價實的寶寶演出。我回老家過聖誕節,傑瑞是我從高中時代迄今的死黨,他正巧出任社區親善委員會主席,而他可是沒得商量的。他在電話裡頭說,教堂離我家只有十分鐘車程,況且,說實話,奧黛莉,你又能有什麼藉口?我無話可說。
我反正悶得慌。報社放我六個月的假,我已經巴不得再度面對截稿的壓力。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星期,我提前回家陪媽媽。她一聽說我還不太習慣跟艾瑪在公寓獨處,就催促我早點回家。第一個月很安靜,我有時候會放點音樂,但是擔心電視太吵了,就算她睡著,我也不會趁那幾個小時偷看打鬥、嘻笑怒罵或者羶腥色的節目。每個月的例行檢查中,伯倫森醫生建議我對寶寶說話,我照辦了。就這樣,我在她喝奶,或乾瞪眼,或在我懷裡睡著的時候,不斷地自言自語。
她才四個月大,但是我對她無話不說。我跟她聊我的工作,還有我寫書寫膩了,還有我領養她的原因。我告訴她,我很抱歉沒辦法餵她母乳,很抱歉沒給她一個爸爸,很抱歉在她也許只想睡覺、喝奶或者探索世界的時候,說個沒完沒了。我告訴她朱利安的事,告訴她我到現在還想著陳年往事,真是可悲!我四十二歲了,她抓著我的手指時,我低聲對她說──你還不明白,不過以我這年紀握你的小手,是有點嫌老了。
我從十六歲開始跟朱利安交往,一直到二十三歲。我們高二就在一起,大學畢業一年後才分開。只要一到聖誕節,我就得返鄉過節,而返鄉過節就意味著朱利安和我被迫同處在方圓八英哩的範圍內,免不了再次面對種種煎熬。我把他每年寄給我的賀卡收在公寓的小抽屜裡:他的三個孩子一年年長大,在海灘、後院和南瓜田裡對著我揮手。
二十四號晚上,我要傑瑞載我們去排練。他很忙,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況且,我也想跟他說說話。我不必多費唇舌說服他。
「你救了我一命,奧黛莉。」他對著電話親了一口,「我四點去接你。」
「布萊特會來嗎?」我趕在他掛電話之前問。
「幹嘛?你不希望他去,是嗎?」
「無所謂啦。」
「我會讓他待在教堂裡。」
「你真是個大好人,傑瑞。」我在他發出另一聲親吻之前掛掉電話。那是他跟布萊特同居之後,從布萊特那兒染上的壞習慣,很討厭。
艾瑪一聽到他的車開上我們家的車道,就推掉高腳椅餐盤上的奇瑞歐圈圈穀片。才第五天吃穀片,艾瑪就已經精通亂撒東西的藝術。穀片成功溢出餐盤邊緣之際,艾瑪兩眼盯著我瞧, 我想像著她從馬槽扔出奇瑞歐穀片,那情景讓我忍俊不住,開始捧腹大笑,艾瑪也跟著咯咯地笑。她高舉雙手在空中揮舞,我一把抱起她,然後上樓抓了一條紅色絲巾,添點喜氣。那是我媽的話,添點喜氣。
「我也得去嗎?」我在傑瑞開門的時候問。
「我也很高興見到你。」他抽走我懷裡的艾瑪,然後溫柔地輕聲細語。「我反正一定要帶走耶穌寶寶,所以我猜,你最好跟著一起上車。」他大剌剌地直接進門,他從十歲起就是那樣。
「告訴我,沒有其他高中同學會去。」講電話那時,我沒想到這個問題,但是此刻,想到艾瑪要以耶穌化身之姿在我的老朋友面前招搖過市,實在太可怕了。傑瑞沒有回答。「有沒有辦法在節目單上註明我不是自願的?」
「但是你是自願的呀!」他咧嘴一笑,然後拿起兒童安全座椅往他的富豪汽車走去,「我問了你,而你答應了!」
同學之中,只有傑瑞不曾真正出走,但是他明白,回到家鄉對我而言並不容易。七年的交往時間不算短,不論當時多年輕。小鎮的一景一物,差不多都能讓我想起朱利安:高中時,我們一起參加舞會,一起看電影;大學放暑假,我們在他的車裡抽大麻殺時間,跟傑瑞、路卡斯和莎拉一起飆車到7-Eleven,輪流挨在對方的單人床上睡覺。我們是一對金童玉女,是讓單身老師在舞會上羨慕不已的佳偶,大家都認定我們是命中注定,絕不會分開。高三那年,我們沒贏得「最佳情侶」的頭銜,輸給了史凱樂和吉莉恩,但那純粹是因為校刊編輯是吉莉恩的死黨,
而且朱利安足球隊的隊友決定投票給別人,故意整整我們。每年暑假,我們跟彼此的家人一起出遊,每年秋天,我們都得吃兩頓感恩節大餐。他很宅,卻很熱情,長得又帥又善解風情。而我愛他。
我試著冷眼看待這些歲月,不帶感情,但是談何容易──到了三十歲左右,回憶開始纏繞著我。他的酒窩、他的鎖骨、他的甜言蜜語,還有朋友們的父母對我媽說他們有多麼嫉妒。有時候,我能夠好幾個月不回想往事,但是「假使當初……」的情節似乎總會在我寂寞、疲憊,或者不得不回家過耶誕節的時候,悄悄爬上我的心頭。他找到了另一個人,而我沒有。我甚至沒再愛過,沒再真心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