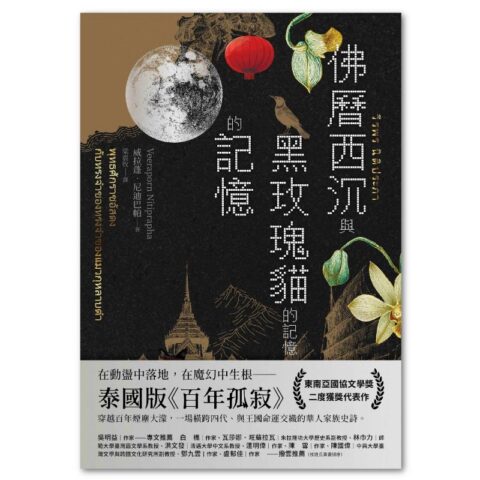電報大道
出版日期:2016-12-02
作者:麥可‧謝朋
譯者:王瑞徽、傅凱羚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20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8182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一齣關於都更、文創、中年危機與性啟蒙的悲喜劇
也是一部以文字演奏的靈魂放克交響曲
繼《失戀排行榜》、《時間裡的癡人》後
美國才子麥可‧謝朋又一音樂小說新經典
珍妮佛‧伊根(《時間裡的癡人》)、傑斯‧沃特(《美麗的廢墟》)等名家推薦
HBO即將改編,由《成名在望》金獎名導 卡麥隆‧克羅 編劇執導
入圍:洛杉磯時報書卷獎、好讀書評網站年度小說、加州圖書獎決選
榮獲:Fernanda Pivano美國文學獎
入選:紐約時報、堪薩斯星報年度百大好書、華盛頓郵報年度注目小說
每日電訊報、倫敦標準晚報、明尼蘇達公共廣播電台年度選書
亞契與奈特是一對黑人加猶太小子的奇特死黨,電報大道上「破爛地」黑膠唱片店合夥人兼樂團搭檔。兩人的妻子葛雯與雅薇娃經營一個多年來接生過上千嬰兒的自然助產中心。然而當前美式足球明星吉布森預備在此開設酷狗購物中心,同時葛雯與雅薇娃的助產方式因一件意外而受人質疑,這兩對好友兼夫婦的事業與友誼首次出現了重大危機……
路瑟是一九七○年代功夫電影明星,息影多年後,再次回鄉為系列電影重開機籌資,卻意外讓一椿陳年謀殺懸案重新浮上檯面……
朱利亞與最近搬進社區的少年泰塔士成為好友。但這個泰塔士身上有著什麼祕密,竟可能成為亞契搖搖欲墜婚姻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奈特與亞契受託為有望進軍白宮的政壇明星舉辦募款音樂會,而當電報大道近日各種紛亂的事主為此齊聚一堂,這條承載著時光印記的大街,它所背負的舊日陰霾與未來方向,能否就此豁然開朗?
※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忘了所謂「喬伊斯式」或「索爾‧貝婁式」之類的比喻吧,用來形容《電報大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是一部「謝朋式」的小說,有著豐富的語言、精彩的群戲、猶如夏夜煙火秀的對白、以及機槍連發般的精譬妙喻。
──《美麗的廢墟》作者,傑斯‧沃特
謝朋的寫作生涯常以流行文化為題進行企圖宏大的寫作計畫,並一慣地交出絕佳成績……《電報大道》的企圖心比起以往一點不少……滿滿的機智……他與生具來令人驚艷的文字風格。我要說的是,這些並非他的刻意賣弄炫燿,而是信手拈來就能如此令人讚嘆。
──《時間裡的癡人》作者,珍妮佛‧伊根
一部關於已逝時代的史詩……一首以現代潮人節奏為底,再用喬伊斯混音的神曲。
──寇克斯評論
這是擁有驚人天分的謝朋又一次令人目眩神迷的寫作技巧展示。
──費城詢問報
麥可‧謝朋是美國小說界的麥可‧喬丹……《電報大道》根本可以直接拿來當作一堂《如何寫作小說》的研究所課程教材。
──丹佛郵報
謝朋仍然是從前的那個魔術師,他能把任何題材搬上舞台,然後讓觀眾為之驚詫並微笑或感嘆。
──紐約時報書評版
《電報大道》是部絕妙小說……書中的世界讓你不由自主迷失其中……這是一部會讓我因為純粹樂趣而放慢速度的小說,我用每日定量配額拖慢進度,就是為了不想要這故事結束。
──觀察家週報
深刻精巧、情感豐富……你所讀的是一部宏大、嚴肅、探索美國內在的小說。這部小說就像謝朋本人,行走於分隔菁英與庶民文化的界線上,讓人一讀便無法釋手。
──衛報
《電報大道》成功塑造出卡麥隆‧克羅的《成名在望》與理察‧林克雷特的《年少輕狂》中歡樂鮮艷的氛圍,但比以上兩部名作更加深刻而機智。
──每日電訊報週日版
這小說就像一張你最愛的爵士樂老唱片,從頭到尾都讓人樂趣無窮。
──獨立報
一部附帶原聲帶的枝蔓龐雜家族劇。
──泰晤士報
一部包含多重世代,剖析都會社群的大部頭小說。有著如同鐘錶發條精準嵌合的情節以及太妃糖般滋味稠密豐富的對白。
──每日電訊報週日版
作者:麥可‧謝朋
1963年出生,成長於美國馬里蘭州。是與強納森‧法蘭岑、強納森‧列瑟等人齊名的美國文壇中生代作家。他擅於自類型文學及影音次文化中擷取創作靈感,自1988年至今,已出版《那一年的神秘夏日》、《Wonder Boys》、《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消逝的六芒星》及本書《電報大道》等叫好亦叫座的長篇小說。此外,他亦長期於《紐約客》、《GQ》等雜誌發表短篇小說及雜文,並已陸續結集成書。在文學創作外,謝朋曾參與多部電影的編劇工作及流行音樂的歌詞創作。他的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Moonglow》,目前與同為小說家的妻子伊黎‧華德曼定居於美國加州柏克萊。
譯者:王瑞徽
淡大法語系畢業,專事翻譯,譯有李查德、約翰‧波恩、派翠西亞‧康薇爾、雷‧布萊伯利、史蒂芬金等作者的系列作品。
譯者:傅凱羚
台大中文系畢業,曾獲多項文學獎,現職編劇、翻譯,寫作。著有舞台劇作集《太平洋瘋人院》,譯有《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等書。目前正在撰寫個人首部長篇小說。
鮮奶油之夢
黑膠聖殿
見多識廣的鳥
回歸永恆
破爛地
臉蛋渾圓、身材魁梧、帶點醉意的亞契‧史多林坐鎮「破爛地唱片行」櫃檯後方,抱著不知誰家的嬰兒,身穿褐色燈芯絨西裝,內搭一件亮橘色高領衫,這衣服雖不難看,但也凸顯出他與日本電影中突變怪獸飛天神龜卡美拉的相似處。他用左臂夾著小孩,空出的右手整理著從班尼茲拉遺物中搬來的十五只木箱裡的第八只。八號箱中的唱片跟亞契一樣,獨鍾爵士樂中鹹辛夠味並滿布漂亮放克油花的腹腩肉。其中有《電音鳥》(Electric Byrd)(藍調之音唱片〔Blue Note〕,1970年)、有強尼‧漢蒙(Johnny Hammond),有麥文‧史派克斯(Melvin Sparks)的頭兩張專輯,查爾斯‧凱納(Charles Kynard)的《美麗人們》(Wu-Tu-Wa-Zui)(傳奇唱片〔Prestige〕,1971年)。一面盤點這批貨,亞契一面聆聽(不時瞇起眼睛)店裡那台耐操四聲道轉換器流出的本屬已故班尼茲拉一張帶薄荷味的四聲道唱片──是阿優圖(Airto)的《手指》(Fingers)(CTI唱片,1972年)。這甜美的小寶貝是奈特‧傑菲徒手從垃圾箱裡挖出來,再由亞契這位前軍中直升機電工翻修,根據最近一次查證,他仍保有加州州大舊金山分校電機工程系學士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的技能。
單手清點唱片技巧如下:從箱中抽出一張唱片,把外殼內的薄紙封套拈出一點。手指一點點探入封套,指尖避開標籤以外部位,像侍者一般小心托出唱片。把唱片斜對著玻璃窗透入的晨光。灣區東岸那晃亮又柔和、犀利又寬容的天光總能馬上讓你得知唱片的真實狀態(儘管奈特認為重點不是天光,而是窗戶,是這一大片厚實的匹茲堡玻璃,讓六十多年歲月中曾經的史賓瑟理髮店與現在的破爛地唱片店免於外面各式各樣的狗屎)。
亞契搖擺身體,閉著眼睛,沉醉在小孩的重量感,在林哥‧席爾曼(Ringo Thielmann)低音大提琴聲線的油脂味中,在昨天艾莎貝‧蓋達秋於衣索匹亞餐廳「示巴女王」的私人包廂內替他口交時媚眼輕抬的回憶裡。回想著她弧線姣好的噘起上唇,舌尖沿著他陰莖的E弦一路攀上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在這週六清晨,趁著鄰居踩著靴子衝進店裡打探壞消息前,他搖擺、沉溺、感受著,彷彿可以就這麼耗上一整天,甚至到永遠。
「可憐的鮑伯‧班尼茲拉,」亞契對那不知誰家的嬰兒說:「我不認識他,但為他難過,留下這麼多珍貴的唱片。所以囉,羅蘭多,看見那可憐傢伙死後帶不走這批漂亮黑膠的當下,我立刻成了無神論者。」要讓孩子了解人生的暗礁、冷酷的真相、生與死等等,永遠不嫌早。「連唱片都不能帶,還算什麼天堂?」
也許小嬰兒明白這純粹只是華麗的修辭,因此完全不想回應。
◎ ◎ ◎
奈特‧傑菲頂著一朵烏雲來上工,一如平日,十一次中約莫五次,或者客氣點,就說每九次有四次吧,會是這副德行。壞心情像頂太空裝頭盔罩著他的頭,可憐的奈特蒙在裡頭,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大氣是否適合呼吸,也沒有儀器能告訴他氧氣何時耗光。他反轉帶鎖門閂,鑰匙串鏗鏗撞擊門板,由於左臂下夾著一箱唱片,他只能用單手努力操作。他垂著頭推門進來,悶聲哼唱;從一段有趣的和弦變換跳到某首乏味的時下流行歌;哼著給兩條街外一家美甲沙龍的懶散老闆,或是給《奧克蘭論壇報》(Oakland Tribune)(該報讀者投書版一向是他抒發怨氣的園地)的一封不滿投書;哼著一篇新文章中討論bossa nova樂風與法國翻唱樂團「新浪潮」(Nouvelle Vague)之關係的開頭幾段;雖沒發出聲響,但就算睡覺時,奈撒尼爾‧傑菲那身骨頭深處的某些弦線也總是嗡嗡響個不停。
他關上門,從裡頭上了鎖,把木箱往櫃檯一放,將炭灰色細紋軟呢帽掛上牆面的鋼鉤,這一排九個雙爪鋼鉤同樣是史賓瑟理髮店時代的遺物。他用單指順了順深色頭髮,他的頭髮比亞契更糾結,髮際線上已有點稀疏。他轉身,正了正(黑底銀點爵士風寬版)領帶,注意到八號箱的狀態。他把腦袋在頸骨上轉了幾圈,彷彿骨頭的咯吱響聲和筋肉拉扯能讓他甩掉逼著他哼個不停的東西。
他走向店內,消失在珠簾後方,門簾上是奈特的兒子朱利費了番功夫手繪的墨西哥聖徒風格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肖像,聖邁爾士受難的心裸露在外,與刀片鐵絲刺網糾纏不清。老實說,畫得不算逼真,在亞契看來倒比較像棒球明星穆奇‧威爾森(Mookie Wilson),不過話說回來,在上千顆半吋大的珠子上畫人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朱利亞斯‧傑菲,大概沒幾個人會想這麼做,更別提動手一試。不久,亞契聽見馬桶沖水聲,緊接著一陣狂咳,朱利的老爸回到外場,準備開始消磨新的一天。
「誰家的嬰兒?」他問。
「什麼嬰兒?」亞契說。
奈特打開店門,翻過吊牌,告知全世界,破爛地唱片店開始營業。他再把頭繞著脊椎頂轉了一圈,又哼了幾聲,咳了一陣,才回頭面對他表情近乎哀怨的合夥人,說道:「我們完蛋了。」
「帳面上看起來是沒錯,」亞契說:「如果真是這樣,又是為什麼呢?」
「我剛去過辛格泰利那裡。」
他們的房東,賈尼特‧辛格泰利先生,珠寶之王,專賣金牙、金戒指和論碼計價的金鍊子,就住在破爛地過去第三棟房子。這整條街都是他的,另外在西奧克蘭還持有十來筆甚至更多房地產。瑣碎、市儈氣。辛格泰利是頭訊息鯨魚,常在街坊四處走動,打探各種八卦流言,用不知疲倦的鯨鬚過濾吸納成為養分。他不曾在破爛地的唱片堆中晃蕩並花過半毛錢,但仍是這裡的常客,每隔幾天就會來一趟,只是過來查核並檢視坊間真假流言的出入帳目。
「是嗎?」亞契說:「辛格泰利有什麼話說?」
「他說我們完蛋了。說真的,你抱著個嬰兒作什麼?」
亞契低頭看著羅蘭多‧殷格利,這鏽棕膚色年輕人嘟著可愛小嘴、滿頭汗濕的柔軟棕色小卷毛黏著腦門一側、緊裹著藍色連身衣加黃色棉毯。亞契舉起羅蘭多,內心響起一聲滿足的輕嘆。羅蘭多的母親愛莎是珠寶王的女兒。亞契自願替她照顧羅蘭多一早上,或許還能代她採買幾樣嬰兒用品什麼的。亞契的妻子正懷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照亞契的想法,將為人父的他或許可在十月一日(也就是預產期)前先練習一下如何帶小孩,或許多少可減緩在三十六歲之齡才突然成為新手爸爸的衝擊,因此他和羅蘭多走了趟Walgreen連鎖藥局。亞契一點都不介意在這晴朗的八月早晨出門散散步,他用愛莎的三十塊錢買了尿布、紙巾、嬰兒奶粉、奶瓶和一包Nuk牌奶嘴(愛莎開了張清單給他),然後就近在藥局門口的巴士站長凳坐下,他和羅蘭多當場換起臭兮兮的尿布,然後吃了些點心,亞契狂嗑一袋在「甜甜圈聯邦」買的糖霜甜甜圈,而羅蘭多只能認分地吃著一小罐Gerber牌嬰兒斷奶食品。
「這位是羅蘭多,」亞契說:「我向愛莎‧殷格利借來的。到目前為止沒幫上什麼忙,不過他很可愛。好啦,奈特,照你剛才的說法,我們快完蛋了是吧?」
「我剛遇見辛格泰利。」
「然後他給了你一些真知灼見。」
奈特把他抱進來的木箱轉過來──是一只裝了三十五到四十張唱片的金吉達水果包裝箱──開始悠哉地在裡頭翻看。亞契起初以為那是奈特從家裡帶來的,也許是他自己想脫手的唱片,或是些帶回家仔細研究的二手唱片,因為這兩位店主的私人收藏與店內存貨間的界線一直以來都未曾嚴格區分。不過,這時亞契看出那些全是回收品。一張裘絲‧紐頓(Juice Newton)的專輯,一張狀況極糟的海軍准將樂團(Commodores)晚期專輯,一張彩虹熊(Care Bears)聖誕專輯。垃圾、路邊攤貨、車庫拍賣撿剩的東西。然而各地被命運拋棄的唱片孤兒會持續呼喚這對合夥人,發出只有奈特和亞契能聽見的求救訊號。「那個人啊,就算跑去南極──」有次雅薇娃‧羅斯‧傑菲這麼形容她丈夫,「──也能抱回一箱七十八轉蠟盤。」這時,奈特有一搭沒一搭地在那批新到貨中翻找。每張唱片都可能是寶物。然而,發現珍品的機率隨著遺棄這批東西那傢伙的糟糕品味,每翻一張便以十倍比例持續下降。
「『安迪‧吉布(Andy Gibb)』,」奈特連不屑的語氣都省了,只淡淡給這名字加上雙引號,彷彿那是人盡皆知的代號。他抽出一張《黑夜之後》(After Dark)(RSO唱片,1980年),高舉著讓羅蘭多檢查。「你喜歡安迪‧吉布嗎,羅蘭多?」
羅蘭多‧殷格利看待吉布兄弟的老么最後一張個人專輯的態度,似乎比問他話的這個大人寬容得多 。
「看在你這麼可愛的分上,就不跟你計較了。」奈特的語氣似乎表示這是他的結論,彷彿他和亞契剛吵過架,然而在亞契的記憶中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我來吧。」
亞契把小孩交給奈特,突然卸除壓力的肩膀反倒一陣痙攣。奈特雙手托著小孩腋下舉起,兩人面對面。羅蘭多乖乖仰著頭,他迎向奈特的目光有種讓人(不管這人是安迪‧吉布或奈特‧傑菲)放鬆的感覺。當兩人互相端詳,奈特的哼唱聲變得柔和,聽起來像搖籃曲。嬰兒羅蘭多給他一種舒適、厚實的感覺,小小身軀有如塞滿襪子球的布袋,紮實、安靜,不像那種三不五時就會遇上的瘦雞一般張牙舞爪的小嬰兒。
「我也有過一個小嬰兒。」奈特語帶傷感地回想。
「這我記得。」那是他第一次見到奈特的時候,當時奈特在華金‧米勒公園自然之友協會中一場婚禮上當樂手,剛從波斯灣回來的亞契在最後一刻進場,趕上為奈特缺席的合作貝斯手代班。那時的嬰兒朱利亞斯如今已十五歲,幾乎仍是從前那個討人喜歡的小怪胎,至少在亞契看來是這樣。老是聽見神祕的和聲,用克林貢語寫 詩,在指甲上彩繪南瓜王骷髏傑克(Jack Skellington)的臉。曾經穿著芭蕾舞衣和蓬蓬裙上托兒所,回家會看芭芭拉‧史翠珊的《彩繪芭芭拉》(Color Me Barbra)音樂特集。才三、四歲就跟他老爸一樣愛鑽牛角尖。會告訴你薯條(french fries)不是法國來的,德式巧克力蛋糕(German chocolate)也不是德國人的發明,父子倆同樣極易沉迷於問題的細微差異。不過,最近他似乎花上不少時間傳送某種只有身為父母才能辨識,目的則是用來把他們逼得抓狂的青少年密碼。
「小嬰兒很酷,」奈特說:「他們會愛斯基摩貼面吻。」奈特和羅蘭多當場示範起來,鼻頭碰鼻頭,小嬰孩懸在那裡,默默忍受。「正點,羅蘭多真棒。」
「我也這麼覺得。」
奈特打量著亞契,那表情和亞契打量鮑伯‧班尼茲拉收藏中的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專輯《慈母禮讚》(Kulu Sé Mama)(脈動唱片〔Impulse〕,1967年)時一模一樣,只想挑點毛病來貶低它的價值。
「原來你在實習當爸爸?是這樣嗎?」
「沒錯。」
「還順利嗎?」
亞契聳聳肩,一副英雄立功後低調謙虛的模樣,彷彿剛拯救了一艘與小行星擦撞而起火燃燒貨機上受困的一百名孤兒,被問到哪來的神力時會有的反應。可是當亞契對奈特擺出這姿態,他心裡明白──或說感覺,就像他能感覺到左臂膀內嬰兒形狀的痠痛──就算他有能力或意願照顧羅蘭多一小時、一天或一整週,也與他有沒有能力或意願勝任父親一職,照顧那即將到來,正在妻子子宮的陰暗廠房內努力讓呼吸與內分泌系統發育成熟的孩子沒半點關係。
擦屁股,把泡好的康乃馨牌牛奶擠出奶瓶,拿擦碗巾把吐奶抹乾淨,這些都只是雜務和程序,一連串的小動作,和生命中的其他事物沒兩樣。有該盡的義務、有該過的難關,還有該輪的班。集中你的思緒,釐清《轉角》(On the Corner)(哥倫比亞唱片〔Columbia〕,1972年)專輯中複雜的拍子、或《沉思錄》(Meditations)(這陣子亞契正第九十三次埋頭讀這本哲學家皇帝馬可‧奧理略的著作)中某個晦澀的段落、單手整理一箱有意思的唱片,一轉眼,小睡時間到了,媽咪回家了,你就可以回頭繼續做自己的事。就像在軍中:你得當心,找個乾燥涼爽的地方,把思緒藏起來,熬到一切結束為止。只不過,當然了(經歷了幾個月全場緊迫盯人式的驚恐戲弄,尤其凌晨三點被懷孕妻子的不安躁動吵醒的時刻後,他意識到,自己想藉練習照顧羅蘭多‧殷格利來減緩這些驚恐──如今看來,全是白費功夫),它永遠不會結束。父親的工作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無論你把思緒藏在哪個角落,或者實踐了多少必要步驟。就算你死了也一樣。不管是死是活,或遠在千里之外,你得隨時準備背負某種既不算必要程序也非完整步驟,而是某種需要你全心全意投入,卻不見得要求你做什麼、說什麼或有任何表現的工作。亞契的父親在他和羅蘭多差不多大的那年拋下他們母子,儘管接下來那幾年,路瑟‧史多林在運氣來時會不時現身,按時支付子女撫養費,帶他去看奧克蘭運動家隊的比賽、去萬豪大美洲遊樂園(Marriott’s Great America)等諸如此類的活動,但還是有些要求老路瑟沒法達成,他還是有所保留,縱使他就站在亞契身邊。為人父親意謂著必須擔負某種超越金錢、體力或時間的義務,一種非關皮相、無法用時間測量的存在:沒有終點,永恆且無形,如同萬有引力對繁星的允諾。
「是啊,」奈特說道,體內的弦頓時鬆了下來。「小嬰兒是很可愛,可是他們會長大,接著就開始不洗澡,還會用襪子打手槍。」
大門玻璃閃過人影,S‧S‧莫欽達尼走了進來,一臉哀傷。那人天生一張苦臉,雙眼凹陷,下巴鬆垂,連那潑翻墨汁似的鬍子都帶著悲傷。
「兩位,」他說起話總是一口正經但悲愁的皇室英語,彷彿追憶著一個更優雅更文明的時代。「你們完了。」
「大家都這麼說,」亞契說:「怎麼回事?」
「酷狗。」莫欽達尼先生說。
「去他的酷狗。」奈特附和著,又開始哼唱起來。
「他們一個月內就要破土施工了。」
「一個月?」亞契說。
「就下個月!我聽到的是這樣。咱們的房東大人辛格泰利先生跟吉布森‧古德的祖母聊過了。」
奈特說:「去他的吉布森‧古德。」
距離今天六個月前,前匹茲堡鋼人隊明星四分衛、酷狗唱片公司及酷狗製片公司總裁兼董事長、古德基金會負責人、全美第五黑人富豪,人稱「壞蛋吉」的吉布森‧古德,乘著一架特製黑紅塗裝飛船與一狗票開發計畫來到奧克蘭,在市長陪同的媒體記者會上,提出要在電報大道荒廢已久的金州市場舊址,也就是破爛地唱片店南邊兩條街處,開設第二家酷狗「號子」(Thang)。預計比庫爾維市附近的巨大前身更具規模的這家奧克蘭分號將包括一座十個放映廳的影城、美食廣場、電玩遊樂場和包含二十個店面的拱廊商店街:號子的核心則是各層分別經營音樂、影視與其他商品(主要是書籍)的三層酷狗影音商場。就像福斯丘的酷狗號子,這家奧克蘭旗艦店除了將推出紮紮實實的綜合影音商品外,更將致力發揚非裔美式文化,「全方位的──」正如古德在記者會中強調,以及「──豐富多元」。古德口袋很深,且他亟欲建立的帝國結合了某種社會企業目的;號子的主要概念不在賺錢,而是要一舉重振加州在興建高速公路的黃金時期被剷除的黑人社區商業中心。在記者會中未提起,但可從洛杉磯酷狗號子的發展現況推知,這座影音商城將不只販賣超低折扣CD,更將專闢一個提供二手及稀有商品──例如爵士、放克、藍調與靈魂樂經典黑膠唱片──的部門。
「可是他還沒拿到營建執照或之類的東西,」亞契指出:「我的老朋友『老錢』‧福勞爾這陣子一直拿環境衝擊、交通評估這些鳥事煩他。」
福勞爾父子葬儀社──就在電報大道上酷狗號子預定店址的正對面──負責人兼經理錢德勒‧福勞爾同時也是奧克蘭市議會議員。但不像辛格泰利,錢德勒‧B‧福勞爾議員是個唱片收藏家,一個手頭闊綽的樂迷。儘管並不明確瞭解他反對酷狗號子的理由,但這對合夥人很仰賴這點,並對未來發展抱著期待。
「顯然某種因素讓議員改變了想法。」滑頭、慵懶,彷彿拿著杯苦艾酒,S‧S‧莫欽達尼用他最擅長的詹姆斯‧梅森 式口音說道。
「哼。」亞契說。
奧克蘭西區沒人能比錢德勒‧福勞爾更強硬、更有活力,能讓他改變想法的所謂某種因素,也一定與脅迫恐嚇扯不上關係。
「我也不知道,莫欽達尼先生。錢老哥就要參選了,」亞契說:「他才勉強通過初選,也許是想鼓動基層,提振一下士氣,激勵社區民眾,沾點吉布森‧古德的明星光芒。」
「那當然,」但莫欽達尼的眼神說著:才怪。「我相信他一定有正當理由。」
收取回扣,他等於如此暗示。賄賂。任何像莫欽達尼先生這樣有本事從印度旁遮普省把堂表親與甥姪子女一波波接到美國,在他的汽車旅館當房務員、在他的加油站洗車,還能不驚動印美兩國執法當局的人,思路很難不往這條路上走。亞契很難想像福勞爾──那個硬頸不屈、溫言軟語並始終堅持走正道,而且還是從萊恩奈爾‧威爾森時代 就一直是街坊心目中英雄的人──會從某個炫富的前足球四分衛手中拿回扣。不過話說回來,亞契為了彌補對黑膠唱片狀態的吹毛求疵,往往對人類又寬容得過了頭。
「總之還是太遲了,對吧?」亞契說:「交易破局。銀行縮手,古德的資金斷了頭,諸如此類,對吧?」
「我不是很懂美式足球,」S‧S‧莫欽達尼說:「不過我聽說吉布森‧古德當四分衛的時候,很擅長一種『帶球進攻』的動作。」
「傳球兼跑陣 ,」奈特說:「當年在球場上幾乎沒人能夠擒殺古德。」
亞契將奈特‧傑菲懷裡的嬰兒抱回來。
「壞蛋吉是個狡猾的渾帳東西。」他附和道。
◎ ◎ ◎
懷舊先生──四十四歲,海象鬍子,老奶奶眼鏡,超大尺寸Reyn Spooner牌夏威夷衫(棕櫚樹、芒草花紋、載著衝浪板的木紋門板老爺車)──站在他那張罩著螢光塗料拼布、參展費五百元的桌後──他的桌位和簽名區之間隔著一條上漆的水泥通道和三個攤位,頭頂是塊印著「懷舊先生展區」的八呎寬橫幅塑膠布──嚼著「瑞典魚」軟糖,不敢相信眼前的操蛋景象。
「喲!」他對朝他攤位走來的一組警衛大喊。那是兩名身穿藍色聚酯纖維西裝外套的壯碩白人打手加一個吉布森‧古德的貼身保鑣,這黑人彪形大漢的粗壯臂圍對他那件黑T恤的袖子實在是嚴酷的試煉。「拜託,給點尊重!」
「媽的沒錯。」從大廳一路被他們押送過來的那人說。當他們走近,懷舊先生看出那確實是他本人。或許老了三十歲,輕了二十磅,明星亮度黯淡了四十瓦,不過是他沒錯。小了幾號的紅色田徑服讓他的腳踝和手腕露出,外套後腰鬆緊帶也被往上拉,外套內是個黃色網點標誌,圖案是雙高舉的拳頭,被「加州奧克蘭李小龍學會」幾個字環繞。他身材修長、肩膀寬闊,腳步像是裝了彈簧,一縮一彈充滿活力。這場展現尊嚴的戲在懷舊先生看來就算不成功,也足夠打動人了。大家都望著那個人,所有挺著啤酒肚、背上長毛、臉孔蒼白如麵團、頭頂漸禿、心中秋葉飄落的人,從他們一箱箱《體壇內幕》(Inside Sports)過期雜誌、從鑲著洛基‧布雷爾(Rocky Bleier)或林恩‧史旺(Lynn Swann)黑色馬克筆虯結簽名字形銅牌的裱框黃色「恐怖毛巾」上 抬起頭來。從排滿偶像球星(彼特‧馬拉維奇(Pete Maravich)、羅賓‧楊特(Robin Yount)、鮑比‧歐爾(Bobby Orr))新人卡及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或喬‧納馬斯(Joe Namath)等人簽名的作廢支票(其中有些銀行早已消失)、未開封的一九七一年Topps牌Cello蠟紙包棒球卡(脆弱的黑色封口仍如過往記憶一般纖毫無損)、以及每一包都可能藏有麥可‧喬丹新人卡的一九八六年Fleer牌籃球卡的攤位上抬起頭來。望著這個有點眼熟的高壯灰髮黑人男子,一張來自他們年輕時代的面孔──被驅逐出去。就是簽名會上那傢伙,跟吉布森‧古德大小聲那個。嘿,沒錯,就是那個人。對他放尊重點,瞧那可憐雜種努力高抬下巴的跩樣。那下巴,有個跟寇克‧道格拉斯一樣的凹渦──果然是他沒錯。那雙淺色眼睛。那雙手,老天,簡直像兩棵連根拔起的大樹。
「各位,算你們走運,」懷舊先生在一行人從他攤位前呼嘯而過時喊道:「他想的話,一根手指頭就能把你們擺平!」
「那不就好厲害!」較年輕的打手說。「誰叫他不買票。」
懷舊先生不愛惹麻煩。他喜歡用處方籤買的藥用印度大麻、看各種二戰相關節目、吃「瑞典魚」軟糖,聽死之華(Grateful Dead)樂團的音樂,以上可任意排列組合。無疑地,他對權威很有意見,他父親是兩度軍旅生涯倖存者,母親參加過華盛頓反戰大遊行,因此懷舊先生無法適應任何必須聽命於上司的工作。儘管體型又寬又圓,但懷舊先生穿上皮編涼鞋也勉強只有五呎六吋高,而且沒什麼打鬥本錢。他唯一的可靠招數,一定要用功夫招式形容的話,大概只能稱為球潮蟲式 。懷舊先生習慣迴避牢騷、爭執、酒吧鬥毆,也不跟人正面攤牌,不管在家鄉或外地皆是。他唾棄暴力,電視上一九四四年的黑白戰爭畫面除外。他是個多年來建立起良好信譽的生意人,而且付了大筆鈔票給「東灣區運動卡暨珍藏卡大展」主辦方,這些錢當中就有一部分付給了這些穿藍色西裝外套的打手提供的保護與心安,至少理論上是這樣。而心安,說穿了,不只是句漂亮口號,而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企圖、是宗教的目標,是保險業者的承諾。但懷舊先生,如同後來他對妻子(她寧可吃下一碗伊波拉病毒粥,也沒興趣參加卡展)解釋自己之所以被激怒,是因看到年輕時的英雄受到這等粗蠻對待──理由只是他沒買票便擅自潛進展覽會場。因此,在凱瑟會展中心的這個週六上午,懷舊先生自己也嚇了一跳。
他走出展區堡壘,那豐富得如同賭城自助餐的展區擺滿他賴以建立特色與專長的各種非運動類系列商品精選收藏,當中有一整套一九七一年鮑比‧雪曼(Bobby Sherman)主演的《相聚》(Getting Together)影集紀念卡,包括最稀有的54號卡。懷舊先生用優雅莊重的滑步往前移動,多年來,至少曾有一位苛刻的路人看他踩著花稍舞步經過時評論道:看來帕薩迪納玫瑰花車遊行中有部花車走失了。
「等等,讓我為這位先生買張門票。」他對著幾個走遠的警衛大叫。
吉布森‧古德的貼身保鑣回頭瞥了一眼,彷彿要確認自己沒踩中狗屎。兩名藍色西裝外套打手繼續往前走。
「嘿,你們!」懷舊先生說:「別這樣!嘿,拜託,各位!那可是路瑟‧史多林欸!」
先停下的反倒是史多林,他站穩腳跟,推開兩名捕快,轉身面對贖身恩人。那熟悉笑容的魅力──早被稀疏的黃板牙、嗑藥、監獄牙醫,或者就只是被連八元入場費都想賴的貧窮給磨得蕩然無存──讓懷舊先生胸口隱隱作痛。
「好心人,謝謝你。」史多林說,這時兩名打手大搖大擺走上前。「這位先生打算……」
懷舊先生報上真實姓氏──又長又古怪的猶太姓,聽起來像某種乳酪或酸麵包。史多林精準地複誦,沒有丁點旁人對這名字常有的戲謔腔調。
「我這位朋友,」史多林像逃脫術專家掙脫束縛衣那般甩掉兩名打手,解釋道:「好心要幫我付入場費。」
語尾微微拉高,幾乎像是問句,想確認自己沒搞錯狀況。
「一點沒錯。」懷舊先生說。他想起三十年前某個週六下午,自己癱坐在卡森雙子戲院的人造皮椅中,胸口充滿巨大無比的喜悅,看著一部演員幾乎全是黑人──觀眾也幾乎全黑的電影《夜行者》。他愛死了這部電影的所有細節。頂著銀色爆炸頭的女孩。徒手搏擊。放克配樂。一場有輛一九七二年款綠色紳寶Sonnet跑車以極速飆過看來顯然是加州卡森市區街道的飛車追逐戲。還有銀行搶匪的工具、動作和炸藥。尤其是本片明星,那身手矯健、舉止沉穩、沈默寡言,有時又顯得大智若愚的主角,簡直就是史提夫‧麥昆的化身,總之就是迷人。而且無庸置疑,他就是一九七三年的功夫大師。「這絕對是我的榮幸。」
這時兩名打手調整目光焦距,集中在懷舊先生身上,掃視他頸間掛繩上的綠色兩日參展識別證。表情變得滯鈍,少了幾分不耐的虛張聲勢,努力回想官方教戰守則中有沒有說過如何應付類似狀況。
「他騷擾古德先生。」古德的保鑣走上前說道,提振一下打手群的士氣。「你替他買票,」他對懷舊先生說:「只會讓他騷擾得更起勁。」
「騷擾?」路瑟‧史多林不可置信地怒道。對於他之前或將來可能遭到指控的所有罪名一概渾然不覺。「我怎麼騷擾那個人?我只想跟他親近親近,跟所有人一樣乖乖排隊,在他身邊待上三十秒,向他要個簽名,然後走人。」
「想要古德先生的親筆簽名,得花四十五元。」保鑣指出這點。以他的腰圍、身高和龐然身形,那聲音顯得相當溫和有耐性,畢竟這人本來就是受雇來忍受蠢蛋的。他得負責把壞蛋吉周圍的蠢蛋清空,同時還得讓老闆臉上掛得住。「你連八塊錢都沒有,拿什麼來付?」
「喂,老弟!」史多林喊道,再次亮出讓人──至少讓懷舊先生──心頭一酸的爛牙笑容,並正確唸出他的姓氏。除了變老之外,不管這人過了光輝歲月後究竟做了什麼才變得如此形銷骨立、一無所有,至少看來未曾損及他的記憶力;但也或許,他就是什麼都沒做才落得如此。「我希望,呃,我在想,」這回完全用疑問句說:「是不是能請您幫我一把?」
懷舊先生後退一步。這無意識的動作是多年來與那些麵粉中的象鼻蟲般玷污珍藏卡展的騙徒、投機分子、叫化子和金光黨周旋養成的反應。他思索著,出於敬意自願為人墊入場費,與出錢讓這人買到,不是別的,而是吉布森‧古德的親筆簽名,兩者之間的差異絕對不只三十七塊錢。懷舊先生努力回想自己這輩子可曾見過,或甚至聽說過哪個名人(不管過氣多久)願意排隊等著付現金買另一個名人的簽名。史多林要這東西幹嘛?他打算讓壞蛋吉簽在哪裡?看樣子他沒帶任何能簽字的物品,書、照片、運動衫,連張節目單、餐巾紙或便利貼都沒有。我只想跟他親近親近。目的何在?懷舊先生的生意能保持興旺,靠的無非就是能拆穿老千和騙子花言巧語的敏銳耳力,這會兒路瑟‧史多林根本全身都響著警報聲,心懷鬼胎、耍著手段。事實上,若非懷舊先生不知怎地感覺有必要走出自己舒適的小展區,出頭管這不該管的事,他這齣戲早就砸了。懷舊先生彷彿聽見妻子對這事輕輕撂下的千篇一律評論:你到底哪根筋不對?可是懷舊先生這名號不只是尊稱;他的商界名號(d/b/a)就藏在他的DNA中。回想一九七四年在卡森雙子戲院那個週六下午胸口充塞的巨象般龐然喜悅,他決意相信路瑟‧史多林。比起簽在一張收銀機發票存根或從紙袋撕下小紙片上的四分衛親筆簽名,一個人會想要更奇怪或更微不足道的東西都不足為奇。
「我能做的或許不只如此。」懷舊先生說。
他伸手從牛仔短褲後口袋掏出一只被汗水浸濕的折疊牛皮紙信封。裡頭是另外兩只連著頸繩的綠色參展識別證,那是他的參展等級配發的證件。他拿起一只掛牌,推開打手人牆。路瑟‧史多林低下頭,露出曼德拉式的初期漸禿頭頂,讓懷舊先生像《綠野仙蹤》的奧茲王賜予獅子勇氣那樣,為他佩上識別證。
「史多林先生今天為我工作。」他說。
「沒錯。」史多林立刻附和,語氣真誠,也帶著幾分不耐,彷彿等了好幾天只求能在懷舊先生的攤位打工。懷舊先生為他掛上證件時,他連瞄都沒瞄一下那牌子,可這會兒他機靈地說:「在懷舊先生展區。」
「打什麼工?」兩個打手中年紀較長的那個說。
「他會在我的攤位簽名,」懷舊先生說:「我有一套完整的和另一套缺李小龍的『功夫大師』(Masters of Kung Fu)漫畫卡;還有其他一些史多林先生好心答應為我簽名的東西,像是《黑眼睛》(Black Eye)的電影宣傳畫,千真萬確。」
「『功夫大師』。」史多林複誦著,幾乎像是完全聽不懂懷舊先生在說什麼。
「Donruss公司一九七六年發行,一套很棒的卡片。」
四雙茫然的眼睛望向懷舊先生尋求開示。
「呃,各位?」懷舊先生說著,雙手在空中畫出一個圍繞他們的音場。「收藏卡?長方形小硬紙板盒?黏著泡泡糖?黏在腳踏車輪輻,讓它跑起來像哈雷機車那樣嚇嚇叫的東西?」
「要命,你說真的?」史多林忍不住問。「『功夫大師』,裡頭有路瑟‧史多林卡?」
「那當然。」懷舊先生說。
「路瑟‧史多林──」兩個藍色西裝人中較老的那位──軟塌的深色頭髮、花盆頭形、俄羅斯或波蘭人的三角下巴,大約與懷舊先生同齡──試著唸出這名字,像是要把鐘錶匠的強力放大鏡套上眼窩似的皺起半邊臉。「是了,沒錯。什麼片子來著?《神行太保史楚特》?真的是你?」
「我演過的第一個角色。」史多林逮住這意想不到能自吹自擂的機會。樂壞了。將一隻鹿角似的巨掌擱在懷舊先生身上,讓他知道能做自己最擅長的事,這感覺有多好。他將這支打手隊伍恰如其分地重新收編為路瑟‧史多林的非正規軍。「那是我贏得冠軍隔年的事。」
「什麼比賽?功夫?」
「當時不叫功夫,是空手道,在馬尼拉,是世界冠軍。」
「世界吹牛冠軍,」古德的貼身保鑣說:「這我倒相信。」
史多林完全不理這名壯漢。此時對自己的表現不能再滿意的懷舊先生也如法炮製。
「咱們沒事了吧,各位?」史多林問兩個藍色外套男。
兩名藍色西裝外套警衛向保鑣確認,那人搖搖頭,一臉厭煩。
「給我聽好,路瑟,」保鑣說:「你在古德先生附近哪怕摳一下鼻屎,我就馬上來收拾你,渾帳東西,而且絕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