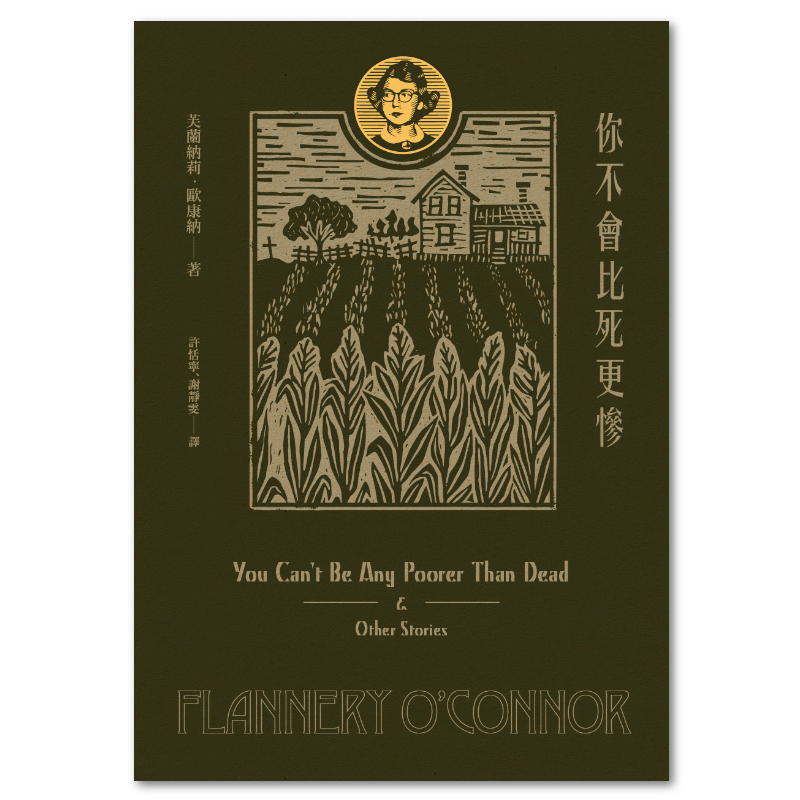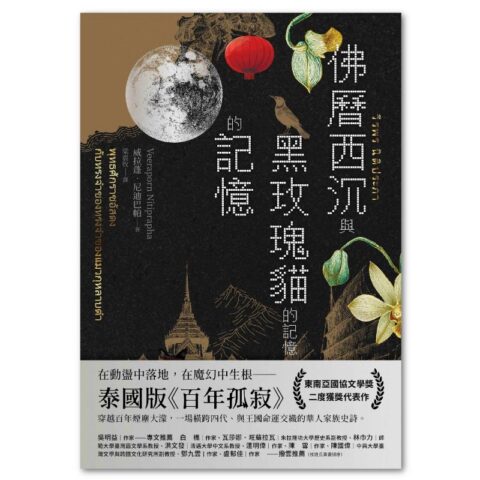你不會比死更慘:芙蘭納莉.歐康納小說集Ⅱ
出版日期:2016-12-28
作者:芙蘭納莉‧歐康納、許恬寧、謝靜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84
EAN:9789570848427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喬、大江健三郎、
美國詩人/小說家瑞蒙•卡佛一致推崇
與卡森•麥卡勒斯並列美國南方哥德文學雙璧
繼福克納後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南方作家──芙蘭納莉.歐康納
貪婪、虛偽、矛盾、善變、自私、無聊、嫉妬、陰險
人類真是上帝選民?或者只是高級動物?
如果神愛世人,為何地獄天堂皆在人間?
芙蘭納莉.歐康納是最虔誠的天主教徒,
也是最犀利的負能量小說家
《你不會比死更慘:芙蘭納莉.歐康納小說集Ⅱ》
17幅徬徨迷亂的眾生相,17篇尖刻而悲憫的文學瑰寶。
繼《好人難遇》後,《你不會比死更慘》一次補完美國知名小說家歐康納短篇作品
收錄8篇未曾集結成書遺珠之作
〈理髮師〉:瑞柏在理髮時聊起即將到來的選舉,但因支持的候選人不同,而遭理髮師及多年老街坊揶揄。他該據理力爭,舌戰小鎮酸民?還是乾脆換個理髮店重建社交圈?
〈莊稼〉:魏勒頓小姐想寫一部以佃農為主角的鄉土小說,在構思過程中,卻越來越討厭主角洛特的妻子,直欲置之於死地。那麼,將自己代換進書裡當女主角,會是個好主意嗎?
〈你不會比死更慘〉:法蘭西斯的叔公死了。叔公生前最怕死後不能以基督徒應得的方式下葬而錯過基督復臨的召喚。法蘭西斯對此嗤之以鼻。然後當他開始料理叔公的後事時才發現,也許留在世上的人,真有比死還糟的境遇……
〈鷓鴣鎮的節慶〉:一心成為作家的年輕人,對於鷓鴣鎮發生的槍擊殺人案充滿好奇,以探訪姑婆為由來到鎮上蒐集寫作資料。不料卻踏上一趟意想不到的荒謬旅程……
※ 一致推薦
對芙蘭納莉‧歐康納而言,存在著另外一個世界。
──瑞蒙•卡佛(美國詩人/小說家)
我相信,就像芙蘭納莉‧歐康納所說,一個小說家最後總會寫到他的童年,這是必須的,是這個時期決定了他的命運。
──勒•克萊喬(法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芙蘭納莉‧歐康納和三島由紀夫生於同年,我時常思考他們的生死觀。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深信她爲數不多的作品會永遠活在美國文學中……她的作品比十幾部詩集帶有更多的真正詩意。
──伊麗莎白•畢夏普(美國詩人/小說家)
歐康納的作品可比莫泊桑,角色刻畫精準犀利、地方色彩濃厚……這些故事開創出一個全新的文類,也是第一次能有一位信仰虔誠與才氣高度相當的作家呈現出眼中的美國南方田園。
──《紐約時報》
這些故事中充斥著荒涼、悲憫、滑稽、陰謀與真理。歐康納筆下的角色栩栩如生,令人毛骨悚然。我很難想出比她更風趣或更令人恐懼的作家。
──羅勃•洛威爾(美國詩人)
一雙看盡人性黑暗面的敏銳雙眼、捕捉日常對話的驚人耳力,加上必不可少的譏諷。芙蘭納莉‧歐康納揭露了美國南方田園日常生活的陰暗面。
──荷莉•史密斯(摘自《女性作家五百傑作選》)
歐康納過世後留下的這些故事將會發出更大的光芒,更深刻地打動人心。
──《新聞週刊》書評,華特•克萊門斯
這些故事是大師之作,她是作家中的作家,是無可匹敵的故事工匠。其中某些作品堪稱英語這門語言中最出色的故事。
──《新聞週刊》
當我閱讀芙蘭納莉‧歐康納的作品,我想到的不是海明威、凱瑟琳‧安‧波特或沙特,而是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對於這樣一位作家,還能有更高的讚譽嗎?在此,我要向她為寫出人類的墮落與卑猥所用的小說技藝與揭示的所有真相致上崇敬之意。
──多瑪斯•牟敦(美國宗教思想家)
芙蘭納莉‧歐康納的文體風格可與馬克‧吐溫及史考特‧費茲傑羅並列為我國最優秀的作家之列。光是她筆下的警句雋語就絕對值回書價……每一位作家、想成為作家的人或寫作愛好者都該閱讀她的作品。
──《紐約時報》書評,約翰‧李歐納
歐康納不僅是她所處時代與地方的最佳女性作家,她以傑出作家代代相傳的卓越文學天賦,寫出一種文化的真實精神,表現出在美國被泛稱為「南方」的那個祕密……她是真正的天才。
──《紐約時報》書評版,艾弗列•卡辛
芙蘭納莉.歐康納是個極其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時也是珍稀至極的負面小說家,聖與魔的奇蹟結合。她總是理直氣壯的極盡怪誕、偏激,每篇小說都彷彿有魔鬼與之共舞,甚至就是魔鬼的化身。她絕不療癒,因為這個世界從不讓人好過;她也絕不正常,因為庸常的生活總是尖銳得使人異常。歐康納的全部作品就像肩住黑暗的閘門,逼人凝視幽黯、醜怖和冷酷的邪惡力量。是的,她渾身散發著負面能量,可她的小說真他媽好看極了。
──黃崇凱
作者:芙蘭納莉‧歐康納
1925年生於美國喬治亞州,1947年得到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工作坊文學碩士學位。但在1950年,在首部長篇小說《智慧之血》(Wise Blood)即將完成之際,被診斷得到紅斑性狼瘡。由於疾病導致行動不便,她搬回喬治亞州的農莊,至1964年過世為止,除少數外出演講和旅行外,皆過著半隱居生活。她一生著有兩部長篇小說《智慧之血》、《暴力奪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與數十個短篇故事及大量評論文字。
她的作品多以家鄉為背景,筆下人物富有美國南方色彩。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作品中亦不時反映其宗教思想。她慣以寫實的描繪架構抽象的感性世界,再層層剝剖直透人物流移的意念。她的文字精準,風格詭譎、陰鬱,每篇作品常自成獨特的心靈宇宙,在看似輕鬆幽默的表象下,充滿其中的是疏離、黑暗與可能的救贖。
歐康納有多個短篇小說已被公認?美國文學經典,震撼並影響一代又一代作家。她與卡森‧麥卡勒斯並被視為美國南方哥德文學雙璧,去世時被評論界喻為自史考特‧費茲傑羅去世後美國文學界最重大的損失,並譽為繼福克納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南方作家。
作者:許恬寧
師大翻譯所畢,自由譯者,近期譯有《何時要從眾?何時又該特立獨行?》、《當上主管後,難道只能默默崩潰?》、《慣性思考大改造》。
作者:謝靜雯
專職譯者,荷蘭葛洛寧恩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化碩士。
譯作集:miataiwan0815.blogspot.tw/。
天竺葵
理髮師
山貓
莊稼
火雞
你不會比死更慘
格林利夫
樹林風景
揮之不去的寒意
家的慰藉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鷓鴣鎮的節慶
瘸腿的先進天堂
外邦為何爭鬧
啟示
帕克的背
審判日
莊稼
魏勒頓小姐向來負責餐後清理桌上麵包屑,那是她獨攬的家事。露西婭與柏莎在洗碗,嘉納跑到客廳玩《晨報》填字遊戲,這下子飯廳只剩她一個人,總算可以鬆一口氣。她有條不紊清理著碎屑。真受不了!每天的早餐時間都是酷刑,露西婭堅持所有人必須在固定時間吃早餐,就跟其他餐一樣,說什麼固定的早餐時間,可以養成固定的其他習慣,再加上嘉納經常腸胃不舒服,一定得立下吃東西的規矩,好看著他把洋菜加進麥片粥。哼,嘉納都這樣吃了五十年了,難道還會搞出什麼新花樣。每天早餐都吵一樣的事,先是嘮叨嘉納的麥片粥,最後挑剔她加了三匙鳳梨泥。「魏魏,妳知道那樣太酸,」露西婭小姐每次都講同一句話,「妳知道那樣太酸」,接著嘉納就會翻白眼,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話回應,然後柏莎就會暴跳如雷,一旁的露西婭一臉委屈,接著鳳梨泥就會讓她反胃。
清理桌上的麵包屑可以放鬆心情,讓人有時間慢慢思考。如果要寫故事,首先得想好要寫些什麼。通常她坐在打字機前最文思泉湧,不過坐在餐桌前也可以。首先,得替故事擬好主題,但身邊可以寫的事實在太多,所以她一直想不出究竟可以寫些什麼。她一向都是這麼說的,寫作最難的就是這點。她思考到底要寫什麼的時間,多過實際寫作的時間。有時她放棄一個又一個主題,通常得花上一兩週時間,才能下定決心。魏勒頓小姐拿出銀色麵包屑撣子和盆子,開始清理桌面,心想,麵包師傅會不會是好主題?外國的麵包師傅意象鮮明,麥泰兒•費蒙阿姨留給她四張戴著蘑菇帽的法國麵包師傅彩色照片,他們又高又帥,一頭金髮,而且……。
「魏魏!」露西婭小姐拿著鹽罐走進飯廳,大喊:「拜託,盆子要接在撣子底下,要不然麵包屑會掉到地毯上。上星期我清了四遍,不想再清了。」
「妳清地毯又不是因為我掉麵包屑,」魏勒頓小姐冷冷回答,「我永遠都撿起自己掉的麵包屑,」她加上一句,「而且我掉的比別人少」。
「還有,這次妳把麵包屑撣子放回去之前,要先洗過。」露西婭小姐不放過她。
魏勒頓小姐把麵包屑倒進手裡,扔出窗外,拿著盆子和撣子進廚房,放在冷水龍頭下沖洗,弄乾,塞回抽屜。好了,可以開始打字了,可以在打字機前待到吃飯時間。
魏勒頓小姐坐在打字機前,吐出一口氣。好了!剛才想寫什麼?噢對了,麵包師傅,嗯,麵包師傅。不行,不能寫麵包師傅,不夠精彩,麵包師傅和社會緊張情勢扯不上邊。魏勒頓小姐瞪著打字機,A─S─D─F─G──眼神在鍵盤上游移。嗯,寫老師?不行,絕對不行,魏勒頓小姐總覺得老師令人渾身不自在,她以前念的柳池學校老師還好,但都是女老師。沒錯,柳池女子中學,她不喜歡那個校名,聽起像是研究生物學的地方。她都只跟別人說自己畢業於「柳池」。男老師總讓魏勒頓小姐覺得好像自己下一秒就會念錯字,而且教師也不是現在的熱門議題,他們甚至不是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嗯……佃農!魏勒頓小姐這輩子和佃農沒什麼來往,但有什麼關係,他們是很好的藝術主題。佃農跟其他主題一樣,會讓她顯得具備社會關懷的精神,在她想打進的圈子,這點尤其重要!「鉤蟲是很好的切入點。」她喃喃自語。有靈感!太棒了!她的手指頭興奮地叮叮噹噹掃過鍵盤,但沒真的按下去,接著一下子打出幾個字。
「洛特•摩頓……」打字機出現她要的字,「呼喚他的狗。」「狗」這個字打出來後,魏勒頓小姐突然停住。她打得最順的永遠是第一句話,她總說:「開場白就那樣靈光一閃,出現在腦中!靈光一閃!」她會說出那句話,彈指,接著再說一遍「靈光一閃!」,然後依據開場白,繼續開展故事。魏勒頓小姐腦中冒出「洛特•摩頓呼喚他的狗」這句話,讀了讀句子,好,「洛特•摩頓」這個名字很適合佃農,而且叫自己的狗過去,也完全是佃農會做的事。「狗兒豎起耳朵,衝向洛特。」魏勒頓小姐打下這句話,才發現不行──這樣寫的話,一段話就出現兩次「洛特」,念起來不好聽。打字機嘎吱嘎吱退回去,魏勒頓小姐在「洛特」兩個字上頭打叉,用鉛筆寫上「他」。好了,重來一遍,「洛特•摩頓呼喚他的狗,狗兒豎起耳朵,衝向他。」魏勒頓小姐心想,這樣「狗」這個字也出現兩次。嗯……但聽起來不會像兩個「洛特」一樣重複,沒錯。
魏勒頓小姐深信所謂的「聲音藝術」理論,主張對讀者而言,耳朵和眼睛一樣重要,她很喜歡那樣講,曾告訴殖民地之女聯合會的聽眾:「眼睛形成抽象事物描繪而成的畫面,而一場成功的文學之旅……」(魏勒頓小姐喜歡「文學之旅」幾個字)「……有賴心靈創造出來的抽象事物,以及耳朵聽見的聲音調性……」(魏勒頓小姐也喜歡「聲音調性」這個詞)。「洛特•摩頓呼喚他的狗」這句話聽起來深具抑揚頓挫,接下來的「狗兒豎起耳朵,衝向他」這句,又給了這段話必要的開展。
「他抓著狗兒瘦巴巴的短耳朵,在泥地裡翻滾。」嗯,魏勒頓小姐想著,這句話不曉得會不會太過頭,但佃農在泥地裡翻滾,聽起來還蠻合理的。她以前讀過一本講那種人的小說,書裡的人會幹那種事,而且四分之三的篇幅中,那些人做的事比在泥地裡打滾還離譜。上次露西婭整理她的書桌抽屜,找到那本書,隨手翻了幾頁,就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扔進火爐。「魏魏,今天早上我清妳的桌子時,發現一本一定是嘉納為了開玩笑亂擺的書。」露西婭小姐告訴她,「糟糕透頂的一本書,不過妳也知道嘉納那個人,我把書燒了。」接著神經質地笑了笑,「我確定那一定不是妳的書。」魏勒頓小姐確定,那的確就是自己的書,但說不出口。那本書她是向出版社郵購的,因為她不想在圖書館開口借那本書。書錢連運費一共花了三點七五元,最後四章還沒看完就被燒掉。不過算了,前面讀得夠多了,可以確認洛特•摩頓在泥地裡和狗一起打滾,不算過於離譜的情節。她決定了,先說洛特在泥地裡打滾,後來得鉤蟲就順理成章。「洛特•摩頓呼喚他的狗,狗兒豎起耳朵,衝向他。他抓著狗兒瘦巴巴的短耳朵,在泥地裡翻滾。」
魏勒頓小姐往椅背一靠。開頭還不錯,接下來要安排情節。當然,一定要安插女性人物,或許讓洛特殺了她好了,那種女人總是製造麻煩,被殺是自找的,因為她水性楊花,接著洛特因為殺人而良心不安,飽受折磨。
如果情節要那樣安排,洛特得是個有原則的人,不過這很簡單。嗯,接下來得講那些設定,還得安排愛情糾葛,必須有很暴力、很自然主義的場景、跟那個階級的虐待狂有關的事。很難安排,不過魏勒頓小姐喜歡那樣的挑戰,她最喜歡安排激情的場景,不過真的開始寫的時候,每次都覺得怪怪的,開始顧慮其他人讀到不曉得會講什麼。嘉納會彈指,一抓到機會就向她擠眉弄眼;柏莎會覺得她居然是這種人,而露西婭會扯著愚蠢的嗓音:「妳都對我們藏了些什麼啊?魏魏,妳都對我們藏了些什麼?」然後發出她平常那種神經質的笑聲。不行,現在不能想那群人的事,眼下的任務是安排角色。
洛特很高,駝著背,不修邊幅,脖子紅紅的,一雙大手有些笨拙,但哀傷的眼神看起來像個紳士。牙齒整齊,而且為了暗示讀者他剛強的氣質,得是紅髮。洛特穿著不合身的衣服,但態度大方。魏勒頓小姐心想,或許還是別讓他跟狗一起打滾比較好。女主角的話,至少得有點姿色──金黃頭髮,腳踝豐腴,土褐色的眼睛。
女主角會送食物到洛特的小屋,他坐在屋內,吃著她連鹽沒加的粗劣燕麥,想著日後要完成的遠大目標──再買一頭母牛,一棟粉刷好的房子,乾淨水井,甚至擁有自己的農場。女人會罵他,說他砍的柴火還不夠她的爐子用,抱怨自己的背在痛。她會盯著他吃下那碗發酸燕麥,罵他是膽小鬼,連偷食物都不敢,笑他:「你只是個該死的窮鬼!」然後男人會要她安靜。「閉上妳的嘴!」他大吼,「我受夠了。」她會翻白眼,模仿他的樣子,然後大笑──「誰會怕你這種人。」然後他會起身,推開椅子走向她,她一把抓住桌上的刀──魏勒頓小姐想著,這女人怎麼這麼蠢──女人後退,刀拿在前方。男人撲向她,但她像一匹野馬逃開,接著兩人再度對峙──眼中充滿恨意──你進一步,我退一步。魏勒頓小姐可以聽見時間一分一秒落在外頭鐵皮屋頂上。他再度衝向她,但她拿好刀,瞬間就能刺向他──魏勒頓小姐再也忍不住,從後方狠狠打女人的頭,刀子從女人手中落下,屋內冒出一陣煙霧捲走她。魏勒頓小姐登場,告訴洛特:「我幫你弄點熱騰騰的燕麥粥。」她走到火爐旁,拿了一個乾淨湯盤,裝進爽口潔白的燕麥,還放上一塊奶油。
「天啊,謝了。」洛特微笑向她道謝,露出一口整齊牙齒。「妳煮的東西總是這麼美味。妳知道的,」他說,「我在想──我們可以離開這座佃農場,找個好一點的地方。如果今年收成不錯,我們就能養頭母牛,開始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魏魏,妳想想,多美好的未來啊,妳想想。」
她倚著他,頭靠在他肩上。「會的,」她說,「今年收成會比先前任何一年都好,到了春天,我們就能買母牛。」
「妳最懂我了,魏魏。」他說,「妳是天底下最懂我的人。」
他們坐在那很長一段時間,想著彼此是如何相知相惜,最後她說:「把東西吃完。」
他吃完後,幫她清理爐灰。在炎熱的七月夜晚,他們漫步過草原,朝著小溪前進,聊著有一天要買下哪塊地。
到了三月下旬,雨季將臨,他們完成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量。過去一個月,洛特每天清晨五點起床,魏魏比他早起一小時,兩個人趁著天氣轉壞前,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洛特說,下星期大概就會開始下雨,如果不搶在那之前收成,一切就完了──過去幾個月的努力將付諸流水。他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接下來的一年,又得和去年一樣清苦,買不起母牛,而且明年會多一個孩子。洛特還是想買母牛。「餵飽孩子花不了那麼多錢,」他辯解,「而且母牛也能餵孩子。」然而魏魏態度堅決──母牛以後再說──孩子一落地就得好好養。「或許,」洛特最後讓步,「或許錢將夠同時養母牛和孩子。」他到外頭巡視新犁好的田,就像能從犁溝中數出農穫量一樣。
他們擁有的不多,但這是美好的一年。魏魏大掃除一番,洛特修理好煙囪,門階旁長著茂密矮牽牛,窗下是花團錦簇的金魚草,日子非常祥和,然而兩人愈來愈擔心農作物,一定得搶在雨季來臨前收成。「我們還需要再一星期。」那天晚上洛特進屋時喃喃自語,「只需要再多一星期就夠了。妳能幫忙收成嗎?不該要妳去,」他嘆氣,「但我請不起人。」
「我可以的,」她把發抖的手藏在背後,「我來幫忙收成。」
「今晚雲層很厚。」洛特憂鬱地說著。
隔天,他們一路工作到傍晚──一直做到沒力氣,跌跌撞撞回小屋,躺進床裡。
晚上她痛醒,那是一陣柔和、透出紫光的綠色痛苦。她懷疑自己究竟醒了沒,頭左右動來動去,裡頭有嗡嗡作響的光影在摩擦石頭。
洛特坐了起來,不安地問她:「妳不舒服嗎?」
她用手肘撐起身體,但又陷了下去。「去河邊找安娜。」她喘氣。
嗡嗡聲愈來愈吵雜,光影愈來愈灰暗,最初參雜幾秒鐘的疼痛,接著是永無止境的劇痛,一遍又一遍。嗡嗡聲愈來愈響,天明之際,她明白過來那是雨聲,啞著嗓子問:「雨下了多久?」
「快兩天了。」洛特回答。
「這麼說,農作物沒了。」魏魏無精打采看著樹木滴水,「一切都完了。」
「沒完,」他柔聲說,「我們有了女兒。」
「你想要兒子。」
「不,我心滿意足──一加一,現在有兩個魏魏了──這比擁有母牛還棒。」他咧嘴而笑,「魏魏,我怎麼這麼幸運?」他俯身親吻她的額頭。
「我該怎麼做?」她緩緩地問,「該怎麼做,才能多幫你一些?」
「那妳幫忙去趟雜貨店好了,魏魏?」
魏勒頓小姐推開身上的洛特。「什─什麼,妳說什麼,露西婭?」她結結巴巴。
「我說,這次妳幫忙去趟雜貨店好不好?這星期每天早上都是我去,我現在很忙。」
魏勒頓小姐從打字機前起身。「好吧,」她尖聲說,「要買什麼?」
「一打蛋,兩磅番茄──要熟番茄──還有妳最好現在就治一治感冒,都在流眼淚了,喉嚨也啞了,浴室有安匹靈。雜貨店那,用這裡的名義開支票,還有記得穿外套,天冷。」
魏勒頓小姐翻白眼,「我都四十四歲了,」她大聲說著,「我能照顧好自己。」
「別忘了挑熟番茄。」露西婭小姐回她。
魏勒頓小姐外套釦子亂扣一通,沒好氣地踩在布羅德街上,走進超市。「現在是要買什麼?」她喃喃自語,「噢,對了,兩打蛋,一磅番茄。」她走過一排排罐頭蔬菜與餅乾,朝著雞蛋箱走去,但裡頭是空的。「怎麼沒蛋?」她問正在秤四季豆的男孩。
「只剩初卵蛋。」男孩又秤了一把四季豆。
「在哪裡?那種蛋有什麼不同?」魏勒頓小姐問。
男孩把幾根四季豆扔回籃子,懶洋洋地彎身從箱子裡遞給她一盒。「其實沒什麼不同。」他回答。男孩拿開黏在門牙上的口香糖,「是小母雞生的蛋還是什麼的,我不知道,要買嗎?」
「要,還要兩磅番茄,要熟的。」魏勒頓小姐吩咐。她不喜歡買東西,店員憑什麼態度這麼差。如果是露西婭來買,這孩子態度一定不會這麼散漫。她付清雞蛋和番茄的錢,連忙離開,這地方讓她心情差了起來。
真無聊,幹嘛為了雜貨店心情不好──雜貨店什麼都沒有,只有瑣碎的家務事──買豆子的女人──手推車上的孩子──為八分之一磅左右的南瓜討價還價──這種事有什麼意思?魏勒頓小姐百思不得其解。這裡難道有機會讓人表達自我,有機會讓人創造,有機會帶來藝術?目光所及都是一樣的東西──人行道上擠滿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個人手上拿著一堆小袋子,腦子裡也是一堆小瑣事──那邊那個女人用皮帶拴著孩子,想把兒子拖離擺著南瓜燈的櫥窗,她大概一輩子都會那樣控制著他。然後那邊又有一個,袋子掉了,東西灑了滿街。還有個擦著孩子鼻子的人。前面一個老女人,帶著三個蹦蹦跳跳的孫子,後面還跟著一對缺乏教養、黏在彼此身上的情侶。
魏勒頓小姐和那對情侶擦身而過,不由得瞪大了眼。女人身材豐滿,金黃頭髮,腳踝圓潤,一雙土褐色眼睛。身上是高跟鞋和藍色短襪,還有過短的棉裙和格子上衣,皮膚佈滿雀斑,脖子往前突,好像在聞前方一直後退的東西,臉上掛著愚蠢笑容。男人高高的,不修邊幅,駝著背,粗紅脖子上長著黃瘤,一路擠開路人,笨手笨腳牽著女孩,沒事還噁心地對著她笑。魏勒頓小姐看見那個男人有著整齊的牙齒,憂鬱的雙眼,額頭還長著疹子。
「噁。」她抖了一下。
魏勒頓小姐把買回來的菜擺在廚房桌上,回到打字機前,看著打字機裡的紙:「洛特•摩頓呼喚他的狗,狗兒豎起耳朵,衝向他。他抓著狗兒瘦巴巴的短耳朵,在泥地裡翻滾。」
「聽起來糟透了!」魏勒頓小姐喃喃自語,她決定了,「反正也不是什麼好主題。」她需要精彩一點的東西──藝術性得更強一點。魏勒頓小姐瞪著打字機,一動也不動,接著突然間興奮地搥起桌子,「愛爾蘭人!」她開心大喊,「愛爾蘭人!」魏勒頓小姐一向喜歡愛爾蘭人,他們說話的腔調充滿音樂性,還有他們的歷史──精彩極了!還有人民,她想著,愛爾蘭人!他們活力十足─紅頭髮,肩膀寬闊,留著長長的濃密鬍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