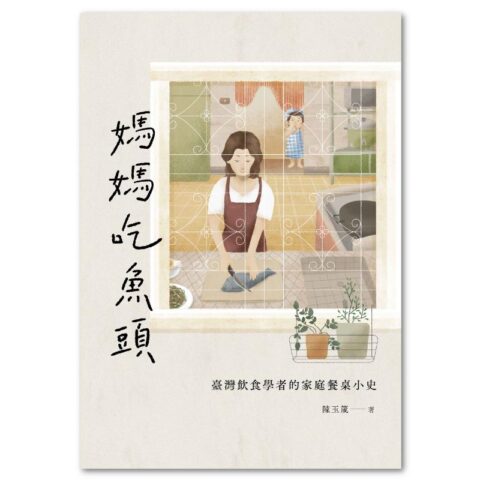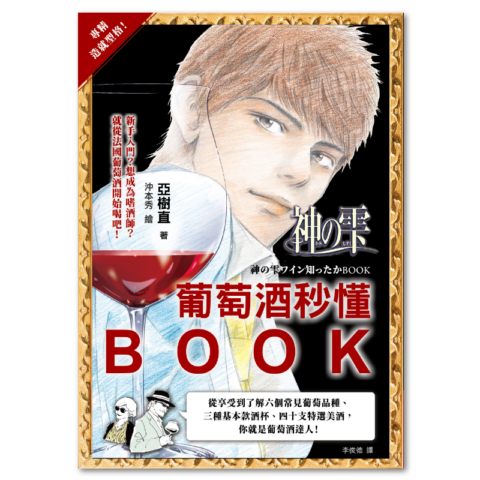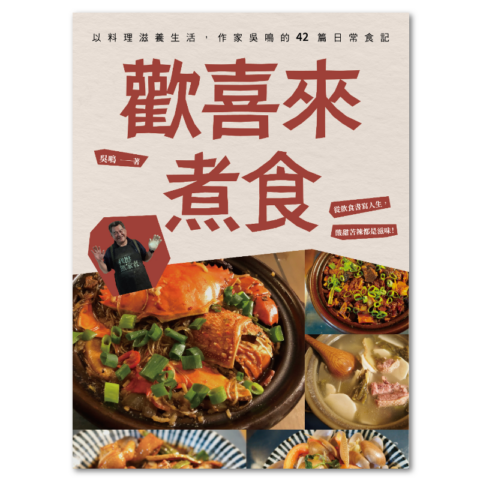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
出版日期:2017-03-25
作者:胡川安、郭婷、郭忠豪
印刷:半彩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5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9127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上最具人氣的「深夜食堂小隊」出擊!
訴說上海、東京、紐約三地鄉愁料理的歷史文化。
帶領讀者品嘗三個國際大城的懷舊美食,感受唇齒間的鄉愁。
體驗異鄉人的生活點滴,串起移民與食物之間的美好記憶。
一本蘊藏著對往昔時光和故鄉脈脈溫情的滋味書寫。
「胡川安以歷史學者的眼光,俯視日本庶民料理漸進交融異國文化的脈絡,郭婷以纖細感性,懷想家族故事與昔日餐飲情境,勾勒出金枝玉葉的上海,郭忠豪則以樸實的筆記錄了台灣移民在美營生的奮鬥史,徘徊今昔,穿越國境,這是一本嚼在唇邊、流抵心田的滋味書寫。」
──梅村月(「Moon’s 月光食堂」部落客)
城市,是鄉愁的起點與終點。
在「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上,晝伏夜出的「深夜食堂小隊」長期為讀者帶來既罪惡又兼具情懷的飲食小品。這一次,「深夜食堂小隊」中的胡川安、郭婷、郭忠豪連袂出擊,嘗試將食人、食事、食地置放於更廣闊的時空脈絡下,打造出《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一書。他們聚焦於東京、上海及紐約三座國際大都市中,移民、離散、流亡、異鄉人和食物的關係,用食物串起世代間關於移動、鄉愁和品味的記憶,以食物訴說時光流轉的故事。
從東京的日式燒肉、咖哩、紅豆麵包和麻婆豆腐,勾起他鄉亦故鄉的情懷,也見證東西方美食交會影響的亙永記憶。一碗羅宋湯的背後,藏著流亡白俄與夜上海的故事,栗子蛋糕及蝴蝶酥更訴說著是蟄居於街角的老上海風華。在紐約打拚的台灣人,則為中國菜或台灣珍珠奶茶闖出一席之地,這些戍守他鄉的移民最終透過鄉愁將台灣的美食扎根於異鄉。這是一場透過食物的時空旅行,從亞洲到美洲、從成都到東京、從土耳其到上海、從台北到紐約……每一道菜溫暖了脾胃之外,更承載著家族、家鄉和文化的記憶。
※ 名家一致推薦
陳芳明(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梅村月(人氣部落客「Moon’s月光食堂」)
金宇澄(作家、《上海文學》執行主編)
舒國治(作家)
謝金魚(故事網站共同創辦人)
蔡詩萍(作家)
莊祖宜(作家)
作者:胡川安
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曾於日本、巴黎、美國、中國和加拿大生活過。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國立臺灣大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碩士,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郭婷
上海成長、英國求學。愛丁堡大學人類學碩士、宗教學博士。曾任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研究宗教與政治、藝術、文化的關係,以及不同政治文化語境中信仰的邊界。同時也是《洛杉磯書評》、openDemocracy、《書城》、BBC中文網等知名中英文媒體撰稿人。
相信審美有反思和改變結構的力量,致力推廣慈善店和舊物upcycle。除「宗教與食物」之外,也曾在「故事」開創「舊物的故事」專欄,希望向中文讀者介紹綠色審美的生活方式。
作者:郭忠豪
高雄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目前任職於台北醫學大學,研究興趣是近代東亞的食物與動物,以及海外華人飲食文化。工作之餘酷愛網球運動,赴外研究必帶上網球拍,征戰各地以球會友,喜愛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嚴謹的學術議題,再將之化簡為有趣的歷史故事。聯繫方式:chk256@nyu.edu。
推薦序 父親的鄉愁味(韓良憶)
序 唇齒間的鄉愁
東京──他鄉亦故鄉
麵包的「和食」化:麵包與紅豆麵包的故事
「日式」燒肉很「韓式」?韓國人留在日本的遺產
獨立領袖的家鄉味:印度咖哩、日式咖哩與亞細亞主義
麻婆豆腐跨海飄香:陳建民與四川料理在日本
上海──風雲際會的註腳
「色戒」中千鈞一發的凱司令咖啡館
羅宋湯與流亡上海的故事
國際飯店的蝴蝶酥與法國的parmier
海上舊夢:沙利文咖啡館的故事
法租界的紅房子西菜社:火焰冰激凌的融化
紐約──戍守他鄉的台灣人
歷史學家進廚房:紐約李正三與張阿雪,以及郭正昭與郭錫玉
曼哈頓的辣椒味道:蜀湘園集團的故事
那一段台灣料理的美好日子:紐約呂明森的「紅葉餐廳」
新台灣移民的珍珠奶茶:Coco 和Vivi
小結:紐約台灣人餐館歷史
後記 從深夜食堂小隊到《食光記憶》(謝金魚)
父親的鄉愁味(韓良憶)
看了《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讓我想起了父親與他的「西餐」。
常聽人說,在異國求學、就業期間,午夜夢迴,想家的時候,最渴望卻不可得的,往往是故鄉路邊攤的一盤蚵仔煎、一碗肉圓或媽媽的炒米粉。我旅居荷蘭的那些年,也不乏凡此種種將鄉愁寄於舌尖的時刻,然而讓我饞到快掉淚了,不光是所謂的台灣味,偶爾還有從小吃到大的西餐,對我而言,那也是家鄉的味道。
比起同一輩台灣人,我算是比較早接觸到西洋食物,原因無他,因為先父愛吃西餐。開始跟著爸爸上西餐廳時,我才五、六歲吧,說不定更小。我們最常去中山北路二段的「大華飯店」,偶爾上嘉新大樓頂樓的「藍天西餐廳」或南京東路的羽球館餐廳,後來大華歇業了,我們就轉去小南門的「中心餐廳」。
多半由爸爸點菜,前菜不是燴牛舌,就是燻鯧魚,湯常常是牛尾湯或鄉下濃湯(番茄蔬菜湯)。主菜呢,最常吃忌士烙魚或烙蝦,一小盅端上桌,表面是焗烤到焦脆的忌士,也就是乳酪。揭開來,熱氣氤氳而上,底下是奶油白醬,裡頭埋著無刺的魚肉或明蝦。還有炸豬排,敷了麵包屑炸成金黃,舖在瓷盤上,偌大的一片。吃豬排時一定要蘸「梅林辣醬油」,爸爸還會吩咐跑堂,多來點酸甜的「酸黃瓜」。
及長才知道,我從小到大吃得津津有味的所謂西餐,包括爸爸三不五時便親自下廚熬煮的「羅宋湯」在內,都是源自上海的海派西餐,亦稱滬式西餐。我所熟悉的那些菜色,全是摻雜了中國味的法國菜、德國菜、義大利菜、英國菜和俄國菜,從來就不是道地的西菜。
根據舊式的身份證,父親籍貫是江蘇東台,但他其實是在與上海崇明島隔江相對的南通長大,成年後在上海住過一陣子。對於像爸爸這樣從小養尊處優又生性好奇的小城富家子弟而言,上海這十里洋場是世上最摩登的所在,也是他與西洋接軌的開始,而好吃也講究吃的父親,與滬上的洋事物最直接也最切身的接觸,想來就是海派西餐了。
海派西餐肯定特別合他的胃口,不然,他怎麼會在來到台灣、結婚生子後,還不時帶著他的本省籍妻子和台灣出生的子女,吃遍台北有名的滬式西餐館?好幾年前,我不知在網上還是書中看到一篇文章,說是六○年代末期,台北大華飯店一客A餐(一湯兩菜外加甜點和飲料)的價錢是普通小學教員將近半個月的薪水。倘若此事不假,雖說孩子胃口小,可以點半客,價錢便宜一點,但是咱一家大小週末去吃頓西餐,終究得花掉當時小學老師一個半月以上的勞務所得!爸爸為了吃西餐,竟如此揮霍。
近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標榜著正宗法國菜、德國菜、義大利菜的餐廳,出現於台北街頭,時代和社會氣氛的變遷,加上父親這一輩的「江浙人」慢慢老去,不中不西的滬式西餐無可避免地凋零了,最終僅存七○年代中期遷居信義路二段的「中心」強撐場面,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又熬了五、六年,才熄火歇業。
父親在世最後幾年,我回台灣探父,三番兩次問他想不想去吃西菜,好比義大利菜或法國菜,他總是不置可否,意興闌珊。有一回跟他聊天,講到兒時的大華飯店,他那天談興甚高,順著我的話頭,一一數說起當年台北有名的西餐館,結論是,「大華算是最好的,不輸老上海的西菜館。」這話一說完,老人家又沉默了,臉上浮現惘然的神情。
就在那一刻,我彷彿明白了,父親愛吃的根本並不是「西洋菜」。對他而言,帶著中國味的滬式西餐,並不只是口腹之欲,那當中尚蘊藏著對往昔時光和故鄉的脈脈溫情,換句話說,那其實是父親的鄉愁滋味,而這樣亦華亦洋的「西餐」,眼下也已成為我將永遠懷念的父系味道。
序
◎ 唇齒間的鄉愁
城市,是鄉愁的起點與終點。
城市,是鄉愁的起點與終點。
東京、紐約和上海都是人群輻輳之地,四面八方的人們聚集於此,除了城市本身的性格外,移民也增添了多元的文化。負笈他鄉,在異地求學、生活、工作,各式各樣的原因讓人群得遠走他鄉,到異地生活。由移民從家鄉所帶來的口味在城市中混合、雜揉,消解了移民的鄉愁,也增加了城市的特色。
《食光記憶》聚焦於移民、離散、流亡、異鄉人和食物的關係,在聚散離合益發頻繁的當代,用食物串起世代間關於移動、鄉愁和品味的記憶,以食物說時光流轉的故事。這是一場透過食物的時空旅行,從亞洲到美洲、從成都到東京、從土耳其到上海、從台北到紐約……每一道菜溫暖了脾胃之外,也承載著家族、家鄉和文化的背景。
◎ 東京
日本的飲食文化透過台灣移民的努力在紐約開枝散葉,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飲食文化也不是那麼的「日式」,而是日本人與不同移民所交錯的結果。美國艦隊司令培里於一八五三年要求日本開港,結束了日本的鎖國,外國人進入日本。隨著明治維新日本的壯大,對外發動戰爭。以往的歷史都強調政治的變遷與技術的革新,但是透過食物也可以理解日本的現代歷程、認識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書中的紅豆麵包、咖哩飯、燒肉和麻婆豆腐分別代表了日本人與西洋、印度、韓國和中國交流的縮影。這四種食物現在都在日本生根,成為日本的國民美食,但每一種食物都展現一個時代的片段,串聯起日本的近代史與大時代的悲歡離合。
紅豆麵包可以看到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對於西洋麵包的吸收與轉化;印度咖哩和日式咖哩則是一段愛情與反殖民戰爭的故事;燒肉則說明了韓國人在殖民期間帶給日本的遺產;而麻婆豆腐的故事則表現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愛恨情仇,但發生的場所卻在東京。每一則故事都有著無數的生命流轉於其中,不同的移民匯聚於東京,東京的飲食改變移民,移民的飲食也改變了東京。
◎ 上海
鄉愁是種記憶,有點模糊,但帶著浪漫,朦朧間將大時代的悲劇美化了。一九三○年代的上海似乎總是帶點洋味,帶點殖民風情,有時看是中又是西,但又不是中也不是西,文化總是介於中間,模糊、不清楚,混雜著多種文化特質的元素。對於郭婷而言,上海不只是懷舊的浪漫,也是家族的生命記錄,繾綣的回憶那興盛與破敗的共榮共生。
或許對於魔都上海的書寫已經過多了,從小說、電影到學術研究不勝枚舉,但缺乏食物給人的溫暖和感情、缺乏凱司令咖啡館中栗子蛋糕的甜蜜,沒有國際飯店蝴蝶酥中所烘焙的記憶和文化、沒有紅房子西餐廳中火焰冰激凌的冰火交融、當然也少了一點羅宋湯當中俄羅斯人流亡的故事。飲食、餐廳和鄉愁的記憶,在餐桌上共同譜寫上海那段畸形、中西雜揉且絢麗的繁華。
◎ 紐約
留學生至異地求學,夜深人靜時除了陪伴自己的書本,還有濃濃的鄉愁。鄉愁的滋味通常只能透過食物來排解,一杯珍珠奶茶、一頓同鄉間的宴席、一碗滷肉飯,總是讓台灣學子們稍稍忘懷思鄉之情。畢業於紐約大學歷史系的忠豪,長期關注紐約華人與台灣移民的飲食文化,除了以吃一解鄉愁,也了解台灣人在異鄉打拚的歷史。台灣人在紐約所開的菜館,反映了台灣的歷史現實,包含著日本文化的浸染、一九四九年中國移民的遷徙,具體而微的展現這個島的身世。
或許是台灣受到日本殖民的影響,很早就習慣日式的飲食文化,所以紐約第一家迴轉壽司「元祿壽司」就是由台灣留學生創業發揚光大的,幫紐約的餐館地圖注入日本味道。有趣的是,甚早在紐約出現的川揚菜館也是台灣人創立的,它結合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智慧,成為當時紐約客的中菜廚房,可以說反映了外省移民與本省交錯的歷史現實。當然,道地的台菜餐廳也讓紐約台灣移民大為驚艷,甚至錯把他鄉當故鄉了。而新世紀的台灣餐飲非珍珠奶茶搭配鹽酥雞莫屬,不但在全美造成風靡,也能看見台灣新移民如何把東方的茶文化帶向全世界各個角落。
紐約、東京、上海,都是國際城市,匯聚各色人種,每個人都帶著自己故鄉的味道,但也沾染了這個城市的色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透過飲食看到了城市的鄉愁,也在城市的多元文化中解消了鄉愁。
獨立領袖的家鄉味:印度咖哩、日式咖哩與亞細亞主義
反帝國主義的中心:東京
一百一十一年前的日俄戰爭,亞洲的小國日本在對馬海峽擊敗俄國,從日本、印度、土耳其、越南到埃及,甚至整個歐洲和美洲都為之震動,歐洲人不看在眼裡的亞洲人竟然戰勝了!美國的老羅斯福和印度後來的獨立領袖甘地都大感驚訝,將之視為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他們說:
「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現象。」老羅斯福說。
「日本戰勝的根已蔓生得太廣太遠,因為它會長出的那些果實,如今已無法完全遇見。」甘地說。
孫文在同一個時間從倫敦前往亞洲的路上,化名中山樵,蘇伊士運河的阿拉伯搬運工以為他是日本人,也向他恭喜。
《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開頭就討論日俄戰爭的意義不僅在於日本打敗俄國那麼簡單!從世界史的意義來說,它是被殖民人群的一道曙光、是亞洲人民走向未來的啟示、是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可能性。
日俄戰爭後,東京取代了巴黎、倫敦,成為亞洲知識分子嚮往的留學之都,中國的魯迅、周作人、梁啟超、孫中山等不同政治理想的年輕知識分子都齊聚東京。
東京取代了北京,成為亞洲世界的中心,也是反西方殖民主義的根據地。
出身印度的革命領袖拉什.貝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支持印度獨立、希望亞洲人民站起來。但是博斯的故事不只於此,他也促進了飲食文化的交流將印度咖哩帶入日本,促進了亞洲飲食文化的交流。
印度出身
博斯出生於印度班加羅爾的殷實家庭,年輕時在法國和德國得到醫學和工程的學位。然而,他像孫中山一樣,熱情地參與國家與民族的復興。中華民國誕生的同一年,一九一二年十月的槍聲和爆炸聲讓滿清政府垮台,而十二月底在印度,英國的殖民政府,將首都從以往蒙兀兒王國的舊都遷到新德里的儀式上,也發生了爆炸事件,總督哈汀(Charles Hardinge)負傷,典禮因為爆炸事件而讓英國政府蒙羞,馬上開始緝凶。
爆炸的主謀就是博斯,在英國的追捕下,選擇棄國離鄉,前往反帝國主義的中心:東京。博斯從德里出港,經過香港,最後在神戶上岸,得到很多支持印度獨立的友人幫忙,像是大川周明、頭山滿,也在日本結識了孫中山。孫中山積極的幫助博斯,讓他可以購買軍火,並且從上海運往印度,然而英國政府聽聞了風聲,查獲了軍火,也得知博斯在日本藏匿,向日本政府施壓。
日本政府雖然同意英國要追查博斯,但卻按兵不動,似乎把他當成一顆活棋,可以和英國政府談判。透過孫文和他的心腹廖仲愷的牽線,讓事情有了轉機,《朝日新聞》的記者山中峯太郎秘密的採訪博斯,並在報紙上刊出〈歐戰與印度〉,文章一出,日本民眾大為支持印度的處境,希望他們能夠脫離英國暴虐的殖民統治。
然而,此時正處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日本是同盟,所以日本政府也不便公開支持博斯。而且,山中峯太郎的文章一出之後,更讓英國政府提出嚴厲的外交抗議,希望日本要求博斯離境。在英國的壓力下,日本限博斯五日離境,命令一出,輿論譁然,《朝日新聞》嚴厲批評政府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下,讓印度三億人民的情感受到傷害。
幸好日本的右翼組織「玄洋社」的領袖頭山滿出面幫助博斯,頭山滿是日本近代的傳奇人物,也是黑幫組織的共主,支持亞洲人民與帝國主義對抗,對於中國革命採同情的立場,並在人力和財力上支持孫中山。
隱匿中村屋與印度咖哩的誕生
頭山滿的好友,在新宿賣西點麵包的中村屋老闆相馬愛藏和相馬黑光夫妻檔,對於日本政府將博斯逐出日本的舉動也無法諒解,主動提供藏匿之處給博斯。由於相馬夫妻和頭山滿之間過從甚密,警察也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相馬夫妻的女兒俊子就負責滿足博斯的生活起居。
俊子從小在父母的栽培下,不僅會讀會寫,還學會了英文,能與博斯溝通。孤獨的印度流亡領袖,平日只能和俊子抒發心中的苦悶,兩人日久生情,在頭山滿的見證下完婚。
博斯和俊子結婚之後,為了報答相馬夫妻,給了他們純正印度咖哩的秘方。中村屋的純正印度式咖哩推出之後,在市場頗受到歡迎,而且廣告上說是「印度貴族的純正咖哩」,不走平民美食的路線,一盤當時賣八十錢,相較於當時一盤十錢到十二錢的咖哩飯,足足貴了八倍,鎖定金字塔頂端的客群。
博斯後來被稱為「中村屋的博斯」,和太太俊子生有一兒一女,歸化成日本人,俊子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博斯則是繼續他的獨立運動。
印度咖哩之所以在昭和時期獲得東京人的歡迎,並且願意花大錢來吃,主要是因為「日式咖哩」已經在明治晚期、大正時代傳播開來,當時的人都知道咖哩飯是甚麼東西。至於咖哩飯如何在日本傳播開來的呢?如何變成「日式咖哩」呢?讓我們從昭和時代回到明治時代早期,看看日本人的咖哩初體驗。
日本人的咖哩初體驗
日本人一開始接觸咖哩,把它當成西洋料理,從夏目漱石的留英日記或是明治時代的報紙當中都可以發現,咖哩不被當成印度料理,而是文明開化的西洋料理。
被視為西洋料理的咖哩,一開始在日本上陸先在通商口岸橫濱,當時只有少數的餐廳賣這種具有奇怪臭味的醬汁,配上日本人本來不吃的家畜肉。
咖哩飯的食用在日本大規模的成長主要跟北海道的開拓有關。北海道的農業開拓並不是以日本本土的農業為藍本,而是以美國的農業技術為目標。出生美國的克拉克博士被日本政府高薪聘請至札幌農學校(後來的北海道大學)擔任校長。
札幌農學校的學生食堂中,咖哩飯就是其中一項常吃的食物。由於北海道的天氣和日本本州差異很大,札幌農學校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此移植合適的蔬菜,引進西洋的野菜。
引進的野菜中,對於日式咖哩誕生最重要的三種是:洋蔥、胡蘿蔔和馬鈴薯。洋蔥雖然在江戶時代就引進,但是大規模的種植還是得等到北海道的開拓。札幌農學校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引進美國的洋蔥以配合北海道寒冷的天氣。
同樣也是江戶時代傳入的馬鈴薯,在日本的生產量並不高。日本本土主要以米食為主,搭配蕎麥麵和烏龍麵等麵食和雜穀。適合寒冷地方種植的馬鈴薯在江戶時代末期引進北海道,並且成為北海道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
馬鈴薯隨著西洋料理引進日本,產量逐漸增加,到大正時代初年(二十世紀早期),就已經超過一百八十萬噸。大正八年(一九一九)的米價高漲,政府也加強推廣馬鈴薯,日式咖哩飯中的馬鈴薯就是在這一個時代脈絡下逐漸滲入日本民間。
至於胡蘿蔔,本來日本人所食用的蘿蔔是從中國傳進的白蘿蔔,為了適應北海道的天氣,在明治時代大量種植西洋的紅蘿蔔,現在日本的紅蘿蔔產量也以北海道最高,占全國的三成以上。
日式咖哩與印度咖哩最大的不同就在這三種配菜,日本人稱作咖哩的「三種神器」,是別的地方看不到的煮法。日式咖哩加入三種配菜的原因在於推廣三種新引進的食物,使日本人熟悉他們。
除了三種配菜之外,日式咖哩還有一項很重要的特色在於配菜:福神漬,也就是吃飯的醬菜。日本人吃飯一定要配醬菜,為了使咖哩飯吃起來像是一餐飯,日本人也加了這種熟悉的配菜。
日本人不僅把咖哩與醬菜一起配,也把常吃的食物加進咖哩,明治時代出現牡蠣咖哩、野菜咖哩和咖哩麵,將原有的食物都加入咖哩,以增加對於咖哩的熟悉感。
明治維新不僅是技術上的革新、觀念上的改變,也是味覺上的新體驗,這個時代的人每天得了解、體驗不同的事物。飲食的文化交流循序漸進,為了熟悉咖哩的味道,日本人在其中加了一些熟悉的東西,讓咖哩不再那麼陌生。
速食咖哩
明治維新也促成了食品工業的發展,將咖哩做成咖哩粉,變成速食咖哩,讓咖哩得以進入一般民眾的飯桌。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東京的一貫堂就製造出了日本的速食咖哩,當時的廣告宣傳:「本咖哩粉採用極上生肉製成,無須擔心腐敗的問題,由熟練的大廚精心製造,味美且芳香,適合旅行攜帶。」一貫堂的咖哩用熱水沖泡即食,使得咖哩得以大眾化。從明治晚期作家的隨筆和日記中就可以看到咖哩飯已經成為當時一般人餐桌上常見的食物,像是出生東京淺草的澤村貞子或是俳句詩人正岡子規的記錄。
從明治晚期到大正初期,所謂的「三大洋食」:豬排飯、可樂餅和咖哩飯在日本的大城市中逐漸成為城市一般民眾的美食。
咖哩飯在日本不同地方也有所差異,一般而言,關東人較喜歡豬肉咖哩、而關西人則喜歡牛肉咖哩,會造成關西、關東肉類食用差異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關西人控制了主要的牛肉產地。
阪急百貨店與咖哩
關西咖哩飯的普及和阪急百貨的展店有著密切的關係。
阪急百貨的創辦人小林一三出身山梨縣的豪商,在創辦阪急百貨前做了各式各樣不同的生意,他抓準了時代的脈動與社會的變化,隨著大阪城區的大規模擴張、阪急鐵道的鋪設,阪急百貨店也隨著在大阪、神戶各地開設。
為了迎接來百貨店購物和通勤的人潮,阪急百貨不斷地擴充百貨店的商場和美食街,其中主要以洋食為主,昭和時期的日本人對於西洋的食物已經逐漸熟悉,但有些餐廳還是消費不起,阪急百貨和飼養牛隻的農家訂定契約,取得廉價的牛肉,壓低咖哩飯的售價,讓一般人搭乘火車和到百貨公司逛街的民眾也能消費得起,當時一天可以賣出一萬三千盤,大受歡迎,這也影響到關西民眾對於咖哩飯的接受,他們一開始吃的就是咖哩牛。軍隊中的咖哩飯
相較於洋食餐廳主要是在大城市裡,使得咖哩飯普及的原因還在於軍隊的推廣。日本人學習西方文化不只是表面的層次,連外國人吃甚麼也一起學。明治維新確認了以英國的海軍作為日本帝國海軍的編制,英國海軍吃咖哩,日本人也一起學。從一九一○年所出版的《軍隊料理法》所羅列的一百四十六道食譜裡,可以看到豬排飯、咖哩飯、馬鈴薯燉菜、牛肉丸等這些日本人以往不吃的肉類食物烹煮方法。
對於大多數的士兵而言,從軍之後的飲食是他們人生的初體驗,也是洋食、咖哩飯和豬排飯的第一次嘗試。當時日本每人每年的牛肉消費量才一公斤左右,但是服役的士兵一年可以吃到十三公斤。而且,服役的士兵可以吃到以往不容易吃到的白米飯,對他們而言,咖哩飯、洋食可以讓他們吃得飽,飲食文化的和、洋交流也比較容易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