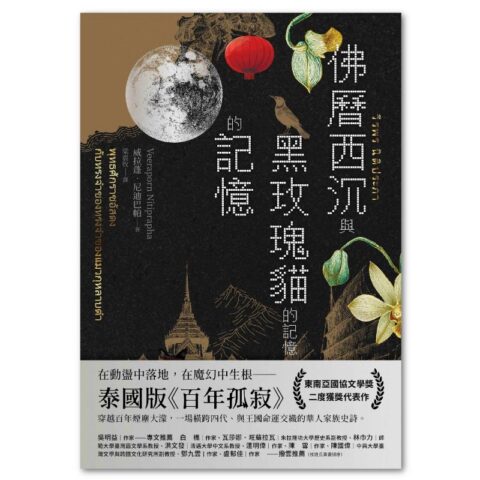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享譽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森鷗外經典之作)
出版日期:2019-07-17
作者:森鷗外
譯者:鄭清茂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56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6cm
EAN:9789570853421
系列:小說精選
尚有庫存
森鷗外──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富影響力的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並稱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
要瞭解日本近代文學,不能不知道森鷗外!要知道森鷗外,就不能忽略奠定他成為文壇巨擘的歷史小說!
由知名學者、翻譯家鄭清茂編選、譯注其歷史代表作五篇《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收錄:
〈山椒大夫〉──觸及奴隸解放問題的代表作、改編之電影更獲威尼斯影展銀熊獎殊榮
〈阿部一族〉、〈護持院原復仇記〉──以傳統大和魂精神切入,重新探討武士道「殉死」與「復仇」之作
〈安井夫人〉、〈魚玄機〉──改寫自歷史真實女性角色,喚起時代包袱下,女性對於自身關注及覺醒
知名學者、翻譯家鄭清茂特從森鷗外的短篇歷史小說編選五篇代表作,略加注釋,包括
〈阿部一族〉汲取了武士道精神演變到後期的變形以及人性矛盾,講述一位身為家臣的武士未獲藩主許可而殉死,結果不但犬死(白死),甚至招致了一家滅絕的悲劇故事;
〈護持院原復仇記〉脫胎自武士復仇的史料,提出申請得以復仇的主角,歷經千辛萬苦,走遍大半日本,幸得神佛保佑才得以了卻復仇之願。
〈安井夫人〉主角是江戶末期至明治初年的大儒安井息軒的夫人佐代,婚後為丈夫及家庭奉獻,終其一生盡力於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卻也讓人看到女性在大時代中無從選擇的無奈;
〈山椒大夫〉為古代傳說的翻案,描寫平安時代末期的貴族姊弟安壽與廚子王,被騙作童奴飽受苦難折磨,最終逃離困境,也點出奴隸買賣、解放的問題;
〈魚玄機〉改編自中國歷史人物,有美人之稱而廣受歡迎的晚唐才女詩人,因為嫉妒之心而殺死婢女,落得入獄受斬之下場,卻也反映當時女性對性慾與自我覺醒之關注。
作者:森鷗外
生於日本石見國(現島根縣),本名森林太郎,自幼即接受漢學、蘭學教育。後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後曾赴德留學,期間致力於醫學研究,但對文學、哲學、藝術皆有涉獵,尤愛歌德、叔本華、惠特曼,並曾譯介不少西方經典,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對其作品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間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醫學家,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並稱為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
早期作品包括〈舞姬〉、〈泡沫記〉、〈信使〉,為日本浪漫主義、美學思想先驅之代表三部曲;中期作品轉向寫實主義如〈青年〉、〈雁〉、〈灰燼〉;晚年則投入歷史小說創作如〈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魚玄機〉。
譯者:鄭清茂
1933年生,臺灣嘉義縣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歷任臺灣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麻州大學、東華大學等校教授,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為中日文學研究領域之知名學者,亦為國內重要的翻譯家,譯有日本古典文學、近代文學經典以及日本漢學著作多種,包括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小西甚一《日本文學史》,《平家物語》,松尾芭蕉《奧之細道》、《芭蕉俳文》、《芭蕉百句》,以及森鷗外《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澀江抽齋》等。
因致力於譯注日本經典文學,2014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
譯者序/鄭清茂
阿部一族
護持院原復仇記
山椒大夫
安井夫人
魚玄機
譯者序/鄭清茂
森鷗外(一八六二─一九二二)是日本近代重要的作家之一,與大約同代的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並稱二大文豪或文壇巨匠。兩人重要的類似點是:都屬於所謂「知性」的作家,都有留學外國的經驗,身為作家都自外於當時的文壇派系或文藝思潮,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派、白樺派等等,而獨立成家;雖不呼朋引類,卻均極受尊崇。
漱石的生平事蹟比較單純。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在高等學校教英文期間,官費留學英國,回國後在東京帝大等校講授英國文學,著有《文學論》《文學評論》等專書。這期間,偶而隨興在雜誌上隨興連載了《我是貓》(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大受歡迎、一舉成名。於是開始傾其全力於文學創作,發表了不少短、中、長篇小說。一九〇七年辭去大學教職,應《朝日新聞》之聘成為該報的專屬作家。果然不負所望,在與宿疾胃潰瘍纏鬥的餘生中,不但推出了一系列傳世的傑作,而且在創作小說之餘,也不忘隨筆小品的書寫,俳句、漢詩的吟詠與文人畫的揮毫,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許多重要小說已有不止一種漢譯本。漱石終其一生始終活躍在廣義的文學領域裡,是個純粹的在野文人或知識份子,附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堅拒政府送上門來的文學博士學位。
比起漱石來,森鷗外的學經歷就複雜多了。原名林太郎,號鷗外,別號牽舟生、腰辨當、歸休兵等,堂號千朵山房主人、觀潮樓主人。就像明治時代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鷗外從幼年起就接受漢學的教育。根據諸多鷗外年譜,鷗外從五歲開始背誦《論語》,七歲讀完《四書》後,開始誦讀《五經》,九歲起誦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十歲開始學習德文。在那學制年年在變而尚未定型的時代,鷗外十二歲就進入醫學校豫科。十五歲成為東京大學醫學部本科生。十八歲拜師學習漢詩作法。十九歲大學畢業後就被派到陸軍軍醫本部服務。二十二歲奉命留學德國四年,研究陸軍衛生學與醫療制度。二十九歲獲頒醫學博士。從此官運亨通,一直活躍於軍醫界。歷經陸軍軍醫教官、軍醫學校校長、軍醫總監等軍職,而至陸軍省醫務局長。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他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與日俄戰爭(一九〇四)期間,都以軍醫部長身分參與前線醫務。三十三歲(一八九五)甲午戰爭後,奉命自滿洲轉至台灣,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同年九月返日,回任陸軍軍醫學校校長之職。四十七歲(一九〇九)文學博士。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五十四歲,退出軍職,轉為文官,出任帝室博物館總掌兼圖書頭。五十七歲任帝國美術院長。六十七歲逝世,病症是腎臟萎縮兼肺結核。
鷗外的一生事業,在表面上,可以說幾乎都在軍事醫學衛生學的領域裡,而且在青壯年時代,除了認真奉行正式的職務之外,也譯介了不少與醫療衛生相關的西方論著,還包括克羅斯威茲(K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然而,儘管官大威大,鷗外在專業方面的貢獻並未受到普遍的瞭解與重視,有人甚至對他的一些醫學理論或主張還提出過負面的評價。其實,在日本早期全盤近代化的過稱中,鷗外在文學理論的倡導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已足以讓他史上留名,而在醫學領域的貢獻也就被人忽略或淡忘了。
森鷗外基本上繼承了江戶時代儒者文人的志節與趣味,加上西洋的科學實證精神;可謂上承傳統文化而致力於開啟西學洋務之風,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文明開化」運動的啟蒙旗手。儒家的文學觀常以「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主要價值。考較鷗外終生之所作所為,似不外乎這種價值的追求過程。或許可以說,這是他奉為圭臬的處世箴言。鷗外的文章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專家身分倡導推行西方醫學衛生學等洋務,對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屬於所謂經國之功、濟世之德;但在同時,他也不忘他所敬仰的江戶文人的文采風流,仕而優則文,業餘喜歡舞筆弄墨,不但在追求現代化的日本文壇上大放異彩,創作了許多重要的作品,贏得了當代大作家、大文豪的稱號;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能以文藝立言,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之名。
其實,鷗外的文學興趣早有跡象可尋。他在十二、三歲時,開始熟讀《古今和歌集》《唐詩選》等書,並試以漢文進行寫作。這些經驗養成了他後來喜歡吟詠和歌、新體詩,或偶而作漢詩的習慣。
鷗外於大學畢業、任職軍醫後,就玩起筆桿,向報紙投稿。留德回國後,更加積極。在廣義的文學領域裡,他介紹了多家西方的哲學、美學與文藝理論,翻譯了不少小說、詩歌、童話與戲劇等作品,終生幾乎未嘗間斷。比較重要的有哈爾特曼的《美學綱領》、安徒生的《即興詩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歌德的《浮士德》、王爾德《莎樂美》等,不勝枚舉。這些譯作對近代日本文學的發展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更重要或最重要的當然是鷗外的創作。他在二十八、九歲時發表了稍帶浪漫主義傾向的所謂留德三短篇〈舞姬〉〈泡沫記〉與〈信使〉,一舉成為文壇名家。其後,約有十六、七年期間,雖然繼續出了不少翻譯、文論、小品、詩歌或腳本等,卻久不見小說的創作。直到四十七歲(一九〇九)發表了被查禁的〈性生活〉(Vita Sexualis)後,聲威反而大震。接著寫了《青年》《雁》《灰燼》等長篇,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些作品完全揚棄了早年的浪漫色彩,轉而以他理性的旁觀態度與寫實手法,關注日本社會在急速近代化的漩渦中,殘留的封建觀念與習性、現代自我意識的抬頭與挫折、人生的希望與無奈等課題。這與當時夏目漱石的立場倒頗相似,只是表現手法有異;而與文壇主流,即帶有私小說傾向的日本自然主義,顯然大不相同。
然而,終於使森鷗外成為文壇巨擘的是他晚年的歷史文學創作。
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駕崩。九月十三日乃木希典大將殉死。鷗外感動之餘深受衝激,立刻寫了〈興津彌五衛門之遺書〉,發表於十月的《中央公論》上。這是他的第一篇以武士道為題材的歷史小說。這篇經過修改後,與〈阿部一族〉等收在翌年刊行的《意地》集中。「意地」是書題,並非篇名,而是概括集中各篇的共同主題或旨趣。日文的意地一詞,蓋指固執己見、意氣用事之意。武士有所謂武士道的道德倫理規範,而在其往往不合常情與人性的規範裡,堵注其生命的存在意義。這種賭注包括個人的生死,甚至一家一族的存亡絕續。所爭的無非是存在的尊嚴。換句話說,就是面子攸關的問題。
鷗外在〈阿部一族〉之後,接著在同年十月,發表了〈護持院原復仇記〉。此後兩年之內,陸續發表了〈大鹽平八郎〉〈堺事件〉〈安井夫人〉〈栗山大膳〉〈山椒大夫〉〈魚玄機〉等中短篇。論者以為在這些作品中,都還潛伏著「意地」的意識暗流。此後,從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五十四歲起,在三年內,完成了以幕府末期的儒醫儒者為題材的長篇:《澀江抽齋》《伊澤蘭軒》《北條霞亭》三部傳記。這些晚年的作品,一般也都廣義地歸為歷史小說,但就文類的形式而言,說是歷史不像歷史,說是傳記不像傳記,說是小說不像小說。作者「我」頻繁出現在敘述過程當中,好像帶領著讀者步步尋找歷史或故事的真實。這是依據公私文獻史料、經過實地訪談查詢,再加考證、分析、整理之後,以「我」的觀點撰成的作品。可說是鷗外自創的文藝形式,類似當今時行的調查報導文學而不失其最重要的文藝本質。日本文學史上或稱之為「史傳」小說。這些史傳小說代表了鷗外文學的最高峰。
阿部一族
寬永十八年辛巳春,從四位下左近衛少將兼越中守細川忠利,不顧領地肥後國比別處早開的櫻花,身為五十四萬石大名,在昂揚的陣仗前後簇擁下,即將緊跟春天由南向北的步伐,前往江戶參勤供職,不料動身之際竟罹重病;侍醫方劑不能奏其效,病情日益惡化。飛腳立刻飛奔江戶,禀報延後參勤的訊息。當時的德川將軍是有賢君之譽的第三代家光,擔心這位在島原農民暴動中,擊敗賊將天草四郎時貞而立下大功的忠利的境況,乃於三月二十日,著由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阿部對馬守三位執政,聯名草擬慰問書翰;又派了名叫以策的鍼醫,從京都南下九州。繼之於二十二日,命武士曾我又左衛門為上使,遞送執政三人署名的慰問信函。將軍家對待一個大名,居然如此鄭重,可算無以復加了。自寬永十五年春天,島原之亂敉平之後,三年以來,將軍家不斷盡其慇懃,或追贈江戶藩邸苑地,或賜以所獵仙鶴,不一而足。何況此次聽說是重病,在有先例可循的範圍之內加以慰問,自是情至義盡、理所當然。
其實,當將軍家還在忙於安排探病事宜時,在熊本花畑的館邸裡,忠利的病情急速惡化,早於三月十七日申時亡故了,享年五十六。夫人是小笠原兵部大輔秀政的女兒,是以將軍的養女身分嫁給忠利的。今年四十五歲,名叫阿千。嫡子六丸在六年前元服時,蒙將軍家賜予光字,因而取名光貞,受封四位下侍從兼肥後守。今年十七歲。正在江戶參勤途中,已來到遠江國濱松,但接到訃訊後,立刻折返肥後。光貞後來改名光尚。次男鶴千代從小便被送到立田山泰勝寺,成為出身京都妙心寺的大淵和尚的弟子,法號宗玄。三男松之助為與細川家有親緣的長岡家所收養。四男勝千代成為家臣南條大膳的養子。女兒有兩個:長女藤姬成為松平周防守忠弘的夫人;次女竹姬後來變成了有吉賴母英長的妻室。忠利是細川三齋的三男,下面有三個弟弟:四男中務大輔立孝、五男刑部興孝、六男長岡式部寄之。妹妹有嫁給稻葉一通的多羅姬,還有嫁給烏丸中納言的萬姬。這個萬姬所生的禰禰姬變成了忠利嫡子光尚的夫人。長輩有姓長岡氏的兩位哥哥,還有姊姊二人,分別嫁入前野家與長岡家。早已隱退的三齋宗立仍然在世,今年七十九歲。這些家屬之中,有人像嫡子光貞那樣經常輪班住在江戶,也有人住在京都或其他更遠的地方。在外地接到訃聞後,當然不免悲歎;但身在熊本別邸當場的人,他們的哀傷,無疑更加悲切。向江戶藩邸的緊急報告,派了六島少吉與津田六左衛門二人,馬上動身上路。
三月二十四日有初七的儀式。四月二十八日,撬開館第起居室的地板,搬出藏在下面的棺木,遵從江戶的指示,把遺體移到飽田郡春日村岫雲院火化,然後葬在高麗門外的山上。過了一年後的冬天,在山上宗廟下方加蓋護國山妙解寺,從江戶品川東海寺,請來澤庵和尚的同門啟室和尚為住持。等到啟室在寺內臨流庵隱居之後,由忠利次男而出家的宗玄繼任,號天岸和尚。忠利的法號是利妙解院殿臺雲宗伍大居士。
火化的地方之所以選在岫雲院,是依從了忠利的遺囑。有一次忠利出外打水鳥,曾在岫雲院休息飲茶時,無意中發覺自己的鬍鬚長長了,便問住持有沒有剃刀。住持立即用盆子打了水,附帶一把剃刀,端了出來。忠利心情大好,邊讓小侍童刮著鬍子,邊問住持說:「怎麼樣,大概用這把剃刀剃了不少死人的頭吧?」住持不知如何回答,相當尷尬。從此以後,忠利與住持變成了摯友,所以才決定在岫雲院舉行火化。正在火化當中,在伴隨靈柩而來的家臣人堆裡,聽到有人忽然驚叫:「哎呀,有鷹、有鷹。」原來在淺灰色的低空下,寺苑內圓形石砌井垣周圍的杉林中,一棵已長嫩葉而下垂如傘狀的櫻樹上面,有兩隻蒼鷹繞著圈圈飛來飛去。而在人人嘖嘖稱奇之際,兩隻蒼鷹一前一後、尾喙相連,倏然落了下來,落入櫻樹下面的古井裡。這時,從原來在寺門前為某事爭辯不休的五六人中,衝出了兩個男子漢,直奔井邊,伏在石砌井欄上,凝視井中的情景。那時蒼鷹已經沈沒水底;從井壁叢生的鳳尾草間所能看到的水面,已恢復了原先的平靜。這兩個男人是馴鷹師。自投井底而死的兩隻蒼鷹是忠利所珍愛的有明與明石。當真相傳開後,可以聽到人人的竊竊私語:「那麼,連獵鷹都以身殉主了嗎?」
其實自主君逝世之後,到了前天,殉死的家臣已有十幾個人。其中前天有八人同時切腹,昨日又有一人。眾家臣之中,沒有一人不在考慮殉死的問題。雖然不知道那兩隻蒼鷹,如何乘隙逃離了馴鷹師的手臂,又如何追著無形的獵物似的飛入了井底,卻沒有一人有心去追究個中原因。獵鷹是主公的寵物,竟在火化當日,而且竟在火化之地的岫雲院,衝入井中而死;只要看到這些事實,便足以判斷獵鷹是殉死無疑。根本沒有置疑而另尋其他原因的餘地。
中陰四十九日,於五月五日結束。在這期間,除了宗玄之外,有既西堂、金兩堂、天授庵、聽松院、不二庵等幾位僧侶,也都趕來誦經念佛。且說,雖然五月六日都過了,但殉死的事件卻仍然時有所聞。殉死者本人及其兄弟妻小自不用說,連有些非親非故的外人,如接待京都鍼醫或江戶上使的人員,也忘記了自己重要的工作,心不在焉,腦子裡只管想著殉死的事。忘記了每年端午要折來插在簷前的菖蒲;還有把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初次升鯉旗慶祝的喜事,也彷彿忘得一乾二淨,家裡反而靜悄悄的,無聲無息。
所謂殉死,無關始於何時與如何,可說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規矩。任何人不能因為敬重主公而感恩戴德,便可隨心所願,自決主動殉死。可比太平盛世的江戶參勤扈從,萬一碰到戰爭時,自願跟隨主公同赴疆場,相伴到黃泉冥途,也非得獲得許可不可。沒有許可而殉死等於白死。武士最在乎的是世人的觀感,所以不肯死得不明不白。衝鋒陷陣、奮戰而死,固然值得欽佩;但若違背軍令,搶先赴敵而亡,便不算立功,等於白死。同樣,未經許可的殉死也是白死。不過,偶然也有這樣的人而不至於白死的,是因為君臣之間有知遇之感而互有默契,所以有許可或沒有許可也便無所謂了。佛祖涅槃之後興起的大乘之教,並沒有佛祖的許可,但對前今來三世無所不知的佛祖,已經預知會有這樣的教派出現了。沒有許可而敢於殉死,好像聽到了如來金口說法,宣示大乘之教將會來臨一般。
那麼,怎樣才能獲得許可?這次在殉死的人們之中,譬如內藤長十郎元續的請願手段是很好的例子。長十郎平時在忠利的書几旁勤務,格外受寵;一直留在忠利的病床邊,細心看顧。當忠利覺得自己康復無望時,囑咐長十郎說:「一到臨終時,請把寫著不二兩個大字的掛軸掛在枕頭邊。」三月十七日病情轉劇,忠利說:「把那幅掛軸掛起來。」長十郎遵囑掛上。忠利看了一下,暫時閉上了眼。過了片刻,忠利說:「腿好酸。」長十郎緩緩捲起睡衣的下襬,一邊揉著忠利的腿,一邊凝視著忠利的臉。忠利也回瞥了一眼。
「長十郎有個請求。」
「所求何事?」
「貴體違和,看似危篤。然而,在神佛加護、良藥功效下,虔誠祈禱早日完全康復。當然不免也有萬一。如果一旦有事,請吩咐長十郎我這個下人,永遠隨從左右吧。」
長十郎說著說著,輕輕擡起忠利的小腿,俯首貼在自己的額上。眼眶裡滿是淚水,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