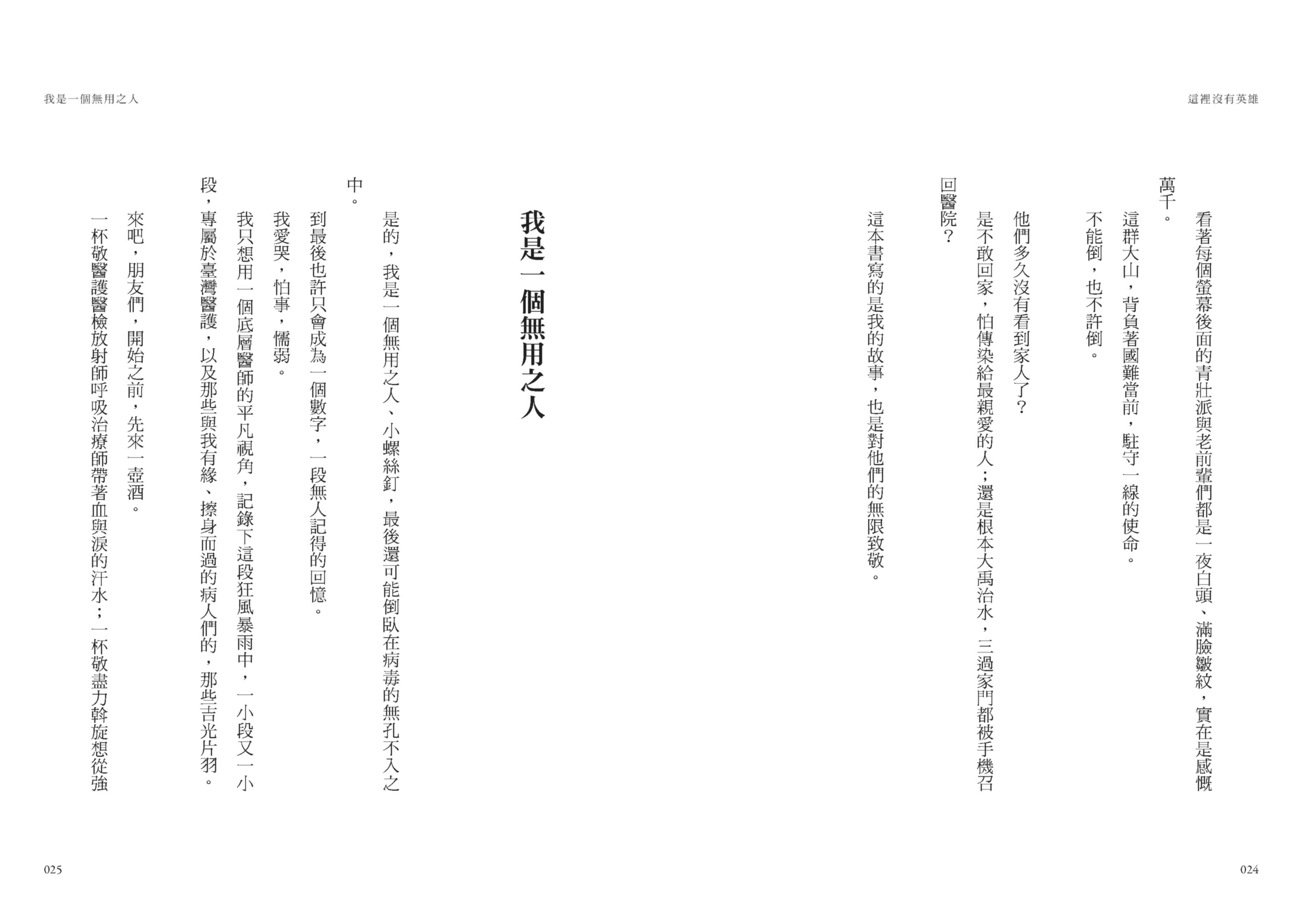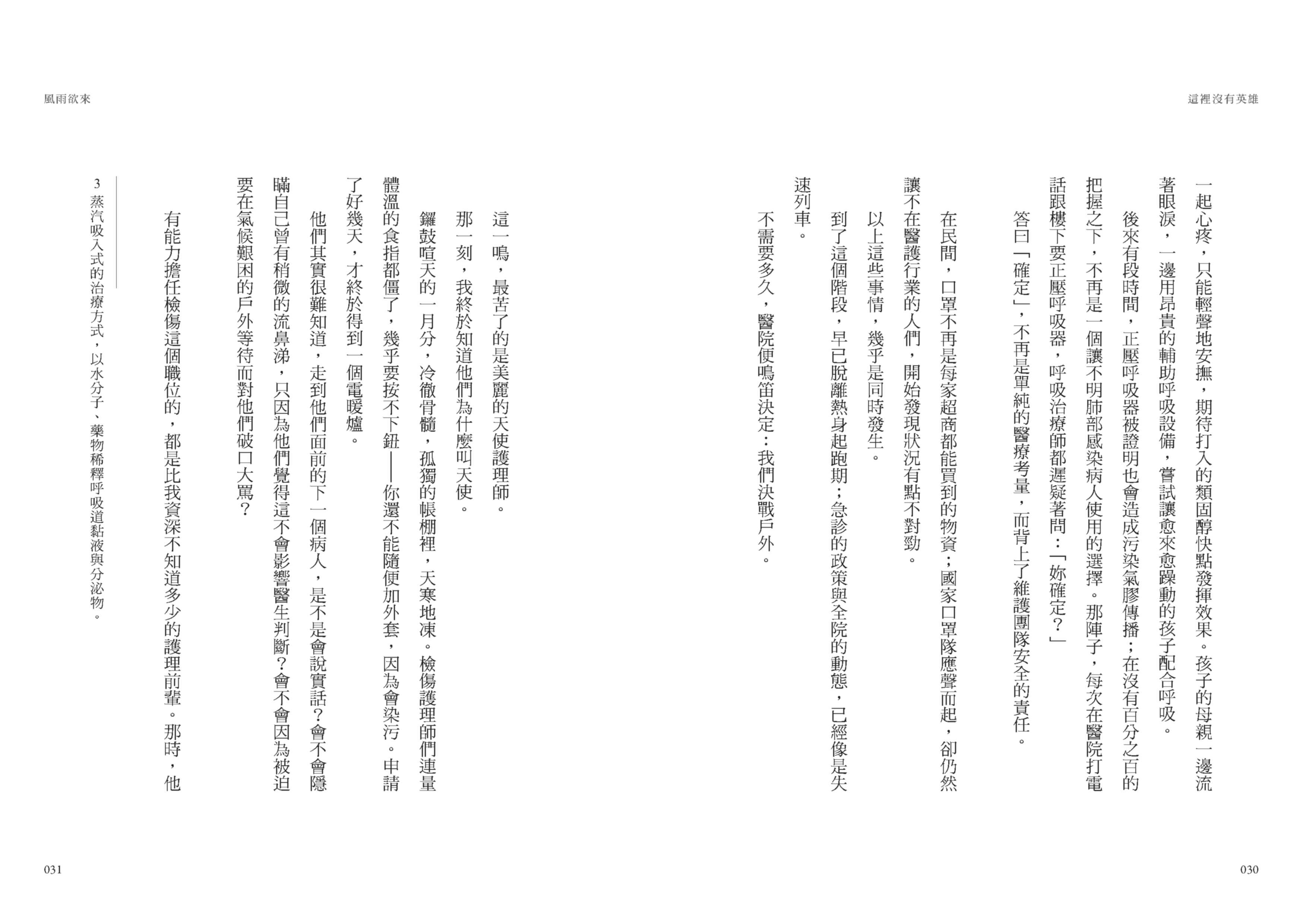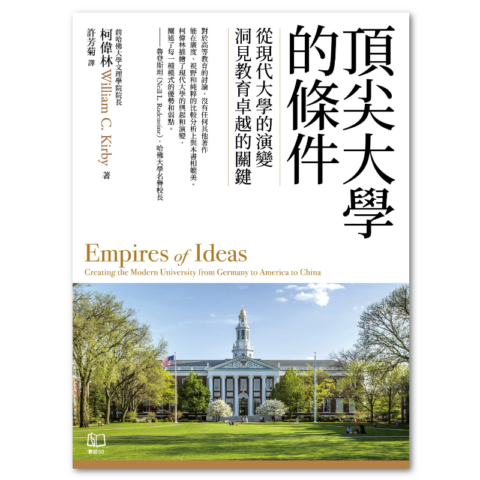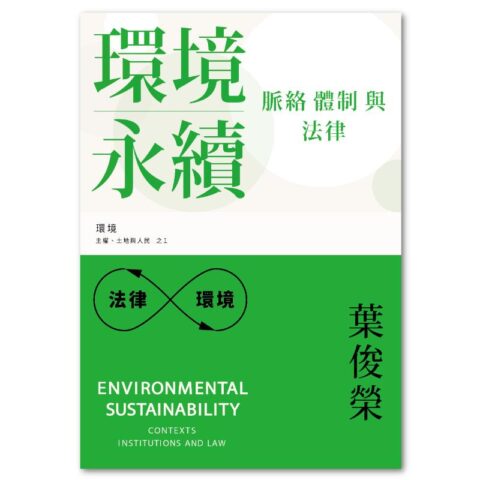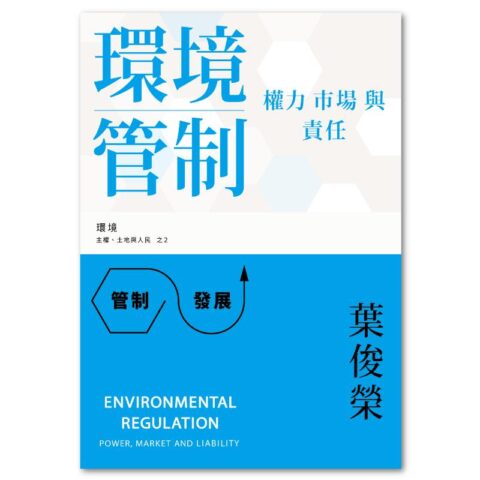這裡沒有英雄:急診室醫師的COVID-19一線戰記
出版日期:2021-07-22
作者:胖鳥
印刷:前8彩+內文黑白
裝訂:平裝
頁數:296
開數:25開,21長*14.8寬*高2cm
EAN:9789570859287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每售出一本《這裡沒有英雄》,聯經出版捐出10元予臺灣 COVID-19防疫工作專款使用。
這是一首急診之詩,一曲醫療前線醫師之歌。
他們憤怒、憂傷、焦躁,卻始終緊握希望的螢光,
在無數次絕望中,浴火重生。
暴起的疫情是猛獸,它無形、無體、無心,而人要面對的,是它徹底的無情。
在醫療現場,沒有神與英雄,只有與死亡對抗的人。
胖鳥:
我是一個無用之人、小螺絲釘,最後還可能倒臥在病毒的無孔不入之中。我愛哭,怕事、懦弱。我只想用一個底層醫師的平凡視角,記錄下這段狂風暴雨中,一小段又一小段,專屬於臺灣醫護,以及那些與我有緣、擦身而過的病人們,那些吉光片羽。
這本書的所有文字,來自一位醫療前線急診科醫師的心。
當疫情襲來,醫生這個職業擋在第一線,承受的壓力、面對的風險、目睹與經歷的一切,讓急診科醫師胖鳥醫師不由得問道:「什麼時候,助人救人,成了一種禍?」而她書寫,以底層醫師的平凡視角,記錄了2021年COVID-19疫情暴起期間,那些專屬於臺灣醫護的吉光片羽。
2020年,臺灣以控制COVID-19疫情得宜而驕傲。一切看來如此平靜,國外的疫苗研發、死亡人數多寡似乎逐漸與我們無關。我們像置身現代烏托邦,而誰也沒料到,烏托邦衰頹得如此迅速。2021年4月20日,爆發華航機師案;5月11日,臺灣正式進入社區感染階段;12日,防疫警戒升至第二級;19日,防疫警戒升至第三級。
本土感染病例日日增多,病毒不只在雙北大量複製,它還搭飛機、搭車南下北上、跨越中央山脈,與所有人錯肩而過。停課了、分流上班了、沒班可上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下午兩點的記者會再開,醫療體系很快要超負荷。
甚囂塵上的謠言與猜疑,還有動搖的人心,一切只彰顯著一件事:人實在太弱小了。
我們如此弱小,因而期望在這個大疫年代有英雄,最好一句話就讓病毒消失;我們也期望在死神敲門的時候有特效藥,最好一針藥到病除。責任沉重地導倒向醫護人員,我們期待他們能像傳說裡的英雄一樣,不眠不休、不知疲勞地拯救世人。然而,駐守急診室的胖鳥醫師說:「醫療現場裡,沒有英雄。」
她筆下場景切換快速的急診室裡,在驚人的高壓處境、緊迫的氛圍中,沒有誰是英雄、沒有人想當什麼英雄,所有人都是重要戰將──正因人脆弱、正因我們在病毒面前能力如此有限,所以我們強大。
我們強大,是為了要保護每一個心愛的人。
胖鳥醫師像我們,會害怕、崩潰、哭泣、絕望,柔軟而堅強;會自我質疑、自我責備,會陷入深深的絕望。
她的心和我們一樣,守護著所愛、盼望著希望。
在這個沒有英雄的戰場裡,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和站在急診室裡的胖鳥醫生,以及所有堅守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一起,在黑夜中,緊緊守護著微微顫動、飄忽不定的螢光。
各界推薦
田知學(急診醫師)
呂立(臺大醫院小兒胸腔加護醫學科醫師)
林靜儀(立法委員)
阿潑(文字工作者)
馬漢平(雙和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
陳建仁(中研院院士/前副總統)
──感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胖鳥
貨真價實的急診科醫師。雖然每天起床也對三商(情商、智商、逆境商數)皆無的自己敢選這行很是震驚,但目前還沒有辭職的打算。
想法古怪,行事大多靠直覺;少年時曾拿過不少重要文學獎項,但已不再能提當年勇。
唯願在奔騰變動的世界裡,以一枝筆,寫下我所愛的人,我所不願忘記的事,以及希望傳達給愈多人愈好的廣闊與勇氣。
前言
序章
我是一個無用之人
風雨欲來
兩個世代,跨越十七年的烽火
不一樣的春節
天要塌了
吹哨人死在了路上
我很想抱抱那隻跳跳虎
還有好多的遺憾,還有好多未完成的事
愈是危險,就愈是要站直了
平行世界裡的淚水
暗潮
請別封院
什麼時候會完結?
美麗的泡泡
我喝水吼,會有點澀澀的
疫情將襲急診知
噩夢之始
「我們對面病房關了,我今天不回家。」
在一線上,我們並不孤單
不能不打的疫苗
一線戰場
那家人確診了
寂靜的臺北城
如果我犧牲了怎麼辦?
最恐懼的時刻
我痛恨自己的渺小
三級警戒
一路好走,沒有疼痛
這裡,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準備戶外插管!
我覺得我死定了
醫生,妳/你覺得呢?
我心目中的真英雄
一點五公尺的思念
我只想變得跟你們一樣勇敢
在戰壕裡瀕臨昏厥
小天使
援軍到底在哪裡?
希望這輩子,我們都不要再看到這樣子的急診
先生,爸爸這個,是新冠肺炎
一點也不快樂的快樂缺氧
戴護目鏡時,你不能哭
妳為什麼坐在這裡?
一點寬容,一點體諒,一點愛
連顧死人的職業也不安全了
OHCA!OHCA請準備!
唯一還有一點價值的事
只有你們的燈是亮著的
生殺予奪的滋味
困在自己的心靈裡面
你有要跟他說說話嗎?
無名的女孩
暴雨來襲
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
沒有盡頭的試煉
誰都有可能是病毒的下一個受害者
他身上有刀!
身在其中的人,身在其外的人
同理心
我害怕太多的人性
有口難辯的結局
一線的戰士們
鴻毛與泰山
充滿希望的世界盡頭
後記
前言(節錄)
感謝翻開這本書的你。
考量到你可能從未認識過我,而這本書前折口的個人簡介也寫得半吞半吐,因此在這裡先做個自我介紹。(也就是幫自己偷偷拉個好感度的時機。也可能反效果。不過,這就是最真實的我。)
我的父親與親姊都是醫師,我也是。
與他們不同,我並不是兢兢業業、朝五晚九、傳統風骨的醫師類型。我的思想如脫韁野馬,不按牌理出牌,並且多少對體制與監督有些漠不關心。
因此,當我從座落臺北的某間醫學大學(在此匿名,以免危害校譽),以吊車尾的名次與剛剛好達標的出席率過關之後,老爸與老姊都鬆了口氣,不再揮動欲把我趕出宗祠的掃把。
但別擔心,如果你我真的有緣在醫院相見,請記得,我當年是連續以「best intern」(最佳實習醫師)與「best PGY」(最佳一般科醫師)身分,從實習期結業的。
怎麼達成的呢?
全靠我莽撞的運氣,以及一批對我非常嚴格的老師。
這些人,堪稱術德兼備。
你在醫學會議、論文以及新聞上,可能已經看過好多次這些醫界骨幹。他們也會多次出現在這本書裡。
結束實習,就來到醫師重要的命運交叉道—選科的時候。
還是醫學生的時候,我曾經在小組討論課上,遇見一位時為急診科主任的馬漢平醫師。當時我對他描述的急診對病人的宏觀全局、急診科醫師的衝鋒陷陣心生嚮往,夢想的種子也就此於心中萌發。遇見馬老師時,我才大三,從那時起直到選科,歷經整整六年,而我始終沒有遺忘走急診的夢想。我只怕自己不夠格,不足以在一線血鬥死神。
後來,不知道哪個好前輩半哄半騙地跟我說:「唉呀來急診啦,急診都不需要念書啊!」
結果,我進急診的第一天,就在師父一陣狗血淋頭的痛罵中,明白了那個不具名的前輩,肯定只是想把我騙進急診室打工。
急診是個瘋狂、充滿變數、永遠在嘗試新鮮玩意兒的行業。
考驗生理時鐘,考驗臨機應變,考驗智商與情商。
而且,急診常是團體作戰模式;這對非常不擅長經營人際關係的我,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頭兩年,我時常想當逃兵,卻無法抗拒急診的吸引力。例如:每道血流如注的傷口被縫起來的時候;每個謎案被迅速破解的時候;看到中毒病人因為選對解藥瞬間好起來的時候;學到一項新奇技藝的時候。
雖然常常脫去白袍準備回家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但是,還是有那麼一些些、很少很少的瞬間,我會感覺自己的存在,好像讓世界,好了這麼一點點。
於是,我就好像還能再撐個一兩天。
如果世界照常,我想我會在風平浪靜中,慢慢的、調適好自己,一直走到結業,一直到成為一個稱職的主治醫師。
然而,就在我的訓練堪堪走到一半時,瘟疫爆發了。
……這本書裡的故事,為了顧全隱私、不去揭人傷疤,時序、性別與年齡,皆做了改動。出場的角色們,也會以代號處理,但容我保證,這些故事就在你我身邊,真實上演。
之所以寫下這本書,是因為想在歷史洪流之中,記錄下這宛若浩劫的日子。
唯有被人遺忘,才是真正的失去希望。
我不想忘記犧牲的人、流下的血、擦不完的汗,與也許一輩子都止不住的淚,也想告訴大家,當你們喊著「醫護加油」的時候,我們相應做出了哪些努力。
你有要跟他說說話嗎?
這天,來的是個有點喘,胖胖的老先生。
EMT(緊急救護技術員)弟兄推輪椅送他,說倒在路邊,被報案送來。
老先生說,他喘。
我低頭,看到他赤著腳,腳上都是磨破的口子,還起了厚厚的繭。
問他住哪裡?說就在橋過去。家裡都有誰?兩個室友。
我頓時明白了他的人生故事。他大概就是辛苦一輩子,「做工的人」。他所說的「橋過去、有兩個室友」,我大概就能猜到那是為了安置弱勢、政府設的、冬冷夏熱的鐵皮屋,勉強讓他們有個安身之處。
他有點噸位,而且全身沒剩什麼力氣了。我用盡全力把他抱到床上,替他安上氧氣鼻管,氣喘吁吁地說:「老先生,你找家人來,好不好?」
他說好。拿出手機,一直按跟他名字很相似的通訊錄號碼,一直撥一直撥,都沒有回應。
「阿伯,你這麼喘,等一下要插管,願不願意?」
他一點都沒考慮,直接回答:「不願意。」
「阿伯,你知道插管是什麼嗎?是要急救。你不插管,可能等一下就走了喔!」
「走了,就走了。」阿伯說。
我沒敢再跟他說話,因為他沒力氣了;連這麼簡單的話,都說得斷斷續續。
他全身上下就幾塊錢,一張健保卡,一張轉診單,一支手機。死死的攢著。
我將他所有的家當塞入他的西裝褲口袋,將褲袋拉鏈封起來,抓著他的手去摸,讓他感覺得到卡片與手機的形狀。
「阿伯!我怕你東西掉,現在都在這邊喔!好不好?」
他握了握我的手,安心地點了點頭。
「我再幫你找家屬,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他已經沒力氣回答我了。頭歪向一邊,似睡非睡地闔上眼睛。
過了幾個小時,報告出來了。
不出所料,是新冠肺炎,而且又是肺臟白成了雪花的那種。
每次閉上眼睛,我都覺得這些X光在嘲笑我。
這群阿伯,象徵著臺北一群無聲無息、容易被遺忘的人口。他們生活的地方擁擠狹小,衛教資訊難以傳遞,更不知道有沒有錢可以替換口罩。首先被新冠肺炎帶走的,一大半就是這批辛苦半生,臨到頭來還不能享清福的苦命人。
我嘆了口氣,準備去跟阿伯解釋,卻意外地看到,家屬居然來了。而且這個家屬衣著嶄新,鬢角修飾得十分乾淨,上衣的標誌顯示著Ralph Lauren。
「現在情況怎樣?」
「情況不好。您是他的……」
「算弟弟吧,不同媽。」他說。
「他有別的家人嗎?」
「沒有。我有結婚啊,他沒有,他自己住。住哪我不曉得。不過我住內湖瑞光路那一段啦!」
他的語氣帶著驕傲,給的資訊卻幾乎沒一條是我需要的。
金邊眼鏡後面的眼睛充滿優越感,仿佛寫著:我與哥哥可不是同路人。
「嗯,他是新冠肺炎。就是最近電視上很紅的那個。他接下來情況可能不是很樂觀,我們有談過了,他說碰到緊急狀況,不要急救,按照規定,我們還是得與家屬講明白情形……」
話還沒說完,他粗魯地打斷:「聽他自己的意思吧。新冠肺炎傳染率是不是很高?」
「非常高。」
「那妳還有需要我做什麼事情嗎?」
我發誓,我已經看到他擦得亮黑的皮鞋,在往門口移動了。
我的聲音也變得稍微森冷。
「你有要跟他說說話嗎?」
「剛剛說過了。」
「那沒事了。」我轉身掀開簾子,看到阿伯仍在半睡半醒的狀況,呼吸並不費力,但血氧是真的在往下掉。
我嘆了口氣。讓阿伯這樣靜靜地睡去,也好。
不過,我還是真心擔心他那兩個室友。
不知道疫調人員,來不來得及找到他們呢?
這裡,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第二階段愈演愈烈,從救護車上下來的病人,也愈來愈接近生死關口。
壓力愈來愈沉,我的脾氣也愈來愈暴躁。
血性被激發起來,偶爾,也會想打一下那注定贏不了的仗。
那天,太過年輕的我,與負責監督我的主治醫師拍桌子對吼。
「您就這樣把病人送到專責病房,上面人手這麼不足,不一定會照顧啊!不插管,您難道要讓她現在就死在我面前嗎?」
主治醫師一摔手機,帶著滿腔的狂怒指著我的鼻子—這是一向溫和的他第一次這樣對我說話──「妳現在插管,她上去一樣死在病房裡!腦子清楚一點!」
我氣得換氣過度。還想再爭,微微轉頭,卻看到了資深護理師的眼神。
帶著悲憫,帶著溫柔與安撫。
年輕護理師則被診間忽然上升的火氣驚得退到了牆角。
我一下安靜下來。
這裡,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我與主治醫師差了三十年的年資,也就是說,我們之間差了至少經手幾十萬個病例的經驗。
病人幾乎沒剩下多少肺容積的X光片,糖尿病、抽菸、慢性肺病長期沒有控制的病史,免疫太差的高齡,實證文獻上那插了呼吸器後低得讓人想哭的存活率。
我又豈不知道病人有多少機會?但是當年的醫療教育只教我無論如何拚一口氣,卻沒有教我讓病人在如此狼籍的情況下,放她舒舒服服地撒手人寰。
我頹然坐下來,迴避了老闆與護理師的眼神。
老闆也不再說話,繼續忙著聯絡專責病床。
我看著肺部X光片,那一個一個的小洞,猙獰地瞪著我。
它們好像在貪婪地說:給我吧,給我吧,她的靈魂我要收走了。
「我。」我低聲說,「去請家屬,與婆婆講講話吧。」
沒人回應。
在臺灣傳統裡,不讓家屬見親人一面就匆匆火化,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但是,讓家屬進到急診室裡道別,其實存在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感染控制風險。
病人家屬必須從熱區穿越暖區再進入熱區,交叉感染,很容易增加病毒傳播鏈。
但醫學豈能不講人情?
我這麼軟弱的人,又豈能阻止與生俱來的血水呼喚?
剎那間,我想起了喪屍片裡,那個站在崗哨上拿著衝鋒槍,接到了「不得讓任何人通過此線」命令的軍人。
有個稚齡孩童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哭著求他,我餓了,我沒病,讓我過去吧。
軍人將槍口抬高了一公分。
防線就此崩塌。人類出現浩劫。
最後的折衷,是我把開著視訊的手機拿給病床上的老太太。
她重聽。通話的雙方不過講幾句話都要重複好多遍,她更是說幾句話就得緩一緩氣。
我坐在急救室外的椅子上等著回收手機,木然地聽著他們家長里短的對話:
市場有沒有開?
孫女喜歡吃的蒿菜還買不買得到啊?
你爹是不是還咳嗽啊?
藥在哪裡知不知道啊?什麼?不在櫃子上?我回家就拿給你啦!
我想,老太太不知道她快死了。
我多麼希望,死神忘了在名單上寫下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