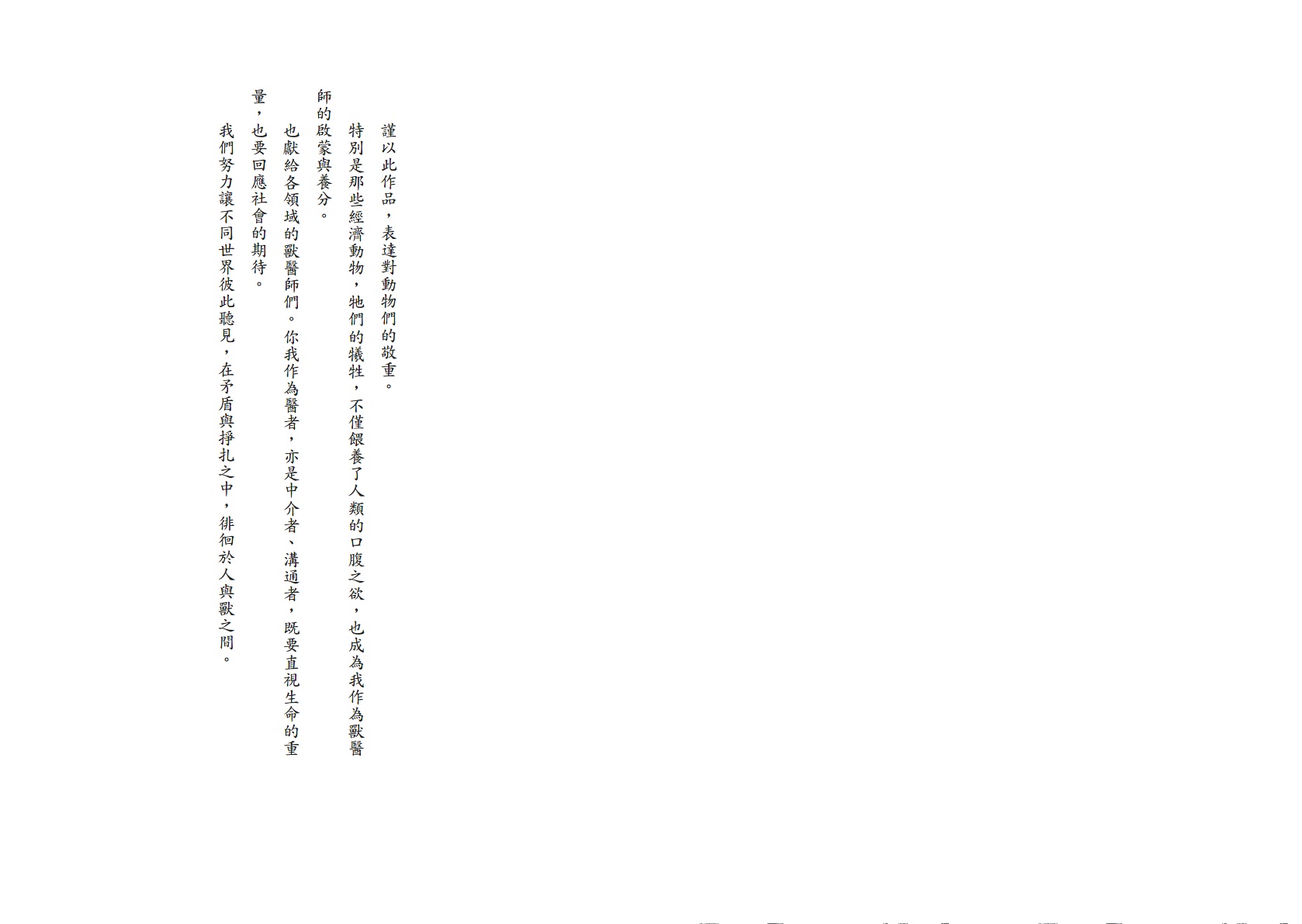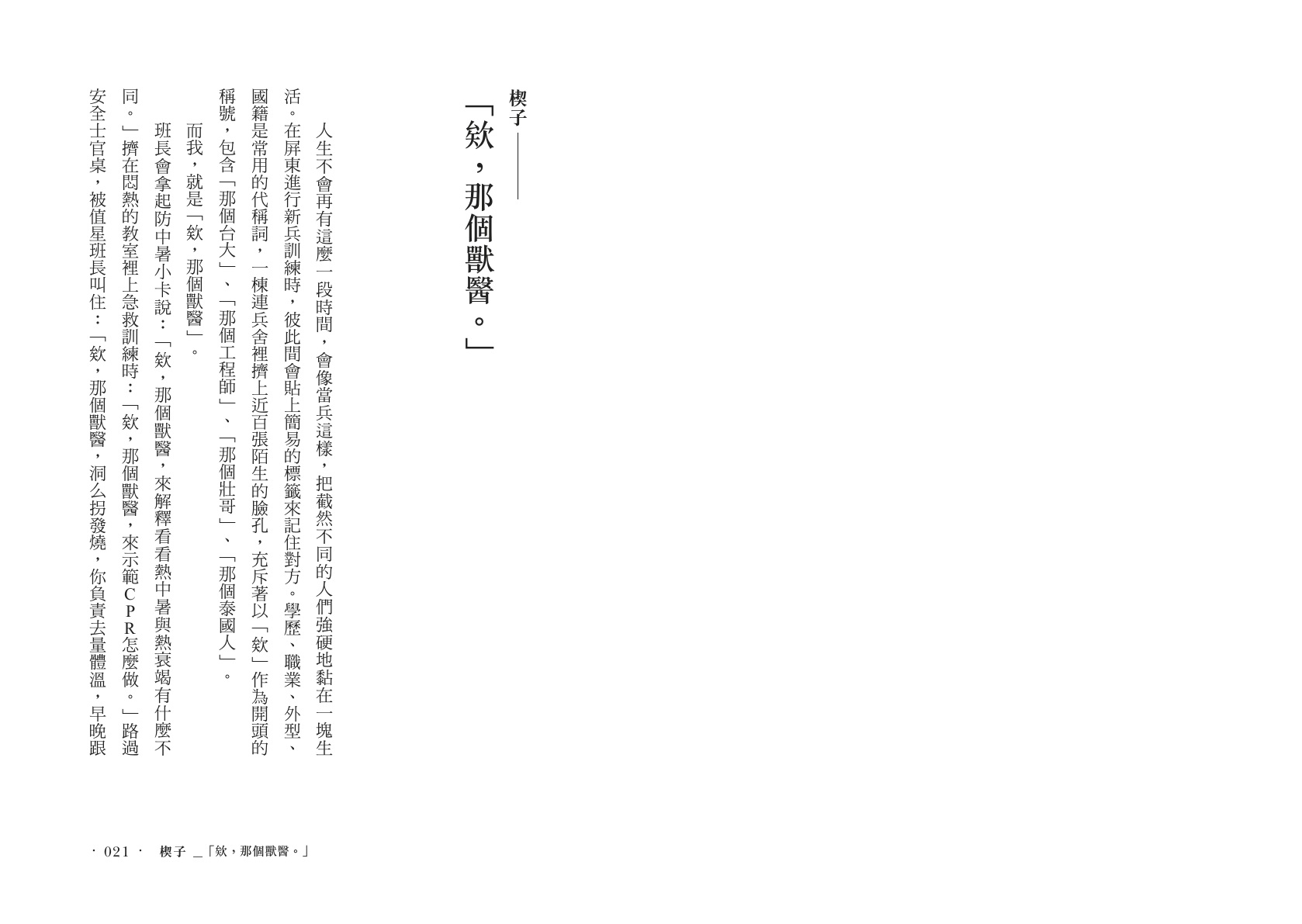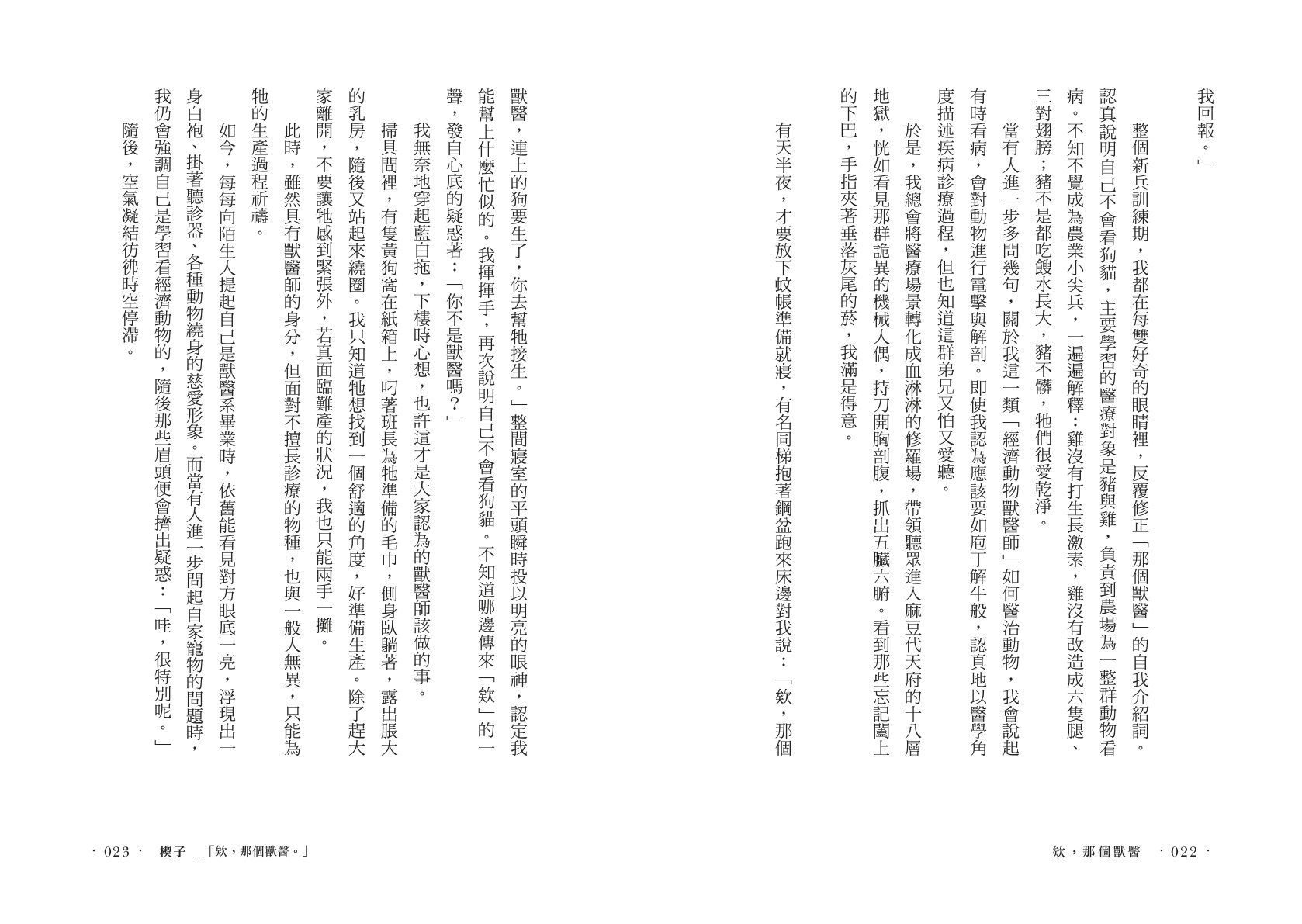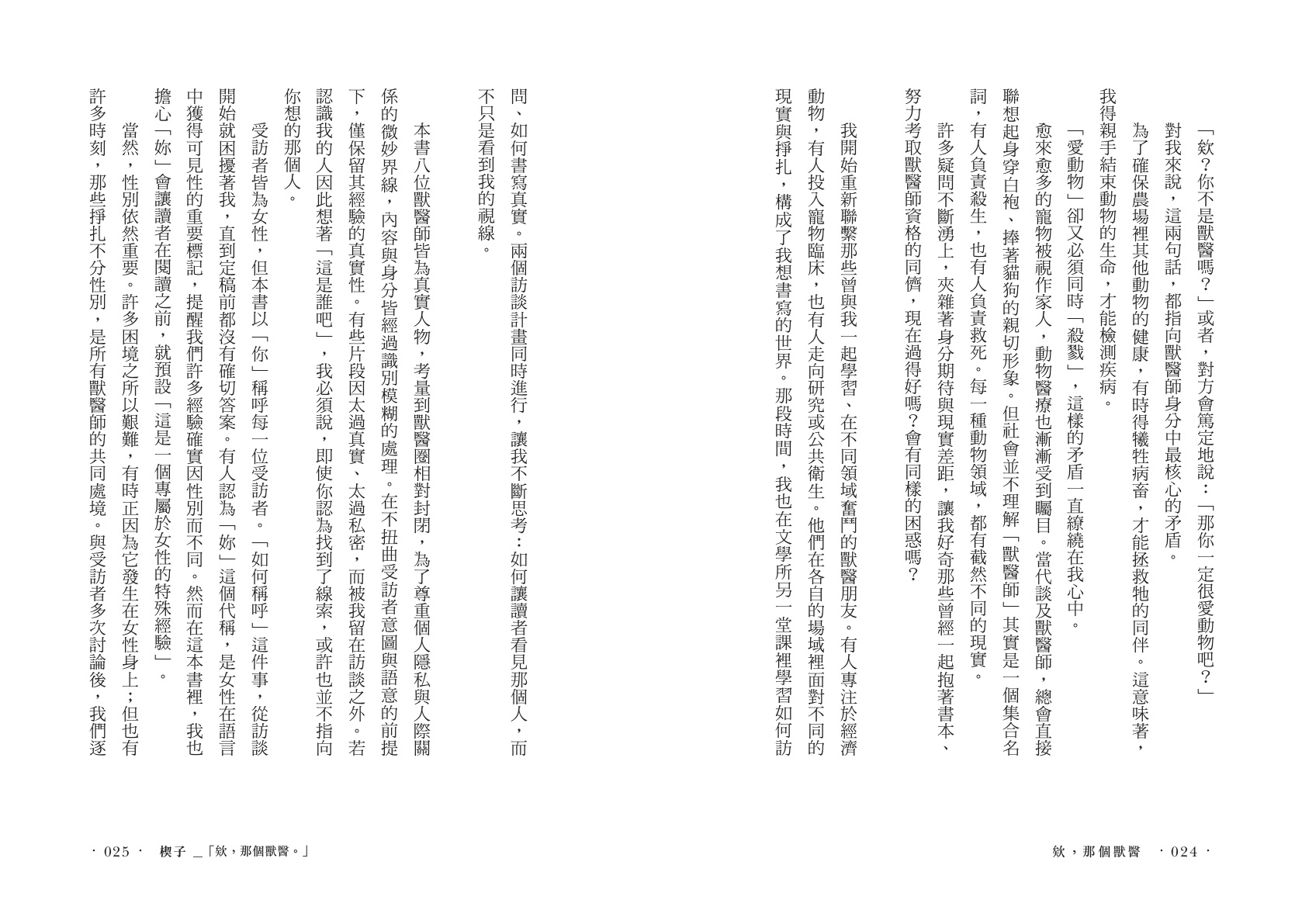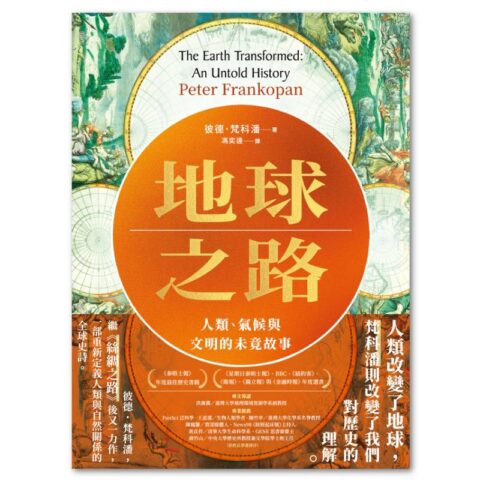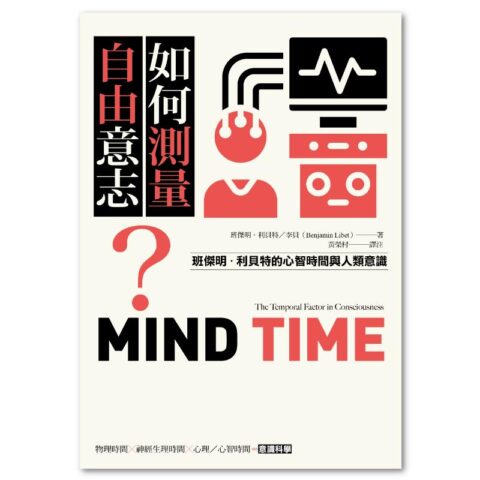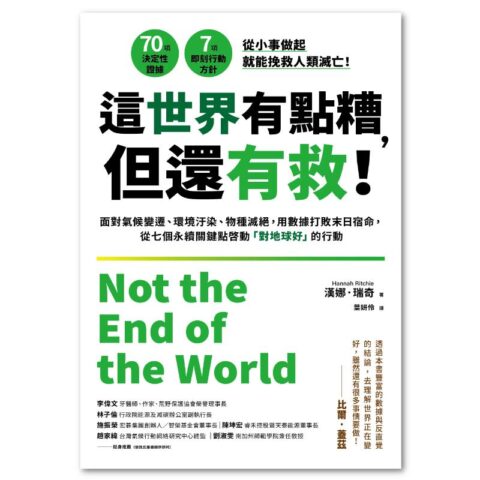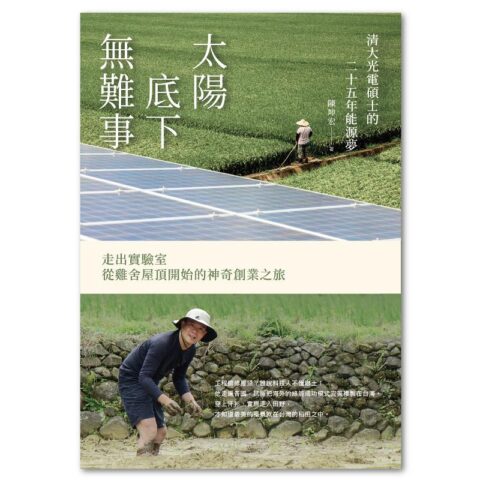欸,那個獸醫
出版日期:2026-01-22
作者:曾達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12
開數:25開,14.8長 × 21寬 × 1.65高cm
EAN:9789570879124
系列:眾聲
尚有庫存
行走於溫暖與痛,愛與犧牲之間,
前所未見,獸醫師這群人的故事。
── 一名經濟動物獸醫師眼中的世界 ──
在生命與生命,活著與死亡之間,
我們前行、前行、前行……
最普通的獸醫師,最真實的紀錄
這本書裡沒有奇珍異獸,沒有爆笑動物故事,有的是一群與獸同行、依獸而生,努力過生活的獸醫師。
作者曾達元是一名經濟動物獸醫師,以與同業、友人的談話為基礎,書寫他們在獸醫領域一路走來的顛簸、掙扎與辛苦。書中每個章節背後都有一個實際受訪者,除了大眾熟悉的犬貓動物診所,他們也在豬場與雞場出沒,在屠宰場工作,在檢疫所上班,更常常需要跑業務、和顧客周旋。他們好似以身體為媒介,以職業作引線,身體力行地在溫暖的毛皮,在一個又一個小生命間隙,見證人類和動物既親密又殘暴的現實關係。
人與獸,之間
動物無法言語,而獸醫師是最能聽懂牠們的專業人士。然而獸醫師從來不只在拯救動物而已,除了治療、防疫,專業訓練也讓他們理性、科學地面對死亡,在必要時採取人道處置、汰除個體。他們常拿起屠刀,對動物握有權力,卻又無能為力。
當經濟需求與情感相互撕扯,當治療挽不回逝去的生命,當理應呵護動物的飼主出現道德問題,獸醫師會困惑、傷心、會痛,也會絕望。他們和任何醫者一樣,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是有血肉之軀的人,在臨生面死的試煉中,選擇繼續前行。
沒有英雄的故事
這群獸醫師是醫者,是飼主,是專業人士,也是最普通不過的人。他們知悉一切的犧牲,曉得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明白人與獸之間那相互依存、利用,而又相伴的複雜關係。
這本書裡沒有英雄,作者曾達元的書寫告訴我們,生命從來都是在殘酷與溫柔、抉擇與選擇之間,努力尋找安然前行的方向。
「謹以此作品,表達對動物們的敬重。
特別是那些經濟動物,牠們的犧牲,不僅餵養了人類的口腹之欲,也成為我作為獸醫師的啟蒙與養分。
也獻給各領域的獸醫師們。你我作為醫者,亦是中介者、溝通者,既要直視生命的重量,也要回應社會的期待。
我們努力讓不同世界彼此聽見,在矛盾與掙扎之中,徘徊於人與獸之間。」
──曾達元
▍本書特色
★ 經濟動物獸醫師的細膩書寫,一窺產業不為人知的真貌。
★ 獸醫師這群人的真實故事,他們的工作、人生、困惑、受傷與療癒。
★ 每篇故事皆有實際受訪者,以真實人物故事為基礎創作而成。
▍各界推薦
這畢竟是一本以「獸醫」為核心的作品,動物視角的切換,顯得小心翼翼與點到即止,但已照見這位年輕寫作者未來將為讀者開展的,更廣大的,人與動物交織的世界。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當我打開《欸,那個獸醫》時,那些熟悉的氣味與聲音都回來了──防疫衣裡悶熱的溼氣、電擊器嗶鳴的瞬間、車子在鄉間小路顛簸的節奏。這不是一本文字的書,而是一場場獸醫人生的重現。
──綦孟柔|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秘書長
書中所有篇章的原型,都來自「女性」獸醫師。……閱讀過程中需要同理的情境實在太多了:陪伴動物飼主的著急傷心、經濟動物被放棄後的求生掙扎、需要薪水因此忍受不合理的受雇日常、遵守法規與實務困境之間的兩難、為了理想不得不放棄的生活品質⋯⋯介於報導文學和散文之間的八個篇章,交織出的豈止是獸醫師的職人日常,更映照了身而為人的舉步維艱。
──劉芷妤|作家
獸醫師曾達元在《欸,那個獸醫》中,以自身的歷程,映照他者的故事,或反過來,以他者的現實,核對自己的處境。整個書寫好似一場長途跋涉,既沒有「我比你知道更多」的老農自信,也拋下「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水手高位,而是帶著置身其中的矛盾與困惑,放下定見,一站一站就教同儕,傾聽別人的生命,把行業環境再拉廣一些,思索時序再拉長一點,回應最初的生死扣問。
──顧玉玲|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序)
作者:曾達元
1990年生,嘉義大學獸醫系、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不務正業獸醫師,在文字間尋找另一種治療方式。最近又回到豬雞的世界裡。曾獲2022建蓁環境文學獎三獎(〈雞械複製時代〉)、《聯合文學》2025年1月小說新人賞(〈數學問題〉)。
推薦序一 醫,不只是拯救,而是陪伴/綦孟柔
推薦序二 你是她與他,你是我,也是牠/顧玉玲
推薦序三 等待被看見的「你」/黃宗潔
楔子 「欸,那個獸醫。」
夥伴:你,與你熱愛的豬
血手:屠檢獸醫師的白日與暗夜
異志:非犬貓獸醫師的非主流之路
奢活:致富路上,毛利滿滿
追夢:一段落地後的飛行手札
雌生:養雞場裡,那片黃色的海
濕羽:與獸對望,照見無常
送行:Gary、阿花,我們的貓
後記 那些暫時還無法被取代的
致謝
參考資料
楔子(節錄)
人生不會再有這麼一段時間,會像當兵這樣,把截然不同的人們強硬地黏在一塊生活。在屏東進行新兵訓練時,彼此間會貼上簡易的標籤來記住對方。學歷、職業、外型、國籍是常用的代稱詞,一棟連兵舍裡擠上近百張陌生的臉孔,充斥著以「欸」作為開頭的稱號,包含「那個台大」、「那個工程師」、「那個壯哥」、「那個泰國人」。
而我,就是「欸,那個獸醫」。
班長會拿起防中暑小卡說:「欸,那個獸醫,來解釋看看熱中暑與熱衰竭有什麼不同。」擠在悶熱的教室裡上急救訓練時:「欸,那個獸醫,來示範CPR怎麼做。」路過安全士官桌,被值星班長叫住:「欸,那個獸醫,洞么拐發燒,你負責去量體溫,早晚跟我回報。」
整個新兵訓練期,我都在每雙好奇的眼睛裡,反覆修正「那個獸醫」的自我介紹詞。認真說明自己不會看狗貓,主要學習的醫療對象是豬與雞,負責到農場為一整群動物看病。不知不覺成為農業小尖兵,一遍遍解釋:雞沒有打生長激素,雞沒有改造成六隻腿、三對翅膀;豬不是都吃餿水長大,豬不髒,牠們很愛乾淨。
當有人進一步多問幾句,關於我這一類「經濟動物獸醫師」如何醫治動物,我會說起有時看病,會對動物進行電擊與解剖。即使我認為應該要如庖丁解牛般,認真地以醫學角度描述疾病診療過程,但也知道這群弟兄又怕又愛聽。
於是,我總會將醫療場景轉化成血淋淋的修羅場,帶領聽眾進入麻豆代天府的十八層地獄,恍如看見那群詭異的機械人偶,持刀開胸剖腹,抓出五臟六腑。看到那些忘記闔上的下巴,手指夾著垂落灰尾的菸,我滿是得意。
有天半夜,才要放下蚊帳準備就寢,有名同梯抱著鋼盆跑來床邊對我說:「欸,那個獸醫,連上的狗要生了,你去幫牠接生。」整間寢室的平頭瞬時投以明亮的眼神,認定我能幫上什麼忙似的。我揮揮手,再次說明自己不會看狗貓。不知道哪邊傳來「欸」的一聲,發自心底的疑惑著:「你不是獸醫嗎?」
我無奈地穿起藍白拖,下樓時心想,也許這才是大家認為的獸醫師該做的事。
掃具間裡,有隻黃狗窩在紙箱上,叼著班長為牠準備的毛巾,側身臥躺著,露出脹大的乳房,隨後又站起來繞圈。我只知道牠想找到一個舒適的角度,好準備生產。除了趕大家離開,不要讓牠感到緊張外,若真面臨難產的狀況,我也只能兩手一攤。
此時,雖然具有獸醫師的身分,但面對不擅長診療的物種,也與一般人無異,只能為牠的生產過程祈禱。
如今,每每向陌生人提起自己是獸醫系畢業時,依舊能看見對方眼底一亮,浮現出一身白袍、掛著聽診器、各種動物繞身的慈愛形象。而當有人進一步問起自家寵物的問題時,我仍會強調自己是學習看經濟動物的,隨後那些眉頭便會擠出疑惑:「哇,很特別呢。」
隨後,空氣凝結彷彿時空停滯。
「欸?你不是獸醫嗎?」或者,對方會篤定地說:「那你一定很愛動物吧?」
對我來說,這兩句話,都指向獸醫師身分中最核心的矛盾。
為了確保農場裡其他動物的健康,有時得犧牲病畜,才能拯救牠的同伴。這意味著,我得親手結束動物的生命,才能檢測疾病。
「愛動物」卻又必須同時「殺戮」,這樣的矛盾一直繚繞在我心中。
愈來愈多的寵物被視作家人,動物醫療也漸漸受到矚目。當代談及獸醫師,總會直接聯想起身穿白袍、捧著貓狗的親切形象。但社會並不理解「獸醫師」其實是一個集合名詞,有人負責殺生,也有人負責救死。每一種動物領域,都有截然不同的現實。
許多疑問不斷湧上,夾雜著身分期待與現實差距,讓我好奇那些曾經一起抱著書本、努力考取獸醫師資格的同儕,現在過得好嗎?會有同樣的困惑嗎?
我開始重新聯繫那些曾與我一起學習、在不同領域奮鬥的獸醫朋友。有人專注於經濟動物,有人投入寵物臨床,也有人走向研究或公共衛生。他們在各自的場域裡面對不同的現實與掙扎,構成了我想書寫的世界。那段時間,我也在文學所另一堂課裡學習如何訪問、如何書寫真實。兩個訪談計畫同時進行,讓我不斷思考:如何讓讀者看見那個人,而不只是看到我的視線……
推薦序1(節錄)/醫,不只是拯救,而是陪伴
綦孟柔/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秘書長
我常在獨自一人時深思,當一名獸醫,究竟有什麼意義?
這份工作很少被看見,也不容易被理解。我們在手術檯上與呼吸交錯的生命搏鬥,在山林裡扛著沈重的醫療器材與陷阱對抗,也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早晨裡,對著剛出生的小豬、剛離世的貓,學會再次呼吸。
當我打開《欸,那個獸醫》時,那些熟悉的氣味與聲音都回來了──防疫衣裡悶熱的溼氣、電擊器嗶鳴的瞬間、車子在鄉間小路顛簸的節奏。這不是一本文字的書,而是一場場獸醫人生的重現。作者曾達元像一位安靜的見證者,把那些日復一日、在體制與倫理邊界中穿梭的獸醫師們,重新放回真實的光線下。
他寫的不是理想化的「醫者」,而是一個個「正在努力撐下去的人」。有人在屠宰線上數著自己殺過多少頭豬,有人在養雞場裡學會用笑話對抗歧視;也有人在診間裡接住民眾投射的期待。那不是冷漠,也不是殘忍,而是無數次選擇之後留下的專業與誠實。書裡的「獸醫」們,不是被浪漫化的英雄,而是和我們一樣會懷疑、會疲倦、會在夜裡問自己:「這樣做真的對嗎?」
特別是,這本書寫的是八位女性獸醫師。
他們在這個仍帶著濃厚陽剛氣息的產業裡工作,得在高溫、糞臭與被質疑的目光中證明自己。有人一邊拉豬、採血、做解剖,一邊被提醒「女生不適合太靠近這些動物」;有人被迫笑著化解騷擾的玩笑,只為保住一個能繼續工作的空間。
他們的身體時常被放進他人眼光的框架裡──太瘦、太柔、太不像獸醫。有人必須用力握緊手中的解剖刀,讓同事相信自己能勝任;有人得把疲憊吞回喉嚨,只為不讓別人覺得「女人太情緒化」。
更艱難的是,這些環境並不總是安全的。
偏遠的養殖場沒有監視器,獸醫師得獨自開車進入陌生的場域,面對不熟識的畜主與工人。當身體的安全與專業的尊嚴同時被挑戰時,他們往往只能以微笑、以客氣掩飾不安,因為太強硬就可能被貼上「難合作」的標籤。書裡那些被拍肩的瞬間、被調侃的語氣、在車上緊握門把的場景,讀起來都那麼真實。
那種「不被當作一回事」的感覺,比任何勞動的痛更深。因為他們不是不夠努力,而是努力被看不見。
我深深明白那樣的矛盾。
推薦序2(節錄)/你是她與他,你是我,也是牠
顧玉玲/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農夫和水手,是古代社會的說故事好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是這麼說的:農夫長年定居,熟知家鄉流傳的典故和勞作細節;水手周遊列國,遠赴異地對新奇事物見多知博。一深一廣都造就了說與聽的默契,可惜工業社會洶洶來襲,逐漸使「說故事」的技藝失傳了。
如果,說故事的人就是農夫,在同一領域深耕已久,卻像水手啟程遠方,四處尋訪同業經驗。那麼,故事必然說得不太一般吧?獸醫師曾達元在《欸,那個獸醫》中,以自身的歷程,映照他者的故事,或反過來,以他者的現實,核對自己的處境。整個書寫好似一場長途跋涉,既沒有「我比你知道更多」的老農自信,也拋下「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水手高位,而是帶著置身其中的矛盾與困惑,放下定見,一站一站就教同儕,傾聽別人的生命,把行業環境再拉廣一些,思索時序再拉長一點,回應最初的生死扣問。
《欸,那個獸醫》不是常見的職人書寫,雖有勞動過程的艱難打磨、就業市場的分析批判,卻少見匠人或技師長年練就的非凡身手,更罕有辛勞成果的榮光與創意。這本書不貪心,跟著作者的關注與關係網絡鋪展開來,受訪對象多是青壯世代,從業時間約十餘載,足夠熟練上手,也得以多方轉換,但尚未被磨平銳角,尚未因習以為常而失去敏感度,且不免徘徊於心有所愛與生死憂思之間。
敘事必然來自特定視框,那是作者的局限,也是條件。幾經易稿,達元最終採取了非虛構寫作中很少使用的第二人稱「你」,作為主要的敘事者。你或是生理期來了卻在荒郊野外找不到如廁地點,或是主掌認證權力卻在多方擠壓下作假蓋章,或是在釣蝦場為拉業務飲酒至忘記「踩罐」的菜鳥,或是痛心於追求流行近親繁殖而打造多病寵物、以及被淘汰卻爭相踩踏多吸一口氣的黃色絨毛之海……同時間,你也是飼主、病人、上班族、普通人。形形色色多稜鏡的你,既具有個人的獨特歷程,又涵括了普遍性的獸醫師群像。
推薦序3(節錄)/等待被看見的「你」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每每向陌生人提起自己是獸醫系畢業時,依舊能看見對方眼底一亮,浮現出一身白袍、掛著聽診器、各種動物繞身的慈愛形象。」曾達元不無困擾地,在《欸,那個獸醫》的〈楔子〉表達了身為經濟動物專業,面對「獸醫」刻板印象的無奈。畢竟為心愛的同伴動物尋求醫療協助,是很多人在生活中與獸醫產生交集的唯一可能。想像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使得他的職業常被誤讀與過度浪漫化。
但是,若提起「獸醫」或「獸醫文學」的「被」浪漫化,那位即使半夜也會因為一通電話艱難起身,冒著寒風開車前往遙遠農舍為母牛接生的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醫生,以及英國約克郡的鄉村風光,反而是獸醫這個詞彙在我心中形塑的最初畫面。本土獸醫形象的具象化,以及獸醫文學在閱讀市場上受到注意,是在九○年代獸醫師杜白出版了一系列以寵物門診故事為主題的作品後,才更普及地進入大眾視野。
閱讀與真實世界並不同步。寵物醫療因應飼養寵物風氣、觀念的改變,在短短幾十年內發生許多變化,小動物繞身的「動物醫生」這個稱呼逐漸取代了鄉村風的「獸醫」,但獸醫/動物醫生臨床經驗的分享卻未以同等比例蓬勃成長。至於更不溫馨浪漫的經濟動物醫療現場,則與經濟動物本身一樣,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欸,那個獸醫》的出版,無疑彌補了長期以來的這塊空缺。
或許也因為意識到這樣的空缺,曾達元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他無意成為「台版吉米.哈利」,明明不乏生動刻畫自身職場故事的能力,卻捨近求遠地,寧可將鏡頭照向同輩之人,以第二人稱的「你」,將八位女性獸醫師的訪談,轉化為銘刻生命軌跡的一幅幅版畫。不過,書寫對象既是同儕,同樣的年齡與養成背景,讓他們也面臨類似的焦慮和困境,本書所呈現的複數面貌,因此相對聚焦在這群已進入職場數年的青年們,回頭檢視來時路,有猶疑有惶惑,仍在現實與理想間試圖找到安身之所的歷程。
屠檢獸醫師的白日與暗夜
■ 執行公務的送行者
當夜空的紫黑漸被日頭驅散,數道白光自遠處樓房頂端竄出,東亞家蝠們拍動雙翼,返回陰暗的棲息地,準備入睡。身為「屠檢獸醫師」的你,則清洗著沾上血漬的圍裙,有些深入纖維的暗紅色,雖然無法洗淨,卻也成為你勞碌的證明。你換回日常樸素的裝扮,離開屠宰動物的場域,跨上機車,返家。
風在耳裡流竄,這單調的白噪音,像是脫離殺戮的儀式,給你帶來平靜與平穩。在近乎無人車的道路上,沖走那隱隱殘留在耳裡的雜音:各種齒輪的摩擦聲、工人們的叫喊,以及動物們被宰殺前的哀嚎。
屠宰場裡令人顫慄的聲響,隨城市與住宅的無限擴張,被貼上「嫌惡設施」的標籤,逐步被驅趕到人們的視線之外,在集體的迴避中變得更加隱密。
過往,屠宰總在夜深人靜時開始,趕在天光破曉前將肉品送往市集。現代,隨著「冷鏈」流程的完備,一部分肉品也會送往肉品加工廠,成為生鮮超市上的盒裝肉塊。因此,現代的屠宰作業時間變得更加「靈活」,不再受限於市集販賣的時程。無論白天或夜晚,都會有動物因為人類的胃口走上犧牲的通道。
屠宰業上班的你,有時依循太陽的軌跡上下班,有時則完全相反,隨著月光的明暗而生息。你的入眠儀式是拉上房間的遮光簾,讓桌燈成為唯一的光源,營造人工的向晚。
不知從何時開始,你開始穩坐於書桌前方,攤開一本日記,也像是一種儀式,將那些無法對人言說的噪音化為文字,一顆一顆在紙上落定,耳邊的喧囂似乎也逐漸寧靜。
你坦白地說,不知道這樣睡前的書寫能維持多久,一如你也未曾將屠檢獸醫師作為一生的志業。但正因無法預期能持續多久,此刻的你反而更認真地對待這件事。轉眼,書寫已橫跨五年,一頁頁承載著你轉換三個獸醫領域工作的心路歷程。
聊起過往與現在的對比,你認為最大的改變是成為屠檢獸醫師後,自己得保持絕對「果斷」且「明確」的態度。
「什麼是『果斷』且『明確』的態度?」我問。
你向我再次確認問題後,說想仔細理解一下這個問題的意思。
我翻著訪綱的題目,正打算換個說法再提出疑問,卻想起剛剛你說:「自己習慣一次只思考一件事情。」你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習慣,或許是因為進入屠宰業前,曾是伴侶動物獸醫師的緣故。在診間的你,不僅得注重眼前的動物,還得時刻注意飼主的情緒,任何說明都得謹慎,小心拿捏語言的分量,才能確保每一次開口都是有效的溝通。
因此,我似乎不該打擾你的思考時刻。咖啡廳裡的磨豆聲順勢加入了談話,它不斷地製造著聲響,而我們則是陷入了一陣靜默。
這個時刻,我在網路上搜尋屠檢獸醫師的工作服裝。防水圍兜、安全帽與雨鞋──一身潔白的套裝。
我想著,如果說伴侶動物獸醫師的白是天使的形象,有著拯救生靈的希望,那屠檢獸醫師的白,對待宰動物來說或許是死神象徵,但不一定是全然負面的。
因為你的職責,是必須讓被迫犧牲的動物,在安全、人道與衛生的準則下走完最後一程。這是一種取走性命,卻又守護眾生的矛盾任務。
■ 血、肉與白衣
或許一切都該從屠檢獸醫師的日常講起。換上白衣的你,站在待宰豬隻繫留的圍欄,雙眼銳利,迅速掃描上百頭的動物是否出現異狀。例如,早已死亡而軀體僵直,或是因疾病引起的皮膚斑點,這些都是無法進入屠宰流程的指標。
人類心臟驟停的四至六分鐘內是黃金救援時間,而讓豬隻踏上生死通道的黃金屠宰時間,大約也是如此。一個救傷,一個取命,時間尺度竟恰好相似。
你緊盯著每一頭豬,當牠們踏上高臺,被機器固定無法動彈,頭部通過電流的瞬間,得符合法規下的描述:「呈現失去知覺、意識的狀態」,也就是以人的角度去猜測動物此刻已感覺不到疼痛,才可以進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關卡。
當刀刃從脖子刺入,澈底將全身血液放乾淨。在人道主義的觀點下,失血能讓待宰動物的腦袋缺氧,從昏厥進入真正的長眠。但在美味的角度上,澈底的放血才能讓肉塊不會帶有古怪的風味。
機械通道上的豬隻,經歷燙毛、脫毛、開腹、開胸、取下內臟、剖半屠體。豬隻在臺灣人的飲食文化中是重要的肉品來源,也因此只要屠宰水線開啟,血液總能匯聚成一條暗色長河。
當屠檢獸醫師站上檢查檯,除了得看顧屠宰環節是否順利,也得細察來到眼前的屠體有無異常樣態、內臟是否通過標準。放血不全、異常消瘦、嚴重黃疸、惡臭異味、全身性病變,全都不該進入消費者的口中。你們的感官是最重要的判斷依據,因此,檢查檯需要光度五百米燭光,足以照亮敞開的胸腹腔。
當屠宰線出現任何狀況時,例如,機械發生故障、眼前有過多待檢驗的屠體,或是當你注意到眼前的肉塊,對食用的安全性有所懷疑時,你便會按下按鈕,讓整條屠宰線暫時停止流動,直到你發出繼續開工的指令為止。
此時,所有人的目光都會集中在獸醫師的身上,你感受到的不僅僅是責任的重大,更是整條生產線因你而停滯的壓力。
大面積的紅不是流淌的血漬,是高舉滑輪印章而快速落下的一道橘紅色記號,代表「安全可食的肉」,隨即推入預冷室,等待送入販售或加工的地點。若是不合格的項目,獸醫師得迅速地記錄,並以藍色墨水進行標記,防止這些不該被食用的肉品流入食客的口中。
部分被報廢的屠體與臟器能換得規定上的補償。這攸關農民或收購方的利潤,往往亦是爭端的來源。有人會刻意地釋出強大的氣場,意圖干預檢查的合格與否。更有業者緊貼在獸醫師的身邊,雖然不發一語,卻散發出沉重的壓迫,如同在昏暗的房間裡,難以忽視的一抹牆角暗影。
我曾聽聞,若是不遵從「某些人」的意見,致使他們受到損失,便會暗示不服從的獸醫師,將活在另一種「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恐懼之中。但在你的職涯中,並沒有經歷到這些誇張的謠言。
雖然你無法清楚解釋什麼是「果斷」且「明確」的心法,但聊完這些工作日常的複雜,你說明了一個信念:只要遵照職責,挑出那些不符合規範的項目,縱使有人直接給予不悅的神情或穢語,猶豫與妥協也從來不在你的考量範圍裡。
你說,若是放過一次,誰知道是不是還有下一次,況且其他業者,可能也會期待你給一樣的「優惠」。
「那樣會沒完沒了。」你無奈地說。
那麼身為屠檢獸醫師的你,如何思索掌握動物生死權力的自己呢?
你不覺得自己握有什麼龐大的權力,畢竟在這封閉的屋子裡,工作的人們、待宰的動物與運轉的機械,均是構成屠宰線的重要齒輪,如同一座精密運轉的工廠。而進入屠宰場的動物,終究得跨越生死的那條界線。
因此,對你而言,屠檢獸醫師更像執行公務的送行者。你們按照詳細的規定,讓動物們好好地告別此生。在這個必要之惡的過程,你的角色是判決者,同時也是見證者。
你說,若真要說有什麼權力,那也是對於人類來說比較重要吧。畢竟肉品是否可以食用,確實需要獸醫師嚴格把關。當你站上檢視屠體的高臺,內心確實會湧起一股壓力,得擔負起食品安全的使命感。這種權力既微小又巨大:微小到只是按下一個按鈕,卻巨大到關乎萬人以上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