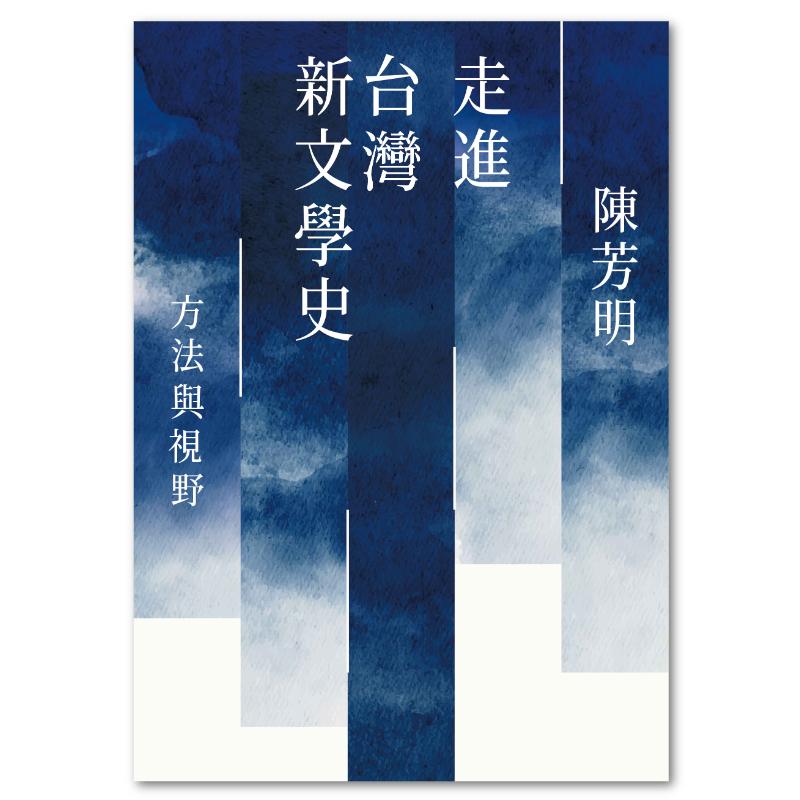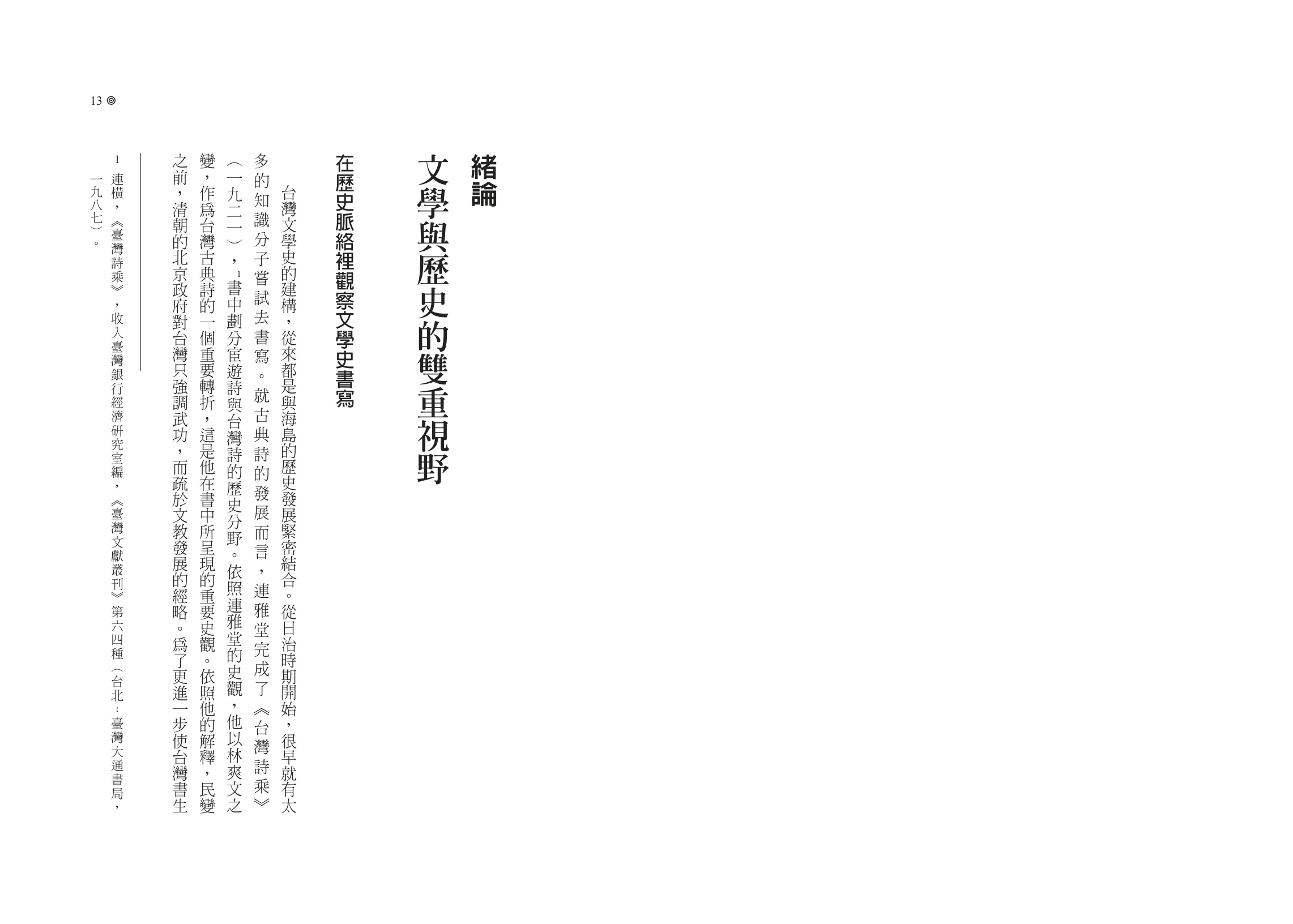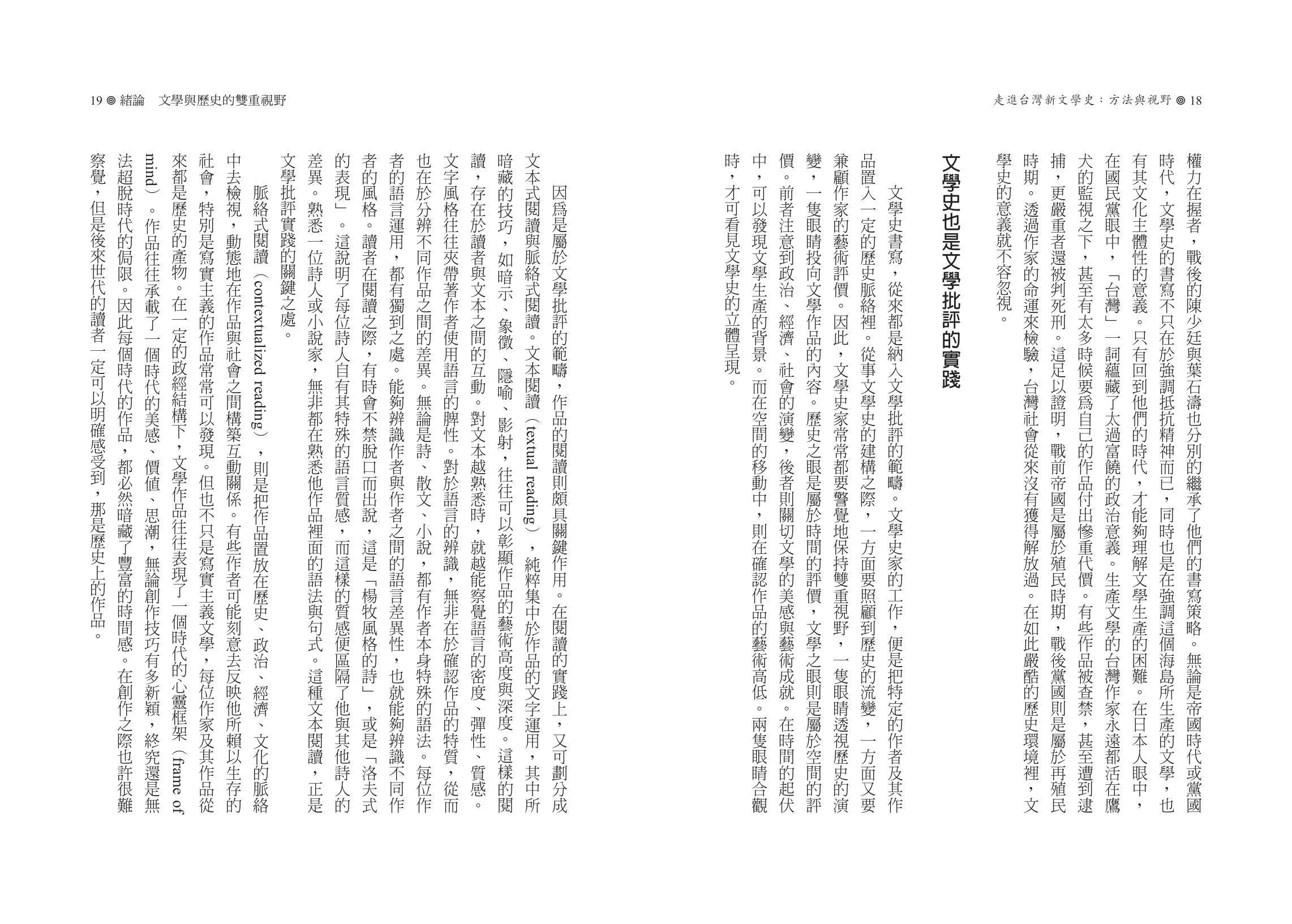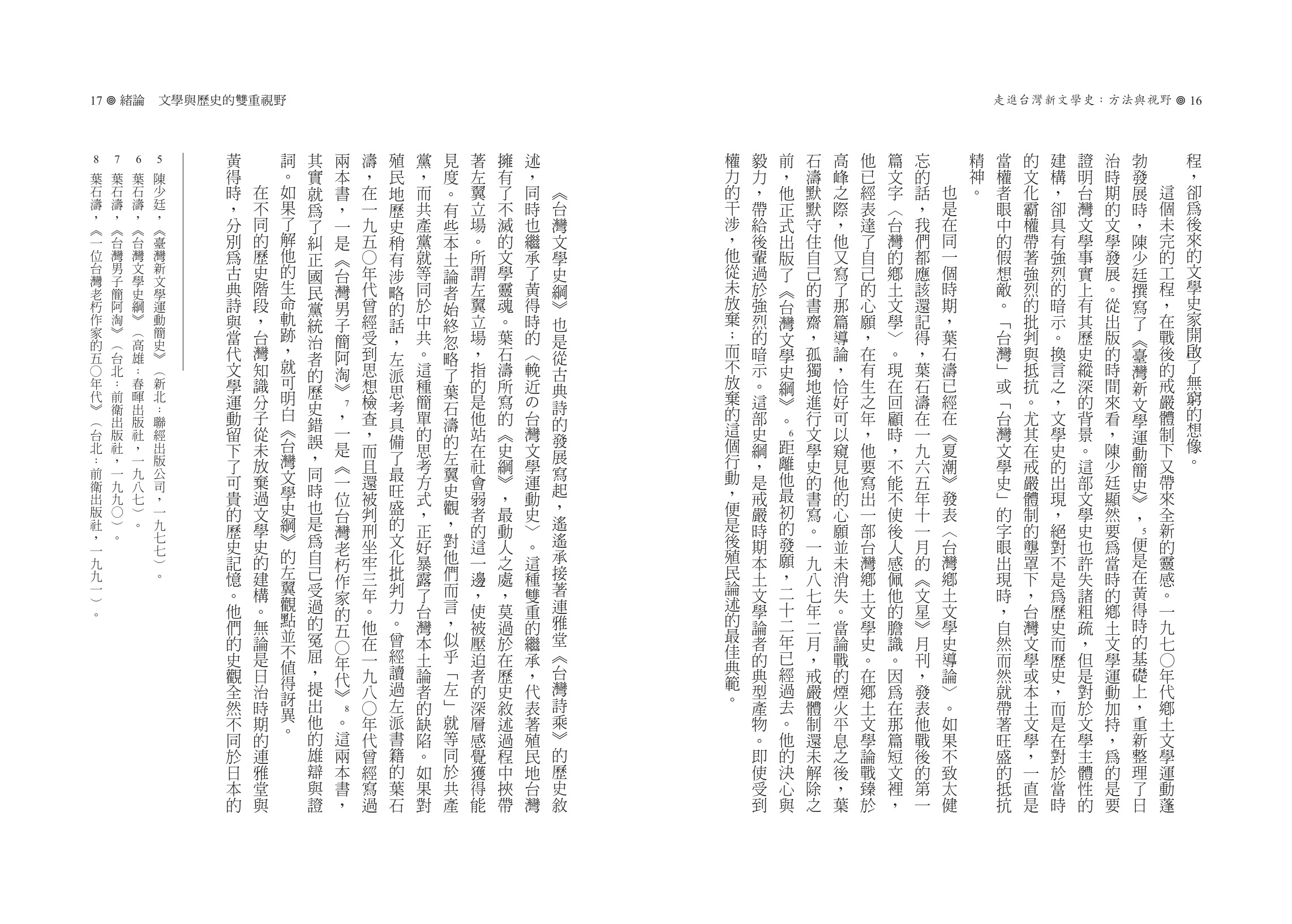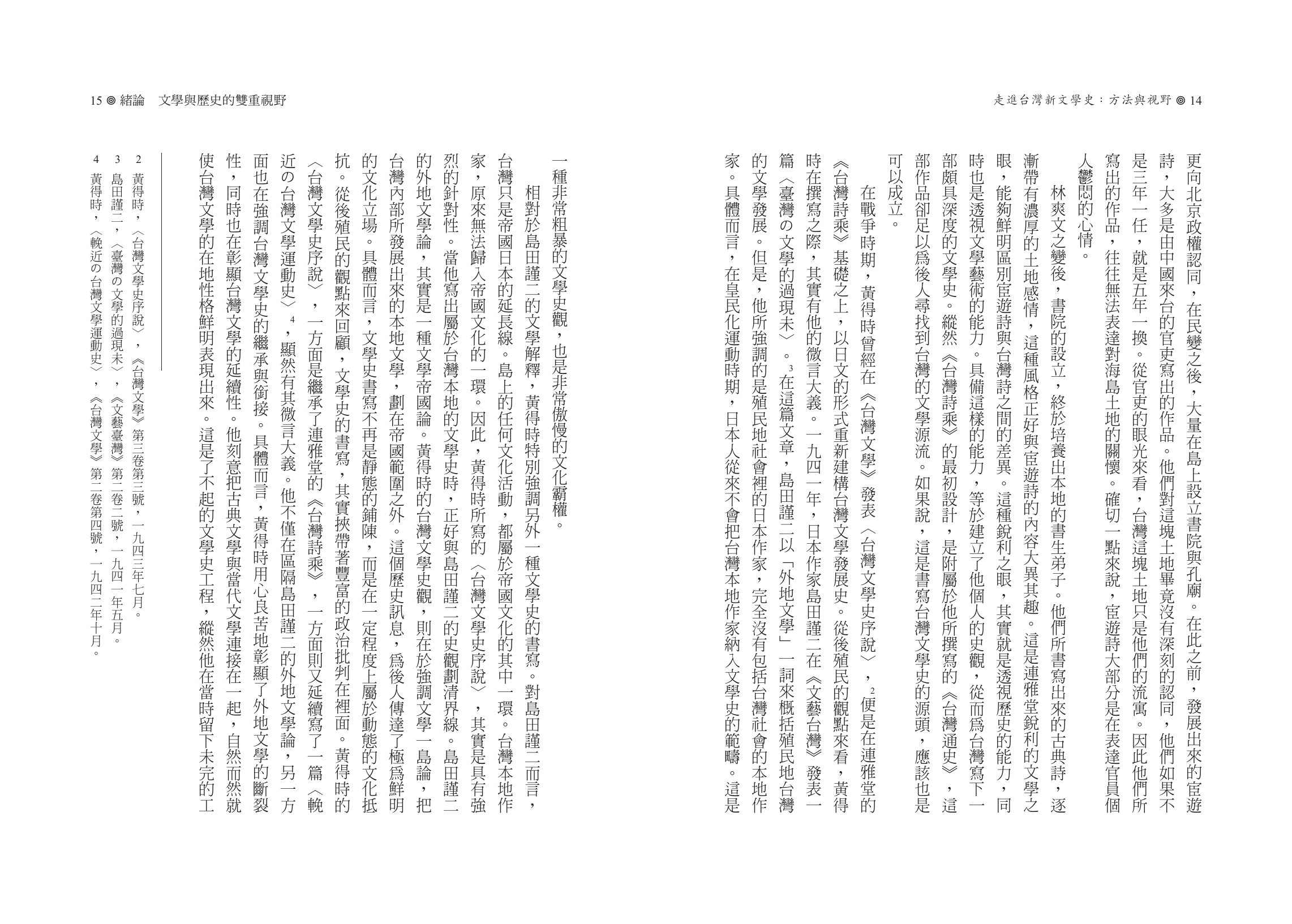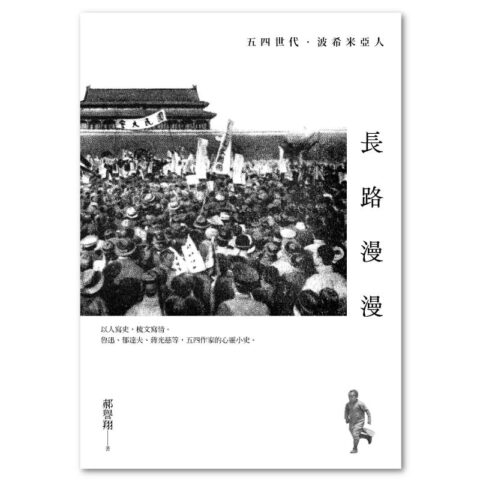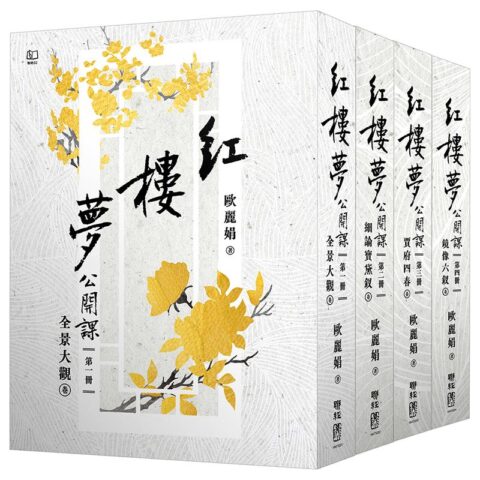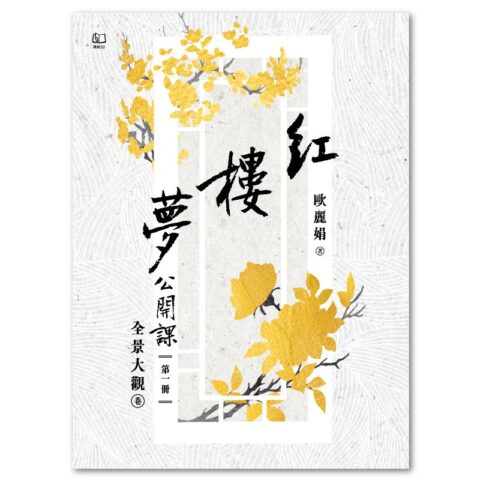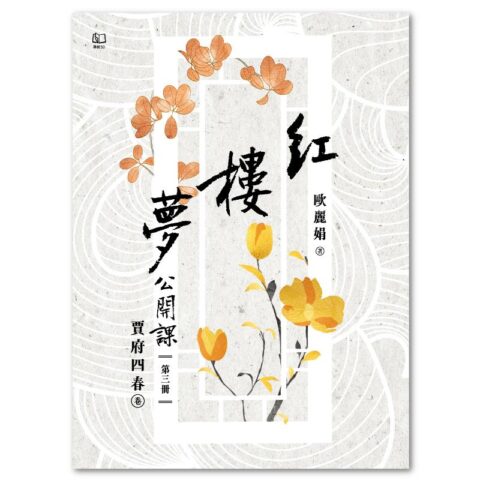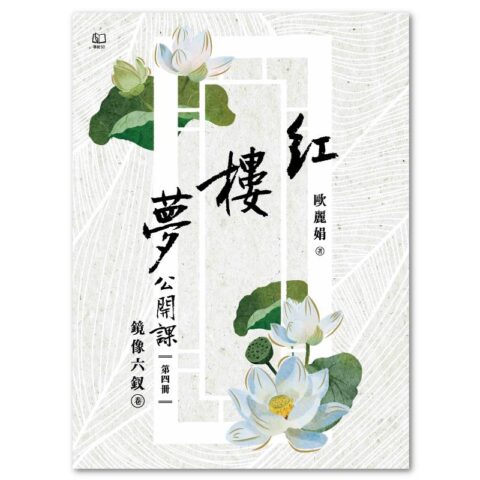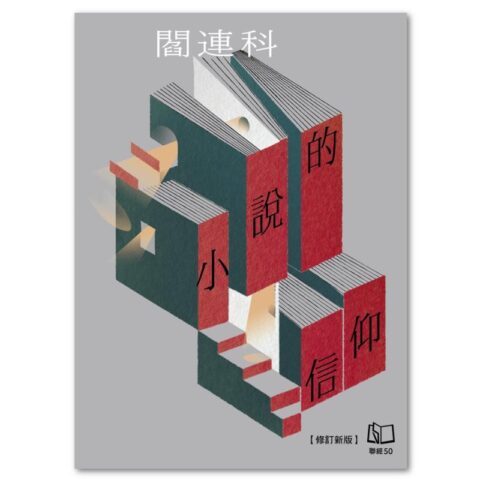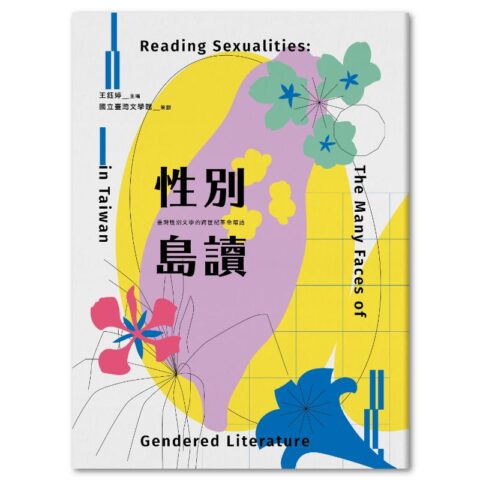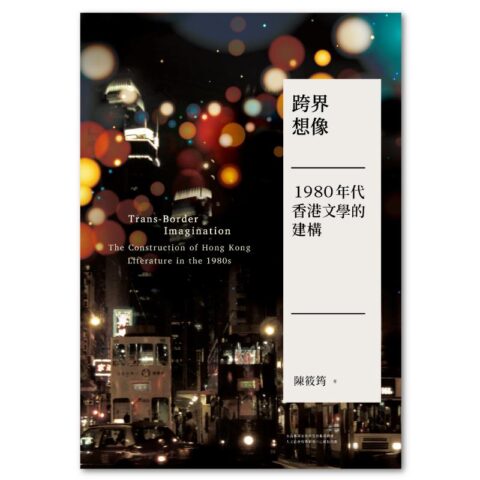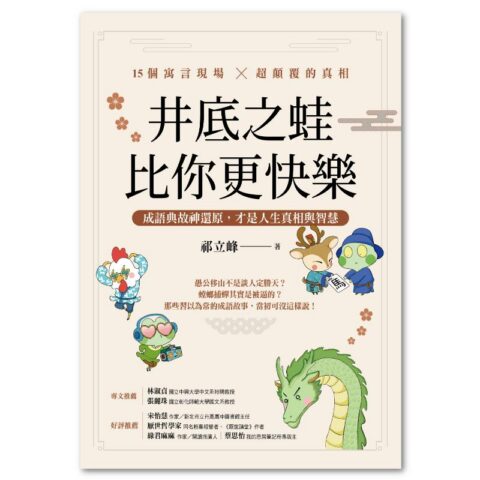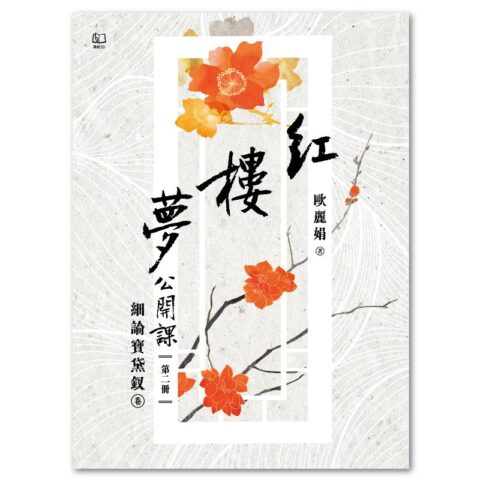走進台灣新文學史:方法與視野
出版日期:2025-10-30
作者:陳芳明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56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1.4 cm
EAN:9789570878226
尚有庫存
在整個東亞歷史的版圖上,台灣文學曾經被置放在非常邊緣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台灣作家歷經了戰前的殖民時期,又穿越了戰後的戒嚴時期,使島上許多文學創作者找不到自我定位。
台灣解嚴之後,台灣文學慢慢獲得解放,政治權力干涉退潮之後,全球化浪潮開始對台灣文壇產生巨大衝擊。文學史的書寫者,需要保持雙重視野,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尋找對話的空間。
很少有作家可以脫離客觀環境的限制,一定的時代有一定的文學特質。從事文學批評,或許無需在意客觀歷史的發展,但是文學史的書寫,不可能把歷史與文學分割開。歷史文獻的閱讀與文學作品的閱讀,應該同時並進。歷史如果是一條時間的長河,文學史是在長河的兩岸尋找禁得起沖刷的文學作品。
本書是陳芳明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授的一門課,課程在解釋《台灣新文學史》背後的思維。在一定基礎上,文學史也是一種文學批評,彰顯出作者的美學思考。這部方法論既有史料學的思考,也有編年史的意義,可以作為台灣現代史書寫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一位知識分子與社會對話的參考。
作者:陳芳明
1947年出生於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並於美國華盛頓州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同時受委籌備、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以顯其治學和教學上的卓越成就。
陳芳明創作逾三十載,其編著的作品影響深遠,例如主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等;其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見證了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而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深淵與火》、《邊界與燈》,在在呈現了高度的文學造詣。
在文學創作之餘,陳芳明的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現代主義及其不滿》,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自 序 在文學大海浮沉
緒 論 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文學史也是文學批評的實踐
第一章 後殖民史觀與歷史分期
為什麼是後殖民史觀
台灣文學史的分期
為什麼解嚴是文學史重大事件
作家的評價與定位
第二章 殖民地現代性與台灣文學啟蒙
現代性與台灣新文學的相生與相剋
台灣新文學與近代知識的建構
文學作為近代知識建構的一環
政治運動作為近代知識建構的基礎
第三章 迷人的一九二○年代風景
文明的滋味
殖民地現代性的衝擊
台灣知識分子的語言苦惱
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
第四章 殖民地作家的成熟與文化認同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意義
「碰壁」的台灣社會
第五章 帝國論述與抵抗精神的交錯
殖民地現代性成熟時期的台灣作家
日語普遍使用與台灣作家的認同
左傾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宿命
台灣日語作家的登場
第六章 太平洋戰爭與台灣作家處境
皇民化與六三法
戰爭時期台灣作家的命運
以家族書寫對抗國族立場
日本近代超克論的提出
第七章 戰後初期的展開:帝國與黨國的交錯
歷史軌道從帝國轉換成黨國
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苦悶
楊逵在「橋」副刊的戰鬥身影
戰後台灣魯迅學的萌芽
第八章 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的鍛接
冷戰體制與現代主義的傳播
現代主義運動的持續發展
壯觀的現代詩運動
台灣現代主義之掙脫西方影響
第九章 台灣現代小說與現代詩的成就
現代小說家的登場
現代詩與台灣抒情傳統
現代主義運動中的性別議題
同志議題浮出地表
第十章 鄉土文學運動的崛起與文學史轉向
文學與政治的辯證關係
台灣文學史的轉向
《夏潮》的誕生與鄉土文學論戰
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
第十一章 一九八○年代的文學與政治
美麗島事件:時代的終結與再啟
後殖民或後現代
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差異
一九八三年的政治意義與文學意義
第十二章 朝向一部台灣文學史的建構
編年體的歷史書寫
文學史是文化特質的彰顯
文學史的世代論
文學史是文化主體的建構
序
在文學大海浮沉
完成這本書之際,也正是面臨我將退休的時刻。二○一一年,正式出版《台灣新文學史》,我曾經告訴自己這是一部生命書。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醞釀,到最後定稿完成前後長達十餘年。所謂生命書,指的是自己閉門書寫之際,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台灣民主政治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婚姻平權的追求,也正好與這本書的撰寫等高同寬。台灣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性別平等、族群平等,也都在埋首撰寫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相應於整個社會的天翻地覆,這部文學史能夠在學院的圍牆內慢慢完成。對於書寫者如我,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幸福。畢竟,我所撰寫的文學內容,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整個社會的脈動吻合。
這部文學史的撰寫,始於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前後。在那次鋪天蓋地的災難中可以倖存下來,隱隱中感受到上天給我的庇護。當時我在暨南大學任教,等餘震完全過去之後,我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才發現室內所有的書架都已經倒下。如果那天我稍遲回去宿舍的話,可能就會被掩埋在倒塌的書架之下。冥冥中,我不能不相信,有一隻看不見的命運之手,默默為我引導。那部未完成的書稿,稍後又跟隨我來到政治大學。為了完成我的餘稿,我一方面在大學部開授台灣文學史,一方面在研究所也開授「書寫台灣文學史方法論」的課程。授課之初,曾經暗自許願,凡是在大學部與研究所開授的任何一門課程,最後都要寫成一本專書。這樣的願望,在過去十一年逐漸實現。如今的這部書,應該是屬於我最後一本上課講義的改寫。能夠順利完成,我應該感謝政治大學繼續延聘我,終於讓最後一冊學術專書得以殺青。
在大學時期,我讀的是歷史系。後來在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便赴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繼續研讀歷史。這條漫長而曲折的旅路,似乎也說明了,自己是如何從歷史系橫跨到中文系。二○○○年,政治大學中文系邀請我來授課,當時開了兩門課程。一是台灣文學史,一是文學批評。這本書的內容,也曾經在台灣文學研究所授課。當年都只是講義與大綱,而且學校也在教室現場錄影。如今得以使用文字,一字一句記錄下來,對我而言是相當珍貴的記憶。全書初稿都只是講義的形式,經過多年之後,才慢慢重新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學術生涯的一種紀錄。彷彿是心靈上的漫長旅行,如今可以用具體的文字保留下來。
在整個東亞歷史的版圖上,台灣文學曾經被置放在非常邊緣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台灣作家歷經了戰前的殖民時期,又穿越了戰後的戒嚴時期,使島上許多文學創作者找不到自我定位。經過漫長的戒嚴時期,必須要到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之後,台灣文學的重要意義才逐漸呈現出來。身為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我曾經在海外流浪十八年,正好可以在美國東西兩岸的重要圖書館涉獵無數「禁書」。沒有那段流亡的時期,我就不可能完成一部《謝雪紅評傳》;也是經由評傳的書寫,才逐漸接近有關左翼運動的史料。在知識追求的歷程中,才開始發現台灣文學史上的左翼運動者,被戒嚴體制所遮蔽的真相。畢竟在台灣戒嚴時期成長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使用「右眼」看世界,對左翼所知甚少。我也是在《謝雪紅評傳》完成時,才更加理解台灣左派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而終於讓自己能夠「左右兩眼睜開」。台灣文學史上,也曾經有無數的左翼作家出現。但是經過日本殖民者的右派統治,又經過戰後國民黨的戒嚴,使得台灣知識分子失去左派的批判精神。
整理台灣文學史之際,才逐漸了解文學史上的許多真相。被奉為台灣文學之父的賴和,在新文學發軔之際,便發表了〈一桿秤仔〉,有意為殖民地社會的底層階級發出聲音。這位歷史上的文學前輩,其實為我們後來的世代帶來許多強烈的暗示。他並不以左派自居,但字裡行間所散發出來的批判精神,到今天仍然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資產。撰寫這部方法論之際,又勾起我在海外追尋史料的記憶。上世紀九○年代,我到達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才發現台灣的所有禁書,都可以在館內找到。國會圖書館之旅,似乎又在我的生命軌跡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我個人而言,一輩子的知識累積,只是在文學史上留下一個逗號。這部書終於完成時,顯然也暗示了自己的書寫工作告一段落。過去所有的書寫,其實都是一種自我反省,也是內心思考的自我鑑照。這部書的完成,是一個長達十一年的承諾,不只是對我自己,也是對上過我課程的學生。站在時間的峰頂,我可以俯望自己所做過的努力。也許還可以繼續文學創作,這不是承諾,而是對自己的一種期許。
緒論: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節錄)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從來都是與海島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從日治時期開始,很早就有太多的知識分子嘗試去書寫。就古典詩的發展而言,連雅堂完成了《台灣詩乘》(一九二一),1書中劃分宦遊詩與台灣詩的歷史分野。依照連雅堂的史觀,他以林爽文之變,作為台灣古典詩的一個重要轉折,這是他在書中所呈現的重要史觀。依照他的解釋,民變之前,清朝的北京政府對台灣只強調武功,而疏於文教發展的經略。為了更進一步使台灣書生更向北京政權認同,在民變之後,大量在島上設立書院與孔廟。在此之前,發展出來的宦遊詩,大多是由中國來台的官吏寫出的作品。他們對這塊土地畢竟沒有深刻的認同,他們如果不是三年一任,就是五年一換。從官吏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只是他們的流寓。因此他們所寫出的作品,往往無法表達對海島土地的關懷。確切一點來說,宦遊詩大部分是在表達官員個人鬱悶的心情。
林爽文之變後,書院的設立,終於培養出本地的書生弟子。他們所書寫出來的古典詩,逐漸帶有濃厚的土地感情,這種風格正好與宦遊詩的內容大異其趣。這是連雅堂銳利的文學之眼,能夠鮮明區別宦遊詩與台灣詩之間的差異。這種銳利之眼,其實就是透視歷史的能力,同時也是透視文學藝術的能力。具備這樣的能力,等於建立了他個人的史觀,從而為台灣寫下一部頗具深度的文學史。縱然《台灣詩乘》的最初設計,是附屬於他所撰寫的《台灣通史》,這部作品卻足以為後人尋找到台灣的文學源流。如果說,這是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源頭,應該也是可以成立。
在戰爭時期,黃得時曾經在《台灣文學》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2便是在連雅堂的《台灣詩乘》基礎之上,以日文的形式重新建構台灣文學發展史。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黃得時在撰寫之際,其實有他的微言大義。一九四一年,日本作家島田謹二在《文藝台灣》發表一篇〈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3在這篇文章,島田謹二以「外地文學」一詞來概括殖民地台灣的文學發展。但是,他所強調的是殖民地社會裡的日本作家,完全沒有包括台灣社會的本地作家。具體而言,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從來不會把台灣本地作家納入文學史的範疇。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文學史觀,也是非常傲慢的文化霸權。
相對於島田謹二的文學解釋,黃得時特別強調另外一種文學史的書寫。對島田謹二而言,台灣只是帝國日本的延長線。島上的任何文化活動,都屬於帝國文化的其中一環。台灣本地作家,原來無法歸入帝國文化的一環。因此,黃得時所寫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其實是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當他寫出屬於台灣本地的文學史時,正好與島田謹二的史觀劃清界線。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其實是一種文學帝國論。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觀,則在於強調文學一島論,把台灣內部所發展出來的本地文學,劃在帝國範圍之外。這個歷史訊息,為後人傳達了極為鮮明的文化立場。具體而言,文學史書寫不再是靜態的鋪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動態的文化抵抗。從後殖民的觀點來回顧,文學史的書寫,其實挾帶著豐富的政治批判在裡面。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一方面是繼承了連雅堂的《台灣詩乘》,一方面則又延續寫了一篇〈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4,顯然有其微言大義。他不僅在區隔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另一方面也在強調台灣文學史的繼承與銜接。具體而言,黃得時用心良苦地彰顯了外地文學的斷裂性,同時也在彰顯台灣文學的延續性。他刻意把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連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使台灣文學的在地性格鮮明表現出來。這是了不起的文學史工程,縱然他在當時留下未完的工程,卻為後來的文學史家開啟了無窮的想像。
這個未完的工程,在戰後的戒嚴體制下又帶來全新的靈感。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時,陳少廷撰寫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5便是在黃得時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了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從出版的時間來看,陳少廷顯然要為當時的鄉土文學運動加持,為的是要證明台灣文學事實上有其歷史縱深的背景。這部文學史也許失諸粗疏,但是對於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卻具有強烈的暗示。換言之,文學史的出現,絕對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在對於當時的文化霸權帶著強烈的批判與抵抗。尤其在戒嚴體制的壟罩下,台灣文學或本土文學,一直是當權者眼中的假想敵。「台灣」或「台灣文學史」的字眼出現時,自然而然就帶著旺盛的抵抗精神。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葉石濤已經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如果不致太健忘的話,我們都應該還記得,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文星》月刊,發表他戰後的第一篇文字〈台灣的鄉土文學〉。現在回顧時,不能不使後人感佩他的膽識。因為在那篇短文裡,他已經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在有生之年,他要寫出一部台灣鄉土文學史。在鄉土文學論戰臻於高峰之際,他又寫了那篇導論,恰好可以窺見他的心願並未消失。當論戰的煙火平息之後,葉石濤默默守住自己的書齋,孤獨地進行文學史的書寫。一九八七年二月,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他正式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6距離他最初的發願,二十二年已經過去。他的決心與毅力,帶給後輩過於強烈的暗示。這部史綱,是戒嚴時期本土文學論者的典型產物。即使受到權力的干涉,他從未放棄;而不放棄的這個行動,便是後殖民論述的最佳典範。
《台灣文學史綱》也是從古典詩的發展寫起,遙遙承接著連雅堂《台灣詩乘》的歷史敘述,同時也繼承了黃得時的〈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這種雙重的繼承,代表著殖民地台灣擁有了不滅的文學靈魂。葉石濤所寫的《史綱》,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在歷史敘述過程中挾帶著左翼立場。所謂左翼立場,指的是他站在社會弱者的這一邊,使被壓迫者的深層感覺獲得能見度。有些本土論者始終忽略了葉石濤的左翼史觀,對他們而言,似乎「左」就等同於共產黨,而共產黨就等同於中共。這種簡單的思考方式,正好暴露了台灣本土論者的缺陷。如果對殖民地歷史稍有涉略的話,左派思考具備了最旺盛的文化批判力。曾經讀過左派書籍的葉石濤,在一九五○年代曾經受到思想檢查,而且還被判刑坐牢三年。他在一九八○年代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是《台灣男子簡阿淘》7,一是《一位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8。這兩本書,其實就為了糾正國民黨統治者的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為自己受過的冤屈,提出他的雄辯與證詞。如果了解他的生命軌跡,就可明白《台灣文學史綱》的左翼觀點並不值得訝異。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知識分子從未放棄過文學史的建構。無論是日治時期的連雅堂與黃得時,分別為古典詩與當代文學運動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記憶。他們的史觀全然不同於日本的權力在握者,戰後的陳少廷與葉石濤也分別的繼承了他們的書寫策略。無論是帝國時代或黨國時代,文學史的書寫不只在於強調抵抗精神而已,同時也是在強調這個海島所生產的文學,也有其文化主體性的意義。只有回到他們的時代,才能夠理解文學生產的困難。在日本人眼中,在國民黨眼中,「台灣」一詞蘊藏了太過富饒的政治意義。生產文學的台灣作家永遠都活在鷹犬的監視之下,甚至有太多時候要為自己的作品付出慘重代價。有些作品被查禁,甚至遭到逮捕,更嚴重者還被判死刑。這足以證明,戰前帝國是屬於殖民時期,戰後黨國則是屬於再殖民時期。透過作家的命運來檢驗,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獲得解放過。在如此嚴酷的歷史環境裡,文學史的意義就不容忽視。
第一章 後殖民史觀與歷史分期
為什麼是後殖民史觀
文學史書寫,牽涉到史家的政治立場與人文思考。從政治立場來看,一位右派思考的史家,可能會集中焦點於歷史過程中的主流價值。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思想為基礎。儒家的文學史觀,表面上強調溫柔敦厚,事實上在書寫過程中卻往往排除異端。所謂異端,就是儒家所無法容忍的天下觀與政治觀。台灣學子受教過程中,最熟悉的思維方式莫過於「大一統」,「萬世一系」,「一以貫之」。所謂「一」,注重的是單一價值觀念。尤其是漢代以後,獨尊儒術的地位確立之後,就使多元、複數的觀念遭到封閉。這種單元論的價值觀念,甚至還放諸四海而皆準。因此,使一個屬於漢人的、男性的、異性戀的父權思維方式得以成立。這種大一統觀念,具體浮現在一個經典的論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國文化最早出現的霸權論述,再加上儒家思想的推波助瀾,正如儒家所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換言之,這種同化的觀念根深蒂固,很早就深植在漢人的靈魂深處。
漢人文化凌駕於邊疆民族之上,已是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文化的同化,在於強調「大同」。對於異族、異質的存在,都得不到文化上的寬容。這種歷史觀與文化觀的核心精神,就在於強調「同」(sameness),完全沒有空間容許平等性與差異性。從歷史書寫的內容來看,都可以發現千篇一律的模型。所有的「正史」,便是以帝王本紀作為開端,以王室為中心權力逐漸向周邊的土地擴張,最後才是有關邊疆或外國的書寫。二十五史相當有系統地貫穿了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從這樣的正史觀念延伸出去,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自然而然也符合這種要求。
凡是受過「中國通史」與「中國文學史」的教育訓練者,都相當熟悉這種文化位階(cultural hierarchy)的觀念。這種屹立不搖的位置,一直到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歷史教育與文學教育,始終都沒有改變。伴隨著一九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威權體制所堅持的儒家思想,才逐漸受到挑戰與質疑。確切而言,依附在戒嚴體制的文化中心論,自然而然也開始發生動搖。如果沒有威權體制的動搖,如果沒有民主運動的崛起,這種單元史觀與霸權史觀可能一直會沿用下去。在現階段的文學教育裡,大一統式的書寫其實還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殘餘。民主運動帶來最大的衝擊,便是使人權觀念在漢人社會裡篤定浮現。人權觀念的確立,逐漸從政治層面而擴散到性別、階級、族群的文化領域。
民主運動的洗禮,無疑就是島上人權觀念的刷新。夾帶而來的衝擊,不能不使既有的歷史書寫模式受到改造。前面一章所提到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便是代表了一個轉變的信號。台灣的歷史與文學,一直受到中國霸權的支配。學界某些人曾經詬病《台灣文學史綱》過於簡略,這其實是皮毛之見。這部文學史的誕生,意味著一個全新思維的時代就要降臨。書中所暗藏的左翼史觀,便是從社會底層的弱者角度回望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這位文學史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女性文學的存在,同時使歷史上毫無能見度的台灣本地作家大量浮出地表。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尤其在戒嚴體制還未宣告終結之前,他的文學史似乎已經預告下一輪的文化突破階段。
從台灣歷史的進程來看,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使得黨國體制終於遭到突破。政黨結構從單一變成雙元,預告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更重要的是,葉石濤在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就寫出了《台灣文學史綱》,1更是一種多元化的象徵。在黨國時期的歷史解釋,從政治史到文學史都完全受到國民黨的控制。葉石濤的文學史,另外開闢一個新的歷史軌跡,也意味著史觀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從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開始,一直到戒嚴體制宣布解除,四十二年已經過去,島上住民的心靈才有獲得解放的感覺。相對於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統治的終結,台灣社會的解放感可以說是遲到了。這說明了為什麼一九八七年代表著一個歷史的突破,具體而言,整個台灣的後殖民時期才正式降臨。
什麼是後殖民時期?正如前面所強調的,戰前的帝國統治與戰後的黨國支配,無論是政治結構、權力結構或文化結構,都受到嚴密的高度控制。所謂後殖民的「後」,指的是高壓統治結束之後,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所有想像力,都全部釋放出來。這種文化想像跨越了族群、性別、階級,使過去未曾有過的創造能量獲得高度提升。當複數的、異質的能量爆發出來時,無疑是對過去的威權統治進行了強烈批判。後殖民所強調的正是這種批判精神,一方面糾正過去單方面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則重新建構社會的文化主體。後殖民的主體重建,首要工作莫過於歷史記憶的恢復。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所寫的《台灣文學史綱》就不容忽視。這位跨語言的資深作家,縱然對於中文書寫並不熟悉,卻願意窮畢生之力建構一部文學史。那種勇氣與識見,已經成為後殖民史觀的典範。
後殖民史觀,並非是全盤否定殖民地時期與再殖民時期的文學成就。一九四○年代的皇民化文學,一九五○年代的反共文學,無論內容的差異有多大,其為殖民體制的產物則完全相同。當一個社會開始發展出主體的解釋,同時對於過去被支配的文學產物具有反省能力時,歷史便開始進入另外一個全新的階段。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的文學史觀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沒有經過他,後來的文學史研究可能就不是今天這種樣貌。台灣文學研究開始進入一個開放、多元、異質的時期,使過去曾經被遮蔽或扭曲的美學精神與藝術內容又重見天日。後殖民強調的是文化的差異性與主體性,同時也在於強調邊緣文化的重要性。所謂邊緣文化,指的是女性、同志、原住民的文學生產力;這些邊緣文化所蘊藏的生產力,絕對高於殖民時期的主流文化。
文學史的建構,必須緊貼著歷史發展的脈絡進行觀察。過去的殖民史觀,大多側重於統治者所偏愛的主流價值。這種主流價值指的是男性、漢人、異性戀,並且以這三個元素作為歷史解釋的全部。在建構所有的知識論時,也從來不會脫離這三個元素,並且以這種觀點來解釋整個世界。只要權力的結構沒有改變,以這種知識論為基礎的世界觀,也從來不會改變。必須是殖民權力被顛覆了,偏頗的知識論才會跟著被顛覆。人類歷史走得那麼遙遠而漫長,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思維方式。一旦殖民體制瓦解之後,男性中心論、漢人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才開始受到挑戰並質疑。後殖民史觀的浮現,正代表一個新的知識地平線逐漸上升。歷史舞台上的女性、同志、原住民,曾經無法站在聚光燈下。後殖民史觀便是把舞台上的所有燈光都打亮,讓黑暗陰影裡不同族群、性別、階級的角色,終於都接受了聚光燈的照射。後殖民史觀的作用,便是讓所有被遮蔽的歷史主角全部都站到亮處。進入後殖民時期,我們才終於發現過去的歷史是如此精彩,如此豐富,如此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