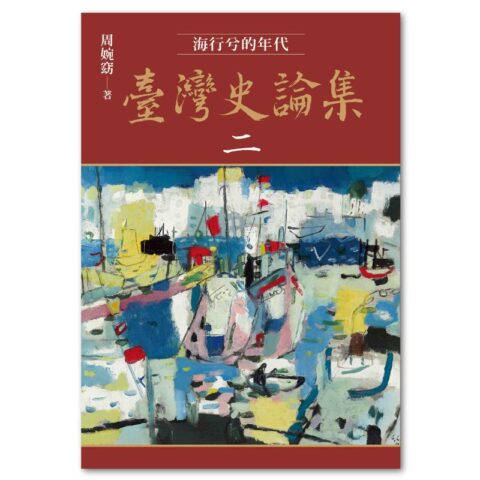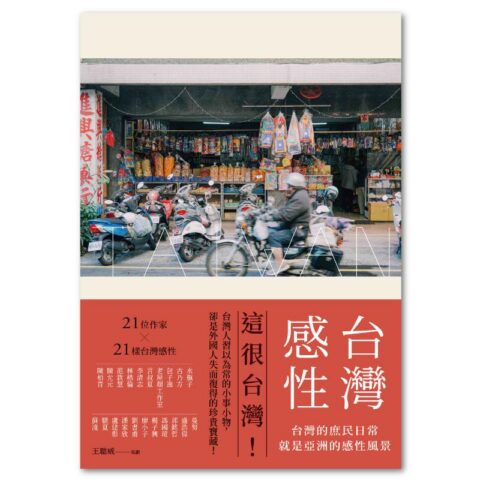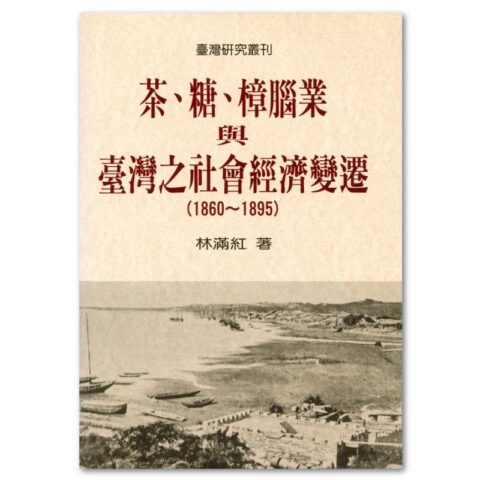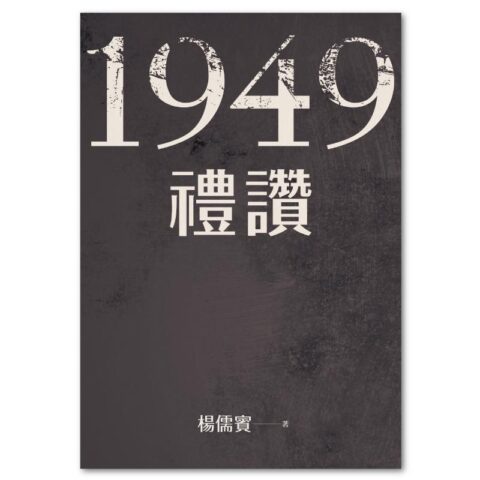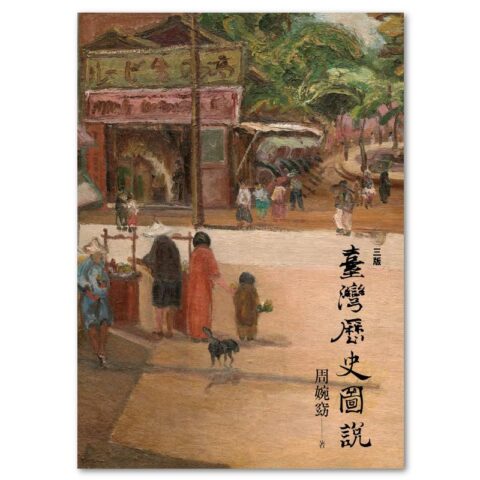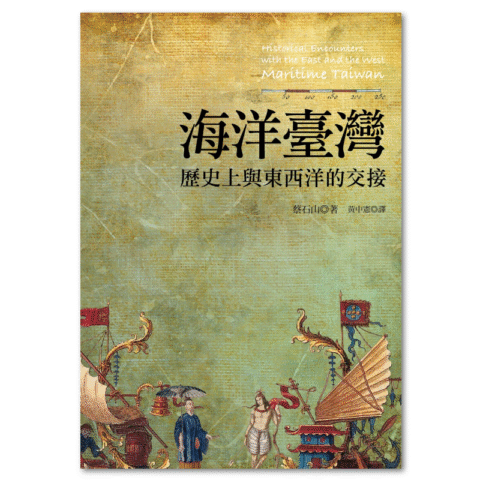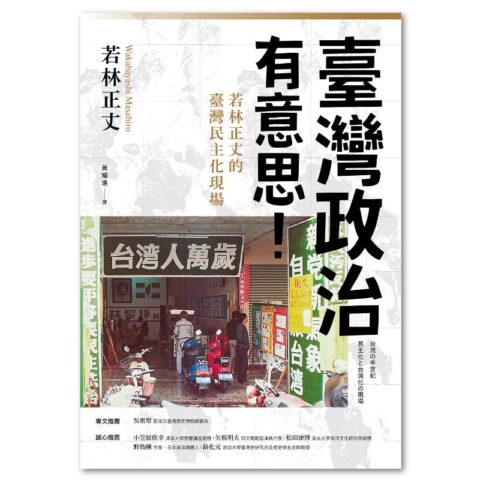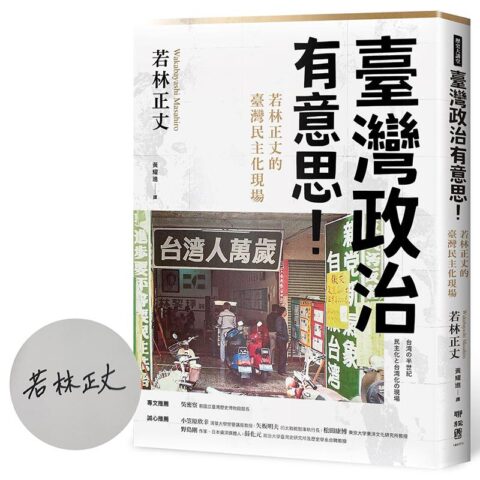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
出版日期:2003-08-03
作者:胡台麗
印刷:平版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67
開數:正25開
EAN:9789570825435
系列:臺灣研究叢刊
尚有庫存
在《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一書中,作者透過多樣性的文字書寫(學術論文、通俗散文與對話訪談等併陳)、民族誌影像紀錄、部落祭儀樂舞、和現代舞台展演等,探觸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深層意涵;並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地尋求人類學知識的社會實踐。在自由不受框限的嚐試中,本書作者與原住民文化交會,激盪出新的研究與實踐路徑。她也發現不同文化對展演的真實有不同的看法與詮釋,影響研究者、媒介者、演出者與該族群的互動。作者的喜怒哀樂在原住民文化脈絡中反芻,坦誠地呈現,是另一種文化展演。
作者:胡台麗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職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並擔任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理事長。著作有:《媳婦入門》、《婆家村落》、《性與死》、《燃燒憂鬱》、《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等。編導製作十六釐米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矮人祭之歌》、《蘭嶼觀點》、《穿過婆家村》、《愛戀排灣笛》等。
人類學者的熱情與社會實踐(代序)◆
●影像實驗篇1
民族誌電影之投影: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11
《蘭嶼觀點》的原點:民族誌電影的實踐49
對話錄一 《蘭嶼觀點》的多面觀點:試映會後座談59
(陳蓁美整理)
對話錄二 深入問題的核心:從《蘭嶼觀點》的眾聲中出發73
(田文玉整理)
愛戀排灣笛的真與幻101
迴響曲一 鼻笛情淚:影音追思蔣忠信先生109
迴響曲二 大安森林公園的笛聲117
(柯惠譯整理)
迴響曲三 思念的詠歎調137
(林宜妙整理)
●田野調查篇145
賽夏矮人祭歌舞祭儀的「疊影」現象161
五峰賽夏族矮人祭歌歌詞223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典儀式:現況評估279
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315
●歌舞展演篇413
文化真實與展演:賽夏、排灣經驗423
備忘錄一 矮人的叮嚀:寫於展演之前459
備忘錄二 從ulung tjavari到iaqu:排灣古樓的古調與傳說…簪471
從田野到舞台:「原舞者」的學習與演出歷程481
訪談錄 訪胡台麗談「原舞者」與原住民歌舞的舞台化505
(陳板訪問整理)
懷念年祭:紀念卑南族民歌作家陸森寶(Baliwak◆s)517
詞曲錄 卑南族民歌作家陸森寶(Baliwak◆s)作品選集525
(陳光榮翻譯說明、胡台麗整理)
人類學者的熱情與社會實踐(代序)
在人類學的圈子裡打滾這麼久,但是我很難講清楚人類學到底是什麼。我只能說我所期盼的人類學,絕對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知識理論建構的同時,有積極熱情的社會實踐意圖。我感覺人類學既然是人類學者取材於人群社會而建構出來的學問,理想上如經由人類學者的熱情和努力,人類學知識應能回饋人群而在社會實踐的領域有相當的發揮。
遺憾的是並非每一位人類學者具有實踐的動機、熱情和環境。人類學本身也不敢對人類學者提出超乎學術標準的要求。在台灣人類學界,多數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地分佈於台灣本土不同的族群社會,他們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完成資料收集與論文撰寫。這樣未始不能算是一種學術實踐,但是與我心目中與人群貼近的人類學社會實踐還有一段距離。純學術論文的知識如不經過另一層次的轉化推廣,只能在人數很少的學術圈中流通,很難主動地對社會傳佈,更無法讓社會大眾瞭解並產生影響。人類學的社會實踐是純學術工作的延伸,需要有很大熱情和耐力支撐。
我個人由於性向與興趣使然,因緣際會地參與了一些與台灣原住民和文化展演相關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活動。「文化展演和台灣原住民」這本書集結的文章,反映了我近十多年來以多種形式和身份與原住民文化接觸的樣貌。但它並不是單純的文字展演,讀者/觀眾在字裡行間、幕前幕後多少可以感受到我追求知識並努力實踐的熱情,以及遭逢的困難。
知識、熱情與實踐間的關係遠比我想像的複雜,如非親身試煉,實難體會其中奧妙。有些人類學者將研究工作「純」化,認為如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對研究工作會有負面影響。但我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常意外地發現,原先在循規蹈矩的田野研究中遍尋不得的族群文化精義,竟在無心插柳之際浮現眼前。我因此覺悟:人類學知識的追求與獲得沒有一定的公式與方法可循,「純」以撰寫論文為目的之學術性田野工作固然重要,但只能保證一定的資料累積,而未必能打開瞭解該社會的心鎖。人類學者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無論是順利或困頓,反而有更多機會觸及該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價值,得到珍貴的知識與情感回報。
通常人類學者一提到「文化展演」,就會聯想起包含許多視聽動感元素的祭儀樂舞,而祭儀樂舞的內容與形式分析便成為研究「文化展演」的學者之最愛。但我覺得人類學的「文化展演」概念如只運用於儀式的展演與類比未免太狹隘了,也極可能將所研究社會對於「真實」
與「展演」的區分掩蓋了。本書所談的「文化展演」雖然涵蓋台灣原住民社會的祭儀樂舞,可是「文化展演」的概念在本書中,並不限於原住民部落實際的祭儀樂舞展演,還包括其他在視聽方面表現突出的文化活動,特別是以視聽呈現為主體的民族誌紀錄片,以及原住民祭儀歌舞的舞台化展演。文化展演的內容與形式一方面是人類學研究和分析的對象;另方面則是透過文化展演,人類學知識得以傳播與實踐。
若與其他人類學論著相較,本書文章的呈現方式顯得多樣而紛雜。但與其說是缺點,毋寧說是有意顯現的特色。事實上,我對每一主題的切入、表達與實踐方式是文字書寫、影像紀錄、舞台展演等並用,無法只由文字的集結而窺得全貌;即使在文字表達的領域中,為了達到不同的溝通與傳播目的,我也嚐試採用不同的文體,而讓學術論文、通俗散文與對話訪談等併陳。在我的認知中,文字、影像與舞台展演等都是理念傳達與實踐的媒介,而每種媒介形式都有其優越和侷限之處,沒有必要作清楚的區隔。我以為人類學者應有足夠的自由度,在各種表現形式中作不同的嚐試。
著名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在「模糊的類型」( “blurred generes”,1980)一文中指出,現代知識的呈現在文類上有混雜的現象,例如寓言寫得像民族誌(Castenada的「唐璜的教訓」1968),理論的陳述寫得像遊記(Levi-Strauss的「憂鬱的熱帶」1974)。社會科學家如今應可隨心所欲地按照需要,而非遵循某些規定,來決定作品的形式。19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學界面對「再現的危機」(Marcus與Fischer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986),興起新民族誌的實驗浪潮。本書則企圖從人類學民族誌書寫類型的實驗再往前推一步,也就是人類學知識的社會實踐與反思。
本書的編排分為「影像實驗篇」、「田野調查篇」、「歌舞展演篇」三部分。在第一部份「影像實驗篇」中,我先針對民族誌和民族誌電影的「科學性」提出討論,我以為「科學」也像影像一樣被投射到民族誌上,我們誤以為它就是真相,結果發現只不過是另一種影像。當「科學典範」在人文社會學界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之際,藝術性的呈現方式受到鼓勵。人類學者在書寫和攝製民族誌時,不必再隱藏自己的情感和藝術表現風格,也比以前更關心作品要給誰看、對誰發生影響的問題。我非常認同Clifford Geertz的看法(1988「作品與生活」):殖民時代已結束,研究者、被研究者與讀者的關係應有所轉變,民族誌的呈現要使得三者之間有所對話。
我以自身在台灣所作的民族誌電影實驗為例,企圖破除過去僵化的、研究者高高在上的文字民族誌的呈現框架,希望透過影像,讓當地人直接發聲,並與其他多重聲音與觀點對話。民族誌影片必須讓當地人意識到對他們「有用」,能真切的表達他們的情感、美感與需求,而不是只服務於學界所關心的某些理論建構。在沒有文字的原住民社會,我覺得影像民族誌更能發揮溝通與傳承的功效,因此迄今我所拍攝的五部民族誌影片中,除「穿過婆家村」(1997),其餘都是以原住民社會為題材:「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1984)、「矮人祭之歌」(1988)、「蘭嶼觀點」(1993)、「愛戀排灣笛」(2000)。
本書中對於這四部分別在台東的排灣族、新竹的賽夏族、蘭嶼的達悟族(雅美族)與屏東的排灣族地區拍攝的民族誌影片,在內容、形式與實踐方面有較多的描述。這些影片完成之後都有在拍攝的村落中放映,攝製者並與被攝者和觀眾對談,產生多層次的激盪。我一直無法忘懷「蘭嶼觀點」一開頭,島上青年si Pozngit在沙灘上說的一段話:「我常常覺得一個人類學者在這個地方做的研究越多,對雅美族的傷害就越深。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我常常覺得人類學者在蘭嶼做研究,只是把蘭嶼當作是他晉級到某一個社會地位的工具而已,並沒有回饋給他們研究的對象,這是我覺得非常遺憾的地方。」人類學界對這樣的批判能做出怎樣的回應?在「蘭嶼觀點」的原點與《對話錄》,以及「愛戀排灣笛」的《迴響曲》中,讀者會發現我嚐試透過影像和推廣活動,讓人類學知識發揮社會實踐的效用,以期對文化的溝通、傳承與省思作出貢獻。參與影片攝製與觀賞的原住民與觀眾都有其主動積極性,和人類學者處於平等的地位,相互鼓勵和學習。
本書的第二部份為「田野調查篇」,其中收錄了四篇文章,包括對賽夏族矮人祭歌舞祭儀「疊影」現象的分析、對祭歌歌詞的詳細記錄與譯註、對台灣原住民祭儀與排灣笛的現況調查與評估。雖然有些工作例如對矮人祭歌歌詞的紀錄與整理是極為艱難繁瑣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唯有經由祭歌「文本」的細密解析,再配合祭儀「文化展演」活動的實地參與觀察,我們才有堅實的資料來揭示賽夏文化記憶中特殊的「疊影」現象,並有助於珍貴祭歌的傳承。當我發現賽夏文化不能以觀看單一影像的方式而必須以「疊影」概念來理解時,那種驚訝與揭密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矮人祭」指涉的不只是矮人,也包括同樣與賽夏族人有恩怨關係的雷女。賽夏族的祭歌與祭歌中的植物都有深刻的含意,一方面是對生命脆弱性的警示與哀惋,另方面則是對生命堅韌茁長的強烈慾求。「疊影」現象強調的是賽夏族人在自然與人文生態環境中一直要面對的生產與生殖、己群與外人的主題,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
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祭典儀式:現況評估」一文中,我們針對不同類別的祭儀在各族的保存現況進行調查,並探討1945年之前與之後祭儀消失與轉變的原因。結果我發現,祭儀消失的主因係受到外界優勢文化包括日本殖民文化、漢文化、西洋宗教等有意識與有組織地打壓。
不論其理由是為「革除迷信惡習」、或「改善生活」、或「給予救贖」,都相當程度地流露出這些外來文化的優越心態,貶損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自尊。近期部落祭儀的發展也仍然無法擺脫外力的干擾,常淪為觀光與官式「表演」的性質,以至於祭儀歌舞原有的文化意涵受到扭曲或隱沒不彰。在「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文章中,我們經過地毯式的搜索後,訪問了30位鼻笛與口笛人才,並釐清了排灣笛的傳承系統、文化意涵與保存現況。後來還出版了「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一書和「笛聲淚影」CD專輯(200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為已趨凋零的排灣笛的傳承、以及排灣族的情感與美感研究奠基。
本書的第三部份為「歌舞展演篇」,以我參與「原舞者」後所經歷的展演活動為重心。早在1986年到1989年,我便與劉斌雄先生共同主持「台灣土著祭儀暨歌舞民俗之研究」計畫(1987出版第一冊報告書,1989出版第二冊報告書),邀請不少研究人員參與。當時負責舞蹈研究的平珩,於研究告一段落時便根據採集的資料,同時敦聘阿美族和鄒族人,教導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學生祭典歌舞,並搬上舞台展演。後來一個源於台灣南部、由原住民青年組成的「原舞者」團體,在藝文界熱心人士支持下,以藝術學院演出過的歌舞節目為基型,進行全省巡迴演出。這些原住民團員到台北演出時,他們的聲音與動作中所流露出的濃厚原住民山林原野氣息,深深地感動了我。從1991到1996長達六年的時間裡,我成為「原舞者」的義務研習與展演指導,協助「原舞者」成員進入不同的文化田野,學習傳統歌舞祭儀,並轉化為現代舞台的演出。這樣的結緣過程記錄在「從田野到舞台:﹃原舞者﹄的學習與演出歷程」
與訪談錄中。
「懷念年祭」是「原舞者」第一個田野學習與展演的主題,將卑南族傳統猴祭、大獵祭的歌舞,以及該族近代傑出民歌作家陸森寶創作的歌曲作有系統的編排組合。「懷念年祭」是陸森寶最後一首遺作,歌詞經過陸森寶女婿陳光榮先生的翻譯,透露老人家希望年輕人不要忘記傳統年祭的心願,感人至深。我們請陸森寶的孫子陳建年為創作民歌配上具原住民風味的樂器伴奏。近年陳建年獲得了「金曲獎」最佳演唱者與最佳詞曲作者的榮譽,相信當年「原舞者」的舞台展演對他產生相當程度的激勵作用。我在1992年「原舞者」於台北社教館演出前寫了一篇「懷念年祭:紀念卑南族民歌作家陸森寶(Baliwak◆s)」,對於他每首作品的產生都與卑南族南王村的生活與發展息息相關,表達無比的讚嘆。這些作品的詞曲與背景介紹附皆在「詞曲錄」中,供我們緬懷歌詠。
當我書寫「文化真實與展演:賽夏、排灣經驗」一文時,情感與思緒洶湧起伏。在此文中,我不毫不隱瞞地將我與「原舞者」學習和展演排灣族及賽夏族神聖祭儀歌舞的刻骨銘心經驗,透過文字再度展演出來。我終於體認到:僅管我們的出發點是多麼的良善、行事是多麼的審慎、社會實踐的熱情是多麼的澎湃,但有些事的演變不是我們所能預料和掌控的。譬如,「原舞者」經過一年多敬謹與專注的學習,1994年賽夏族矮人祭歌舞在國家劇院的演出可謂空前地成功,可是其後卻發生了讓我難以釋懷的賽夏族主祭妻子去世的事件。在難過之餘,人類學的訓練幫助我探索並反省「社會實踐」與「文化真實」之間的關係。
我們如果將「原舞者」在賽夏族與在排灣族的學習與演出經驗對照,便可發現二族對文化真實與展演有不同的理解。賽夏族的「疊影」視角,讓他們習於將外人融入自身的文化中,並將外人的「展演」視為自己人的真實「演出」,必須受賽夏規範的約制;如有違犯,無論是自己人或外人都會受到矮人等老前輩的懲罰。研究者或展演者在這樣的文化中進行「社會實踐」,有其優點也有其危險處。優點方面,這些年來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了:當初賽夏族南祭團中只有一、二位年輕人會唱矮人祭歌,之後受到「原舞者」的刺激並透過自身的努力,如今會唱祭歌的賽夏年輕人不斷增加,矮人祭的三個通宵已有十餘人分組輪流帶唱,使得神聖的矮人祭歌舞傳統得以維續不墜。可是另方面,「外人」的混融現象也可能增加賽夏族人的內在壓力,甚而危及賽夏族的內部秩序。萬一不幸事件發生,「外人」必須懂得運用賽夏族的化解之道。不同於賽夏族的「交融性」文化真實,我們在排灣族經歷了「區隔性」的文化真實,亦即「外人」絕對不可能被排灣村落視為「自己人」,因此外人的學習和展演不必遵從排灣文化禁忌。相對的,外人也不容易直接參與排灣村落活動,無法對它產生重大影響。我認為任何有「社會實踐」意圖的人,不能不努力理解他所處環境的「文化真實」。
透過不同形式的文化展演與社會實踐的辯證對話,在本書的篇章中,我不是一個冷眼旁觀、保持距離的客觀分析者,而是熱情地、積極地參與了文化展演。其中有淚有笑、有滿足也有辛酸,在此毫無避諱地一併呈現在讀者眼前。我同時也期盼讀者加入「演出」,為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研究、傳承與展演注入源源不斷的創意與活力。
民族誌電影之投影: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影像實驗篇影像實驗篇民族誌電影之投影: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民族誌電影之投影:
兼述台灣人類學影像實驗 一「我對於以電影作為科學性人類學傳達工具之價值甚表懷疑。」I. C. Jarvie 1983年在“Current Anthropology”雜誌上毫不容情地提出批判,反對電影與人類學結合。因人類學在他的認知裡是順應理論之需要而展現真實(reality),而影片拙於辯證性地呈現材料,使得理論與思想觀念難以進展。他指出影片製作者與人類學家的目標可能不同,前者主要處理的是具有想像力的視像,後者則懷抱審慎、精確、質疑等科學態度,如果湊合在一起雙方都不會滿意。Jarvie並認為影片充其量也不過是輔助性的紀錄工具與視覺教材,大多數民族誌影片的說明性不足,對民族誌沒什麼貢獻。
我也曾經產生過這樣的懷疑。在我接受人類學訓練的1970年代,「科學」的典範仍強有力地支配著人類學領域,影片的最大功用是在為科學研究服務。民族誌影片正如Jarvie所述有許多「不夠科學」的缺憾,嚴肅的人類學者多不予重視,更不會鼓勵學生往這方向發展。
我的正規人類學教育裡從未包括民族誌電影這一科目。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重新看了一遍Robert Flaherty(佛萊賀提)1922年完成的影片“Nanook of the North”(北方那努克)。我記得很清楚這是我在紐約唸研究所時無意中看到的一部默片經典作。“Nanook”這位愛斯基摩人的影像一開始是以面部特寫鏡頭出現,他的眼睛一眨動把我帶入他生活的冰天雪地的世界。投射在平面銀幕上的立體影像給予只熟悉文字記載的「原住民」的我極大震撼,科學性的民族誌從來沒有讓我這麼真切地體味到另一個文化的氣息。影像與文字、科學與藝術、人類學和電影自此在我的思考中徘徊不去。看“Nanook”影片產生的激動餘波蕩漾,促使我後來拿起攝影機拍攝,拿起筆寫這篇檢視民族誌電影發展的文字。
“Nanook of the North”是不是一部民族誌電影?無疑地它是紀錄片史中不朽之作,而所有談民族誌影片的書籍文章都會提到這部片子,但對於它是不是民族誌電影卻有爭議。Flaherty不是一位人類學家而是礦藏探勘者,1913年起便在加拿大哈德遜灣東岸Inuit愛斯基摩人的活動區探測鐵礦,與當地人共同生活,並拍攝影片。1920年開始拍攝的“Nanook”一片企圖呈現人類如何在荒寒酷劣的環境中奮鬥以求存活。1922年產生了這部電影史上第一部真正可稱為紀錄片的電影。有趣的是人類學史上也是在1922年出版了第一部民族誌經典之作: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自此才奠立了人類學田野工作以及書寫民族誌的基礎。就嚴格的「民族誌」定義來看,“Nanook”並不是在人類學的理念與訓練下拍攝的片子。Flaherty長期參與觀察Eskimo社會,並得到Nanook的信任與協助拍攝這部影片。從Nanook及其家人的活動中,我們看到Flaherty所欲表達的北方的憂鬱精神,永遠為風雪、狗吠、饑饉的氛圍所籠罩,但是在荒寒中人們還是流露出相濡以沫的溫情。
什麼是民族誌?什麼是民族誌電影?馬林諾斯基的功能理論今日人類學界少有人信服,Adam Kuper便提出:馬林諾斯基的卓越處不在於理論,而在於他能穿透理論之網觸到真正的人(1985:{35})。馬林諾斯基自己也在田野日記中問道:我探究的最深意義何在?——發掘當地人的主要情感、行為動機以及目標(1967:{119})。可是他只願意在不準備發表的田野日記中發抒自己的情感以及對當地人不同的評斷。換言之,筆寫出版的民族誌基本上是客觀不摻雜研究者情感的科學性民族誌。不過馬林諾斯基顯然察覺到一些科學研究的問題:
某些科學性研究結果……只給我們美好的骨架……卻缺少血肉。我們習得許多有關該社會框架的知識,但無法感知或想像人們真實的生活:日常事件的平穩流動或者是偶爾發生的祭典等狀況激起的興奮漣漪。我們從田野收集的資料與報導人的訪談中建構出當地習俗的律則與精確公式,但會發現與真實生活無關,因為真實生活從不僵硬地附著於任何法則上面(1922:17)。在討論何謂民族誌電影時,Karl Heider避免用是/否的二分法,而以民族誌的強弱(ethnographicness)來判斷。但是他認定的「民族誌」是科學事業(scientific enterprise),電影只是工具,科學的民族誌才是目標。如果民族誌的科學要求與電影的美學要求發生衝突,民族誌電影要重科學而犧牲美學(1976:4-5)。類似的觀點出現於Jay Ruby(1975)的文章中。他主張民族誌影片要儘量符合科學的民族誌的標準,無論在方法上以及資料的收集分析上,都要具科學的邏輯和理論意涵。影片作為溝通的媒介與技術,必須將科學的論述傳達出去,而大多數的民族誌電影在他看來未能達到這效果。雖然所有的影片都可供人類學研究分析之用,但不應隨意冠上「民族誌」電影之名。
民族誌和民族誌影片真的是以「科學性」為優先的考慮嗎?{1980}年代人類學界掀起洶湧的反擊浪潮,其背後形成的原因係與科學典範在整個人文社會學界廣泛遭質疑的思潮發展有關,本文不擬詳加討論。「科學」也像「影像」一樣被投影到民族誌上,我們誤以為它就是真相,結果發現仍然只不過是另一種影像。以往在科學準則指導民族誌的時代裡,並非所有的民族誌作品都以透明中性的科學語言與形式呈現,但是比較藝術性的呈現方式並不受鼓勵與重視,「E. Sapir 和R. Benedict在F. Boas的科學凝視下必須把他們的詩隱藏起來」(Cilfford 1986:4)。書寫民族誌的文學性和風格在晚近的討論裡才出現,民族誌被當作文本 (text)與作品來評析。Clifford Geertz(1988)明白地指出:人類學作品不應以是否合乎「科學」標準之先入為主的觀念作評斷。科學要求客觀與不顯現研究者的情感,結果人類學者面臨必須將帶傳記性的田野經驗轉化為科學的作品時,常顯現出焦慮不安。不過Geertz檢視了 Malinowski、 Levi—Strauss、 Evans—Pritchard、 Benedict等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民族誌後發現,他們作品中的理論辯論力量如今已消失,但人們依然樂於閱讀。追究原因是由於這些作品的呈現具有特殊的文學風格,令讀者相信研究者確實溶入另一種生命形式。民族誌的文學性格,人類學者的作家角色不容忽視。
此外,民族誌的寫作到底是給誰看的問題也被提出來。過去人類學者以西方學界關心的理論帶到殖民地的田野去印證,完成的民族誌出版後也只在學界閱讀討論。Geertz認為殖民時代如今已結束,研究者、被研究者與讀者的關係應有所轉變,被研究者不只是被描述的對象,讀者不只是被動的被告知,民族誌的呈現要使得三者之間有所對話。科學的修辭、科學的面具在後殖民時代不再適合,民族誌的寫作要注重風格與美學,把一個群體的意識適切地傳達給其他人群。近些年愈來愈多的民族誌擺脫科學金箍咒的束縛,嚐試以更自由、更合乎人性的方式書寫,舊有的規範與權威在崩解中(Marcus與Fischer 1986)。
這類對民族誌的反省與我長期以來的感觸不謀而合。在第一個田野工作結束要寫論文時,我就產生是否要符合「科學」規格的矛盾,結果還是順應內心的要求,以小說形式先寫了一篇《媳婦入門》(1978),後來再逐漸發展論文的其他部分(1982,1984)。論文草稿完成重返美國的一年中,我不能忘懷文字之外影像給我的震撼,修改論文之餘全力投入電影理論與技術的學習。在藝術電影院、電影系、課堂、影展和電影圖書館中觀賞電影史上的重要作品,也包括不少民族誌電影。整體的感覺是民族誌電影還處於摸索的階段未臻成熟,而且過去在民族誌的「科學」要求與電影的「美學」要求中掙扎,步履維艱。不過由於影像確有文字無法企及的某些優越性,民族誌電影在人類學界已取得一席之地。讓我們概略回顧一下它發展的歷程。
二前節已敘述民族誌電影一直受「科學」的研究取向與書寫形式的影響。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真正成為民族誌電影必須是有結構的,經過影像資料之選取剪輯過程,像正式出版物一樣可供人「閱讀」、評賞的作品。民族誌電影於是無可避免地受到電影理論與形式之影響。
幾篇描述民族誌電影發展史的文章(De Brigard 1975; Heider 1976; Mac Dougall 1978; Chiozzi 1989)都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談起,但是早期的所謂民族誌影片實在只是毛片(footage)而不是經過組合、結構的電影。它們如同人類學家在田野紀錄的筆記資料,還沒有寫成文章發表。可是由於早期影像之攝製非常稀少珍貴,後來也有人將毛片整理發表作為研究和教學之用。基本上這些毛片的攝製目的都是為科學研究分析之用,只不過是收集的資料而已,並沒有以影像作為研究結果予以呈現的意圖。
一般認為Felix—Louis Regnault(赫格惱)是最早有系統地使用電影做人類動作研究並建議設立人類學影片資料檔者。1895年電影機剛發明不久,這位對人類學有興趣的病理解剖醫生,便用影片紀錄一位Wolof婦女製陶的影片。同一年度電影之開創先驅盧米埃兄弟(Auguste Lumiere與louis Lumiere),將攝製的影片作第一次商業試映。亦即電影之紀錄人類行為以供研究之價值(Regnault並紀錄比較分析不同文化的蹲、走等動作)在電影產生之初就受到注意。接著便是1898年Alfred Cort Haddon 在英國劍橋人類學Torres海峽探索之行中,拍攝了一些當地居民生活的毛片。Haddon又鼓勵Baldwin Spencer於1901年研究中部澳洲以及1912年在北部澳洲時用攝影機紀錄,共拍攝了七千多呎民族誌毛片。另一位Haddon的同事Rudolf Poch於1904年及1907年在新幾內亞及西南非以影片紀錄。De Brigard認為1930年代Mead與Bateson攝製影片之前,人類學家拍攝的片子雖有保存文化之價值,但在觀念上都沒有什麼創新。
Margaret Mead(米德)與Gregory Bateson(貝特生)1936—{38}年在印尼的Bali島做有關文化與性格的研究。他們對於視覺人類學最大的貢獻在於使照片與影片成為人類學研究與成果報告的重要部分。他們在自然狀況下大量攝取影像,經過選取編排後,影像不再是文字的附屬品而在人類學研究中贏得尊重。他們運用影像來消滅以往對Bateson文字分析過於抽象,以及Mead文字描述流於主觀印象化的批評(1942)。Bateson拍攝的22,000呎毛片由Mead剪輯,1950年才以六部短片的形式發表。這些影片從兒童之間與兒童與成人的互動中顯示Bali人的性格,其中尚包括Bali與新幾內亞Iatmul部落兒童養育行為的比較。Bateson與Mead在研究過程拍攝的毛片,透過剪輯配音成為供大眾觀賞的影片,讓觀眾瞭解他們的研究主旨與主要發現,可作為研究民族誌毛片提升為民族誌影片的範例。然而若以電影的美學標準來評斷,Mead剪輯的影片遠遜於Flaherty 1922年拍攝的“Nanook”。Mead文字上顯現的才華並沒有在影片上發揮。
1950年以後攝製的民族誌電影受紀錄片美學影響較深,有不同的發展。某些影片呈現的形式與風格相當具創新性,甚至凌駕民族誌的內容成為討論的焦點。其中以法國民族誌電影作者Jean Rouch(胡許)的表現最傑出。他四十餘年持續不懈的努力完成許多藝術評價極高的民族誌電影,將藝術與科學、劇情片與紀錄片、真實與超現實、文字語言與影像之間的樊籬拆除,無論對電影或民族誌在觀念及方法上都有深刻的刺激與啟發。
Rouch在人類學方面最主要的指導者是Marcel Griaule。不過他原先專長數學與工程,1941年二次大戰期間前往西非擔任堤防與橋樑工程師,因接觸當地文化發生興趣,返回法國就在Griaule鼓勵下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Griaule學派」的民族誌包含三個特性:長期的田野工作(Griaule本身在非洲Dogon族做了三十年田野),對收集實物和影像資料十分狂熱(Griaule本人也拍攝影片),強調人類學家在長期的戲劇性的田野過程中需經過「入會」體驗,讓當地人引入文化的奧妙殿堂(Clifford 1988)。1946—47年以及1949年,Rouch在西非Niger的Songhay部族做研究,後來共寫了三本民族誌:“Les Songhay”(1953)、“Contribution a l′Histoire des Songhay”(1953)、“La Religion et la Magie Songhay”(1960)。前兩本是關於Songhay社會各個層面以及歷史的敘述;第三本專注於宗教與巫術的探討,對神話、儀式與神靈附體等有十分細密的描述。但是Rouch不喜歡直接探討理論,只不著痕跡地隱含在章節文句中。如今閱讀Rouch書寫民族誌的人很少,一位法國人類學研究生告訴我:「現在學生不喜歡讀民族誌,但大家都看過Rouch的民族誌電影!」
Rouch自認電影方面對他影響最深的是1920年兩位紀錄片先驅:美國的Robert Flaherty(佛萊賀提)與蘇聯的Dziga Vertov(弗爾托夫)。Flaherty代表作“Nanook of the North”中包含了極有創意的「參與攝影機」(participant camera)與回饋(feedback)作法,合乎Rouch「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的理念;Vertov這位未來派的詩人以攝影機攝取真實生活的片段,提出「電影眼」(cine—eye):攝影機的機械眼不斷地移動,「看」和「寫」下真實,但這些真實的片段必須「組織」(選擇)成視覺上有主題、有意義、有韻律的秩序。Rouch認為Vertov的「電影眼」是有生命的攝影機,攝製影片者要隨攝影機進入「電影恍惚狀態」(cine—trance),他不再只是他自己,而是一個機械眼伴隨著一個電子耳,真正地進入被攝對象的世界(Rouch 1975)。
Flaherty與Vertov在電影史上的重要性,在於為Lumier起以影片紀錄真實生活的紀錄片電影類型奠立堅實基礎。Vertov最為人熟知的影片“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拿攝影機的人)便是「電影眼」的實驗作品,期望建立一種真正的國際電影語言,有別於依賴劇本演員與道具的劇情片(Vertov 1928)。Vertov稱這類影片為Kino Pravda(真實電影),Rouch與Morin 1962年完成的著名紀錄片“Chronique d′un Ete”(夏日紀事)是獻給Vertov的新「真實電影」(法文譯為cinema—verite)。不過他們都認為紀錄片捕捉的「真實」並非客觀的真實,而是經過攝製者主觀選取組織的真實。Rouch的民族誌電影便呈現強烈的個人風格,甚至有人撰文討論他影片的「民族誌超現實主義」(ethnographic surrealism)色彩(Jeanett DeBouzek 1989)。我們可以幾部影片為例來瞭解他的表現方式與特殊貢獻。
“Les Maitres Fous”(瘋狂主人 1953—54)是Rouch連串有關西非Songhay族神靈附體影片中引發最多爭議的片子。Rouch曾在Niger的Songhay聚落拍攝巫術與附身的影片,這部片子則是紀錄移民到Ghana城市Accra的Songhay人一年一度的神靈附體儀式。Rouch把整個儀式的戲劇性與嘲諷性表露無遺,附體的神靈是一組殖民政權下產生的角色,而被附身的Songhay人則藉瘋狂的儀式化解他們現實生活的鬱結。Rouch喜歡運用戲劇性高潮結構和故事敘述情節來呈現影片。Rouch為影片作的旁白也極富實驗性,《瘋狂主人》是他第一次試著將他對此儀式的直接觀察、「科學」訊息、學術解析、內心反射、對話詩意翻譯等拼貼起來,在不看講稿的情形下作旁白,如同他被影片「附身」了,進入恍惚狀態。在另一部紀錄Songhay巫師附身的影片“Tourou et Bitti”(1971)拍攝過程中,Rouch發覺攝影機成為攝影者之延伸,不僅舞動的巫師為神靈附身,攝影者也被「附身」,經驗「電影恍惚狀態」。Rouch的民族誌電影是「真實」也是「想像」,是接近「科學小說」的「主觀科學」。所謂「民族誌超現實主義」便是一種特殊的心靈狀態,將不同的文化符碼、怪異和尋常物件並置,以顯露另一個層面的真實——超現實。《瘋狂主人》一片包含Rouch拍攝與旁白時無意識心靈運作的面相,將多種元素並置,產生令人惶惑的綜合體,也因此刺激新的思想,向「真實」與「理性」挑戰(DeBouzek 1989)。
“Chronique d′un 霈t◆”(夏日紀事 1962)這部Rouch與社會學家Edger Morin合作的影片成為紀錄片史上經典之作。1960年他們首度試驗使用可與十六釐米攝影機配合、攜帶方便的同步錄音機,更接近Vertov理念中的真實電影,是直接紀錄下真實人生聲音與影像的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讓他們得以自由走上巴黎街頭當街訪問,探索1960年夏天(Algeria戰爭尚未結束,法屬非洲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巴黎人的心靈。這部影片最引人興味的是觀察之外,積極參與的拍攝方式。攝製者與被攝者有許多互動,Rouch和Morin毫不避諱他們介入者的角色,進而讓這角色產生觸媒作用,刺激被攝對象有所反應,無意間顯現他們平時不輕易示人的心靈真實面。參與(participation)和反思(reflexion)的精神在《夏日紀事》中十分突出,研究者(攝製者)與被研究者(被攝者)之間的距離拉近,互為主體,在即興隨意間捕捉生活的真實,必要時演出真實(staging reality)。此片並且有被攝者觀看影片與攝製者討論、發表評論的鏡頭。Rouch認為當年Flaherty拍攝“Nanook”時就建立了參與、回饋、分享的典範(Barnouw 1974;Rouch 1975;Feld 1989)。
Rouch以文字書寫民族誌時,大致遵守科學性學術論著的規範,把自我隱藏起來。可是當他以影像作為表達工具,以攝影機代替筆紀錄時,則大膽地讓個人的主觀性與想像力充分發揮。
Flaherty與Vertov事實上並沒有那麼有意識地提倡「參與的攝影機」與「電影恍惚狀態」,而是Rouch個人做人類學田野的體驗及理念的發揮,並且這種理念在書寫的民族誌中並未體現。Rouch成功建立的民族誌影片風格有違「科學性」書寫民族誌的傳統。幸而電影已發展成對風格、主觀性與美學相當尊重的藝術,使得Rouch在處理影像時擺脫成規束縛,讓自我解放,嚐試達成分享的、人性的人類學理想。他的作品對紀錄片及法國新浪潮寫實主義劇情片產生極大的衝擊。他在電影界享有盛譽,反而是人類學界未能普遍體認他的貢獻。不過從事民族誌電影攝製者都公認他是最有創意、成就最大者。1981年法國為他舉辦電影回顧展,接著歐洲其他幾個國家、非洲Niger及美國都有類似活動。他長期間擔任法國電影圖書館主任及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之職,仍不斷有新的電影作品發表。
美國方面Mead與Bateson之後民族誌影片發展有限,一直到1950年代才活躍起來。哈佛大學人類學系Peabody博物館設立影片研究中心,由Robert Gardner負責,協助1951年起跟隨家人在西南非Kalahari沙漠收集資料,並累積數萬呎毛片的John Marshall剪輯“The Hunters”(獵人 1956)影片;1961年Gardner本人帶領博物館探險隊前往荷屬新幾內亞的Dani族做研究同時拍攝影片,{1963}年完成“Dead Birds”(死鳥)這部關於Dani戰爭的片子。這兩部民族誌電影研究教學時廣受歡迎,可是在觀念和技法上並沒有什麼突破。同步錄音技術一直要等到1960年代中期以後才較普及,這之前的民族誌影片大多仰賴旁白說明,觀眾聽不到被攝者的現身說法。同步錄音、讓人物在事件中自然言語動作、不用旁白只加字幕翻譯以顯現文化意義之影片,要以David MacDougall的作品最具民族誌說服力,代表作有“To Live with Herds”(1972)。另外,Timothy Asch與Napoleon Chagnon合作拍攝系列南美Yanomamo的民族誌影片,有些事件例如“The Feast”在剪輯時嚐試先用靜止畫面及圖表作民族誌內容解說,再以正常速度不加旁白地呈現,以求彌補影像無法充分表達意涵的缺點。另外有Sol Worth與John Adair訓練印地安人自己攝製自身的文化,表現不同的影像拍攝觀點。Asen Balikci等人的Netsilik Eskimo影片系列是以影像紀錄重塑傳統生活技術面,此種表演式的拍攝法,早期Flaherty與Franz Boas都曾使用過(Heider 1976;Chiozzi {1989})。
德國方面的民族誌電影主要由位於G蜷ttingen的科學電影所(Institut f◆r den Wissenschaftlichen)提倡。拍攝的影片走的是嚴謹科學紀錄路線,避免戲劇性的鏡位移動與剪接。1952年這個機構建立了第一個有系統的人類學影片資料檔,供比較研究之用(De Grigard {1975})。
《蘭嶼觀點》的多面觀點:
試映會後座談陳蓁美整理繼《神祖之靈歸來》、《矮人祭之歌》之後,胡台麗以人類學者的涵養,新近完成一部關注蘭嶼現代面臨的問題的紀錄片《蘭嶼觀點》,片中探討了觀光、醫療、核廢料等問題,試圖以蘭嶼當地人的立場抒發出來。
1993年雙十節前夕,中研院民族所舉行了兩場試片與座談會,分享他們的拍攝心得。主要人士包括策劃、導演胡台麗(胡)、蘭嶼知識青年施努來(施)、郭建平(郭)、布農族醫生田雅各(田),以及攝影師林建享(林)。其他與會並表達了意見的人士包括民族所內研究人員劉斌雄、蔣斌、黃智慧等人,關心原住民文化的人士:孫大川、謝世忠、丁松筠神父、虞戡平等,以及蘭嶼青年學子。
《蘭嶼觀點》提出問題,引發與會人士熱烈討論。在大家提出心得、疑問及鼓勵時,我們紀錄下來。以下是內容摘要。上什討論部份施:時間的累積讓我成長了很多,在蘭嶼島上四年的生活,讓我從影片中真正認識到我的族群,包括我在內,是如何生存。開始進入傳統工作生活之後,我才發現自己真正是一個人。
在台北的十多年是我最荒唐的歲月。看了影片之後,給我很大的啟示:未來,在為自己的同胞、為自己小孩的求生過程中,有了很大的「太陽」吧!
在這部影片裡,除了讓觀者感受到他們還有這樣的生活,發自內心去同情這樣一個族群時,其中歷史背景的因素,以及蘭嶼人無法在短時間之內適應社會的變遷,是最讓我思考的地方。
前些日子,胡台麗問我要不要來,本來不想來的,因為想趁最近好天氣多打些魚。今天看了試片,覺得很值得。
田: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童年也是這麼快樂。慢慢地,接觸到漢人社會,布農族就漸漸消失了。後來和幾個朋友一起用文字呈現自己的民族,然而文字呈現出來的多少與實際有些出入;就好比我們讀某些資料時,以本身既有的立場來看,這裡邊一定有些偏差,以漢人的眼光看,我們也絕對有些偏差。
我一直覺得影像不能那麼深入表達意念。《蘭嶼觀點》在這麼有限的時間裡,或許無法將蘭嶼的全貌完全表達,但如果用心去看,可以有個深刻的了解。
《蘭嶼觀點》只是台灣原住民的一個縮影,在日月潭、阿里山的原住民也面對觀光的不平,政府很多施政措施就像核能廢料一樣,是用欺騙、強制達成目的。
我滿高興的是,從這部片子可以看到台灣政府為原住民社會做了些什麼,雖然只呈現蘭嶼一個小島,也呈現出很多可供我們思考的東西。
林:第一次搭乘往蘭嶼的飛機,很害怕,後來卻演變成擋不住的想法。能夠順利完成這個工作,我真的相信是雅美的神眷顧我這個漢人。
胡:影像是有限的。在台灣紀錄片裡,七十五分鐘算很長的了,可是,依然有很多未盡之處。
基本上,我是策劃,並未主導整部影片。這次的拍攝工作,跟以前作人類學田野研究工作的心情不同,跟以前拍攝祭典的影片的心情也不太一樣。為什麼我敢涉入一個未曾做過長期研究的點,甚至這個點曾經是我最不願用影片表達的地方?
我有個機會去參觀蘭嶼退輔會的農場,發現農場的確給當地人很大的壓迫,而政府似未意識到自己造成的壓迫。雅美人的觀點認為是無理的強占土地,而且還威脅到他們的生計。
其實,根據日據時代的文獻記載,蘭嶼非常早就為人類學者所發現,蘭嶼也是最早有最傑出影像表現的地方。從日據時代起,到劉斌雄先生、衛惠林先生等,蘭嶼一直是為人類學家記錄、研究的島嶼,但這些研究沒有辦法直接觸及他們希望外界聽到的聲音。前人已作過很多研究了,站在這個基礎上,我能做什麼呢?可能就是怎麼樣藉一部影片讓蘭嶼的聲音發出來。
在這部影片裡,我不能避免地摻入自己的觀點。怎麼樣選擇畫面的內容而不扭曲原意是需下一番工夫的;初剪完畢時,請他們先行觀賞,除了呈現他們的觀點,我們也在思考如何輔助這些觀點的呈現。
難得的是,努來、建平等人的觀點都很強烈,跟我們人類學者所關懷的方向一致。當初問他們為什麼要抗議核廢場,他們回答:「跟政府官員談的時候,他們都以﹃你們不了解什麼叫做放射性﹄為托辭。可是我們又不是科學家,為什麼要了解!問題是它的確造成我們心理的困擾,給我們和諧的生活帶來不安。」
所以影片的表現上加入一些他們生活的內容,像漁撈耕作和祭典儀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如詩人般的吟唱,與大自然一致的節奏感,這是一般文字記載很難表現的。很盼望這部影片能呈現這個民族的美。
劉斌雄:他們是一個有文化、有文學修養的民族,越去了解他們的神話、故事及歌詞,感受越深。但是我們這一代的人類學家不是很勤勞,語言的隔閡使我們不易了解他們的文化,不懂他們的語言,談他們的文化是荒唐的。
看到影片裡美麗的海洋,令我回想起人類的故鄉。蘭嶼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的,一個善的、理想的世界。蘭嶼的資源相當豐富,經由自己的努力,建立美好的生活,是很容易的。
另一方面,他們對惡很排斥,以為死亡會傳染。所以,像核廢料這樣可以把全人類滅亡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他們認同的方法處理,死亡陰影會籠罩在整個島上。
他們的恐懼正是由他們的文化來的,其實他們真是有知識。
影片裡有許多珍貴的鏡頭,譬如「小米祭」,是世上難得見到的。雅美人是很有戲劇天份的民族,若能從頭欣賞大船落成典禮到完,更能感受他們對整個儀式的安排有分寸、有系統。雖說我們是「文化大國」,卻難能見到如雅美人精闢的表現。標準的雅美族必須是人人可以作詩唱歌,反倒是「文化大國」的我們所望塵莫及的。
雅美人是很美的,有生命、會開美麗花朵的民族。反觀我們對人生的努力、對生活的感受,都不如他們來得深刻。
黃美英:老一輩的人類學者是比較溫和的,胡小姐則站在很敏銳的角度揭露問題。其中可能牽涉到時代的因素。同時,我看到雅美社會在不同年代及不同年齡層面對外來的衝擊,表現了不同的反應形態,我想,這部影片所代表的意義屬於晚近的,卻不能烘托老一代的宇宙觀。
外來的衝擊如浪潮般拍打上岸,蘭嶼長期醞釀的文化岩層要如何處理出來?
下什討論部份丁松筠:《蘭嶼觀點》代表蘭嶼人本身的觀點嗎?
郭:影片有其極限性,這部影片已把蘭嶼潛在嚴重的問題暴露出來,提供台灣的社會很大很好的觀點了解蘭嶼。
施:我不希望是胡台麗的觀點,也不希望是郭建平或我自己的觀點。看完影片,不管林建享的攝影背後的感情,胡台麗個人想呈現出來什麼樣的內容,也不管我或郭建平的心態,我深深感覺到影片給予每個人反省的機會,包括胡台麗和我自己。
我身上雖流著雅美人的血液,卻有二十六年的時間,接受了漢人制式的教育。漢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幾乎主宰了我,一直到遇見建平,才慢慢反省自己、反省整個族群,在面臨一個機器、一個消費市場,當所有的外來者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宰制我們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在影片中講得太少了。
這幾年我回到蘭嶼生活。今天有很多青年想離開蘭嶼,不是因為他們不再愛這個島。當原住民族接觸到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改變,再加上政府有意地教育漢化,我們要付出的實在太多了。
當外來的文化來得越多時,我們就消失得越快。
剛剛看完影片,我真是覺得建平、雅各和我內心的話講得太少了,影片呈現出來的問題也不夠充足。
胡:基本上,我們是做為仲介者的角色,讓越多人了解蘭嶼,讓越多人談論他們的問題,越了解他們的問題。但是,紀錄片要以什麼管道放映給廣大的觀眾看,將是《蘭嶼觀點》試映後還須繼續努力的部分。
問:請攝影者發表他的觀點。
林:當初動機單純,只是一名電影工作者罷了。初次見到施努來、田雅各和郭建平他們,進入一個男人相知的世界。一開始,儘管腦子裡有這三個方向,但拍的過程常很混亂。今天第一次完整地看了影片,發覺很多感覺經過時間的醞釀,已不是原有的了。今天重溫老人家如此祥和的肢體語言,當時共同的生活經驗歷歷在目。雅美人給了我很多東西,並成為我身體的一部份。
攝影對我不僅是提攝影機的工作而已,而是當身心透過這種行為,去感受他們承擔了什麼。
胡:我們是抱著摸索的態度完成此片。透過這個拍攝過程,對雅美人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尊敬。
能完成這部影片的拍攝工作,真是要非常喜歡這個地方才行。
孫:對身為原住民的我而言,我們的將來恐怕是更需關心的問題。
影片似乎企圖透過觀光、醫療、勞動方式和反核等幾個現象,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反抗背後的脈絡問題,這個脈絡可能跟雅美人的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我想,這個脈絡是影片的重心,但影片裡脈絡的呈現卻不太清楚。
影片似乎還停留在較立即淺顯的層次,譬如表現憤怒,來讓台灣主體社會的人了解這些抗爭與感受,或雅美人的精神與文化。
就影片來看,要的部份是從否定角度的要,可是將來怎麼辦?勞動的方式在改變,觀光客、金錢的流入似乎都是莫可奈何的事。我們真的很關心蘭嶼的將來和希望。
另外,以反核遊行作為影片的結束,會使得影片的功能侷限在要大家支持他們反核罷了。
我覺得影片應該處理兩個問題:一個是解釋脈絡的傳統背景,一個是面對了傳統的、現代化的問題之後,雅美人將來要什麼?
郭:攝影林建享和我既是工作夥伴,也是朋友。一個雅美人和一個台灣的朋友,在拍攝過程裡難免有衝突,但會因朋友的交情而不去談論。
我們這裡有許多從事文字工作的和攝影界的朋友。假如筆和攝影機是武器的話,當你拿著這些武器去面對沒有同樣武器的人時,是不是應該思考他們會作什麼反擊與防衛。
我很納悶很多攝影界的朋友並沒有思考到這個問題,若不去思考的話,當你拿起武器去面對你的對象時,他的反應就會令你措手不及。
對於剛才孫老師提出切入點在哪裡的問題,事實上已經點出來了。我們回到人與人的關係:你跟雅美族的關係。影片呈現了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對立下的雅美族近況。透過影片,我們也可以看見一個弱勢團體在面對龐大的政治體制時,他們如何面對與改變,怎麼樣在強勢的文化中感應他自己。
大部份的原住民站在equal line的底下看待自己的文化,大多數的漢人站在equal line的上頭看待底下的原住民文化,這個問題使得很多現象看來很複雜,其實很簡單。
影片無心說服觀眾,而是提出存在的問題,你決定如何看待罷。
施:我昨天下什去打魚。天氣很好,我潛到海裡,看著很多魚群在頭上游來游去。我決定等牠們再大點,卻又不能空手回,所以打了條女人魚給我媽媽吃。回去以後,我太太生氣我沒有打到魚,我的父母卻很高興。因為蘭嶼有個觀念,你不可以天天豐收。
胡:我並不想在影片裡提供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我拍攝此片的動機之一,來自於對以前有關蘭嶼這類問題的報導方式的不滿;站在「正義」的立場,一味地頌揚或一味地指摘。
而且,合作的幾位都是具有文化省思的人,我真心希望提出問題,大家共同來思考。
第一部份,是希望觀光客重新從當地人的立場思考,為什麼他們會反對觀光客隨意跑到他的家裡去?影片也試圖提出背後的東西,包括交換體系,你觀光客來,我得到了什麼利益?在原有蘭嶼社會裡,我今天送你,你明天送我,是很清楚的。
第二部份有關醫療方面,田雅各在當地服務了三年,帶著現代醫療設備與布農族身分,他不能理解雅美人對醫療的抗拒。
就我看來,他的付出與得到的不成比例,如果他不是這麼地具有反省能力,恐怕所受的打擊將更大。影片後頭,田雅各提到,當地人可以選擇到台灣醫療,但他有沒有條件去?如果沒有的話,為什麼不更依賴本身傳統體系來處理這些問題?
第一部份,我也希望當地人思考祭典表演的問題。另外結尾部份,重點不是趕魔鬼的動作,而是一個平和的民族竟會以此來表示自己的憤怒。
這一段裡,我更看重背後舖陳的部份,希望呈現出島嶼韻律感。所以,我不希望觀眾在這裡只看到揮拳、憤怒。傳達蘭嶼文化的秩序和美感是我更大的企圖。
孫大川:我並非要一個明確的答案。經過這番講解,讓我更清楚了;我只是希望畫面可以帶到這些比較深刻的東西。
虞戡平:有個問題想請教田雅各,當你本身的布農族文化邏輯跟雅美人文化邏輯套在一起時,產生什麼樣的衝擊?而你又是如何調和拉近和雅美人的關係?
田:可以用一句話表示:誠懇。
當初來到蘭嶼,發覺他們很排斥醫療,原因除了對醫療不了解外,主因是對我的不信任。
我曾經為了博取好感,跑去跟當地人說,我跟他一樣是山地人,他竟然嚇一跳,回答我,他不是山地人,他住海邊,令我很失望。雖然我也是原住民,但是當地人把我看成台灣人。
只要有誠懇的心,互相取得了解信任,隔閡是可以化解的。像在醫療的過程中,當他們有了一些療效的經驗之後,漸漸地,會相信醫療。縱使醫療有科學的根據,但在當地,他們對很多事情已有幾千年的經驗,不可能一下子推翻它。可能要顧及當地的生活文化,來傳播好的東西,較為可行。
謝世忠:我想在這三個部分裡整合一個主題,發現只有「對立」。觀光客與當地人的對立、現代醫療與當地傳統療法的對立,以及核廢料對當地造成的恐懼與衝突,這是影片要傳達的意念?
胡:在觀光、攝影部分,影片裡有些雅美人也提到了在平等的條件下,是不會反對觀光攝影的。這裡,我們希望觀眾想一個方式把平等的架構建立起來,觀光客與當地人不再彼此傷害。
或者需要耐性。細心的觀眾可以看到在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連接上,是以田雅各提出自己攝影的心得來串連,他說花了三年的時間才能自在的拍照;意味著要取得當地人的信任感需要較長的時間,得到信任以後,做起事來才順利,像接下來探討的醫療就是。
其實,醫療到當地的時間還很短,或許經過長時間給予他們信心,或許在了解他們原本的生活經驗下,納入醫療的觀念,現代醫療與民俗醫療不一定是對立狀況。
第三部分裡,場長的話有些前後矛盾,從一開始解說核廢料處理情況的安全性應可信任,當地人是因不明瞭而恐慌,但到後頭,他也明白指出,選擇在蘭嶼島上存放,是考慮到對老百姓的影響最小之故。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說服雅美族人接受核廢料呢?如果這種不合理的對待繼續存在的話,抗爭會繼續存在。
虞戡平:在當地放映時,可不可能作份民意調查,或許更能呈現蘭嶼的觀點?
胡:我希望他們自由發言,這種形式化的東西比較不能進入他們。
蔣斌:剛才問了許多問題,你都需要長篇地回答,這是不是暗示了影片的缺憾?影片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以前拍了排灣族、賽夏族以至今天的雅美族,此種針對每一族的研究在影片結束後即告終了,似乎見你遊耕似地從事拍攝工作。影片裡未呈現出來他們的宇宙觀,是一大缺憾,是不是會繼續做下去?
胡:影像的確有它的優點、缺點。我想,影片出來後,我可以緘默,觀眾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不同的人很可能看到不同的東西,不僅影片如此,文字資料也是啊!
這次的拍攝,依靠許多前人的研究文獻,才得以完成。我也希望,藉由影片呈現一些文字所無法呈現的東西。
我也期待,這類的研究、拍攝工作,大家都來做;如果,原住民能夠拍攝屬於他們的故事,可能更有說服力。所以不一定非我來做不可。
林:我已經繼續做下來了。將以施努來為主,描述雅美人的歷史以及老人家的觀念。
黃智慧:攝影者有沒有做好事前準備工作,比如讀過大量文獻,或是請教別人等等,加強對蘭嶼的了解。我在想,是否事前的工作準備充分了,比較能夠從畫面上感受蘭嶼的祥和?
林:我並沒有閱讀文獻資料,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是對的。
我曾與建平的爸爸,不藉語言的溝通,相處數天,慢慢地去體會他的內心。這些體會出來的經驗與後來讀到的文字資料是相互印證的。
如果我把人類學文獻資料當作材料,終有用盡之時,如果把它當「人」,將越來越豐富。正如雅各說的「誠懇」,是的,我相信自己是抱著誠懇謹慎的態度來拍,我希望攝影機不是武器,而是我身體的一部份。不盡理想之處盼望在往後的工作裡去克服、去改善。
黃智慧:請教郭建平先生,你在影片中提到人類學工作者隨意進出蘭嶼從事拍攝、研究的工作,對蘭嶼住民非但沒有助益和回饋,甚至造成傷害的情況,那麼你覺得人類學工作者要如何回饋,才能達到所謂的平等互惠?郭:假如人類學家本身的研究工作是在累積個人的資源,相對的,這些資源應該分享,但不是物質的分享。
人類學家的研究工作除了可以豐富學術論文,提升本身的社會地位,我主觀地以為,我們被研究了,我們的問題能被暴露、解決。
很多時候,這些研究加速政府對原住民的壓榨和破壞。我希望,人類學者能提出幫助解決問題的回饋。
虞戡平:可不可能把拍好的畫面交由原住民來選擇,或許出來的東西他們比較能夠接受。
胡:拍攝的選擇不在他的話,你把選擇過的畫面交給他去剪,是滿形式化的。
我所做的是,在初剪後,請他們來看,是否扭曲他們的原意。
未來,很希望能看到原住民自己拍攝、剪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