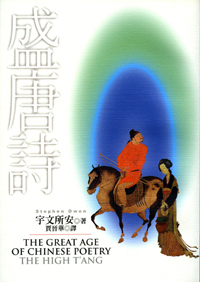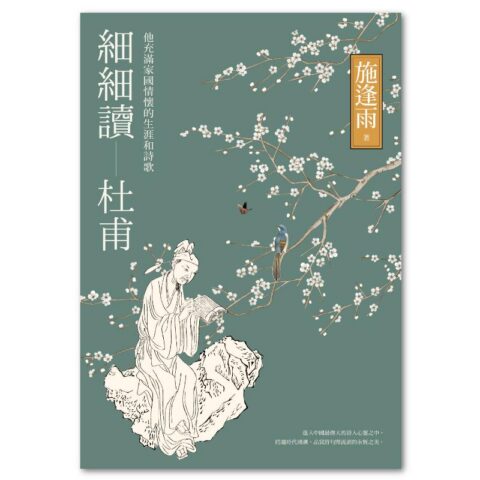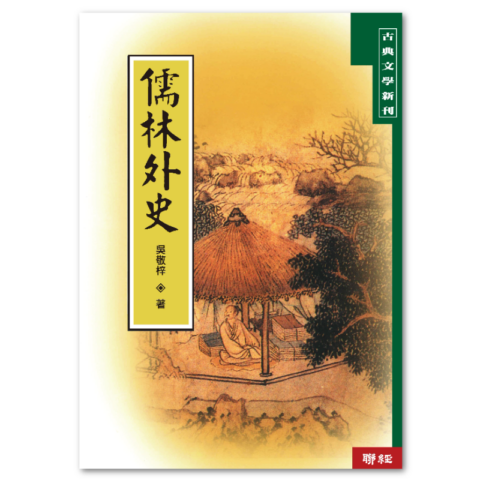盛唐詩
原書名:THE GREAT AGE OF CHINESS POETRY:THE HIGH T’ANG
出版日期:2007-01-09
作者:宇文所安
譯者:賈晉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9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1085
系列:宇文所安系列
已售完
盛唐詩代表「唐朝黃金時代」的詩歌,從沒有一個朝代的詩歌曾經如此稱呼,這是多麼輝煌壯麗的光彩!後代詩人面對盛唐的璀璨光輝,悲歎自己的黯淡晦昧,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它,就是激烈地反叛它,或聲稱將忽視它,並按照自己內在本性的要求自由地抒寫。
但是在中國詩歌史上,盛唐始終保持著固定不變的中心位置,規定著所有後代詩人的地位。如果我們想對這一時代及其詩歌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就必須將這種輝煌絢麗的神話撇在一旁,並注意以下三件事:
一、 不能將這一時代等同於李白和杜甫,文學史並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
二、 時代風格是實際存在的,但是是無形的、多側面的、相互滲透的實體,並不容易界定。
三、 盛唐神話的最嚴重危險是被切斷其內在發展歷程,變成一個光輝燦爛、多姿多彩的瞬間。
本書以《初唐詩》為基礎,建議兩本書最好連續閱讀。
作者:宇文所安
美國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特級講座教授,任教於比較文學系和東亞語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研究以中國中古時代(200-1200)的文學為主,目前正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主要著作包括《晚唐》(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2006)、《諾頓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1985)、《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等等。
譯者:賈晉華
福建漳州人。1982年於廈門大學獲文學碩士,1982年至1994年任廈門大學講師、副教授,1999年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2000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學助理教授,2005/2006年任哈佛大學神學院客座研究員。已出版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 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等中英文專著五部,及眾多中英文論文。
盛唐年表
導言
第一部分 盛唐的開始和第一代詩人
第一章初唐和盛唐
第二章過渡時期的詩人
第三章社會背景
第四章王維:簡樸的技巧
第五章第一代:開元時期的京城詩人
第六章孟浩然:超越典雅的自由
第七章王昌齡和李頎:京城詩的新趣味
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觀念
第九章高適
第二部分 「後生」:盛唐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引子
第十章岑參:追求奇異
第十一章杜甫
第十二章復古的復興:元結、《篋中集》及儒士
第十三章開元、天寶時期的次要詩人
第十四章八世紀後期的京城詩傳統
第十五章東南地區的文學活動:詩僧、皎然、聯句詩、顧況
第十六章韋應物:盛唐的輓歌
譯後記
序 傅璇琮
自從歐洲的第一批耶穌會士抱著傳教的虔誠,越過重洋,在明朝末年來到中國,開始接觸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如果按照《國際政策的文化基礎之研究》作者諾思羅普(F. S. C. Northrop)所說,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文化,這種分歧深深植根於各自傳統的不同概念之中,那麼,四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固有精神和價值的探索,實際上可以說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互相認識和補充。這也構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豐富繁複的圖像。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被世界所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課題。從這個背景上說,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詩》被介紹到中國來,它的意義就不僅僅是中國學術界增加一本優秀的漢譯名著,而且還在於它是文化交流的鏈索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環節。
在探索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過程中,我們不應該忘記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國讀書界的注意,特別是近幾年顯得十分突出。是他揚棄了在他之前的歐洲學者的共同學風,即服從於自己的時代背景和相應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來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正是從韋伯開始,主張應當密切聯繫社會歷史的實際狀況來研究觀念的形成和演變軌跡。這就為爾後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對中國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應當探求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來進行課題的研究。這種情況,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學者那裡,表現得更其明顯。
關於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文系及語言學系教授李珍華博士的︿美國學者與唐詩研究﹀(載《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第一輯,一九八三)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這篇文章講的雖然是美國的唐詩研究,實際上足以反映美國於本世紀五○年代以來漢學研究的巨大進展。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上一世紀同一時期法國學者對中國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說《平山冷燕》、《玉嬌李》的推崇,和本世紀近三十餘年來美國學者(包括美籍華人學者)對唐詩、宋詞及明清小說的認真探討,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以綿密的材料考證見長,而美國在這方面卻常以見識的通達和體制的闊大取勝。
正是從李珍華先生的文章中,我知道了宇文先生在唐詩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華先生把宇文先生列為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第三代學人。而稱為「特別值得一提」,並推許出版於一九七七年的《初唐詩》為「一本傑作」,說「把整個初唐詩作一系統性處理,歐氏可以說是第一人」。李珍華先生對歐洲文化與美國文學均有深邃的認識,而又對唐詩,特別是初、盛唐詩有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話是可信的。由於我參與《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的編輯,較早讀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別提及的宇文先生著作給我的印象很深,並盼望能早日見到全書的中文譯本。現在依靠賈晉華女士的努力,這個願望得以實現,甚感欣慰,我想我們國內的唐詩研究者也會從這一譯著中獲得啟發。賈晉華女士前數年從廈門大學周祖譔先生研治唐代文學,她的碩士學位論文論皎然《詩式》及大曆時期江南詩風的特點,也給我很深的印象,她的從文學演進的內部規律與外界社會文化思潮相互影響的研究,與宇文先生的治學,也確有不謀而合之處。以賈晉華女士對唐詩所具有的修養來從事於本書的翻譯,必能準確表達原書的勝義,這應當是無可懷疑的。
在過去一個很長時期中,初唐詩的研究在我國整個唐詩研究中是一個極為薄弱的環節。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時,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占了唐代歷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對於這一階段文學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說明盛唐的高潮。對這九十年時期的文學,過去的論著往往只停留在一個籠統的認識,細節研究非常缺乏,這種情況在最近四五年內才有所變化。作為近體的律詩,到底是經過什麼樣的軌跡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詩,特別是盛唐、中唐時一些大家所擅長運用的七古,怎樣從南北朝的涓涓細流,經過初唐作家的多方嘗試和大膽變革,而彙成長江大河,這中間有什麼規律和經驗可求?由「四傑」而陳子昂,而沈、宋,是怎樣一步步遞嬗演進的?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給予詩人和詩風以什麼樣的影響?初唐時期幾個帝王的宮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賦予文學風格以什麼樣的特色?這些,都需要做細緻的分析。而近幾年來我國初唐文學研究的進展,也正是在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探討。從這一研究的歷史背景來看,宇文先生作於一九七七年的這本《初唐詩》,在中國學者之先對初唐詩歌做了整體的研究,並且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這不但迥然不同於前此時期西方學者的學風,而且較中國學者早幾年進行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求。雖然近幾年來中國學者的論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學研究的進程,但宇文先生的貢獻還是應該受到中國同行的贊許的。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初唐詩》之後,作者又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盛唐詩》,更進一步論述了初唐與盛唐的關係,並對盛唐詩人作了使人感興趣的分類(如把張說、張九齡、王維作為「京城詩人」,把孟浩然等作為「非京城詩人」,把王昌齡、高適、岑參作為處於兩者之間的詩人,「京城詩人」多用律體,「非京城詩人」多用古體)。宇文先生近年來的研究格局似更為放開,由論述詩歌創作進而研討詩歌理論。他說他更強烈地感覺到詩歌中那些無法為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學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對詩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討來補充。為此,他又撰寫了關於中國詩論的論文,結集成八篇文章,起名為《中國傳統詩歌和詩論:預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緊接著又是一組八篇文章的集子:《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他自己說這八篇文章是一種反系統的處理,將互不相關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嘗試著使單篇的詩作和散文煥發出生命力。這樣做,作者也抱著一種希望,這就是打破美國的中國文學狹窄的閱讀圈子,尋求更多的讀者。
宇文先生的學術著作在其已經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中,更有新的進展。他認為,過去大部分論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英文著作,都傾向於運用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術語,而在他的這部近著裡,卻試圖向英語讀者表明,作為中國詩歌基礎的概念和趣味,與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種傳統的文學思想都具有偉大的力量,但是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宇文先生的這一認識的確值得讚許,這是對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充分尊重的態度,只有持這種態度,才能達到真正清晰的理解。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在獨立的研究中擺脫西方習以為常的觀念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一個富有洞見的認識。
近十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已取得可觀的成績。但人們對研究現狀仍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多種多樣的。在我所接觸的一些研究者中,越來越感到對古典文學的研究結構需要有所反省,這就是說,研究結構存在不合理的情況。有些課題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卻並不多,許多情況下往往是一窩蜂,趕熱門,結果卻出現了不少缺門,這就必然影響總體水準的提高。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論證的問題,不是這篇短序所能承擔的。由宇文先生的著作,使我進一步感覺到,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結構中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狀的了解,是多麼的不夠。我相信,在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價值的著作,一定還有不少,它們以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獨特的文學現象,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誤失,也能促使我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研究這些誤差的原因,加深我們的認識。如果我們能有計畫地編印一套漢譯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肯定會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讀書界的歡迎,也將會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結構起到積極協調的作用,這是我個人作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著的。
導言
中國的批評家在劃分文學史時期時,通常採用年號、朝代的名稱,或諸如「初」、「中」、「晚」等朝代細分期名稱。可是,當他們回顧唐代時,卻將一個源於植物生長週期的新名稱插入「初唐」和「中唐」之間。這一名稱的採用,是文學史家超出平常的冷靜而驚歎不已的表現:「盛唐」││「唐朝的黃金時代」,沒有一個朝代的詩歌曾經如此稱呼。在後世讀者看來,以玄宗朝為中心的這一時代,閃耀著獨一無二、輝煌壯麗的光彩,是文化繁盛和文學天才幸運地巧合的時刻。他們的敬畏是有道理的:至少三位偉大詩人和十餘位重要詩人的作品流光漾彩,使得任何讀者都無法忽視。然而,這種特別的光彩也遮蓋了這一時期文學史的廬山真面目:一個持續變化的複雜過程,卻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樣化風格如同雨後太陽突現,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現一樣迅速,留下後來的時代為獲取其餘輝而努力奮鬥。
將盛唐看成中國詩歌頂峰的信念,出現於九世紀,發展於宋代,牢固地植根於所有後來者的心中。後代詩人面對盛唐的璀璨光輝,悲歎自己的黯淡晦昧;他們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它,就是激烈地反叛它,聲稱將忽視它,並按照自己的內在本性的要求自由地抒寫。但是在中國詩歌史上,盛唐始終保持著其固定不變的中心位置,規定著所有後代詩人的地位。
如果我們想對這一時代及其詩歌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就必須將這種輝煌絢麗的神話撇在一旁。王維的一些詩篇蘊含著一種寓意:山寺自然美的存在,是為了將訪寺者引向隱藏在誘人外表後面的真理(見第四章)。與此相似,詩歌黃金時代的神話也不是其本身的目標,而是為了誘使人們進入這一時代並認識其真實本質。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從遠處觀察它,就不能充分賞識其蓬勃生機和多彩豐姿:詩人之間的內在聯繫被曲解了,這一時代深植於過去詩歌中的根被切斷了,一系列簡單化的、陳舊的詞語被用來描繪這一時代的風格特徵。
要堅持盛唐是詩歌黃金時代的神話,就必須對三個重要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不能將這一時代等同於李白和杜甫,兩位被後代讀者看成是這一時代占主導地位的詩人。文學史並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較為謹慎的做法是將天才安置於其基本背景之下。如果我們撇開盛唐神話,就會發現李白和杜甫並不是這一時代的典型代表。後代讀者往往滿足於李白和杜甫的這一形象:他們不僅被視為詩歌的頂點,而且被視為詩歌個性的兩種對立典範。但是,同時代詩歌的背景卻使我們對李白和杜甫有了殊為不同的眼光,這種眼光能使我們看出他們獨創性的本質和程度。王維和孟浩然由於對隱逸主題的共同愛好而經常被後代讀者聯繫在一起。但是,當時詩壇的背景卻表明這兩位詩人相去甚遠,他們在詩歌修養、感覺及才性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們的目標不是用主要天才來界定時代,而是用那一時代的實際標準來理解其最偉大的詩人。
其次是關於時代風格的一般問題。保守的文學史家幻想時代風格是一種完全一致的實體,具有方便的固定年代。另外一些人則不相信任何時代的標誌,認為其中存在著不利於真正的詩歌鑑賞的東西。但時代風格是實際存在的:沒有一位敏感的中文詩或英文詩讀者,能夠擺脫語言、風格及文學背景所體現的歷史感,這是閱讀過程中自然而然的、令人愉悅的組成部分。然而,時代風格又是無形的、多側面的、相互滲透的實體,並不容易界定。它們在分界處體現得最明顯:新的觀念、有影響的詩人或各種再發現能夠在短短幾年的過程中引起詩歌的普遍變化。這些分界線是高度滲透的:新風格的起源和舊風格的延續在這裡最清晰地顯現。大約在七一五年至七二五年間初具規模的盛唐詩,顯然衍生於初唐風格;同時,這一期間所發生的各種變化,正是基於許多初唐詩人對自己時代詩歌的不滿。在分界線的另一端,盛唐最後一位主要天才杜甫去世後,盛唐風格仍餘音不絕。直到八世紀九○年代初,對復古的關注重新興起,這才真正進入了中唐。但這一分界線決不是絕對的:保守的詩人繼續寫著王昌齡風格的邊塞詩,而激進的革新者在形成新詩歌的同時,仍然盯著李白和杜甫。
其三,盛唐神話的最嚴重危險是被切斷其內在發展歷程,變成一個光輝燦爛、多姿多彩的瞬間。盛唐詩的豐富多彩一部分確實是由於詩人個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卻是七十多年歷程中文學發展演變的結果。成熟於八世紀二○年代的詩人對於詩歌和詩歌傳統的觀念,與成熟於八世紀四○年代的詩人是迥然不同的。在八世紀二○年代,詩歌是一種優美圓熟的技巧,從理論上說可以用來激發深刻的道德和文化意義。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幾世紀來沒有出現過無可爭議的大詩人,這就給天才的出現留下了寬廣的空間。而成熟於八世紀四○年代的詩人,卻面對著二十年來所創造的宏麗遺產。因此,杜甫面對其直接前驅者的特殊體驗,是年輩較早的孟浩然從未有過的。
除了單純的描述職責,文學史還應當研究詩歌的各種標準和變化過程。我不打算用一系列新特徵來界定時代風格,而是設立幾個普遍性的關注範疇,以之貫穿整部書。這些關注範疇大致地將盛唐與其前後的時期區別開來,同時又容納各種促使盛唐風格多樣化的個性反應。
盛唐詩由一種我們稱之為「京城詩」的現象所主宰,這是上一世紀宮廷詩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詩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它卻具有驚人地牢固、一致、持續的文學標準。京城詩涉及京城上流社會所創作和欣賞的社交詩和應景詩的各種準則。八世紀各個大家族的成員在京城詩的實踐者和接受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詩人們主要依靠他們而「聞名當世」。京城詩最喜歡採用格律詩的形式(雖然某些場合也需要其他形式)。隨著各種棄世的高尚主題被改善為對美妙的田園風光的嚮往,我們在京城詩中發現了對於佛教和隱逸主題的特殊興趣。京城詩雖然不像宮廷詩那樣受到嚴格的規範限制,我們在其中仍然看到了詩體和題材規範的強烈意識。與宮廷詩一樣,京城詩很少被看成是一門獨立的「藝術」,而是主要被當作一種社交實踐;人際關係和詩歌關係的網,將中宗朝的宮廷詩人與受帝王青睞的《御覽詩》(九世紀初的選集)詩人連接了起來。這種社交關係的網清楚地顯現在應景詩的交換,而此類詩無例外地構成京城詩人集子的很大部分。
儘管京城詩人有著社會聲望和影響,但這一時代最偉大的詩歌卻是由京城外部的詩人寫出來的,其中只有王維是值得注意的例外。王維同時處於京城詩及其變體的頂峰:他既按照京城詩的規則創作,又超越了這些規則。從九世紀起,李白和杜甫占據了讀者的想像中心,但是在八世紀後半葉,王維的詩歌聲音久久地縈繞於次要詩人的作品中。盛唐其他大詩人孟浩然、高適、王昌齡、李白、岑參、杜甫、韋應物等,由於社會地位、歷史處境或個人氣質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京城詩的世界。有些詩人嚮往京城詩,有些詩人反對京城詩,但正是在京城詩背景的襯托下,他們成了真正具有個人風格的詩人。
這正是盛唐偉大成就的部分原因:盛唐既擁有單獨的、統一的美學標準,又允許詩人充分自由地發揮個性才能,這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宮廷詩的時代也擁有統一的詩歌標準,但這一標準過度僵化,限制了詩歌的特性,連庾信那樣的天才詩人,也為其嚴格的修飾法則所束縛。而另一方面,在九世紀及後來的時代,雖然有著眾多的美學標準,卻沒有一個能夠單獨成為社會認可的全面權威。
與這種統一的美學標準和個性才能之間的平衡相關,詩歌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京城詩代表了將詩歌看成社交活動的觀念,其根源出自宮廷詩傳統;另一種觀念則將詩歌看成超脫社交場合的屬於文化和個人範圍的藝術,這兩種觀念在這一時期開始轉換。盛唐應景詩人寫詩時,一隻眼盯著後代人,另一隻眼盯著詩歌的接受者。中國的應景詩即使到了今天還有生命力,但是在盛唐之後,大詩人的眼光越來越專注於後代人。詩人們開始準備和編輯自己的集子,每一首應景詩在詩歌傳統的完整背景下較為妥貼地安置了下來。中國詩歌這種向著自覺藝術形式的緩慢轉變,並沒有妨礙產生與盛唐同樣優秀的詩篇,但我們可以感覺到,盛唐詩較深地植根於歷史和社會背景的現實世界。此外,宮廷詩遺留下來的對於技巧的極端重視,確實促使一些小詩人寫出了不少出色的詩篇。作為對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宋代的小詩人,他們寫一些只符合韻律而不考慮美學標準的詩,拙劣得不堪卒讀。應景詩不再是社交過程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而是成為一種令人愉悅的、審美的消遣品。
盛唐時期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事件,即對詩歌傳統的「重新發現」,以及伴之而來的詩人們的激情。六七世紀的詩人們雖然也意識到了詩歌傳統,但是他們往往將它看成是精緻的人工製品,而詩歌的現實社交要求要迫切得多。宋之問在頌揚皇帝出訪貴族別墅時,決不會由於為陶潛風格所吸引,或認為這一風格可以產生偉大的詩歌,就去模仿它。而盛唐詩人卻迅速地、連續地從過去時代裡找出各種風格和詩人,使他們成為整整十年或單獨一首詩的潛在中心。阮籍、陶潛、司馬相如、庾信、謝靈運及其他人,在幾十年的歷程中先後起落。這種重新發現詩歌傳統的激情一直持續到中唐,但是在其後的幾個世紀中,詩歌傳統變成了當代詩歌的一個成熟部分,變成了一組供人取用、模仿或重新組合的風格。成熟化所帶來的不是輕視而是局限,於是文學傳統成了真正的負擔,不再是解放的手段。
盛唐的頭幾十年本身很快就成為一個負擔沉重的文學傳統。在八世紀五○年代,詩人們已經以渴慕的目光回瞻開元和天寶前期,先是將其看成一個失落的文化和社會的鼎盛時代,隨即又看成一個消逝的文學繁盛時代。盛唐神話幾乎緊跟著安祿山叛亂而開始出現,此次戰亂標誌著天寶盛世和文學繁榮的結束。這一神話是由杜甫、韋應物這些詩人自覺地構造出來的,也是由感傷而守舊的後期京城詩人不自覺地構造出來的。中唐詩人所受盛唐神話的影響,並不比後期京城詩人少,但是他們與這些直接前輩的不同在於,他們帶頭對盛唐的偉大成就作了創造性的重新闡釋,而這種闡釋此後持續不斷,連綿長久。
我試圖盡可能使這部著作自我包容,但是由於它以《初唐詩》(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為基礎,所以兩部書最好連續閱讀。這部書所採用的格式與《初唐詩》基本相同。引詩都標上《唐代的詩篇》中的編碼數位。凡有可用的校注本,我都予以採用;否則就在最早的文本中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