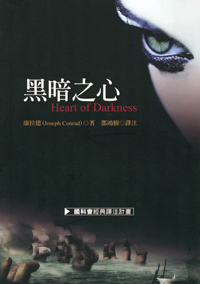黑暗之心
原書名:Heart of Darkness
出版日期:2006-08-11
作者:康拉德
譯注者:鄧鴻樹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00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0439
系列:聯經經典
尚有庫存
〈黑暗之心〉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篇小說。故事敘述船員馬羅回顧他在異域營救貿易站經理庫茲這件事,娓娓道出文明邊疆的陰謀故事,並藉庫茲投身黑暗勢力的轉變過程,警寓現代文明之野蠻。文化學者薩依德表示,〈黑暗之心〉以堅定無畏之姿處理非理性的題材,遠勝於任何文學作品。〈黑暗之心〉以短短四萬字的篇幅揭發文明之貪婪與好鬥,正如湯馬士‧曼所言,預言性地揭開了20世紀的序幕。
本書特色
◎ 本書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經典譯注計畫之一。
目 次
譯序──讀了再說
中譯導讀
一、〈黑暗之心〉的經典地位
二、康拉德的黑暗之旅
三、「俗世的夢想,邦聯的萌芽,帝國的興起」
四、「整個歐洲造就了庫茲的誕生」
五、「無法言傳的恐怖黑暗處」
六、「一個故事並不具有核心意義」
附錄一、〈黑暗之心〉的版本與國內現行中譯本之評介
附錄二、關鍵用語的翻譯說明
附錄三、關鍵情節頁碼對照
附錄四、康拉德年表
附錄五、重要研究書目提要
作者:康拉德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英國船長兼小說家,原名科忍尼奧斯基(Józef Konrad Korzeniowsky),生於帝俄統治下的波蘭,雙親皆死於政治迫害。他於1874年赴法國當上水手,1878年加入英國商船服務,並取得船長資格,於1886年歸化英國籍。康拉德乃英國文學裡耐人尋味的異客。多年的航海生涯,累積成為他日後寫作的題材。康拉德筆下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墮落或失敗的英雄、貪婪而無能的殖民者。作品內容對殖民者的貪婪墮落有深刻的觀察;同時也描寫對冒險生活的浪漫憧憬,並在作品中呈現歐亞民族與文化間複雜傾軋的關係。
他周遊世界近二十年,37歲(1894年)才改行成為作家:在寫第一本小說前,他僅自學十多年的英文。康拉德的作品深刻反映新舊世紀交替對人性之衝擊。面對文化與人性的衝突,他並沒有提供答案,而是如同哲學家提供思索答案的過程。所寫的作品:《吉姆爺》(Lord Jim)、《黑心》(Heart of Darkness,或譯《黑暗的心》)、《救援》(The Rescue,或譯《拯救》)、《我們的人》(Nostromo或譯《諾斯楚摩》)入選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著名的批評家李維斯(F. R. LEAVIS, 1895-1978)更將他列在英國小說家的前四名之內。
譯注者:鄧鴻樹
鄧鴻樹,台灣台東人。倫敦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專攻康拉德。研究領域為現代英國文學、殖民論述、文學理論。現任台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講授英國文學、英詩選讀等課程。
緒論
一、〈黑暗之心〉的經典地位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篇小說 。〈黑暗之心〉作於1898年12月至1899年2月間,同年2月至4月以〈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之篇名分三期連載於英國著名之《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故事記敘船員馬羅(Marlow)回顧其於異域參與「解救」任務,營救貿易站經理庫茲(Kurtz)一事,娓娓道出文明邊疆的陰謀故事,並藉庫茲「退化」(degenerate)、投身黑暗勢力的轉變過程,警寓現代文明之野蠻。
〈黑暗之心〉以短短的篇幅,如湯馬士‧曼(Thomas Mann)所言:「預言性地揭開了20世紀的序幕。」 現代主義代表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之短詩〈空人〉(“The Hollow Man”)正是藉故事中黑人小弟的「庫茲ㄙㄧㄢ生——他死」(“Mistah Kurtz–he dead”)一句,諷刺現代人偶像崇拜之空虛及對文明發展之惶恐。同期作家福特(Ford Madox Ford)早已指出,沒有其他現代文學作品能比〈黑暗之心〉更迫切地揭發文明之虛偽、貪婪、好鬥 。
自從文學家李維斯(F. R. Leavis)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奠定康拉德於英國文學的經典地位,〈黑暗之心〉就成為文學批評的核心文本。本書不僅是20世紀研讀最多、印行最廣的小說,也是各派理論鳴放的主要「戰場」 。心理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同志研究、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各派大師都曾藉〈黑暗之心〉探討文學研究之最新議題 。尤其是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開創文化與後殖民研究的薩依德(Edward Said),其思想亦深受康拉德的影響。他的早期研究以康拉德為主 ,而其鉅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之中心思想更是透過〈黑暗之心〉之文本分析才得以彰顯 。薩依德於生前最後一次訪談時甚至表示,〈黑暗之心〉以堅定無畏之姿處理非理性、未知的題材,遠勝於任何文學作品 。1977年尼日作家阿奇貝(Chinua Achebe)以〈黑暗之心〉的種族主義為題發表演講,公開宣示康拉德乃「該死的種族主義者」(“a bloody racist”) ,顛覆康拉德的典律地位,引發廣泛討論與爭議。雖然阿奇貝化約式的解讀值得商榷,他的說法碰觸到西方社會敏感的種族議題,深深影響康拉德研究的走向,立下後殖民批評的新里程碑,再次突顯複雜多樣的〈黑暗之心〉與大時代之密切關聯。
康拉德是現代英國文學裡耐人尋味的異客。他生於帝俄統治下的波蘭,繼承古老悠久的東歐文化;他通曉俄、法、德等語言,崇拜19世紀歐陸作家;他當船員周遊世界近二十年(1874至1894年),從法籍水手一路做到英籍船長,親身造訪許多「黑暗」之處。康拉德直到二十多歲才學英文,37歲才出版小說;在寫第一本小說前,他只學了十多年的英文,還曾一度考慮用法文寫作。他於1886年歸化英國籍,日後於英國落地生根,但終其一生卻連有些簡單的英語都不會唸。多樣的人生讓他具有「作家船長」與「船長作家」的雙面性。與到過薩摩亞群島的史帝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住過印度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身染歐美文化的詹姆士(Henry James)等同期作家相比,康拉德的小說背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他無疑是現代英國文學史上最世界性(cosmopolitan)的作家。
康拉德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新舊世紀交替過程對人性之衝擊,替歷史所下的註腳遠超越國族分野。「整個歐洲造就了庫茲」;整個歐洲也塑造了康拉德。〈黑暗之心〉忠實呈現康拉德「異客」身分所表露的多元文化觀。面對文化與人性的衝突,〈黑暗之心〉得以歷久彌新在於康拉德並沒有提供答案,而是如同哲學家提供思索答案的過程。如馬羅指出:「一個故事並不具有核心意義,其含義不像堅果的核心,而是如同外殼,包覆著整個故事。」(7) 因此〈黑暗之心〉運用許多「不可知」的詞藻(如李維斯指出:「神秘莫測」〔inscrutable〕、「難以想像」〔inconceivable〕等) ,不僅顯示〈黑暗之心〉欲表達的是超乎語言、小說文體之外的,還表示康拉德的寫作與馬羅說故事一樣極具「後設」與自覺。〈黑暗之心〉總結19世紀的小說傳統,另闢20世紀的小說新天地,借用改編的電影名稱來說,對文學的衝擊可謂寫下了「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二、康拉德的黑暗之旅
1890年9月1日的晚上,比屬剛果的運補船比王號(Roi des Belges)靜靜泊在剛果河中游的史坦利瀑布站(Stanley Falls,現名Kisangani)。航程的疲憊加上高燒、痢疾不斷,船員早已疲憊不堪。夜幕逼走惡毒的烈日,招來致命的瘧蚊,大夥都躲到船艙提早就寢,昏睡過去。具有船長資格的英籍乘員科忍尼奧斯基(Józef Konrad Korzeniowsky)獨自在甲板徹夜未眠,默默品嚐難得的獨處時間。星空下一片漆黑陌生,河岸上可見魑魅般的樹影,鬼火般的燈火。瀑布聲中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這就是黑暗大陸。他終於實現童年夢想,來到黑暗深處。
不過在此文明前哨他並沒有嚐到夢想實現的喜悅。環顧四周,他覺得異常孤獨。這三個月來的溯游之旅讓他親眼目睹文明拓荒的慘狀,夜色因受苦的黑奴而愈形黑暗。非洲大陸淪為列強瓜分的大餅,「文明」雖為剛果流域帶來貿易,貪婪的征服慾望卻將這片大陸領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如他日後描述當時的心境:「一股悲情深深籠罩在我身上。」科忍尼奧斯基的夢想在那晚的冥想裡幻滅,他腦海裡縈繞不去的是文明世界的虛偽及其黑暗之心。他回憶道:「想到報紙上乏善可陳的『宣傳花招』與那些卑鄙的瓜分玷污了人類歷史與地理探勘,就令人反感。男孩夢想中理想化的現實就這樣幻滅了!」
這趟剛果行令他差點死於痢疾與瘧疾,帶來一輩子的痛風與憂鬱症,使他身心徹底受損。但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也帶來轉機,讓他脫胎換骨。如友人嘉納(Edward Garnett)轉述其告白:在這之前,「早年跑船的日子他『腦袋空空』。『我是不折不扣的動物。』」 四年後(1894年)這位波蘭裔的英籍船長毅然決然改行寫小說,化名康拉德(Joseph Conrad);而這如夢魘般揮之不去的黑暗之旅將於八年後化為現代英國文學的經典之作〈黑暗之心〉。如傳記家奧比(G. Jean-Aubry)指出,剛果行乃康拉德人生的轉捩點:「非洲扼殺了水手康拉德,但塑造了小說家康拉德。」
康拉德於1878年成為英國商船(British Merchant Service)船員,從見習生做起,通過各級考試,駕馭複雜的帆船航海技術,不到十年(1886年11月)便獲得船長資格。不過當時英國每年有近千人拿到帆船船長資格,可供指揮的帆船卻逐年遞減 。偉大的帆船時代已經落幕,帆船水手「跑船」的日子越來越辛苦。1890年代帆船數量急遽衰減,繼以代之的是載貨量更大的蒸汽船。因此,甫獲船長資格的康拉德並沒有如願找到職務。在生活壓力下,他於1887年2月與船東簽約,降級擔任高地森林號(Highland Forest)的大副,航向爪哇,展開為期四個月的遠東之行。在三寶瓏(Semarang)港口卸貨時,因操作失當被吊桿擊傷背部,被迫離職前往新加坡住院休養。這段期間他首度窺探神秘的東方世界。同年8月出院後他轉任蒸汽船維達號(Vidar)的大副一職,航遍婆羅洲與爪哇附近各大港口。但康拉德難以適應單調的蒸汽船生活,急於尋找帆船船長的職務,便於1888年1月辭職。恰巧曼谷有艘帆船渥太哥號(Otago)有船長缺,他於是前去爭取。他指揮這艘船約一年,航行於雪梨、模里西斯、墨爾本間。當時康拉德已在亞洲獨自闖蕩近兩年,船長的路走得並不順利,他於是決定辭職返回歐洲(1889年3月)。
〈黑暗之心〉頗具自傳性,如康拉德於序言中指出,〈黑暗之心〉與〈青春〉(“Youth”)一樣都是「經驗的紀錄」,唯〈黑暗之心〉是從真人真事衍生而來 。如馬羅所言:「要弄清楚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要先了解我怎麼到那邊、看到了什麼。」(10)跟馬羅一樣,康拉德的剛果之行是為現實所迫的無奈選擇:「你們記得我那次回倫敦,跑遍印度洋、太平洋、中國海——定期的東方之旅——六年多前,整天閒混…這樣過一陣子還不錯,但不久就閒得發慌。就想找條船——最難辦不過了。但沒船要我。」(10)從渥太哥號離職後,康拉德失業一年半才找到工作,而新職務的工作環境是歷年來最差的:到非洲內地指揮一艘破爛不堪的小蒸汽船。馬羅找工作有賴親戚動用關係,運作「權威人士」(12);康拉德能獲得新職務亦多虧當時在倫敦經營船務公司的有力人士克萊格(Adolf Krieger)幫忙。在其推薦下他獲得面談的機會,1889年11月前往布魯塞爾拜訪比屬剛果上游商業有限公司(the Société Anonyme Belge pour le Commerce du Haut-Congo)的董事長帝斯(Albert Thys)。但當時並無合適職位,要到1890年4月公司有位船長意外身亡(與馬羅境遇相仿),康拉德才接獲通知須即刻前往剛果遞補職缺。
康拉德於1890年5月10日搭船從法國波多港(Bordeaux)出發,經非洲西岸前往剛果,跟馬羅一樣徐徐邁向黑暗深處。讀者可從馬羅的描述窺探當時康拉德的心境:
死亡與貿易在那裡歡樂舞蹈,氣氛猶如悶熱的地下墓室,寧靜、充滿泥土味;一路上惡浪環伺無形的海岸,彷彿大自然想把入侵者擋開;迂迴曲折的河道——人世間的死亡之川,河床腐蝕成淤泥,河水濃稠,盡是爛泥——遍布扭曲的紅樹林,似乎因我們而苦,處於極端無助絕望的困境。我們每處皆停留不久,對這些地方都無具體印象,但我漸感受到一股莫名難耐的迷惑。這種感覺就好像苦悶的朝聖之旅,噩夢將降。(20)
6月12日康拉德抵達剛果河河口大城波馬(Boma,相當於故事裡的「政府所在地」),改搭小船繼續航向上游30哩處的馬塔地(Matadi,即公司總部),因河道難以航行,6月28日康拉德一行三十多人採步行的方式前往上游200哩遠的金夏沙(Kinshasa,即中央貿易站)。歷經36天的長途跋涉,8月2日抵達時他才得知原本要指揮的蒸汽船佛羅里達號(Florida)船身受損,無法啟航。他只好改搭比王號繼續前往上游的史坦利瀑布站(即內陸基地)。9月6日回航時船上搭載了病重命危的公司代表克萊恩(George Antoine Klein,康拉德手稿顯示他原本要以Klein稱呼庫茲)。當時比王號的船長生病無法視事,康拉德即代理船長職務,9月15日船長康復後才交還指揮權。幾天後康拉德也染上嚴重的痢疾,差點死於回程途中。
康拉德出發前簽下三年合同,一心一意想到非洲發揮所長,當上船長,實現童年夢想。可是這趟剛果行只讓他當了十天的船長,還差點要了他的命。康拉德與公司經理德孔繆(Camille Delcommune)相處極為不睦,彼此互相厭惡,使他意識到在非洲的路子必定坎坷,於是便以健康為由提早解約,於1891年1月返抵英國。促使康拉德遠離非洲的主因可能就是因為他與周遭的白人格格不入。跟馬羅一樣,康拉德在剛果流域見識到「事實真相」——「文明人」的貪婪與醜陋,「好像目睹預兆般」(23)深感震撼。他在馬塔地開始用英文寫日記以為慰藉。第一則日記就顯示他早已決定要與當地白人劃清界線:「我想我跟這些白人在一起一定不好過。盡可能避免結交朋友。」他早已洞察白人的「黑暗之心」:「此地社交風氣的特質:大家互相攻訐。」
康拉德的剛果行使他鄙視汲汲營利的歐洲商賈與高傲的「文明人」,刻意與人保持距離的自我防衛心態深化了心中的疏離感:他永遠是個局外人。如傳記權威奈傑(Zdzisław Najder)指出,康拉德的剛果行令他否定「陸上族群」(land-dwelling community)的價值觀 。不論是早期的海上小說、中期的政治小說、或是具浪漫(romance)文風的晚期小說,康拉德的作品在在呈現「陸地」與「海洋」的鴻溝:陸地充滿誘惑,腐化人心;海洋提昇心智,造就英雄 。〈黑暗之心〉的馬羅與康拉德一樣永遠心繫大海:「浪濤聲有如兄弟之音,帶來喜樂。是自然的,有其道理,有其意義。」(19)
不過在馬塔地他倒結識了影響至深的「岸上人」凱斯曼(Roger Casement)。凱斯曼已在非洲多年,當時受雇於運輸公司,負責籌劃馬塔地至金夏沙的鐵路。愛爾蘭裔的凱斯曼極度關懷人權,他藉工作之便深入了解殖民內幕,窺探種種慘狀,見義勇為的他日後(1903年)還發起運動,控訴比屬剛果奴役非洲人的暴行。馬羅的感嘆忠實呈現相同的人道關懷:「我見識過暴力、貪婪、慾望這些魔鬼;但是,哎呀!這些強大、貪得無厭、眼睛布滿血絲的魔鬼所支配、所驅使的是人——聽清楚,是人啊。」(23)1916年凱斯曼因支持愛爾蘭武裝暴動被控叛國罪處死,康拉德晚期對他不免語多保留 。但凱斯曼無疑促使康拉德揭發文明假貌,批判殘暴的殖民主義。1903年康拉德向摯友葛拉罕(Cunninghame Graham)大力推崇凱斯曼,因為「他會告訴你很多事情!我試著忘卻的事情;我不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