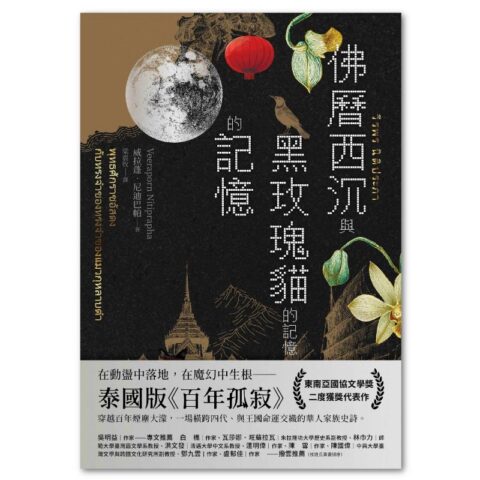我們一家陌生人
原書名:Strangers in the House
出版日期:2010-09-28
作者: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2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6721
已售完
多年之後,我終究變得跟父親一樣,一起走上熟悉又陌生,那條回家的路
《父後七日》編導劉梓潔、作家袁瓊瓊強力推薦
歐威爾文學獎得主拉加.薛哈德用情至深之作
紐約時報盛讚:以無比誠實寫就的美麗之書,擁有開放心靈的巴勒斯坦人,如此坦率!
一生一世,父親和兒子最動人的回憶:歐威爾文學獎得主,拉加‧薛哈德的深情之作《我們一家陌生人》,巴勒斯坦的大江大海!
外婆、媽媽,還有父親,建構了小拉加認識世界的最初模樣,
這一家人生猛又有力,要他們閉上嘴,根本辦不到!
老爸看不成材的兒子不順眼,兒子看曾經叱吒風雲的老爸不長進。這個家,還有整天搞不清楚狀況的外婆,以為過去的六十年都在度假。哈佛法學院畢業的老爸阿齊茲;一個整天耍聰明惹麻煩的兒子拉加,原本以為永遠都無法繼承父業,卻最終還是聽了爸爸的話攻讀法律。拉加還沒出生的時候,他們家和其他住在海法的阿拉伯人一樣,被迫搬離,遷居拉姆安拉。這一家人的故事當然沒有在這裡結束。自此之後,他們每天望向山另外一頭的海法,閃爍著明亮的光輝,家所在的方向。
這是一本回憶錄,說的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家庭革命,內容笑鬧連連,但因為背景是20世紀至今軍事政治暴力最嚴重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這場超現實的鬧劇,將當代歷史透過這一家人所面臨的日常荒謬顯示了出來。父親阿齊茲,以自身專業加上處理國際事務的背景,成為以巴和平條約起草最重要的人之一;兒子拉加,創立巴勒斯坦第一個及最重要的人道人權組織阿勒-哈克。1985年,拉加在美國舉行新書發表會的同時,他的父親在拉姆安拉被人以刺刀殺害身亡。雖然阿齊茲身為和平推動重要人士,也是世界知名人物,但當局政府並沒有積極處理這個案件。拉加及其他家人只感得到悲痛卻不憤恨。雖說這樣的遭遇並非沒有準備,但是如此厄運降臨身上仍令人無從負荷。以一家人的故事探看一個民族的遭遇,《我們一家陌生人》在阿齊茲被謀殺的十七年後出版。父親歷經這樣的事件,讓拉加的日常生活中充滿陰影,這也正是其他一千萬巴勒斯坦人每天必須經歷的恐懼。
一生一世,父親和兒子最動人的回憶,巴勒斯坦的大江大海
※ ※ ※
關於我們一家陌生人的幾個問答
訪拉加.薛哈德
※問題一:從一開始你就把朱莉雅描繪成了一個相當強勢的角色,相較之下,你自己的父親反而是以漸強的方式在書中現身。為什麼你會以朱莉雅為主角開始而非你的父親,或是你自己的出生呢?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父親對我來說,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這個世界卻將他獲撂,從我的生命中把他剝離,所以我的母親及外祖母代表著家裡的這個世界,而這兩位女性,外祖母的存在又比母親來得更強烈一些。她代表著穩定,其他人幾乎無從掌握的安全感,在她身上可以感受得到。這樣的感覺對我這個體弱多病的小孩來說,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及舒適感。這本書的開頭所試著呈現的「我所感知的地方」,並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比透過描述外祖母朱莉雅、也就是那個「我所感知的地方」的人,還容易訴諸讀者的方法嗎?同時,朱莉雅也代表雅法。她也代表了我個性的重心,比較感性、貴族又菁英的那一塊。我在第一章嘗試以一個小孩的感官認知來建構敘事主幹;對還是個孩子的我來說,朱莉雅影響很大。
※問題二:在第三章你寫到,你懷疑對外祖母來說,沒辦法用自己的茶杯喝茶,比海法被占領更慘,你有找到答案嗎,如果有,你怎麼看外祖母這個人?
從海法被驅逐的意義,是離開某種生活,意味著降級、屈辱,以及被貶為難民。靠著堅持照著她的方式(找到最適合喝茶的杯子)過日子,我外祖母反抗了所有要打壓她和破壞她理念的嘗試。她不是一個懷有國家主義或是政治理念的人,卻是頑固的菁英主義者,試著保存她本來的生活方式。被打敗,意味著任憑擺布,外祖母絕不會是放棄的那個人。即使連雅法也待不下去,她仍會盡最大努力保留以往的生活之道,繼續找尋她用下午茶時不可缺的頂級骨瓷茶杯。
※問題三:第四章中,你描述你父親的道德觀相當「模糊」,這也是他得以保持開放、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原因,而且如果到了下決定的時刻,他永遠不會讓別人受難。你父親這樣的態度,在對待你的時候有所不同嗎?
我不認為我父親會特別想以什麼不同的方法對待我,他的觀念傳統,做好一位父親之於的孩子所有義務,用盡全力盡好所有責任。他以身作則、實踐他所認同的道德價值,當然,也期待做兒子的我以他為榜樣;而最後,也的確如此,但他對我的強烈期待我不是沒掙扎過,上頭說的這些,我曾以為將困住我一輩子。
※問題四:這本回憶錄寫成的主要意義似乎是個人的故事,但是你在書中所附的大事紀卻完全沒提到個人事件。請問你是怎麼決定整理這個大事紀?又,這本書是把個人故事與外在世界的政治緊密交織而成的嗎?
我一直認為書應該可以被單獨作為檢視。但是我覺得如果有些讀者讀這本書可能會要有一些與這些經歷相關的政治及歷史背景,進而可以更清楚認識過去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在這個大事紀中,用我所能夠最客觀的方式提供重要的事件資訊。其中所列舉的事情,包括重要歷史事件及與書裡提到的故事相關的事件。我的故事到處都有政治的痕跡,這是事實,但這本書不是政治書。大事紀只是幫助讀者能夠更容易閱讀,如果把個人紀事放入這個大事紀中,就與這本書想要呈現的個人故事精神相互矛盾了。
書評、推薦
一名律師與他的父親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為真理而奮鬥的故事,一本哀傷卻極尊嚴的回憶錄。作者筆調清晰而簡單,不帶痛苦,跳脫了悲情因而更顯力度。
──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魂牽夢縈,一本全巴勒斯坦人的招魂之書。
── 美國《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上百篇的政論文章也無法像這本書清楚地說明,中東未見和平的原因。
── 美國社會學家阿摩斯.阿隆(Amos Elon)
目次
我們一家陌生人(1-23章)
結語
後記 一個巴勒斯坦之子的正義追索
附錄一 文/安東尼•路易士
附錄二 大事記
序
後記:一個巴勒斯坦之子的正義追索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接到一通拉姆安拉醫院院長打來的電話。「一個很有可能就是殺害你父親兇手的人剛剛坦承罪行。他從希伯崙被送到這裡,肚子上有嚴重的槍傷。你想來這裡看看這個人嗎?」
自從那位希伯崙軍事總部的警官否認這同一個人招認殺害我父親至今已經悠悠過了六個年頭。
病患受的傷是在希伯崙住家附近被人從駛過的車上開槍射擊。希伯倫當地的醫院不肯收他;大家曉得他是殺人兇手和通敵者。所以他被送到拉姆安拉,醫院也予以救治。
接下來的幾天,我反覆尋思是否要去醫院看這個我已經追索超過八年的男人。我密切留意他的傷勢。我知道他狀況不佳,他發出惡臭,有一條腿被截肢。人家告訴我來了個身份不明的訪客,他整天臥床,呻吟不斷。接著他哥哥來探望。人家形容他哥哥陰沉兇惡。「像隻野獸一樣。」他帶了一顆西瓜。病房不准攜帶食物,不過誰敢出面阻止。兄弟倆剖開紅肉西瓜,用手抓了就啃,吸吮汁液,滴得到處都是。沒多久同房的病患就要求搬走。換房的要求得到核准。醫院裡人人曉得離他們遠一點為妙。幾天後病患傷勢惡化,呻吟聲加劇。他死了。我沒有去看。
那個禮拜正值我四十三歲生日。父親出現在我夢裡。我們一起整理家中幾個架子的東西。他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他的頭靠在我的肩膀和胸膛。我們非常親密和快樂,場面溫暖而慈愛。當時我感覺或許在兇手死了之後我父親的靈魂得到平靜。或許更可能是因為我終於能夠敞開胸懷迎接我的父親,如今我可以卸下追索殺父兇手的重擔和罪惡感。這是長久以來我第一次夢見父親顯露出接納、慈愛和平靜。
在這之後又過了十二年,這名死在拉姆安拉醫院的男子千真萬確是謀殺我父親的兇手才得到最終的證實。消息來自我的朋友,一位英國歷史學者,他從一名看過安全部門秘密檔案的以色列前任內閣部長那裡聽到這件事情。如今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懷疑,和我父親謀殺案調查有關的痛苦回憶――我畢生最難熬的那兩年――一一浮上心頭。那些我寄予信任、負責這場調查騙局的人不僅從一開始便知道兇手的身份,他們還利用我的弱點,故意誤導我。
警探聲稱謀殺者來自拉姆安拉的基督教家庭,他們就在我們事務所隔壁開店。他們持續拘留被指控的人,接著,在沒有講明他是無辜者的狀況下將其釋放,故意讓我知道他是頭號嫌犯,只可惜他們缺乏明確的起訴證據。他們一定希望我會動用自己手頭的法律。用這種方式他們就可以讓全世界看到巴勒斯坦人有多麼原始落後,即便像我這樣口口聲聲把法治掛在嘴上的人也不例外。如同歷史上每一個殖民者那樣,以色列一貫企圖讓巴勒斯坦人互鬥對立,驅使他們鋌而走險。
那幾年是我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我,讓我免於衰頹的絕望。七年之後,當奧斯陸協議簽署使我寄予以巴和談的希望破滅,我又經歷一次椎心刺骨的絕望。我遭受的精神死亡之苦應該和我父親八○年代初期忍受的相似,當時他已經覺得局勢無可挽回,和平的機會渺茫。要是他有寫下一生遭遇的天資和意願,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他卻只能告誡我唯有權力才是真的有用。他不願意接受寫作同樣也是權力的一種行使,足以撼動人心,改變觀念,鼓舞力量朝新的方向前進。《我們一家陌生人》這本書的寫作救了我。
如今真相大白,那麼過去我質疑的種種問題更迫切地回到檯面:兇手到底提供了以色列政府什麼東西讓他可以有恃無恐地謀害我的父親而免受懲罰?他是否幫助他們在土地交易上取得猶太屯墾區所需的資源?是否這是吸收其他通敵者的手段?或者他僅是一個受僱執行骯髒脅迫任務的小嘍囉?我曉得每個殖民政權都會從被殖民的百姓當中吸收通敵者。然而,對我傷害最大的是想到當我四處奔走,向色列官僚和社會各個階層當中不同的官員和我父親的友人呼籲求助,不管是警政部長,調查小組的領導人,或者高等法院的法官,或者其他和我父親往來密切、正式前來弔唁的友人,他們統統一定知道兇手不可能被繩之以法,因為他替以色列政府立下汗馬功勞,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
在以色列似乎安全部門凌駕其餘的機構,控制著國家的走向。由它決定對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何者至關緊要。替一個追求和平的人伸張正義與卑鄙的通敵者之間,安全部門――與其身後的政府――選擇了後者。「安全」的霸權及其對政策的主宰並沒有隨著時間減弱。它會抓住任何東西來強化自身的主宰。由這一點看來,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適足以勾勒出兩個社會之間的巨幅圖像。好幾萬個居住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北方接壤的黎巴嫩的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慘遭殺害,以色列強大的陸海空兵力發動侵略和戰爭,他們誤以為這是保衛以色列國家所必需的手段。偏袒通敵者勝過追求和平人士依循的也是相同的邏輯。
翻開以色列一九六七年戰爭的紀錄,研究歷史的人可以找到幾份會議檔案,與會者有我父親和其他來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帶著和平計畫聯繫以色列政府,想要在戰後迅速解決衝突。以色列的歷史學者,湯姆.斯哥夫(Tom Segev)將這些巴勒斯坦人描述成「合作者」(collaborators),他寫道:「以色列的紀錄顯示他們對於合作者抱持一種矛盾的價值觀,他們既鼓勵又鄙視合作者。」
這麼多年以來,以色列偏愛與合作者而非巴勒斯坦愛國人士打交道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正如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如此痛苦地顯示出來那般。從一九九一年馬德里國際和平會議我參與協商的個人經驗可以得知,相同的態度依舊佔了上風。我父親提交他的和平方案過了二十四年之後,以色列依舊迴避那些追求協商擬定真正和平協定的巴勒斯坦人士。相反地他們拉攏可以和他們簽署屈服文件的合作者。不把和平當作自身安全的屏障,以色列反倒持續專門仰賴軍事武力,一味拒絕承認它的巴勒斯坦對手做為一個民族團體,如同所有的民族團體一樣,有自決的權力。
去年夏天巴勒斯坦地方電視臺有位製作人找我,打算拍攝一部關於我的工作的紀錄片。籌備過程中派來訪問我的研究員問我是否想要討論我父親的謀殺案。就在那時我了解到如果同意這樣做,我得用「殉道者」(shaheed)指稱我的父親,否則在本地觀眾耳中聽起來會覺得很怪,「兇殺」(murder)一詞他們只會用來描述殺害一名通敵者。但我不能這樣做。在我眼中,殺害我父親的罪行絕對不是用殉道者來稱呼他就可以變得比較好聽。
我父親是被一個替以色列政府效勞的卑劣的通敵者冷血謀殺。就是因為如此,以色列警探幫他遮掩可憎的罪行,未曾將他繩之以法。我所追求的俗世正義,不管是為了父親或為了更廣泛的同胞,絕對不是用神聖的字眼來昇華正義闕如的後果就可以妥協折衷。就讓宗教的問題和來世的一切留待其他的權威來論斷。
這次經驗讓我了解到我心目中的正義和我自身社會其他許多人之間的距離,以及以色列促成了一個何等新奇的現實。如今必須處理新生一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週遭圍繞的穆斯林的問題。教人傷心的是我居然沒有想到利用地方電視節目的機會論說我對俗世正義的信念。不過我又怎能希望自己做出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陳述?我在父親謀殺案調查騙局當中所經歷的漫長痛苦的折磨徒然見證這種正義蕩然無存而已。
不過這已經超越我父親的個案。來到二十一世紀,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是最後少數殘存的例子之一,一個國家被殖民計畫進行宗教剝削以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土地。我深深相信唯有這些奇特的歷史、宗教與國際法律歪曲受到挑戰,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才能相互接納,如同我父親和我力所能為。那麼,到時候我們的家園再也不會有陌生人。
拉加.薛哈德寫於拉姆安拉
二○○九年五月
作者: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
作者簡介
拉加‧薛哈德 Raja Shehadeh
備受讚譽的自傳《巴勒斯坦的步伐》(Palestinian Walks)一書的作者,該書贏得2008年的歐威爾獎。他同時也寫了廣受好評的《鵯鳥止歌》(When the Bulbul Stopped Singing),曾搬上舞台劇演出。他是位住在拉姆安拉的律師和作家。他創立了開拓性的、無黨無派的人權組織「阿勒-哈克」(Al-Haq),成為國際法律人協會的分支機構,他還寫了數本關於國際法、人權和中東的書籍。
譯者簡介
郭品潔
著有詩集《讓我們一起軟弱》;譯有《簽名買賣人》、《戀人版中英詞典》、《青春,飢不擇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