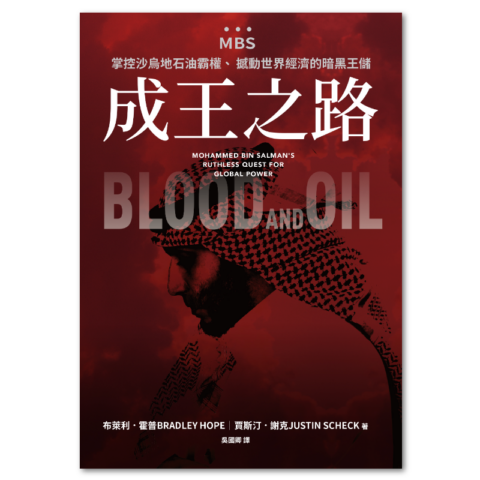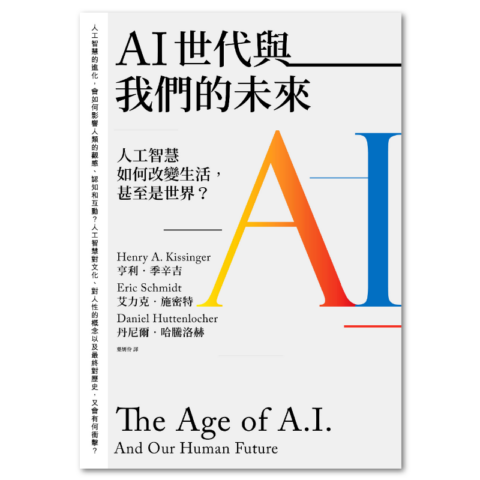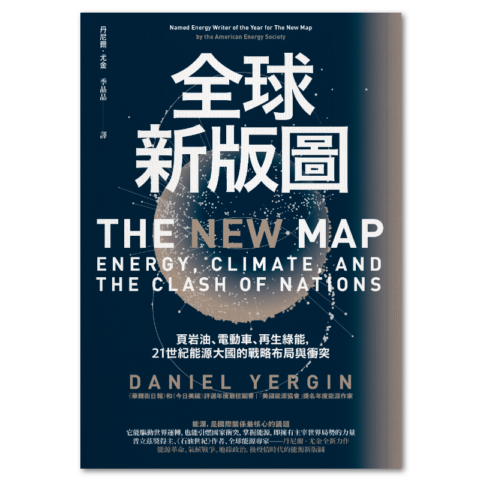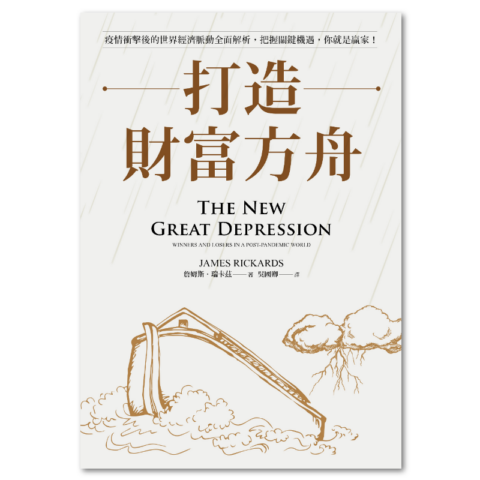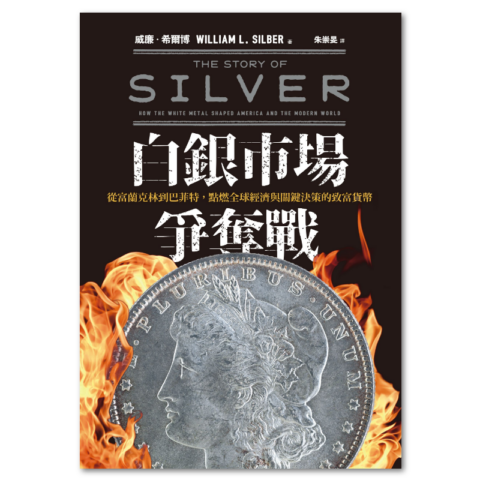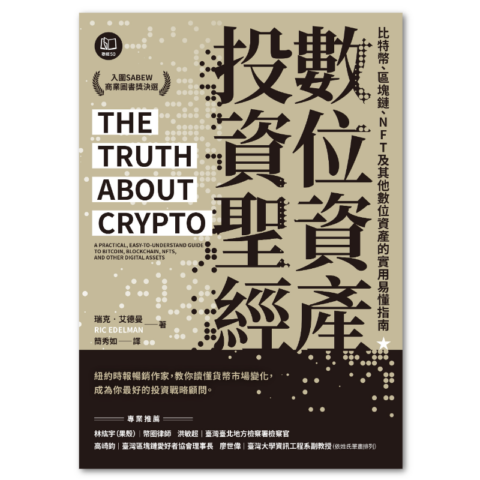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原書名: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出版日期:2008-06-25
作者:余英時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84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2907
已售完
本書以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為中心,全面考察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外關係,在廣泛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審視了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對厘清諸多近年來的史學熱點問題頗有裨益,對了解中國歷史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如納貢體系,依據當時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對中國納貢體系在漢代的建立與成長,做了極其精彩的闡述。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第一章 導論:問題及其緣起
第二章 政策背景和貿易基礎
第三章 納貢體系下的漢胡經濟關係概況
第四章 歸降的胡族人及其待遇
第五章 邊境貿易
第六章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
第七章 海上貿易
第八章 結語:歷史視野中的貿易與擴張
漢代的飲食
匈奴
評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
自序
我在本書中嘗試以貿易與擴張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中心主題,對漢代與胡族之間的經濟關係進行系統的描述。這一工作之所以可能,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背景。
首先,我們今天能夠獲得大量即使是漢代兩個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和班固也無法看到的資料,尤其是許多近來的考古發現。其次,儘管現代中西方學者對這一主題所涉及到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進行了縝密的考察,但現代歷史研究的結果仍然需要在解釋框架方面得到加強,以便其意義能夠更容易得到認識。
最後,更好地理解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的需要在日益增強。近年來,中國的貢納體系在處理西方對清王朝的挑戰時所暴露出來的不足之處,已為許多著作所涉及。眾所周知,在面臨新的世界秩序時,這一體系已經崩潰而無法修復;但是應該記住,中國的貢納體系有著悠久的歷史。我認為,要對它作出任何公正的評價,不僅必須要考慮到它的衰落和崩潰,而且必須要考慮到它的建立和成長。鑑於這一體系在漢朝時期開始形成,因此我依據當時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來分析它的發展演進。
在設計本書的整體框架的過程中,我主要依靠各個朝代的正史記載,因為在其編年紀中對基本的事實都有記述。正如我在前面的解釋中所指出的那樣,本書極大地受益於現代歷史學成就,如果沒有現代歷史學成就,任何綜合性研究(即使像本書這樣有限的綜合研究)都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
考古學的發現主要被用於證實歷史記載。然而,在重構漢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尤其是絲綢貿易的過程中,考古學的證據發揮了主要作用。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敦煌和居延發現的漢代簡牘資料,這些資料是任何本段歷史的研究者都不能夠忽略的。在許多場合中,它們對於我澄清邊境貿易的制度背景極有幫助。
每一本書都是其作者欠付他的老師和朋友的知識債務的一個標誌。我的書也不例外。我首先要提到錢穆博士,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本科學習期間,正是他激勵我進入中國研究領域,同時教導我熱愛中國歷史。我要特別感謝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他不僅指導了本書每一階段的寫作,而且親自作序,為本書增色不少。我還要感謝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教授和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勞榦教授,他們熱心地閱讀了本書的部分或全部初稿,並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見。
1963年至1966年,從密西根大學洛克罕研究生院獲得的三筆研究經費,使我能夠有機會到美國的幾個亞洲圖書館為本研究收集資料。在同一時期,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為本書的準備提供了物質上的便利,不僅給予大量打印服務,而且為我配備研究助手,使我能夠將重要的德國和俄國考古資料結合到我的研究中。我特別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教授對我的不斷激勵。此外,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工作人員的熱情支持,使本稿得以迅速付梓。
余英時 麻薩諸塞 劍橋 1966年10月
第一章
導論:問題及其緣起
作為一個歷史時期,漢代中國在眾多的輝煌業績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在貿易和擴張方面所達到的前所未有的成就。絲綢之路的開闢和通往中亞的西北通道的開通,儘管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但也只是構成整個歷史的一小部分。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講,貿易可以包含所有類型的交換,這些交換可以涉及到一切有經濟價值的東西;因此,韋伯把古代君主之間無償的禮物交換視為一種貿易形式——「禮物貿易」 。然而,就傳統中國來說,皇帝的禮物與胡族的納貢之間的交換長期以來就被稱為「通貢貿易」 。另一方面,擴張也是多方面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擴張的涵義包括從最具體意義上的領土擴張到最抽象意義上的文化擴張——中國對境外異族的文化滲透,或者簡言之,就是使之中國化。
儘管在概念上它們是截然不同的,但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現實中很難將它們割裂開來。在整個漢代,它們通過相互促進並肩發展。但是,任何想弄清它們二者中何者為原因、何者為結果的嘗試都將不可避免地以失望而告終。事實上,其作用都是雙向的:有時是貿易為擴張鋪平了道路,有時是擴張為貿易開闢了機會。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在這裡注意力應該更多地集中在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上,而不是將二者割裂開來的任何一方。
從歷史的觀點看,這一時期的貿易和擴張最初只是對北部和西北邊境上匈奴的威脅作出的反應,但結果是,不僅許多胡族群體,諸如北部的匈奴、羌、烏桓和西南夷被納入帝國的範圍之內,而且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被中國化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擴張到了西域和中亞,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與更偏西的國家建立了貿易往來。儘管其後來的發展在漢帝國歷史上非常重要,但西部擴張仍然只能被理解為一種附帶的趨勢。在總的對外關係領域,一直為朝廷所關注的中心是如何成功地對付中國邊境的各個胡族群體,以防止他們擾亂帝國的秩序。只有服務於這一目的時,西部擴張才是必要而值得一試的。簡言之,它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這段歷史為這一看法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譬如說,漢武帝死後,其過度的擴張政策在朝廷中遭到了嚴厲的批評 。甚至奉行擴張政策的漢武帝本人也在臨死前下詔悔過 。在下文中將會看到,幾個繼任的皇帝,尤其是西漢的宣帝和東漢的光武帝,在是否遵循對西域採取擴張政策上大費躊躇;一些朝廷官員甚至提出了頗有意思的反對擴張的理論。然而,最好的證據可以在東漢對納貢的各胡族群體的援助比例中找到:每年用於整個西域納貢國家的支出總額是7,480萬錢,而僅用於南匈奴的開支數額就達10,090萬錢。
所有這些事實無可辯駁地表明了漢代對外政策的重點指向何處。正是基於這種理解,本研究才特地將重點放在中國和邊境胡族之間普遍的經濟往來上。由此,歸順的胡族在中國的安置情況和中國與非漢族人之間的境內外貿易,都會被視為本研究中同樣重要的不同方面。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呈現出有關貿易和擴張的基本事實的均衡圖景。而且,通過對這些歷史事實的分析,也企望揭示出漢代中國與胡族之間經濟關係的總體結構。這裡的結構,不僅包括其間發生的各種類型的經濟交往方式,而且也包括這些經濟交往是如何被嵌入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中去的。
在西方,傳統中國一直被稱為「儒教」國家或者「儒家」社會,而這一稱謂的涵義決不是清晰明瞭的。如果這一稱謂意指一個國家或社會是遵照先秦儒家關於政治和社會的著述所確立的路線或者原理建立起來的,那麼,漢代的中國也許可以被看作是比其後任何朝代都更加典型的儒家社會。而且,就制度層面而言,漢代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中華帝國秩序基本模式的形成時期——就傳統內部的不同發展階段而言,這一模式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從這個觀點看,對漢朝時期的中國與胡族之間經濟關係結構的詳細分析也可以闡明所謂「儒教」國家或者「儒家」社會的特徵。
在中國歷史上,胡族的威脅問題並不是始於漢朝初年的。為了理解整個歷史背景,我們必須將其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時期。胡族的威脅問題最早在春秋時期(前771-前481)就變得特別嚴重。首先,我們知道,周的都城從今陝西西安附近的鎬東遷到河南洛陽的活動標誌著春秋時期的開始,而且周的遷都活動即便不是由西北邊境的戎人入侵所導致的結果,也與之有直接關係。整個春秋時期,胡族都在不時地入侵漢族各國。因此,擊退胡族是霸權體系下霸主國家最緊迫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義務之一。在這一時期,牢記漢族更多地是在文化標準上而不是種族意義上有別於胡族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北部和西北部的戎人和狄人被視為野蠻人;另一方面,南方欠發達而富於進攻性的楚人也同樣被視為野蠻人。《公羊春秋》說:「南夷(即楚)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就經濟生活而言,春秋時期漢族和胡族之間的區別在本質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區別,後來漢代的情況也是如此。作為遊牧民族,除了放牧牲畜的目的之外,胡族人通常對易於攜帶的諸如金錢和商品等可流動的財富比對土地更有興趣 。
早在西元前6世紀,在與胡族人長期密切的接觸中,漢族人就了解了他們的經濟行為模式,而且開始利用這一點來對付他們。比如,西元前568年,晉國(在今山西境內)的大臣魏絳提出了一個針對鄰近戎狄的和平政策,他指出了和平協議必將帶來的大量好處;在這些好處當中,下述兩點尤其與討論的主題即貿易和擴張有關。第一,戎人和狄人都是遊動不居的,因此,他們寧願要貨物而不要土地。可以設想,通過和平的手段,可以用錢買他們的土地讓漢人耕種。第二,隨著和平的到來,邊境上的緊張局勢可以得到緩解,反過來,邊境上的漢族農民也有可能從事他們的農業工作 。
根據第一點,我們可以知道,甚至在這樣早的時期,貿易就像在漢代一樣已經被中國政府當作控制邊境上的胡族的政治武器來使用了。拉提摩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他強調,在抵抗胡族的戰爭中,戰國時期(前450?-前221)的中國是在進行擴張,而不是保衛它的領土 。現在,這第一點進一步表明,中國的擴張不僅採取戰爭的形式,而且也採取貿易的形式,有時候貿易證明是更加有效和徹底的方式。根據第二點,就像下文會充分展示的那樣,很顯然,春秋時期胡族的威脅預示了漢代的情況,即,遊牧民族對漢族農民定居生活的威脅隨時在不斷的邊境襲擊中表現出來。
正如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那樣,戰國時期尤其是西元前3世紀以後,中國和胡族的經濟交往普遍地存在於許多邊境地區。北部的燕國據稱和鄰近的胡族尤其是位於東北的烏桓有著密切的聯繫。燕國國人的貿易關係據說延伸得更遠,甚至到了朝鮮 。這一文學性的記載得到了現代考古發現的證實,在朝鮮發現了大量稱為「明刀」的刀幣 。1958年至1960年,東北地區發掘了幾個戰國時期的墓葬;這些墓葬被認為是屬於所謂的東胡的,很可能是烏桓人的。遺物中有包括武器在內的青銅器,清晰地顯示出其受中國文化和匈奴文化共同影響的痕跡。譬如說,戰國時期的漢族戈戟就可以作為很好的證據,證明這些胡族人和中國內地的漢族人之間一定建立了某種聯繫,尤其是經濟聯繫 。
在中國西南的邊境地區,尤其是四川,土著蠻夷人與內地漢族之間的文化和經濟聯繫也許可以追溯到殷周時期。但是,這種聯繫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西元前316年秦國征服蜀地(四川北部)之後,才變得意義重大 。考古調查表明,在戰國時期,來自中原各國的輸入品被不斷地帶進四川,這些物品包括秦的青銅器皿,楚的青銅三足鼎和武器。在四川東部,不但發現了中原風格的產品、銘文和鐵器,而且發現了秦國的銅錢,這是土著蠻夷人與外部的漢族之間有貿易交換的可靠標誌 。
在這一點上,考古發現能夠結合文獻資料進行最富成效的研究。根據文獻記載,直到西元前3世紀末,只有極少數的中國人是通過與四川和雲南的土著蠻夷之間的貿易而致富的。譬如,著名的蜀地卓氏,靠鼓鑄冶鐵致富,最終壟斷了與中國西南邊境上的蠻夷之間的貿易。大約與此同時,另一位著名的四川商人程鄭,也經營冶鐵業,通常與一群在歷史中被描繪為「椎髻之民」的蠻夷之間進行貿易 。在漢代,這些蠻夷人顯然與那些被總稱為西南夷的部落是相同的 。很可能正是通過這些中國商人中介如卓氏、程鄭,中國的物品尤其是金屬製品得以首次到達西南邊境,最近考古學家們發現了這些器物。
在西北邊境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中國商人的活動。據載,一位名叫烏氏的商人(在今甘肅境內)通過與胡族首領之間的絲綢貿易而致富。每次他賣了牲畜之後,就買一些精美的絲織品或其他一些珍奇的物品獻給戎王。戎王總是以十倍的價格回報他,而且賜給他牛和馬以示答謝。就像故事中所講的那樣,通過這種方式,烏氏 得以積累起不計其數的牲畜 。再引證另外一個例子:西元3世紀晚期,偉大的漢代歷史學家班固的祖先,作為畜牧業的最主要的家族出現在西北邊境地區。班氏的馬、牛、羊的數量達到數千群。而且,根據班固的說法,其家族的成功激勵和鼓舞了邊境上的中國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追隨班氏,步其後塵 。
從總體上看,正如上文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樣,不應該過分強調戰國晚期中國與胡族之間的邊境貿易的歷史意義。首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必須將其放置到整個戰國時期手工業和商業快速發展的總體背景以及當時各個國家之間或地區之間貿易的特殊背景中進行考察。第二,戰國時期所實行的那種個別中國人與胡族人之間的邊境貿易,也許可以合乎邏輯地看作是漢代邊境上的許多中國商人所採取的一種特殊貿易模式的原型,這一點將在下文中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