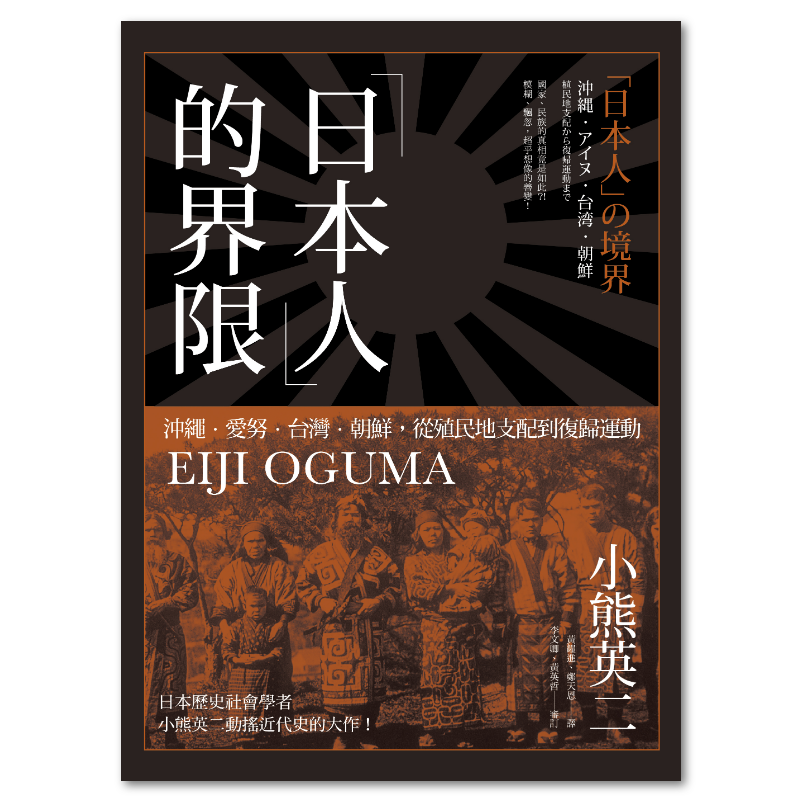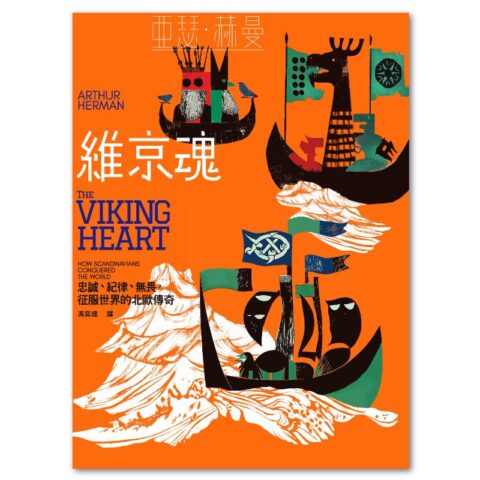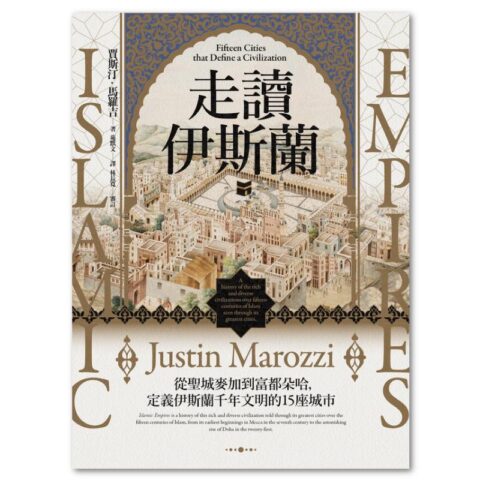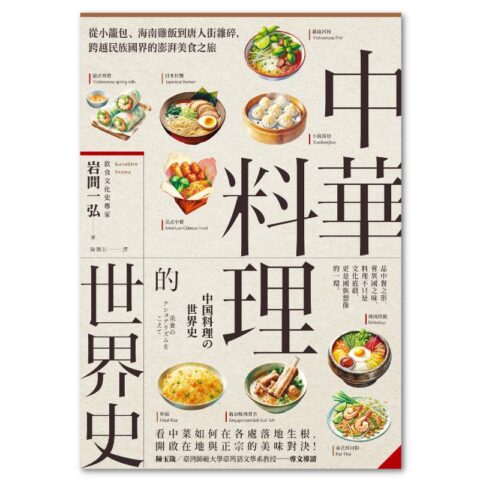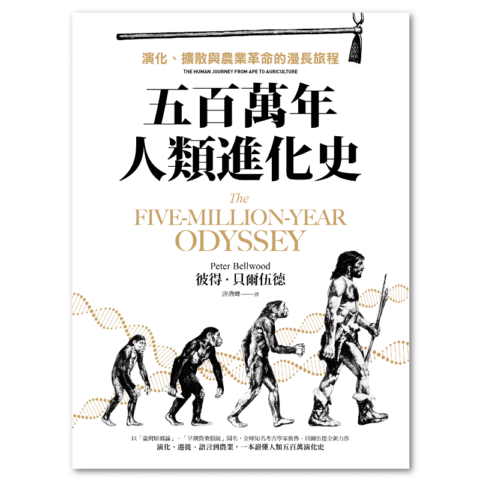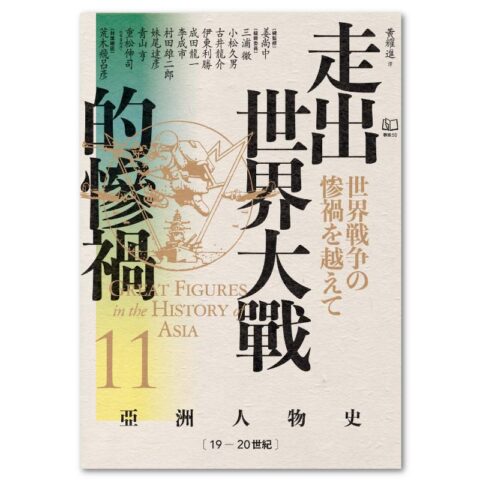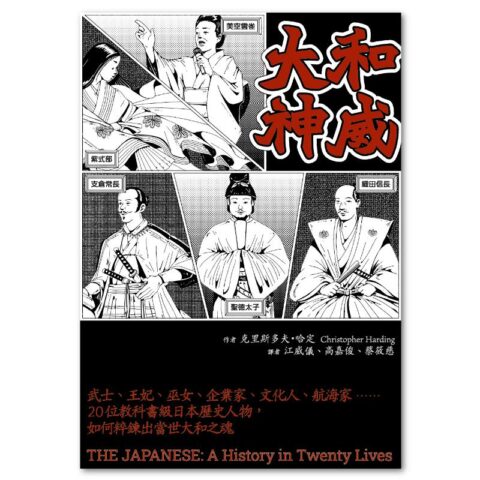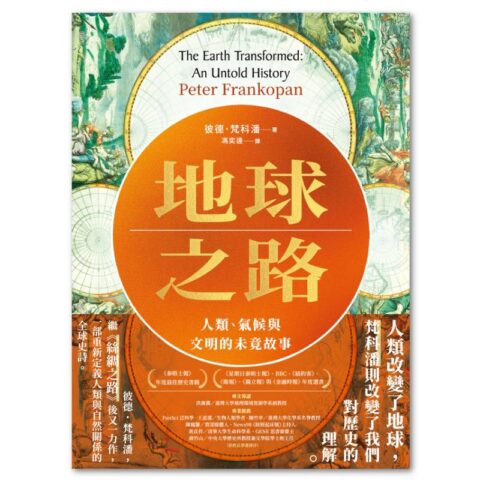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原書名:「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
出版日期:2020-11-12
作者:小熊英二
審訂:李文卿、黃英哲
譯者:黃耀進、鄭天恩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656
開數:18開,長23×寬17×高4cm
EAN:9789570855562
系列:歷史大講堂
尚有庫存
民族的界限竟是如此模糊、飄忽,超乎想像的善變!
中央吞噬地方,還是地方反噬中央?
帝國擴張帶來的也許並非壯大國家的福音,而是對自身定義的挑戰。
日本知名學者小熊英二,透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試圖探詢「『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質問曖昧難釐清的民族與國家界限,直探文化最核心、地域最本質,擘劃出日本與其周邊地區近百年來若即若離、糾纏難解的歷史。
小熊英二表示,自19世紀中旬開始,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並非一以貫之,反而政策相對模糊,其統治下的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的定位和人民因而搖擺不定,中央和地方相互映照、拉扯,反覆辯論「何謂日本、何謂日本人」?指出了1879年以後,日本與周邊地區的辯證中,國家與人民的概念是如何複雜而多層次,並詳細分析各時期的政策、法律、教育方針,呈現出尚待我們明辨、釐清的幽微處,以及這些衝突與融合如何同時影響、挑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定義。
《「日本人」的界限》梳理了以日本為中心,複雜多變的民族、國家面貌,探問日本百年來的殖民政策、國家與人民的本質,釐清近代東亞歷史最難辨難解的一面。
作者:小熊英二
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1996年以《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賞;2003年以《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2013年以《社会を変えるには》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賞。《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其他重要著作包括《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市民と武装 :アメリカ合衆国における戦争と銃規制》、《清水幾太郎:ある戦後知識人の軌跡》。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已於2015年公開上映。
審訂:李文卿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兼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中文專著有《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想像帝國:戰爭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合譯有北岡正子著《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從弘文學院入學到「退學」事件,青年魯迅的東瀛啟蒙》等。
審訂:黃英哲
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暨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近現代史、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文專著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日文學術著作多部。
譯者:黃耀進
翻譯工作者。單譯有《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等;共譯有陳舜臣《半路上》、《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東京審判》等書。
譯者:鄭天恩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譯有《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作品。
I
序章
「日本人」界限的變動
「日本」與「殖民地」,以及「歐美」
「包容」與「排除」
「政治語言」與「無法表達的事物」
用語說明
第一章 琉球處分──納入「日本人」
對「國內人類」的統合與排除
外國人顧問的提議
作為「日本人」的琉球人
圍繞歷史的爭端
第二章 沖繩教育與「日本人」化──同化教育的內涵
維持舊慣與養成忠誠心
「文明化」與「日本化」
改造歷史觀
第三章 「帝國北門」的人們──愛努教育與特別保護法
從國境紛爭到成為「日本人」
「日本人居住的土地」
傳教士的威脅
「漸化」理論
設立《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
第四章 領有台灣──同化教育的矛盾與衝突
台灣統治的紛亂
外國人顧問的同化反對論
是「殖民地」或「非殖民地」?
國防重視論與對歐美的意識
「日本人」化教育的開始
捲土重來的非同化論
「漸進」的折衷型態
第五章 總督府王國的誕生──台灣的「六三法問題」
實際上的立法權
「台灣自治王國」構想
作為折衷案的「不是法律的法律」
議會方面的反對
「日本人」的意義
後藤新平的台灣王國化
依據不明的獨裁統治
第六章 身為韓國人的日本人──日韓合併下的「新日本人」戶籍問題
承襲的折衷型態
「漸進主義」的教育
國籍上的排除與包容
同化言說的完成
II
第七章 差別即平等──殖民政策與種族主義
法國同化主義與啟蒙思想
勒龐與同化主義批判的興起
「生物學的原則」
「自治」和「隔離」
「自主」的兩難
兩種差別之間
第八章 「民權」與「一視同仁」──殖民者與通婚問題
高唱「一視同仁」
「殖民者民權」的出現
通婚與「日本人」
第九章 花紅柳綠──日系移民的朝鮮統治論
言論界錯綜複雜的統治批判
民主主義者的文明性同化主義
大亞細亞主義者的文化多元主義
自由主義者的分離主義
「民族問題」的狹路
第十章 內地延長主義──原敬與台灣
作為文明化的「日本人」
編入「日本」的模型
總督府的抵抗與「漸進」
受挫的統治改革
第十一章 統治改革的挫折──朝鮮參政問題
總督府主導的統治改革
自治或者參政權
「總督府自治」的出現
III
第十二章 沖繩民族主義的創生──伊波普猷的沖繩學
對沖繩而言的同化
重層的少數族群
作為屏障的同祖論
沖繩民族主義與「同祖」
排除與同化的連鎖
身為啟蒙知識份子
受挫的沖繩民族主義
第十三章「異身同體」的夢想──設置台灣自治議會請願運動
作為獲得權利的「同化」
對於多樣性的期盼
對殖民政策學的置換概念
基督教徒與大亞洲主義者
多元的日本、多元的台灣
「違憲」的界限
分裂的請願運動
第十四章 「生於朝鮮的日本人」──唯一的朝鮮人眾議院議員•朴春琴
作為「日本人」的權利
居住內地朝鮮人的參政權
通往「我們的國家」的崎嶇之路
「一視同仁」的高牆
虛像的「日本人」
第十五章 東方主義的折射──柳宗悅與沖繩語言論爭
東方主義視野下的「民藝」
沖繩的強烈反彈
「西洋人」視角的方言擁護者
對「日本人」的強調
沖繩同化的最終階段
第十六章 皇民化與「日本人」──總體戰與「民族」
否定「朝鮮」
民族概念的相對化
平等與現代化的期待
第十七章 最後的改革──戰敗前的參政權
界限動搖的三要因
移籍問題的浮現
無法跨越的臨界點
名為「日本人」的牢獄
IV
第十八章 國界線上的島嶼──沖繩作為「外國」
身為「少數民族」的沖繩人
「琉球總督府」的誕生
排除在「美國人」之外
身為「日本人」卻又不是「日本人」的存在
第十九章 從獨立論到復歸論──戰敗後的沖繩歸屬論爭
沖繩獨立論與美國觀
由保守派主導的復歸運動
急遽浮上的歸屬問題
搖擺中的復歸論
第二十章 「祖國日本」的意涵──1950年代的復歸運動
作為人權代名詞的「日本人」
以親美反共為號召的復歸運動
日本民族主義的語彙
第二十一章 革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受學者的「日本人」論點影響的沖繩觀
作為「亞洲殖民地」的日本
「健全民族主義」的極限
單一民族史觀的興起
從「殖民地支配」到「民族統一」
作為民族統一的琉球處分
成為批判用語的「琉球獨立論」
第二十二章 1960年的方言牌──戰後沖繩教育的復歸運動
作為復興活動一環的復歸
方言牌的復活
對「日之丸」、〈君之代〉的獎勵
憧憬與拒絕的共存
「祖國是日本嗎?」
政治上的變動與轉換
第二十三章 反復歸──1972年的復歸與反復歸論
琉球獨立論的譜系
復歸的現實化
對「面具」的嫌惡
與獨立論的距離
「否」的思想
結論
後進帝國主義的特徵
國民國家的包容
官方民族主義
「脫亞」與「興亞」
分類外的曖昧
被支配者的反應
有色的帝國
後記
圖片出處
注釋
序章(節錄)
所謂「日本人」這個詞彙,指涉著哪些範圍裡的人們?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設問。
這個「日本人」的界限,又是依據哪些要素而設定的?這是本書的第二個設問。
透過「政策論述」的觀點來檢證近代日本的邊境地區—亦即沖繩、愛努(現今北海道)、台灣、朝鮮等地—重新檢討「日本人」和「日本」的概念,便是此書的主題。
「日本人」界限的變動
所謂的「日本」、「日本人」,這些詞彙指涉的範圍究竟到哪裡(為何)?乍看之下似乎是很奇怪的設問。在現今普遍的概念中,認為上述地區裡的沖繩及北海道一直都是「日本」,而朝鮮與台灣則不是「日本」,只是在某段時期以「殖民地」形式領有過的區域。但是,這種區分相當模糊不清。
例如,近年來有人傾向倡議將北海道與沖繩也定位為日本的「殖民地」。這種看法認為,上述兩地在明治時期之前都屬於別的「國家」,是後來透過侵略與同化政策才將其納入「日本」。同時就侵略與同化政策而言,與對朝鮮或台灣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
不過,面對這樣的論述,也有可能採取相反的觀點。亦即,在二戰之前,無論朝鮮或台灣人,還是沖繩與愛努人,同樣都擁有日本國籍,是法律定義的「日本人」。就這點而言,住在日本拓展勢力範圍內—遼東半島租借地(即所謂的「關東州」)以及華北占領地區—的居民,其國籍為「中國人」,另外「滿洲國」的大多數居民(除了住在那裡的「內地人」及「朝鮮人」外),並不具有日本國籍,這些都與前者不同。在1930年代的國定教科書中,理所當然把沖繩與北海道居民視為國民,甚至朝鮮、台灣、樺太(庫頁島)等地的居民,也全都被視為日本的「國民」;另一方面,國定教科書並沒有把「滿洲國」、華北占領區、南方占領區及國際聯盟託管的南洋群島等地居民視為「國民」。從此可看出,這裡存在著與當今略有不同的「日本人」的界限。
但是,朝鮮人與台灣人即便是擁有日本國籍,卻不曾平等享有屬於「日本人」的待遇。以法制面來舉例,他們大部分(居住於日本內地的人除外)沒有參政權,也就是無法在帝國議會中擁有自己的代表;初等教育也非無償教育。愛努人則根據《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沖繩人也得等到1919年才取得參政權。在法制面之外,他們所受的莫大差別待遇,自不待言。即便持有日本國籍,無論在制度上或日常生活中也都受到差別待遇,成為一種雖然是「日本人」卻又不是「日本人」的存在,這就是遭遇到所謂「『日本人』界限」的人們。
本書設定的主題如下:通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探求「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
當然,此處所指的「日本」或「日本人」並非固定不動的實體,而是依據時代或時勢而改變、屬於「言說」層面的概念。某一些人—例如原本居住在沖繩或朝鮮的人們—因為時代或時勢緣故,有時被視為「日本人」;有時則不被視為「日本人」。在這種情況下去質問「這些人是否真的為日本人」,並沒有意義。嚴格來說,「真正的日本人」的概念並不成立。上述這些人在「國籍上」都是日本人,同時他們也以某種形式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另外有一些人—例如沖繩居民—為了論證他們是「真正的日本人」,屢屢拿出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說根據,但這些論證也毫無意義。因為正如本書接下來將討論的,這些學說都是在沖繩已經被納入日本之後才出現。此外,例如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朝鮮人,也曾依據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說來「舉證」為「日本人」的一支。
針對這些現象,本書要探問的是:「這些人為何以及如何被分類為『日本人』?」更準確地來說,這個問題應該是:「所謂『日本』這個國民國家的政治言說,是根據什麼樣的要素與型態來分類,而將某些人納入『日本人』的範圍內;或者將他們排除在『日本人』之外?」本書之所以要探討近代日本統治周邊地區的相關政策論述,並不只是為了回顧日本的歷史,而是要透過這些案例研究來考察驗證「國民國家在設定『國民』界限時的機制」……
1895年,在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獲得勝利的大日本帝國,取得了清朝割讓的台灣。台灣與稍後納入日本的朝鮮同樣具有獨特的地位,雖然皆處於日本國境線的內側,但都是與「內地」制度有所區別的地方。當地居民雖然成為了持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但也被定位成非「日本人」般的存在。
當然,沖繩人與愛努人也是遭「日本人」歧視的對象,但台灣的狀況又與他們有些許不同。即便承受嚴重的歧視,沖繩及北海道在制度上屬於帝國的縣與道,也就是被當作正規的「日本人」納入帝國。然而台灣—如本章與下一章將探討的—在究竟是要把他們包容入「日本人」範疇?或是要自日本人範疇中加以「排除」?在各家提出的諸多議論下,最終仍舊沒有得出明確的方針,只隨著事態而發展。
以下,本章將側重於教育,下一章則將側重於法制,檢證針對把台灣及台灣人包容入「日本」、「日本人」的相關論述之是非對錯。此外,這些關於台灣的論述,一如關於沖繩和北海道的論述,也反應出一個無法忽略的要素,那便是所謂「歐美」這個他者的視線。
台灣統治的紛亂
在檢證關於台灣統治的論述之前,先掌握一下領有台灣時的最初情況。因為這段統治初期的混亂,直到日後仍對台灣的定位帶來影響。
1895年4月,日清締結和約,決定割讓台灣後,日本軍出發前往台灣。然而,台灣當地居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發表獨立宣言,一方面希冀獲得清朝與歐美列強支持,一方面頑強抵抗日本軍。結果,歐美默認了日本有權統治台灣,台人抵抗終遭鎮壓,但在10月宣布平定全島之前,日本軍蒙受了重大損傷,戰死、病死者約有4千5百人—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在內—相當於甲午戰爭中日本陸軍陣亡人數的三成。日後被日本方面稱為「土匪」的漢族武裝集團與居住山岳地區的原住民,仍舊不斷的抵抗,武力鎮壓持續到1915年為止。日本面對意料之外的激烈抵抗,一開始是把總督府定位為軍事組織,實施軍政。發布平定宣言後,1896年3月改採名義上的民政移管,但仍舊保有軍事規條。
此事對於應該採用什麼方法來統治台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決定領有台灣之際,日本方面對台灣的統治構想非常模糊曖昧。根據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說法:「在我們搭船抵達基隆港之前……幾乎誰也沒考慮過。」從這種白紙狀態突然被帶入軍政狀態,為日後的統治烙印下了深刻的軍事性特質。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決定任命軍人擔任總督。在沖繩與北海道,雖然國防是決定統治方針的重大要素,但縣令與道長官仍為文官。然而台灣的制度上與統治中樞內都有軍人的存在。
這種情況當然也反映在關於統治方針的議論上。1896年,首相松方正義提出的當地報告書〈台灣之實況〉中,對於「關於台灣的施政方針」舉出如下兩種選擇:帝國對該島之領有係應專注於國防上之必要,是否欲排除該島土民致力移殖日本人民?或者帝國領有該島以開發富源為主,綏撫該島土民以利用其資本勞力?
如同過去的沖繩,台灣也屢屢作為國防上的據點而被形容為「南門鎖鑰」。究竟統治的目的是要重視國防,將此地改造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或者要重視經濟利潤與成本?這樣的選擇在沖繩與北海道也發生過。在此應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書在這個設問之後又說道:「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亦即軍人與幾乎全數的總督府文官都主張重視國防。
但是此處的重視國防路線,是提議將台灣改造為「日本人居住土地」的方法,並非要把台灣原居民「日本人」化,而是透過推動(日本)移民,將台灣原居民驅逐出台灣島。這份報告書中提及,因為總督府中充滿了這種共通理念,因此為了將原本住在台灣的人驅離該島,故意採用「以嚴酷武斷為最佳手段,一切政令舉動皆採苛暴橫虐、違反公道的方法,使土民怨恨不滿」的措施。
這種共通理念的背後,其實還存在另一項因素,根據決定割讓台灣的日、清之間條約,將給予台灣居民2年的緩衝期間,決定是留在台灣接受日本政府給予的日本國籍,或者賣掉不動產所有權,宣示離開台島。也就是說,這2年之間若能策動台灣居民離開台島,此後只要從日本內地送入殖民者,便有可能把台灣改造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在日本內地也存在著這樣的主張,例如福澤諭吉提倡「模仿彼等盎格魯薩克遜人開拓亞美利加大陸之法,將無知蒙昧蠻民悉數驅逐境外,殖產上一切權力由日本人掌握,舉其全土斷然施行日本化」,「藉兵力進行無情掃蕩,斬草除根,殲滅一切醜類(惡黨之意,指台灣居民),悉數收沒土地,抱持將全島收歸為官有地之覺悟」至於在這種想法之下的實際統治狀況,又是如何?
根據這份〈台灣之實況〉報告書,當時的台灣統治大概沒有能稱得上政策的東西,情況極度混亂。首先日軍在島內各地「蠻橫虐待土民,無故加以毆打並以低價強購商品;或以徵收的名義掠奪物資,占領民家祠廟;或者妄加嫌疑逮捕土民並殺害」,應當維持治安的憲兵與警察也「為了掠奪而毆打鞭笞土民,以靴子踢擊,或妄加嫌疑逮捕拷問土民並殺害」。從日軍登陸到宣布平定台島的5個月之間,台灣方面的犧牲者攀升到1萬4千餘人,之後自1898年起的5年期間,據稱尚有超過1萬人遭到殺害或處刑。
對於統治的失敗原由,這份報告書還舉出「破壞廢除固有風俗習慣」一事。只是這裡指責的並非強制推行日本文化等行為,而是占領與破壞寺院及書院、開挖墳墓與暴露遺骨、侮辱或妨礙婚姻儀式等等,由軍方或殖民者對原居民施加的侮蔑行為而已。這並非是依據同化政策施行的系統性文化侵略,而只是單純的失序暴力。
實行這種殘虐拙劣統治的原因之一,在於派駐台灣官僚的素質和道德之低落。對於被日本政府派遣到台灣的官僚而言,在台勤務不過是地方勤務,他們只想盡早回到日本中央去;而且優秀人才也不願前往台灣,因此人事異動相當頻繁。根據這份報告書「在台官吏大抵為庸才劣等之屬,或是在內地無法謀得職位者,或是行為不檢不見容於內地,而前往新領土尋求仕宦者」,「對職務缺乏經驗才能自不待言,加上轉任頻繁,不僅無法熟悉業務,而且性格好逸惡勞,往往託病逃避公務」,處於「缺勤官吏占定員的1/4乃至1/3,且出勤時勤勉守規矩者寥寥可數」的狀態。
台灣總督府官吏素質低落,已經成為一種固定評價,不僅是止於此份報告書。日後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就形容自己前往台灣赴任是「流放台島」,表示:「在轉任台灣官吏的當下,升官之途已絕。」從大藏省次官(次長)轉任台灣銀行頭取(總裁)的添田壽一也幾乎一口斷定地說:「在內地找不到出路的人會申請要前去(台灣),但在內地能有所作為的人是不願意前往的。」在這種素質與道德低落的情況下,當然也頻頻發生貪污瀆職的行為。根據報告書,官吏「不僅與商業買賣勾結,干預工程建設或商務經營,或者威嚇壓抑土民,強買土地與民宅,還透過其他種種手段積蓄自己財富」。
此外,為了把台灣轉換成「日本人居住的土地」,有必要獎勵從內地前往台灣殖民,但渡海前往台灣的殖民者大多數也是在內地無法維生的下層民眾。〈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指出,居住台灣的內地民間人士「過半與官吏勾結,繳納賄賂,透過各種巧詐手段從事建築營造與採買官方所需物資,皆為貪圖不當利益之徒」。當然他們對原本台灣居民的態度惡劣,「威嚇壓迫土人締結契約,使其賤賣貨物,其行徑幾乎等同盜賊」,「從商人到軍夫、勞工、婦女等,大多數言行暴戾放縱,與土人接觸時肆意詈罵任性毆打,這些情狀看來彷若野獸,毫無親和之情」。
想當然耳,內地人的這種態度自然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抗。對當地居民的歧視意識,或許與北海道殖民者對愛努人的態度相似。然而,台灣與北海道不同之處,是愛努人在北海道統治上屬於不至於造成困擾的少數人口,反過來,台灣當地居民的去留則屬於無法忽視的情況。此外,原本人口密度已經相當高的台灣,也沒有餘地像北海道一般再送入開拓農民,比起作為農民定居下來,寄生在總督府的下尋求一獲千金的拜金者比例更高。這些殖民者抱持的想法,幾乎都是不圖得到台灣人民信任,以長期獲利為目標,而是使用類似犯罪的手法,盡可能在短期間內攫取利潤然後返鄉。
〈台灣之實況〉報告書中陳述這些內地人的態度「不僅讓土人憎惡,同時也助長了蔑視(日本人)的心境」,對大日本帝國而言,來自當地居民的憎惡不僅與統治困難相關,遭「蔑視」則更關係到帝國的威信問題。在威信問題中特別需要關注的,是與這些拜金者一同流入台灣的內地人女性。高揭促進台灣殖民而成立的《台灣協會會報》所刊登的當地報告中,就有這樣的記述:
……無論前往台北或前往台南,在街上見到跋扈橫行的,就是藝者(藝妓),甚至是酌取女(陪酒女)之流……在台北的日本婦女約有1千3百人左右,其中娼妓、藝妓與酌婦(陪酒女)超過8百人,這種風俗使原本應該向人民表現威嚴的公務員,登上這些酒樓,在土人眼前飲酒、同女人嬉戲,呈現至極醜態……土人見此情狀,也不得不以為這些稱為日本人的傢伙果然是狄夷之流,他們口中說什麼文明,其實跟生蕃一樣……
另外這些內地人女性「被」台灣人買春的事態,也成為造成內地人威嚴低下的因素。台灣也有不少內地去的人力車夫,他們一方面侮蔑台灣人並施加暴力,另一方面卻爭先恐後地爭取有權勢的台灣人搭乘自己的人力車,這種舉止同樣也遭到批判。此種現象不限於台灣,也發生在朝鮮。依據1899年前往朝鮮視察的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的說法,朝鮮鋪設的鐵路上,「乘坐中等以上車廂的是西洋人與朝鮮人」,日本殖民者則大多數搭乘三等車廂。殖民者與當地居民的這種關係型態,反映出日本的國際地位,一方面身為領有周邊地區的帝國,但同時也是把貧困階級作為移民送至海外的弱小國家。在這種狀況下,當時有內地的媒體報導形容:「台灣是內地的人的垃圾場。」
在當地居民持續反抗之下,疾呼「重視國防」的官吏倚賴警力與軍力,不斷反覆進行虐殺與掠奪。人才不足導致統治手法低劣與瀆職,又反招來當地居民的輕蔑。而且台灣居民對土地感情根深蒂固,即便過了2年期限,也僅有0.16%的人離開,日本方面的殘虐行為最終只是徒增台灣人的反感。在這種只能說是惡性循環的情況下,4年間便換了四任總督。
在統治實效無法提升的情況下,唯有統治費用不斷攀升。因為當地治安不穩,地方行政機構也尚未確立,所以無法施行地租改正政策—地租是當時稅收的根基—因此在台灣的稅收終究無法補足對台的統治費用。當時日本政府整體稅收約8千多萬日圓,1896年國庫對台灣的補助達690萬日圓,1897年度也有590萬日圓。而且因為預估1897年台灣財政會出現大幅赤字,當時的松方正義內閣企圖對內地增稅,在增稅失敗之後最終總辭。報紙攻擊政府方面的失策,並形容台灣為「內地國庫的一大負擔」、「母國的一大麻煩」。當時甚至出現一種論調,主張以1億日圓價格把台灣賣給歐美的隨便一國。
即便如此,放棄或出售台灣的主張終究未占多數。中日甲午戰爭後,因三國干涉還遼,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於此戰爭中獲得的唯一土地就只有台灣,借用伊澤修二的說法,「台灣是我數千將士以血買來之地」。這種放棄台灣的想法,與報復三國干涉還遼的民族主義復仇輿論並不相容。
而且,即便經濟上出現赤字,台灣在國防上仍具有價值。例如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雖在當時的談話中承認「世人動輒質疑在台灣投下莫大經費究竟能否獲得回收」、「像德國的膠州灣以及俄國的大連、旅順一樣,明顯是許多國家的必爭之地,若我邦未領有台灣,屆時他國在北方據有海參威,在南方以台灣為根據地,那我邦將受雙方夾擊」。在帝國主義競爭的漩渦當中,如同三國干涉中德國與俄國奪取的膠州灣和旅順,考量到被當成歐美列強的前進基地,即便不計成本領有台灣也具有戰略意義,類似這樣的言論在屢見於各處。
雖說如此,對大日本帝國而言,台灣的情況並不容置之不理。不僅因為經濟的負擔問題,也牽扯到帝國面對歐美時的面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