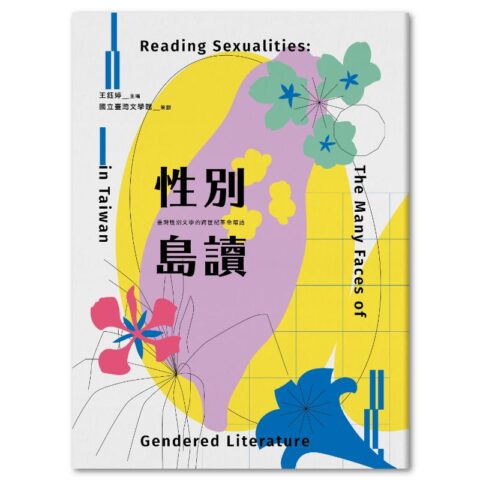中日文學之間:鄭清茂論著集
出版日期:2022-10-27
作者:鄭清茂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5011
系列:聯經評論
尚有庫存
鄭清茂先生為知名學者、翻譯家,在中日文學關係與日本漢文學方面,亦開學界之先聲,為首屈一指的國際漢學者。《中日文學之間》全面集結其學術生涯之中文單篇論著及講稿,其中多篇更曾以英、日文發表於美國、日本學界,論題涵蓋中國文學、文字學、中日比較文學、日本漢學的學術史問題以及漢文學研究,為作者迄今最完整的論著集。
本論集所收篇目如〈王次回研究〉、〈周作人的日本經驗〉、〈夏目漱石的漢詩〉、〈永井荷風與漢文學〉等作,皆於中文學界有開創先行之功;而作者對中日文學的視野、方法與洞見,至今亦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書末並附有翔實的徵引書目,對中文學界及有志研究中日文學關係者,將有所裨益。
作者:鄭清茂
1933年生,臺灣嘉義縣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歷任臺灣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麻州大學、東華大學等校教授,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為中日文學研究領域之知名學者,亦為國內重要的翻譯家,譯有日本古典文學、近代文學經典以及日本漢學著作多種,包括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小西甚一《日本文學史》,《平家物語》,松尾芭蕉《奧之細道》、《芭蕉俳文》、《芭蕉百句》,以及森鷗外《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澀江抽齋》等。
因致力於譯注日本經典文學,2014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
導論 中日文學的相互凝視 廖肇亨
寫在本書之前 鄭清茂
上編
《中國文學在日本》原序
夏目漱石的漢詩
中國文人與日本文人
永井荷風與漢文學
王次回研究
下編
漢字之發生及其年代之推測
中島敦的歷史小說
周作人的日本經驗
菅原道真的漢詩
取徑於東洋──略論中國現代文學與日本
談日本人中國文學研究的中譯問題
海內文章落布衣──談日本江戶時代的文人
他山之石──日本漢學對華人的意義
出處一覽
徵引書目
第一章 夏目漱石的漢詩
一
日本近代最偉大的作家,無疑的是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他的名字對我們並不陌生。記得以前在臺灣大學旁聽黃仲圖先生的日文課,教材裡就有夏目漱石《我是貓》的一段文章。他的長篇小說《心》很早就有了中文譯本。聽說《我是貓》也有節譯本,可惜我還沒看到。他的作品被譯成西方文字的更多。除了《心》和《我是貓》之外,如《少爺》、《行人》、《虞美人草》、《草枕》、《三四郎》、《門》等,都有譯本在歐美發行過。尤其是《少爺》一書,據我所知,竟有英譯本五種和俄、德譯本各一種。《心》也有三種英譯本和一種法譯本,可見他受推薦及重視的一斑。
夏目漱石不但是日本最偉大的作家,而且也是最受歡迎的作家。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他去世已經五十年了,可是他的作品依然暢銷不衰。根據去年(一九六五)三枝康高主持的「讀書調查」,在東西古今大作家中,漱石所得的票數遙遙領先,其他如芥川龍之介、森鷗外、島崎藤村、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紀德等,都瞠乎其後,即以得到第二位的芥川而言,所得票數也不過他的三分之一而已。看情形,他的聲望還會繼續增加下去。岩波書店為了紀念他的百年誕辰,從去年十二月起,又開始發行該店第九次《漱石全集》,共十六大冊,每月出一冊,到現在還沒出完。據說光是預約的部數就超過了二十萬。此外,自第二次大戰後,創藝社、角川、筑摩、春陽堂等書店,也都先後出過他的全集,銷路都相當不錯。至於其他無數作品的單行本,更是不勝枚舉了。
漱石可說已變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而且也變成「世界作家」之一了。今年(一九六六)九月十六日的《朝日新聞》有一條消息說,聯合國擬定於一九六七年發表的「世界偉人」名單上,可以看到夏目漱石的名字。日本文部省正在計畫成立一特別委員會,召集有名的專家學者,編印一本「最高水準」的英文版漱石傳記、作品評論和文獻目錄,以便分發各國,向世界介紹這位偉大的日本作家。漱石生前淡於名利,連日本政府送上門來的博士學位都拒絕接受。沒想到在他死後,無限功名滾滾而來,如果他泉下有知,不知將做何感想?但想拒絕做「世界偉人」,除非起死回生,已經辦不到了。
關於他辭退博士學位的事,是他生命中一個有趣的插曲。當他接到通知以後,立刻加以辭退。但政府卻一定非送他不可。消息漏了出來,變成當時(一九一一)的熱門新聞。不過他的原意並不是想以退為進,藉這種反常的做法去博取清高的令譽。他的理由是:「如果政府賦與博士過高的評價,而使世人相信非博士即非學者,那麼學問將會變成少數博士的專利品,結果是一切學問的權利會被少數『學者的貴族』所掌握,而漏選的多數文人學者也會失去社會的重視。」而且他以為文學藝術是「個人的」表現,原來與政府無關的。要是一個「文士」被政府看中而授與某種特殊榮譽或地位,他便不得不脫離「普通文士」的身分,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代表國家權威的工具。這樣一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不但要受到牽制或斲傷,而且也會間接地阻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見漱石最重視的是文人的獨立自主的人格。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是威武不能屈的。所以他不願意接受政府的學位而紓尊降貴,仰人鼻息;也不願意假借政府的權威而居高臨下、傲視文壇。他是最忠實於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智識分子。為保衛自己的誠實和純潔,他不惜放棄目前的尊榮,而終生甘為一介書生。這一點可與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相媲美。夏目漱石喜歡讀淵明詩,仔細想一下,就會覺得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
這幾年來,我也變成了漱石的「愛讀者」之一。去年(一九六五)秋天來到日本後,省吃儉用,花了一萬多圓日幣,在神田古書鋪購得一套岩波袖珍版《漱石全集》,共三十四冊,擺在書架上,一有空閒,就隨便抽出一本來看看。他早期的作品如《我是貓》和《少爺》等,幽默諧謔,令人微笑。但我更喜歡他晚期的作品《門》、《行人》、《心》、《道草》、《明暗》等。因為在這些作品中,他開始面對人生的心理和道德等問題,頗有發人猛省、使人沉思的地方。
漱石的作品引人的力量,並不在結構的整飭或情節的微妙,而在其中所描寫的人生內在問題的深刻、嚴重和複雜。由於他賦性敏感、正直,而做事又一絲不苟,極為認真,所以對人類心理的探求,總是剝絲抽繭一般,一層一絲都不輕易放過。結果越求越深,越發覺人類本性的醜惡。這種醜惡植根於與生俱來的自私自利,貪生怕死;而表視在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便是人與人之間不能推心置腹;愛情、友誼、慈善的虛偽;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知識的無用……。總之,在漱石看來,人類世界彷彿是個黑暗的地獄、絕望的深淵。每個人都無法逃出這種可怕的宿命。因為有其生便有其「我」,無其「我」便無其生。而一切煩惱、痛苦、孤獨、罪惡,都由於「我執」而來。但是,一個有心有血有肉的人,怎能沒有「我」呢?
漱石寫小說時發掘問題、分析問題的認真深切,只要是有心人都會受到感動。他從事寫作,雖說是觀察人生,追求擺脫宿命的途徑。但他一輩子在小說裡提出不少問題,卻一輩子找不到一個答案。也許可以說,他根本就不相信會有滿意的答案。因此,對他來說,寫作等於自尋煩惱。每次讀他的小說,總使我想起李後主的「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兩句詞;也連帶想起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的話。我覺得如果拿這句話來批評漱石,也許更恰當些。
不過,漱石並不以剖析人類心理、描寫人類醜惡為已足。假定只是那樣,他配不上「偉大」兩個字了。他儘管知道一個人只要活著,便絕免不了要背著煩惱、痛苦、孤獨、甚至罪惡的宿命。但在絕望悲觀的泥沼中,他仍然不肯放棄人類真愛和善意的追求,至少不曾放棄這種追求的欲望。譬如在《明暗》等小說中,幾乎每個人物都在為頑強固執的利己心所苦,但他們都在掙扎著,企圖脫離這種醜惡的利己主義的枷鎖。可以說是身在地獄而心在天堂;也可以說是處於山窮水盡的絕路,仍在渴望柳暗花明的境界。漱石無意以感傷的美麗故事取悅讀者,相反的,他卻始終執著於描述人類關係的危機,給讀者以沉思反省的機會,而使他們認識自己的真相,體諒別人的處境,進而互相了解,創造更幸福的生活。他曾說:「有倫理始有藝術;藝術必具倫理。」 正說明了他創作的態度。雖然,他從不在作品中訓誨讀者,也不主張「文藝的目的在鼓吹德義心」,但是「對作品中描寫足以啟發讀者做道德判斷的事件,或提供能夠刺激讀者去考慮是非善惡的問題」,他不但不反對,而且極力贊成。簡單一點說,他是個道德主義者,但他的道德並不是忠孝節義的教條,而是一種啟導人們向善的力量。
漱石對人生悲觀的看法,許多批評家都同意,是跟他自己不幸的遭遇有關。但更重要的,我想該是由於他狷介自守、不與人苟合的性格而來。在別人的心目中他是個怪物,而他自己也恆以怪物自居。他厭惡人類,更厭惡自己。他經常徘徊逡巡於人生窮途上,卻不能像芥川龍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有島武郎(一八七八-一九二三)或太宰治(一九○九一九四八)那樣,乾乾脆脆一死了之。這正是他的苦惱,也是構成他的悲劇的原因。江藤淳(一九三二-一九九九)先生說他的悲劇是「一個具有旺盛生活欲望的拙劣生活者的悲劇」,令人同感。總之,這位以文筆征服了全日本,而且在向世界進軍的偉大作家,在實際生活裡不但不是個超人,相反的,卻是個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是個人生悲劇裡的拙劣角色。但是,正因為他是個凡夫俗子,加上他高深的文學修養,才能深入淺出地剖析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問題,使人讀他的小說彷彿對著一面鏡子,結果每個人所看到的似乎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因而能分擔小說裡的人物的喜怒哀樂,而產生一種「我原來也在這裡面」的幻覺。所以讀夏目漱石的作品,不但在欣賞藝術,而且無意中也在了解人生,觀照自己。我想,這是他作品偉大的地方,也是能吸引廣大讀者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