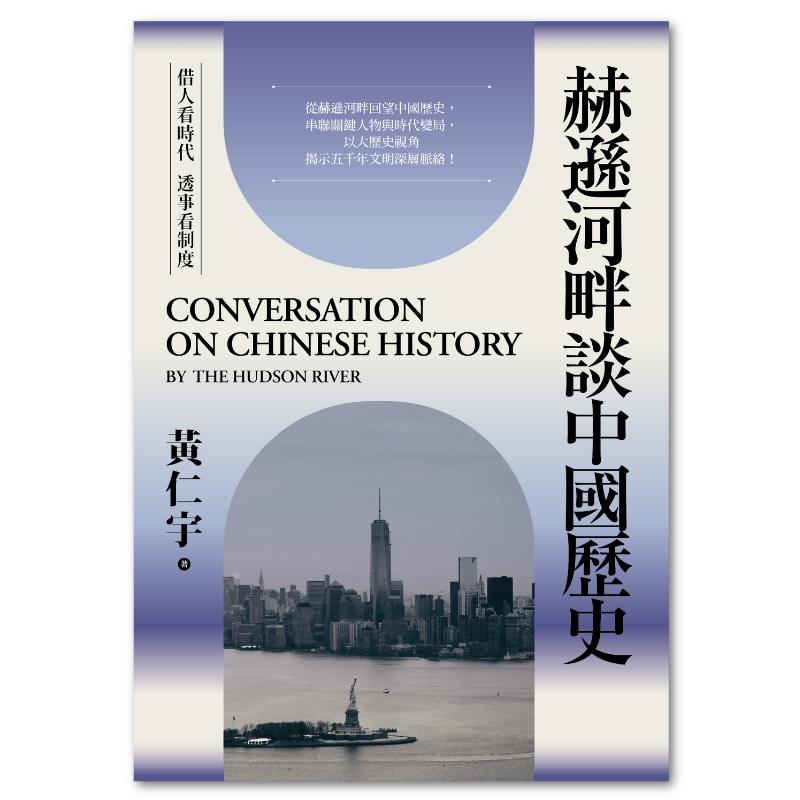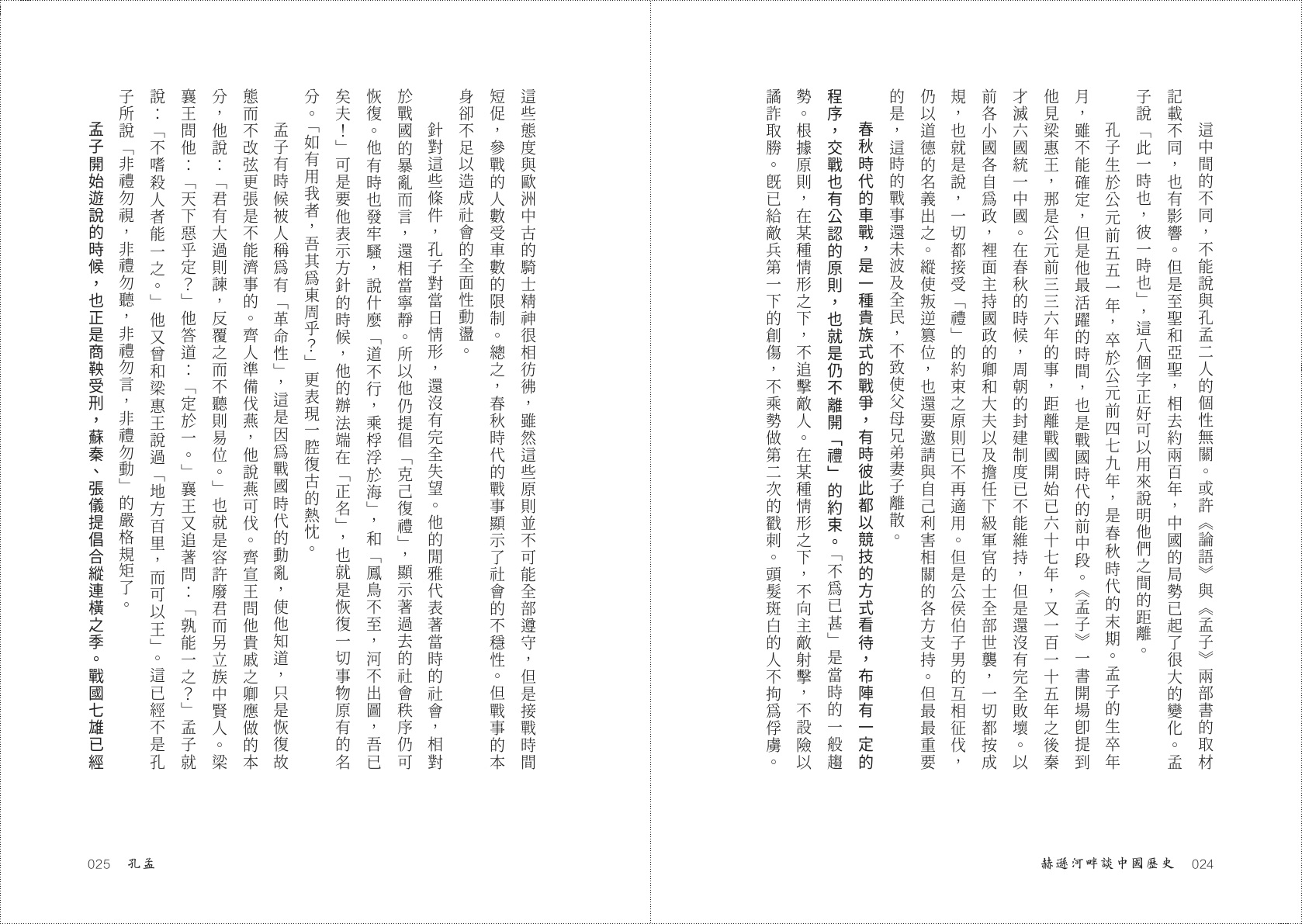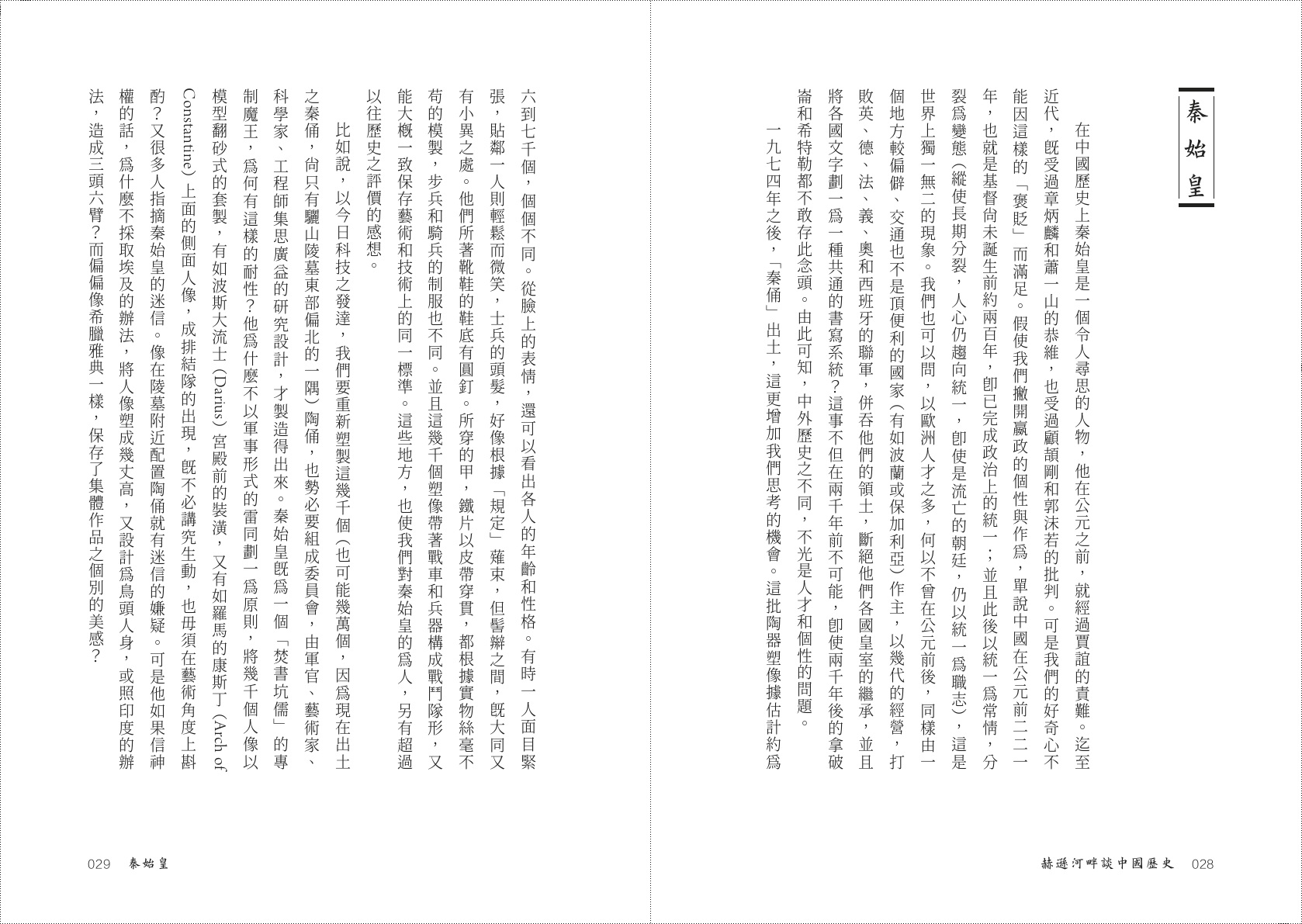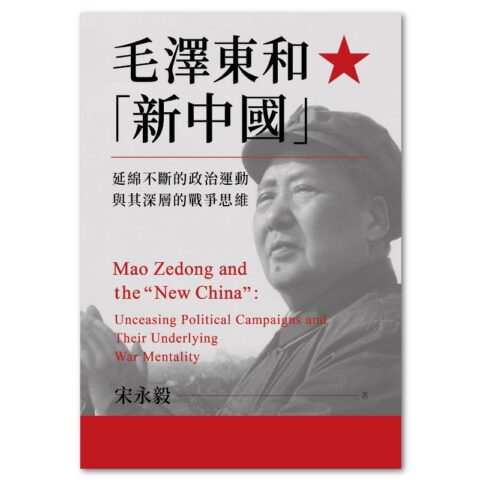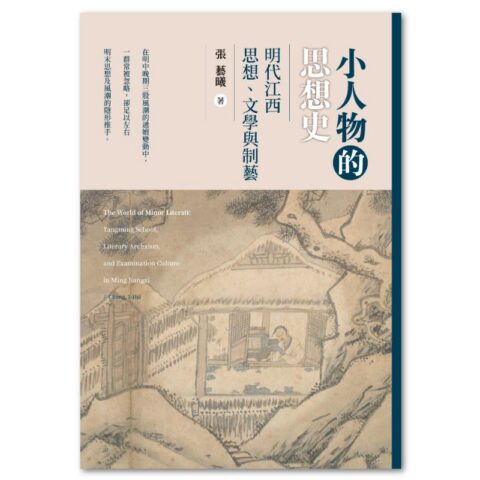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出版日期:2026-01-01
作者:黃仁宇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04
開數:25開,長 21 × 寬 14.8 × 高 1.7 cm
EAN:9789570878844
系列:黃仁宇文集
尚有庫存
【最完整的黃仁宇,最經典的史學系列】
——借人看時代,透事見制度——
從赫遜河畔回望中國歷史
串聯關鍵人物與時代變局
以大歷史視角揭示五千年文明深層脈絡
本書收錄黃仁宇於 1987 至 1989 年間發表的三十三篇歷史論述,內容涵蓋自先秦至元末的歷史關鍵時刻與重要人物。作者以「大歷史觀」為視角,用歸納法將史料高度壓縮,透過分析歷史人物在關鍵時刻的決策,勾勒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探討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如何塑造中國的歷史命運。
與傳統的歷史研究不同,本書擺脫了繁瑣考證,以生動流暢的敘述方式,娓娓道來那些看似偶然卻深具影響的歷史瞬間。貫穿全書的,是黃仁宇所倡導的「大歷史觀」——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方式審視歷史,不拘泥於片段的人物成敗,而是試圖勾勒出歷史發展的整體輪廓,使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更能與當下產生對話。這種史觀,來自他對中國歷史長期的觀察與反思,也承載著他對歷史研究方法的探索與實踐。
作為《中國大歷史》的延伸與補充,本書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學術論文的敘事方式,適合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以及希望從更廣闊視角理解歷史發展的研究者。無論是尋找歷史線索,還是思考中國未來,這部作品都將帶來發人深省的啟發。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出版計畫
集結黃仁宇思想全貌,重現大歷史視野
黃仁宇(1918–2000)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歷史學家之一。他以「大歷史觀」著稱,擅長從宏觀視野審視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結構,並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深刻的文化觀察和動人的文學筆法,為世人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
聯經出版特別規劃完整的【黃仁宇文集】,將其分散於各出版社的著作重新彙整,陸續改版推出,分為五大系列:
l 大歷史觀與歷史方法論:重新定義歷史格局與中國定位。
l 明代研究專著:嚴謹考證,深掘制度與社會運作。
l 歷史類散文:知性與感性的交織,展現文化洞察。
l 戰爭與近現代中國:親歷時代動盪,書寫生命史詩。
l 小說與文學創作:以文學筆法重現歷史氛圍與情感。
這是一部完整的思想工程,引領讀者全面認識黃仁宇的思想脈絡,也讓經典再度回到當代視野,持續發揮影響力。透過【黃仁宇文集】,我們將再次看見——歷史不是片段,而是千萬重的關聯。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
《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明代的漕運,1368-1644》
《中國大歷史》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放寬歷史的視界》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地北天南敘古今》
《關係千萬重》
《大歷史不會萎縮》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緬北之戰》
《長沙白茉莉》
《汴京殘夢》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作者: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
黃仁宇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並提倡「大歷史觀」而為人所知。「大歷史觀」不對單一歷史人物或事件作評價,而是透過分析當時代政治、社會整體面貌,進而掌握歷史的特點。主要著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
開場白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馬遷和班固
文景之治
漢武帝
從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
西漢與東漢
光武中興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淝水之戰
北魏拓跋氏
從分裂到統一
隋煬帝
貞觀之治
武則天
漁陽鼙鼓動地來
九重城闕煙塵生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黃巢
五代十國
宋太祖趙匡胤
澶淵之盟
王安石變法
靖康恥
賈似道買公田
道學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元順帝
卷尾瑣語
附錄
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裡。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板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玉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後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挑,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做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裡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於利則行,不合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哩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苗,不管是砍伐樹幹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穫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語,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利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台,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裡,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只好一塊一片的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像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會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其他都為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哩內外一體植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採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現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菸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裡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的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植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to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著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十九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系統」優勝於農業的系統。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型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所有人雇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哩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穫之後才算帳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產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且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雇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做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做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
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五十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蹟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做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占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筦」,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恪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十三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稱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做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裡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獃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于則被他改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都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演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pseudo-science)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係因天旱而動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aesthetically)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古代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natural law)須待不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櫫的知識很難與朝廷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型態做他行動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一○五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型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做渾天儀,又於公元一三二年做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徑之π為三.一六二二。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五十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做有系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裡寫他的傳記,只寥寥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之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祕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上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個大書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