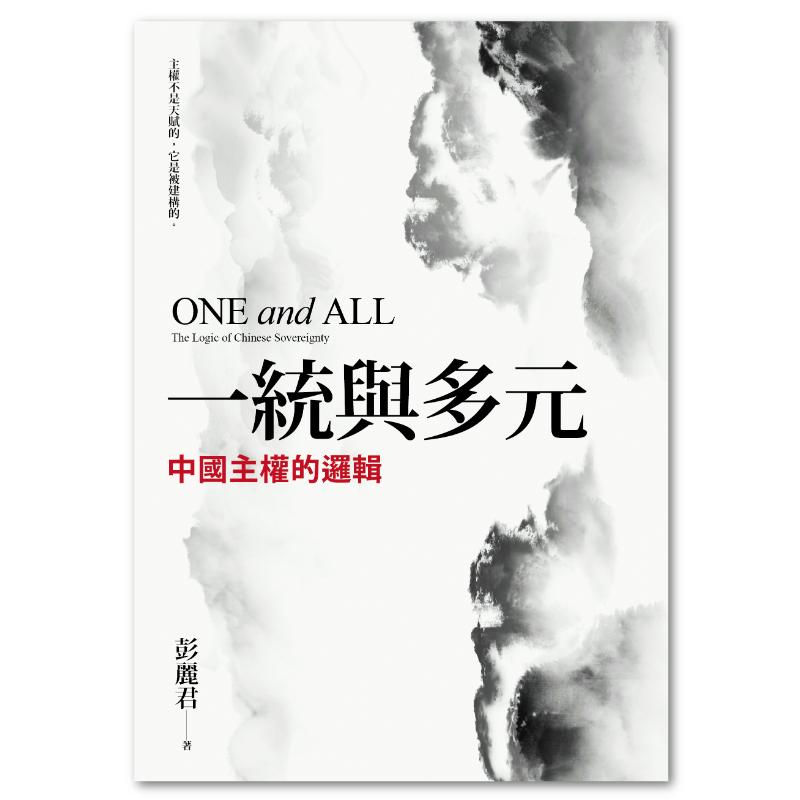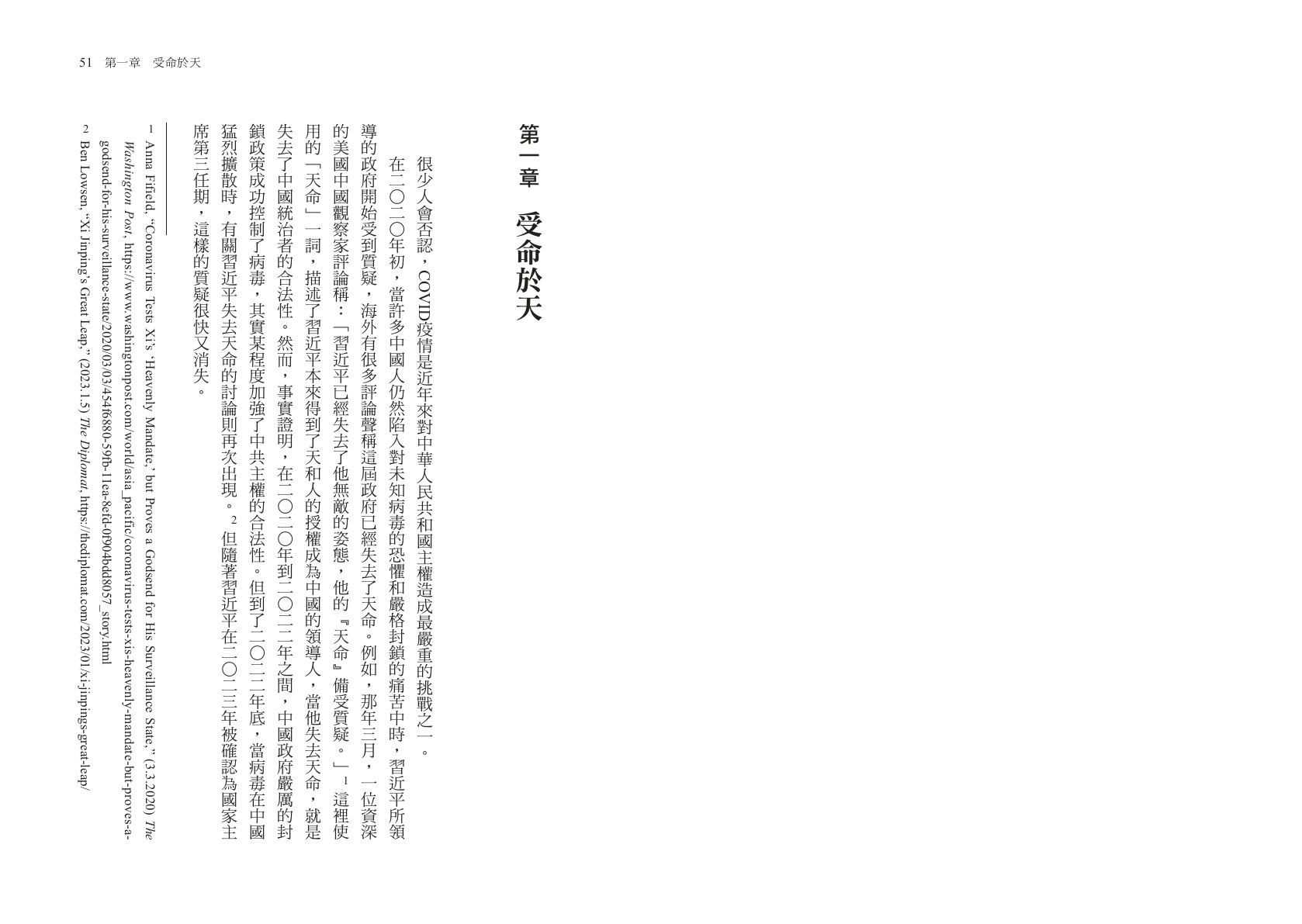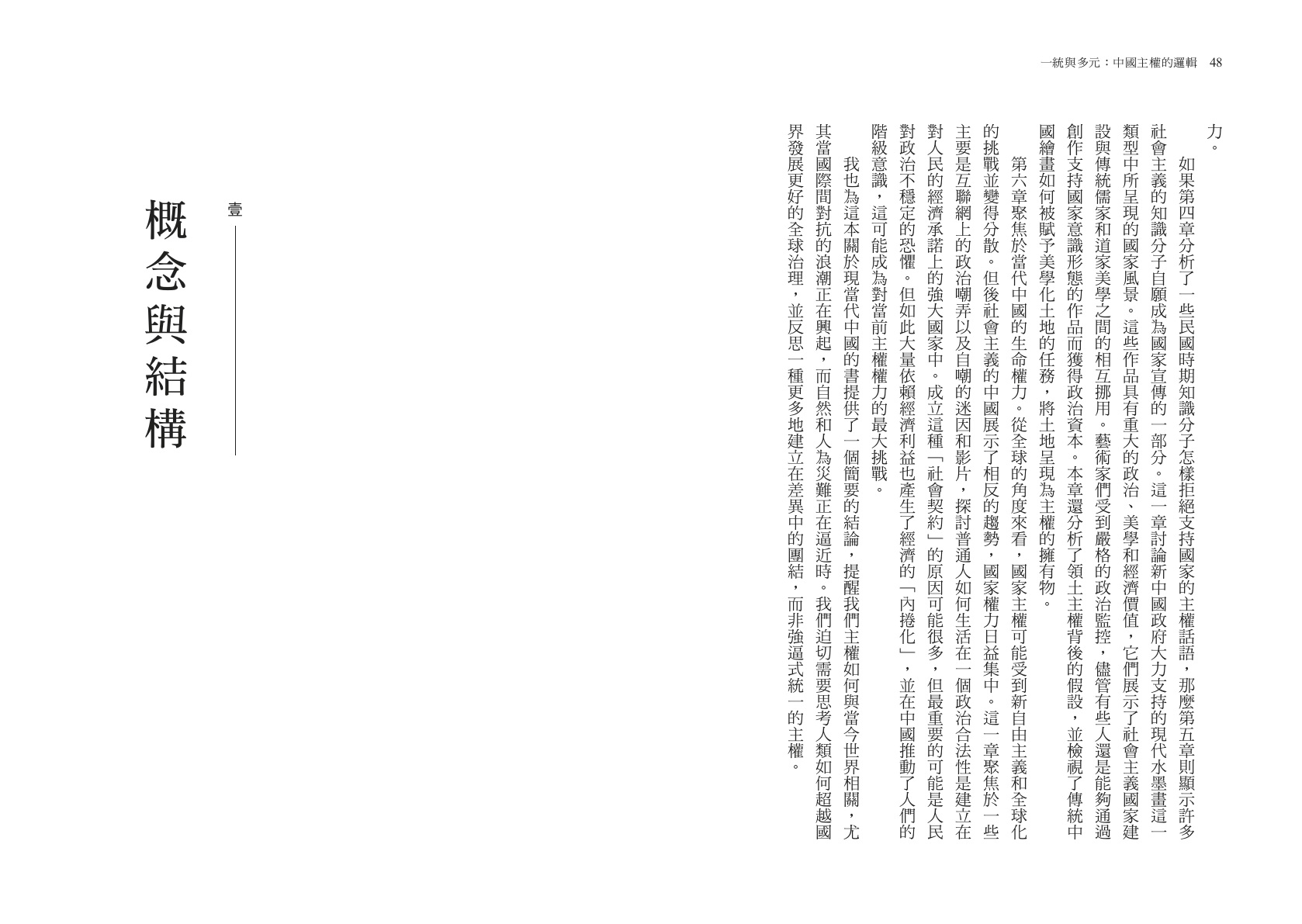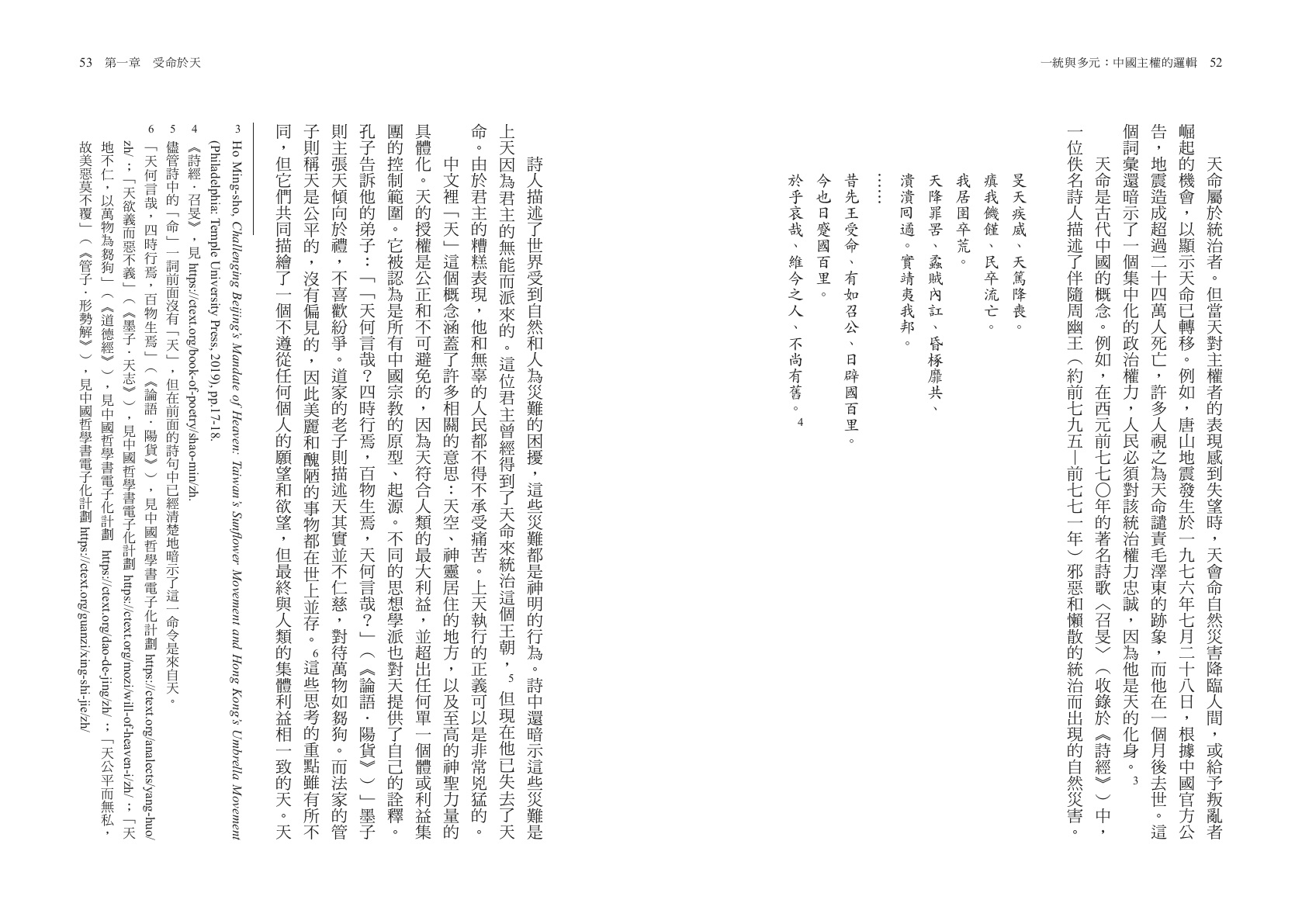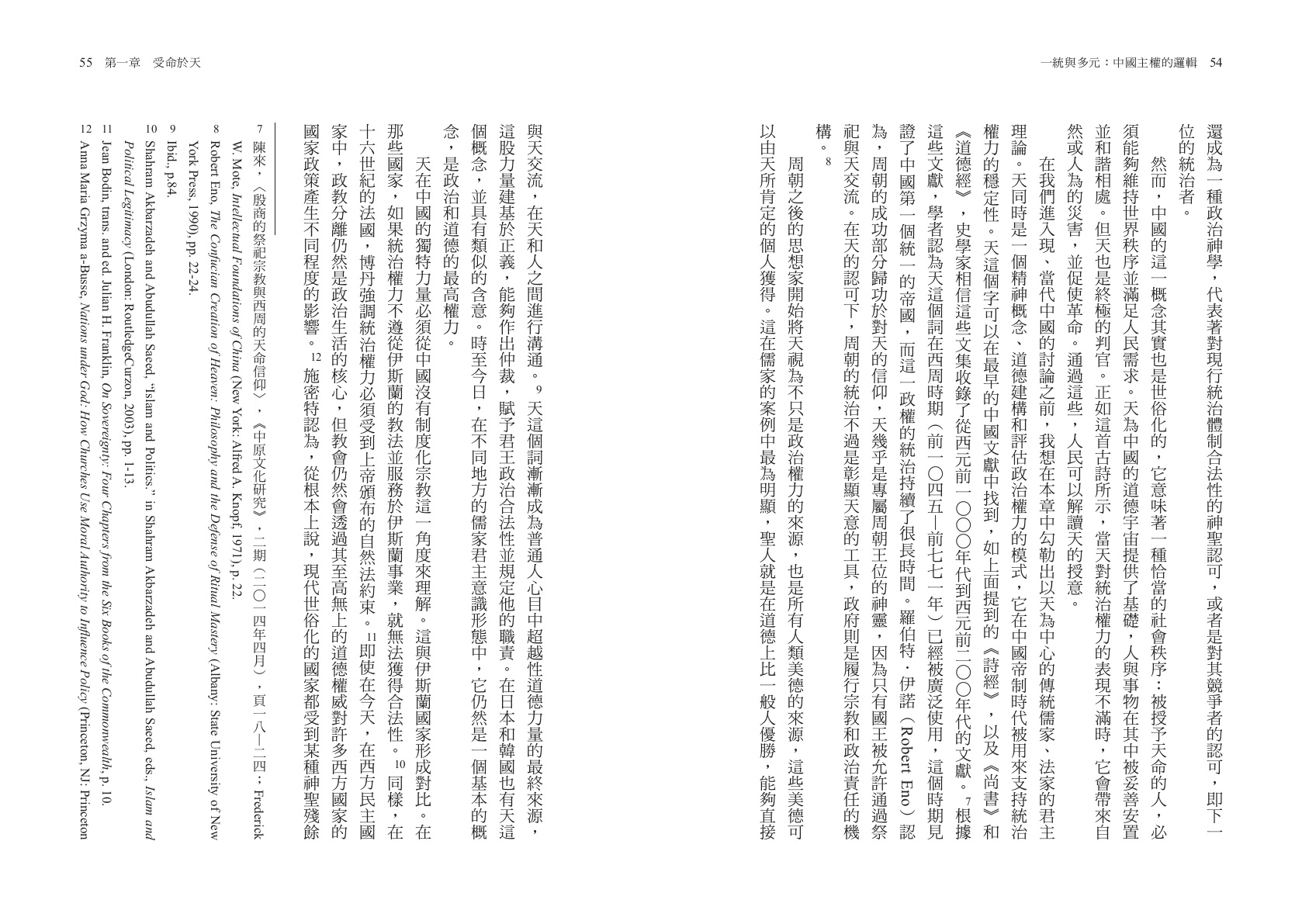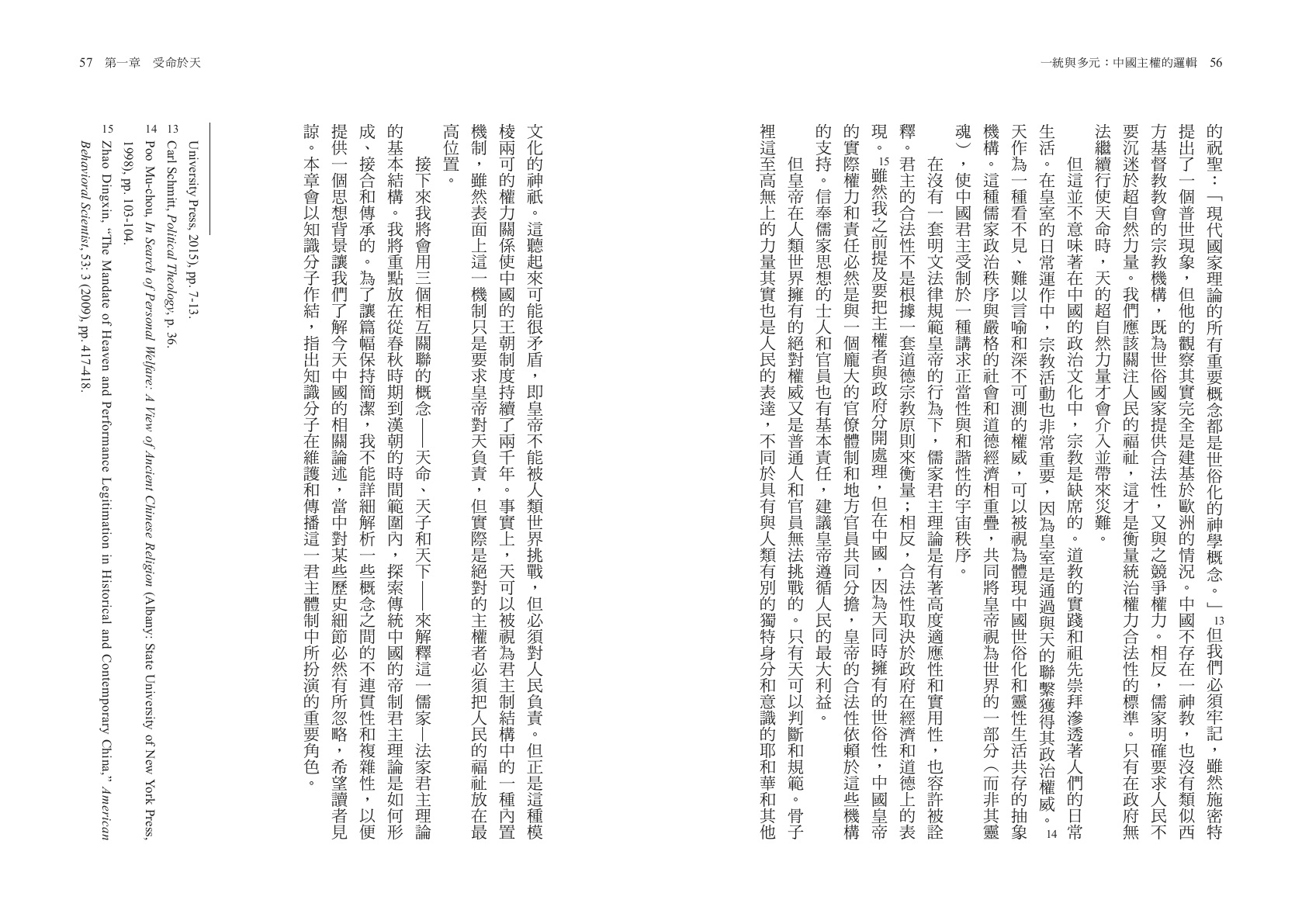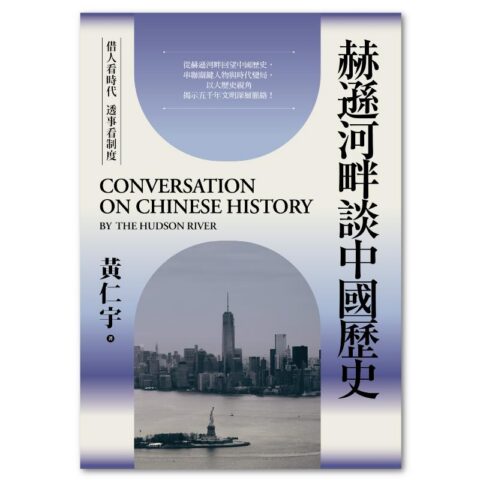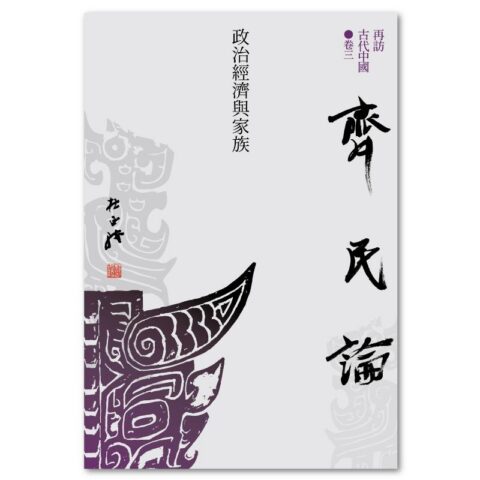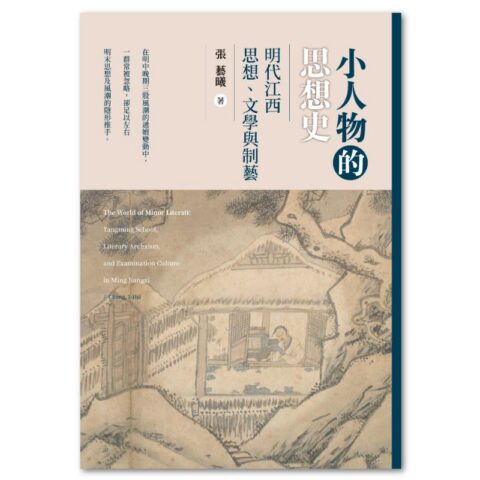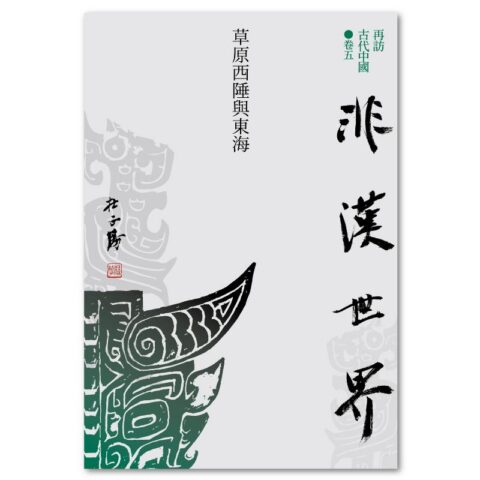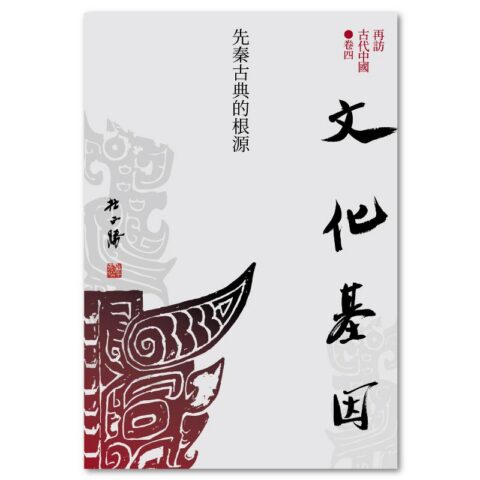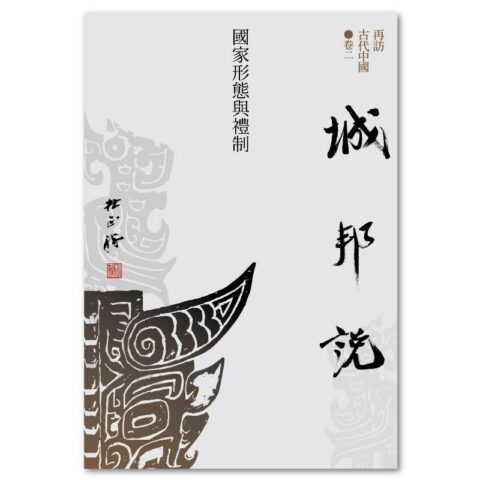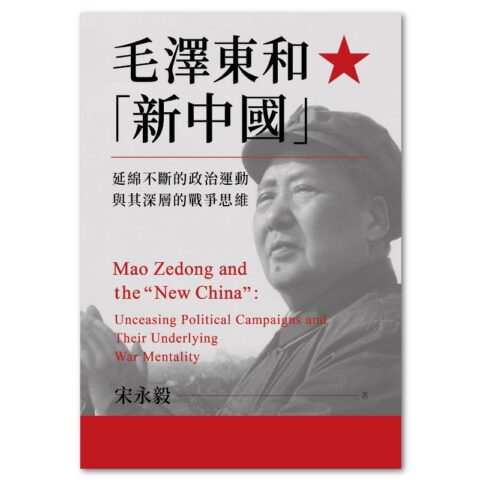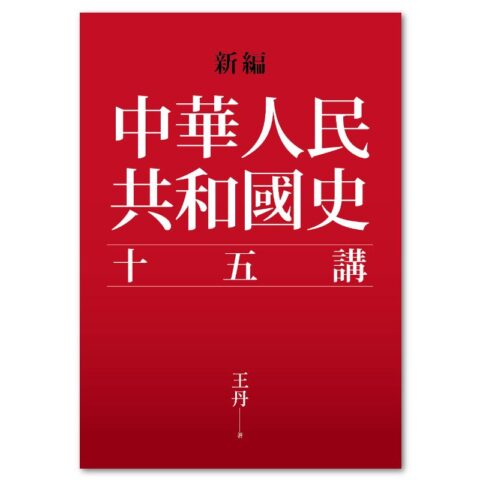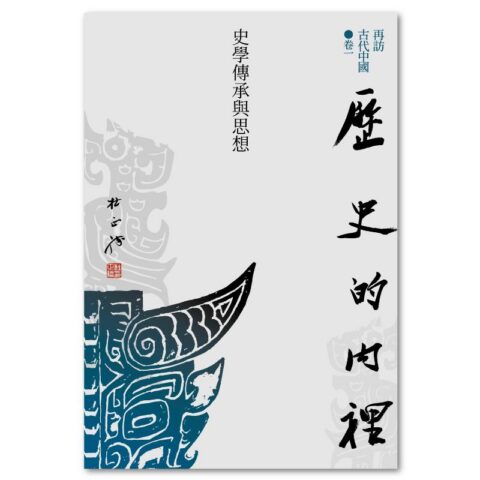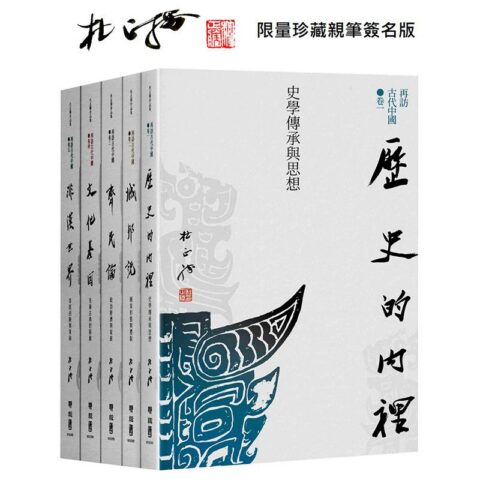一統與多元:中國主權的邏輯
原書名:One and All: The Logic of Chinese Sovereignty
出版日期:2025-10-16
作者:彭麗君
譯者:艾加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04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1.6cm
EAN:9789570878127
系列:歷史大講堂
尚有庫存
主權不是天賦的,它是被建構的。
在帝制、革命、現代國家的交錯之間,本書帶你拆解「一統」神話,直面中國主權的歷史幻象與現實邏輯。
當國家面對危機、輿論或人民情感時,主權究竟如何運作?這本跨越歷史、政治與文化的深度之作,帶領讀者直面中國主權背後的權力邏輯與想像結構。作者以歷史作為方法,從帝國「受命於天」、民國「革命制度」、社會主義下的山水畫,到當代數位文化中主權的再製,爬梳歷史上中國政權如何以主權之名,統攝人民、領土與歷史。
本書挑戰了將「一統」視為中國國家本質的論述,也警惕「多元」成為新神話,透過細膩的文本分析與文化現象觀察,揭露主權在實踐中的矛盾、流動與辭藻。這不是一本宣判答案的書,而是激發思辨的提問之書──關於國家、個人與共同體,如何在一統與多元間,尋找共生的可能。
在民族國家捲土重來、全球民主焦慮加劇的時代,《一統與多元》不只是理解中國的關鍵讀本,更是一面映照人類如何共同生活的鏡子。
作者:彭麗君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長年關注中國與香港現代文化,研究聚焦於文化與政治、複製與原型、多元與一體、民主與主權之間的張力與辯證。著作屢獲國際肯定,包括美國圖書館學會「傑出學術書籍獎」、蔣經國基金會出版獎等,並獲澳洲研究委員會Discovery獎及中大傑出研究獎。
譯者:艾加
文化研究畢業。
中文版序
序
導 論
壹 概念與結構
第一章 受命於天
第二章 統一的寓言
第三章 革命作為制度
貳 文化與再現
第四章 人民主權與民國文學
第五章 領土主權與社會主義山水畫
第六章 經濟主權與後社會主義數位文化
結 論
參考書目
中文版序
本書大概在二○二○年啟筆,二○二三年完稿,英文版二○二四年出版,中文版二○二五年面世,中間五、六年的光景,作為學術出版已經很匆忙了。但現在回想這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波譎雲詭,也可以說亂作一團,自己身處的社會也栽了不少個觔斗,一個一個所謂的世界大局,變得越來越虛無縹緲、漂泊無根。但我也很感恩,有緣成為本書的作者,寫這本書令我踏實下來,可說是一段療癒過程。今天回看,感到自己和城市又累積了一些,雖然距離彼岸肯定是遠了,反而更心安於當下。
我的初衷是以歷史作為方法,把「主權」這個政治概念祛魅,所以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本歷史書。但我不想把它寫得累贅,所以不斷提醒自己處理史實可以流暢一點,一方面是因為歷史本身已經是沉甸甸的,很多相關的討論因為要遵守學術規範,容易變得乏味;另一方面,書內不少章節涉及的史料眾多,而當中我引用的資料大部分是源自前人豐盛的研究,在一手資料上我沒有很多貢獻,所以除了史實的鋪排和對歷史解讀須負應有的責任外,我希望在這樣一個嚴肅的題目下本書依然保持某種輕快,開拓讀者的好奇心而不是成為封閉的知識。我批評道統,所以不想成為道統的一員;我不相信永恆,所以希望這本書能夠參與在時間的消逝中。當然,眼高手低是源於自己視野和能力的局限,也因為學術有它逃不掉的厚重。
《一統與多元》並不是本書原名One and All的最佳翻譯,後者的層次比較多,但我想不到一個相似的中文對應,就選擇了兩個我一直很感興趣的概念作為主旨。本書確實立意討論一統與多元、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但我不希望將之變成一種二元的對立,希望這個「與」字不會把兩者二分為非此即彼的關係。我相信互構共生,除了提出「一統」和「多元」確實涉及的不同世界觀外,本書也希望能夠呈現「一體」和「全體」、「一」和「萬物」的複雜關係。我很清楚,盲目地提出多元可能引申更多的問題,例如世界很多極端組織都以多元作為合法化自己的藉口,我們也不可以因為反對極權而反對團結……,很多困局都要進入情境中才能解決,這是智慧所在。我也希望在變化越來越快的社會中,這書能保有一點點的獨立存在。只有盤根,才可以超越。
第一章 受命於天
很少人會否認,COVID疫情是近年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造成最嚴重的挑戰之一。
在二○二○年初,當許多中國人仍然陷入對未知病毒的恐懼和嚴格封鎖的痛苦中時,習近平所領導的政府開始受到質疑,海外有很多評論聲稱這屆政府已經失去了天命。例如,那年三月,一位資深的美國中國觀察家評論稱:「習近平已經失去了他無敵的姿態,他的『天命』備受質疑。」這裡使用的「天命」一詞,描述了習近平本來得到了天和人的授權成為中國的領導人,當他失去天命,就是失去了中國統治者的合法性。然而,事實證明,在二○二○年到二○二二年之間,中國政府嚴厲的封鎖政策成功控制了病毒,其實某程度加強了中共主權的合法性。但到了二○二二年底,當病毒在中國猛烈擴散時,有關習近平失去天命的討論則再次出現。但隨著習近平在二○二三年被確認為國家主席第三任期,這樣的質疑很快又消失。
天命屬於統治者。但當天對主權者的表現感到失望時,天會命自然災害降臨人間,或給予叛亂者崛起的機會,以顯示天命已轉移。例如,唐山地震發生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根據中國官方公告,地震造成超過二十四萬人死亡,許多人視之為天命譴責毛澤東的跡象,而他在一個月後去世。這個詞彙還暗示了一個集中化的政治權力,人民必須對該統治權力忠誠,因為他是天的化身。
天命是古代中國的概念。例如,在西元前七七○年的著名詩歌〈召旻〉(收錄於《詩經》)中,一位佚名詩人描述了伴隨周幽王(約前七九五—前七七一年)邪惡和懶散的統治而出現的自然災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
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
潰潰囘遹。實靖夷我邦。
……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
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詩人描述了世界受到自然和人為災難的困擾,這些災難都是神明的行為。詩中還暗示這些災難是上天因為君主的無能而派來的。這位君主曾經得到了天命來統治這個王朝,但現在他已失去了天命。由於君主的糟糕表現,他和無辜的人民都不得不承受痛苦。上天執行的正義可以是非常兇猛的。
中文裡「天」這個概念涵蓋了許多相關的意思:天空、神靈居住的地方,以及至高的神聖力量的具體化。天的授權是公正和不可避免的,因為天符合人類的最大利益,並超出任何單一個體或利益集團的控制範圍。它被認為是所有中國宗教的原型、起源。不同的思想學派也對天提供了自己的詮釋。孔子告訴他的弟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墨子則主張天傾向於禮,不喜歡紛爭。道家的老子則描述天其實並不仁慈,對待萬物如芻狗。而法家的管子則稱天是公平的,沒有偏見的,因此美麗和醜陋的事物都在世上並存。這些思考的重點雖有所不同,但它們共同描繪了一個不遵從任何個人的願望和欲望,但最終與人類的集體利益相一致的天。天還成為一種政治神學,代表著對現行統治體制合法性的神聖認可,或者是對其競爭者的認可,即下一位的統治者。
然而,中國的這一概念其實也是世俗化的,它意味著一種恰當的社會秩序:被授予天命的人,必須能夠維持世界秩序並滿足人民需求。天為中國的道德宇宙提供了基礎,人與事物在其中被妥善安置並和諧相處。但天也是終極的判官。正如這首古詩所示,當天對統治權力的表現不滿時,它會帶來自然或人為的災害,並促使革命。通過這些,人民可以解讀天的授意。
在我們進入現、當代中國的討論之前,我想在本章中勾勒出以天為中心的傳統儒家、法家的君主理論。天同時是一個精神概念、道德建構和評估政治權力的模式,它在中國帝制時代被用來支持統治權力的穩定性。天這個字可以在最早的中國文獻中找到,如上面提到的《詩經》,以及《尚書》和《道德經》,史學家相信這些文集收錄了從西元前一○○○年代到西元前二○○年代的文獻。7根據這些文獻,學者認為天這個詞在西周時期(前一○四五—前七七一年)已經被廣泛使用,這個時期見證了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帝國,而這一政權的統治持續了很長時間。羅伯特.伊諾(Robert Eno)認為,周朝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對天的信仰,天幾乎是專屬周朝王位的神靈,因為只有國王被允許通過祭祀與天交流。在天的認可下,周朝的統治不過是彰顯天意的工具,政府則是履行宗教和政治責任的機構。
周朝之後的思想家開始將天視為不只是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是所有人類美德的來源,這些美德可以由天所肯定的個人獲得。這在儒家的案例中最為明顯,聖人就是在道德上比一般人優勝,能夠直接與天交流,在天和人之間進行溝通。9 天這個詞漸漸成為普通人心目中超越性道德力量的最終來源,這股力量建基於正義,能夠作出仲裁,賦予君王政治合法性並規定他的職責。在日本和韓國也有天這個概念,並具有類似的含意。時至今日,在不同地方的儒家君主意識形態中,它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概念,是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權力。
天在中國的獨特力量必須從中國沒有制度化宗教這一角度來理解。這與伊斯蘭國家形成對比。在那些國家,如果統治權力不遵從伊斯蘭的教法並服務於伊斯蘭事業,就無法獲得合法性。同樣,在十六世紀的法國,博丹強調統治權力必須受到上帝頒布的自然法約束。即使在今天,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政教分離仍然是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教會仍然會透過其至高無上的道德權威對許多西方國家的國家政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施密特認為,從根本上說,現代世俗化的國家都受到某種神聖殘餘的祝聖:「現代國家理論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但我們必須牢記,雖然施密特提出了一個普世現象,但他的觀察其實完全是建基於歐洲的情況。中國不存在一神教,也沒有類似西方基督教教會的宗教機構,既為世俗國家提供合法性,又與之競爭權力。相反,儒家明確要求人民不要沉迷於超自然力量。我們應該關注人民的福祉,這才是衡量統治權力合法性的標準。只有在政府無法繼續行使天命時,天的超自然力量才會介入並帶來災難。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宗教是缺席的。道教的實踐和祖先崇拜滲透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在皇室的日常運作中,宗教活動也非常重要,因為皇室是通過與天的聯繫獲得其政治權威。天作為一種看不見、難以言喻和深不可測的權威,可以被視為體現中國世俗化和靈性生活共存的抽象機構。這種儒家政治秩序與嚴格的社會和道德經濟相重疊,共同將皇帝視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其靈魂),使中國君主受制於一種講求正當性與和諧性的宇宙秩序。
在沒有一套明文法律規範皇帝的行為下,儒家君主理論是有著高度適應性和實用性,也容許被詮釋。君主的合法性不是根據一套道德宗教原則來衡量;相反,合法性取決於政府在經濟和道德上的表現。雖然我之前提及要把主權者與政府分開處理,但在中國,因為天同時擁有的世俗性,中國皇帝的實際權力和責任必然是與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和地方官員共同分擔,皇帝的合法性依賴於這些機構的支持。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和官員也有基本責任,建議皇帝遵循人民的最大利益。
但皇帝在人類世界擁有的絕對權威又是普通人和官員無法挑戰的。只有天可以判斷和規範。骨子裡這至高無上的力量其實也是人民的表達,不同於具有與人類有別的獨特身分和意識的耶和華和其他文化的神祇。這聽起來可能很矛盾,即皇帝不能被人類世界挑戰,但必須對人民負責。但正是這種模棱兩可的權力關係使中國的王朝制度持續了兩千年。事實上,天可以被視為君主制結構中的一種內置機制,雖然表面上這一機制只是要求皇帝對天負責,但實際是絕對的主權者必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最高位置。
接下來我將會用三個相互關聯的概念—天命、天子和天下—來解釋這一儒家—法家君主理論的基本結構。我將重點放在從春秋時期到漢朝的時間範圍內,探索傳統中國的帝制君主理論是如何形成、接合和傳承的。為了讓篇幅保持簡潔,我不能詳細解析一些概念之間的不連貫性和複雜性,以便提供一個思想背景讓我們了解今天中國的相關論述,當中對某些歷史細節必然有所忽略,希望讀者見諒。本章會以知識分子作結,指出知識分子在維護和傳播這一君主體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天 命
中國最早有文字記錄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商朝的殷商時期(前一三○○—前一○四五年)。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分析,在這個時期,包括上帝、皇室祖先和自然神在內的眾神受到朝廷的祭拜,顯示出神祇和祖先是如何同時支持君主權力。天這個詞在隨後的西周時期出現,部分原因是為了指代這個包含神聖力量的道德宗教概念。後來的儒家學者將西周視為他們烏托邦式的過去,它體現了中國文明的最高點。據稱,這是一個道德端正的世界,實行著仁厚的封建主義,人們樂意履行自己被賦予的社會角色,從而實現了繁榮與和諧的社會。但這個王朝逐漸變得腐敗,到了幽王統治的年代,即前述詩歌中指稱之時,它的都城據稱被犬戎所劫掠。新繼任的平王逃到東方,建立了一個新的都城,與其他崛起的勢力並存,開啟了東周時期。歷史學家將這個東周時期進一步劃分為春秋時期(前七七○—前四七六年)和戰國時期(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在這兩個時期,周朝必須與許多新興的國家競爭。經過五百年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秦國的嬴政最終取得了勝利,統一了廣闊的領土,建立了短暫的秦朝(前二二一—前二○七年),之後繼承秦朝的是漢朝(前二○二—二二○年)。
以上是一個大家都很清楚的古代中國史,但我想提出的是,春秋和戰國時期的中國,情況與中世紀的歐洲相似,許多國家並立,它們彼此之間既不斷發動戰爭,也互相影響。雖然中國沒有像歐洲的天主教教廷那樣的組織來調解和平,但這些相互競爭的國家有很多溝通,也開始發展可以共同理解的書寫文字。在這個政治多元的時代,也是大部分經典學說形成的時期。當時的文獻和文物表明,天的概念在各國之間都被使用。
像天一樣,天命這個詞也首次出現在西周時期,文字描述了天接受君王所獻的祭品後,賦予君王在大地上統治的權力。在這個時期,天逐漸從一個個體化的神祇轉變為普世的道德政治秩序的創造者。根據余英時的說法,一個周朝之前的神話故事顯示,為了合法化自身巨大的權力,第一位君王承擔起原本屬於巫師的角色,壟斷了超自然世界與普通人之間的交流。17這就是天命的起源,也是中國君主理論的最早版本。
在孔子的時代(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天這個詞加入了道德的層面。孔子聲稱自己能夠直接與天溝通,理解天命。這位思想家自稱能夠與天交流的能力擴大了天命這個詞的涵義,它不僅描述了統治的合法性,還描述了聖人能通達的世俗秩序。從那時起,中國的君主理論具有兩個主要特點:統治權屬於君主,但統治權也基於人民的認可。
讓我們聚焦於《尚書》這本書中的天命一詞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尚書》收集了大約西元前二○○○年至西元前一○○○年期間的官方文件和其他散文作品。這些文本的日期、編纂方式以及其中的歷史材料的準確性一直是學術界無休止地辯論的話題。儘管如此,某些章節被普遍認為是西周時期的真實記錄。我們也可以確定這本書是在春秋和戰國時期集合很多人的學術努力下產生的。在那個時期,已有的歷史文獻被系統地編纂成一卷又一卷獨立的作品,其中不僅包括《尚書》,還包括《論語》和《孟子》等對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經典。
《尚書》中名為〈康誥〉的一章記錄了周武王與他的兄弟周公的對話。武王告訴他的弟弟要記住他們父親文王的偉大事業,並說天命不會只授予或終於一人。武王強調,儘管他們的父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來自天的祝福並非是自動出現;相反,兄弟倆必須努力證明自己分別是一位偉大的國王和一位偉大的王子。
這種天命不歸於任何一個人的觀點在許多後來的儒家文獻中都有出現,顯示了這個觀念對儒家政治思想的影響力。例如,《左傳》中批評很多魯國統治者都是放縱懈怠,因此人民對魯昭公被驅逐並在國外死亡並不感到同情:「君臣無常位」。另一方面,《禮記》中引用了孔子的話,他說只有能夠實踐善治的人才能保有天命,而不能保持善良的人將失去天命。天命的核心概念是它會轉移,所以那些想要維持天命的人必須努力去爭取。
但如何爭取?天命的另一個核心層面是必須取得人民的許可。《尚書.泰誓》中的一句話對此作出解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句話表明了天與人民之間固有的感知和心理連結。由於這種強烈的相互聯繫,天意必然反映了民意。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內在於天這一概念的辯證層面。作為一切權力的源頭,天既是深不可測的,卻又是容易觀察到的。人類必須臣服於它的無所不能,而天也傾聽人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苦難,並通過授予天命來保護人民。因此,天命會發生變化,但它與人民是始終一致的。雖然人無法直接理解天,但我們可以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發現,天命只會授予那些實踐仁政的統治者。天命不會永遠只授予一位統治者,但它卻是一貫與人民保持一致。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權力是這種君主理論的核心。在沒有明確路線圖指示如何罷黜腐敗統治者的情況下,天命的理論間接支持了行使武力。一方面,如果有挑戰者認為當今的王朝已無法繼續統治,那麼他們可以解析自己已被授予天命,可以甚至應該動用武力奪取權力。另一方面,只要現任統治者認為自己被授予的天命仍然是有效的,他就有權壓制異議聲音;這就是強調刑法條例和帝王權威的法家發揮作用的地方。
因此,儒家經典既為政治權威提供了合法性和指導,同時也為異議者提供了推翻政權的理據。朝代更迭是儒家歷史結構中不可避免且必要的一部分,儒家承認統治者可能會變得非常腐敗,以至於天必須阻止他們繼續執政。成功推翻政權的革命者並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被授予天命的人。更準確地說,被選中的叛亂者既是實踐自己野心的積極參與者,又是讓天彰顯其天命的被動工具。這種對革命的認可也給了人民希望,即革命是可能的,官逼民反,天助義者。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帝國政治歷史中的眾多革命和叛亂見證了這種不透明的天命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等同於武力,但沒有天命認可的政治權力也是不合法的。
這種主權哲學實際上為中國帶來了長達兩千年相對的社會穩定。雖然君主的權力有所變動,但作為基礎的主權邏輯並未有著根本上的變化。與中世紀歐洲相比,中國帝國的統治者和官僚體系較為強大,不像歐洲各國需要依靠人民的合作才可以進行徵稅和徵兵。26因此,中國的君王往往沒有多少動機與普通人分享他們的政治權力。然而,也有人認為,中國人民支持這種帝國社會秩序,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安全和可預測的政治環境。中國王朝統治中較好的部分在於相比歐洲,它更穩定、富裕也更有威望。中國人民也相應地不太有動力向皇帝要求權力。雖然有些勇敢或被逼上絕路的叛亂者敢於挑戰王位,但許多人還是被動地相信由天來判斷甚至推翻那些無能的統治者。中國在接下來的歷史時間繼續產生無數戰爭,但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大體沿用從上一個王朝繼承下來的行政結構、政治意識形態和法律法規,只是會做出不同程度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