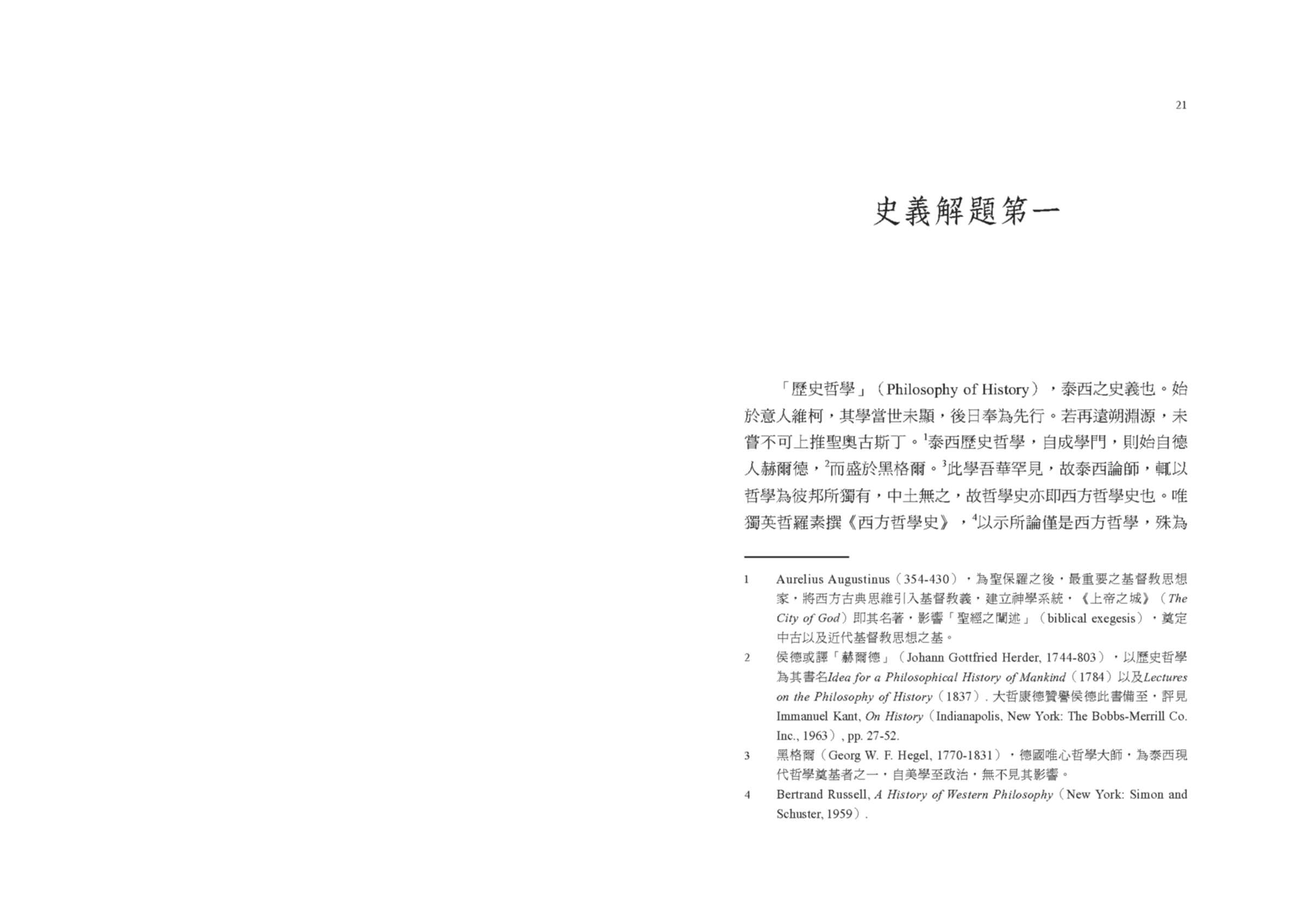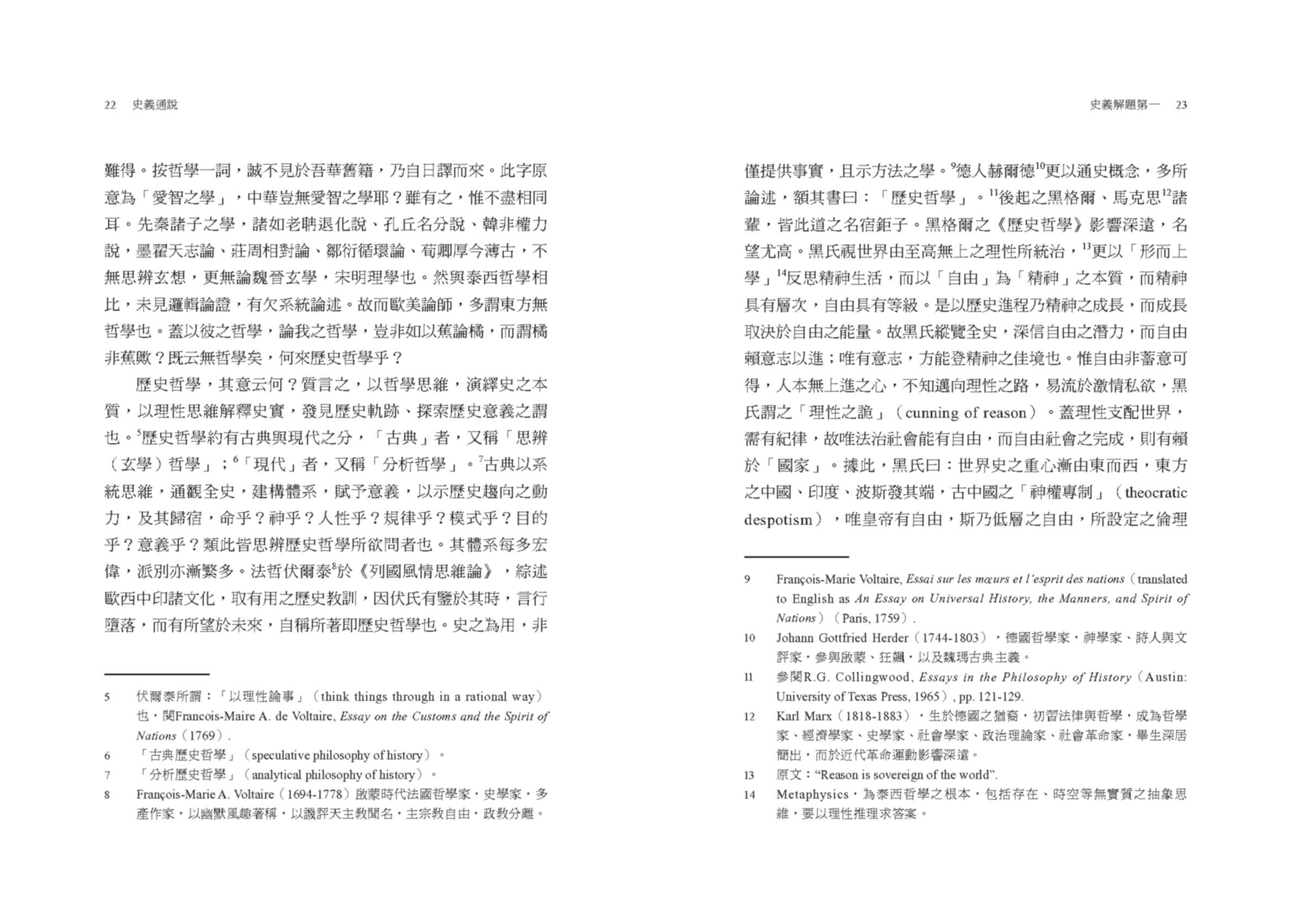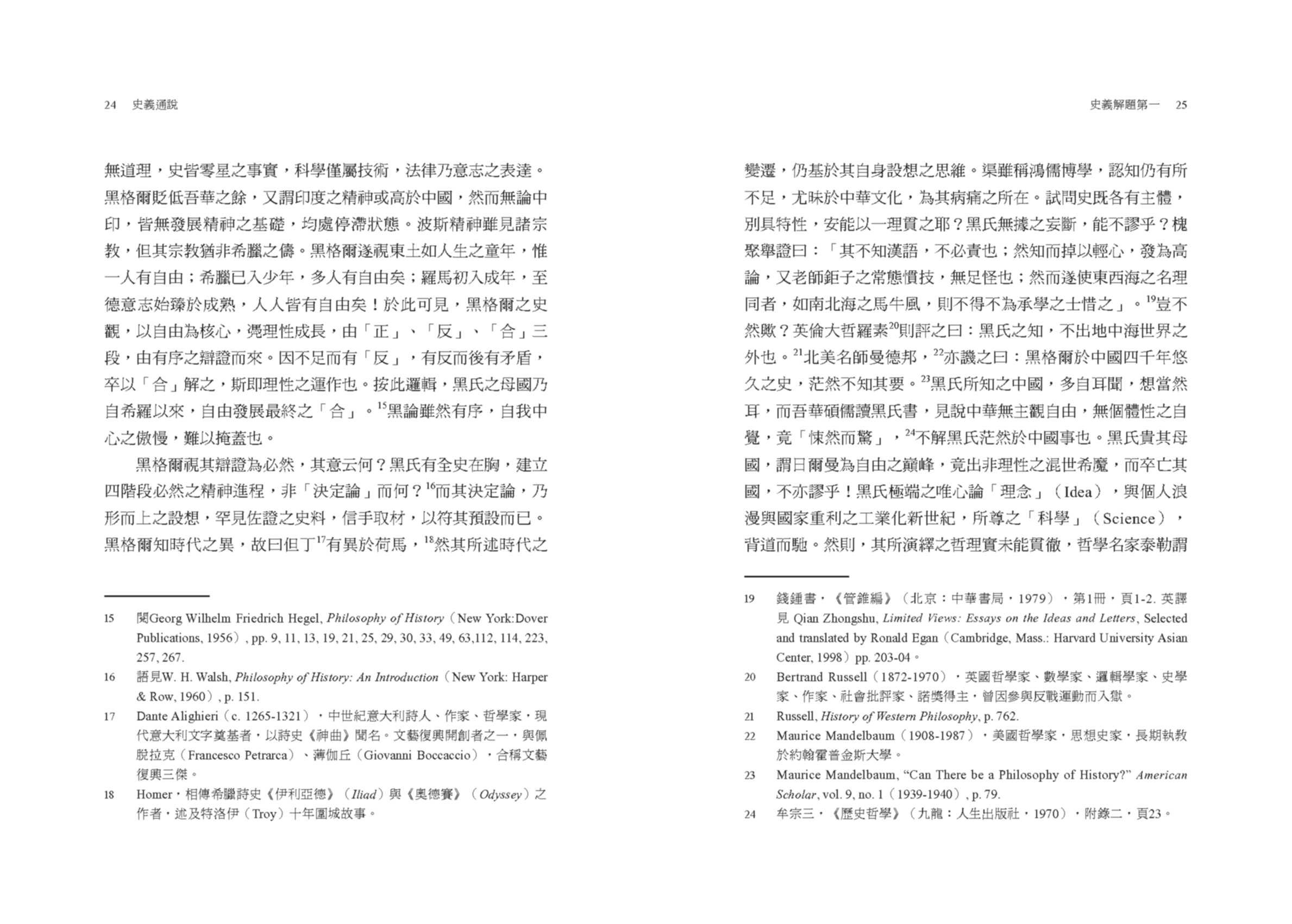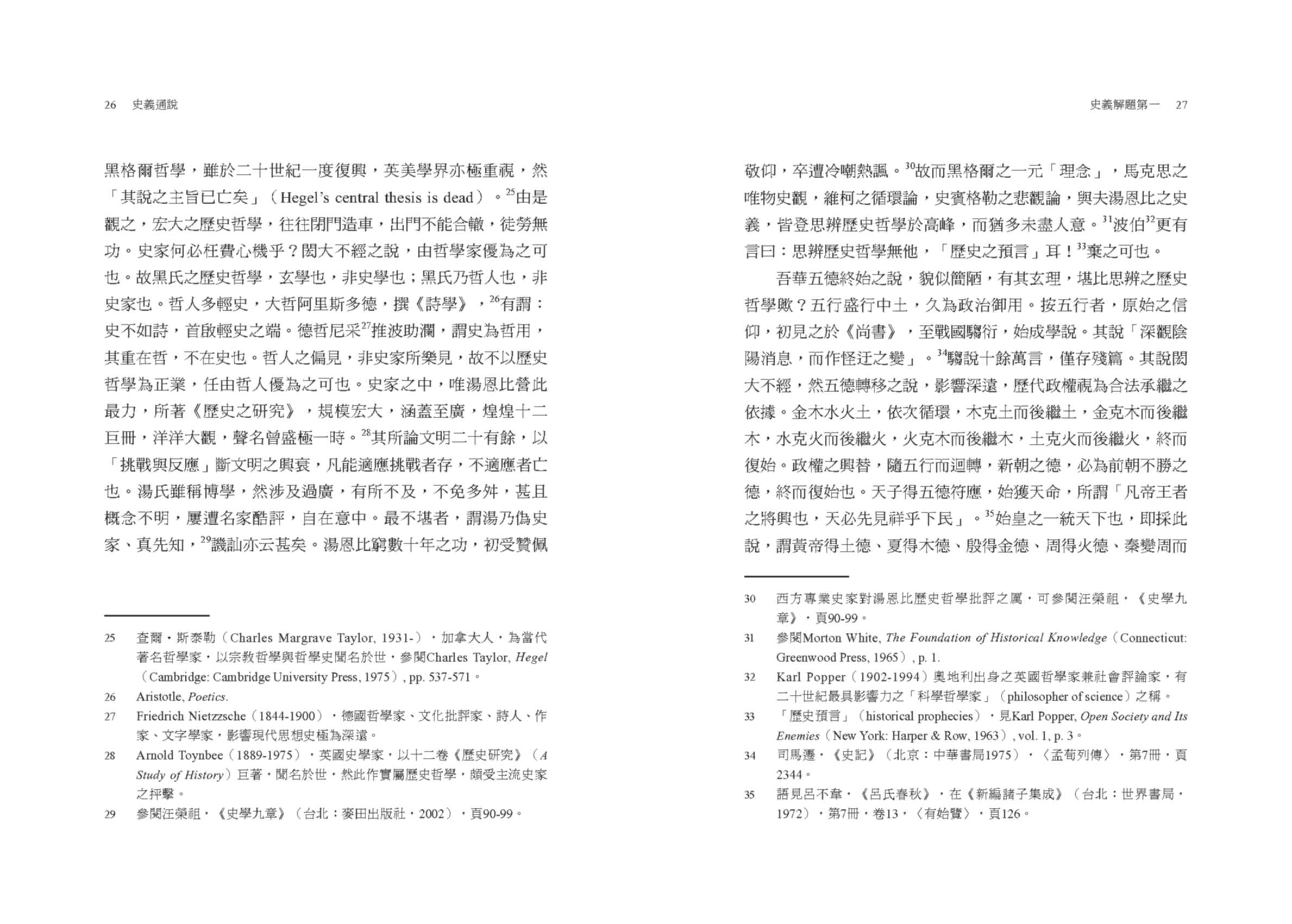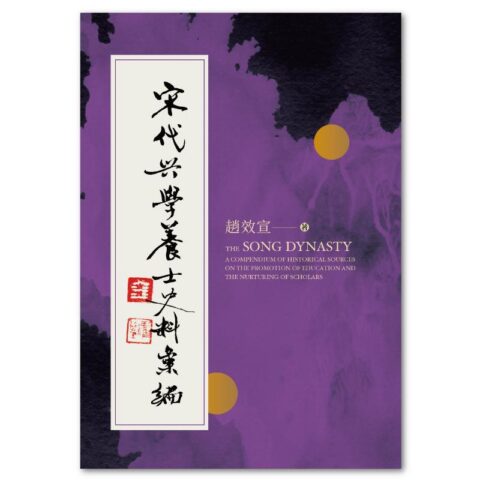史義通說
出版日期:2025-04-17
作者:汪榮祖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604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3.15 cm
EAN:9789570876079
尚有庫存
《史義通説》是《史傳通說》的姊妹篇。全書探討中國傳統史學,亦旁參西方史學,共有十五個議題:「史義解題」、「居今識古」、「經史之間」、「以易釋史」、「史有專職」、「尺幅千里」、「馳騁古今」、「實錄無隱」、「推果知因」、「疏通致遠」、「彰善癉惡」、「會萃諸錄」、「經世致用」、「史蘊詩心」、「承風繼統」。
汪榮祖强調,史學為文化之產物,有其淵源,必須縱承而後踵事增華,不能如自然科學那般橫向挪植。故對自西潮東漸以來,史學以西史為指歸,將西方之新取代中國之舊,華夏史學因西化而漸失主體性,詮釋之權往往旁落於外人,以至於國人重外人所說,而外人下視國人所說的窘境,感觸尤甚。
全書旁徵博引,比照西學,深入闡述,彰顯中西史學的異同,以及中國史學之特色與價值。
書封題字/陸善儀(隸書)
作者:汪榮祖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1971),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三十一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2003年之後的16年間,先後在海峽兩岸任教。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Routledge)等,中文專書《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等,以及中英文論文和書評多篇。
引言
史義解題第一
居今識古第二
經史之間第三
以易釋史第四
史有專職第五
尺幅千里第六
馳騁古今第七
實錄無隱第八
推果知因第九
疏通致遠第十
彰善癉惡第十一
會萃諸錄第十二
經世致用第十三
史蘊詩心第十四
承風繼統第十五
引用書目
引言(選摘)
泰西文藝復興,回歸古典,發現個人,因而人文崛起,神道衰微,學術始大昌明,開「啟蒙時代」之新境。啟蒙崇尚「理性」,視「自然法」為超時空之常法;然以科學之定法衡史,殊有未當,故歐陸史家超越自然律,發「歷史主義」之先聲,史觀為之一變。治史者非知不易之天理,無以明一時之陳跡。蓋陳跡有其「特性」,難以概括。是知理性而外,尚有個性。個性之「內在感覺」、「心理素質」(psychological qualities.)、「文化背景」(cultural background),與夫「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istics),各不相同,未可概而論之也。史有時地人之異,誠不可概論,新史觀於焉出矣!意國名師維柯已言之:「天界」(The World of Nature)有別於「心界」(The World of Minds);「心界」所重者,人也,迥異於天界所重之物,蓋兩者有「內外之異趣」也。維柯之見,預見形而上學之革命」;經此革命,遂有「物質科學」與「精神學科」,分立於日爾曼之壤。德人輒以科學等同學科,故有「歷史科學」(historischen Wisenschaften)之稱,以別於「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也。其別在於:聲光化電皆能親眼目睹,以精確之物理檢驗查證,萬無一失,而往事無從目睫,惟由史家轉述,心解殘存之遺跡,而遺跡乃滄海之一粟,難見其全,故人事之複雜,不同於物理之單純,兩者之異趣,固不可不知也。或曰:「史學致知,最能見及藝術與科學之相互輝映」,所言乃求史如科學之真,如藝術之美,非謂史能包攬藝術與科學也。科學一詞,若嚴格而論,乃自然科學,固毋庸贅言。竊以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鼎足而三,史學乃人文學科之屬也。
人文學科屬於精神範疇,所造之「心界」,不可預測,乃由典章制度而來,因具「史境」故也。舉凡思想制度,均落實於時空,而時空之變換,非由神力,亦非由天,而由於人,即維柯所謂:人文社會既由人創,其理路必由人心而知之。人之心靈、思維、感情,遂為治史者所不可輕忽者。維柯社會意識與時俱進之論,頗得晚近思想史家伯林之賞識,亟言史學之自立,維柯厥功至偉也,謂渠乃「史界之培根」!心界異於天界,唐代詩鬼李賀已有言:「天若有情天亦老」,惟天無情,所以不老也。按天界日夜流轉,四季相循,天理未嘗有失。故而英哲懷海德曰:現代物理之學,發源於西歐,地無分南北,人各東西,凡理性之域,皆能光大之也。驗諸泰西科技在華之突飛精進,已證懷氏所言之不虛。然而「心界」非若是!西山無不落之日,而人有悲歡離合之情。文化各異,史跡不同,價值有別,故而事實雖同,認知未必盡同,太炎所謂「不齊而齊,乃上哲之玄談」,亦即伯林 所謂「文化多元論」之義蒂也。泰西持「歐美文化中心之論」(Euroamerican culture),漫炫傲慢,不足為訓。蓋寰宇文化繁多,價值不一,安能定於一尊乎?斯言無他,文化各有特性,無分高低,非可盲目假借也。人類學家尤能辨識異同,明特色而後知價值有別,有助於史事之理解也。史者非科學之屬,乃文化之屬也。史之意義,出自作者,有其主觀,而需以理性思維抑之。惟現代理論之多富感性,有導史於虛無之虞,能不慎哉?
西士狄爾泰,認同心天兩界之異,亦即絕對與相對之異。心界無絕對,乃「經驗」之知,蓋史實有賴於內感與同情也。經驗易代有變,社會隔世有異,更無論中西之異同矣!然則,歷史主義所昭示者無他,文化因「史境」(historical context)之異而異耳。時空流轉,物換星移,故文化由時空界定,普世不能一體,誠屬不移之說。蓋人事異趣,斷無永恆之理。此論既風行歐陸,崇尚各異之地方色彩,於今兩百餘年矣。各異之文化,影響歷史之演進,既深且遠,已屬定論。然則,既不宜以洋論華,亦不能「以今論古」(anachronism)。以今論古,今之偏見有焉;以洋論華,偏見亦有焉。故而史家所重者,應凴原始史料,理解特殊情景,如此而已。
章太炎嘗言國之特性有三:語文、習俗與歷史。按文明古國,諸如巴比倫與埃及古國,因失特性而亡。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至今猶在,文化特性猶在也。惟古文式微,習俗有失有存,尚待惜而固之;國史雖未斷,然師法泰西,史統已不絕如縷。西化之挑戰,至今未能盡解。要因精神文明有異於物質,要能縱承,香火宜傳;可以旁參,何須橫植,無根浮萍,安得成長?中華史學一如泰西,各自有其傳承、時空觀念、問題意識、理論架構。英法德俄諸國,史學之話語權,無不自握其手,不隨他人起舞也。中西之間,自有不期相契,神會妙悟之處,笑與忭會之趣,然若不求甚解,以西方學理為真理,以彼既成之見,傾心相從。甚而外人誤釋吾中華歷史,亦盲從無疑,以為外人於廬山之外,更能見廬山之真貌,欣賞無已,不自覺入其主而自奴乎?例不細舉,北美有「新清史」論者,以其解構理論,顛覆清史,否認滿族漢化,視族群認同為國家認同,故稱大清非中國,乾隆非中國皇帝,妄稱滿清上承北元,而非繼承明室云云,因而質疑當今中國之疆域,何異於日寇侵華之「滿蒙非中國」論歟?如此謬論,能不駁斥?失學之徒,不聞康熙帝曾諭大學士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見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清帝親諭在目,足正邪說也。元人滅宋,宋有忠義之士;明人滅元,亦有為故主隕身之臣,清室既屋,民國遺老,亦不乏漢人,豈因蒙元滿清,入主中國,而有異情哉?況元明間盛傳元順帝乃宋恭帝之子,若然,則八十九年之蒙元,順帝獨得三十六年,元帝乃趙宋之遺胤歟?或謂此說微噯難明,傳聞異詞,或乃南宋遺民不忘故國之流言?錢牧齋以閩人余應諸詩及權衡所撰《庚申外史》,比而觀之,發覺若合符節,以為可信不誣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九跋《庚申外史》,以為「大抵為傳聞之失漏」。萬斯同《群書疑辨》卷十一,舉例力證:「順帝之為恭帝子,可無疑矣」,又謂:「趙氏之復有天下也,章章明矣」!近人王國維初不之信,考而後信之矣。余嘉錫辯證甚力,曰雖無確證,然不可盡以外史之說,荒誕不經,而以錢、全、萬、王諸名家所說,可存也。蓋當時無DNA可資驗證,所謂確證安可得乎?惟異族入主中國,胡漢交融,血脈莫可追究,一如章太炎所云:數千年之中華,已成歷史民族矣!而域外之人,動輒謂滿蒙非中國,焉能相從?由此可見,史學之話語權,不容假借;若授人以柄,何異陷入薩依德之「東方主義」論歟?是知史學有其主體性也,若無主體,則史權拱手相讓,往事任由外人評說,何異青史成灰、國魄淪喪耶?史滅而國亦裂矣!
然則,徑自橫植泰西文化於中土,殊有違歷史主義之微意也。欲以泰西之歷史哲學,詮釋吾華之歷史演進,必有扞格。然自五四以來,歐風美雨,普降中土,一時風從,名師宣揚,承學之士,驚豔之餘,傾心西化,以洋為師,範式理論,一以泰西為尊,視中華學統,有違時尚,而棄如蔽履,舊學因而消沉矣!固然仍有識者,驚愕「詆苛往哲,攘斥舊籍」、「稗販歐風,幾亡國性」,然人少言輕,難敵西潮洪流。五四至今百年,傳統斷層已見,經典雖存,讀者日少,豈無名存實亡之虞?固有文化,日薄西山,誠非虛言。再百年而後,吾華之物質文明,或可獨步寰宇,引領風騷;惟人文國魄,或將淪為泰西之臣虜歟?晚清詩人金亞匏,有〈西施咏〉詩曰:「溪水溪花一樣春,東施偏讓入宮人;自家未必無顏色,錯絕當年是效顰」。全盤西化論者,豈非東施效顰者歟?錯絕當年,奈何悔之晚矣。
吾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先秦百家爭鳴,秦漢而後,儒法道為重,政統重法,而道統重儒。洋人稱吾華為「儒教國」(Confucian China),未見允當。秦政以法立國,未嘗諱言專制;漢鑒秦之弊,儒法兼用。其治術也,可稱以儒飾法。儒家其表,法家其裏,歷代皆如是也。帝制非法不治,法術嚴苛,賴儒術柔之。儒為政用,可以救法之弊,故非儒,政不穩也。儒家君親師並舉,以倫理尊君,惟儒學非僅隨政術而變,其基本教義,久而深入人心,士人遵奉莫疑,形成西士所謂之「大傳統」(Great Tradition)也;影響所及,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儒家遂有民間之「次傳統」(Little Tradition)矣。所謂上行下效也。故儒為政用,亦為深植人心之社會價值矣。
儒學非僅孔學,儒先於孔,孔後諸家各有異趣,孟荀善惡不同,朱陸敬靜有別。儒者各自詮釋,非有違尼山初旨,實欲踵事增華,猶如泰西所謂「思想史」(intellectul history)者,乃歷代思想家之所思,思想承繼,並非一陳不變也。儒家為漢文化之主體,然漢文化非僅儒家,亦非僅先秦諸子,魏晉而後,佛學昌盛,華夷種姓,復多交融。胡漢文化之互動也,漢化有之,胡化亦有之,惟自先秦至晚清,始終以漢文化為主,綿延不絕,而後有今日多民族之中國。然悠久之傳統文化,因西化而式微。西潮固然洶湧,而五四激進之士,捨身風從,甚且推波助瀾,狂瀾莫之能禦矣!觀乎具舊學根底者,幾皆生長於五四之前,史學二陳,固無論矣,民國蜀人劉咸炘,生於光緒丙申,繼浙東章氏之學,有志踵舊史而增其華,積稿甚多,惜不永年也。凡生於五四之後者,去舊學日遠,崇洋鄙舊,學風為之丕變。帝制終結,政統雖盡,學統猶在,然而趨新之徒,以為除舊未盡,不足迎新。於是以打孔是尚,苦相折挫,不留餘地。儒教曾為帝制所用,固不足取,然儒學何辜,竟遭池魚之殃!凡舊學幾一併棄之,精粹與糟粕俱盡,豈非如西諺所謂:「嬰兒與浴水俱傾之矣」(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魯莽滅絕,莫此為甚也!
吾華傳統文化之特色,其犖犖大者,曰漢字、曰歷史、曰習俗、而近人視傳統為「中世紀」、視為「封建」而鄙之。視漢字為古文字,難以適應現代之需而應去之,故有「錢君玄同主廢漢字為羅馬拼音」,更以舊史不可信而欲以西法代之;以儒學為「帝王之學」,而宜掊之;以習俗守舊,而應棄之,而後方得進入現代文明云。惟現代文明自何而來?非出自西方文化乎?西方得現代之先機,故而開出現代文明,現代遂具歐美特色,不足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也。現代物質文明雖日漸趨同,然精神文明難能一致,故有文明衝突之說。晚近美國日裔學者福山,以為歐美精神文明,諸如民主自由,市場經濟,於蘇聯解體之後,已一統寰宇,故有「歷史終結」之論。然事與心違,後冷戰之世界,非如福山所見,其立論多舛,尤無視國族意識之強,基本教義信念之堅,為識者所譏訕。福山一時之樂觀,難掩其霸權心態。當今世事變幻,足稱「歷史終結之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也乎?文明既有衝突,是知歐美之價值不能普世也。傾心西化者,授人以柄,將如太炎所慮:「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太炎嘗言:欲免國性淪亡,語文、歷史、習俗,三者斷不能棄。五四而後,婚喪喜慶,衣食住行,飲食之外,幾盡西化,其中固有不得不爾者,亦有不必然者,服飾宅邸,宜能變舊為新,別具華夏風貌,何須全盤西化?固有之親情孝心,何莫存而惜之,以避舶來之疏離。儒教屢經質疑,訂孔、打孔之餘,三綱五常,陰陽五行,隨風而逝可也。儒為今用要能以王道救霸道之弊,霸道以力制人,難服人心,而王道以德服人,始其宜矣;霸道尚武,烽火不熄,生靈塗炭;王道以和為貴,雙贏互利,乃正義之世界秩序。漢字幸而未廢,否則舊學所剩餘幾?五四而後,以白話取代文言,有俗語而無雅文,影響所及,舊學難繼也。按雅文乃典章文物之寶筏,失此彼岸莫登。不識古文,則固有之典籍、書畫、歌詩、戲劇,皆因失語境而趨式微。迦陵先生傾畢生之力,起舊詩詞於既衰,白兄先勇賦昆曲以新生命,遂令古典風雅之美,未隨西潮東流而去,此挽瀾有成之例也。至於史學,先秦至乎晚清,史冊無不以古文書寫,無此鑰匙,堂奧莫啟,千年之史統,何以為繼?苟唯西法是從,無異削足適履,自主之史學,安可得乎?
三十餘年前撰《史傳通說》既竟,嘗言意興未盡,果有此作也。斯稿欲探舊史要義,再作野芹之獻。蓋文史之學,與傳統血脈相連,乃自主之學,未可自毀立場。義寧陳氏所慮者,「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感同身受也。或謂中華史學,惟中央史觀,昧於域外。此說不知近代之前,東西相隔,殊少往來,泰西史學亦不知有華夏也。德國大哲黑格爾所謂之「通史」(universal history),乃歐洲之通史耳。黑氏區分有史之世界,無史之世界,歐洲之外,別無史也。泰西史學即寰宇敘事,「大聲獨唱」(a grand récit),不惜湮滅眾聲。以彼之見,異域之史,無足輕重者也。然則彼所謂之「全史」,何全之有?吾華舊史,雖多因循蹈襲,常以古人之心為心,較少推陳出新,然非可一概而論也。近人因而捨舊取新,盡從西洋,昧於傳承不可輟,承古方能開今也。何莫旁參西學,借照鄰壁之光,以踵事增華,求舊學之翻新也。按史有事有文有義,而以義為至要,實齋重之,故謂「作史貴知其意」,其意在明道經世,斯即義也。民國史家柳翼謀亦曰:「史學所重者義也,徒騖事跡,或精究文辭,皆未得治史之究竟」。章柳兩氏之史義,近乎夫子所「竊取」之大義也。
予借「史義」舊詞,承舊出新,繼劉章先賢之後,不以《春秋》懲惡勸善為宗,無囿於綱常名教之說,旁採泰西史學精義,參照華夏特色,以冀披沙揀金,折中求是,重光中華史學之要義,譬如提陳醑之佳釀,同品遠方之美酒,所謂食得三珍,味始刁也。惟學海無涯,一帆難渡,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史義通說之所望云爾。回首前塵,開筆於庚子之凋年,藏身於庸椽高樓,讀寫度日,時光之容易把人拋也。鼠去牛來,不覺虎年又至,終於稿成。偶憶東坡所謂:「哀吾身之須臾,羡長江之無窮」,正見人文與自然之異趣。古今同情,豈不謂然?唯有提煉精華,庶能繼往開來也。稿成之際,念徐子老之啟迪,感蕭跡園之扶持,珍惜金華何先生之關愛,羡迦陵之承風,嘆槐聚之難繼。臨筆神馳,感念無已!書前題詩,略表作者之心意耳。
史義解題第一
「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泰西之史義也。始於意人維柯,其學當世未顯,後日奉為先行。若再遠朔淵源,未嘗不可上推聖奧古斯丁。泰西歷史哲學,自成學門,則始自德人赫爾德,而盛於黑格爾。此學吾華罕見,故泰西論師,輒以哲學為彼邦所獨有,中土無之,故哲學史亦即西方哲學史也。唯獨英哲羅素撰《西方哲學史》,以示所論僅是西方哲學,殊為難得。按哲學一詞,誠不見於吾華舊籍,乃自日譯而來。此字原意為「愛智之學」,中華豈無愛智之學耶?雖有之,惟不盡相同耳。先秦諸子之學,諸如老聃退化說、孔丘名分說、韓非權力說,墨翟天志論、莊周相對論、鄒衍循環論、荀卿厚今薄古,不無思辨玄想,更無論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也。然與泰西哲學相比,未見邏輯論證,有欠系統論述。故而歐美論師,多謂東方無哲學也。蓋以彼之哲學,論我之哲學,豈非如以蕉論橘,而謂橘非蕉歟?既云無哲學矣,何來歷史哲學乎?
歷史哲學,其意云何?質言之,以哲學思維,演繹史之本質,以理性思維解釋史實,發見歷史軌跡、探索歷史意義之謂也。歷史哲學約有古典與現代之分,「古典」者,又稱「思辨(玄學)哲學」;「現代」者,又稱「分析哲學」。古典以系統思維,通觀全史,建構體系,賦予意義,以示歷史趨向之動力,及其歸宿,命乎?神乎?人性乎?規律乎?模式乎?目的乎?意義乎?類此皆思辨歷史哲學所欲問者也。其體系每多宏偉,派別亦漸繁多。法哲伏爾泰於《列國風情思維論》,綜述歐西中印諸文化,取有用之歷史教訓,因伏氏有鑒於其時,言行墮落,而有所望於未來,自稱所著即歷史哲學也。史之為用,非僅提供事實,且示方法之學。德人赫爾德更以通史概念,多所論述,額其書曰:「歷史哲學」。後起之黑格爾、馬克思諸輩,皆此道之名宿鉅子。黑格爾之《歷史哲學》影響深遠,名望尤高。黑氏視世界由至高無上之理性所統治,更以「形而上學」反思精神生活,而以「自由」為「精神」之本質,而精神具有層次,自由具有等級。是以歷史進程乃精神之成長,而成長取決於自由之能量。故黑氏縱覽全史,深信自由之潛力,而自由賴意志以進;唯有意志,方能登精神之佳境也。惟自由非蓄意可得,人本無上進之心,不知邁向理性之路,易流於激情私欲,黑氏謂之「理性之詭」(cunning of reason)。蓋理性支配世界,需有紀律,故唯法治社會能有自由,而自由社會之完成,則有賴於「國家」。據此,黑氏曰:世界史之重心漸由東而西,東方之中國、印度、波斯發其端,古中國之「神權專制」(theocratic despotism),唯皇帝有自由,斯乃低層之自由,所設定之倫理無道理,史皆零星之事實,科學僅屬技術,法律乃意志之表達。黑格爾貶低吾華之餘,又謂印度之精神或高於中國,然而無論中印,皆無發展精神之基礎,均處停滯狀態。波斯精神雖見諸宗教,但其宗教猶非希臘之儔。黑格爾遂視東土如人生之童年,惟一人有自由;希臘已入少年,多人有自由矣;羅馬初入成年,至德意志始臻於成熟,人人皆有自由矣!於此可見,黑格爾之史觀,以自由為核心,凴理性成長,由「正」、「反」、「合」三段,由有序之辯證而來。因不足而有「反」,有反而後有矛盾,卒以「合」解之,斯即理性之運作也。按此邏輯,黑氏之母國乃自希羅以來,自由發展最終之「合」。黑論雖然有序,自我中心之傲慢,難以掩蓋也。
黑格爾視其辯證為必然,其意云何?黑氏有全史在胸,建立四階段必然之精神進程,非「決定論」而何?而其決定論,乃形而上之設想,罕見佐證之史料,信手取材,以符其預設而已。黑格爾知時代之異,故曰但丁有異於荷馬,然其所述時代之變遷,仍基於其自身設想之思維。渠雖稱鴻儒博學,認知仍有所不足,尤昧於中華文化,為其病痛之所在。試問史既各有主體,別具特性,安能以一理貫之耶?黑氏無據之妄斷,能不謬乎?槐聚舉證曰:「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然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鉅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豈不然歟?英倫大哲羅素則評之曰:黑氏之知,不出地中海世界之外也。北美名師曼德邦,亦譏之曰:黑格爾於中國四千年悠久之史,茫然不知其要。黑氏所知之中國,多自耳聞,想當然耳,而吾華碩儒讀黑氏書,見說中華無主觀自由,無個體性之自覺,竟「悚然而驚」,不解黑氏茫然於中國事也。黑氏貴其母國,謂日爾曼為自由之巔峰,竟出非理性之混世希魔,而卒亡其國,不亦謬乎!黑氏極端之唯心論「理念」(Idea),與個人浪漫與國家重利之工業化新世紀,所尊之「科學」(Science),背道而馳。然則,其所演繹之哲理實未能貫徹,哲學名家泰勒謂黑格爾哲學,雖於二十世紀一度復興,英美學界亦極重視,然「其說之主旨已亡矣」(Hegel’s central thesis is dead)。由是觀之,宏大之歷史哲學,往往閉門造車,出門不能合轍,徒勞無功。史家何必枉費心機乎?閎大不經之說,由哲學家優為之可也。故黑氏之歷史哲學,玄學也,非史學也;黑氏乃哲人也,非史家也。哲人多輕史,大哲阿里斯多德,撰《詩學》,有謂:史不如詩,首啟輕史之端。德哲尼采推波助瀾,謂史為哲用,其重在哲,不在史也。哲人之偏見,非史家所樂見,故不以歷史哲學為正業,任由哲人優為之可也。史家之中,唯湯恩比營此最力,所著《歷史之研究》,規模宏大,涵蓋至廣,煌煌十二巨冊,洋洋大觀,聲名曾盛極一時。其所論文明二十有餘,以「挑戰與反應」斷文明之興衰,凡能適應挑戰者存,不適應者亡也。湯氏雖稱博學,然涉及過廣,有所不及,不免多舛,甚且概念不明,屢遭名家酷評,自在意中。最不堪者,謂湯乃偽史家、真先知,譏訕亦云甚矣。湯恩比窮數十年之功,初受贊佩敬仰,卒遭冷嘲熱諷。故而黑格爾之一元「理念」,馬克思之唯物史觀,維柯之循環論,史賓格勒之悲觀論,與夫湯恩比之史義,皆登思辨歷史哲學於高峰,而猶多未盡人意。波伯更有言曰:思辨歷史哲學無他,「歷史之預言」耳!棄之可也。
吾華五德終始之說,貌似簡陋,有其玄理,堪比思辨之歷史哲學歟?五行盛行中土,久為政治御用。按五行者,原始之信仰,初見之於《尚書》,至戰國騶衍,始成學說。其說「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騶說十餘萬言,僅存殘篇。其說閎大不經,然五德轉移之說,影響深遠,歷代政權視為合法承繼之依據。金木水火土,依次循環,木克土而後繼土,金克木而後繼木,水克火而後繼火,火克木而後繼木,土克火而後繼火,終而復始。政權之興替,隨五行而迴轉,新朝之德,必為前朝不勝之德,終而復始也。天子得五德符應,始獲天命,所謂「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始皇之一統天下也,即採此說,謂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變周而得水德,其色尚黑,名河曰德水,為水德之始。秦德其短,漢續水德;武帝改制,易為土德。董仲舒有五德為三統四法之說,將朝代之遞嬗,視為黑統、白統、赤統之循環,以及夏商文質之循環。三統以三數循環,四法以四數循環,三四十二代,即成一大循環矣。五德轉移,遂淪為政治工具。以五德終始、五行相勝,說王朝之興替,自兩漢而後,皆以大一統為主流,綿延兩千餘年矣!此說何以稱之?通觀歟?玄學歟?難言之也。蓋五行思維有序,不免參雜迷信。明人王廷相有言:「淫僻于陰陽者,必厚誣天道;傅會於五行者,必熒惑主聽」。皇家以此論正統,乃治術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