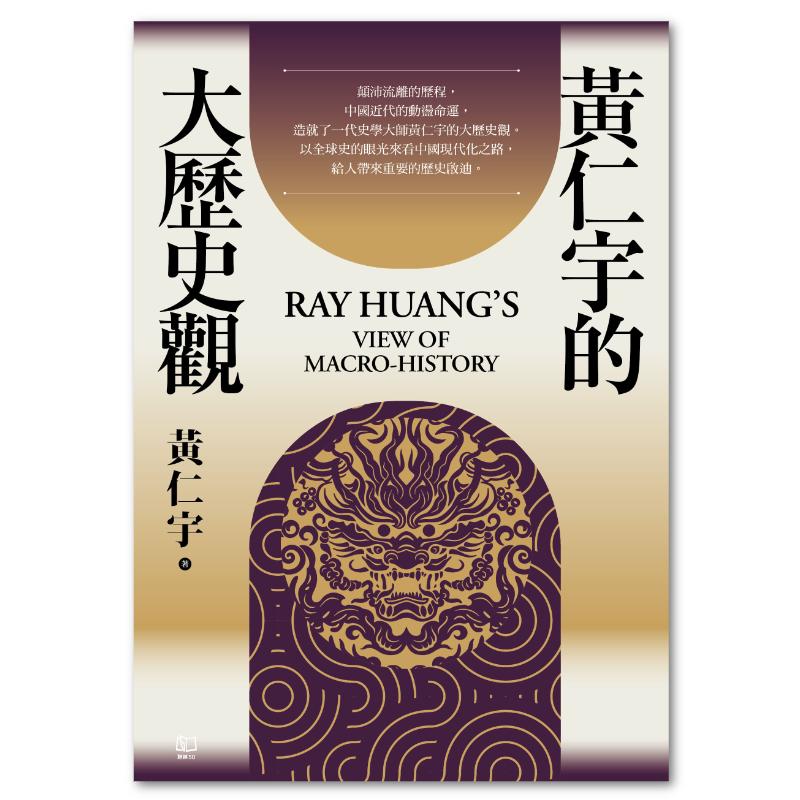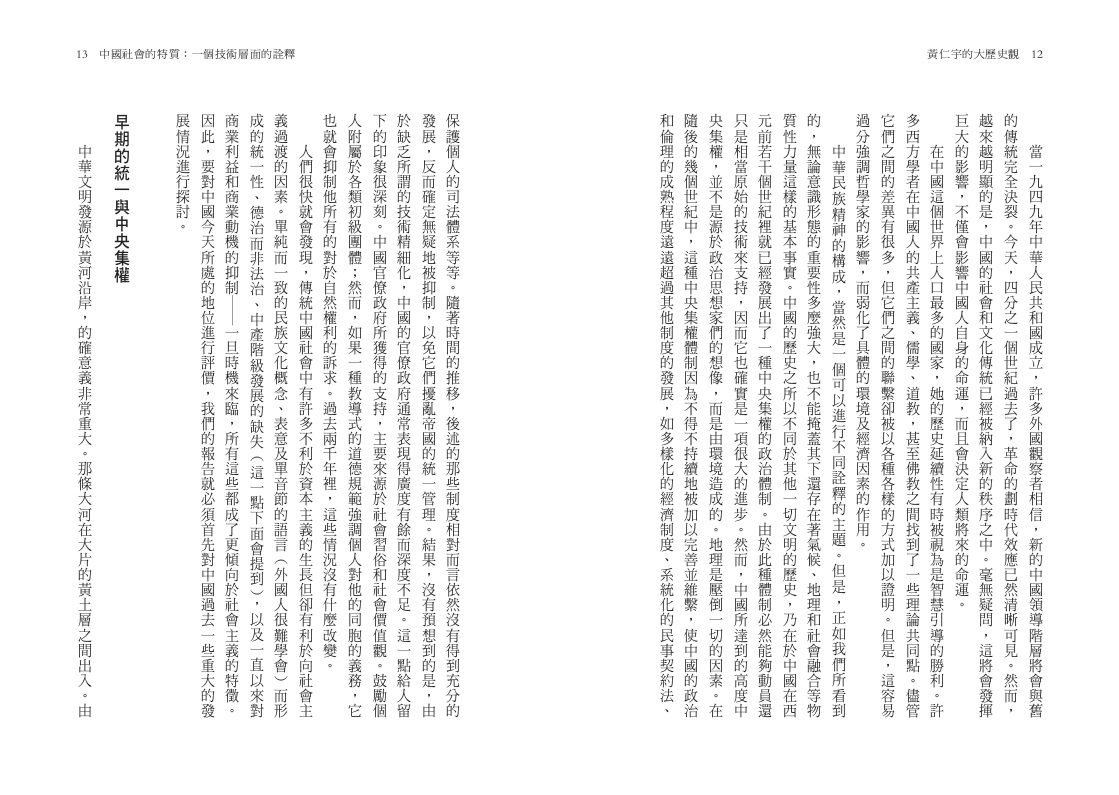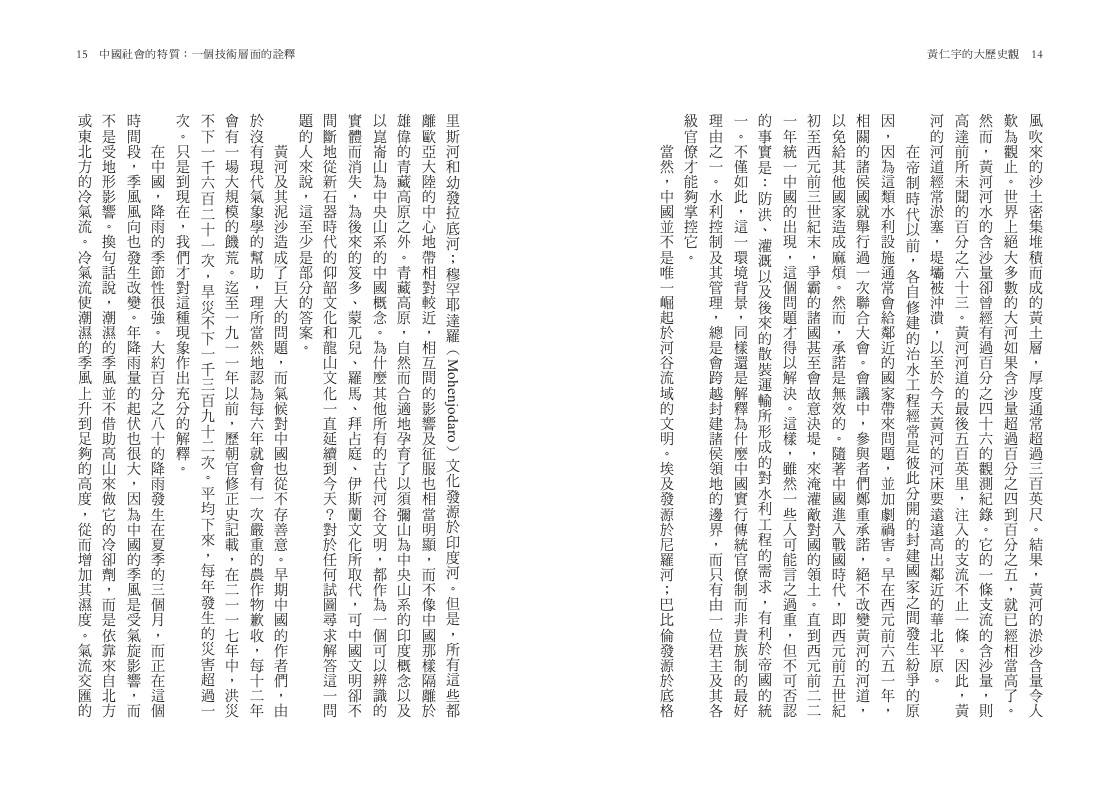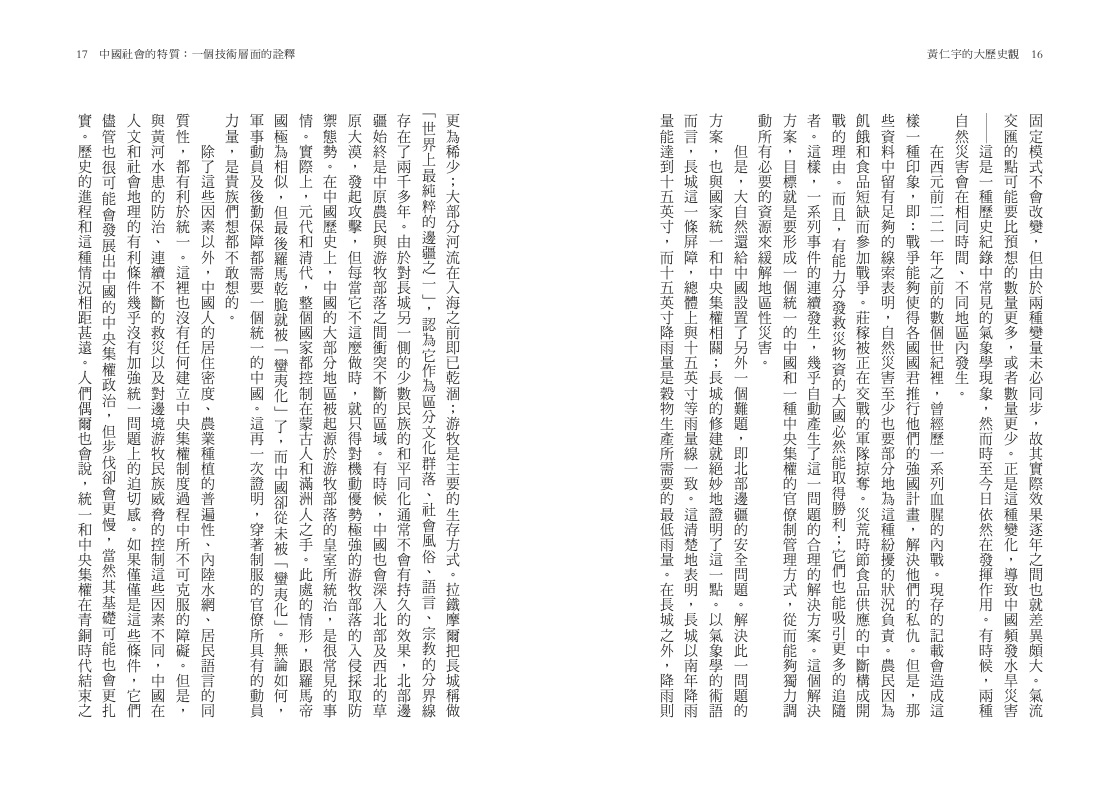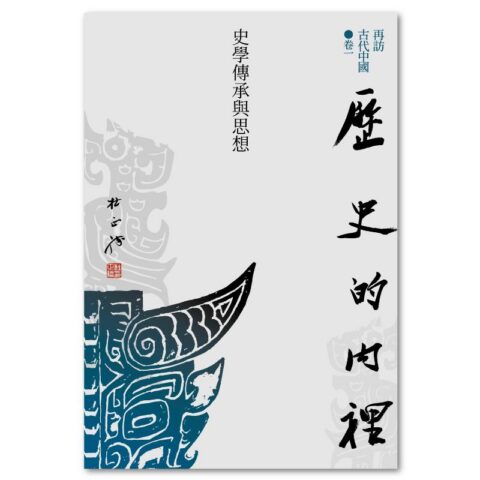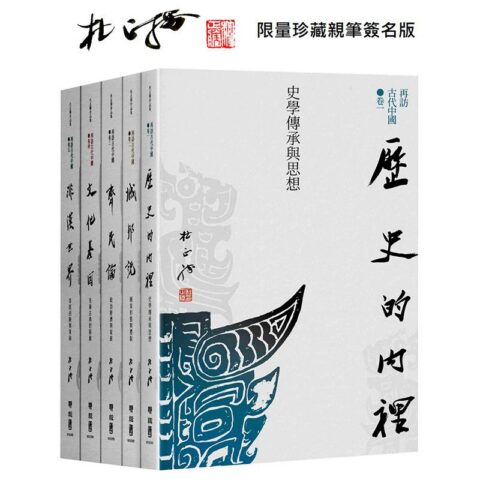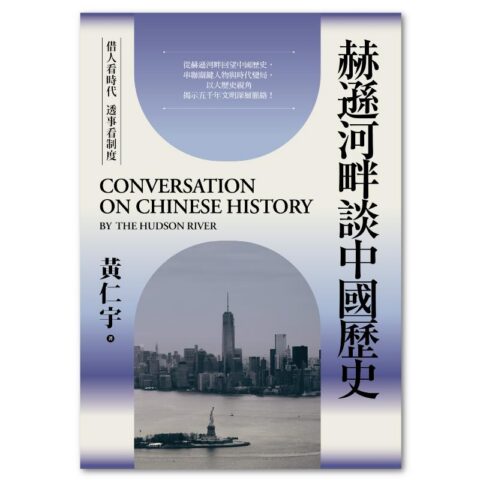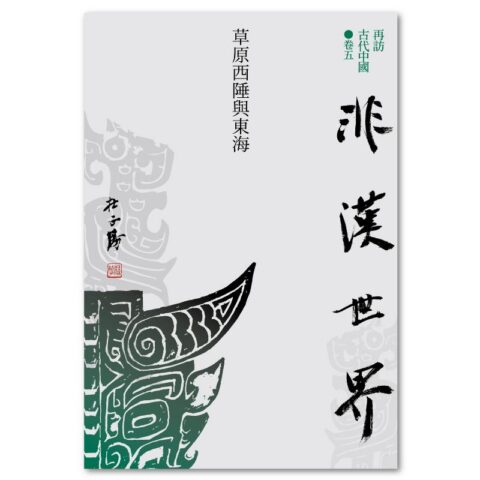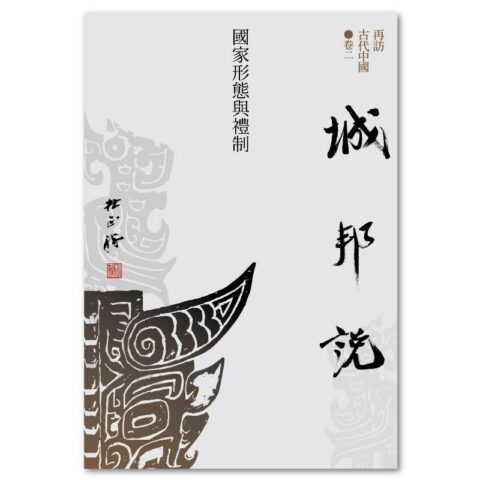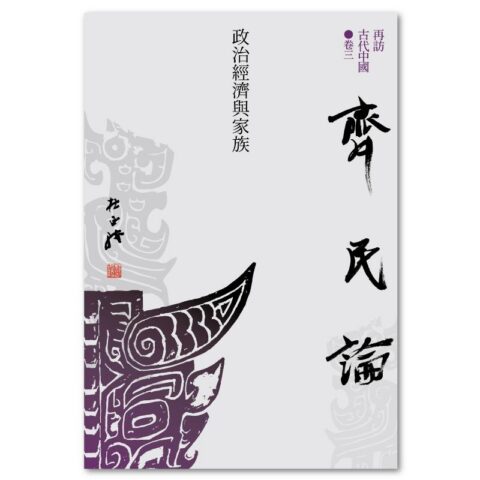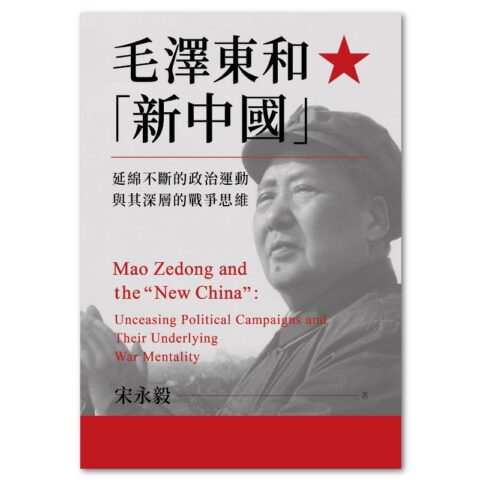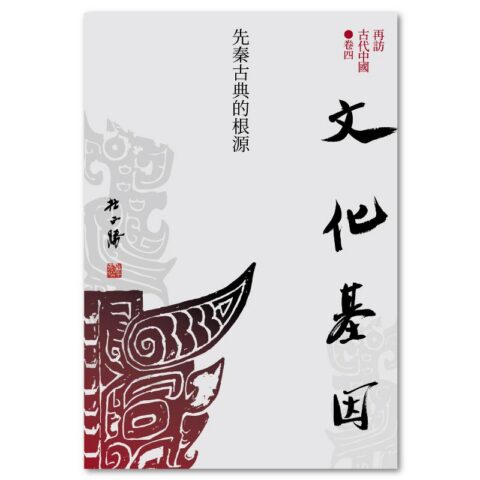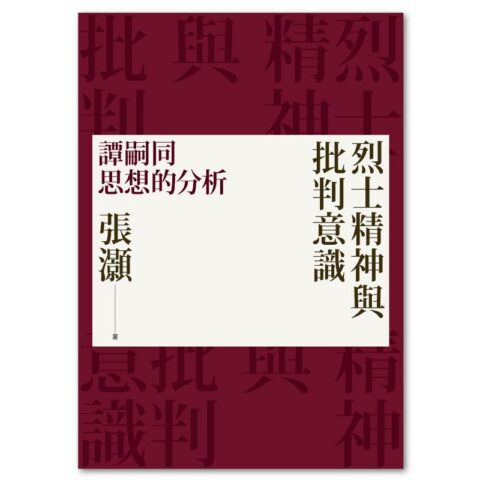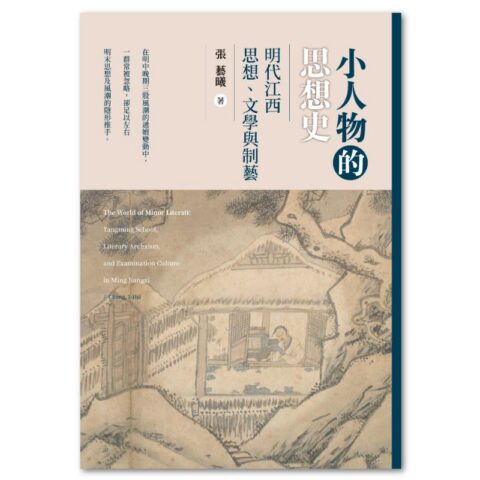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出版日期:2025-04-17
作者:黃仁宇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長 21 × 寬 14.8 × 1.9 cm
EAN:9789570875324
系列:黃仁宇文集
尚有庫存
顛沛流離的歷程,中國近代的動盪命運,造就了一代史學大師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以全球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現代化之路,給人帶來重要的歷史啟迪。
「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我開始接觸(歷史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我才發現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緊密相連。」
本書收錄黃仁宇未曾結集出版的單篇專文,散見於英國、美國、德國、香港、臺灣等地報刊雜誌,透過多方蒐集整理成冊。並以黃仁宇的長時段、慢結構的大歷史觀點為題,是窺視黃仁宇思想的最佳途徑。
書中探討內容極為廣泛,涵蓋了從中國社會的特質、明代的財政管理系統,到蔣介石的歷史定位等,充分展現了黃仁宇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獨到見解。他因親身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苦難,決意投身歷史研究,探究歷史的因果。唯有釐清這些因果,才能為近現代中國尋求一個可能的解方。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
《萬曆十五年》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明代的漕運,1368-1644》
《中國大歷史》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放寬歷史的視界》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地北天南敘古今》
《關係千萬重》
《大歷史不會萎縮》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緬北之戰》
《長沙白茉莉》
《汴京殘夢》
《黃河青山》
作者: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
黃仁宇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並提倡「大歷史觀」而為人所知。「大歷史觀」不對單一歷史人物或事件作評價,而是通過分析當時代政治、社會整體面貌,進而掌握歷史的特點。主要著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
出版說明
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
早期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農業社會的官僚政治管理
科學技術和貨幣經濟的低水平發展
社會後果
歐洲的過去和中國的未來
從唐宋帝國到明清帝國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
明代的財政管理
傳統理財思想與措施的影響
戶部及戶部尚書
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一五九○年前的財政管理
一五九○年後的財政管理
結論
什麼是資本主義?
當代論述資本主義的學派
資本主義的精神
布勞岱對中國經濟史的解釋
官僚體系的障礙
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法律與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範圍
資本主義的時空剖析
資本主義的條件
蔣介石
蔣介石的歷史地位:為陶希聖先生九十壽辰作
站在歷史的前端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臺灣的機會與困境
中國歷史的規律、節奏
黃仁宇著作目錄
出版說明
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已經出版十餘本,但仍然有一些論文散落各處,未曾收入現已出版的著作中,對於喜愛黃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黃仁宇先生的讀者都知道,他最擅長的就是以具體的例子說明大歷史的道理。他常提到「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這一觀念,意思是說,我們看歷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個人的道德立場講解歷史。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一個國家與社會之所以會與時代脫節,並非任何人的過失,我們要看的是,各時期的土地政策、財政管理、軍備情形、社會狀態、法律制度等。我們要考慮的是,能夠列入因果關係的,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的細微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要認為是次要的。
本書共收論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明代的財政管理〉、〈中國社會的特質〉等四篇原為英文論文,由陳時龍先生譯為中文。透過這十篇過去沒有機會閱讀的文章,讀者當能更加體會上述的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點。
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
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外國觀察者相信,新的中國領導階層將會與舊的傳統完全決裂。今天,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革命的劃時代效應已然清晰可見。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傳統已經被納入新的秩序之中。毫無疑問,這將會發揮巨大的影響,不僅會影響中國人自身的命運,而且會決定人類將來的命運。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她的歷史延續性有時被視為是智慧引導的勝利。許多西方學者在中國人的共產主義、儒學、道教,甚至佛教之間找到了一些理論共同點。儘管它們之間的差異有很多,但它們之間的聯繫卻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證明。但是,這容易過分強調哲學家的影響,而弱化了具體的環境及經濟因素的作用。
中華民族精神的構成,當然是一個可以進行不同詮釋的主題。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多麼強大,也不能掩蓋其下還存在著氣候、地理和社會融合等物質性力量這樣的基本事實。中國的歷史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文明的歷史,乃在於中國在西元前若干個世紀裡就已經發展出了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由於此種體制必然能夠動員還只是相當原始的技術來支持,因而它也確實是一項很大的進步。然而,中國所達到的高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源於政治思想家們的想像,而是由環境造成的。地理是壓倒一切的因素。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這種中央集權體制因為不得不持續地被加以完善並維繫,使中國的政治和倫理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制度的發展,如多樣化的經濟制度、系統化的民事契約法、保護個人的司法體系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後述的那些制度相對而言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反而確定無疑地被抑制,以免它們擾亂帝國的統一管理。結果,沒有預想到的是,由於缺乏所謂的技術精細化,中國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現得廣度有餘而深度不足。這一點給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國官僚政府所獲得的支持,主要來源於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觀。鼓勵個人附屬於各類初級團體;然而,如果一種教導式的道德規範強調個人對他的同胞的義務,它也就會抑制他所有的對於自然權利的訴求。過去兩千年裡,這些情況沒有什麼改變。
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傳統中國社會中有許多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生長但卻有利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因素。單純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單音節的語言(外國人很難學會)而形成的統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產階級發展的缺失(這一點下面會提到),以及一直以來對商業利益和商業動機的抑制──一旦時機來臨,所有這些都成了更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特徵。因此,要對中國今天所處的地位進行評價,我們的報告就必須首先對中國過去一些重大的發展情況進行探討。
■ 早期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沿岸,的確意義非常重大。那條大河在大片的黃土層之間出入。由風吹來的沙土密集堆積而成的黃土層,厚度通常超過三百英尺。結果,黃河的淤沙含量令人歎為觀止。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過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就已經相當高了。然而,黃河河水的含沙量卻曾經有過百分之四十六的觀測紀錄。它的一條支流的含沙量,則高達前所未聞的百分之六十三。黃河河道的最後五百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條。因此,黃河的河道經常淤塞,堤壩被沖潰,以至於今天黃河的河床要遠遠高出鄰近的華北平原。
在帝制時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經常是彼此分開的封建國家之間發生紛爭的原因,因為這類水利設施通常會給鄰近的國家帶來問題,並加劇禍害。早在西元前六五一年,相關的諸侯國就舉行過一次聯合大會。會議中,參與者們鄭重承諾,絕不改變黃河的河道,以免給其他國家造成麻煩。然而,承諾是無效的。隨著中國進入戰國時代,即西元前五世紀初至西元前三世紀末,爭霸的諸國甚至會故意決堤,來淹灌敵對國的領土。直到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的出現,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這樣,雖然一些人可能言之過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防洪、灌溉以及後來的散裝運輸所形成的對水利工程的需求,有利於帝國的統一。不僅如此,這一環境背景,同樣還是解釋為什麼中國實行傳統官僚制而非貴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總是會跨越封建諸侯領地的邊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級官僚才能夠掌控它。
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崛起於河谷流域的文明。埃及發源於尼羅河;巴比倫發源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穆罕耶達羅(Mohenjodaro)文化發源於印度河。但是,所有這些都離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相對較近,相互間的影響及征服也相當明顯,而不像中國那樣隔離於雄偉的青藏高原之外。青藏高原,自然而合適地孕育了以須彌山為中央山系的印度概念以及以崑崙山為中央山系的中國概念。為什麼其他所有的古代河谷文明,都作為一個可以辨識的實體而消失,為後來的笈多、蒙兀兒、羅馬、拜占庭、伊斯蘭文化所取代,可中國文明卻不間斷地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對於任何試圖尋求解答這一問題的人來說,這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黃河及其泥沙造成了巨大的問題,而氣候對中國也從不存善意。早期中國的作者們,由於沒有現代氣象學的幫助,理所當然地認為每六年就會有一次嚴重的農作物歉收,每十二年會有一場大規模的饑荒。迄至一九一一年以前,歷朝官修正史記載,在二一一七年中,洪災不下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災不下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平均下來,每年發生的災害超過一次。只是到現在,我們才對這種現象作出充分的解釋。
在中國,降雨的季節性很強。大約百分之八十的降雨發生在夏季的三個月,而正在這個時間段,季風風向也發生改變。年降雨量的起伏也很大,因為中國的季風是受氣旋影響,而不是受地形影響。換句話說,潮濕的季風並不借助高山來做它的冷卻劑,而是依靠來自北方或東北方的冷氣流。冷氣流使潮濕的季風上升到足夠的高度,從而增加其濕度。氣流交匯的固定模式不會改變,但由於兩種變量未必同步,故其實際效果逐年之間也就差異頗大。氣流交匯的點可能要比預想的數量更多,或者數量更少。正是這種變化,導致中國頻發水旱災害──這是一種歷史紀錄中常見的氣象學現象,然而時至今日依然在發揮作用。有時候,兩種自然災害會在相同時間、不同地區內發生。
在西元前二二一年之前的數個世紀裡,曾經歷一系列血腥的內戰。現存的記載會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戰爭能夠使得各國國君推行他們的強國計畫,解決他們的私仇。但是,那些資料中留有足夠的線索表明,自然災害至少也要部分地為這種紛擾的狀況負責。農民因為飢餓和食品短缺而參加戰爭。莊稼被正在交戰的軍隊掠奪。災荒時節食品供應的中斷構成開戰的理由。而且,有能力分發救災物資的大國必然能取得勝利;它們也能吸引更多的追隨者。這樣,一系列事件的連續發生,幾乎自動產生了這一問題的合理的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目標就是要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和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管理方式,從而能夠獨力調動所有必要的資源來緩解地區性災害。
但是,大自然還給中國設置了另外一個難題,即北部邊疆的安全問題。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案,也與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相關;長城的修建就絕妙地證明了這一點。以氣象學的術語而言,長城這一條屏障,總體上與十五英寸等雨量線一致。這清楚地表明,長城以南年降雨量能達到十五英寸,而十五英寸降雨量是穀物生產所需要的最低雨量。在長城之外,降雨則更為稀少;大部分河流在入海之前即已乾涸;游牧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拉鐵摩爾把長城稱做「世界上最純粹的邊疆之一」,認為它作為區分文化群落、社會風俗、語言、宗教的分界線存在了兩千多年。由於對長城另一側的少數民族的和平同化通常不會有持久的效果,北部邊疆始終是中原農民與游牧部落之間衝突不斷的區域。有時候,中國也會深入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大漠,發起攻擊,但每當它不這麼做時,就只得對機動優勢極強的游牧部落的入侵採取防禦態勢。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被起源於游牧部落的皇室所統治,是很常見的事情。實際上,元代和清代,整個國家都控制在蒙古人和滿洲人之手。此處的情形,跟羅馬帝國極為相似,但最後羅馬乾脆就被「蠻夷化」了,而中國卻從未被「蠻夷化」。無論如何,軍事動員及後勤保障都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再一次證明,穿著制服的官僚所具有的動員力量,是貴族們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這些因素以外,中國人的居住密度、農業種植的普遍性、內陸水網、居民語言的同質性,都有利於統一。這裡也沒有任何建立中央集權制度過程中所不可克服的障礙。但是,與黃河水患的防治、連續不斷的救災以及對邊境游牧民族威脅的控制這些因素不同,中國在人文和社會地理的有利條件幾乎沒有加強統一問題上的迫切感。如果僅僅是這些條件,它們儘管也很可能會發展出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但步伐卻會更慢,當然其基礎可能也會更扎實。歷史的進程和這種情況相距甚遠。人們偶爾也會說,統一和中央集權在青銅時代結束之後很快就誕生於中國。由於生存壓力,統一化進程沒有為地方性制度和習俗做法的成熟留出任何時間。貴族政治的特質也許能培育出地方性制度和習俗做法,而廣泛推行的、注重效率和統一的官僚政治卻不能。道家的技術和放任主義、墨家的科學和宗教、法家的講求統一以及享樂主義者的自我修養,在某種意義上說都因高度必要的中央集權的儒家官僚制國家而受到了傷害。帝制中國的權威之獲得,是傳承自兩種資源:官僚制之前的諸侯國的體制結構、在這些諸侯國發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們尤其是儒家的相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