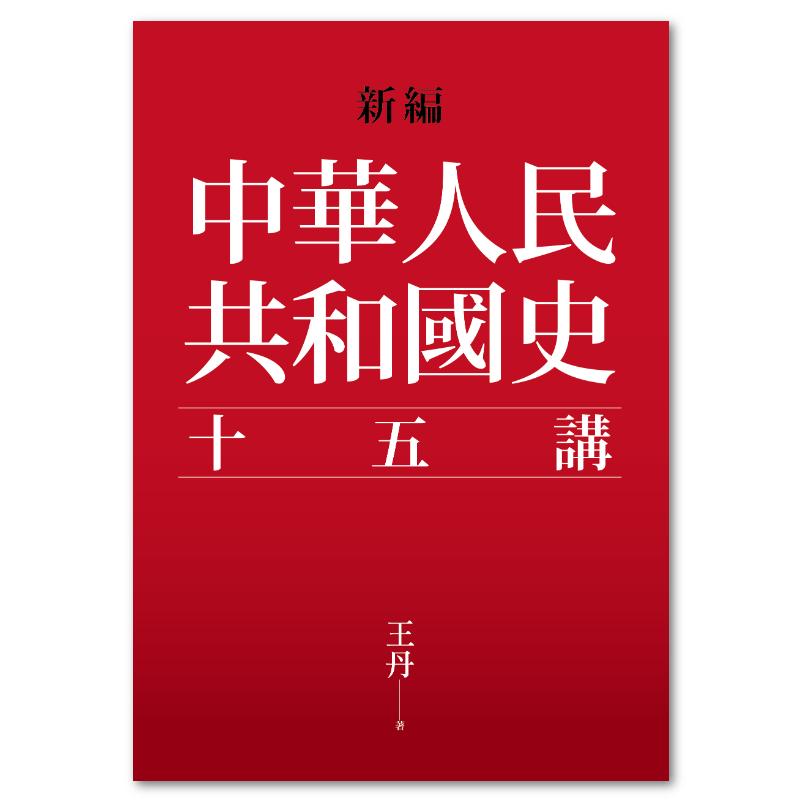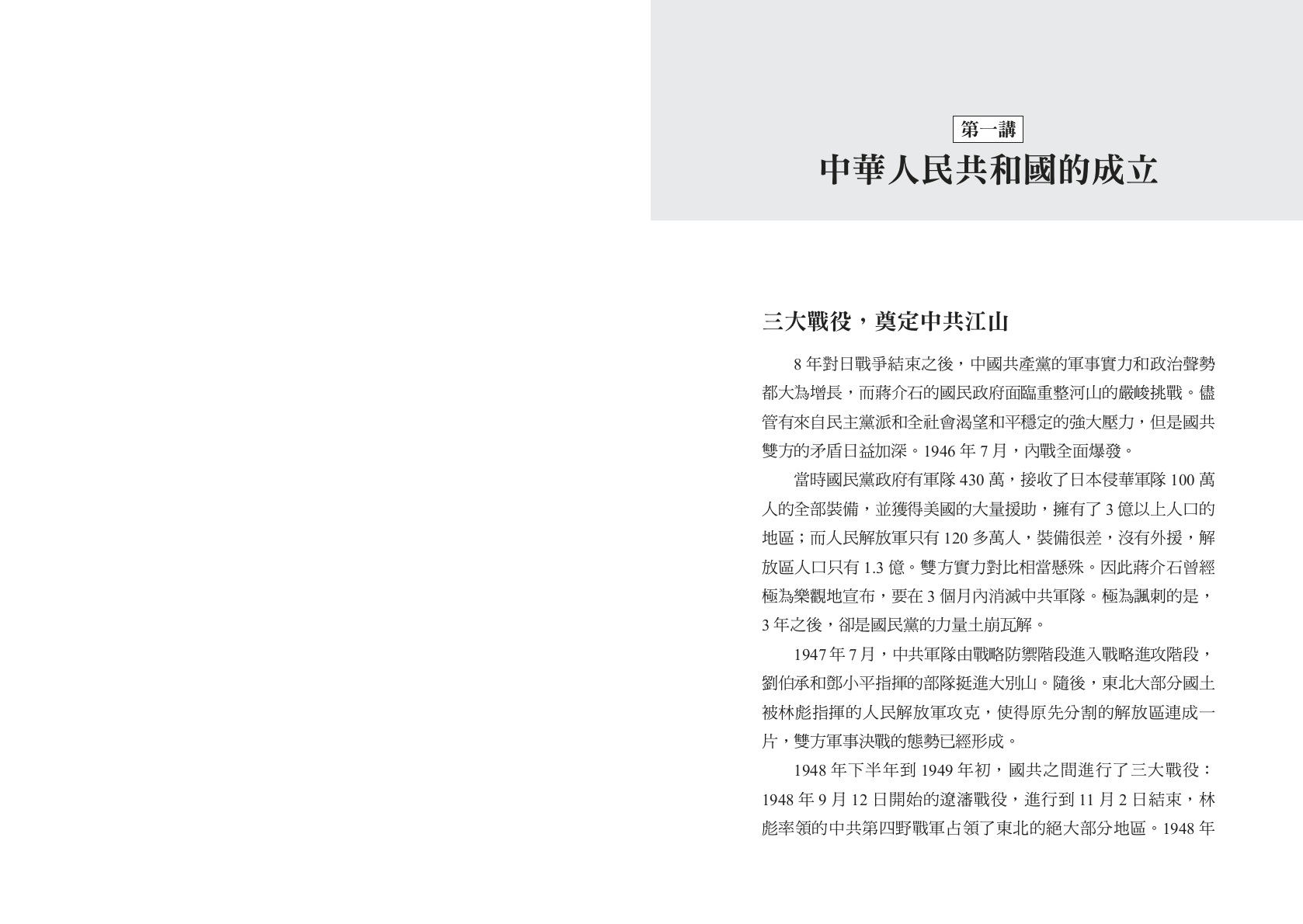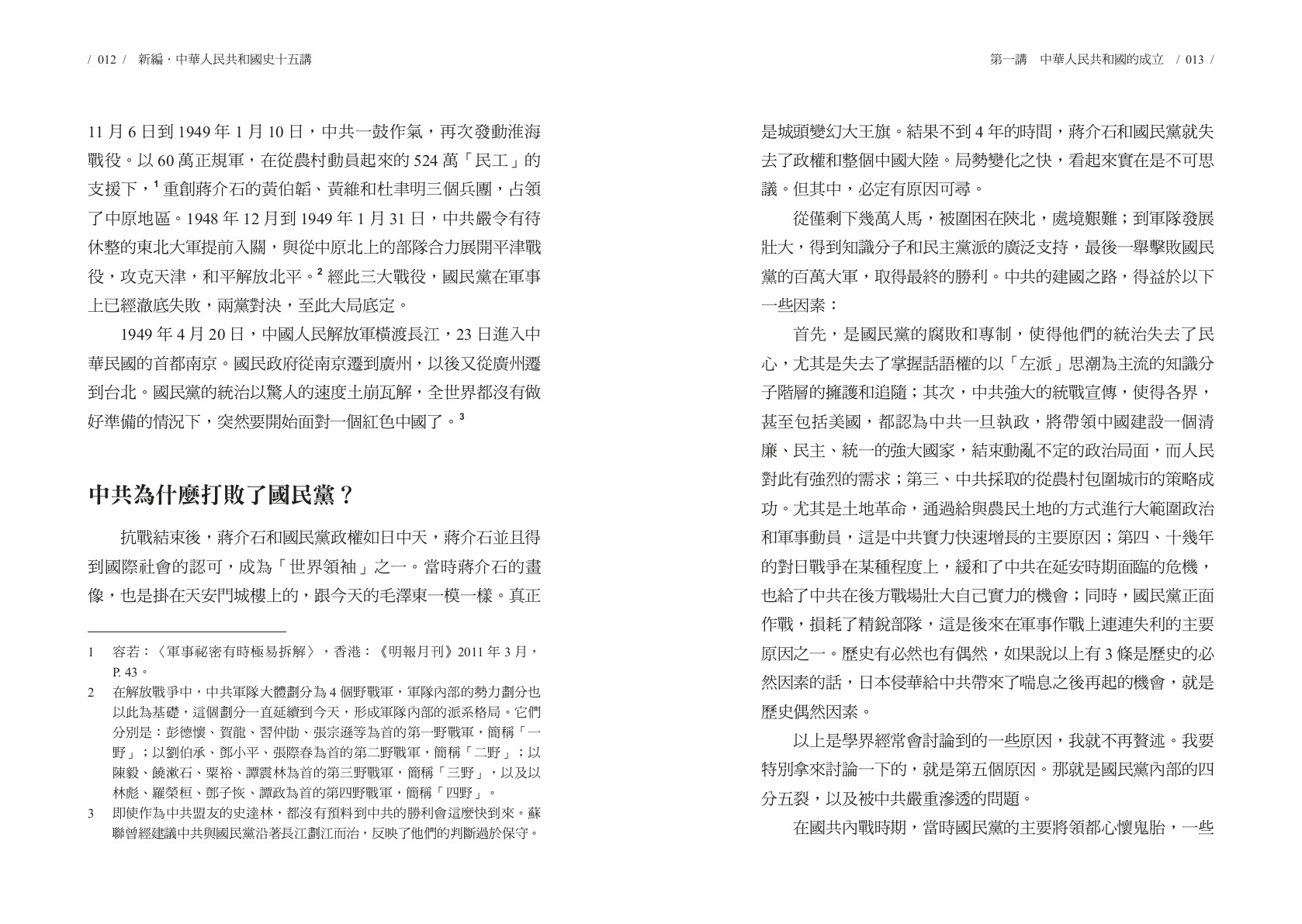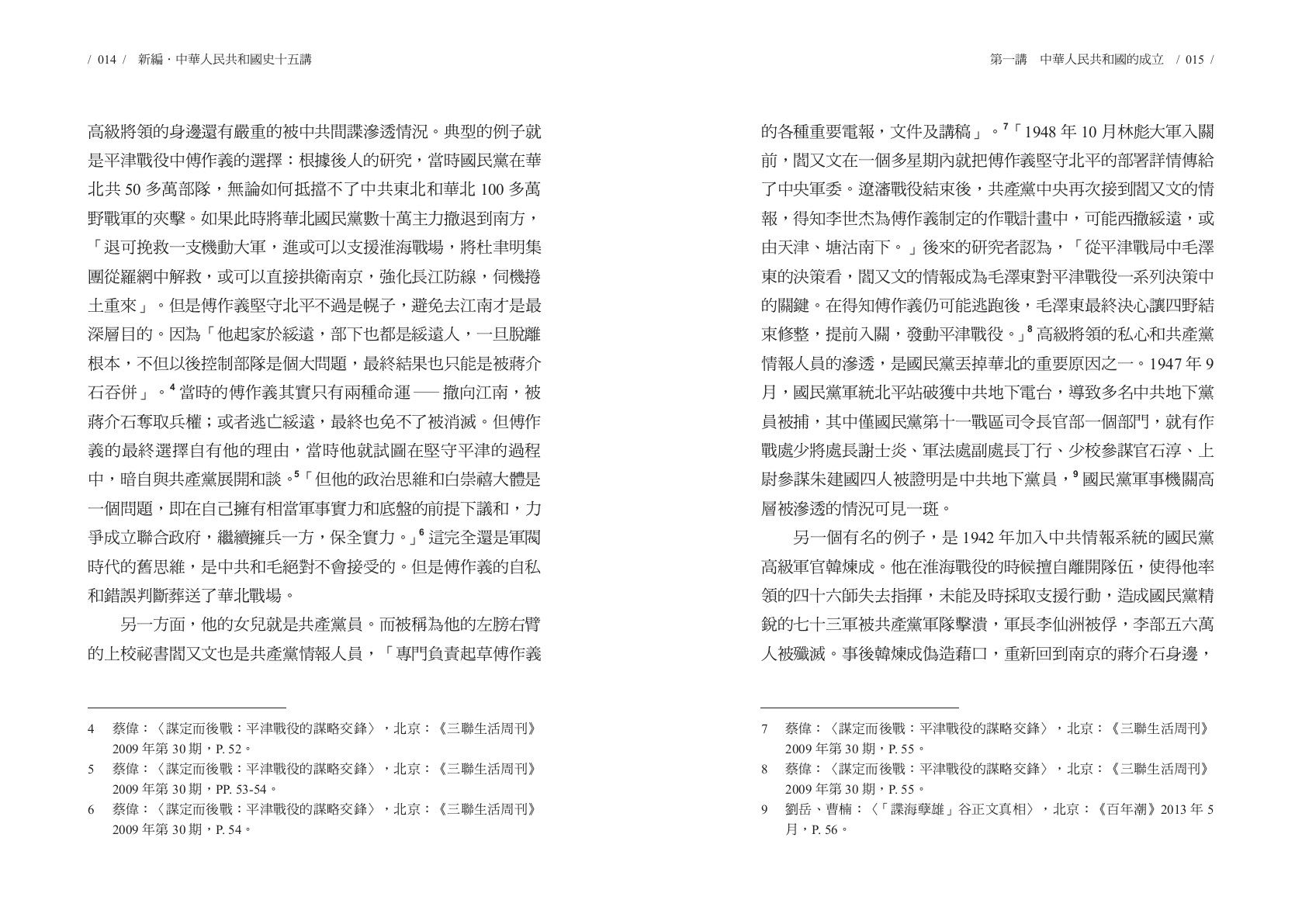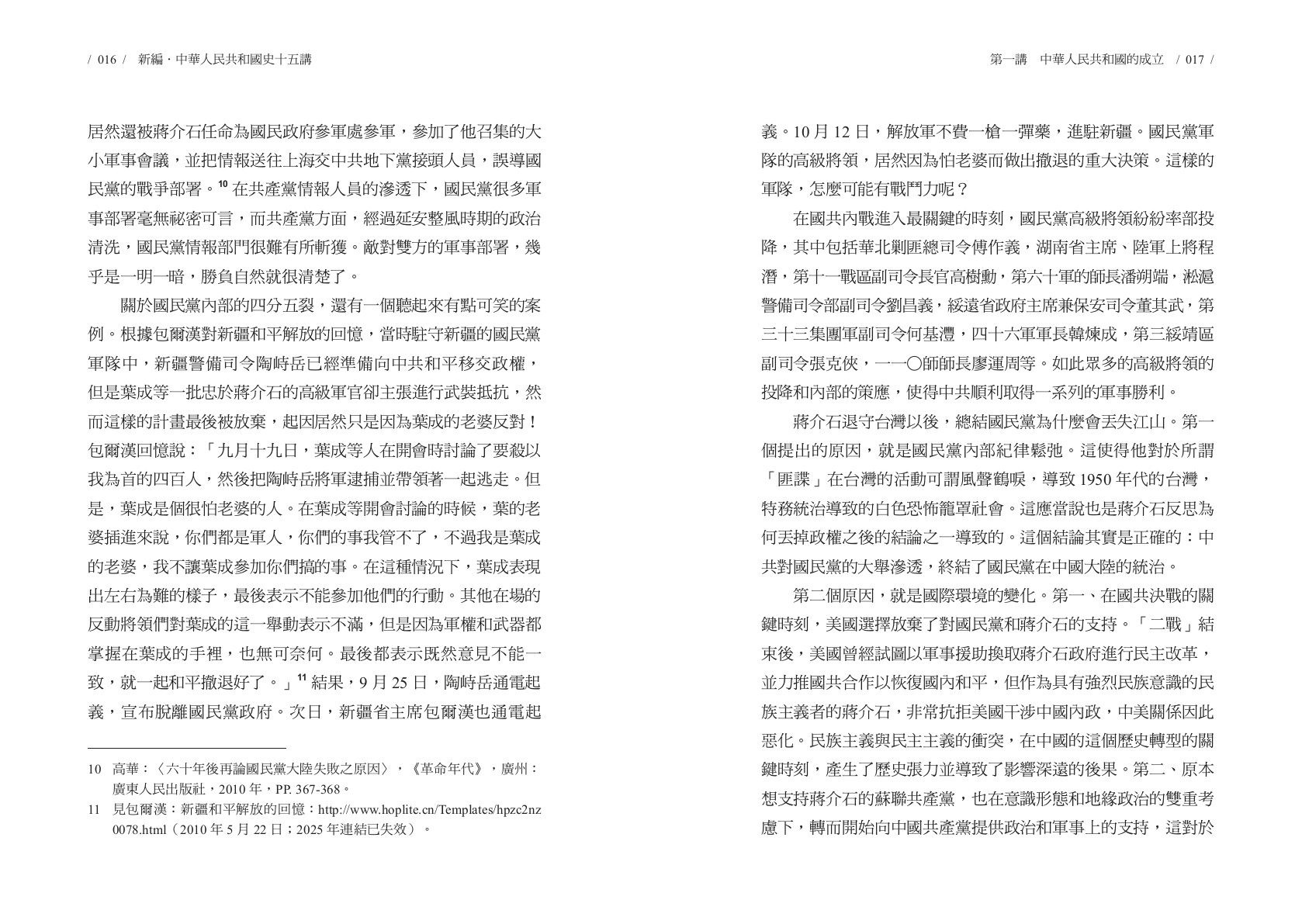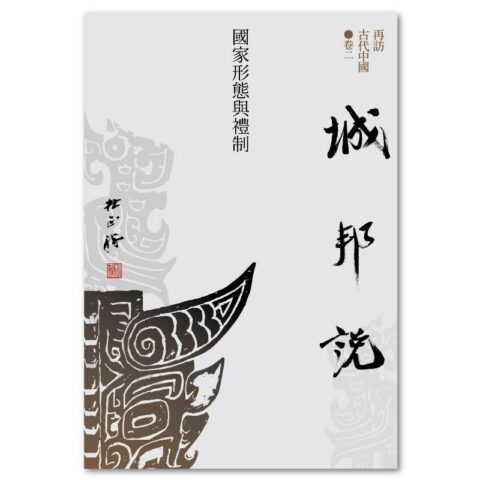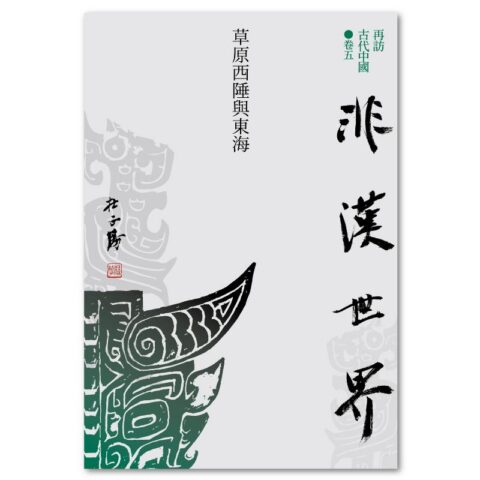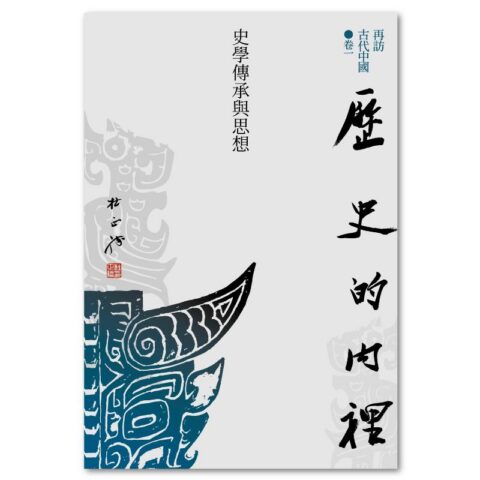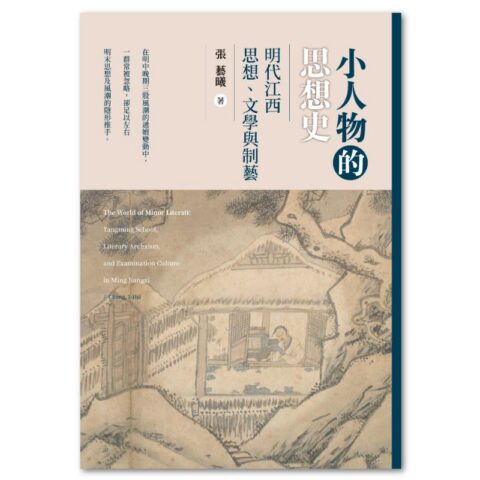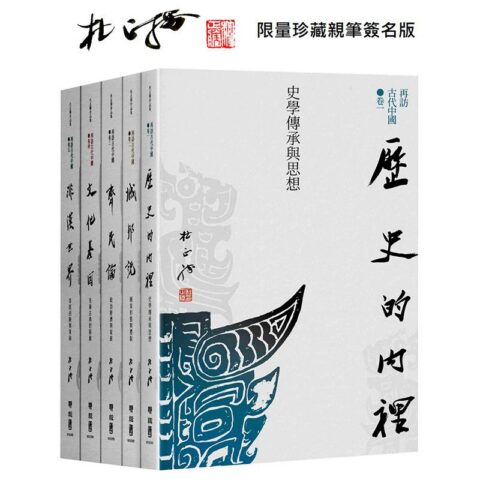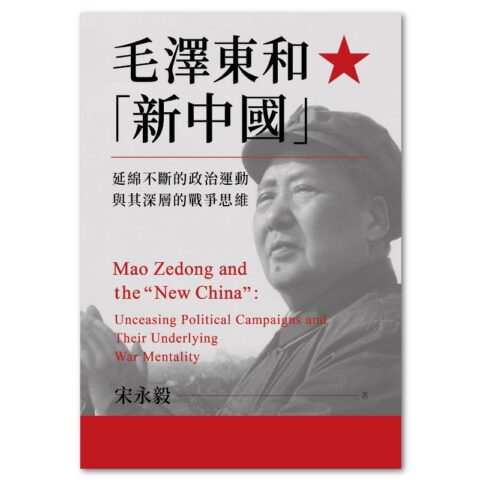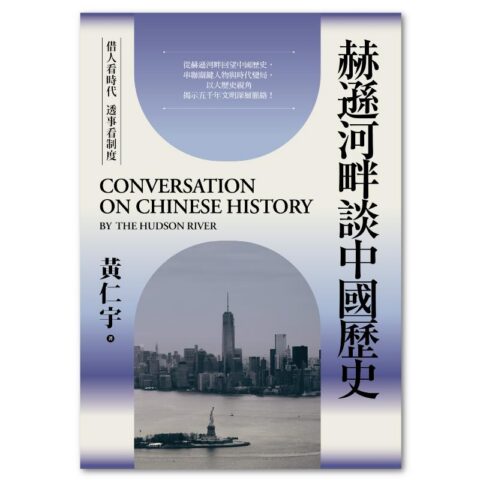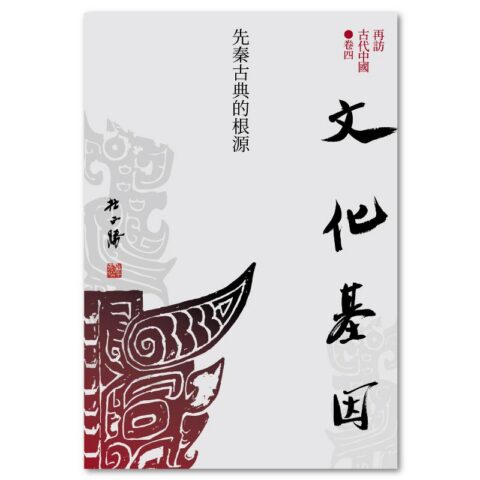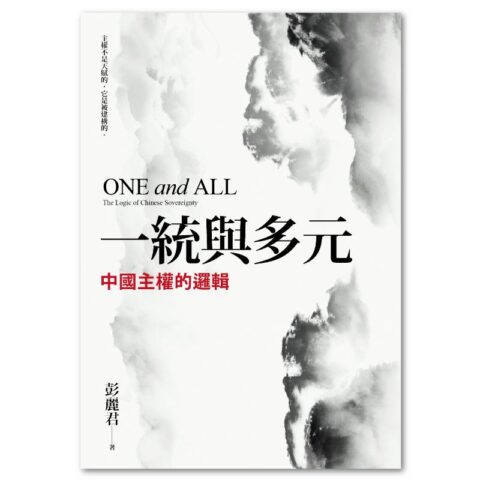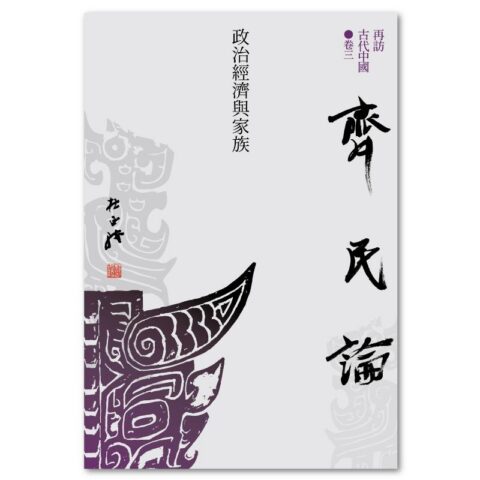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
出版日期:2025-10-09
作者:王丹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20
開數:25開,21長 × 14.8寬 ×高3cm
EAN:9789570878035
尚有庫存
歷史的氣味、喧囂、風雨、煙塵……
看親臨現場者,如何重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太多、太多的事。有些事,成為歷史書上的記載;有些事,只有親臨現場者才知一二;
更有許多事,被掩蓋、被忘卻,遺失在記憶之外。
《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較舊版新增四分之一篇幅,書寫時序推進至晚近,並綜合十餘年來讀者與授課時獲得的反饋,重思歷史,將許多事件與問題說得更為周全、清楚。
本書自八年抗戰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寫起,爬梳國民黨為何敗落、中國共產黨如何鞏固新政權,再寫朝鮮戰爭毛澤東的盤算,敘述打擊城市工商業的「三反」、「五反」運動,和從土地改革到大躍進進而大飢荒的過程,接著是一連串的知識分子、黨內的整肅,也分析當時的中蘇關係、中美關係。書中更寫到「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勾勒出該段歷史更為清晰的側面,也留下中國官方史學中沒有說、不能說,隱去的內容。不只如此,更書寫新時代──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發展,90年代以後起飛的經濟、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最後回顧七十五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風雨蒼黃。
本書精彩分析:
.中共為什麼能夠打敗國民黨奪得天下?
.為什麼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中共政權依然穩定?
.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運動始末。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始末與影響。
.中國知識分子的飄搖風雨。
.鄧小平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四封信。
.從西單民主牆到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的回顧。
.「六四」的爆發原因、過程與相關澄清。
.在天安門廣場的那一夜。
.後八九時代的劉曉波、韓寒到艾未未: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公民社會的成長。
▍本書特色
★十餘年來讀者回饋與課堂積累修訂而成。
★親臨歷史現場者書寫的真實歷史。
作者:王丹
王丹,1969年生,1987年就讀北京大學歷史系,後就讀美國哈佛大學,先後獲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曾在台灣數所大學任教十年,現定居美國。
第一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第二講 軍事:朝鮮戰爭
第三講 城市:「三反五反」運動,消滅工商資產階級
第四講 農村:從「土改」到人民公社
第五講 知識分子:從思想改造、胡風事件到「反右」運動
第六講 黨內清洗:從高崗到彭德懷
第七講 外交:中蘇關係的破裂與中美互動
第八講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開展
第九講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從林彪事件到天安門事件
第十講 鄧小平時代開始
第十一講 80年代的改革開放:從胡耀邦到趙紫陽
第十二講 六四事件
第十三講 後八九時代:經濟成長
第十四講 後八九時代:公民社會的成長
第十五講 75年回顧
附錄一 難忘的一夜
附錄二 《國家的囚徒》(《改革歷程》)說出的祕密──趙紫陽回憶錄讀後感
自序(節錄)
2009年秋季,我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院給學士班的學生開了一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課程。開這門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因為兩岸交流越來越多,但是兩岸彼此之間的了解並不充分,對彼此的歷史的掌握更是匱乏。我認為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環,有必要補足這個方面的缺憾。同時,過去不論是台灣的學生還是大陸來的交換生,對於中國1949年以後的歷史的了解,我覺得是先天不足的。這當然是跟中共方面對很多重大歷史問題進行隱瞞甚至歪曲有關。作為一個老師,我希望學生們能看到更多歷史的真相和不同側面。
然而,如何講這門課,如何讓學生既掌握基本知識,又能從中了解一些與其他同類課程的內容不同的歷史。對我來說,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當時,我希望給學生上一門與眾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個不同,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我希望盡量挖掘與過去主流的論述面目不同的歷史。作為已經發生的事情,歷史本身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由於歷史涵蓋了龐雜紛繁的內容,而我們能處理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同樣的歷史,可以呈現出不同的面向。這正是歷史吸引人的地方。而我們作為教師,只有讓學生盡可能地從最多元的側面去認知周圍的世界,當然也包括歷史,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提高思考能力。
以這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例:75年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很多都遺失在了記憶之外。遠的如「文化大革命」,近的如「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大陸都是禁忌。即使是在海外,因為資料的有限,對大陸的當代歷史的認識也大多是霧裡看花。我希望能盡量多提供一些以前不是那麼為外界所知的事情,為那一段歷史勾勒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側面。或者說,我希望給聽眾和讀者一些中國官方史學中沒有說,或者不能說的內容。
其次,我將盡量讓這段歷史更加人性化,更加個人化,更加生活化,更加具有故事性。我們過去的歷史陳述,有時會被認為枯燥,是因為充斥了太多的時間、事件與原因的分析,甚至數據。即使是對人物的呈現,也是依託在事件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歷史中,我們其實看不到真正的「個人」。我們看到的人,都是某一個種類的人中間的一個,或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但是,那並不是他/她那個個人本身。而我一向認為,具體的個人性的東西,比如個性、心理狀態、身體狀況,甚至是性生活的部分,都在形塑歷史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只是我們過去不屑於處理這個部分,因為被過於忽視了。我們要用近乎「八卦」的方式去挖掘和審視這些個體性的東西,歷史才會鮮活,才會有趣。
舉一個小例子:過去我們認識毛澤東,都是從政治出發,從而確立一個政治強人或者領袖的形象。但是從一些接近他的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另一面的毛澤東:這個明確倡導以「殺人」治理國家,整肅自己的戰友面不改色的暴君,其實對身邊的女人往往無可奈何。晚年在他身邊服侍的張玉鳳,可以對他大喊大叫。長期服侍他的衛士長離開他,他也會不能自已地抱住對方不捨得分手。他晚年最愛讀庾信的〈枯樹賦〉,反覆讀,並能大段背誦。而每每讀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句子便老淚縱橫。這樣複雜的個性和幾乎是淒涼的晚年心境,也許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另外的角度,來理解他做出的影響歷史的政治決策。
那個學期很快就結束了。對於自己的授課是否給學生們帶來很大的收穫,我不得而知,但是期末學生的教師評鑑結果出爐,我的得分在學校教師中名列前茅,還得到清華大學教務長來信感謝。這對於剛剛進入大學教書的我來說算是很大的鼓勵。同時我也認識到,不論是台灣的學生,還是在台灣交流的大陸學生,對於中國過去70多年發生的事情的了解,不僅是相當不夠的,而且是有很大的求知需求。這促使我想到,如果把我授課的講義編排整理出來,加以補充和完善,也許會有一些讀者有興趣。更可以在台灣的環境下,促進對中國當代歷史的了解。
這樣的想法,得到了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先生的鼓勵,這是本書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2011年,本書的前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在台灣出版,很快就銷售破萬冊,證明了外界對於一本不一樣、比較系統完整的中國當代史的需求是存在的。
《十五講》出版至今已經14年了。過去這段時間,我不斷收到讀者來信,除了對本書出版的鼓勵之外,也有不少指正之處,讓我獲益匪淺。同時,在過去的14年中,我本人也對《十五講》的內容做了大量的審視並發現了諸多不足。而這14年來,我仍然持續關注和跟進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積累了不少新的材料。在這些甄別、更正、積累的基礎上,我覺得出於對歷史和讀者的尊重,我有必要對原書進行修訂和增補。因此才有了這本《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在這個修訂版中,我對原有的內容進行了重新審訂,增加了不少於四分之一篇幅的新的材料,讓這部歷史更加接近現實,也更加完整……
八九民運的發展經過
胡耀邦逝世,學潮爆發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於早上7時53分病逝於北京醫院。下午13時30分起,北京大學等校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報,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等。並有對聯針對鄧小平:「小平84健在,耀邦73先死,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70未全,中華40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亦哀。」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600餘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抬著自製花圈,放著哀樂,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這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場遊行行動。事後,約有60餘人到胡耀邦家中慰問。下午3時,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等「民主沙龍」成員,在校內募捐530元買了花圈,組織40餘人送至天安門廣場,並到胡耀邦家悼念。24時起,北大、北師大、北航、政法、清華等北京高校約千名學生從各校出發,匯集並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並在紀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懲辦官倒等內容的「七條」要求。次日上午,與數萬群眾開始在人民大會堂門前靜坐,要求當局接受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從北大研究生會主席任內卸職的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回憶了17日晚上北大學生集會遊行的過程:
4月17日晚飯後,我與其他幾位博士生在我房間裡閒談,突然聽到一陣一陣嘈雜聲。是什麼聲音?原來是來自學生宿舍的敲碗聲。這聲音把我們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號樓前。強烈的敲碗聲夾雜著「遊行去」的喊叫聲,讓人感到震撼。這聲音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是這樣原始的聲音將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在學生們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的時候,突然從二十八樓樓上降下一個巨幅輓聯:「中國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師生敬輓」。幾位學生將這幅輓聯托起並引導學生們繞校園而行。北大的學生們托著輓聯在各個學生樓前轉,目的在號召更多的學生參加遊行。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在這輓聯周圍,跟隨它,走出校園,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門。
4月18日清晨,大會堂前的靜坐結束,轉移到新華門前。7時30分,王丹傳達了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海淀區人大代表李淑嫻「一要堅持,二要把請願書遞交人大常委」的意見。李淑嫻則在北大校園的布告欄上貼出題為「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的大字報,「希望學生去聲援」。上午8點左右,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人邀請王丹、郭海峰等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會面,並接受了請願書,但僅承諾轉達有關負責機構,並未針對學生的訴求具體回應。王丹等人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後向等候的學生和民眾表示: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靜坐行動繼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的官員出來接見。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兩千餘人向新華門聚集,要求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並以「七條」作為請願要求。政法大學周勇軍、北師大吾爾開希等發表演講。
4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辦警衛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單位開會,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布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並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到清晨4點半左右,新華門前的學生被驅散。
4月19日晚上九點,北京大學的王丹等人在校內三角地召集約上千餘名學生參加「第十六期民主沙龍」,討論建立「團結學生會」問題。會上通過了三點決議:(1)拒絕承認現屆學生會、研究生會;(2)成立北大籌委會,由當場集會的同學授權,籌委會負責主持北大同學選舉大家信任的新的學生組織,並負責倡導成立北京市高校統一的學生領導組織或聯絡組織。新學生組織在近期內選舉。在新的學生領導機構成立之前,北大的學生運動由籌委會統一組織,公開領導;(3)中國應當儘快辦起人民自己的、民主的、公正的報紙。北大學生應立即辦起自己相應的報紙,任何政黨、政府、組織及個人不得干涉。第一批籌委會成員包括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焱、封從德和常勁。同時,清華大學數百餘名學生也在校內聚會,然後來到北大與北大學生匯集在圖書館東門廣場,討論學生運動應當如何進行。這一天在上海、西安、合肥等地,均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安徽大學300餘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前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4月21日,北大、人大等校貼出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47名作家和學者連署簽名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提出:「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公開信稱「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
當天晚上8點前後,北京近20所高校四萬餘名學生舉著旗幟、標語,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先後走出校門上街遊行。午夜,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外。此時,廣場約有萬餘名學生,加上圍觀群眾有10萬人。
4月22日上午10時起,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有關當局與廣場上四萬學生的代表達成協議,同意學生留在廣場上參加追悼會。郭海峰、張智勇、周勇軍等3名學生代表穿過士兵封鎖線,走上大會堂的台階,並在台階上下跪交請願書,但始終無人出來接受,學生群情激憤,離開時喊出了「全國罷課」的口號。追悼會後,由21所北京高校代表發起成立「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後來有名的「高自聯」。
這個階段的運動,以「悼念胡耀邦」為主要訴求。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經試圖緩和局勢。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了3點意見:一、追悼會已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阻止,讓他們復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行為要依法懲處。根據時任政治局常委會祕書的鮑彤回憶,「當時常委中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但是,在中共高層中,顯然有人內心是不同意的,他們開始試圖把運動推向激化,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四二六」社論激化了學生情緒
4月23日晚上,原中科院物理系研究生劉剛,召集29所高校的35名代表在圓明園南門開會,討論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確立運動的目標是: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會議中,北大、清華、師大、人大、政法、民族學院以及8個藝術院校的聯合代表被提議當選為常委院校、代表,政法大學為主席院校,周勇軍代表政法大學成為主席。至此,「高自聯」正式成立。
4月25日晚上,新成立的「高自聯」在政法大學開會,有幾十所學校的代表參加。會議開到一半,有人播放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次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即「四二六社論」。社論的調子完全是文革的語言,給學生運動定性為「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並危言聳聽地表示「如果對這場運動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這篇社論,完全把學生放到了政府的對立面。現場立刻群情激憤,各校代表當場討論決定,為了抗議社論,要發起大遊行。
「四二六」社論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關鍵點。在25日以前,整起事件的發展事態,完全沒有失控。在這種情況下,發表這樣一篇措辭極為嚴厲蠻橫的社論,激怒學生的用心十分明顯。這個時候趙紫陽不在國內,主持社論起草和發表工作的是李鵬。這是李鵬故意激怒鄧小平,然後借鄧小平之口炮製這個社論,使得事態發展更加惡化,從而製造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最終的目的,是給趙紫陽出難題,以便拉他下台。「四二六社論」後來成為整個運動的焦點。學生絕食提出的兩個要求之一,就是修改這個社論,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可見這個社論的影響有多大。後來趙紫陽回國,也批評了這個社論的基調,這是鄧小平對趙紫陽開始不滿的關鍵。因為這個社論根據的,就是鄧小平內部的一個講話。李鵬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雕」。據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的會議,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之後,陳一諮對趙說:「若按四二六社論的方針辦,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少倒退十至二十年。」趙紫陽表示同意,回答說:「十年不止,二十年多了。」 這個時候,對於政治局勢的判斷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趙紫陽與鄧小平的立場,已經越來越背道而馳了。
隨後,鄧小平25日的講話開始在各基層單位進行傳達。鄧小平說:「我們不怕罵娘,我們不怕國際輿論。我們不願流血,但我們不怕流血,我們還有三百萬軍隊。」他還提出:「哪怕殺死二十萬人,也要控制住局勢,贏得二十年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