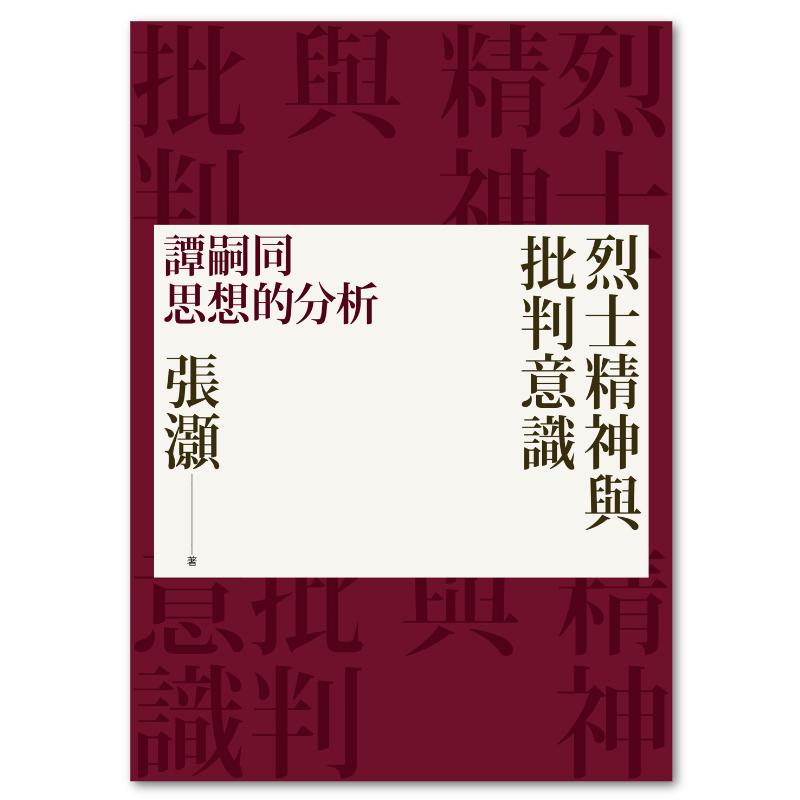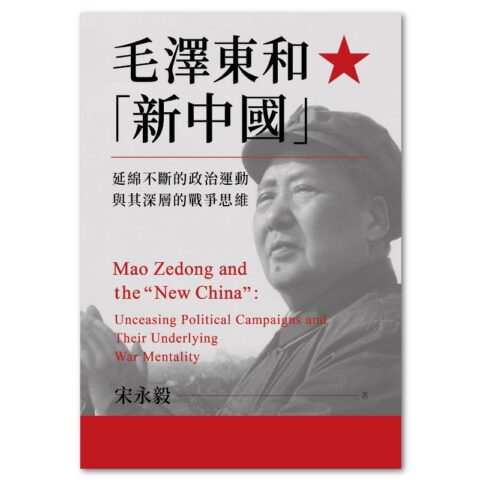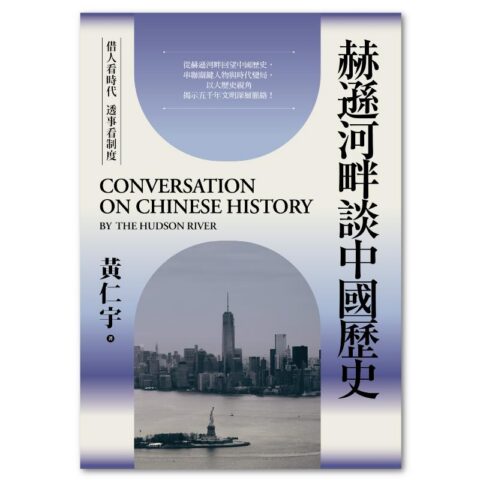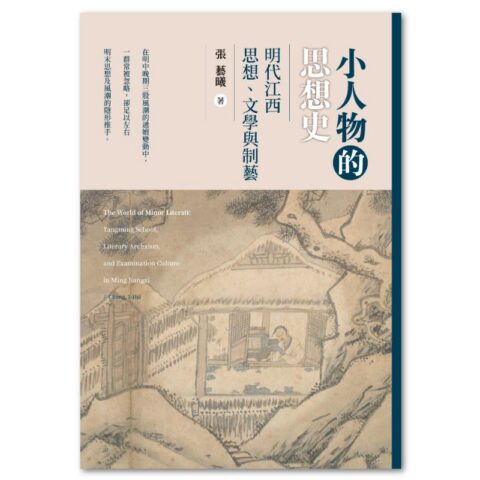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經典重排新版)
出版日期:2026-02-26
作者:張灝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24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2 cm
EAN:9789570879155
系列:聯經評論
一個時代崩塌時,思想該何去何從?
看見譚嗣同燃燒的信念與勇氣,讓百年前的靈魂再次發光
烈士以身殉道,學者以筆重現靈魂
理解譚嗣同、戊戌變法與近代思想危機的關鍵之作
譚嗣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極具象徵性的人物。他尚在而立之年,卻於戊戌政變前後,以生命實踐理想,凝聚「以身殉道」的烈士精神,並以《仁學》挑戰傳統秩序,開啟知識分子自我批判與超越的現代契機。
本書為張灝的重要早期著作,透過嚴謹史學與深刻哲思,細緻剖析譚嗣同的性格、心靈歷程與思想轉折,呈現其如何在宗教情懷、人生困境與時代壓力中,走向仁學的思想高峰,並作出以生命承擔理念的抉擇。
這不僅是一部傳記,更是一場思想探索。張灝將譚嗣同置於十九世紀末「傳統解紐、價值重構」的關鍵時刻,揭示其思想如何映照時代裂縫,並引發對自由、責任與犧牲的深層反思。
本書既是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導讀,也是理解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必讀之作。
作者:張灝
1937—2022,國際重要漢學及思想史研究學家,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博士,曾任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曾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研究獎金、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研究獎金、王安東亞學術研究獎金,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多項榮譽。中文著作主要有《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時代的探索》,均由聯經出版。
前言
一、序論
二、性格、身世與環境
三、心路歷程之一──宗教心靈的湧現
四、心路歷程之二──影響和變化
五、心路歷程之三──由保守到激進
六、譚嗣同的仁學
七、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序論
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卻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他的一生總共只有三十六年,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也不過三、四年的時間,然而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他卻留下了光彩的事蹟、感人的身世和深遠的影響。這一本小書,不是譚嗣同的傳記,而是希望透過他的一生行跡和他的作品,勾畫出他的主要思想發展,他的「心路歷程」。
譚嗣同的心路歷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過他的心路歷程,我們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見一些近代思潮演變的痕跡。
稱之為「心路歷程」,不是隨便的譬喻,因為我在這裡所謂的思想,不僅是指觀念層次上的意識,同時也是指情感層次上的意識;它包括內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綜合內心生活的各面,我們才能看到譚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靈世界。
大約而言,思想史有兩種,一種是觀念發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這種思想史的著眼點是觀念的歷史發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觀念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從而分析這些觀念間的衍生與邏輯關係,探討這些觀念與其他觀念之間所產生的緊張性和激盪性。西方史家魯佛覺(Arthur Lovejoy)的《存在的鏈鎖》(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和萊根(Anders Nygren)論「愛」這一觀念在西方傳統裡的演變(Agape and Eros)都是這一類思想史的典範之作。這種思想史用來處理哲學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有其特殊的價值,但是作者在這本書裡不擬採取這種方法,因為譚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離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沒有什麼重要的價值。因此,我所採取的是另一種治思想史的途徑,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時代脈絡裡去看,看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覺的反應。只有這樣來處理,譚嗣同的思想的歷史意義才能彰顯。
譚嗣同生長的時代是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發揮影響的時期也正是中國文化在近代進入一個轉型的時代(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在這轉型過程中,譚嗣同的思想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當時的思想界作一個定位並非易事。首先,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他幾乎都未曾直接參與。當時辯論激烈的今古文之爭,譚嗣同並未真正捲入。梁啟超與康有為本人都強調譚嗣同受康有為之今文學的影響。事實上,康梁的這種強調都嫌誇大。譚嗣同受康有為之影響甚晚,直至死前的兩三年他才與康有為的思想有所接觸,而其時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態已大致形成。故當時康有為的今文學雖然在譚嗣同的思想裡留下一些痕跡,這些痕跡卻與他的基本思想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論戰——革命與改革之爭,譚嗣同也未介入。這固然是由於這個論戰主要爆發在譚嗣同戊戌死難之後,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雖參加康梁變法,他的思想實兼有當時所了解的革命與改革兩種成分,假若他未死於戊戌之難,他後來的思想演變究竟屬於改革型還是革命型,實在很難說。
以當時思想界的重大論爭去給譚嗣同「定位」固然不易,以今天史學家對中國近代思想的一些流行的觀念去了解他的心態也頗有隔靴搔癢之虞。「民族主義」這個常用的觀念就是一個例子。不錯,民族主義之變為近代中國的一個主要思潮,是始於清季轉型時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思想雖含有一些國家觀念與種族意識,這些觀念和意識對他的中心思想卻影響不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稱譚嗣同思想為「世界主義」,實在是有所見而發的。
除「民族主義」之外,中外學者有時以「現代化」這個觀念去分析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趨勢,但所謂「現代化」是現代學者所用之範疇,是否可以適用於清季知識分子的思想也很成問題。大致而言,「現代化」這一觀念有廣狹二義:就其狹義而言,「現代化」與一般所謂的「經濟發展」不分。就其廣義而言,則指社會學家以韋伯(Max Weber)的「功效理性」為基礎而建立的「理性化」這一發展過程。重要的是,不論是狹義或廣義,「現代化」都不是以「道德取向」為主的概念,而譚嗣同的思想卻含有極濃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在詮釋譚嗣同的思想時,我們很難乞助於「現代化」這一範疇。
此外,已故美國學者李文孫(Joseph Levenson)在其所著《中國儒家文化與其命運》一書中,曾特別強調「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這一觀念,並以此去分析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心態。李文孫此處所謂之「文化認同」乃指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衝擊與震盪之下,由挫折感與屈辱感所產生的文化自卑心理。李文孫認為,由於這種自卑感的作祟,中國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往往有美化傳統的心理需要。從這個觀點去看,譚嗣同早年思想容或含有這種心理因素。但其晚年成熟之思想則難以用此種心理解釋去概括。由上面的分析可見:現代史家所習用的一些觀點與範疇,我們都不能藉以窺譚嗣同思想的全豹。
因此,今天我們要了解譚嗣同之思想特色,必須跳出既有的一些觀點的窠臼。我們必須認識,譚嗣同一生,因為興趣和活動極為廣泛,思想難免相當駁雜,但是我們若仔細分析他一生的著作和行跡,亦不難發現他的思想有其脈絡可循,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透露一種特殊的心態,這種心態充分反映在他一生中最有影響的兩件大事:戊戌死難時他所表現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難前兩年所寫的一本書——《仁學》,要了解這種心態和產生這種心態的思想背景,我們必須先對他個人的性格、身世和環境作一番分析。
性格、身世與環境
譚嗣同從小就展現出他的性格中最大特色:豐富的情感與豪邁的氣質。這種「浪漫型」的性格,在他早年生命的兩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第一是他的詩詞。譚嗣同從少年時就開始寫詩詞,許多作品極富感性,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才華。例如他在十五歲時為送別他的仲兄赴甘肅省父,寫了一首七絕:
一曲陽關意外聲,青楓浦口送兄行。
頻將雙淚溪邊灑,流到長江載遠征。
碧山深處小橋東,兄自西馳我未同。
羨煞洞庭連漢水,布帆斜掛落花風。
瀟瀟連夜雨聲多,一曲驪駒喚奈何。
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渡關河。
鷓鴣聲裡路迢迢,匹馬春風過灞橋,
灞上垂楊牽客思,也應回首故鄉遙。
春煙澹澹黯離愁,雨後山光冷似秋,
楚樹邊雲四千里,夢魂飛不到秦州。
譚嗣同的感情不但發為濃厚的手足之愛,而且也時而表現為強烈的社會同情心和正義感。他在旅行時,偶爾見到一些悲慘的或者不平的事件,便會觸發他的情感,反映在他的詩篇裡。例如,他在二十四歲出外旅行時,曾寫下〈兒纜船並敘〉這樣一篇詩章:
友人泛舟衡陽,遇風,舟瀕覆。船上兒甫十齡,曳舟入港,風引舟退,連 曳兒仆,兒啼號不釋纜,卒曳入港,兒兩掌骨見焉。北風蓬蓬,大浪雷吼,小兒曳纜逆風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兒手。纜倒曳兒兒屢仆,持纜愈力纜縻肉,兒肉附纜去,兒掌惟見骨。掌見骨,兒莫哭,兒掌有白骨,江心無白骨。
同年,他又寫了下列兩首小詩:
〈罌粟米囊謠〉
罌無粟,囊無米,室如縣磬飢欲死,飢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療飢,罌粟栽千里,非米非粟,蒼生病矣。
〈六盤山轉餉謠〉
馬足蹩,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嗔官!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
短短的幾行,淡淡的幾句,這些小詩卻道盡了他對社會大眾的關懷和同情!
至於他性格中豪邁超逸的一面,譚嗣同在他十八歲時,為自題小照所寫的一首〈望海潮〉詞裡,曾有清楚的流露: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纔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因人,形還向影,豈緣酒後顏酡;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
「詩如其人」這句話,就譚嗣同而言,是再恰當不過了,譚嗣同在這首詞中自稱「有幾根俠骨」,而他的一生行跡也確實常常顯出俠氣縱橫。這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突出面,據梁啟超說,譚嗣同年輕時「好任俠,善劍術」,當他父親在甘肅服官時,他常常出入西北邊塞,騎馬射箭,奔逐馳騁。這種任俠的傾向,正如同他豐富的感情,是他性格中與生俱來的,對於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
要了解譚嗣同的思想,他的主觀性格和稟賦固然重要,客觀環境也同樣不容忽視。與許多人一樣,譚嗣同的思想大部分來自他對所處環境所作的回應。所謂環境是指三個因素。首先是他的社會背景,特別是他的家世。這個因素對他的影響至少有三方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因此受到極良好的傳統教育。父親的游宦,加上他本人南北奔走應試,使他有許多旅行遊覽的機會。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一文中,對自己的旅行之廣,特別引以為傲,他曾計算他的旅行「合數都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這些旅行自然增廣了他的交遊與見識,開闊了他的眼界,例如他在二十六歲時,曾隨他的父親赴湖北巡撫任所——武昌。武昌也是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駐節所在,張的幕府中人才濟濟,如汪康年、繆荃蓀、徐建寅與黃紹箕等,都是當時有學問、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譚嗣同在武昌有機會與他們結識來往,對他的眼界和學識自然極有增益。
譚嗣同的家世不但給他一個良好的學識環境,也給他帶來很多問題和困擾,對他的精神產生相當的刺激。他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官僚,有妻有妾。譚嗣同是嫡出,但母親死得很早,在家裡很受庶母的歧視,和父親的感情也有隔閡。譚嗣同後來在其《仁學.自敘》裡曾提及他的家庭:「吾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瀕死累矣。」可見家庭給他帶來的痛苦。
要了解環境如何影響了譚嗣同的思想,我們不能只注意他的家世背景,我們也得注意他一生中的各種處境,所謂「處境」是指個人生命過程中所自覺其重要性的一些事實或情況,就了解譚嗣同這種知識分子的思想而言,有兩種處境特別值得重視,一種是所謂「生命的處境」。這種處境是指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情況和遭遇,例如死亡、戀愛、疾病、衰老和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逆境和重大變遷。
另一種可稱之為「歷史的處境」。這種處境是指國家社會所經歷的重大變遷。譚嗣同生長於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十年,正是中國文化思想開始鉅變的時代。外力的震盪已由文化的邊緣漸漸波及文化的中心。這種鉅變,大約而言,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傳統宇宙觀的動搖。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傳統儒家的宇宙觀,因為它是當時一般士大夫主要信仰之所在。這種儒家宇宙觀的核心當然是「天人之際」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天人之際的思想在傳統儒家是由一些形而上學概念如陰陽、氣化、五行、四時、天、道、性、命等構成的8。對於這些觀念和天人之際的思想來說,十九世紀末葉輸入的西學,特別是當時的科學宇宙觀和基督教創世觀,當然都是一種挑戰,一八九五年左右,四川的一位士大夫——宋育仁寫了一本書叫《采風記》,就把這種挑戰說得很清楚:「其(指西學)用心尤在破中國祖先之言,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為無物,地與諸星同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兩大陰陽,無分貴賤,日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擬於不倫,上祀誣而無理,六經皆虛言,聖人為妄作。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下,從發源處決去天尊地卑,則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權,婦不統於夫,子不制於父,族性無別,人倫無處立根,舉憲天法地,順陰陽,陳五行諸大義,一掃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稟秀五行,其降曰命,人與天息息相通,天垂象見吉凶,儆人改過遷善,故談天之學,以推天象,知人事為考驗,以畏天命修人事為根本,以陰陽消長,五行勝建皇極,敬五事為作用,如彼學所云,則一部《周易》全無是處,洪範五行,春秋災異,皆成瞽說,中國所謂聖人者,亦無知妄人耳,學術日微,為異端所劫,學者以耳為心,視為無關要義,從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為操器,可不重思之乎?」
宋育仁的這段話透露了一個重要的消息:西學和西教的流入不僅威脅著傳統的宇宙觀,而且因為傳統的宇宙觀與價值觀是互相依存,無法分開的,對傳統宇宙觀的挑戰也就是對傳統價值觀的挑戰,我們由此看到十九世紀末葉思想變遷的另一面:中國傳統價值秩序開始解紐。要了解這種解紐形勢的出現,在考慮西方科技與西教的輸入之外,我們尚需注意帝國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所造成的刺激。在這種刺激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八六○到一九○○年這段時間裡漸漸認識到:中國之受外強欺壓不僅是因為科技的落後,而且也因為制度的不臧。一八九○年代,特別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以後,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已開始覺察到:對於傳統制度的批判,不能只限於枝葉,必須深入到它的根本。而因為傳統制度的基礎是建築在以三綱思想為中心的價值觀上,對於傳統制度的批判終於演為對傳統政治和社會價值中心觀念的懷疑和挑戰。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傳統的帝制思想。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眼裡,帝制不但無法應付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危機,而且也失去了道德的威信。總之,不論從現實的功效角度或者道德價值的角度,帝制均不足以充當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問題很自然地浮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裡:傳統秩序的思想基礎既然動搖,如何重建一個新的秩序?這也就是「群」這個問題為何在甲午以後變成當時知識分子所關心的焦點。
傳統宇宙觀和價值秩序的動搖,象徵著近代中國思想危機的序幕。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歷史處境的重要特徵,以譚嗣同的稟賦、學識和眼界,他當然要比當時一般的知識分子對這種歷史處境來得更為敏感。因此,歷史處境和譚嗣同個人的生命處境一樣,是影響譚嗣同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上面我簡略地討論了家世背景和處境對譚嗣同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但是影響譚嗣同思想的環境尚有另一面,那就是他所處的時代的思潮與學風。
譚嗣同出身士大夫階層,是當時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自然對他的時代的思潮與學風有強烈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因素一方面可以像社會背景一樣造成一種文化氛圍,使人浸沉於其中,受其潛移默化。另一方面,它們的影響往往是透過對處境的自覺而造成的,一個人面對各種生命和歷史的處境,自然發生問題,產生困惑和焦慮,從而希望能在他的時代的思想和學術潮流中尋求解答。
前面說過,譚嗣同一生遊歷極廣,思想接觸面極大。因此,要了解他所受的思想影響,我們需要對晚清的思想界作一全面的鳥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