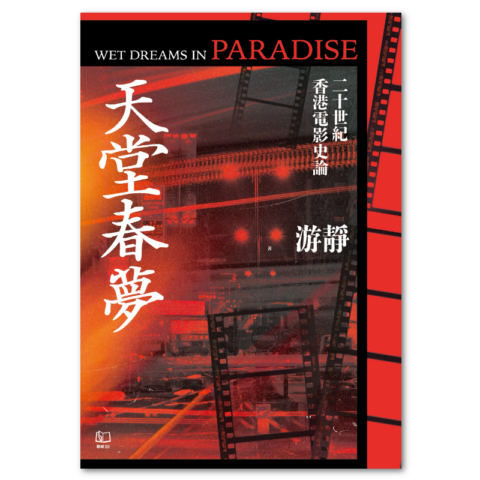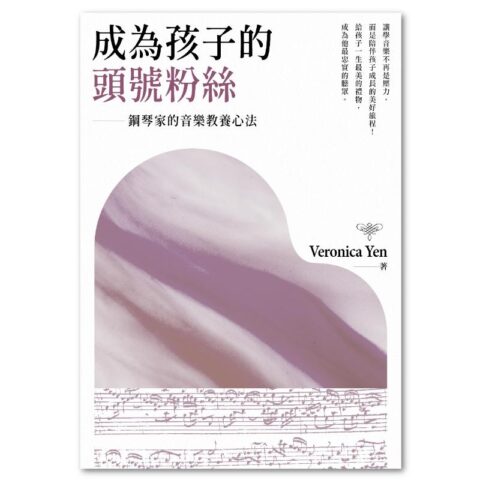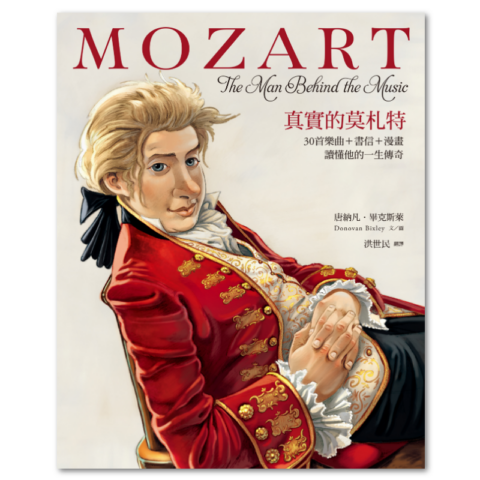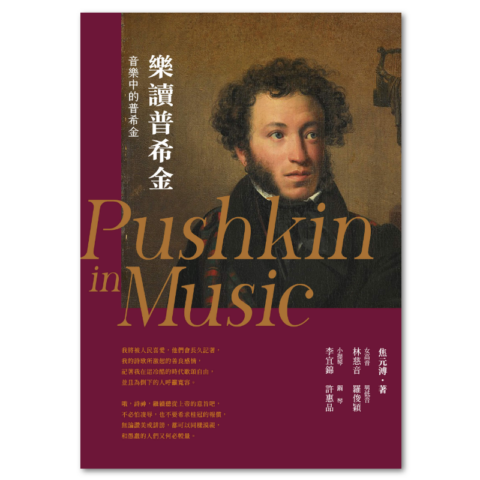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
出版日期:2018-04-26
作者:許維賢
頁數:392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50987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本書入圍2019年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國際圖書獎決審名單
從蔡明亮、雅斯敏、阿牛、陳翠梅、劉城達、黃明志到廖克發
探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的崛起
以及處於離散與反離散間距中的不即不離
電影研究一直比較偏重以從敘事、影像或美學等幾個層面進行文本和理論分析,華語電影中的土腔、語言等聲音元素,卻少有研究觸及。《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探討一批在馬來西亞出生成長的電影導演在後馬來西亞語境下如何在國內外催生一組揉合土腔風格、華夷風或作者論的華語電影。結合近年在全球興起的土腔電影和華語語系,此書探討當代馬來西亞土腔電影文化中的華語、方言和多語現象,這些交織著各種土腔、多元聲音和多元拼字的揉雜化語言景觀,如何在離散和反離散的邊界內外進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同時,也在全球化的大都會主義和本土第三世界後殖民的雙重語境下,操演諸種涉及本土、國族、文化、階級和性╱別的身分認同?這些離散電影和反離散電影又是如何在後馬來西亞語境下運用華夷風的聲音和土腔去回應或超克「國家失敗」的預兆?
作者許維賢指出,無論是從蔡明亮到廖克發不時重返馬來西亞歷史現場的離散電影,抑或從阿牛到黃明志對離散去疆界化的土腔電影,再回到本土雅斯敏、陳翠梅和劉城達對國族叩問的反離散電影,馬華的離散論述不盡然是反本土化的書寫;馬華的反離散論述也不必然就是對國家仰慕和充滿願景的國族主義。
《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同時收錄作者走訪多位導演和歐洲影展選片人的第一手資料,對華語電影在馬來西亞內外的生產、消費和傳播進行田野調查,從而更深入理解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的崛起。
※名家推薦
許維賢教授的新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本書資料詳實、理論嚴謹、視野開闊,極大地幫助人們了解在南洋乃至全球範圍內的華語、華人、和華語電影這些當今學術界的關鍵問題。
──魯曉鵬╱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文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本書的最大貢獻,是以歷史的材料與東南亞的視角,回應並補充華語語系此一顯學的研究。馬來西亞新銳電影導演的作品,應當得到更大的關注。
──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本書將華語語系文化與電影的論述,推進到大馬與新加坡的史前史。聚集了中文、英文、馬來文等豐富的在地資料,本書跨出了主流華語語系論述被限制在北美與大中華圈內的視角。
──林建國╱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本書不但從跨國、跨族、跨語言、跨文化和跨類型的角度鉅細靡遺敘述華語語系電影製作在馬來西亞電影歷史上的存在,並以新穎的理論和關鍵術語來探討和闡明馬來西亞電影多方面在美學與社會評論提出的尖銳議題,以及這些電影跟其他後殖民電影在主題上的共振回響。作者展示個別不同的電影作者如何創意性地跟國家保持不即不離的間距,以「後馬來西亞」的概念對馬來西亞電影提出極其重要的質詢,從而富有成效地質疑國屬分類的使用。
──Brian Bernards╱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與比較文學系副教授
作者:許維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專任副教授,執教華語電影、性別研究與華語語系文學和文化等課程,並獲得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最佳教師獎。傅爾布萊特研究基金得主兼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訪問學者和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訪問學者。其他學術著作有Remapping the Sinophon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hinese-Language Cinema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ld War和《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與Brian Bergen-Aurand, Mary Mazzilli 合編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Corporeality, Desire and the Ethics of Failure。與柯思仁合編Memorandum: A Sinophone Singaporean Short Story Reader。在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ultural Critique,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Queer Sinophone Cultures ,《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文化研究》、《藝術學研究》、《中外文學》、《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當代電影》和日本《野火》等書刊發表論文。
名家推薦
圖片說明
導論
一、有關「華語」與「華語電影」的兩種說法
二、「華語」與「華語電影」在新馬的原初記憶和歷史
三、華語語系論述:1.0、2.0和3.0版本
四、華夷風的邊界:冷戰與身分認同的再造
五、土腔電影:作者論、馬華電影與後馬來西亞
六、研究目的和章節概述
第一章 在鏡像中現身:重探蔡明亮電影的作者論和肉身化
一、肉身化與作者論的共盟
二、庶民的肉身:早期作品、《黑眼圈》與後馬來西亞
三、在鏡像中現身:小康與蔡明亮的「影像迷戀」
四、作者論:同志和直男攜手共盟的美麗暗櫃?
第二章 鏡外之域:論雅斯敏電影的國族寓言、華夷風和跨性別
一、雅斯敏與「一個馬來西亞」
二、華夷風與鏡外之域的跨性別
三、作者論:從羅曼史到國族寓言
四、酷讀《木星》和《單眼皮》的跨性別
五、鏡外之域與書信體:作為幽靈的阿龍
六、「一個馬來西亞」作為「國家失敗」的隱喻
第三章 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與《初戀紅豆冰》
一、離散華人、反本土化與反離散
二、原住民神話、巫族與土著特權
三、邊界想像、主奴結構與離散有其終時
四、《初戀紅豆冰》:土腔電影與土腔風格
五、離散的去疆界化
第四章 反離散的在地實踐:以陳翠梅和劉城達的大荒電影為中心
一、大荒電影:土腔電影模式
二、哀悼馬共和再現底層:大荒電影的階級面向
三、劉城達:華巫關係的越界
四、陳翠梅:反離散與後馬來西亞
五、華語語系作為電影書信的連結
第五章 土腔風格:以黃明志的饒舌歌和土腔電影為例
一、華夷風:反離散的饒舌歌與土腔電影
二、《辣死你媽!2.0》的土腔風格
三、土腔口音:出境和入境
結語 不即不離
附錄:導演和選片人訪談
「你必須相信電影有一個作者」:在鹿特丹訪問蔡明亮
放映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巴黎和鹿特丹與選片人的一席談
新浪潮?與馬來西亞獨立電影工作者的對話
大荒電影的故事:兼側寫幾位大荒導演
無夏之年,老家沉進海底:走訪陳翠梅導演
引用文獻
本書各章發表出處
導演和選片人訪談發表出處
致謝
索引
導論(節錄)
本書採納魯曉鵬在〈華語電影研究的四種範式〉的說法:「華語語系電影這一術語基本上是能與華語電影互換使用的」。正如魯曉鵬也已指出,「華語語系電影指涉了與華語電影所指相同的區域和範圍」,兩者之間的不同僅在於華語語系電影「對諸如離散、身分構成、殖民主義和後殖民性等問題保持了特殊的敏感性」。誠哉斯言,「華語語系電影」只是「華語電影」四種範式中的其中一種而已,兩者之間在本書的從屬關係也接近如此。
華語語系電影被理解為那些在中國大陸以外的離散華人社群以及在中國境內生產的多元語言、多元方言和多元土腔的電影。這些多語元素是多種華語和外語、方言和土腔(accent)的交織和共響,形成華語語系電影的混語化(creolized)語言景觀。這是語言學和人類學意義上的「語言馬賽克」(linguistic mosaic)現象,它是全球化進程下的「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現象,尤其發生在語言生態非常多元的亞洲。語言學家估計至少有一千五百種語言在亞洲被言說,從語言的譜系來看,至少有六大語系共存於亞洲社會中。語言馬賽克指涉主體語言的詞彙或詞組夾雜著少許客體語言的詞彙或詞組,形成一種多語並用、混成一體的特殊口語。馬華電影正體現了大馬社會的語言馬賽克現象。馬華電影從文本延伸到導演多元的語言能力,均展現這些多語並用的元素。因此馬華電影在本書可以是「馬來西亞華語語系電影」或「馬來西亞華語電影」的簡稱,它包含由大馬導演以華語方言拍攝的獨立電影和商業電影。張錦忠近年著書《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持見認為「馬華文學」後可以是「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的另一簡稱,而不一定是過去「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的簡稱而已。這賦予馬華文學新的意涵,讓馬華文學擺脫其族裔文學範疇,進入多語和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ed)的生產空間。馬華電影更可以作如此觀。本書把馬來裔導演雅斯敏也納入華夷風的視野就是要讓馬華電影擺脫其族裔電影範疇,進入多語和去疆界化的生產空間。雅斯敏那些跨語際的電影大量再現華語和方言,為日後的大馬各族導演樹立了去疆界化的華夷風典範,其影響不可小覷。大馬語境的土腔正是包含了華夷風,華夷風是大馬土腔中的本土再現之一。
根據彭麗君〈馬華電影新浪潮〉的描述,馬華電影近年「造就了洶湧的馬國新浪潮,攻占了全球主要的電影節,贏了掌聲也摘了獎項」。馬華導演至今在國際影展的得獎影片,以大馬華語和方言的多元土腔作為主要媒介語,再夾雜英語、馬來語等外語。其多元土腔再現了大馬現實中南腔北調的華語和方言,構成了馬華電影的多元口音特色。「土腔」被界定為在區域上或社會裡能辨識一個人從哪裡來的發音特質,因而所形成的聽覺效果,說話人著重使用的某個詞彙或音節在言說流程中顯得突兀。不同的土腔有不同的社會成因,這除了涉及到發言者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在發音上的互相滲透,也通常包含其他同等的社會成因,例如社會和階級出身、宗教背景、教育程度和政治分類。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所有土腔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但是所有土腔在社會屬性和政治層面上,卻往往沒有在價值上得到平等對待。人們不但傾向於從發言者的土腔,評估其社會地位,也從中評估其人格。依賴於土腔的評估,一些人在口音上很可能被看成是土包子、下流的或醜陋的,而其他不同口音的人卻被看成具有教育水準、上層階級和美麗的。這不幸導致土腔成為其中一種最能分辨身分認同組別和其一致性的強大標籤工具,甚至也包含個人差異和其人格的評估。
第一章 在鏡像中現身:重探蔡明亮電影的作者論和肉身化
三、在鏡像中現身:小康與蔡明亮的「影像迷戀」
身體在蔡的創作裡,不只是單純的表面,它「變成了一個發展虛構、幻念、欲望的場域。」他的電影鏡頭時常觸摸到人類身體極其複雜的性欲望。其中經常令人爭議的是裡面重複浮現的同性戀元素。其實早期蔡的文學創作也不乏這些元素,劇作《房間裡的衣櫃》最為明顯。當年蔡自編自導自演這部劇作,他沒有否認他在演繹自己,他說:「創作本來就是很自私的,我其實是為自己而做。」這些告白都直截了當承認了這部劇作的私密性。這種私密性是往後蔡電影走向肉身化的基礎。
《房間裡的衣櫃》生動地展現了一個藝術工作者在工作、理想和情欲之間的受挫和困惑。表面上,這只是一部一人自導自演的獨幕劇,可見的僅有男主人公一人和他房間裡的衣櫃。不過此作高度熟練地藉主人公和外部聲音的互動,把整部劇作提升到眾聲喧譁的氛圍,裡邊的動作和聲音,互為交織融合在一起,在敘事邏輯上層層相扣,顯得非常緊密。例如主人公頻頻打電話的聲音、電視主持人主持節目的聲音、女人在牆外和主人公對話的聲音、主人公和衣櫃無形人對話的聲音。這些各種各樣的聲音,在同一個時空內,互為因果,都跟主人公發生互動的邏輯關係,它們讓主人公的動作、情緒和表情都產生豐富又有趣的變化。整部看似主人公在一個封閉的空間──房間自言自語的劇作,卻讓我們看到了華人酷兒既熱鬧又孤獨的生存困境。房間裡的那架衣櫃更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它是主人公內心世界的一個暗櫃,裡邊藏著的那位衣櫃無形人,他是主人公「本我」(id)的一個隱喻,他不斷通過干擾主人公的起居生活,引發了主人公對他的注意和對話。
一開始引發主人公和衣櫃無形人對話的是一個巧克力鐵盒,裡邊裝著男主人公過去寫給男友的情書碎片。這些情書被主人公撕碎了,當第一幕男友突然來電說他決定要結婚,痛苦不堪的主人公在掛下電話後「蹲在浴室門口,撕信,撕了一地,一會,又愕愕地將信撿起,塞進巧克力鐵盒,扔進塑膠衣櫃裡。」這一切動作除了細緻展示了男主人公對男友的眷戀,也微妙表明了主人公在經歷感情打擊後,只能更隱蔽地把自己的同性戀傾向藏在暗櫃裡。
這個巧克力鐵盒巧妙地帶出了衣櫃無形人在房子裡的存而不現。衣櫃無形人顯然不滿意男主人公如此隱藏自己的性傾向,他開始在房間裡抗議和搗蛋:無故熄了房間裡的吊燈、在衣櫃裡自動亮起燈等等。這些動作把整部劇帶入一種既超現實又恐怖的黑色幽默裡。孤單無助的主人公從開始的害怕,到漸漸跟衣櫃無形人的對話,整個進程其實是男主人公在真實面對自己的過程。這位衣櫃無形人在受到主人公冷漠對待的時候,他會把衣櫃裡全部的東西,包括那個裝信的巧克力盒給扔了出來。如果主人公待他好一點,他不但會在深夜裡偷偷幫主人蓋被,還會走出來陪主人公坐在一起創作和對戲。當最後主人公終於排除艱難,把自己搞劇場的理想付諸於實現,他既興奮又滿懷感觸地回來,把一朵玫瑰插在衣櫃的拉鍊上,衣櫃在最後的劇幕裡悄悄地飛了起來。衣櫃的飛起,這象徵著蔡企圖對同性戀困境的一種超脫姿態。無法確定是這個衣櫃載著蔡起飛,還是蔡背負著這個衣櫃飛起?但肯定的是,作為酷兒的主人公,並無法拋棄暗櫃,也沒有從暗櫃裡至此現身。
小康的出現,讓蔡的創作,可以把《房間裡的衣櫃》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衣櫃無形人,漸漸賦予形體化。根據小康的敘述,1990年有一天,蔡在臺灣大學對面的大世紀影院看完電影出來,看到小康坐在電動玩具店外面的機車上,即走上前問小康,要不要當演員?小康當場嚇了一跳,因為他覺得此人長得不像導演。蔡事後追憶,當時覺得小康像一個外表看起來很乖但實質上不乖的「壞小孩」。有些像以前的自己。當年小康是在一間非法的電動玩具店打雜工,當時他的工作是坐在電動玩具店外面的機車上把風,一有嫌疑的員警出現,即打手機電話通知電動玩具店的老闆,電動玩具店會迅速關門休業。小康當年自身處於底層的邊沿身分,正好也符合蔡電視單元劇《小孩》裡那位向小學生勒索的高中生。小康隨後成功通過試鏡,扮演這個未成年的高中生。在此片裡,臺灣女演員陸奕靜開始扮演小康的母親,小康之家的雛形已顯露端倪。蔡開始通過《小孩》的螢幕鏡像,以小孩形象作為起點,把小康作為蔡自身的自我扮演,這是他倆鏡像關係的開始。
《小孩》片中小康向一名小學生勒索。小康勒索來的錢也是要交給幕後的主腦,換言之,他本人也被勒索。在劇中,施予暴力和承受暴力的主體,並不是二元對立的「正」與「邪」、「好」與「壞」。蔡沒有草率地為邊緣少年套上僵固的刻板形象。雖然小康表面上是個問題少年,但他卻是身邊朋友眼中共赴患難的摯友,母親眼中少不更事的孩子。他和小學生在一起的時候分別扮演壓迫者和受害者的關係,但雙方回到家裡卻同樣要面對受到父母忽略的孤獨處境。蔡與小康聯手合作初試啼聲,即對異性戀傳統家庭的意義展開反思:「所有孩子都可能在家庭結構裡淪為一個表面自主但內心無依的孤獨個體。」
小康則是這個孤獨個體的代表。他逃離這個異性戀傳統家庭的方式,就是不斷終日從一個街頭場景,遊走到另一個街頭場景。在《青少年哪吒》裡,小康在後半部戲裡,在西門町從頭到尾跟蹤著直男阿澤,連夜沒有回家。有一幕,小康發現阿澤和一個女孩在旅館做愛,他莫名憤怒地把阿澤的機車給砸了。這個暴力動作設置,可作為之前同樣拍西門町市景的《海角天涯》中,美雪砸毀男同學機車的內在互文性,那是作者導演的欲望暴力重複機制的再現,它讓觀眾看到小康砸毀阿澤機車,不純粹是為了報復阿澤砸破了小康父親的汽車,還夾雜小康對阿澤帶女孩上旅館開房的醋意,總歸來說是小康對阿澤的窮追不捨和莫名的愛恨交織。這背後牽制著他的都是一股對阿澤莫明的曖昧欲望。小康對阿澤的同性情愫,在《愛情萬歲》裡才得以公開展示。
在《愛情萬歲》裡,小康終於在床上偷吻同性屋友阿澤,幫他洗衣服,一起吃火鍋,說穿了就是要和對方一起生活,這似乎和待售公寓女仲介一進房間就跟阿澤上床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姚一葦在分析這部電影時寫道:「所謂『愛情萬歲』裡的『愛情』,並不是存在於男女之間,而是男同性之間。」顯然在蔡的視界裡,兩個同性之間的愛情不僅僅是性,他們也有渴望一起生活的願望,但眼前的事實是小康只能偷住在一間待售的公寓裡,現實的社會並沒有合法提供空間,讓酷兒生存下來。酷兒只能躲在暗櫃裡。
蔡的電影至今,雖然不時再現同性戀行為,然而沒有一個主角,包括小康,認同於自身的酷兒/同志身分,也不曾在影片敘鏡中公開現身,而且片中這些酷兒對直男特別鍾愛。片中的小康把自身的性傾向隱藏在暗櫃裡,就像《房間裡的衣櫃》的衣櫃無形人。《房間裡的衣櫃》的男主人公和衣櫃無形人,後來在蔡電影裡,發展成蔡(導演)和小康(角色)「共生共存」的一種鏡像關係。蔡通過影片機制,賦予衣櫃無形人一個形體:他在現實裡由一位名叫小康的男生飾演,讓衣櫃無形人從衣櫃走進銀幕鏡像裡,而蔡自己卻在更多時候退居幕後,走進暗櫃工作。換言之,蔡只能通過虛構的電影機制,投射了作者(auteur)的同性戀欲望,虛構的電影機制打造了蔡最安全的暗櫃。在這個由鏡像組織而成的電影機制裡,蔡通過攝影機凝視鏡像裡的小康,蔡的自我表現得到展現了,但作為酷兒的事實卻隱身在暗櫃裡。蔡的主體繼續保持緘默,沒有自己的語言,一如鏡像裡的小康。小康一直是蔡的自我投射,這個自我(ego)依舊固置在想像的鏡像階段裡,拒絕過渡到語言的階段,因此作為主體的酷兒一直無法在蔡影片敘鏡中建立起來,更遑論現身。
或者需要追問,為什麼很多華人酷兒像《房間裡的衣櫃》的主人公那樣,非但無法拋棄暗櫃,反而只能通過藝術的虛構形式,對同性戀議題進行自我展現的同時,卻無法把酷兒主體給建立起來。到底藝術的虛構形式,是鞏固了華人酷兒現實生活中那個真實的暗櫃?抑或保護了酷兒在現實生活中免受直接歧視的困境?
在華人社會裡,對同性愛者的無形壓迫,一如西方女同性戀面對的困境,是「通過一種不可想像、不可命名的生產範疇來進行的」。這種無法命名的生產範疇在華人文化裡是以家庭倫理為中心,然後再延伸成無邊無界的社會人際網路。這個拒絕把同性戀者給予命名的華人家庭倫理文化,構成了華人酷兒暗櫃的基礎。同性愛自古以來在中國社會多半並沒有受到法律明文公開的禁止,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中華文化對同性愛的寬容,而是因為在歷史長河裡,同性戀經常無法進入華人家庭倫理文化中,成為一種可以被想像和被真誠描述的次文化資源。
鑑於自古以來人們以各種各樣的侮辱和詛咒來解釋同性愛的存在,一開始就假定了這些邊緣族群在法律和倫理上並沒有一種承認的需要。每一代的同性戀者都要被迫重複面臨自我認同的危機。自我認同在這裡主要是指涉一個人對於他是誰,以及對於他欲望行為的特徵理解。無論是一個異性戀者或者同性戀者,他們的自我認同,有極大部分是需要人們的承認才足以構成,反過來說,倘若得不到人們的承認,或者只是得到人們扭曲的承認,肯定會對他們的自我認同造成扭曲、傷害和影響。
換言之,華人酷兒的自我認同根源,往往不是直接來自現實中人們的承認,而是往往產生於酷兒藝術的閱讀或創作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過度依賴作為鏡像的藝術媒介,才能表現自己的酷兒欲望。因此導致這樣的自我表現和自我認同,一開始就是一個誤認的結果,酷兒的主體也因而無法建立或現身。
有些同志/酷兒運動家強烈批評蔡總是通過電影鏡頭,從側面或者反面的角度,例如總以生病的身體、陰暗的三溫暖、骯髒的廁所等把酷兒帶到觀眾的面前,例如香港同志鬥士兼藝術家林奕華在1997 年,就曾在影評裡質疑蔡電影《河流》的同性戀元素:「同性戀,真有必要麼?還是只為貪一點偏鋒的風頭?」他也在影評提到幾位美國同志影展的主腦看了《河流》,也認為這不是一個關於同性戀的電影,因為《河流》沒有替同志發聲,爭取正面的曝光。這些批評否定了蔡電影對華人同志平權運動的正面意義。
蔡則炮轟由林奕華主催的臺灣金馬獎影展同志/酷兒電影專題,連續幾年「把它搞成流行甚至某種情調,我認為有點譁眾取寵。」蔡認為「同性戀不應被歸類及自我異化」,因此他一直很抗拒自己的電影被貼上「同志電影」的標籤,每次回答問題,他都有言在先:「這不是一部同志電影。」這些言論也惹惱了林奕華和幾位同志影展的主腦。
雙方的孰是孰非,攸關同志在現實和影像上的「現身」議題。港臺同志平權運動的話語基本上可被分類成三派,「現身派」、「中間派」和「隱身派」。「現身派」認為同志有必要「現身」,因為他們認為同性戀的暗櫃處境並不是異性戀壓迫的附帶結果,而是構成異性戀壓迫的重要機制。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林奕華和臺灣的林賢修。中間派則認為同志一定要掌握現身的自主權:要不要現身/現身到什麼程度/要不要冒險,都該由同志自己決定。這一派傾向於認為只要一個國家還沒立法保護性傾向的機會平等,每個華人同志在特定場合所謂的現身,總是不同程度的、特定人群前或特定人際關係中的現身。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不少是非常友善和關懷同志群體的異性戀者,例如臺大學者張小虹等人,他們主辦同志的「十大夢中情人票選」和「彩虹情人週」,呼籲同志夾雜在那些支持同志運動的異性戀群體中,集體現身,在媒體面前造勢。那些公開代表同志請願的同志代表們,也被鼓勵集體戴上面具(mask),以抗議媒體對他們的獵奇。
「隱身派」由香港學者周華山等人為代表,他們並不低估或否定現身的意義,只是質疑英美同志運動的現身模式和策略。這一派認為英美主流同志主導的現身政治,是一種對抗式的身分政治,不適用於華人社會以家庭為本,強調和諧、安定和團結的人際關係網路。這一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同性性事只是默言寬容,而非公開接納。」華人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極少像英美同性戀那樣普遍遭受到宗教和國家法律的迫害和處決,因此把英美同志的現身政治,強制移植到華人社會,這是一種「最血腥的情欲殖民主義」,這只會讓華人同志被驅逐於華人家庭倫理文化所延伸的社會人際網路,讓華人同志最終孤立,徹底失去自身的文化身分,甚至連工作和居住的空間都受到牽累。
朱偉誠認為1990年代臺灣同志運動至今,基本上是卡在同志有否必要「現身」的議題上,停滯不前。臺灣1990年代整個同志運動的歷程,基本上是一種發生在主流媒體上的運動。有所改變的,主要是同志在主流視界中的認知形象以及文化位置,但是大多數的臺灣同志仍然在現實生活中不敢太過公開地現身。蔡在媒體一談及同志議題,就會強調自己不想被貼標籤,同性戀者不需要把「同性戀」寫在額頭上,並解釋說他本身有他的困惑、羞恥、包袱、顧慮和社會壓力,但承認會把自己內在的壓抑情感,揭露在自己的電影裡。在某種程度上蔡的言行,讓他看起來更傾向於介於「隱身派」和「中間派」之間。
蔡電影裡的同志頻頻出現在「性貧民區」(sexual ghetto),例如《河流》的同性戀三溫暖和《你那邊幾點》的男廁,似乎只有在這些「性貧民區」,同志之間才能產生互動。這構成了當代「現身派」和「隱身派」所爭論的焦點。在「現身派」看來,這些再現只會加劇社會大眾對同志的刻板印象,把更多同志推向暗櫃裡,最終無助於同志人權的爭取。但「隱身派」卻認為不能強求每個同志都具備正面的同志形象,即使異性戀者都有他們「墮落」和「悲觀消沉」的一面,為何卻不容許某些同志再現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現實處境?從「現身派」的立場來看,所有同志都有義務獻身於同志平權運動,這恰好是「隱身派」所抗拒承擔的不可能任務。
英美同志平權運動的主流話語,主張同性戀者必須現身。現身有不少好處,包括它可以讓同性戀者避免孤單、尋求更多支持、解決社會逼婚的問題,以及改變社會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以便建立起同性戀的角色模範。況且,修訂現代法律條文的國家決策者,在法律條文可實施性的修訂考量上,需要同志在身分認同上的點算和確認,法律條文不可能把平等尊嚴的公民權利,給予一大群寧願選擇隱身在衣櫃裡,拒絕被點算和確認的同志。
美國非洲裔學者安東尼.阿皮亞(Anthony Appiah)則認為,這世界並不是只有一種同性戀者或純粹屬於一種黑人的行為舉止,而是存在著無數種黑人和同性愛者的行為模式。可是同志平權運動宣導的「承認的政治」,卻經常處在一種敵我分明以及自我窄化的困境裡,它迫使各自的群體認同為了迫切得到政治性的承認,紛紛走向一種定型化的訴求裡──只有一種膚色和只有一種性別身體,這導致那些要傾向於自我面向的性別身體和不同膚色的個人都面臨了自我實踐的困難。他認為在目前西方的多元文化社會,女人、同性愛者和黑人等一直以來並沒有獲得平等尊嚴的對待。身為一名黑人同性戀者,如果硬要他在暗櫃的封閉世界和解放的同性戀者世界裡做一個抉擇,他雖然還是會選擇後者,不過他更希望他可以不需要做任何選擇,或者應該還有其他選擇。他認為僅僅停留於同性愛者的現身權利是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到與異性戀者享有平等尊嚴的權利。
亞洲華人的同志平權運動,由於主要受到歐美同志平權運動的影響,有一部分的激進同志會主張現身,然而更多的華人同志無法現身,因為一旦現身,首先必須面對以父權體制為中心的家庭倫理政治的高壓,其次才是承受國家體制與社會大眾對同志的集體歧視。換言之,家庭倫理往往構成了華人同志現身的第一大難關,很多同志跨不出去。華人的家庭倫理文化講究折中與和諧,這是受到儒家中庸教義的體現,它的特徵是不走激進路線。魯迅曾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來開窗了。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這番話,雖然不是針對同性戀而言,但或許可以為華人同志的現身議題,提供反思的基礎。換言之,華人同志的激進主義,例如現身,在口號的策略上有其合理性。然而這個口號在多大程度上能化為同志的實際生活行動,實際上首先還很可能有賴於各別同志如何克服自身的家庭倫理政治。
在一項訪談中,蔡表示他難以接受華人在儒家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套家庭至上的價值觀:「在這種尊敬父親、家庭至上的觀念為前提之下,結婚便成了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義務。我想,在我的影片裡,我對這樣的價值觀提出了非常多的質疑。」蔡是如何通過影片對華人家庭倫理提出質疑呢?通過一個不斷漏水的小康之家,蔡只是沉默和象徵性地把片中的那個小康之家的屋頂給拆卸下來,通過影片嘗試重造一座酷兒之家。《河流》就作了其中一次的示範。
《河流》的小康,在臨時飾演一具漂在淡水河上的浮屍後,在街上遇見了女同學,然後跟她去旅館做愛,之後脖子得了怪病,歪向一邊,劇痛無比。這種劇痛遍尋藥方皆無效,最後在小康站在陽臺上抬頭望天的電影最後一幕,彷彿宣告了它已經得到紓解。我們不太清楚紓解的原因是不是昨夜父子倆意外在同性戀三溫暖現身的結果:父親當時摑了小康一巴掌,意外地把小康的脖子給扭正了過來?還是之前父親在三溫暖從背後緊抱著小康愛撫呻吟,猶如「聖母慟子圖」的一幕,讓小康的疼痛得以消除?我們只在影幕上看到正當父子在黑暗中進行著一切,母親獨守空閨的家在不停漏水,似乎這是一個沒有屋頂的小康之家,顯然這個家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中。有些學者認為蔡藉這一幕父子在三溫暖做愛的場景,牽動了儒家文化最深層的絕嗣恐懼,也直接「侵犯了『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正確性」。張小虹認為《河流》意外為我們的文化象徵語言提供了一個文化影像的想像可能,不再都是佛洛伊德論述下的「父」場景:「這一次他與父親狹路相逢,他沒有殺了他,他只是和他做了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