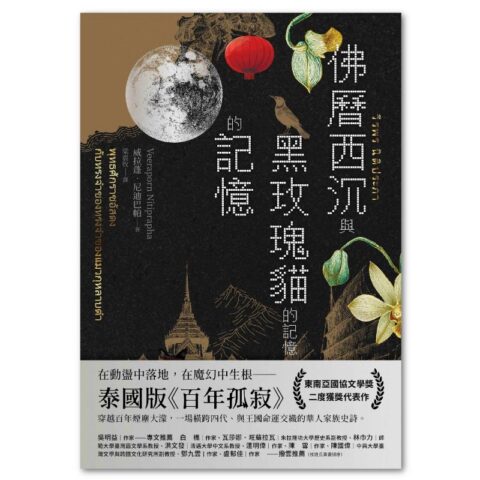慾望莊園(重溫優雅愛慾和古典頹廢經典小說,英倫唯美電影/獲獎電視劇之原著神作)
原書名:Brideshead Revisited
出版日期:2020-09-17
作者:伊夫林‧沃
譯者:李斯毅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64
開數:25開,高21×寬14.8×高3cm
EAN:9789570855982
系列:不朽Classic
尚有庫存
絕美的莊園,消逝的純真
成功、情愛、名利……你想要什麼樣的人生?
與二十世紀的頹廢優雅再次相遇
從經典文學探問何謂生命的自由
二十世紀百大小說|作家生涯代表作|影集電影經典原作
英國現代主義,一流敘事大師──伊夫林‧沃,生涯暢銷代表作
英國八○年代膾炙人口、迷你影集《故園風雨後》(夢斷白莊)、
《珍愛來臨》導演茱利安.賈洛執導之電影《慾望莊園》暢銷原著小說
踏入慾望莊園,窺探二戰前夕英國名流貴族的上層生活。
擁有權勢、財富、美貌的人們,徘徊在慾望與信仰之間,失去快樂。
難道唯有信仰才能獲救贖?選擇不信才能得到自由?
原文書名《慾望莊園:查爾斯.萊德上尉的敬神與瀆神回憶錄》,從副題即能知悉,這是有關主角查爾斯‧萊德回望人生前半段的懺情錄。描述一戰後的英國貴族、天主教、牛津大學校園、異性/同性情愛等議題,出版後旋即成為作者最暢銷代表作,也因電視劇/電影改編而廣為人知、迴響不斷,名列經典文學小說。
故事背景設定在一戰後、二戰前這二十年間。男主角查爾斯.萊德和賽巴斯提安.佛萊在牛津大學相識。出身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的查爾斯,個性拘謹卻嚮往隨性自由的生活;賽巴斯提安則出身於傳統英國貴族世家,天性浪漫不畏世俗禮教。兩人相交,為喜愛藝術、欲成為畫家的查爾斯打開了一扇通往上流社會的門扉,使他得以造訪布萊茲赫德莊園,進而認識賽巴斯提安的親友,包括其母親佛萊夫人和妹妹茱莉亞等人。朝夕相處中,查爾斯漸漸發現自己為賽巴斯提安所吸引,兩人之間的關係日漸升溫而變得微妙曖昧。但這樣的相處,讓保守的佛萊夫人表示不再歡迎查爾斯的來訪,兩人也斷了聯繫。
多年後,查爾斯如願成為了成功的畫家,結婚育有兩子的他,仍對年少時在布萊茲赫德莊園的記憶有所憧憬,在一趟旅途中遇見了正與丈夫分居的茱莉亞,當年未萌發的激情一點即燃,兩人立即陷入愛河。這回雖然沒有佛萊夫人的阻撓,然而在世俗道德和宗教教條約束下的兩人,能何去何從?正逢茱莉亞的父親瑪奇梅因侯爵因病回到故莊,打算在病危時急召家人回來見他最後一面……
國際媒體好評
★ 美國當月選書俱樂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 出版當月選書
★ 現代圖書館(Modern Library)評選二十世紀百大英語小說
★ 英國BBC「大閱讀」(The Big Read)公眾票選最佳英語小說之一
★ 時代雜誌(Times)百大英語小說
★ 美國Newsweek 雜誌歷年百大文學小說
專業推薦
《慾望莊園》中兩個男性角色——查爾斯與賽巴斯提安,發展了一段比友誼還深厚的感情,「幾乎」就要是同性戀了。或許正因為這份曖昧性,本書中並沒有《墨利斯的情人》中那種直接對於同性戀傷害壓抑的文字,而是以隱晦的美感來呈現,這種曖昧的,隱喻的,文學性的表達,也襯托出了那個時代的純真/無知。
—— 但唐謨(作家、影評人)
作者:伊夫林‧沃
英國小說家,傳記和旅行書寫作家,也是一位多產的記者和書評人。出生於英格蘭漢普斯特德的出版業與作家家族,畢業於牛津藍辛學院與赫特福德學院,主修新聞學與現代史。1928年出版第一本傳記著作《羅賽提:他的一生與志業》,同年首部小說《衰落與瓦解》亦問世。出版代表作包括《一掬塵土》、《慾望莊園》、二戰三部曲《榮耀之劍》等,晚年其作品被經常改編成電視影集、電影而廣為知曉,咸認為是二十世紀英語寫作大師之一。
1998年,在美國現代圖書公司(Modern Library)所選出的「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中,其著作就占了三本:《一掬塵土》、《欲望莊園》與《獨家新聞》。
譯者:李斯毅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美國波士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財經法學碩士,具臺灣證券分析師(CSIA)資格。喜愛閱讀,關心弱勢,譯有《印度之旅》、《一掬塵土》、《判決》、《等星星發亮的男孩》、《對不起,我不正常》等。人生路上處處有貴人相助,充滿感激。未來會繼續努力。
前言
序幕:重返布萊茲赫德莊園
第一部:我也在阿爾卡迪亞
一、遇見賽巴斯提安‧佛萊特◆以及安東尼‧布蘭屈◆初訪布萊茲赫德莊園
二、賈斯伯堂哥的嚴重告誡◆抵抗迷人魅力的警告◆牛津的星期天早晨
三、父親在家◆茱莉亞‧佛萊特小姐
四、賽巴斯提安在家◆瑪奇梅因侯爵在國外
五、牛津的秋天◆與雷克斯‧莫特崔恩共進晚餐,和博伊‧穆開斯特共嚐睡前點心◆山姆葛拉斯先生◆瑪奇梅因侯爵夫人在家◆賽巴斯提安與全世界為敵
第二部:荒廢的布萊茲赫德莊園
一、山姆葛拉斯先生露出真面目◆我離開布萊茲赫德莊園◆雷克斯露出真面目
二、茱莉亞與雷克斯
三、穆開斯特與我捍衛家園◆賽巴斯提安在國外◆我離開瑪奇梅因公館
第三部:輕拉一線
一、暴風雨的孤兒
二、私人視角◆雷克斯‧莫特崔恩在家
三、噴泉
四、賽巴斯提安與全世界為敵
五、瑪奇梅因侯爵在家◆在中國式客廳過世◆顯露目的
尾聲:重返布萊茲赫德莊園
屬於上個世紀的優雅愛慾──閱讀《慾望莊園》 但唐謨
伊夫林‧沃 大事年表
作者前言
此刻再版的這部小說,除了許多新增的補充,也有大篇幅的刪減。各界對這部小說的讚譽曾讓我一度迷失,讓我走進一個充滿書迷來信及大量媒體鎂光燈的陌生世界。這本小說的主題──神聖恩典在一群性格迥異但彼此相繫的人物身上如何展現──或許過於放肆,但我不認為自己需要為此道歉。我比較不滿意的是它呈現的形式,然而這部小說在形式上的明顯缺失,應該可以歸咎於我撰寫時的外在環境。
1943年12月,我在軍中因跳傘受到輕傷,必須暫時離開部隊。後來有一位富同情心的指揮官同意我延長休假,我才能夠幸運地休養至1944年6月,並且完成這部小說。我在撰寫這本書時有一種罕見的熱情,讓我幾乎不想重返戰場。那是一段荒涼的歲月,貧瘠且惶恐──只有大豆與基本英語的年代──導致這本書充斥著一種貪婪的氣息:對於食物、對於美酒、對於不久前的輝煌燦爛,以及對於精心修辭之華麗語言,都充滿渴求。這些事物在人們胃口獲得滿足的今天,看起來毫無品味可言。不過,我只對一些過度明顯的篇章進行修改,沒有將之完全刪除,因為那些內容其實是這本書的核心。
茱莉亞在討論原罪時的大爆發,以及瑪奇梅因侯爵臨終之前的獨白,我寫作時對這兩段的內容一直猶豫不決。我原本無意寫入這些情節,因為這一類的內容屬於另種寫作形式,與早期查爾斯和他父親之間的互動極為不同。倘若我現在重寫這本書,我不會將這種寫作方式放入一部整體而言非常逼真的寫實小說裡。然而我還是決定保留它基本的原貌,因為就像書中提到的勃艮第紅酒和月光一樣,這些代表著我寫作時盈滿在我心中的情緒,而且許多讀者喜歡這些段落,儘管這並非我考量的重點。
我在1944年春天時,很難想像今日的人們會對英國鄉村莊園如此感興趣。在那個年代,豪華大型宅邸這種英國式的主要藝術成就,就宛如十六世紀的修道院,註定無法逃脫衰敗及遭到掠奪的命運,因此我在字裡行間堆砌了許多真誠的熱情。倘若布萊茲赫德莊園存在於今日,應該已經可以對外開放,供大眾參觀。那棟大宅裡收藏的奇珍異寶,應該也已經經過專家之手重新擺設,掛毯與針織品肯定會比瑪奇梅因侯爵在世時得到更好的照護。英國的貴族氣派將維持它在從前幾乎無法具有的特色。胡柏爾的升官之途後來屢屢受阻,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本書成了一首唱給空棺材聽的輓歌。但假如未經徹底摧毀,就無法在今日得到重生。這是一部讓年輕讀者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作,重點不在於對二○年代和三○年代的闡述,那些部分都只是在表面上簡單帶過而已。
伊夫林‧沃
一九五九年於康蒙‧佛洛瑞
序幕:重返布萊茲赫德莊園
在抵達駐紮山頂的第三連之後,我停下腳步回頭張望。灰茫茫的晨霧中,山下的營區映入我的眼簾。我們今天就要拔營了,三個月前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時,這裡還被厚厚的大雪覆蓋著,如今春天的嫩芽都已經開始萌發。當初我一度認為,無論我們將來還要前往哪些荒蕪之境,都不可能比這個地方更為嚴苛。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這裡確實沒有任何愉快的回憶。
我對軍隊的熱愛,在這裡已經完全消逝殆盡。
這裡是火車鐵軌的盡頭,在格拉斯哥喝得醉醺醺才準備返營的士兵,可以先在車廂的座位上打個盹兒,一路睡到火車駛達終點。從火車站到軍營還有一段距離,那些士兵得先走四分之一英哩的路,在經過哨站之前還有充分的時間將襯衫扣緊、軍帽戴正。過了哨站還有四分之一英哩的路得走,這段路的水泥路面早已被從兩側蔓生的野草覆蓋。由於軍營在市區的最外圍,因此這裡已經看不到外觀相似且緊密相連的住宅,也沒有電影院,只有偏僻的空地。
軍營的所在位置,不久之前還是牧地和耕地。農舍依舊座落於山谷坑窪處,目前充任軍團的辦公室。果園已經荒廢了,有些地方的外牆爬滿了常春藤;洗衣房後面那片佔地半英畝的老樹林雖然只下剩斷枝殘幹,但是尚且倖存。在軍隊抵達之前,這片土地早已經被標註為拆除區。倘若戰爭晚一年才爆發,這裡的農舍、果園外牆及蘋果樹就會全部遭到鏟除。貧瘠的泥巴田埂之間已經鋪上半英哩長的水泥路面,市政工程承包商設計的排水系統,裝設在棋盤格狀的開放式溝渠兩側。倘若晚一年開戰,這個地方早已被開發為新興衛星城鎮。不過,曾為我們抵禦寒冬的小屋,現在將面臨遭拆除的命運。
道路的另一頭有一間市立瘋人院,即使在草枯葉落的冬季,這間瘋人院也終日隱藏在樹林間。相較於瘋人院的鑄鐵圍欄和宏偉大門,軍營粗糙的鐵絲網圍牆看起來顯得寒微,實在非常諷刺。在天氣晴朗時,我們可以看見病人們在瘋人院平整的碎石子路或舒適草坪上悠閒散步或蹦蹦跳跳。那些人放棄以微薄的力量掙扎,不僅消除了他們對各種事物的懷疑,也終結了他們所有的責任。在人類文明的進展過程中,他們無庸置疑是法律所保障的受益者,輕輕鬆鬆享受權利。我們行軍經過瘋人院時,有些士兵會隔著圍欄對著那些病人大喊──「夥伴,替我暖一張床!不久之後我就會進去了!」──但我手下新來的排長胡柏爾非常怨恨那些瘋人享受的特權。「如果英國由希特勒統治,那些傢伙早就被送進毒氣室了。」胡柏爾表示。「我覺得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向希特勒學習。」
仲冬時節當我們進駐此地時,我帶領的這支團隊人人身強體壯且充滿希望。我們從沼澤地區行軍到這個碼頭區的時候,連隊裡流傳著振奮人心的耳語,說我們終於可以出發前往中東作戰了,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每天只是不停地鏟雪和整理閱兵場,我看得出連上弟兄已經慢慢從失望變成順服命運。他們每天聞著炸魚店傳來的氣味,耳朵留意著和平時期常聽見的工廠上下班鈴聲和舞廳樂隊演奏聲。現在只要每逢放假日,連上的弟兄就會無所事事地站在街角;若是有長官接近,他們便立刻側身溜走,因為不想在新認識的女性面前向長官行禮,覺得看起來沒面子。連隊辦公室經常得忙著處理違紀懲處和事假申請,而且每天還不到天亮,就已經有人為了偷懶而開始裝病,或者因為不滿而沉著臉,兩眼放空。
身為連上弟兄的長官,我理應全心關照他們──可是我根本自顧不暇,哪裡還有能力幫助他們?帶領這支連隊的上校,升官之後就從我們眼前消失了,他的位子由另一個軍團的主官兼任。那個人的年紀稍輕,也比較不討人喜歡。在戰爭剛開始時,那些和我一同接受訓練的志願兵,基於種種原因,如今已經沒剩下幾個人,幾乎快要走光了──有人因為傷病而退役、有人升遷之後調至別的軍團、有人轉任後勤幕僚單位、有人自願加入特殊兵種,還有一個在靶場上不幸殞命,一個被送進軍事法庭──這些人的空缺都由義務兵來填補。結果現在三不五時就有人來會客,晚餐前的啤酒消耗量也遠比以前增多,一切都和從前大不相同。
三十九歲的我開始覺得自己老了,每天晚上都覺得全身僵硬、疲憊不堪,甚至懶得踏出營房一步。我還慢慢養成一些特殊的要求和習慣:只坐特定的座位、閱讀特定的報紙、晚餐前固定喝三杯琴酒,絕對不會多一杯也不會少一杯,而且只要一看完九點鐘的新聞就立刻上床睡覺,每天清晨總在起床號響起前一個小時就心浮氣躁地醒來。
在這個地方,我人生中最後的愛已經死去。它的死去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之處,總之在某一天,在我們駐紮於此地最後一日的前夕,我在起床號響起前醒來,靜靜躺在這個有水泥地板的隧道狀營房中,眼睛凝視著全然的漆黑,耳邊聽著同寢室另外四人發出的呼吸聲與夢囈聲,腦中反覆思忖著當天必須完成的工作──那兩個參加武器訓練課程的人員名單我交出去了嗎?今天又會有一大群人在收假時間逾期歸營嗎?我能放心讓胡柏爾自己帶儲備軍官出去勘查地形嗎?──在那個身處黑暗的一個小時裡,我突然驚覺自己心中某種枯萎許久的東西已經悄悄死去,那種感覺就像一個邁入婚姻生活第四年的丈夫,赫然發現自己對曾經深愛妻子已經不再有任何慾望與柔情,也不再有任何敬重。他對妻子的相伴已經無法感到任何愉悅,自己也無心取悅妻子。妻子所做、所說、所想的一切,他都已經不再感到好奇,亦不期望修補這段婚姻關係,或者因為這種災難般的情況責怪自己。這些我都明白,因為這種婚姻走向毀滅的過程,正是我從軍之後所經歷的感受。最初的執著追求,到如今除了法律、責任及規範的冰冷維繫之外,軍隊和我之間早就什麼都沒有了。在這段以悲劇收場的婚姻關係中,我從頭到尾參與了各種情況:從起初的小爭執越來越常發生、眼淚越來越難產生感動,到每一次和好之後也不再甜蜜,最後則是開始產生冷漠的情緒與冷酷的批評。我越來越確定,錯的是對方而不是我。我察覺對方說話的語調充滿虛假,並學會了以理解的心情去聆聽這種虛偽;我看見對方因為不理解而在眼中浮現茫然和不滿、聽見對方從嘴中說出自私與無情。我瞭解軍隊,就像丈夫一定會瞭解三年半來日復一日與自己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妻子。我瞭解她的散漫、她的習慣和手法,以及她說謊時因緊張而有的小動作。她所有的神奇魅力都已經剝落,如今我眼中的她,只是一個與我志趣不合的陌生人。只能怪我一時糊塗,才會將自己與她緊緊綁在一起。
於是,在我們拔營的這個早晨,我對我們的下一站完全不感興趣。我會繼續履行我的職責、完成我的任務,但除此之外,我不會多投入一絲心力。我們接獲的命令,是要在早上九點十五分從附近的火車停靠站上車,背包裡帶著當天配給的乾糧。我只需要知道這些。連上的副官已經隨著先發部隊離開,物資也都在前一天打包完畢。胡柏爾仔細檢查隊伍的裝備,他們於七點半開始整隊,包裹都堆在營房外。自1940年我們誤以為將前往保衛加萊的那個令士氣大振的清晨之後,我們經歷了許多次類似的行軍與遷營,每年大概三到四次。這次,我們的指揮官採用一種不同於平常的保密措施,要我們把制服和車輛上的標誌全部拆掉。「這是針對當前軍事情況非常具有價值的訓練。」指揮官表示。「如果我在目的地發現任何一個跟隨著軍隊而來的女性,就可以確定一定有人洩露我們的行蹤。」
伙房飄出的炊煙消散在晨霧中,此刻的營地看起來像一個雜亂無章的迷宮,再加上未完成的房屋規劃,在經過多年之後被考古隊挖掘出來的模樣。
「波拉克考古隊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考古證據,證明二十世紀公民奴隸社會與其後繼的無政府部落社會之間的關係。從挖掘現場可看出一個極為頂尖的人類文明,不僅能修築精巧的下水道系統,還能建造可永久使用的高速公路,但最後卻被一個最低等的種族所取代。」
我猜,未來的專家們將會如此寫道。轉身之後,我向迎面走來的連隊士官長打招呼。「你有沒有看見胡柏爾排長?」我問。
「報告長官,我今天早上都沒有見到他。」
我們來到已經清空的連隊辦公室,發現一扇在破損清單完成後才破掉的窗戶。「長官,這扇窗是夜裡的風吹破的。」士官長表示。
(所有裝備的破損,都是用這個理由,不然就是「被挖地道的工兵不小心震破的」。)
胡柏爾出現了。他是一個臉色蠟黃的年輕人,頭髮從前額梳往後腦,沒有分線,說話時有無趣的英格蘭中部方言口音,進入連隊已經有兩個月的時間。
軍隊裡的人都不太喜歡胡柏爾,因為他對軍中事務懂得太少,而且有時候會在大家稍息時誤稱每個人為「喬治」。然而我對他有一種近乎心疼的關懷,主要是因為他來報到後第一晚的遭遇。
當時新來的上校才上任不到一個星期,我們都還沒有摸清楚他的脾氣。新上校在休息室裡喝了幾杯琴酒,當他第一眼看見胡柏爾時,腦子已經有點不清楚。
「萊德,那個年輕軍官是你的部下,是嗎?」新上校對我說。「他的頭髮該剪了。」
名家評讀/屬於上個世紀的優雅愛慾——閱讀《慾望莊園》/但唐謨(作家、影評人)
2017的夏日,大英圖書館的走廊辦了一個小巧的英國同志歷史展,紀念英國同性戀除罪化五十年。瀏覽其中,看到了這西方古國有最耀眼/妖冶的八○年代的酷兒流行文化,也看到最惡名昭彰的同志黑歷史,包括王爾德,圖靈等事件。英國的同志歷史多元而有趣,每個世代都有不同的媒材紀錄同志的記憶。在二十世紀初,整個人類開始邁向新文明之際,英國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說《慾望莊園》(Brideshed Revisited)呈現了一個帶著點嘆息與時代印記的同志文本。
慾望的時空
《慾望莊園》的背景是個美好優雅的烏托邦。故事開始於1920年代,英國剛經歷過世界大戰,還在緬懷歌頌戰爭英雄,僅管國力已不如以往,昔日的榮光仍足以支撐那份富饒的傳統,此時的英國,仍然是個日不落的帝國,即使已經到了尾聲。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這世代的最後貴族。他們養尊處優,談吐高尚,遵守上流社會的規範,至少,他們都意識到了這規範的制約。他們對生命都有各自的執著,然而,生命卻不一定如他們的執著所願。
《慾望莊園》誠如它的副標題:「查爾斯.萊德上尉的敬神與瀆神回憶錄」,是一份生命/成長的紀錄,標題中的查爾斯.萊德是個成長在二十世紀初末代帝國的年輕人。他的出生雖非超級富裕,至少他也進得起牛津名校。他帶著一絲不切實際的青春浪漫,希望當一個藝術家。在風格特異的大學生態中,他結識了同樣年輕帥氣,但是小小年紀卻彷彿承載了生命無比重量的賽巴斯提安。兩個男孩馬上莫名奇妙地彼此吸引。然後,賽巴斯提安帶著查爾斯造訪了他的家,也就是故事的中心,書名中的——布萊茲赫德莊園。
對於布萊茲赫德莊園,我們應該一點也不難去想像,就像我們在電影電視看過的那種大得不得了的西方大豪宅,裡面有一大堆複雜的房間走廊,有下人住的地方,還有一大片草坪,可能還會有河流小湖。豪宅內好像博物館,滿滿的藝術品,每個人都穿著正式服裝走來走去……你彷彿可以在這地方優雅地過完一生一世。
宗教與逃離
這本書中對於布萊茲赫德莊園的描述,應該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那種過度的豐富,絕對的完好,風格化的完美要求,從今天的角度看,根本沒人會去住吧(累死);但是今天的我們卻願意去從旁欣賞這份古典的頹「廢」。故事中兩個男孩來到莊園的時候,家裡沒大人,豐盛的莊園是他們的玩耍空間,他們可以盡情揮灑生命,享受/分享彼此,彷彿無憂無慮的伊甸園;但是當大人(母親瑪奇梅因侯爵夫人)在家的時候,這個大莊園頓時變成了地獄。
《慾望莊園》中的家庭,我們也不陌生:美麗的母親一絲不苟的執念,逼瘋了每個人,於是父親拋棄一切離家,兒子也選擇自我放逐,幾乎是典型的《玻璃動物園》的家庭生態。然而這故事中,一切的衝突的源頭卻是宗教(天主教)的執念。英國歷史上的天主教與「異教」一直在互相廝殺,爛事一堆。這份悖乎人性的宗教執念被放進名門豪宅中,演變成了這場宿命悲劇。於是,逃離與流放,就是唯一的宿命了。
慾望的流放
在空間場域上,《慾望莊園》也是個慾望流放的過程。英國人超級愛往外跑,有個說法是英國太冷,所以他們喜愛跑去溫暖的地方;但也或許是,英國的拘謹壓抑,讓他們很想逃離。《慾望莊園》以英國/倫敦/牛津為中心,故事空間卻涵蓋了歐陸,北非,拉美,以及美國。每個地點都彷彿是個慾望的流放之地。無法擺脫壓抑的賽巴斯提安,最後選擇了北非摩洛哥的坦吉爾,當作慾望的終點;無法忍受妻子的瑪奇梅因侯爵逃到了威尼斯,藉著異國氛圍來解放自己;查爾斯來到法國,故事中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一場法國大餐飲食的過程,也是另一種慾望的實踐(大家都知道英國食物超難吃);他也流放到了墨西哥,從相異的文化中尋找創作靈感。故事到了最後面還有一場紐約豪華郵輪的壯麗景觀,也是從另外一個文化觀點,對比人物內心的慾望衝突。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理由,選擇各自的流放;只有英國,只能孤零零地死守著一片大而無當的莊園。
曖昧的同性戀
《慾望莊園》中兩個男性角色——查爾斯與賽巴斯提安——發展了一段比友誼還深厚的感情,「幾乎」就要是同性戀了。或許正因為這份曖昧性,本書中並沒有《墨利斯的情人》中那種直接對於同性戀傷害壓抑的文字,而是以隱晦的美感來呈現,這種曖昧的,隱喻的,文學性的表達,也襯托出了那個時代的純真/無知。例如侯爵夫人會在對話中直接對查爾斯說:「賽巴斯提安愛你,」但是母親不知道兒子的同性戀,在她的思維中,那根本是不存在,不可能發生的東西。又如故事中賽巴斯提安在告解室「總是花很長的時間懺悔,因此我相當好奇,他到底在懺悔什麼?他從來沒有做錯過任何事……」那麼?他到底在告解室幹嘛?跟神父打情罵俏嗎?
至於查爾斯,他或許是那種青春時期有過同志慾望的暫時性異性戀,因為他後來選擇了女性;然而他卻更像一個隱性的,深櫃的,想要轉性卻沒有成功的同性戀。他喜歡上賽巴斯提安的妹妹茱莉亞,只是因為她像極了她哥哥(如果不像的話呢?);他娶了俗不可耐的妻子,只是因為「我很寂寞,我很思念賽巴斯提安。」
同性戀在這整個故事中,彷彿一個洶湧的暗流,從來沒有在文字中明喻,從來沒有過性慾的描述;這道暗流也從來沒有真的射出來過,但文字依然抒情撩人,正如那個保守,壓抑,卻不失優雅的年代。
純真的慾望
保守不失優雅的年代,也是《慾望莊園》所讚美或緬懷的,查爾斯在二戰的時候回歸了她愛情的起點——布萊茲赫德莊園,但是昔日的優雅,已經永遠失去。同樣的人物故事,放在今天的脈絡,絕對是完全不一樣的結局,甚至可能是個勵志喜劇;但是唯有在二十世紀初,思想剛剛開始解放,現代化剛剛成型完畢,人們對於舊秩序仍然存在著頭腦不清楚的執著,以及所有人物耽溺到不行的感性背景下,才能成就出如此一個「敬神與瀆神」的紀錄。這份對慾望傻傻分不清的「純真」也讓故事格外吸引人,因為,那些都是我們已經失去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