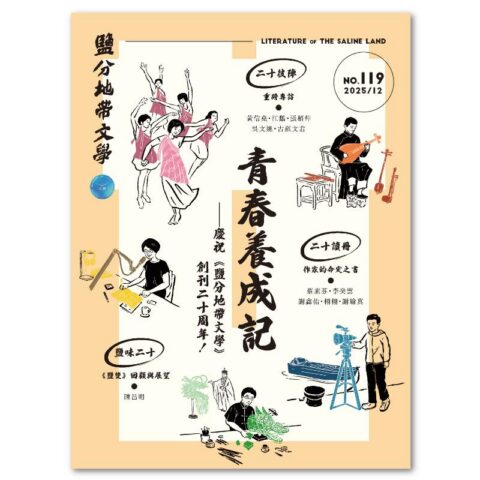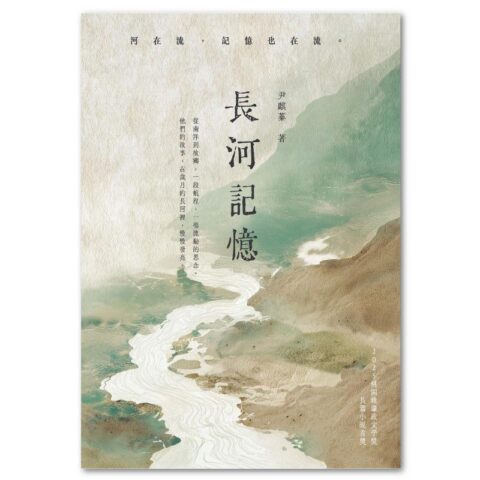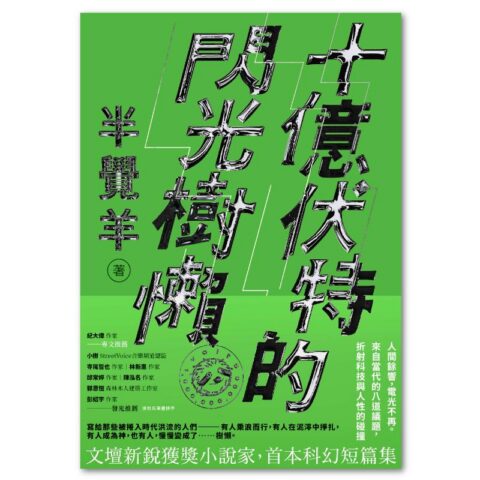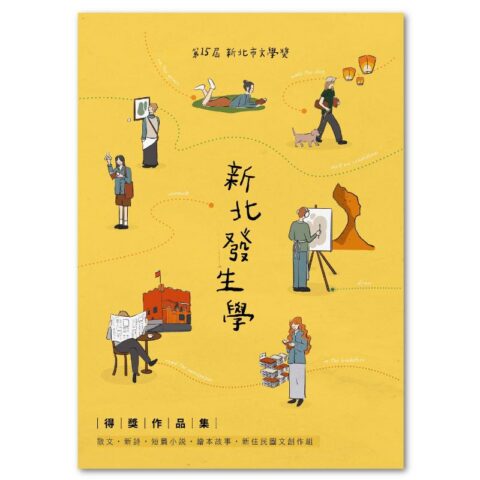反調
出版日期:2012-05-25
作者:李煒
譯者:陳青、於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39944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2011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李煒新作!
一本
無意時尚
無暇傳統
無視市場
無關老套的
西方文化散文集
從二十世紀到中世紀,倒流的時光,反轉的音調
將西方文化裡最經典,卻又鮮為人知的東西,介紹給讀者
在這個已不再關注純藝術、純文學、純哲學的時代,一個學者如果想要取悅大眾,唯一能做的不外乎是評論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闡釋那些眾所周知的作品,重述那些老掉牙的話題。
結果,絕大多數討論藝術、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都沒什麼新意,總是重複著那幾個人、那幾樁事,好像除此之外,沒什麼別的好說。
許多被大眾忽略的藝術家、作家與哲學家其實都是一流的,他們的才華與成就絕不亞於那些老是被吹捧上天的人物。這也是李煒寫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為他喜歡與流行唱反調,而是因為他覺得有必要,把這些值得認識、甚至深究的人物、軼事,介紹給更多的讀者。
※ 媒體讚譽
(李煒)嘗試,把大師精髓用每個人都會碰到的情境寫出來,希望願意花一點時間讀書的人,都能理解。──《中國時報》
不管是文學、藝術、歷史、政治、哲學,在(李煒)筆下往往一兩段,立刻理出重點。──《聯合報》
芝加哥大學英美文學系畢業的李煒,博覽群書,他在書寫的時候,將世界各國的文學經典,以及作家對人生哲學層面的思考,全部自然融入書中……──《人間福報》
李煒約取的慢慢拿出來肚子裡的龐大素材,是旁證主題,是風趣鋪陳,是親切抒情,是活潑對話,更是研究文學者少見的幽默想像……──《吾愛吾家》
在當今臺灣文壇,李煒無疑是株境外移入的奇花異卉……在《4444》出版後,他的光芒相信也已是無法掩蓋的了。──《文訊》
李煒用英語寫作,寫的是侵襲人靈魂的音樂,寫的是傲慢的憂鬱,他將身心靈肉揉進音符,用英文作載體表現出來,再和譯者轉譯為母語中文,這種靈感淵源及文字形成的雙重奏鳴,本身就是一種複雜的創作,一定能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新聞晨報》
李煒雖然年輕,西學之博中有精卻相當驚人,令我想到錢鍾書……──《文匯報》
作者面對死亡,謳歌生命,感悟文學,思索哲學,文字中蕩漾著音樂。──《出版商務週報》
和他前面的兩本書《書中書》、《碎心曲》一樣,(《4444》)也是一本頗為詭祕、飽含激情、充滿想像力的才子書。──《廣州日報》
作者:李煒
出生於臺北,靠優異的數學成績進入芝加哥大學,後轉讀文學系,開始苦修英、法、德、義、拉丁以及古希臘語。近年長住大陸,並於上海《書城》雜誌發表多篇文章。出版有《4444》等書。
譯者:陳青
四川外語學院畢業,主修英語語言文學翻譯。二○○五年畢業後常住上海,一直從事專職翻譯工作,迄今已譯有數百萬字。
譯者:於是
居於上海,寫字為生,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系,著有小說散文四五本,譯作十數本,包括《美與暴烈:三島由紀夫的生與死》、《杜馬島》、《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
13、在哲學的邊緣
12、雙情記
11、愚人動物園
10、死胡同裡的冷幽默家
9、月亮上最高的人
8、魔鬼與天使
7、致命的完美
6、哀鬱的文字玩家
5、灰色手記
4、失敗的脫身術
3、職業惡人
2、黑暗之旅
1、後記
0、進一步的參考讀物
後記
黎巴嫩詩人兼小說家古伊葛塔(Venus Khoury-Ghata)客居巴黎時,她的祖國爆發了內戰。情況慘絕,讓她無法回返。
但她還是比大多數流亡者幸運,因為她已能流利的使用容身之地的語言。而且還不只是遊刃有餘,她可以直接用法語寫作並出版。這種令人豔羨的外語能力卻得讓她付出高昂的代價:新語言把她擰成一個似乎沒有國籍的人,既不再屬於她的本籍文化,也不算是道地的法國作家。
古伊葛塔在寫給法文讀者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她用阿拉伯語寫作時是從右寫到左;而用法語寫作時,卻是從左到右。一個是她的母語;另一個則是「讓她接受教育並經歷文學啟迪的語言」(借用她英語譯者的美妙說法)。這條「雙向路」充滿隱喻,兩種語言彷彿在紙上迎面相逢,但這竟讓她自覺是個非法侵入者。她本人用的類比喻體是「重婚者」:一個「藉語言的掩護而過著雙重生活」的女人。
古伊葛塔的用詞挑明了一點:她覺得精通兩種語言有點不妥,甚至不該被允許。正因如此,她才會為自己選定的文學語言進行辯護。提及「重婚者」的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為什麼我用法語寫作〉。
說得也是。為什麼「硬要用不屬於自己祖國的語言」講述故國家園的故事?
「答案很簡單,」古伊葛塔自己回道:
住在黎巴嫩,我不可能寫書;我會忙於育兒和煮食。因有距離,才有必要講述黎巴嫩。我需要重建它,模擬它的初態、分裂和傷痛,從而給自己一種幻覺,好像和留在那裡的同胞們一起分擔了日常生活中的恐怖。
重要的是,用法語寫作並不意味著阿拉伯語被迫隱沒。事實正相反,古伊葛塔的母語仍然想被聞見:「阿拉伯語把它的甜蜜和瘋狂注入法語」,雖然這也讓她成為「流離於兩種語言之間的那種人」。
‧
在《與我的父親阿朵尼斯(Adonis)的對談錄》中,敘利亞最受尊崇的詩人不厭其詳地和他的女兒進行了一系列廣泛話題的互問互答。最終,語言的問題浮出水面。女兒請父親解釋他和阿拉伯語的關係。
「我無法想像自己使用別的語言,」阿朵尼斯坦承地說,「阿拉伯語旺盛地活在我的身體裡,以至於它會去嫉妒所有其他語言。我相信阿拉伯語已深切的植根於我,讓我在其他語言面前顯得笨拙愚蠢。」
無論這番話多麼謙虛動人,它並不完全屬實。別的不說,父女間的這些對談都是用法語進行的。阿朵尼斯不僅受過正式的法語教育,還在法國住了許多年,因而可以流暢無礙地使用這種語言。至於他的女兒,法語則是她的第一語言。「我可以寫一點阿拉伯語,」她在書中承認,「但只懂皮毛。這門語言更像是一種硬加在我身上的責任、甚或重擔。」
阿朵尼斯對女兒的困窘感同身受,但他還是堅稱:「如果你真想理解一位詩人,就必須用他的母語閱讀他。」
所以,她的阿拉伯語到底得要多好才能理解她父親?
「你必須通曉阿拉伯語,」父親回答說,「但你已經不太可能達到這種境界了。」不過,面對希望成為作家的女兒,他還是寬慰了一番:她只需要徹底掌握一門語言,就能符合作家該有的標準。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選擇法語;但這麼一來,我們之間就會存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詩意的以及語言的鴻溝……我不知道你吼叫和哀泣時用法語還是阿拉伯語,但我覺得,阿拉伯語將永遠是你的文化語言,而不是母語……
‧
吼叫和哀泣時的語言:還有比這個更像「母語」的精準定義嗎?當我們陷入沮喪絕望時,要是不能毫無顧忌地依賴某種語言,它還怎能擔當我們最主要的溝通方式?
正是這個原因,古伊葛塔在闡釋她為何用法語寫作的文章裡還坦白了一點:「新近征服的語言對解決日常繁文縟節毫無助益」。用阿朵尼斯的說法,這是因為法語只是古伊葛塔的「文化語言」,而非她處理俗世問題時的母語。
這不是說一個人無法在第二語言中如魚得水,只用那種語言就能解決生活中的煩惱。只不過,要達到這種程度,他必須投入所有時間,一直使用他想要精通的語言。他必須徹底的棄械倒戈,直到在夢裡都說那種語言為止。
因此,讓兩種語言都保持完好無損的狀態簡直是異想天開。連古伊葛塔都承認,「保留舊語言並且掌握新語言,需要走鋼索的技藝。」
就算一個人有這種技藝,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嗎?想想日常生活中需要了解的零碎事物:新觀念,新流行語,新玩意兒,新人名和新地名──誰真有耐心以及決心同時用兩種語言學會這些東西?
所以,無論是否心甘情願,我們終究會疏遠一種語言,慢慢讓它老朽、蒙塵乃至閒置。每一週、每一月,我們又多忘了一些詞、幾句話,直到有一天才驚覺到,對於那種語言我們不再能夠運用自如,哪怕它是我們的母語。
‧
二
不久之前,我的一部小品得了個獎,繼而也讓它的作者面臨了一個有關母語的問題: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北人為何選擇用英語寫作?
琢磨了半天,最終我只能說,因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更適合用來寫作。
事實上,我不僅是英文寫作更好,就連一般思考也都是用英語。但我並不是所謂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生華裔〕的縮寫)。其實,使用英語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自然──至少一開始不是。
為了改變語言,我十五歲移居美國後就一頭扎進了英語。像一名船難中的水手,與其禱告救援在船沉前抵達,不如一個猛子地扎進水裡,奮力划動四肢,游向最近的陸地,因為這幾乎是唯一的生機。轉換語言的人都如此,必須在源源不絕的文字中急流勇進,試著不被險惡的語法暗流沖走,不被無窮無盡的詞彙淹沒。
回頭去想,這麼做還真得有點勇氣。但一個遭難的人很少會有當英雄的念頭,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存活。對一個青少年來說,「存活」就是結交新朋友、融入新環境,在學校裡不做那種不敢張口說話、老是被取笑的可憐蟲。
‧
因此我在英語上投注了不少功夫。這讓我沒有變成那種一眼就能認出來的移民。即使是在紐約這個出名的文化大熔爐裡,還是有不少外國僑民從未被「熔化」過。他們成天和同胞黏在一起,唯讀母語報紙,看那些從遙遠國度傳來的電視劇,除了祖國的傳統飲食什麼都不碰,就連衣著好像也從未隨著潮流更換過。
我年輕時常想,這樣的人去了異國有什麼意義?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後,他們仍不能用第二語言拼湊出一個像樣的句子。
但現在的我卻不再那麼肯定那些人需要憐憫,更不會去鄙夷他們。也許他們有意識的做出了抉擇,也許僅僅出於恐懼、甚或懶惰,無論如何,他們拒絕被「熔化」,因而妥善保存了自己的母語;他們的發音依然清晰,提筆時仍可運用大量的詞彙。這難道不值得褒獎嗎?
‧
人們通常認為,一個人更改了他的主要語言,就切斷了自己和母國文化的重要紐帶。偶爾,還可能被詬斥為拋棄同胞和故國。
實際上,更換語言這種事頻繁發生,並不見得有太多寓意。為了開展一段新生活,人們往往需要同步接收一種新語言。
真該問個究竟的是,以我們使用的語言來「界定」我們的身分,這麼做是否合理?例如,一個女人必須說出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才能被認定為「阿拉伯人」嗎?難道只因為她更擅用另一種語言,就不再能屬於她的出生地?
不應該這樣吧?至少,我希望不是。理由很簡單:我們使用哪種語言通常都是由「命運」所擺布。這一點在猶太作家貝克(Jurek Becker)的生平故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闡釋:
如果,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我被看作是一名德國作家,這只是出於一系列的巧合。我出生在枯燥乏味的波蘭小城羅茲……如果我出生後不久德軍沒有入侵;如果我的國家沒有淪陷;如果後來我和父母沒有被趕進猶太人居住區、然後又從一個集中營送入另一個;如果蘇俄紅軍沒有解放我最後被關進的那個集中營,那麼,我倒很想知道,今天我會站在誰面前,又會被看作是哪一國人……
戰後,我父親──也是我們家除了我之外的唯一倖存者──莫名其妙地在柏林住下了。如果他移民去了布魯克林,我豈不是成了美國作家?要是他選擇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是臺拉維夫?可是他沒有。在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性裡,他做出最驚人的選擇:他留在這裡……並安排我成為一個德國人。
‧
貝克如此,可能我也相差無幾。或許我用英文寫作的「真正」原因在於,我母親在紐約生活了許多年。
如果她不是個作家;如果她沒有和我父親離婚;如果紐約的文化沒有那麼豐富;如果當初臺灣的教育體制沒有那麼糟糕,從頭到尾只強調死記硬背;那麼,我也不大可能會改變我使用的語言。
然而,生命中的重大決定往往都由不得我們自己做主。所以今天用英文寫作的我,才常被稱為「美國作家」,雖然這並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在內心深處,我仍舊是個說漢語的人。陷入沮喪絕望時,我依然仰仗這最初的語言來吼叫和哀泣。
‧
三
在《天下之美》中,捷克詩人塞弗爾特(Jaroslav Seifert)談到了哈謝克(Jaroslav Hasek):
他總是坐在桌角寫作,每寫完幾頁,他的朋友就會把稿子直接拿給出版商,出版商也會按篇幅付款,一毛錢也不會多給。就這樣,一天的酒錢都解決了。倘若第二天他不想面對一個空杯子,他就必須繼續寫下去。
令塞弗爾特好奇的是,如果他祖國這位小說家「能夠平平靜靜、舒舒服服地在書房裡寫作」;如果他沒有從早到晚在「一家嘰嘰喳喳的酒吧」裡跟他那群酒友混在一起;如果他不需要「在一張啤酒四濺的桌子上」創作;如果他提筆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需要賺點酒錢」;那麼,《好兵帥克歷險記》是否會有任何改變?
然而,塞弗爾特也清楚,要是沒有上述的這些因素,很可能小說家根本就不會寫出他最著名的那本小說,也不會成為「那個揚名全歐洲的『哈謝克』」。
但這仍然只是一種猜測,誰也無法確定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這個或那個結果。就像塞弗爾特所說,任何一件事,從策畫到完工,都涉及到一連串可以「決定命運」、改變結果的「如果」。
這本書也不例外。要是我母親還沒有過世,要是她沒有留下一點遺產,讓我可以專心寫作,我也不可能有時間寫出這些絕不是為了討好市場,而只是因為自己想寫而寫的文章。
‧
老實說,這世上沒有一個作家不想要有更多的讀者;不想看到自己的著作登上暢銷排行榜。問題是,在這個已不再關注純藝術、純文學、純哲學的時代,一個學者如果想要取悅大眾,唯一能做的不外乎是評論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闡釋那些眾所周知的作品,重述那些老掉牙的話題。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絕大多數討論藝術、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都沒什麼新意,總是重複著那幾個人、那幾樁事,好像除此之外,沒什麼別的好說。
事實卻不然。有許多被大眾忽略的藝術家、作家與哲學家其實都是一流的,他們的才華與成就絕不亞於那些老是被吹捧上天的人物。
我想,這也是我寫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為我喜歡與流行唱反調,而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值得認識、甚至深究的人物、軼事介紹給更多的讀者。
‧
薩克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三十六歲時,策畫了六組小說,每一組都由六部中篇構成。這六組小說的主題分別是愛情、財物、政治、戰爭、事業,以及死亡。每一組的前五部作品會通過虛構的故事來討論主題所涉及到的問題;第六部則會提供答案。這麼一來,薩克馬索克宣稱,他便可以描述「世上所有重要的問題、生存中所有的危險,以及人類所有的弊病」。
不消說,這位十九世紀奧地利作家並沒有達成他的夢想。他雄心勃勃計畫的一系列小說,只完成了兩組,而且一本比一本寫得糟糕。這兩組作品中唯一一部常被提到的,仍是《穿貂皮衣的維納斯》,一本打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描述「性變態」行為的小說,最後還讓作者的名字被心理學家用來命名「受虐癖」(德語中的「Masochismus」)。
當然,惡名昭彰也有它的好處。尤其在這樣一個對醜聞誹謗特別有興趣的時代,一個文人想要引人注意,或許真的得不擇手段。但我想,要是一個人能從薩克馬索克身上學到什麼,最踏實的,大概還是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換言之,與其宣布有一天,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寫出一系列的文章,把西方文化裡最經典卻又鮮為人知的東西介紹給讀者,還不如默默地寫下去,一篇篇文章、一本本書地發表。這麼一來,就算最終無法完成夢想,我還是寫了許多關於自己欣賞的藝術家、作家、哲學家的文章。每一人的作品都讓我在閱讀研究的那些深夜裡,在孤獨中得到樂趣;在黑暗中得到啟迪。
要說這是文化可提供的最基本報酬,或許也不為過吧。
13.在哲學的邊緣
一間老人院的小病房。屋子裡擺著的,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書作。
住在這兒的人早就不再閱讀了。大多數時間他都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莫名地焦躁不安。他已經到了老年痴呆症晚期。
在他情緒特別差的時候,唯一能寬慰他的就是把那些書放在他手裡,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這時他往往會瞇起眼睛,一臉疑惑卻又天真的表情,有時還會觸摸名字的每個字母,似乎不明白那些符號代表著什麼。
儘管如此,這總能讓他安靜良久。閱讀一定曾是他最愛的消遣,所以他才會不停地撫弄這些書本,即便他已不記得自己這樣做的原因,甚至不記得自己就是它們的創作者。
這是好些年前發生在巴黎的事了。
•
時光再倒轉六十年,慕尼黑,同一個人。
他信步走在城市中,像塊新海綿一樣,拚命吸納周遭的一切新鮮事物。
在感受視覺和聽覺衝擊的同時,他仍試著保持敏銳的批判力。這麼做並非是要評判德國。不,他所有的責難都指向自己的祖國羅馬尼亞,那裡的「落後」和「渺小」一直使他苦惱。現在,望著一向現代、激進的德國,他更感到自己國家的微鄙。
於是,他開始在一篇篇雜誌文章中讚揚德國的新任總理。「在當今的政治家裡,沒有誰能比希特勒讓我更認同、更崇敬」,其中一篇文章這樣開頭,而結尾更令人咂舌:
希特勒對政治鬥爭投入了火熱的激情,並為一整套被民主與民族主義貶抑得毫無意義的價值觀注入新生。我們都需要這樣一種神奇的魅力,因為有太多惹人生厭的真理從未迸發出火花。
這番結論就算沒讓布加勒斯特的編輯部破口大罵,也讓他們感到極為不解。在向這名年輕作家邀稿時,他們指明要的是針對德國國內剛發生的大規模殺戮的報導。這一系列在「長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做出的凶殺案是為了爭奪納粹黨的控制權,而下令的正是那位「向政治鬥爭投入了火熱激情」的先生。
但這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作家非但沒寫預定的新聞報導,反而發出了一封公開的「情書」。顯然他覺得幾十宗謀殺案不算什麼。喋血不但沒有破壞希特勒在他眼裡的神奇魅力,還可能將它抬得更高。哪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不佩服一個敢說敢做的「男子漢」?
•
聽起來這像個單純的道德故事:一名固執己見的納粹同情者最終得到了報應,儘管正義之輪在轉了六十多年之後才發揮作用。
如果要從這個角度來解讀蕭沆(E. M. Cioran)一生中的這兩個場景,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樣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間的所有成就,讓這一切變成「罪行」與「懲罰」二者之間的小插曲。
這種理解還會引申出蕭沆本人絕不會認同的一個觀點:世間存在著某種對善惡賞罰分明的法則和秩序。
在蕭沆看來,「不公正統治著全宇宙……在這個屠宰場裡,袖手旁觀和拔刀相助都同樣毫無意義。」
•
說句公道話,蕭沆究竟做了什麼,要受到譴責,遭到報應?除了他二十二至二十三歲期間在德國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章,還有那本在他年僅二十五歲就出版的《羅馬尼亞變形記》。儘管這本書已經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而且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中還不斷會有新書面世,這本卻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在蕭沆所有的著作當中,唯獨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統的研討,也只有這一本發出強烈呼籲,要讓一位無情的獨裁者來徹底轉變羅馬尼亞,消滅一切阻擋變革的人事物,無論是猶太人還是民主本身。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本能讓任何作者事後感到驕傲的書。所以蕭沆在近七十歲時才會說:「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廬時做過些蠢事,就會像一個有著不堪過往的女人,永遠都得不到寬恕和遺忘。」
•
其實,蕭沆走向他那條恥辱之路的開端極其平常,或許連解釋都顯得多餘。一個來到大城市的鄉下人,只要他血管裡流淌的血多過水──借用蕭沆自己的比喻──就會立刻頭暈目眩、心跳加速,因為他所見的事事幕幕都閃耀著超乎自己想像的美。
如果說是希特勒把這樣迷人的美帶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利而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的德國,那麼,羅馬尼亞自然也需要這麼一號人才。因為唯有像希特勒這樣的領袖,才能讓一個擠滿了「永遠沉浸在麻木和愚鈍之中的農民」的國家擺脫自滿,並帶領她登上世界的舞臺。
不用說,對於蕭沆這樣的憤青而言,如果讓他選擇「平淡」或「殘暴」,他永遠會挑後者。這一點他早已在自己的第一本書中就說得一清二楚:「唯有平庸之輩才會甘於『溫吞吞』地過活。」像他這樣的人當然不會被「長刀之夜」這種瑣事震撼到。
•
不過,他對政治的狂熱很快就會消退。第三帝國製造的許多恐怖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很明顯,唯有故意視而不見的納粹支持者才看不出蕭沆挑錯了陣線。
因此,在一九三七年把自己「放逐」到法國之後,他會在一本書裡問到一位作家的「源頭」究竟是什麼。「是他的恥辱」,他自己答到。
無論這說法正確與否,用在蕭沆自己身上,倒是分毫不差。當初他之所以不斷書寫自己的偏狹和憤怒,就是出於恥辱:因為他來自一個如此「不重要」的國家,「它的存在對世界沒有任何意義。」
不幸的是,對一個自知自覺的人來說,恥辱只能是一條單行道,最終也只會來到一個死胡同。所以蕭沆才會說:「我恨過自己的國家,恨過所有的人,恨過整個世界:到最後,唯一剩下可恨的,就只有我自己。」
•
儘管蕭沆很快就會為自己的「羅馬尼亞版納粹黨」這一言論感到懊悔,他卻從未軟化過對自己國家的偏見,直到去世那天仍在藐視她。
所以當初一有機會,他就奔向法國。此後他努力營造的公眾形象是個無祖國可歸、無同胞可靠的文化流浪者。但他並沒有為此感到困擾,反而覺得自己的新處境充滿了吸引力,甚至很有必要:「思想者因那些從他身上離開的和奪走的而充實。
如果他碰巧失去自己的祖國,那更是橫財一筆!」
•
於是史上最傑出的一場「變形記」在巴黎上演了:蕭沆從一名有潛力的羅馬尼亞辯論家變成了一位一流的法語作家。
要達成這一轉變,他首先必須擯棄自己的母語──那個「陽光與糞便的混合物,充溢著對醜惡的緬懷、對骯髒的稱頌。」
所以,當整個歐洲都致力於阻止、加入或效仿納粹勢力時,蕭沆卻不亦樂乎地忙著一個字一個字地重塑自己。他靠「喝咖啡、抽香菸、查字典,寫出一個個勉強像樣的句子」,以此來提升自己的法文水準。他深知,「一個人拋棄自己的語言去選擇另一種,就會改變自己的身分,甚至改變讓自己失望的原因。」
顯然,對蕭沆來說,不論身為一名法語作家會帶給他怎樣的失望,也不及陷於「一種文化菁英要麼不知要麼不屑的語言」那麼失望。
•
在初到巴黎的日子裡,蕭沆賴以謀生的只有一份微薄的研究生獎學金。至於獎學金所資助的那篇博士論文,他連筆都沒動過。那不過是個藉口罷了,以便他在事態變得血腥時──也就是說,當他在《羅馬尼亞變形記》中大力宣揚的觀點開始成真時──及時逃離他那個即將成為大屠宰場的祖國。
所以他在巴黎到處混吃混喝──學生餐廳、熟人家裡,甚至是當地向窮人分發食物的羅馬尼亞教堂。最後這處想必不是他的第一選擇;他一直極其反感基督教(或許這與他的父親是牧師,而母親又是基督徒女性組織的領袖不無關係)。但他別無選擇,因為那時他一貧如洗,又擔心被驅逐出境。他甚至在納稅申報單上虛報更多的收入,以免引起逃稅的誤會,被法國政府趕回羅馬尼亞。
那幾年,發生在蕭沆身上最幸運的一樁事無疑就是在學生餐廳裡遇到了布韋(Simone Boué)。她正是這位窮困潦倒的憂鬱症患者急需的:一位忠誠謙和的夥伴,願意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為他的一生提供所需和照料。
•
當蕭沆第一本用法語寫作的書在一九四九年面世時,他已經三十八歲,在法國待了十二年。
《衰亡短史》可說是一大勝利。它為作者贏得了評論界的讚賞,爭到了一個體面的文學獎項,讓他多年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更有甚者,它完成了蕭沆的自我重塑。
但在經濟層面上,這本書,以及下一本,甚至之後的每一本都對他毫無幫助。
他還要等將近四十年才能看到自己的著作產生市場效應。
所以在這期間,生活依然艱辛。或許這也是應該的。蕭沆是個標準的悲觀主義者,白天被厭世和懷疑困擾,晚上又受失眠和憂鬱症的折磨。這樣的人如果居於膏粱錦繡之中,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可信度?誰還會相信他那套陰鬱的想法?可能連他自己都無法接受。
好在布韋一直給予他堅定不移的支持,讓他得以繼續沉浸在悲觀主義之中,把他當成病獅一樣悉心照料,以便他能不時發出那種所有哲學家都夢寐以求、但只有極少數有能力實現的威吼。
因為蕭沆對社會習俗毫不在意,自然也從未考慮過婚姻。不過,為了避免「白頭偕老」這樣枯燥無味的結局,他倒是跟布韋認真談過,他們倆該趁著彼此都還年輕時,一起走上絕路。或許,對一名貨真價實的悲觀主義者來說,再也沒有比「同時自殺」這個更好的情人節禮物了。
無論如何,他們低調而貌似愉悅的同居生活仍然引出了一個小疑問。當他貶低愛情時,說它「偉大並且唯一的獨創之處就是把幸福和悲慘搞得難以區分」,是否腦海裡正想著某一對情侶呢?
•
至少在男女關係方面,蕭沆並不脫俗;這世上多的是一方為了另一方做出種種犧牲的感情。但是作為一名思想家,這位一向愛唱反調的作家是否又稱得上「獨創」?
答案可能會令他的崇拜者失望。蕭沆所受到的影響都非常明顯,包括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古希臘犬儒學者和詭辯學者,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法國道德家,以及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從叔本華那裡他汲取了絕望,把人生看作受苦受難,或許也初次接觸到了佛教思想。
從尼采那裡他學會了如何顛覆原則與論點,尤其那些被視為最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觀念,包括宗教信仰、正義和道德倫理。從犬儒學派那裡他繼承了對舒適和愉悅的質疑及蔑視;從詭辯學派那裡,他囊獲了懷疑主義,以及所有的修辭手段。
從法國道德家那裡,他抄襲了他們的散文風格。也許這是蕭沆作為思想者最明智的一個選擇。他模仿的風格非常純粹,讀起來總是優雅精簡,即使作品空洞無物。
至於史賓格勒,蕭沆吸取的是文化誕生和最終死亡的理念。只不過他依照自己的一貫作風,把這想法弄得更加悲觀:
一切都表明,人類已經到達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地步。即使我們將目睹其他文明的誕生,它們也絕不及古代文明,甚至現代文明,更不要說它們終將不可避免地淪入相同的下場。
要是有人指責蕭沆缺乏獨創性,他可能只會聳聳肩膀。「我沒有創造過任何東西,」他曾經宣稱,帶著談論自己時常有的那股謙遜和冷漠,「我只充當了自己感覺的祕書。」
•
蕭沆對警句的依賴無疑是讓他從同行中脫穎而出的一大特點。雖然不少哲學家也涉足這種形式,但沒有一個像他一樣專門致力於此。甚至可以說,就連他那些篇幅較長的文章,也不過是一些「警句選集」,連接了許多相關題目的句子。
但蕭沆為什麼要堅持用這種形式寫作?畢竟,受長度所限,警句無法提供解釋哲學立場所需的文字空間。它唯一能展現的,是急智和敏思。
答案可能是,年輕時長篇大論地犯了錯、出了醜,他不自覺地質疑所有思想體系,無論這些體系的出發點有多理想。「本質上說,每個觀點都是中立的,或應該是中立的,」蕭沆曾這樣解釋。
但人會賦予思想生命力,把自己的激情和缺點注入其中。這些思想也因而變得不純粹並進而轉為信仰,適時得到實踐,成為活生生的事件。邏輯推理到癲癇病發的路徑也由此形成。意識的形態、教義的信條還有致命的嗜好都如此誕生。
對於蕭沆這麼一個反正統思想者,擺脫這種僵局的唯一辦法就是採用隻字片語和自相矛盾的表達方式。簡言之,警句。
但他選擇這種寫作風格還可能牽涉到另一個原因。不論他有多貧窮或多勤奮,他在性格上最接近的模式,其實是「貴公子」(dandy),也就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在十九世紀稱讚過的那種時尚先鋒。他們對自己的形象、言行非常挑剔,觀點總要與眾不同,一味追求優雅,卻又拚命裝出一副沒有強求的樣子。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最靈敏的寫作方式無外乎警句;即便是談論痛苦和折磨,也要顯得輕描淡寫。
波特萊爾在描繪「貴公子式作風」時,形容它為一個「正在下沉的太陽;就像殞落的星星一樣,光輝燦爛卻沒有熱量,唯有憂鬱。」這裡預言的,不就是蕭沆這顆未來的隕星?
•
「就像其他人去上班一樣,我每天都去『懷疑』那裡報到」,蕭沆在自己的日記裡這樣寫到。
但他這種充斥著負面觀點的思想──老是不信任、不滿、不認同──永遠都只能迎合少數人的趣味。這也讓他承受了不少「投機取巧」的指控。畢竟,破壞永遠比創造容易得多,抱怨也比澄清輕鬆得多。
更不要說,一旦成為了警句家,他自然而然就和所有「傳統」的哲學家劃清界線,轉而與「貴公子式」的作家扯上了關係,比如尚福爾(Sébastien-Roch Nicolas Chamfort)和儒貝爾(Joseph Joubert)、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和拉.羅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這些都是出色的作家,文筆優雅、洞察入微,但沒有一個拿到過「思想家」的頭銜。也因為這樣,蕭沆的哲學地位才會搖搖欲墜。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恐怕只有蕭沆自己才能體會。他竭盡全力脫離一個在自己眼裡太過「邊緣」的國家,結果還是讓自己被排除在外。雖住在法國的文化中心,卻從未真正屬於過這裡。一向避世隱居的他,厭惡受到矚目,從不試著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也不想要哲學友人,更別提追隨者了。
但無論情況有多孤獨悲慘,這一切都源於他自己的安排。「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名先知」,他曾經不無諷刺地說,「只要他一覺醒,世上就多了一點邪惡。」這樣看來,蕭沆所面臨的這種「邊緣狀態」,可說是他作為思想者唯一謙遜的行為。
永遠置身局外,他才能繼續「詆譭全宇宙」(他自己的話),而又不造成更大的破壞。
•
拜老年痴呆症所賜,他很可能是世上第一個忘記「蕭沆」這名字的人。但他寫的那些警句,它們是否也有可能被遺忘?
曾經有位名叫本拿寶(Marcel Bénabou)的法國作家想出了一套製造警句的「法則」。這套法則非常簡單,只有兩部分:總是成對出現的對義詞(例如「罪行」和「懲罰」),以及警句中最常見的語法結構,例如:
(1)「甲」是「乙」其他形式的延續。
(2)「甲」如果不是「乙」,那它就不成其為「甲」。只要把成對的詞放入這些句子裡,就能生成無數的警句。以「罪行/懲罰」這對詞為例,我們馬上可以得出:
(1)懲罰是罪行其他形式的延續。
(2)懲罰如果本身不是一種罪行,就不成其為「懲罰」。
這些句子顯然不怎麼出色,但乍看之下似乎也夠深沉,甚至夠機智,足以迎合普通大眾。
這不是說蕭沆也採用了本拿寶的法則;實際上,他很可能完全沒聽過這套法則。再說,當本拿寶這篇半開玩笑的短論文出版時,蕭沆已經寫作了半個世紀。此外,他絕大多數的警句也不落入任何「基本」格式。要是他的手法那麼容易就能摸透,蕭沆也不會成為一流的作家。
然而,本拿寶的法則還是指出了一個問題:警句難逃膚淺。這不該令人驚訝,因為這種寫作格式多半是靠文字的巧妙運作來達成效果;傳達思想、隱含深意並不是它的主要目標。
蕭沆之所以偏愛這種格式,歸根結柢,是因為他無法把信任交給文字,尤其是哲學術語。他知道──正如蘇格拉底(Socrates)早就知道的那樣──言語其實是我們掩飾無知的最佳手段。只要讓一個人說上足夠久的時間,他遲早會被自己的話絆倒。
這也是為什麼蕭沆聲稱「能寫出警句的人都知道文字中隱藏的恐懼──那種和所有文字一起崩潰的恐懼。」既然這種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別忘了蕭沆是個頑固的悲觀主義者──何必要反覆測驗文字的脆弱性?長篇大論和簡要表述:這兩者真有區別嗎?
「一個人怎麼能成為哲學家?」蕭沆在走完自己三分之一的哲學生涯時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怎能蠻橫無禮地與時間、美、上帝還有其他種種要素對抗?思緒不知羞恥地膨脹、跳躍。玄學、詩歌──這一切不過是一隻跳蚤的非分之想罷了。」
•
「一本書可以像一場戰爭那樣偉大」,英國作家、政治家兼貴公子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認為,「有些哲學體系導致了一些重大的革命,甚至改變了我們社會和政治的形態。」
不消說,蕭沆的書沒有一本激起過變革,連示威都沒有。不過,除了《羅馬尼亞變形記》,他寫書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鼓勵任何起義。如此下功夫的事顯然不符合一名貴公子的形象。正如波特萊爾所說:
貴公子特有的美在於,骨子裡想要保持無動於衷的冷酷外表。這讓人想起暗火,極少有人察覺到它的存在。只要願意它就能爆發出所有的光亮,然而它並不願意。
「只要願意……然而它並不願意」:這恰巧道出了蕭沆的兩難境地。他知道自己不應煩憂,所有舉動都毫無意義,不過是徒勞無益。但他骨子裡的那名思想者,那位作家,甚至那個先知都無法從容冷靜。他們堅持要痛訴世上的一切悲憤、侮辱和嘲諷。
然而,在年輕時損毀了自己的名譽,他再也沒試過充任革命者,再也沒想過要改變歷史。他首選的位置是站在邊緣,坐觀成敗。心血來潮時,他也會舉起自己的那把文字步槍。他每一個精雕細琢的警句都像是一次目標精準的射擊,瞄準所厭惡對象的四肢,管他是上帝、生命的意義,還是充滿浮誇概念和複雜體系的哲學本身。
儘管他算得上是史上最好的玄學神槍手,他射擊的卻永遠只是他厭惡對象的四肢,因為他知道言語、思想或論點最終都起不了作用。它們無法消滅任何東西──即使到現在,人們仍然崇拜上帝,仍然在生命的荒誕之中尋求意義,仍然爭論那些早已被推翻的哲學體系。但蕭沆至少能借助自己機敏而尖銳的警句,讓這些可笑的東西遭罪,在地上拖著傷肢四處爬行,同時讓那些仍舊相信它們的人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