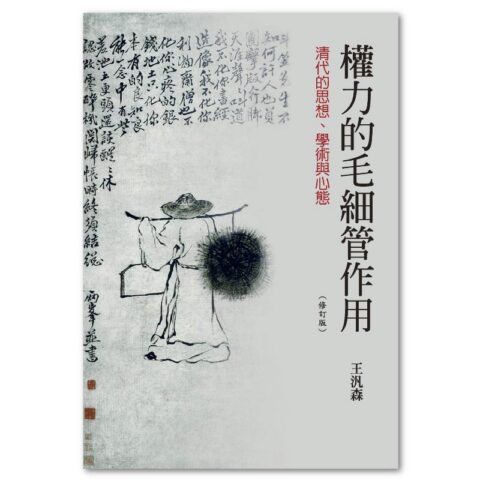「五四」一百週年 (思想37)
出版日期:2019-05-01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8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7cm
EAN:9789570852929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積累了什麼精神遺產?
200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五四」一百週年(思想37)》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本期還有「讀書人的古今遭逢」、「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等專欄。
※ 本書作者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
戴燕(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元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文碩士)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唐小兵(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
賴慈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
彭錦堂(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魏淑珠(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外文系)
馬國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兼任副教授)
李懷宇(出版人)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中國革命:「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王曉明)
現實與歷史的糾葛:內藤湖南的中國觀及其反響:百年後重讀《支那論》(戴燕)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兼談中國施特勞斯派的問題(朱元海)
余英時先生析論「五四」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唐小兵)
譯書人的古今遭逢
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李奭學)
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賴慈芸)
彭淮棟與所譯《浮士德博士》(彭錦堂)
彭淮棟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魏淑珠)
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
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馬國明)
金庸的晚年心境(李懷宇)
致讀者
致讀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
如余先生所再三強調的,「五四」精神在近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他指出,這個精神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即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或者批判的精神。五四的傳統一路發揮這種批判精神,在中國大陸鼓舞了歷次的民主思潮,在台灣則經由《自由中國》在思想上啟發了日後的民主運動。在海峽兩岸,它都確實是「真實的歷史動力」。
但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本土的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加上後現代與去中國化的潮流沖刷,五四在台灣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官方固然對五四的批判精神多所壓抑,即使在知識界,自由派批評五四的激進主義,保守派不滿五四的反傳統,「中國道路」論則否定五四的普遍主義,五四與這個時代彷彿失去了有機的聯繫。余先生的分析與論證兼顧政治與思想,旨在展現廣義五四運動的豐富內容,值得我們參考、反思。
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翻譯。在中文世界的文化積累中,來自翻譯的比重堪稱驚人,構成了我們文化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兩岸皆然,都不視翻譯為「正業」,無論物質的酬報還是專業地位的認可都遠遠不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投身翻譯,藉著引進另一個語種的文化精華為中文讀者開拓視野,自己也在嘔心瀝血的翻譯過程中發揮才情、文采、知識的儲備,尤其是跨文化的文化涵養,獲得了成就感。
在台灣,彭淮棟先生正是一位以翻譯為志業的有心人。他的譯筆精湛高雅,除了忠實轉達原文,往往還能引讀者含咏玩味,一些經典譯著在海峽兩岸乃至於華人世界擁有無數讀者。淮棟兄在去年去世,在本期,我們邀請到他的摯友彭錦堂、魏淑珠記述他的為人與譯筆,聊表紀念之意。我們也獲得李奭學、賴慈芸兩位分別撰文,探討翻譯史上的兩段故事。譯書人的遭遇極為多樣,本刊36期發表訓練先生的〈清河翻譯組蠡測〉,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或可與本期的文章對觀。
內藤湖南的史學著作非常知名,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著可觀的影響。他也是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次以記者身份或者受命於日本政府到中國調查,與中國政界的來往也稱頻繁。他所著《支那論》對於中國的國情與走向提出許多觀察與建議,即使在一百年之後,其獨特處依然值得參考。戴燕教授正在從事此書的中譯,先將所撰的譯本導讀交給本刊發表,對於內藤湖南的經歷、《支那論》的內容,以及生前身後幾代學者的回應與評論,做了細緻的梳理介紹,相信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我在海外也讀過一些介紹大陸思想動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發表的有關「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訴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評介各種「天下」論述的長文。(《思想》第36號,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證一些大陸來訪者述及的親身觀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一傾向使我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民主牆」的作者主要是體制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大字報中批判一黨專政並強烈要求民主,都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可見他們是「為民請命」,而不僅僅是表達了個人的政治思想。「民主牆」的衝擊力在當時是巨大的,引起各國記者的注視和報導,甚至鄧小平在未奪回領導權之前,也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人民用大字報表達不滿的權利是應當尊重的。(按:鄧取得領導權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案的。)所以「民主牆」通過對毛時代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為了挽救這一危機,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虛會」,由即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識形態,為鄧小平改革路線提供正當性。會議的最後成果是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一望可知,這正是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這個新意識形態在「務虛會」之後雖受到廣泛的傳播,但黨內黨外的批評也層出不窮,更由於它過於抽象,完全未能展現黨的最新動向,最後只有不了了之。從1979到1989的十年之間,不斷有人向黨提出新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這裡有一個不但有趣而且反映當時政治形勢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爆發的瞬間,趙紫陽在和鄧小平的一次對話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權威主義」。趙告訴鄧,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認為,「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必須掃除障礙,保持穩定,必要時不惜採取鐵腕手段……」話猶未畢,鄧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就是這個主張!」(見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0,我在此書〈序〉中特別討論了這一對話。)「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聚談最盛的論題,正是因為它差一點便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多數知識人,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正在發起「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以展開民主運動。「新權威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所得到的,是抨擊遠多於認同,否定遠多於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能提出「不問姓『社』姓『資』的要求」,用避而不談的方式暫時和緩一下意識形態的危機。
上面關於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興起密相關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二者之間的關聯,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五四」新文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處境。概括地說,鄧小平在復出奪權和掌權的過程中(大致是從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識形態以發揮雙重作用:第一、取代華國鋒所繼承的毛澤東路線,這是奪權的先決條件;第二、為他的「改革開放」的新路線提供理論根據,這是強化掌權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經指出,1979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這樣確立的。但是這一「實踐」主義雖然有效地摧毀了華的「凡是」主義(即「凡是毛主席贊成的我們都贊成;凡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都反對。」),卻不足以支持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開放」路線。後來新權威主義也曾得到鄧的擊節稱賞,然而官方始終沒有正式出面宣導過它,其地位還遠在「實踐」主義之下。可見1989年以前鄧在尋求新意識形態這件大事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我們更看到,1989年以後,他竟坦然採取了避而不談的消極態度。為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竟如此困難?讓我從歷史角度稍作推測。
首先我要指出:這十幾年中,「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為「五四」精神的回歸開闢了道路,「五四」時代所強調的普世價值,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觀念,頓時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訪問大陸,正值「思想解放」運動全面展開。當時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讀書無禁區」。這就表示,大批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之內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觸到的黨內人士往往將「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相提並論;並且很有信心地說,這次的「放」決不會落到「陽謀」的下場。我在11月回到美國之後,很快便有「民主牆」的崛起,遠遠超出「思想解放」的範疇了。「五四」精神在為下一段時期演出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贅說。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現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我們應該記得,1957年那個短暫的所謂「百家爭鳴」,便是由北京大學學生在5月4日發動起來的。這一天八千個學生開「五四」運動紀念會,十九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的迫害。他們還編印了一個名之為《民眾接力棒》的期刊,寄給全國各級學校,呼籲全體學生為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關於這一事件,參看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的講詞“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冊,頁 1490-1491)當時「黨天下」統治中國已八年之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適批判」之類的運動也已在全國範圍內深入而持續地進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澤東不顧黨內反對,一心一意要搞「鳴放」,是他深信知識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導向亂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些動盪,但是沒有引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必須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肅清了反革命。」見胡適上引文,頁1495)但他絕對沒有料到,「鳴放」的風聲剛剛傳出,「五四」精神便復活了。「陽謀」之說其實不過是事後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潛力,在此獲得清楚的印證。至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運動,從「思想解放」、「民主牆」到天安門結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籠罩之下,更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這裡唯一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知識人致力於「五四」精神的復活完全是自覺的,所以他們公開喊出了「回歸五四」或「重新啟蒙」的明確口號。(參看陳樂民(1930-2008)在《啟蒙劄記》中追憶李慎之的文章,《萬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改革開放時期不能發展出一個為「黨」所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動力,在共產黨內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僅限於經濟領域。但在改革過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發現:經濟體制的改革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政治體制;後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後雖在黨內保守派強烈反對之下,鄧小平終於接受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原則,並在1986年指定趙紫陽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接受了趙的報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內部的分歧也立即開始了。簡單地說,以胡、趙為首的改革派,由於其中往往有人和體制外的知識人互通聲息,傾向於參照西方體制以擴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黨專政的權力。另一方面,鄧小平雖號稱「改革總設計師」,但是他整體構想是通過經濟改革以強化「一黨專政」。自始至終他決無一絲一毫開放政權的意思。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討論學潮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調。例如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又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這兩段話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當時「五四」精神的影響,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徑。所以鄧才有此針鋒相對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