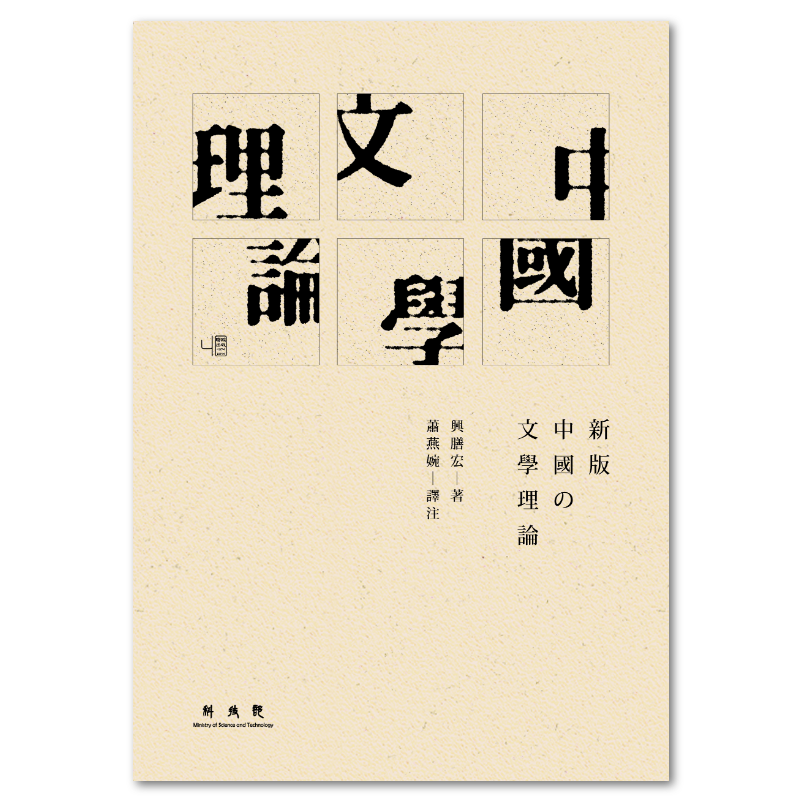中國文學理論
原書名:新版中國の文學理論
出版日期:2014-12-24
作者:興膳宏
譯注者:蕭燕婉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4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4917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已售完
享譽國際的六朝文學研究學者──興膳宏
聯結東亞文學理論傳統與文化傳承的權威之作
為「龍學」注入活水的新視野
為「詩品」延伸藝評淵源的新觀點
《中國文學理論》是興膳宏集結二十多年來,關於魏晉南北朝至中唐文學理論的專論,若要對魏晉南北朝的作家、詩文、文學理論有全盤性的了解,這部深具學術價值的專著為必讀之傑作。這部專著奠定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基礎,也誕生了眾多饒富特色的文學理論。綜觀本書,每篇論文都與《文心雕龍》、《詩品》緊密相扣。興膳宏把書名冠以「中國文學理論」,是對《文心雕龍》與《詩品》二書的定位,深具企圖心的嘗試。《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已無庸再論,然興膳宏的論述更為「龍學」研究錦上添花。劉勰在主張文章創作的要諦必須回歸儒家經典,而作者以精闢的論證,回歸劉勰本源的思維形式當中,分析除了儒教之外,佛教與老莊思想亦潛藏其中。同時他又以中日文化交涉的比較文學的角度,檢視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藉此探索《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如何跨越國境在日本人之間傳播,又如何成為當時東亞文化共同的知識體系與文學淵源。
對於帶給宋代文學批評之主流的詩話極大影響的《詩品》研究方面,作者首度嘗試從詩、畫等藝術領域找尋其品評的淵源,在比較《文心雕龍》與《詩品》後,發現鍾嶸的評論角度不同於劉勰,相較於劉勰,鍾嶸更重視奇拔的表現與「氣」的充實。由於興膳宏具敏銳的洞察力,加上他能從文學與宗教、中日文學交流等宏大的角度進行研究,所以,本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不僅呈現出異於以往的嶄新意義,也讓我們看到,作者如何成功賦予這兩部六朝文學理論雙璧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本書及《中國文學理論的開展》等一系列以《文心雕龍》與《詩品》為主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專著,獲頒「日本學士院賞」,足見其研究成果已在日本學術界得到最高權威的肯定,更凸顯本書中譯本的必要性。
作者:興膳宏
1936-,日本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院,並受教於吉川幸次郎與小川環樹兩位教授。興膳宏於1986年出版的《文心雕龍》翻譯,是日本最早完成這部博大精深的文學理論之全譯本。他於1989年以《中國文學理論》一書取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擔任愛知教育大學、名古屋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院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講座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院院長。2000年於京都大學退休,獲頒京都大學名譽教授,2001年出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2013年,以《中國文學理論》(清文堂,2008)、《中國文學理論之開展》(清文堂,2008)等一系列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專著,獲頒「日本學士院賞」。
譯注者:蕭燕婉
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副教授。九州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日中比較文學、江戶時期女性文學。著有〈日本?紹介???『?園女弟子詩選選』????〉、〈袁枚?女弟子屈秉筠?蕊宮花史圖????〉等論文,譯有興膳宏《中國的文學理論》(聯經出版)。
導讀 興膳宏《中國文學理論》之定位:從中古文學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
Ⅰ
六朝時期文學觀的發展:以文體論為中心
Ⅱ
從文學理論史的角度看〈文賦〉
摯虞《文章流別志論》考
論〈宋書謝靈運傳論〉
Ⅲ
《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二者的內在關係
《文心雕龍》的自然觀:探本溯源
日本對《文心雕龍》的接受與研究
Ⅳ
關於《詩品》之我見
《詩品》與書畫論
《文心雕龍》與《詩品》文學觀之對立
Ⅴ
《玉臺新詠》成書考
顏之推的文學論
王昌齡的創作論
《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
《古今集》真名序紀要
後記
寫於新版之後
興膳宏教授年表
興膳宏教授著作目錄
興膳宏教授中文論著暨中文譯著
中譯導讀(節錄)
興膳宏的《中國文學理論》,每篇論文都與《文心雕龍》、《詩品》緊密相扣。譯完此書之後,深覺興膳宏把書名冠以「中國文學理論」,可謂一項企圖心頗強的嘗試。因為,《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已無庸再論,而興膳宏在研究「龍學」上的貢獻,莫過於其論證告訴了我們,劉勰主張文章創作的要諦必須回歸儒家經典,而回歸本源的思維形式當中,除了儒教之外,佛教與老莊思想亦潛藏其中。同時他又以中日文化交涉等比較文學的角度,檢視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藉此探索《文心雕龍》等中國的文學理論如何跨越國境在日本人之間傳播,又如何成為當時東亞文化共同的知識體系與文學淵源。
至於帶給宋代文學批評之主流的詩話極大影響的《詩品》研究方面,作者首度嘗試從詩、畫等藝術領域找尋其品評的淵源,接著在比較《文心雕龍》與《詩品》後,發現鍾嶸的評論角度不同於劉勰,因為鍾嶸更重視奇拔的表現與「氣」的充實。由於興膳宏具敏銳的洞察力,加上其從文學與宗教、中日文學交流等宏大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所以,本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不僅呈現出異於以往的嶄新意義,我們也看到作者成功的賦予這兩部六朝文學理論的雙璧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
本書第五章〈《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二者的內在關係〉,乃興膳宏研究龍學的代表作。本章興膳宏以《出三藏記集》為焦點,用了長達一百二十頁的篇幅,細繹窮究《文心雕龍》與佛教既深層又幽微的內在關係。他認為從表面上看,《文心雕龍》受儒家的影響最大,而佛教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是在邏輯方法上,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本章的第一至第六節,興膳宏把《出三藏記集》當近景,《文心雕龍》當遠景,剖析兩者的關係。首先論證《出三藏記集》並非出於僧祐一人之手,事實上劉勰也參與了《出三藏記集》的撰述。接著從語義的角度出發,發現了《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的〈總序〉,皆把「原」字當動詞、「源」字當名詞來使用,而且,是有意的在區分這兩個字的用法。同時,這個現象與劉勰〈滅惑論〉是共通的。此外,又從文章的理論結構出發,考證《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總序〉的相似處。作者分別舉《出三藏記集》〈總序〉中一個例子和《文心雕龍》中「六義」、「三準」、「八體」、「四對」等七個例子,分析這些文章皆具有分析性的理論結構,同時又從《南本涅盤經》中舉出四個例子,證明這種文章結構,不僅與佛典契合,慧遠的文體,亦如出一轍。
《出三藏記集》中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主要在敘述佛經翻譯的歷史,同時也是中國最早的翻譯理論。興膳宏指出〈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的「半字」、「滿字」之概念,脫胎自《涅槃經‧文字品》,而《文心雕龍‧練字篇》的「半字」,實與〈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出自相同的本源。而且,就語言現象的方法論而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與〈滅惑論〉、《文心雕龍‧練字篇》在論述「音訛」、「字訛」的方法時,也有共通的現象。
在第七至第九節,繼續把論述焦點轉移到《文心雕龍》,再度確認了劉勰強調文學必須回歸經書的主張後,作者指出在理論結構上,《文心雕龍》前半部的〈明詩篇〉、〈詮賦篇〉、〈論說篇〉與後半部的〈章句篇〉、〈附會篇〉都用了「回歸」的理論。然後,又找出「原始要終」、「沿波討源」等重要的關鍵詞,說明這兩個關鍵詞,除了象徵《文心雕龍》的基本原理,也是「回歸」理論的主要旋律。於是,沿著這條線索,興膳宏繼續檢討了《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的序文與《出三藏記集》〈緣記〉、〈名錄〉、〈經序〉、〈列傳〉的編輯方針,發現了「回歸」的理論,亦貫穿在整部《出三藏記集》之中。此外,又聚焦僧祐的其他著作,發現僧祐在他的《釋迦譜》與《法苑雜源原始集》的序文中再三地流露其對「回歸」理論與「原始要終」的關心。最後,則反思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背景,發現當時玄學與佛學合流,許多文人的思想基礎雖然以儒家為主,但是,釋、道的思想,在其身上也是統一並存的。因為,劉勰的〈滅惑論〉,就清楚地展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不過,《文心雕龍》是劉勰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寫的,只是佛教思想在論述方法與嚴密的邏輯體系上,悄然地發揮了潛藏的作用。
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興膳宏對佛學的深厚學養,故能利用劉勰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僧祐的《釋迦譜》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及〈阿毗曇心序〉等等諸多佛教典籍,詳盡的整理出《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幽微的內在關係。另外,此文也提示了不少具啟發性的觀點,例如在推論劉勰的出家時間與動機時,興膳宏注意到對劉勰而言僧祐是宗教世界的象徵,昭明太子是文學世界的象徵,其一生的精神世界,一直在兩者之間擺動;另外,更指出劉勰有著根深蒂固的「孔釋一也」之思想,而這也是當時六朝崇佛者的普遍思惟。不難發現,本章的論證,成功的結合了中國的文學理論與宗教史、文化史等範疇,這項嶄新的嘗試確實讓《文心雕龍》的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興膳宏還有一個令人欽佩的研究成果,他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長達一千兩百頁以上的弘法大師空海的《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譯注,繼而開始一連串《文鏡秘府論》的相關研究。
唐德宗二十年(八○四年),空海擔任第十六回遣唐使抵達中國長安,兩年後回到日本。空海編輯的《文鏡秘府論》,完成於日本弘仁年間(八一○─八二三),分為天、地、東、南、西、北六卷,裡面收錄了晉陸機的〈文賦〉,從譯文上看,可知與傳本《文選》當屬不同版本,另外還有梁沈約的《四聲譜》、隋劉善經的《四聲指歸》、中唐皎然的《詩議》等許多重要的詩文創作理論,其中「對偶」與「聲病」是《文鏡秘府論》最重要的兩大理論支柱。空海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把這些中國的創作理論介紹到日本,使日本的漢詩文創作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日本學者比中國更早著手《文鏡秘府論》的考證、註解與研究工作。興膳宏之前,小西甚一 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陸續出版了《文鏡秘府論考》之〈研究篇〉上、下 與〈考文篇〉。對《文鏡秘府論》的成書年代、撰寫緣由、引用原典、與《文筆眼心抄》的關係做了有系統的分析研究。在中國方面,十九世紀末駐日公使館員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介紹了《文鏡秘府論》在資料上的價值後,中國學者便開始注意到此書,爾後,陸續出版了幾部校注。例如,周維德校點《文鏡秘府論》、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 等,王利器校注本堪稱中國最詳盡的注本。
興膳宏《文鏡秘府論》的譯註出版於王利器校注本之後,但興膳宏仍可在王利器校注本的基礎上找到許多原典的出處,例如,查到〈地卷十體〉「七飛動體」所引「月光隨浪動」出自梁劉孝綽〈月半夜泊鵲尾〉。其譯註引證之詳實殊為難得。
本書第十四章〈《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興膳宏指出《文鏡秘府論》中,明顯反映出《文心雕龍》理論的,只有劉善經的《四聲指歸》與《文筆式》等隋至初唐的作品。雖然,皎然的《詩議》或者王昌齡的《詩格》也有部分內容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但是他們相異的地方卻更多。尤其是《詩議》、《詩格》的文章風格比較類似後來的詩話,與《文心雕龍》的文體有著相當大的隔閡。興膳宏比較了空海作於留學唐代後的《性靈集》與留學前的《聾瞽指歸》(七九七年,自唐返國後,改名為《三教指歸》),發現空海的詩在留學唐代以前有許多地方未能符合唐詩的聲律規範。而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在七五一年成立的日本漢詩集《懷風藻》,然而,到了第九世紀的唐風謳歌時代,由於日本漢詩人已積極從空海編纂的《文鏡秘府論》中消化唐代的文學理論,因此收錄於《凌雲集》(八一四年)、《文華秀麗集》(八一八年)的漢詩,對聲律、平仄規律的認識,已明顯地提高,而且,七言詩大量增加,足見《文鏡秘府論》對日本平安時代漢文學的影響及意義十分重大。
無庸置疑,《文鏡秘府論》是研究中國中世文學最重要的資料書,因為,其保存了中國已經亡佚的中唐以前論述聲韻與詩文作法的大量文獻。例如,閱讀《文鏡秘府論》南卷的〈論體〉、〈定位〉,我們可以了解《文心雕龍》以後文章的風格論、鎔裁篇的理論有了何種進展。要釐清六朝至唐的文學理論,許多地方皆需利用《文鏡秘府論》。若從日本文學史的角度而言,《文鏡秘府論》不僅奠定了日本漢詩文的基礎,其影響還及於日本的和歌。
綜上所述,興膳宏的《文鏡秘府論》譯註雖然不是先驅,但其在《文鏡秘府論》的研究課題與問題意識的開拓上,卻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例如,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中,王昌齡的《詩格》如今已成為常識,而這是興膳宏在譯註《文鏡秘府論》的過程中首度發掘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他還意外地發現了《文鏡秘府論》北卷的〈帝德錄〉帶有駢體文寫作指南之性質。因此,其對《文鏡秘府論》的研究,不僅具有集里程碑之大成的意義,在《文鏡秘府論》對日本文學之影響的研究方面,亦有篳路藍縷之功。
方才稍微提到《文鏡秘府論》的影響亦及於日本的和歌。以下,請容譯者贅述一些日本古典文學史的基礎知識。奈良時代的《萬葉集》(八世紀後半成立?)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平安時代的《古今和歌集》(905年成立?)為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在日本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古今和歌集》卷首收錄了紀貫之的〈假名序〉,主要闡述和歌是與漢詩對等的文學,意味著作者已有深刻的和歌詩人之自覺意識,此篇假名序亦是日本和歌史上文學理論的先驅,具有極高的價值,對後代影響深遠。假名序之後,各卷的編排順序如下:春(上、下)、夏、秋(上、下)、冬、賀、離別、羇旅、物名、戀(一─五)、哀傷、雜(上、下)、雜體、大歌所御歌。卷末為紀淑望的〈真名序〉。而上述的分類、卷數,皆成為後代敕撰和歌集的典範。敕撰和歌集自平安朝《古今和歌集》以後至室町時代奉後花園天皇之命編纂的《新續古今集》(一四三九年)為止,大約維持了五百三十年的傳統。此後,雖不再出現敕撰和歌集,但《古今和歌集》的歌風一直是和歌的主流。所謂「古今調」的歌風,指優雅的、纖細的、抒情的「女性風(たおやめぶり)」,與其相對的則是率直、樸素的「萬葉調」歌風,「萬葉調」歌風又稱「男性風(ますらをぶり)」(江戶時代國學者賀茂真淵評)。
歷來,探討《古今和歌集》中的假名序、真名序與漢文學之關係者,大多是研究日本古典文學的學者。例如,小西甚一的《文鏡秘府論考》、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學と中國詩學》、小澤正夫的《古代歌學の形成》、藤原克己的〈古今集歌の日本的特質と六朝・唐詩〉等等。而出自中國學者的研究有森野繁夫的〈六朝・唐詩と王朝和歌〉。
興膳宏在本書第十五章〈《古今集》真名序紀要〉中,以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立場出發,將《古今集》的真名序,置之於漢語文章表現與六朝文學理論的脈絡上做了有趣的分析。指出儘管真名序作者努力把其習得的中國文學理論消化成自己的理論,然在說明「六義」的理論構造以及在「歌仙」的語彙運用上,仍出現了與中國的文學理論不協調之處。並且,興膳宏透過《日本國見在書目》,發現真名序作者可能也涉獵了《古今書評》等書。這一點則是前輩學者未曾指出過的。由此不難看出興膳宏企圖藉由《古今集》真名序的解析,照射中國的文學理論、書論,於平安時期在日本受容與變容之情形。
當然,當興膳宏勾勒出中國、日本之間透過空海等留學僧往來所形成的書籍流通網與知識傳播網後,一群東亞社會菁英(中國六朝文人、貴族官僚、日本僧侶、和歌詩人等)所共有的知識結構,也自然的浮現在我們眼前。
興膳宏在此確實為我們拓展了研究中國中世文學理論方法的新視點。或許國內的學者也可以嘗試以和漢比較文學的角度,重新為六朝文學理論的傳播與影響作進一步的研究突破,例如,日本人在《萬葉集》中對漢詩的攝取與《古今和歌集》中對漢詩文的受容有何差異?亦或後來的《新古今集》(1205年成立)、《續古今集》(1265年成立)、《風雅集》(1349年成立)等敕撰和歌集的〈真名序〉與中國中古的文學理論有何關聯。諸如此類,皆是有待後來學者去積極挑戰的新課題。
譯者認為興膳宏《中國文學理論》與上述諸書相較之下,其中所突顯的意義,在於作者建立了有系統的理論架構,為我們從歷史文化的時空脈絡中,清楚地勾勒出六朝重要的文學理論〈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從產生、傳播乃至於影響的整體圖像。同時,透過劉勰、僧祐與空海相互影響關係的具體呈現,讓我們連帶觀看到中國與印度、日本之間的知識系譜與文化、書籍之移動路線。
再者,本書另一重要的意義則是興膳宏帶入了大量佛教的資料,讓我們認識到悉曇文字對謝靈運與劉勰的影響,悉曇的研究如今已大有拓展,對佛教研究者而言實為常識,但興膳宏以文學的角度出發,說明中國詩學的重要命題「聲律」之濫觴,亦建築在文化撞擊的脈絡上。此外,如《文心雕龍》在邏輯結構上受到佛教極大的影響,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的〈歸心篇〉專論佛教信仰的問題,稱釋迦的「辯才智慧」勝過堯、舜、周公、孔子等中國聖人等等;興膳宏於論述之間提示了我們不該拘泥於過去傳統所謂的「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想法,因為,實際上中國南北朝時代的知識分子受佛教的影響是比其他時代都來得大的。簡言之,本書不同於以往僅停留在文學理論的框架中去探討中國的文學理論內涵,而是綜合了文學傳播史、宗教史、藝術理論史等多元的角度,去深究中國中古文學理論的專著。
《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兩者的內在關係
一
眾所周知,《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與佛教的關係深厚。《梁書》本傳(〈文學傳〉下)等曾經提到了劉勰與佛教的關聯,內容大致如下。
劉勰早年喪父,然生性好學;家貧不能成婚,故投靠當時的高僧僧祐,在僧祐的指導下,篤志勤讀。僧祐是南朝齊、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住在建康郊外的定林、建初兩寺,慧皎《高僧傳》明律之部有僧祐的列傳,稱他尤其長於律學。或許僧祐發覺了年少的劉勰才能非凡,故領養了他。十餘年來,劉勰在僧祐身旁,致力專研學問,終於成為博學多聞的佛教學家。成為佛教學家後,劉勰灌注了全部的精神製作佛教典籍目錄。《梁書》只記載了:「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卻沒有指出劉勰編輯之書的書目為何,後來經過考證,推測劉勰所編的可能是《出三藏記集》,而《出三藏記集》的作者,署名為劉勰的業師僧祐,成書年代比《文心雕龍》還晚。另外,《高僧傳‧僧祐傳》:「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集)》、《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上述諸書,皆著錄於《出三藏記集》卷十二,而劉勰則是編輯此書的重要人物之一!
梁天監初期,劉勰的《文心雕龍》得到沈約的賞識後,開始聞名於世,劉勰因此步上仕途,他以奉朝請起家,兼中軍臨川王蕭宏的記室,後來累官至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臨川王蕭宏,是梁武帝的異母胞弟,蕭宏非常尊重僧祐,對僧祐「崇其戒範,盡師資之禮」(《高僧傳‧僧祐傳》)。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收入《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總第九輯,1979,以下稱《新箋》)的考證指出,臨川王蕭宏因為經常出入僧祐的住所,所以認識了劉勰,蕭宏欣賞劉勰的文辭之才,故任命他掌文翰的記室。
劉勰曾經擔任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當時他建議南北二郊的祭祀,應該仿效七廟的祭祀法,供品必須廢除牲畜而改採蔬果。這個建議後來被篤信佛教的武帝採納。楊明照曾據《梁書‧武帝紀》及《通典‧禮部》作了考證,認為劉勰上表的時間在天監十八年(519)以後(《文心雕龍校注》附〈梁書劉勰傳箋注〉,以下稱《舊箋》),然而,後來楊明照在《新箋》作了修正,推定上表時間應該在天監十七年八月以後。
劉勰於天監年間,大部份是離開寺院,過著世俗般的生活,不過,他與佛教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梁書》:「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撰文」。可見劉勰一生撰寫了不少的碑誌。可惜這些碑誌大多失傳了,以下依照年代先後順序,列舉劉勰殘存的作品。劉勰著有卒於齊永明十年(492)的釋超辯碑銘(《高僧傳》卷十二〈釋超辯傳〉)、卒於延興元年(494)的僧柔碑銘(同書卷八〈僧柔傳〉),這些是劉勰的初期作品;而後者僧柔的碑銘又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集雜記銘目錄〉著錄的〈僧柔法師碑銘一卷〉。後期之作有卒於梁天監十七年(518)的業師僧祐碑銘(《高僧傳》卷十一〈僧祐傳〉)。此外,寺廟碑銘有〈鍾山定林上寺碑銘〉與〈建初寺初創碑銘〉(均著錄於〈法集雜記銘目錄〉)。以上皆只傳其名,而現存唯一的碑銘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參照第十一節),《藝文類聚》卷七十六〈內典上〉收錄了此碑銘的部分內容,全文則收錄在宋‧孔延之編《會稽掇英總集》卷十六。除了碑誌以外,劉勰還有一篇駁斥道教對佛教攻擊的〈滅惑論〉,〈滅惑論〉收錄在僧祐編纂的《弘明集》卷八(參照第六節)。
劉勰晚年奉敕命與僧慧震(傳不詳)一起於定林寺整理經典,此項任務結束後,劉勰突然決定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可見劉勰下了很大的決心。得到梁武帝的許可後,劉勰就把名字改為法名慧地,長年在他住慣的定林寺中,過著沙門生活。劉勰年輕在僧祐身邊時,一直維持著居士的身分,十多年來,都不曾決定出家,為何到了晚年步入仕途之後,才突然想要遁入空門?這件事直到目前都還是個謎。《梁書》指出「未朞而卒」,也就是劉勰出家後不到一年便過世了。
范文瀾首先推定劉勰從出家到死亡的時間大約在普通一年至二年之間(520-521)(《文心雕龍註》卷十),後來,海內外的學者也幾乎認為劉勰卒於此時。又楊明照在《舊箋》中,主張劉勰於普通二年至三年之間出家。推測的證據雖然不是很明確,但是,劉勰的老師僧祐,以七十四歲的高齡,於天監十七年(518)五月二十六日去世。這件事的確有助於我們推測劉勰的出家時間。因為,對劉勰而言,僧祐是他畢生心靈的支柱,如今突然逝世,這個衝擊或許使得劉勰必須對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出家問題作出決定。
可是,這種說法會有一個問題。楊明照《舊箋》見解,本范氏之說,現在將其主張製成表Ⅰ。由此表可知,天監十八年(519),劉勰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同年或第二年的普通元年(520),劉勰奉敕命於定林寺整理經典,任務結束後,於普通二年至三年(521-522)之間出家。顯然,他晚年的三、四年,十分忙碌。然而,整理大部經卷的工作,是否能在簡短的一、二年內就能完成則是個問題!
實際上,關於劉勰的出家問題,還有一種說法,只是歷來都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這種說法,見於後來南宋‧志磐的《佛祖統紀》卷三十七(《大正藏經》卷四十九),志磐把劉勰出家的時間大幅度延後至大同四年(538),不過,其所持的根據不詳。以下,列舉部分相關內容:「通事舍人劉勰,雅為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中提到了劉勰與昭明太子的關係,《佛祖統記》指出,昭明太子死於大同三年。由於昭明太子不僅愛護劉勰,對劉勰的文學也有深刻地理解,故會讓人聯想到劉勰的出家可能與昭明太子之死有關。
可惜遺憾的是,要就此承認《佛祖統記》的說法,仍存在著一個難題。因為《梁書》、《南史》等較為可信的記載指出,昭明太子病死於中大通三年(531),並非大同三年。元‧念常撰《佛祖歷代通載》,本書內容要旨與《佛祖統記》接近,《佛祖歷代通載》卷九(《大正藏經》卷四十九)與《梁書》一樣主張昭明太子卒於中大通三年,同時還指出劉勰亦卒於這一年。這或許是作者念常把劉勰的出家與昭明太子之死聯想在一起之故。如此看來,可能《佛祖統記》的作者,把中大通三年誤當成大同三年,將錯就錯之下,繼續推論劉勰在大同四年出家。又元‧覺岸撰《釋氏稽古錄》,《釋氏稽古錄》卷二(《大正藏經》卷四十九)指出劉勰在大同二年(五三六)出家,如此一來,劉勰出家動機,就與昭明太子之死沒有直接相關。不過,到底劉勰何時出家?《佛祖統記》與《釋氏稽古錄》的推論,皆比近代學者晚了十年以上。
昭明太子的晚年,未必是幸福的。由於他死後繼位的是其弟蕭綱,昭明太子的遺孤並沒有被冊封為太子,可見父親武帝對昭明太子的感情可能早就蒙上了一層陰影。立太子的問題,引起了種種議論,故讓相當重視感情的武帝極為煩惱。《南史‧昭明太子傳》:「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但是,這些優待措施並無法撫慰長子蕭歡等五位遺孤內心的創傷。其中排行第三的蕭詧,最無法壓抑內心的不平。據說他流涕拜命,因憂憤難解,多日未能進食。後來梁末發生動亂,蕭詧於侯景之亂時,竟成為敵國西魏的附庸,而這個悲劇的導火線,可能在其父昭明太子死後就埋下了。除了蕭詧,蕭詧的二哥蕭譽,也因為與叔父元帝對立,被指控為叛徒,遭到斬死;侯景之亂以後,廢了簡文帝,蕭詧長兄蕭歡之子蕭棟,曾一時被擁護為傀儡皇帝。總之,昭明太子死後,遺孤們的命運,紛紛捲入了反梁室的風暴之中。
昭明太子愛好文學,身邊不乏劉孝綽、王筠、殷芸、陸倕、到洽等文人。其中殷、陸、到三人先太子亡故;劉孝綽最得昭明太子信賴,太子去世時,他正在為母親服喪,不久,湘東王繹被解除諮議參軍的職位,離開了京都。曾經為太子書哀冊文的王筠,也被賦予貞威將軍、臨海太首之職,前往地方赴任。劉杳與劉勰同為東宮通事舍人,〈劉杳傳〉云:「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梁書‧文學傳》下)。此外,太子中庶子殷鈞、陸襄傳亦云:「昭明太子薨,官屬罷」(《梁書》卷二十七)。又東宮通事舍人何思澄:「昭明太子薨,出為黟縣令」(《梁書‧文學傳》下)。可見,昭明太子死後,平時與劉勰親善的文學集團就此瓦解,劉勰也無法向東宮求得自己應得的官職。
如果照《佛祖統記》及《佛祖歷代通載》的說法,昭明太子之死導致劉勰想要出家,那麼,劉勰應該是在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去世後不久就決定要出家了。而剛好長久以來整理佛典的工作終於結束,於是,更加深了劉勰出家的決心。
不過,也可以把昭明太子之死與劉勰開始整理經典這兩件事做一連結。楊明照《舊箋》指出,劉勰於普通二、三年出家,但是《新箋》中,楊明照大幅度地修改了以上的論點。他以《佛祖統記》劉勰於大同四年出家的觀點,指出劉勰可能在太子去世、舊臣紛紛遭到遣散之時,奉敕命整理佛教典籍。為了便於分析這個問題,筆者將「中大通三年出家說」(表Ⅱ)與「大同四年出家說」(表Ⅲ)作一表格,相互對照。李慶甲〈劉勰卒年考〉認為(收入《文學評論叢刊》第一輯,1978),據《佛祖統記》所見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劉勰應該於中大通三年出家,筆者也認為這種推論最為妥當。表Ⅲ的缺點在於從天監末至中大通年三年的十幾年間,都沒有記載劉勰的官職。楊明照認為這段期間,劉勰一直隨侍昭明太子之側。又楊明照還根據《梁書‧文學傳》所載,鑑於謝幾卿與王籍的傳記在劉勰的前後位置,他們卒於大同四、五年,加上合傳經常以卒年來排列順序之通例,故據此推測劉勰的卒年當如《佛祖統記》所載,在大同四、五年之間。
不過,既然從《梁書》及《南史》的本傳,無法歸納出劉勰出家與卒年的正確時間,那麼,楊明照的推論也可能成立。而楊明照在推論時,以《梁書‧文學傳》的排列法作為旁證資料。筆者並不認為《梁書‧文學傳》從頭到尾嚴格地遵守按照卒年先後排列列傳的原則。例如,在劉勰後面第二個人是何思澄的列傳,何思澄在昭明太子死後沒隔幾年就去世了(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作何思澄卒於中大通四年),而顏協(顏之推之父)卒於大同五年(539),他的列傳,竟置於侯景之亂(549-)前後去世的庾仲容、陸雲公、任孝恭等人的列傳之後。由於《南史‧文學傳》中劉勰與何思澄的列傳相鄰,故如果以楊明照之矛攻其盾,也可以推定劉勰卒於中大通四年(532)。若把《佛祖統記》或《佛祖歷代通載》的記載,當成考證資料之一的話,筆者認為,儘管劉勰出家與昭明太子之死有關只是一種推論,但是,這個推論卻相當值得重視。
綜上所述,劉勰出家和死亡時間,可能有三種假設。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劉勰出家的動機可能與師僧祐或昭明太子之死有關。簡而言之,假如對劉勰而言,僧祐與昭明太子分別象徵宗教世界與文學世界,那麼,劉勰的精神經常在這兩個象徵中不停地來回擺盪。也就是劉勰的生命與功業,是在宗教和文學兩個世界(後者帶有世俗世界之觀感)的擺盪之中留下重要足跡的。決心出家,可能意味著劉勰將終止這種精神上的擺盪,換言之,他要脫離文學世界,將整個人委身於另一方的宗教世界。
二
劉勰一生與佛教的關係很深,他精通內典,又撰寫了很多寺塔、名僧的碑誌。不難想像,劉勰的經歷會對其文學理論《文心雕龍》產生影響,使其帶有佛教的色彩。《文心雕龍》在中國的文學理論中,具有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體系,而且《文心雕龍》的背後,也流露著異於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世界。因此,就這個意義而言,近來許多學者皆致力探討佛教帶給《文心雕龍》的影響。
然而,不巧地,這裡出現了極大的阻礙。楊明照在《文心雕龍校注》卷末附錄了歷代諸家批評,其中清代的史念祖就說:「《南史》本傳稱其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是固寝饋於禪學者也。顧當摛藻揚葩、群言奔腕之際,乃能不雜內典一字。」(《俞俞齋文稿初集‧文心雕龍書後》)
史念祖指出,要從《文心雕龍》中,找到屬於內典的語彙是很難的。楊明照於此處加注:「按〈論說篇〉用般若字」,可見,史念祖忽略了佛教用語「般若」, 雖然後面我們還會引用《文心雕龍》中可能與佛教有關的詞彙。但是就《文心雕龍》的整體方向而言,史念祖的意見是正確的。當然,一開始我們或許想嘗試從語彙來探討《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的話,馬上會有一種侷限性,故不宜拿這個方法作為決定性的手段。
相對的,范文瀾嘗試以《文心雕龍》全書的構思,探討佛教思想帶給《文心雕龍》的影響。范文瀾考證第五十章〈序志篇〉的「文心」一詞時,引用了慧遠的〈阿毗曇心序〉(《出三藏記集》卷十),序文一開始說:「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范文瀾認為這一節的內容,帶給書名「文心」某種邏輯上的啟發意義。慧遠的序還說了,《阿毗曇心論》的構成是:「始自〈界品〉,迄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因此,范文瀾據此主張《阿毗曇心論》與《文心雕龍》的結構十分相近:「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自〈書記篇〉以上,即所謂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謂問論也。蓋採取釋書方式而為之,故能鰓理明析若此。」
范文瀾的意思是說,《文心雕龍》第一章〈原道篇〉至第二十五章〈書記篇〉,相當於《阿毗曇心論》的〈界品〉,第二十六章〈神思篇〉至第五十章〈序志篇〉,相當於〈問論〉;同時范文瀾還強力主張,正因為有佛教典籍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劉勰條理分明的理論。王利器亦根據范文瀾的見解言:「印度佛學的進步的思考方法,對劉勰的治學方法很有影響」(《文心雕龍新書》〈序錄〉,1951,及其修訂本《文心雕龍校証》〈序錄〉,1980年)。此外,陸侃如、牟世金也繼承范文瀾的意見:「他學習了佛經分析理論的方法,使自己的論述也做到既深刻又明確」(《文心雕龍選譯》引言)。
范文瀾的理論雖然極富啟發性的意義,但是卻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因為范文瀾把慧遠序中的「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解釋為由〈界品〉與〈問論〉組成的二百五十偈,然而事實上,按照字面的解釋應該是自〈界品〉至〈問論〉,總共有二百五十偈,換言之,整部《阿毗曇心論》是由第一章〈界品〉至第十章〈問論〉所組成。為了慎重起見,以下列舉僧伽提婆、慧遠共譯的《阿毗曇心論》(《大正藏經》卷二十八)所有篇名:一、〈界品〉二、〈行品〉三、〈業品〉四、〈使品〉五、〈賢聖品〉六、〈至品〉七、〈定品〉八、〈契經品〉九、〈雜品〉十、〈論品〉,《阿毗曇心論》總共有十章。最後第十章在此作〈論品〉,不過,同書的另外譯本《阿毗曇心論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大正藏經》卷二十八)作〈問論品〉,而兩者的內容相同。如果,范文瀾誤解了慧遠序文的意思,那麼,《文心雕龍》與《阿毗曇心論》結構相同之說則有欠妥當。
儘管如此,筆者並不打算全盤否定范文瀾的意見。因為書名《文心》,非常特別,劉勰在〈序志篇〉中說了書名的由來:「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雇用之焉」。因此,「心」有總括文學的根本理論之意,言外之意,還透露出作者劉勰的自負。同時,劉勰的潛意識中,對慧遠〈阿毗曇心序〉的「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明焉」,有深刻的認識,所以,才會把著作名為《文心雕龍》!《文心雕龍》在第一章〈原道篇〉闡述文學的原理,裡面出現了很多次「心」。例如,論述人存在於天地之間的意義時說:「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讚美《易》的文言則說:「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論述古代聖人撰述的經典時說:「莫不原道,心已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這些「心」字都有「根本」之意。雖然先前指出,范文瀾的說法或許未必完全正確,但是,仍有許多地方值得充分探討。在考察《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時,我們還是能從范文瀾的意見中,得到一些啟發。
探索《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時,還必須注意《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大正藏經》卷五十五〈目錄部〉)。因為,劉勰對這部典籍有正面的貢獻。劉勰極可能在《出三藏記集》中補充自己的意見,因此,若從《出三藏記集》來研究《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或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與其茫然地檢討《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不如以劉勰為媒介,然後一一探討各別具體的問題,自不待言,如此一來,問題意識會更加明確。基於這個立場,筆者將於下一章討論《出三藏記集》。
三
《出三藏記集》的「出」,意思是「翻譯」;故《出三藏記集》的意思是譯成中文的「三藏」,也就是本書是由經、律、論三部分構成的佛教典籍綜合目錄。本書乃增補晉代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而成,是現存最早的佛經目錄;僧祐有許多著作,而完整地流傳至今的則有《出三藏記集》和《弘明集》十四卷(《大正藏經》卷五十二史傳部四)及《釋迦譜》五卷(《大正藏經》卷五十史傳部二)。雖然《出三藏記集》是佛經目錄,但不是一部只單純羅列佛典的書目。總之,此書對中國自漢至梁受到佛教何種影響作了詳細的考證,同時,本書也是有關翻譯佛經基本資料的集大成。因此,《出三藏記集》類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既是圖書目錄,也是當時學術文化的總合歷史紀錄。不過,《出三藏記集》的體例,卻異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或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出三藏記集》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緣記〉(一卷),闡述匯集佛典的經過與譯經的歷史。第二部分是〈名錄〉(四卷),為漢代以來的佛經翻譯目錄。而且,仔細地分門別類,在各類下面附有簡單的解說,相當於藝文志或經籍志。陳垣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指出,〈名錄〉不像中國的目錄學,以四部分類來區分內容,而是根據譯出的時代順序來排列,甚至,還按照不同的譯者,作分類整理。第三部分為〈經序〉(七卷),主要收錄漢譯佛典所附的序和後記。不少留傳於後世的貴重資料皆收錄在此。陳垣還指出,清代朱彝尊仿效《出三藏記集》,在《經義考》各經中著錄前序與後跋。第四部分為〈列傳〉(三卷),收錄了對翻譯佛經有貢獻的國內外高僧傳記。這一部分可能是最早有系統的僧侶傳記,總共收錄了二十二名外國僧侶和十名中國僧侶的傳記。後來慧皎著《高僧傳》,他在序中說:「沙門僧祐傳《三藏記》,止有三十余僧,所無甚眾」。《高僧傳》中,〈譯經第一〉的大部分和〈義解第二〉的某一部分資料,大多取材自《出三藏記集》中這三十餘人的傳記,甚至有些篇章,完全原封不動地抄錄《出三藏記集》的內容。
《出三藏記集》並沒有說明此書完成於何時,但從其他資料中,我們可以推定出大概的成書時間。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五(《大正藏經》卷四十九史傳部一):「出三藏集記錄齊建武年律師僧祐撰」。又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歷代所出眾經目錄〉(《大正藏經》卷五十五目錄部):「齊末梁初沙門釋僧祐撰」。仔細檢視《出三藏記集》的內容後,可以發現前者隋‧費長房的說法犯了明顯的錯誤。因為《出三藏記集》的第二部分〈名錄〉,經常出現梁‧天監的年號。例如卷五〈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列舉了年輕的尼僧於齊末至梁初年間,誦出的二十一種疑經,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天監四年(505)《喻陀衛經》一卷、《阿那含經》二卷及《妙音獅子吼經》三卷。此外,同卷中還記錄了僧妙光於天監九年(510)作疑經《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一卷。又卷七〈經序〉部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中,記有時間「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這是在《出三藏記集》中出現的最晚日期。因此,本書應該是完成於天監十四年以後。
另一方面,《歷代三寶記》卷十一錄有《華林佛殿眾經目錄》四卷,其解題云:「右一部四卷,天監十四年,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敕撰。紹略取祐之《三藏集記目錄》,分為四色,餘增減之」。(此經錄之名稱,於同書卷十五又重複出現,仍作「梁天監十四年敕沙門釋僧紹撰」。)如果僧紹確實參考了《出三藏記集》,又依據前面《出三藏記集》卷七的記載,推論《眾經目錄》完成於天監十四年(515),是不合理的。故《出三藏記集》成書時期,應該在天監十五年(516)後一、二年之內。
倘若劉勰曾經參與撰述《出三藏記集》,那麼,在此書完成時,他應該已經在昭明太子身邊擔任東宮通事舍人了,而劉勰的《文心雕龍》成書於天監初年,故他從事撰寫《出三藏記集》的工作,應該是在《文心雕龍》完成後 才開始的。當然,撰述《出三藏記集》需要耗費相當的時日,因此,劉勰可能在出仕前,仍在僧祐身旁時,就著開始手編撰了。《梁書》與《南史》的劉勰傳,都把劉勰編纂佛經目錄的事蹟,當成他最早的重要事業,這意味著劉勰很早就參與這方面的工作。
僧祐擔任整理內容浩瀚的佛經之主持人。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大正藏經》卷五十)云:「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嚴〔寺〕僧旻,於定林上寺纘《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同書卷五〈僧旻傳〉的內容指出:「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旻、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旻取衷」。可知,當時劉勰也曾參與編纂佛經的工作。《眾經要抄》著錄了《歷代三寶記》,《歷代三寶記》卷十一稱本書的編撰始於天監七年十一月,終於天監八年四月。不過,劉勰從事過的佛經整理工作,可能比我們想像中來的要多。而且,這些整理佛經的經驗,對他後來編纂《出三藏記集》,有極大的幫助。
到目前為止,筆者一直推論劉勰對《出三藏記集》的編纂貢獻極大,同時,劉勰在編纂《出三藏記集》過程中,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當然,不能一直就此停留在推測的範圍,我們若仔細研究《出三藏記集》,便會發覺這部書並非單靠僧祐一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當體認到這一點後,越覺得《出三藏記集》中劉勰的身影,更加鮮明。以下將把重點放在《出三藏記集》與劉勰有關的文章,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般認為《出三藏記集》的作者是僧祐,可是諷刺的是,僧祐在本書中,暗指《出三藏記集》並非全部出自他個人之手。例如,卷十二〈經部〉末尾有僧祐編的《法集雜記銘》七卷,裡面列舉了序和篇名,其中不但有僧祐著述的文章,還有劉勰的〈鍾山定林上寺碑銘〉一卷、撰者不詳的〈鍾山定林上寺絕跡京邑五僧傳〉一卷、〈建初寺初創碑銘〉一卷、〈僧柔法師碑銘〉一卷及沈約的〈獻統上碑銘〉一卷。僧祐在序中說:「其山寺碑銘,僧眾行記,文自彼製,造自鄙衷」。也就是說,以上列舉的四篇文章,雖然出自劉勰、沈約之筆,但是內容卻屬於僧祐;換言之,就是僧祐跟劉、沈二人敘述了自己的想法,然後再請他們執筆。雖然我們不太清楚僧祐與沈約之間的關係,但是,僧祐經常囑託弟子劉勰為他撰寫文章,是不足以大驚小怪的。按照三段式的推論,我們有充分的條件,支持《出三藏記集》的文章出劉勰之手的假設。
其次,在《出三藏記集》中,往往讓人覺得書中隨處插入的文章並非出自僧祐之手。例如,上文所舉的部分指出,(卷五〈名錄部〉〈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第四),僧妙光曾作疑經,由於他的著作遭到眾人批評,所以武帝命令僧祐及其他高僧,集會於建康,進行審理:「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喚京師能講大法師宿德僧祐、曇準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辯妙光事」。
「序列」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按照常識來判斷,作為二十名高僧總代表的僧祐,在上面那段文章中,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是非常不自然的。而且,又在自己名字的前面冠以莊嚴的「宿德」二字,這種記載方式,不免讓人覺得滑稽。因為,「宿德」僧祐,如果真是本書的作者,那麼,他一定不會這樣寫。故從這則例子就可以看出,代筆者在此不慎露出了馬腳。范文瀾曾說,僧祐忙著宣揚佛法,無暇專心著述,故推測以其名發表的作品皆出自劉勰之手(〈序志篇〉注六)。
因此,《出三藏記集》的部分內容,可能是劉勰或者其他人撰寫的。然該如何證明哪些文章可能出自劉勰之手?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必須詳細地檢討、比較《出三藏記集》的主要文章與《文心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