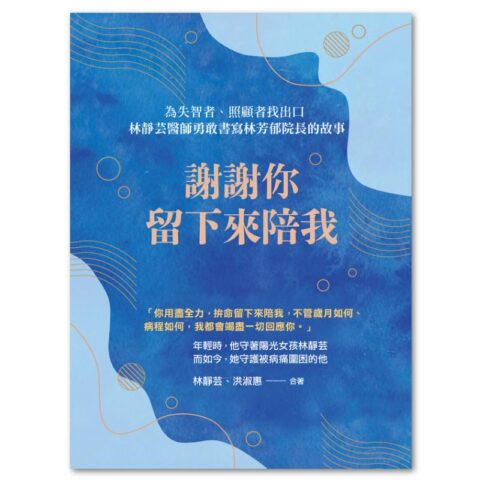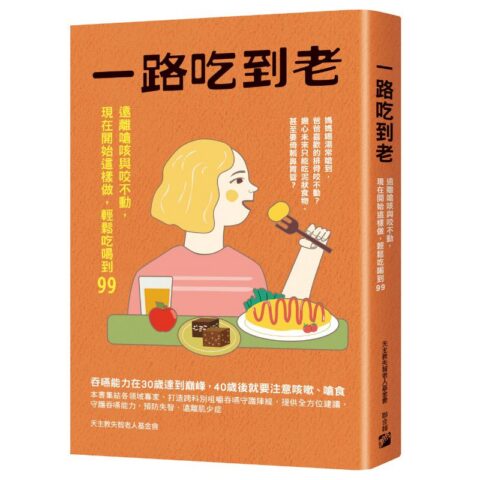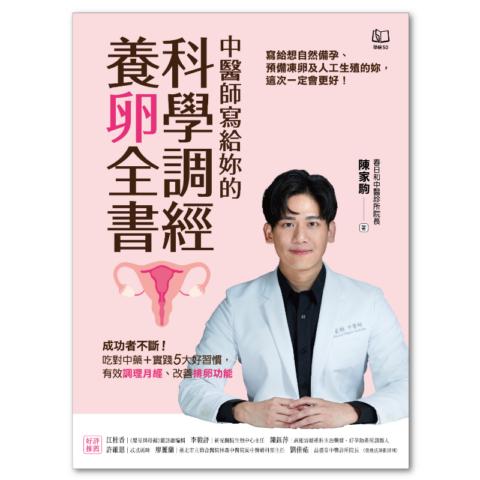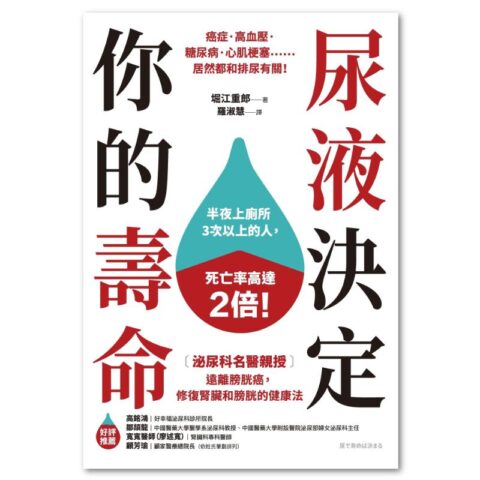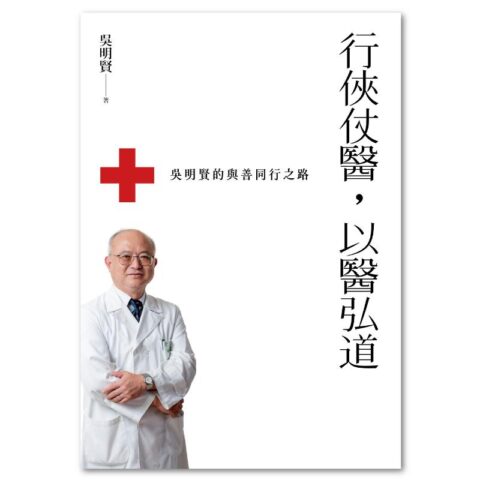宗教與醫療
出版日期:2011-12-21
作者:林富士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04
開數:18開
EAN:9789570839333
系列:生命醫療史
尚有庫存
即使已進入科學昌明的時代,
宗教的幽靈似乎無處不在。
許多宗教團體都介入醫院的經營,
新興的宗教團體也以替人治病或教人養生吸引信徒,
民眾生病之時,不但求醫也求神,
為什麼宗教與醫療會如此緊密相連?
本書收錄了十二篇論文,探討中國傳統宗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在中國與臺灣社會的醫療布教活動,介紹其疾病觀念與治病方法,並分析宗教醫療與世俗醫學之間的關係模式。透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無論是宗教人物從事醫療工作,還是民眾生病時尋求宗教救助,在中國和臺灣,都是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宗教對於世俗醫學有時會貶抑或拒斥,但通常會兼容並蓄。至於醫者則常視宗教醫療為迷信,並批評病人「信巫不信醫」或「棄醫而就巫」的行為。
作者:林富士
1960年出生於臺灣雲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史、疾病史與文化史。著有《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初版,1999新版)、《紅色印象》(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0)、《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小歷史──歷史的邊陲》(臺北:三民書局,2000)、《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臺北:三民書局,2001)、《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等書。
導言:宗教與醫療的糾葛(林富士)
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李宗焜)
一、前言
二、研究歷史的回顧
三、甲骨文中所見的疾病
四、殷人心目中致病的原因和疾病的治療
五、結論
古代東亞世界的咒禁師(張寅成)
一、序言
二、中國古代咒禁師的出現與傳播
三、日本古代咒禁師與道教
四、餘論
醫者或病人:童乩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林富士)
一、引言
二、「童乩」釋義
三、童乩的醫療者角色
四、童乩的疾病觀與醫療法
五、精神異常與人格解離
六、巫病與成乩
七、另一種病人
八、結語:另一種醫者
宋代道教醫療:以洪邁《夷堅志》為主之研究(莊宏誼)
一、前言
二、洪邁《夷堅志》所載道教醫療案例
三、《夷堅志》反映的道教醫療觀念與方法
四、結語
道教與種痘術(姜生)
一、道教之特有傳統與種痘免疫術之發明問題
二、從司痘神到種痘神信仰之發展及其內部結構
三、道書及醫籍所存道教迎神種痘科儀
漢譯密教文獻中的生命吠陀成分辨析:以童子方和眼藥方為例(陳 明)
戒律與養生之間:唐宋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劉淑芬)
一、前言
二、佛教戒律中的藥與酒
三、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石藥
四、寺院中的藥酒
五、寺院養生藥物的背景:唐宋世俗社會中的養生風氣
六、結語
當病人見到鬼:試論明清醫者對於「邪祟」的態度(陳秀芬)
一、前言
二、邪祟的意涵與病機
三、邪祟的分類與病證
四、邪祟的診斷與治療:兼論「祝由」之義
五、小結
展示、說服與謠言:十九世紀傳教醫療在中國(李尚仁)
一、前言
二、中國醫療傳教事業的興起
三、傳教醫學的理想與實務
四、醫療傳教遭遇到的困難
五、中國人對傳教醫療的攻擊
六、反教謠言的醫療與政治成分
七、結語
天學與歷史意識的變遷:王宏翰的《古今醫史》(祝平一)
一、引言
二、王宏翰的新資料、《古今醫史》的版本與本文的詮釋策略
三、天、儒、醫三位一體的醫學觀
四、闢妄
五、定義醫療實踐
六、朱熹與醫者之社會地位
七、結語
癩病園裡的異鄉人:戴仁壽與臺灣醫療宣教(王文基)
一、治療身體或/與拯救靈魂
二、樂生院與雙重教化工作
三、結語:作為文明任務的醫療宣教
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李貞德)
一、前言
二、孫理蓮的傳道生涯
三、從施藥包紮到集資建院的醫療救助事業
四、從非正式到正式的女宣工作
五、基督教的美國與自由中國
六、結論
導言(節錄)
宗教與醫療的糾葛(林富士)
一、緣起
即使我們已進入多數知識分子所讚頌的理性昂揚、科學昌明的時代,宗教的幽靈似乎仍然無處不在。即使有不少醫學史家宣稱醫學已打敗宗教,在二十世紀的醫療市場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所謂的「醫療布教」與「宗教醫療」依然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實況。這在當代臺灣社會表現得格外清楚。首先,我們發現,許多宗教團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的慈濟功德會、行天宮等)都介入醫院的經營。其次,有一些新興的宗教團體,往往以替人治病或教人養生法(或是所謂的氣功)吸引信徒。此外,民眾生病之時,往往求醫也求神,兼用醫藥和宗教療法。身處這樣的情境,我們不禁要問:這是近來才有的、偶然的社會現象?還是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文化習性?宗教與醫療又為什麼會如此緊密相連?
二、解惑之道
為了解決這樣的困惑,我們勢必要採取歷史學的方法,探索各個宗教在中國社會(包括以漢人為主體的臺灣社會)的醫療活動及相關的觀念和信仰。至於更具體的問題則包括:
(一)各個宗教是否曾從事醫療活動?其動機為何?
(二)各個宗教是否曾利用醫療活動傳布其信仰?
(三)各個宗教如何看待疾病與醫療?
(四)各個宗教如何解釋病因?如何治療疾病?
(五)「醫療」在各個宗教的信仰體系中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六)各個宗教的「疾病觀」和「醫療法」與「世俗」醫學有何異同?
(七)各個宗教的「疾病觀」和「醫療法」彼此之間有何異同?
上述課題,雖然已有學者進行討論,但大多單純的從個別的宗教(如道教、佛教)著眼,而且很少能全面的考量所有的課題。當然,這也是因為中國和臺灣社會的宗教太多,歷史也相當久遠,單憑一人之力確實很難進行較為全面性的研究。因此,我和我的同仁覺得有必要聚集研究各個宗教的專家以及醫學史的研究者,針對存在於中國和臺灣社會中的傳統信仰(巫覡信仰、民間信仰、術數信仰)、主要的組織性宗教(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若干近代的新興宗教,一方面各自進行細緻的個案研究,另一方面則相互對話,進行跨宗教和跨時空的比較研究,期待能尋繹出宗教與醫療之間的各種關係模式。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以「宗教與醫療」為題,向中央研究院提出一個為期三年(2002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整合性研究計畫。
「傳統信仰」的部分,由林富士(專長為巫覡史、道教史和醫療文化史)研究中國的「巫醫」傳統和臺灣「童乩」的療病活動;李宗焜(專長為古文字學)利用殷墟的甲骨材料和遺址,探討殷人宗教中涉及醫療和疾病的儀式和觀念;李建民(專長為術數史和中國傳統醫學史)探討「方術」傳統中的「身體」觀;宋錦秀(專長為臺灣史、醫療人類學)分析臺灣民間信仰中有關婦人胎產疾病和祟病的觀念與習俗。
「組織性宗教」的部分,則由劉淑芬(專長為佛教史)和康樂(專長為佛教史、宗教社會學)分別探究佛教與中古醫療文化之關係,及佛教對於中國飲食、養生文化的影響;李貞德(專長為性別史、西方基督教史、醫療文化史)、祝平一(專長為科技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醫學史)、李尚仁(專長為西方殖民醫學史)分別探討基督教在臺灣和中國的醫療事業和傳教活動。此外,張哲嘉(專長為中國傳統醫學史)則分析佛、道二教的教義如何影響中國的醫學理論。
上述學者的研究課題雖然不足以包括所有的宗教,也無法涵蓋所有的歷史時期和地理空間,不過,以臺灣學術社群的規模和中央研究院的人力,以及計畫的時限來說,能有這樣的組合,已經頗不容易。具體的分工與合作方式是採雙軌制,一方面由各子計畫的主持人進行其個案研究,另一方面則是以工作會報、討論會的方式,針對共同的課題,提出其專業的意見,以進行各個宗教之間的比較研究。至於不足的地方,則是以聘請博士後研究人員(王文基、Gregoire Espesset),以及培育博士候選人(陳元朋)的方式,並邀請更多的相關領域的專家,不定期召開研討會,擴大參與。
五、主要內容
在這本論文集中,我挑選了十二篇不同時間、空間與宗教的論文:一、李宗焜的〈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介紹殷人貞卜傳統中的疾病觀與醫療法,其中的核心觀念與作為,如祖先與鬼神譴祟致疾、祭祀與禱告以求癒疾,便是中國傳統宗教解釋病因與治療疾病的基本模式。二、張寅成的〈古代東亞世界的咒禁師〉,說明中古時期咒禁療法的主要內涵、咒禁術的出現,及其在東亞世界(中、韓、日)的流傳。三、林富士的〈醫者或病人:童乩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說明童乩在近、現代臺灣社會中的醫療者角色,以及其所承繼的中國巫醫傳統的疾病觀與醫療法。四、莊宏誼的〈宋代道教醫療:以洪邁《夷堅志》為主之研究〉,說明道士在中國社會的醫療活動,及其特殊的醫療體系(包括醫藥、養生、法術與儀式)。五、姜生的〈道教與種痘術〉,闡述道教如何結合純粹的醫療技術(種痘術)和宗教信仰(痘神信仰與種痘科儀)。六、陳明的〈漢譯密教文獻中的生命吠陀成分辨析:以童子方和眼藥方為例〉,說明密教的醫療方法除了使用咒語與相關的儀軌之外,還運用源自印度生命吠陀的藥物治療,但一如道教,密教也企圖將純粹的醫療技術(藥方)融入其宗教體系之中。七、劉淑芬的〈戒律與養生之間:唐宋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說明唐宋時期的禪宗如何將當時流行的養生文化(湯藥與各種藥物),融入寺院生活和宗教儀式,這也是較為少見的世俗醫學影響宗教的例證。八、陳秀芬的〈當病人見到鬼:試論明清醫者對於「邪祟」的態度〉,檢視世俗醫學與宗教傳統對於「邪祟」解釋與療法的異同,以及明清醫者對於「宗教醫療」(祝由術)的看法。九、李尚仁的〈展示、說服與謠言:十九世紀傳教醫療在中國〉,探討十九世紀西方醫療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及他們所激起的爭議與衝突,並分析傳教士如何透過宗教儀式與論述,讓他們的醫療活動具有濃厚的宗教意涵。十、祝平一的〈天學與歷史意識的變遷:王宏翰的《古今醫史》〉,探討一位天主教徒如何透過醫學史的寫作,闡揚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醫學理念,並批判中國醫學中的「異教」成分。十一、王文基的〈癩病園裡的異鄉人:戴仁壽與臺灣醫療宣教〉,說明基督教的醫療宣教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臺灣癩病防治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十二、李貞德的〈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闡述二十世紀後半葉基督教在臺灣醫療傳道的轉變及其中的性別與政治意涵。
六、結語
上述十二篇論文,涉及的宗教傳統有:中國傳統宗教(術數傳統、巫覡文化)、道教、佛教(密教、禪宗)、基督教和天主教;觸及的醫學體系有:中國傳統醫學、祝由醫學、印度傳統醫學(生命吠陀)和西方近代醫學。雖然本書收錄論文的範疇,遠不足以涵蓋所有的宗教傳統和醫療體系,但透過這些例證,我們可以確信: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中國,甚至是在整個東亞世界,也無論古今,幾乎所有宗教都曾涉入醫療事務,從事醫療布教活動,也都具備對於疾病的獨特看法和醫治方法。不過,他們的疾病觀與醫療法和世俗醫學之間的關係,親疏不一,醫學在各個宗教信仰體系中所佔有的位置也不盡相同。
其中,中國傳統宗教基本上是以「宗教療法」為主,宗教與醫療高度混同,但與世俗醫學的距離較遠,且常飽受醫者抨擊。道教則兼採「宗教療法」與世俗醫學的觀念與技術,並發展出獨特的養生文化,甚至有融混了醫學技術與宗教儀式的療法,同時,道教也高度重視研修醫術並以醫療布教。而中國佛教的情形,雖然與道教頗為相似,但佛教與世俗醫學的關係並不緊密,養生文化也大多採借而來。至於基督教和天主教,其在中國與臺灣社會的傳教活動,確實高度仰賴醫療,而其醫療活動雖然也具有某種程度的宗教意涵,甚至也有宗教療法,但相較於其他宗教傳統,這一方面顯得較不發達,而且,其所採用的近代西方醫學與基督宗教信仰本身,通常可以完全切割。換句話說,醫療(尤其是世俗的醫學知識與技術)在基督宗教的信仰體系中並未占據重要的位置。
除此之外,經過三年的研討,我們發現,無論是宗教人物從事醫療工作,還是民眾生病時尋求宗教救助,在中國和臺灣,都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有些宗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還提出了一套有別於世俗醫學的疾病觀和治療方法。他們大多強調,人之所以生病,主要起因於道德上的敗壞和鬼神的責罰,因此,治療方法也偏重於懺悔、祭禱、齋醮、功德這一類的宗教療法,或是以符咒、厭勝為主的巫術療法。此外,他們也採納食療、沐浴、按摩、導引、房中之類的養生術。對於世俗醫學,他們有時會加以貶抑或拒斥,但是,通常都會兼容並蓄。有些宗教,尤其是近代的基督宗教和若干佛教團體(如慈濟功德會),更幾乎全賴世俗醫學。至於宗教人士或宗教團體介入醫療事務的緣由,主要是基於宗教信仰。有的是為了傳教,有的是為了救人以積累功德,有的純粹是出自慈悲之心。不過,也有人是為了營生或名聲。由於各個宗教積極介入醫療事務,傳揚他們對於疾病的看法,並且提供各式各樣的治療方法,傳統中國及臺灣的民眾,生病之時,便可以在多元的醫療系統中抉擇或遊移。因此,患者的就醫行為,有時便被知識分子和專業醫師批評為「信巫不信醫」或「棄醫而就巫」,而「巫醫並用」也的確是長期以來常見的社會現象,治病時「要人也要神」(人的醫技加上神的庇佑)也成為民眾普遍的心態。
整體而言,宗教的確常以醫療做為傳教或個人修道的工具,有些宗教甚至將醫療視為其信仰體系的一環,強調習醫以自療或濟世為其天職。不過,宗教與世俗醫學之間也會有互斥的現象。有些宗教認為疾病與壽夭都由天(神)所決定,生病時只能聽天由命或尋求神靈的救助,因此,並不贊同或鼓勵病人尋求醫藥治療。而專業醫師則往往視宗教信仰或宗教療法為「迷信」,不僅無助於治病,甚至會妨害醫療。然而,從實務來看,不管宗教所採取的療法為何,對於其信徒而言,似乎可以緩解病人在心理和道德上的焦慮與不安,甚至強化其對於療癒的信心。而且,傳統中國及臺灣社會面對瘟疫流行的因應之道,除了醫療救助之外,往往也會採取政治改革、社會救濟和道德重整。因此,我個人認為,政府可以鼓勵宗教團體投入醫療工作,宗教人士也應一本其傳統及善心,協助社會照護病人之身心;另一方面,醫生則應和宗教界合作,提供病人更全面的醫療服務,至少,應該學習聆聽、理解民眾對於自身病痛的感受、不安和詮釋。
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臺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李貞德)
一、前言
《路加福音》第十章記載耶穌到馬大和馬利亞的家中拜訪,馬大為伺候的事多而忙亂,抱怨妹妹馬利亞只顧坐在耶穌的腳前聽道。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份,是不能奪去的。」自中世紀以來,基督教會鼓勵婦女服事,便常以新約聖經中這段故事申論「天父取代家父,求道勝於家務」的道理。一九五四年為推廣臺灣傳道事業而創立芥菜種會(The Mustard Seeds Inc.)的美籍宣教士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在向丈夫申述自己走出家庭、服事社會的志向時,便曾表示「馬大的工作已處理好,想做馬利亞的事了」,並且宣稱自己「不願只當宣教師的妻子(missionary’s wife),而要當宣教的妻子(missionary wife)!」
中年立志走出家庭的孫理蓮,其宣教事業包羅萬象,卻大多以醫療救助始,以職訓教育終。自一九二七年抵臺之初,便以師母身分接待馬偕醫院痲瘋病患。一九四七年戰後重返則入山施藥、宣導衛生,在各山地鄉鎮設立巡迴診療所,並介入改善省立樂生療養院痲瘋病患福利。一九六○年代更因救助臺南北門鄉烏腳病患而聲名大噪,除數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表揚之外,亦引起美國宣教機構與社會大眾的重視。孫理蓮並非醫療專業人員,但其參與醫療傳道獨樹一幟,有目共睹,是現代醫療傳道史中的重要人物。
孫理蓮雖受過基本的醫護訓練,但不以醫護人員自居;她雖參與第一線的醫護工作,卻不以醫護技術為傳道主力。寫信募款,創設機構,在臺灣各地建立病院、診所、產院、育幼院和職訓班等,才是她的宣教模式。她網羅歐美各國在臺傳道的醫護專業人士,卻大量仰賴美國本土信徒的捐贈推動事工。而在戰後臺灣特殊的政經環境下,愛與關懷的宗教情操毋寧是透過「美國」此一象徵網絡傳達和表現。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醫療救助一直是西方傳教士進入東方社會、宣揚基督教義的重要媒介,西方醫學亦藉此傳入中國。其間所引起的異文化接觸與殖民經驗,乃至傳教士與醫師之間的論爭問題,相關研究方興未艾。由於最初女性難以按立為牧師,有志於海外宣教者,若非以醫生、護士或教師等專業身分接受差派,便是以「醫生娘」或「牧師娘」等宣教士之妻的角色前往傳道地區。她們或持有醫護執照,或受過基礎護理訓練,在宣教人力總是不足的情況下,大多曾有協助醫療照護的經驗。可惜的是,雖然自始至終醫療傳道都有女性的參與,她們的角色、行止與掙扎,卻因論之者少,故隱而不顯。針對十九世紀到中國的女傳教士,不論是女醫師或女教師,最近都有學者論及,逐漸嶄露頭角。但自一八七○年代即參與臺灣傳道的女性,不論其醫療救助的型態如何,則仍少見學術專文討論,僅在教會紀念與宣導文字中偶現身影。
孫理蓮一九二七年初次抵臺,可謂承美國婦女宣教運動之遺緒東來。至一九八三年逝世,經歷日本殖民和國民黨政府兩個時代。她雖因丈夫接受加拿大長老會差派而來,卻是以美國人的身分在臺灣生活與行動。當孫理蓮宣稱不僅要做妻子,還要做宣教士時,她採用傳統的聖經故事,將馬大和馬利亞作為兩種不同的象徵符號,用以詮釋自己中年之前與之後的活動。然而,孫理蓮的馬利亞工作包括哪些?和之前的馬大工作有何異同?她如何自我理解?別人又如何看待她?孫理蓮的宣教事工大多藉由她的書信向美國贊助教會報導,引起廣泛注意之後則又有宣教機構派員來臺參訪,為她撰寫傳記並製作宣傳影片。透過這些交流,美國人認識了什麼樣的臺灣?而臺灣人又如何理解美國和基督教?其中內涵具有何種性別意義?表現什麼醫療傳道發展上的現象?又傳達了什麼特殊的臺灣經驗?本文利用孫理蓮的書信、報告、傳記和新聞資料,嘗試回答上述問題。期望透過一位女性參與宣教的個案,呈現醫療傳道、異文化接觸和殖民議題在二十世紀臺灣的風貌。
二、孫理蓮的傳道生涯
孫理蓮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湃洱湖(PriorLake)畔的小鎮,一九二五年自該州聖保羅市的馬加勒斯特學院(Macalaster College)畢業,在紐約聖經學校受訓兩年,一九二七年新婚不久便隨同丈夫孫雅各(James Dickson, 1900-1967)接受加拿大長老會差派來臺宣教。由於一九二五年加拿大長老會內部分裂,導致原屬加拿大長老會教區的北臺灣人心浮動,一九二六年宣教士多人離臺或南下加入英國長老會,因此北臺灣人手極度缺乏。美國籍的孫氏夫婦便是呼應加拿大長老會的緊急招募而來,並且一抵達臺灣便加入宣教,除了努力適應環境、學習語言之外,亦協助當時留守北臺灣的偕叡廉牧師(Rev. G. W. Mackay)、明有德牧師(Rev. Hugh MacMillan)和戴仁壽醫師(Dr. George Gushue-Taylor)。孫氏夫婦來臺兩個月之後寫信回國,以自嘲的語氣形容在上街購物時抓住機會和客氣恭謹的店家練習臺語,並提及必須在新年期間準備餐點招待戴仁壽醫師在馬偕癩病診療所的兩百多名病患。事實上,到一九四○年十一月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緊張暫時離臺之前,孫理蓮大多也是以學習適應和協助招待的方式參與宣教工作。
(一)「馬大」的歲月
一九二七到一九四○的十三年間,孫理蓮以師母,也是宣教士之妻的身分在臺灣生活。孫雅各在一九三○年代理淡水中學校長,翌年又出掌臺北神學校(臺灣神學院前身),身兼數職加上慷慨好客,同事學生往來聚會頻繁,家中經常高朋滿座。雖然宣教士的薪水在初來乍到時尚稱夠用,但各種細節卻不能不靠孫理蓮打點,幾年下來,亦不無捉襟見肘的時候。身為女主人,除了張羅訪客的飲食起居,還得在同工意見相左、爭執不休時,巧妙介入、化解僵局。孫家被臺灣教友暱稱為旅店,孫理蓮便以旅店主婦自況。水土不服加以辛勞持家,使她最初三年兩度喪子,見證了宣教生涯的代價。她的家信亦透露在臺外國人士因長期處在緊張狀態以致於身體患病或道德崩潰。面對勞累困難,她選擇到淡水海邊散步,保持平靜。由於宣教士之間住房分配之故而數度搬家,她則形容窗簾因頻遭修剪已面露憂鬱之色。事實上,嘗試幽默以對,是孫理蓮早期以師母身分在臺生活時自處處人之道,使她的書信一方面洋溢著風趣的文采,另方面也透露對自己生活並不滿意,但對環境也無可奈何的態度。
寫信是孫理蓮調整情緒、紀錄人事、報導臺灣的方式。由於這個時期她並非以宣教士而是以師母的身分寫信,她的信中充滿側面觀察的奇聞逸事,比較少關於教會事工的直接說明。來臺初期,她筆下的臺灣人具有勤儉、率直、不諳文明禮儀的形象。她形容教堂敬拜時男女分坐兩邊;本地牧師講道比手劃腳、充滿戲劇感。她描繪臺灣婦女面容光潔、個性堅毅,有如聖徒;但姊妹會時卻人聲嘈雜,私下交談者有之,小孩奔跑哭鬧者有之,以致於領會講道者會施行權威式的震撼教育,不如北美教會來得溫柔安靜。至於在孫家舉行的茶會,則因本地人號召鄰里「到外國人家裡喝茶」而造成人數爆滿,加上「從山地來的女人不瞭解我們的方式」,只顧著取用茶點,並不會暫停和女主人寒暄,以致於蛋糕總是供不應求。孫理蓮的家信中充滿這類寫異述奇的小故事,透露了她來臺初期經由人我差異認識他人並定位自己的過程。
不過,自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舉侵華,殖民政府在臺軍事演習日益增加,軍事管制漸趨嚴格,在臺宣教士的生活也越發困難。雖然孫理蓮在信中仍努力以詼諧的筆調形容槍尖下的生活,嘲笑自己的日文能力僅足以“kon nichi wa”面對日本哨兵的刺刀,不過物資日漸困乏、家中頻遭監視,都使她深感寂寞和危險。同時她筆下的臺灣人也開始充滿苦難的形象。她描述一九三七年九月的某天傍晚和孩子吃過晚餐,便看見日本軍機紅光閃過淡水上空,不禁為成千上萬即將喪子的中國母親哀痛;又形容自己在震耳欲聾的轟炸機飛越時努力撰寫代禱信,卻不知該如何請求在美親友為臺灣禱告。由於臺灣的統治者發動戰爭,孫理蓮擔心美國信徒不能體會臺灣人民的進退維谷。她在信中轉述宣教士和本地信徒之間口耳相傳的故事,描寫臺灣男丁如何不願當兵、女孩不願隨軍服務,而他們又如何遭到日本統治者的監視逮捕。同時,美國政府對於堅守崗位的海外宣教士並未積極支援,則令她產生怨尤,認為「美國政府看待我們就如我們看待一些腦袋壞掉的窮親戚一般,雖生氣丟臉卻又不能完全斷絕關係」。這種同處邊緣流離的經歷,似乎使她和她傳道對象的臺灣人產生了特殊的情感認同。
由於美日關係日趨緊張,在臺宣教士安全堪虞,孫氏一家終於決定在一九四○年十一月離臺。在美短暫停留之後,孫氏夫婦旋經加拿大長老會重新差派,前往南美洲英屬圭亞那宣教。在圭亞那的五年令孫理蓮對自己的認識頗有轉變。雖然同屬白種人,孫理蓮自覺和英國殖民婦女風格迥異。她形容白種殖民人士以各種舊社會的繁文縟節來展現特權,而來自民主新世界的她則完全不理會這一套。她騎自行車出入,令有司機駕車的英國婦女目瞪口呆,又親自擦洗教會地板,對比當地女性只會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而且她還是殖民地唯一一位自己做飯的白種女人,但她卻自豪地表示她的家人都「擁有良好、清潔、健康的食物」。
孫理蓮從圭亞那寄回家鄉的信中,那些來臺初期用以形容臺灣婦女勤儉率真卻不符合文明禮儀的形象,似乎轉而用來描繪她自己,成為區隔美國新世界宣教婦女和英國舊社會殖民婦女的一種方式。此外,由於在圭亞那宣教的人手和資源匱乏,孫理蓮必須參與家戶以外的事工。她在路邊向人佈道,拜訪平民家庭,負責農場上的聚會,對著成百的兒童講道等等。這些超越過去照顧食衣住行等妻母角色的服事,令她深感快樂。一九四七年戰後返臺,孫理蓮回憶在圭亞那的兒童事工和戶外宣教經驗,希望能在臺灣繼續類似的服事。
(二)「馬利亞」的事工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孫雅各便迫不及待重返臺灣,藉著為美國政府發放救援物資的名義,於一九四六年返臺考察教會情況,發現山地教會在日治末期的威脅迫害之下反而經歷復興。由於一雙兒女此時皆已返美就讀中學,孫理蓮傾向留在比較靠近家鄉的南美圭亞那,然而敵不過孫雅各對臺宣教的熱誠,最後兩人還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再度來臺。四十六歲的孫理蓮這次來臺,沒有兒女之累,卻有了圭亞那的佈道經驗,便提出新的期望和計畫,宣稱自己「不願只當宣教師的妻子,而要當宣教的妻子」。
孫理蓮返臺之後,仍持續寫信回家鄉的習慣,聊天敘舊般的信件在親友之間流傳,一方面介紹她眼中的臺灣,另方面也成為募款的管道。她的文字親切動人,筆下的臺灣百廢待興,北美教會機構和個人紛紛要求轉寄以便考慮捐款。從複寫到鋼板油印,至一九五四年時,每個月寄出的募款信已超過兩萬五千份。為了方便美國捐款人節稅,鼓勵奉獻,她終於在友人的勸說之下,成立非營利事業機構芥菜種會,透過設在加州的總部接受捐款。而她在臺五十年近千封的信件,在當時是美國教友認識臺灣的途徑,在今日則成為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
從一九四七年再度來臺到一九八三年逝世的三十六年間,孫理蓮或透過信件向在美親友和教會募款,或藉返回北美述職的機會巡迴演講、拜訪教會慈善機構尋求贊助,或接受媒體採訪、報導在臺宣教需要,然後將獲得的金錢和實物捐贈,透過美國軍方和在臺使館人員的協助運達分發,救濟臺灣各地不足之處。經由孫理蓮的努力,在臺成立的機構無數,包括各山地診療所、護理訓練班、肺病療養院、馬利亞產院、托兒所、育幼院、未婚媽媽之家、中途之家、女子習藝所、男子職業訓練班,以及轟動一時的臺南縣北門鄉烏腳病院等。在一九六七年孫雅各逝世之後,她為了實踐丈夫的遺志,創立「焚棘海外傳道會」(Burning Bush Mission),派遣臺灣原住民宣教師至北婆羅州沙勞越等南洋地區,進行「部落對部落」的傳道工作。
大致觀之,她的傳道事工初期多為醫療救助和衛生宣導,後則輔以教育訓練。雖然她從圭亞那經驗中得到的靈感是戶外佈道和兒童主日學,而她自稱最有興趣的是婦幼工作,但她吸引美國教友注意、獲得大量捐贈的,卻是山地醫療服務、救助痲瘋病患,以及興建北門烏腳病院等事蹟。她自己曾經為前兩項工作著書立說,而美國教會媒體則對最後一項事工關切有加。以下先分別介紹孫理蓮這些醫療救助事工,然後再分析其中的性別與政治意義。
三、從施藥包紮到集資建院的醫療救助事業
一九四七年八月,原在日本宣教的馬文夫婦(MacIllwaine)來臺,其中瑤珍妮.馬文(Eugenia MacIllwaine)是護士,因此孫理蓮打算帶她入山協助原住民。孫理蓮在寫給女兒的信中,形容自己在花蓮山地的工作計畫:
我要告訴他們耶穌的故事、環境衛生,以及各種事情。我要教導這些原住民洗澡和洗衣服。聽說他們從不洗衣服,而是穿到破爛為止。我要讓他們蓋有隔間的公共澡堂,給他們澡缸和肥皂,並且獎賞那些每天洗澡洗衣服的人。
帶著醫護人員前往探訪,禱告宣講耶穌,然後施藥包紮、改善環境衛生、建立醫療救助設施,最後則蓋教堂,可以說是孫理蓮一系列結合醫療與傳道的工作模式。不論是一九四七年起進入山地施藥佈道,或一九四九年介入省立樂生療養院的管理,大多循此進行。而在醫療救助的資源逐漸穩定時,便另立育幼或生技訓練機構,協助病患及其家屬自立謀生。
(一)穿著護士服的師母
孫理蓮最初進入花蓮山區,僅由一兩位外國醫護人員和一兩位本地牧師或師母陪同。後來孫雅各請求其他教會協助,遂有門諾會組成的醫療團隊參與支援。為了吸引群眾,孫理蓮將兒童佈道的方式納入山地宣教之中。她以法蘭絨壁畫講故事,並學手風琴邊彈邊唱。從她的信中可知,她每到一處會先唱詩歌,召集兒童,並將醫療團隊來訪的消息傳開,等群眾逐漸聚集,便說一些安慰的話、講一兩段聖經故事(通常是耶穌和尼哥底母的故事),接著便請原住民將病患領來,表示可以為他們看病。此時她也會穿上護士服分發奎寧,說明服藥須知,塗抹疥癬藥膏,協助包紮潰爛、燙傷、感染和刀割等外傷。她在信中不只一次提到自己面對病患時的痛苦,最初入山時是因為尚無醫藥可供救助,她感到「無力醫治他們,只能愛他們並為他們禱告」,後來則因施藥包紮時目睹各種傷口而幾乎暈厥。她聲明自己不是天生的護士材料,靠的只是一股精神意志力。不過,護士服所提供的專業印象,顯然使她和其他醫療人員沒有外觀上的差異。當她在花蓮山區救助難產婦女時,也為自己能在醫療器材極端不足,以圍裙包裹新生兒、在炒菜鍋中洗嬰的應變能力頗感自豪。
巡迴醫療團在山區的活動並非每次都受到原住民的歡迎。雖然她的信中曾經提到在花蓮山地有全村改信、要求聽道的故事,但在南投山區也曾面臨村民懷疑醫療團隊所發放的腸道寄生蟲藥有毒。來自中國的門諾會牧師則將這種現象歸咎於日治時期的霧社事件,認為造成原住民對外國人的敵意。
不過,醫療團隊發現最棘手的問題尚非寄生蟲,而是原住民感染肺結核的情況嚴重,難以處理。由於埔里位於中部山區的中心,可以服務附近約兩萬名原住民,因此孫理蓮倡議在埔里設立山地診所,並積極寫信募款。然而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日趨激烈,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接二連三的戰事,使得美國民眾不確定是否要將經費花在前途未卜的臺灣。直到世界展望會伸出援手,允諾提供藥品和員工薪資,一九五五年埔里基督教診所終於開張。由於肺結核病患需要隔離治療,又為免陪同就診參與照顧的家屬長途跋涉往返於部落和醫院之間,孫理蓮計劃蓋療養院和宿舍支援,便繼續寫信回美加募款,向個人、主日學班級、教會社團等不同單位請求每個月六美元的贊助,提供床位,並將該床位的病患拍照寄給贊助者,以便贊助者認識自己所招待的「客人」。
最初埔里基督教診所的數百名病患,皆仰賴區區幾位員工照顧。由孫理蓮贊助自美習醫返臺的謝緯醫師負責看診,而挪威籍的護理師徐賓諾(Bjarne Gislefoss)和一位護士、一名工友則協助治療。之後在謝緯的倡議和孫理蓮募款支持之下,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山地護士訓練班,一方面提供山地少女訓練和工作,另方面也補充診所病院的人力資源。孫理蓮則每週前往埔里視察,瞭解當地需要,然後回臺北寫信募款。這類持續不斷寫信回北美、大量匯集小額捐款的方式,正是孫理蓮接著在花蓮等其他山區陸續設立肺病療養院、產院、護理班和技訓所、乃至蓋教堂的主要管道。一九五六年美國電視臺為了表揚世界展望會創辦人包伯皮爾斯博士(Bob Pierce)的慈善事蹟,邀請曾經受惠的孫理蓮自臺返美擔任貴賓,結果在節目中,孫理蓮意外獲得了由惠輝(Charles Pfizer Co.)等藥廠贊助價值兩千美元的肺結核藥,以及一台由猶太醫院贈送的X光機。在滯美的三個禮拜期間,孫理蓮寫就These My People一書,報導在臺灣山地的工作經驗。該書在一九五八年出版,書末肯定美國教會作為「大哥哥教會」(Big Brother Church)伸出援手的榜樣。
(二)募款高手集資建院
孫理蓮雖然參與實際的醫療行為,但她的長才顯然不在施藥包紮,而在網羅人才、寫信募款、集資建院。這不僅在山區,也在她的平地事工中表現無遺。
一九四九年,位於臺北縣新莊的省立樂生療養院陸續傳出痲瘋病患自殺事件,在院中牧會的蔡牧師幾度向孫理蓮尋求協助。孫理蓮先邀請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的何師母(Mrs. Hogan)同往探訪,彈手風琴講聖經故事安慰院內信徒,並藉以瞭解院內情況,發現院長苛扣衣食津貼,置病患於不顧。在長期沒有醫生訪視的情況下,患者或營養不良,或灼傷跌倒而手足殘缺,或臥病等死,慘況不一,以致部分病患計劃群聚抗爭。孫理蓮允諾協助,勸退抗爭,遊說剛從大陸撤退來臺,在馬偕醫院服務的白姓女醫師(Dr. Signe Berg)一同前往,在樂生院的大廳設立臨時診所,每天從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四點為患者看病。由於患者操臺語而白醫師說國語,孫理蓮便一方面權充醫病之間的翻譯,另方面為頭痛、胃痛或症狀比較輕微的患者施藥包紮。這些問題,根據她的說法,都是「母親在家中就會處理的小毛病」。白醫師義診之後,孫理蓮又聯絡受過護士訓練的路德會女宣教士杜愛明(Miss Alma Drucks)長期駐院照顧病患。初步的醫療救助之後,孫理蓮判斷樂生院長採取觀望態度,既不支援也不會干涉,便繼續其他部分的改革。一方面她仰賴一貫寫信回鄉的方式,向美國的親友和教會募款購買奶粉、魚肝油、維他命、糧食、毛毯,乃至睡床和有靠背的椅子,並且在病房裝擴音器播放音樂、設圖書室。另方面她聯絡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到院內播放影片娛樂病人,又請求在臺美援總部(American Aid Headquarters)贊助,為院內六百多名病患改建房舍。一九五二年則在病患養雞賺錢、美加教友聯合捐助之下,以兩千兩百美元的資金,為痲瘋病友蓋了一座教堂。
孫理蓮在臺灣救助痲瘋病患的事蹟經由她的信件傳回美國,美國遠東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的羅伯牧師(William F. Roberts)一九五一年來臺時便拜訪孫理蓮,並在返美之後透過廣播代為募款,所得兩千五百美元即轉為樂生病患所生兒女成立育幼院「安樂之家」。患者的病痛獲得照顧,子女亦得安頓,樂生院中卻仍傳出病人企圖自殺之事。經過懇談,孫理蓮發現痊癒患者不得留院又無家可歸,以致了無生趣。她宣稱忙碌的人沒有功夫自殺,便決定讓他們勞動振作。她再度向世界展望會的皮爾斯博士請求協助設立中途之家,並在一九五三年返美述職時,繞道紐約拜訪《基督教先鋒報》(Christian Herald)負責人波林博士(Daniel Poling),詢問贊助職訓工作的可能性。皮爾斯博士伸出援手,為痊癒的男女患者各建一棟房屋。波林博士由於事工過多,起初不敢首肯,卻在數天之後接到一筆指定救助痲瘋病人的捐款,於是便順理成章地轉給孫理蓮在樂生建立了職業治療室(Occupational Therapy Room),讓患者透過木工,一方面紓解心情,另方面製作工藝品販賣貼補。
孫理蓮長期透過書信報導臺灣狀況並且募款,因此不少美國教友在訪臺期間主動和她聯絡甚至登門造訪。芥菜種會救助臺南北門鹽區烏腳病患的源起,正是因為一九六○年某天孫理蓮接獲一位到臺南神學院訪問的外國人的電話,告訴她在北門所見慘狀,請求她的支援。在初步探訪瞭解狀況之後,孫理蓮邀請在埔基服務的謝緯醫師和負責樂生病患的護士杜愛明同往協助。由於當時尚未確定烏腳病的成因,孫理蓮採取一貫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的作法。她一方面借用原本在當地開業的王金河醫師診所,成立「憐憫之門」(Mercy’s Door)免費看診,另方面徵得基督教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協助,在沿海鹽區設立牛奶和維他命分發站,增進貧困居民的營養。不久之後,孫理蓮募得好萊塢長老教會主日學的捐贈,在北門購地建舍,設立「基督教芥菜種會北門免費診所」,又獲得在臺美軍夫人俱樂部的贊助,購買手術臺的照明設備等。一九六一年沿海地區的營養品分發站擴充到二十五個據點,而診所則在一九六五年賴一位因烏腳病過世的臺灣富翁捐贈遺產新臺幣十萬元而得以整修。
烏腳病的成因在於飲用水中含砷量過重。砷中毒的患者因末端血管不通,四肢肌膚或逐漸脫水而變乾,或日益壞疽,發黑發臭,若再遭細菌感染,則傷口化膿潰瘍,腐爛蔓延,最後則可能導致死亡。最初幾年醫生們除了截肢之外,可說束手無策。謝緯醫師每個禮拜四一早從埔里南下為病患開刀,由王金河醫師協助,通常工作到入夜才能休息。而原本生計困難的病患,截肢之後更加辛苦,孫理蓮請求美援單位贊助,王金河則向農復會和縣政府申請補助,成立了草蓆編織工廠,讓失去雙足但仍有雙手的病患自力更生。烏腳病患的慘狀和芥菜種會等教會機構的努力,透過新聞媒體不斷披露,總算引起政府的重視。在中央和省府官員陸續造訪之後,一九七一年終於頒布臺灣省烏腳病防治第一期五年計畫,一九七三年在北門郊區成立了「省立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政府出面之後,烏腳病患得以轉院治療,芥菜種會的財政負擔才逐漸減輕。不過,北門的免費診所則是到了一九八四年才正式停辦。
孫理蓮在大學畢業之後、新婚來臺之前,曾經在紐約聖經學校就讀,接受宣教訓練,其中包括基本的醫護課程。但在她最初十多年的臺灣生活中,很難看到她描述自己這方面的活動。一九四七年她再度來臺開展傳道事業,時移事變加上風雲際會,她的醫療傳道活動除了施藥包紮、衛生宣導和緊急接生之外,募集資源並創立醫療救助機構反而成為最主要的工作。和她一同上山進行第一線醫護工作,或經她邀請參與痲瘋和烏腳病患救助的醫療傳道人士,來自英、德、挪威、加拿大等各個國家,但當她需要集資建院時,從捐贈、運輸到在地發放,卻都少不了美國人的影子。
綜觀孫理蓮的宣教事工,大多以醫療救助起始,而後擴及育幼及生技訓練等教育事業。有些工作是延續戰前孫雅各的宣教活動而展開,例如入山探訪原住民部落;有些是本地牧師碰上困境前來尋求支援,例如樂生的事;有些則是來臺訪問的外籍人士告知,例如臺南北門烏腳病患的苦情。孫雅各是臺灣神學院的院長,而孫氏夫婦是戰前最後一批撤走,戰後最早返臺的宣教士,他們在本地教會中的聲望和長期的人際網絡,都使他們成為求援的對象,而孫理蓮的宣教事工,也從起初的搭配服事走向獨立作業。